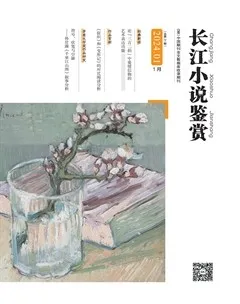先鋒小說的空白藝術
谷巖
[摘? 要] 在文學作品中,運用空白技法逐漸成為寫作者的一種自覺意識和藝術追求。20世紀80年代,以格非為代表的先鋒作家以先鋒實驗者的姿態登上中國文壇,向傳統小說的創作技法發起挑戰,突破了傳統小說的寫作結構。他們在小說創作中自覺運用空白藝術,在敘事結構、人物塑造、結局設計以及主題意蘊上有意制造空白,特別重視讀者對文本意義的闡發和再創造。空白藝術的運用,不僅意味著文本的結構自由度增加,也意味著文本內容的開放和自由度增加,使作品呈現出巨大的藝術魅力,最終以“不寫”達到了“隱而欲顯”的美學效果,也使文本抵達了一種悠遠遼闊的審美意境。
[關鍵詞] 小說? ?空白? ?敘事? ?格非
[中圖分類號] I207.4?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1-0107-04
一、空白藝術與小說
空白也稱留白,是中國傳統繪畫藝術中的一種創作構思,也是一種創作技法。中國的水墨畫追求的是布局的虛實相生、意境的開闊悠遠,它所表現的形式美與意境的深厚往往要通過留白這一技巧來實現。總之,空白是構成中國畫形式美及意境延續方面的重要內容,關系著畫作的結構安排、審美趣味、主題意蘊等。在畫作中有意識地留出空白,在有限的空間中表現無限,成為畫家的一種藝術共識。
事實上,不僅在繪畫領域,在文學作品中,運用空白這種技巧也成為寫作者的一種自覺追求。汪曾祺認為:“一個小說家,不應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訴讀者,只能告訴讀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讓讀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補充,去完成。”徐則臣則認為小說“有些留白是因為必須‘詳略得當”,有些則是因為對小說的內在認知,特別是“對于一個短篇小說來說,故事的確切結局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蘊的結局”,因此對故事要“保持必要的沉默”。這些都是作家對小說創作中空白藝術運用的經驗積累。空白的出現給讀者提供豐富的想象空間,讓讀者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參與作品意義的闡發和再創造。在西方文藝理論中,空白是與讀者接受聯系在一起的。德國接受美學的創始人之一沃爾夫岡·伊瑟爾最先在文學的接受理論中提出了空白這一概念,并且在他的代表作《文本的召喚結構》一文中明確使用了空白一詞。空白指文本中未實寫出來的或未明確寫出來的部分,它們是文本中已經實寫出的部分向讀者所暗示或提示的東西。何艷艷在《論小說的空白藝術》一文中認為,在傳統的小說創作上,“小說的空白大致包括小說題目、人名的空白(與確定的姓名相對而言)、人物塑造方面的空白、故事敘述方式的空白、環境描寫的空白以及由此產生的綜合審美意象的空白”[1]。簡而言之,小說的“空白”是有意地省略、設置空缺,蘊涵著豐厚的審美潛能和藝術張力。
從根本上講,小說是一種敘述的藝術。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小說本身的固有局限導致了它不可能完整地敘述所有內容,其必須對內容進行有目的的取舍。中國古典小說創作重心在于故事內容的編織,故事講述方式則是受到忽略的。20世紀80年代,一批先鋒作家致力于小說文體形式的革新,他們關注的焦點不是講了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講述故事。換言之,先鋒作家關注的是小說的敘述方式或敘述策略,而不是敘述內容。格非在與張學昕的訪談中曾提及,在20世紀80年代,他們關注的不是寫什么而是怎么寫。
20世紀80年代,以馬原、蘇童、格非、余華等為代表的寫作者不再僅僅只關注故事內核的創作,他們把故事內核虛化、淡化、弱化和隱藏,將興趣轉向了文本形式。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他們以先鋒實驗者的姿態登上中國文壇,向傳統小說的寫作成規發起挑戰,突破了傳統小說的寫作結構。先鋒作家在小說創作中,表現出明顯的空白意識,他們自覺運用空白藝術,使作品呈現出巨大的魅力,增強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可讀性。所謂當代先鋒小說的空白意識,是指他們在敘事形態上的變化,這種變化讓敘事的表現力拓展到說與不說之間、表現與非表現(或不表現)之間[2]。在敘述上設置空白成為他們講述故事的一種敘述策略。中國古典小說向來講究結構的整齊嚴謹、布局勻稱和諧,而中國先鋒派作家則顯示出對傳統的“高超越姿態”,格非就是其中的突出人物。
二、格非小說的敘事策略:“空缺”
格非是一位從實踐到理論對小說敘事問題有深入思考和探索的中國作家。他認為,“敘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或者是一個修辭的問題,它當中反映了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個變革”[3]。這充分說明20世紀80年代的創作是在特定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展開的,寫作形式和個人經驗受到時代環境的制約,也就有了現實針對性。
格非在《收獲》上發表的《迷舟》(1987年第6期)和《青黃》(1988年第6期)以及在《鐘山》發表的《褐色鳥群》(1988年第2期)被認為是其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也是先鋒派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代表作。格非作品中設置了大量的“空缺”,造成故事的懸念和真相的迷失或真相的不可確認,成為先鋒文學引人注目的現象。格非的大部分小說類似于偵探推理小說,以探究真相為敘述動機,故事撲朔迷離,情節破碎。讀者讀小說的過程其實就是探尋真相的過程,由于敘事空缺造成了敘述的不可靠,往往使讀者陷入敘述迷宮,不能自拔。從某種程度上講,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執著追求的真相被作者巧妙地隱藏了。
陳曉明在《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一書中對敘述的“空缺”做出過專章論述,肯定了格非小說使用的敘事策略——“空缺”的意義。他寫道:“格非小說中的‘空缺不僅表現了先鋒小說對傳統小說的巧妙而有力的損毀,而且可以從中透視到當代小說對生活現實的隱喻式的理解。”[4]
1.《迷舟》的真相與敘事空缺
格非的早期代表作《迷舟》敘述了一個由戰爭和情愛兩條平行線索構成的歷史故事。這個歷史故事由引子和主人公蕭在七天內所發生和回憶的事情構成,圍繞著人物蕭展開,由他的失蹤始,由他的死亡結局終。戰爭和情愛兩條線索在蕭下落不明的第六天交織在一起。那么,第六天就成為故事發生的關鍵,但是蕭之前去往榆關的情節是破碎的、不完整的。在這個時間里,蕭的行動是模糊的,情節的空缺造成了敘述的不可靠。讀者閱讀文本是為了知道蕭的行蹤,但故事的結局并沒有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為什么這樣說呢?最后小說結尾處雖然給出了蕭的下落——被警衛員連開六槍打死了,但讀者卻陷入了另一個困惑:蕭被打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警衛員的理由是蕭去榆關是和他的北伐軍哥哥會面,以通敵罪將他處決了。可文本中蕭去榆關的行蹤是空白的,第六天晚上到第七天凌晨這段時間,蕭的具體蹤跡也是缺失的。文本中并沒有明確的信息表明蕭去榆關究竟是去看望杏還是去和他哥哥見面,或者二者兼有。在杏的丈夫三順看來,蕭去榆關當然是為了看望杏,因為他從杏的行為態度中判斷出蕭對杏很迷戀。而警衛員卻認定蕭去榆關是向他的哥哥傳送情報。由此來看,蕭去榆關的目的和蹤跡是有多重可能的。警衛員在沒有明確掌握蕭“通敵”的證據下就武斷地把他殺死了,這使蕭的死亡原因更加神秘而模糊。格非在最關鍵的部分留下“空缺”,蕭去榆關的重要情節缺失,警衛員以自身的假定填充了蕭去榆關的空白,自認為判斷是正確的,把蕭打死也使講述的故事變得“完整”。然而,警衛員的判斷是不可靠的,他的武斷行為使這個空缺永遠無法被填上。結果是故事的真相——蕭的死亡原因永遠無法被揭示。
陳曉明對《迷舟》的敘事“空缺”是這樣解釋的:“故事本源性的缺乏不過是生活本源性缺乏的隱喻方式,不管是蕭用情愛來填補戰爭反倒造成生活的空缺,還是警衛員用六發子彈填補故事的空缺,都使生活的歷史起源和故事的歷史生成變得更加不完整。”[5]
2.《人面桃花》中的敘事空缺
2004年《人面桃花》出版即好評如潮,宗仁發認為“這是當代作家逼近經典的有效標志”,謝有順認為《人面桃花》是喚醒他對文學熱望的一部優秀作品。《人面桃花》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它典雅純粹的語言。從某種程度上講,小說創作的過程也是語言使用的過程。《人面桃花》具有如此的豐富性和吸引力,除了語言運用技巧外,敘事技巧也十分純熟。《人面桃花》是格非沉寂了十年之后寫就的一部力作,“骨子里的先鋒趣味依然絲絲縷縷地從里面滲透出來”,這意味著格非寫作和敘事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江南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為背景,通過敘事空白建構起近代革命與烏托邦(桃源理想)的歷史想象。小說以主人公陸秀米的生活經歷為線索,講述了她在革命者張季元、韓六等人的影響下逐漸成長為革命者的故事。陸秀米對革命的認識是與她對張季元懵懂的愛情聯系在一起的,她對革命和社會現實沒有清楚的理解,加上自己的精神寄托是烏托邦式的,注定了她的革命行動和革命之路是失敗的。文本在眾多關鍵的情節設置上留有許多空白,故事結構的完整性因此遭到破壞,如小說開篇敘述陸秀米因看到發瘋多年的父親陸侃下閣樓而驚恐不已,接著父親離家出走了。文本中陸侃因何發瘋,眾人似乎有意回避了這一問題,一幅據說是出自韓愈手筆的《桃源圖》使父親陸侃的發瘋更具神秘色彩。父親離家后的下落也是空白的,成為一個誰也解不開的謎。張季元與母親蕓兒的相識是他進入陸府閣樓的前提,但他們二人是如何認識的,這一情節也是空缺的。秀米是在張季元死后遺留的日記本中才得知了他的革命者身份,以及與母親的關系。花家舍的人和事也都有神秘色彩,尤其是尼姑韓六。在花家舍,韓六對秀米的成長起了重要的引導作用。文本對韓六的身份是有意遮蔽的,她從何而來,最終去向何處?她一個普通的尼姑怎么會有金蟬,是否暗示她也是一個隱秘的革命者?陸秀米從花家舍逃亡到日本,在日本完成了思想轉變。當秀米再次出現在普濟時,她已經有了新的身份:女校長。這意味著秀米由少女成長為革命者,由被啟蒙的對象轉變為啟蒙者,她的身份實現了重大轉變。文本中對秀米在日本是如何接受的系統教育改造卻只字未提,這一關鍵性的轉變階段在文本敘述中是缺失的,這給讀者創造了豐富的想象空間。《人面桃花》有意地使用了空白這一敘事技巧,不僅給予讀者巨大的闡釋空間,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填充缺失的空白,而且還以“不寫”達到了“隱而欲顯”的美學效果,使這部作品更具魅力。
總而言之,空白對格非而言,既是一種自覺的寫作意圖,也是一種小說技巧上的敘事策略。格非故事中的“空缺”是其小說先鋒性的體現,不僅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也為作品闡釋帶來了更大的生成空間。在敘述中巧妙設置“空缺”而形成敘述迷宮,這最終成為格非獨特的寫作風格。
三、結語
小說中的空白藝術可以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想象空間,使作品的內在意蘊獲得無限的闡釋性。任何一部優秀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會有空白。空白技法在小說中的使用,不僅意味著文本的結構自由度增加,也意味著文本內容的開放和自由度增加。魏家俊在《汪曾祺的小說世界剖析》中寫道:“小說結構自由度的增加,也使作家有可能從編織故事的精神桎梏中解脫出來,從而致力于小說文體的追求。”[6]文本內容的開放和自由度的增加是與讀者能否在閱讀接受中填充尚未言明的空白相關的。總之,“敘事上的空白不僅是對讀者接受想象的尊重和鼓勵,而且也是對于敘述者局限性的肯定。小說空白的增加無疑擴大了小說的能指隱喻功能,使接受系統富有張力和彈性”[7]。格非的空缺敘事策略是先鋒作家具有空白意識的例證,表現出先鋒作家創作的自由性和其創作文本的開放性。
參考文獻
[1] 何艷艷.論小說的空白藝術[D].呼和浩特:內蒙古師范大學,2009.
[2] 程德培.當代小說中的“空白”意識[J].文藝評論,1986(3).
[3] 張學昕,格非.文學敘事是對生命和存在的超越[J].當代作家評論,2009(5).
[4] 陳曉明.眾妙之門: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5] 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6] 魏家駿.汪曾祺的小說世界剖析[J].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3).
[7] 季進,吳義勤.文體:實驗與操作——蘇童小說論之一[J].當代作家評論,1990(1).
[8] 李徽昭.繪畫留白的現代小說轉化及其意義[J].文藝理論研究,2018(4).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