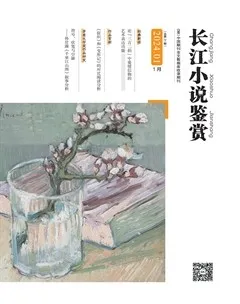解構主義視域下對《河童》的荒誕性探析
劉思雨
[摘? 要] 《河童》是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代表作之一,小說講述了主人公誤入河童國的奇幻經歷,并通過河童荒誕的生活方式諷刺日本社會現實。本文以藝術手法、角色形象、故事內容為基點,通過解構主義的視角分析小說的荒誕情節以及小說對傳統的顛覆,小說以充滿奇幻色彩的河童國為背景,直指社會的黑暗,借河童之間的社會關系與矛盾對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雙重諷刺,批判社會與人性的扭曲,表現主人公在畸形的生活環境下的痛苦與絕望。
[關鍵詞] 《河童》? 芥川龍之介? 解構主義? 荒誕性
[中圖分類號] I1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1-0044-04
解構主義源于對結構主義的重新解釋與改造,旨在消解傳統的二元對立思想。德里達重新解讀了能指與所指的關系,他認為能指并不能確定地指向一個所指,能指的指向不斷延續,意義不斷向外撒播,落向四面八方沒有中心,并提出“延異”這一概念指涉事物之間因差異產生的意義,表示語言意義的不在場。二元對立的哲學思想最早能追溯到《理想國》,柏拉圖在構建理想國中的主體人物時將理智、意志與情欲劃分等級,贊揚理性,貶低情欲,這種二元對立的思想直至德里達提出解構主義才得以消解,對傳統觀念的服從也得以破壞。在此基礎上,福柯的權力觀對理性與瘋癲進行深刻的剖析,解構了社會權力話語,揭示了社會剝削的本質和人在社會中受制的現狀,將視角轉向對自身的關注。
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河童》講述主人公從現實世界誤入河童國的奇幻經歷,在見證了河童社會的荒誕后感到痛苦,選擇離開河童國返回人類世界,而現實世界的黑暗遠超河童國,主人公被關進精神病院陷入瘋狂,在痛苦中喪失對生命意義的探尋。解構主義對終極意義的否定、去中心化與福柯的權力觀為《河童》提供了解讀思路,主人公在河童國的虛幻經歷,以及回到現實世界后被關進精神病院的荒誕情節,還有他的瘋狂行為、瘋言瘋語,都在一步步消解小說的中心思想,使得小說看似荒誕無意義,卻又暗含諸多深意,抨擊了社會荒誕與黑暗。
一、敘事的荒誕:藝術手法的解構
芥川龍之介在《河童》中建構了兩個世界,并且夢幻世界與現實世界這兩個場域不再是理想與現實、美好與丑惡的對立關系,而是一個比一個更加丑惡畸形。作者打破了兩個世界的對立性,也打破了讀者的思維慣性,創造出空間上的陌生化快感。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主人公作為審視河童國制度與文化的外來者,旁觀視角更能幫助其深入地看清世界,河童國的荒誕喚醒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幫助他意識到社會規則并不是真理一般不容置疑的存在,現實社會中很多習以為常的規矩都是扭曲的、反人性的。
1.敘事空間的消解
空間作為承載敘事功能的工具不僅展示了小說的社會環境,還提供了人物的活動空間,能夠最直觀地呈現人物與環境的關系。芥川龍之介在《河童》中創造了虛擬的河童國,構建了兩個空間供主人公體驗,但不同于傳統對理想國度烏托邦式的想象性描述,作者消解了現實與幻境的二元對立關系,幻想國度不再被描繪成桃花源般的世界。虛幻的河童國世界因其充滿想象性、神秘性等特點與現實世界區分開來,但在表露虛偽、壓迫與痛苦上卻與現實世界是共通的。
社會空間是人際交往活動的延伸,是社會各種階級與權力交織出的一張蛛網,福柯“把空間看作種種關系和權力角逐和斗爭的場所”[1]。文本借河童國的社會空間展示社會各階級關系的矛盾,在被河童抬著緩慢前進的路上,主人公觀察了河童世界的街道和店鋪,看起來與現實中的“銀座大街”并無區別,河童的家整潔舒適,與現實社會也十分相似。生活空間的相似性是引導主人公快速適應新環境,認識到河童社會與人類社會并無太大差別的催化劑,幫助主人公看到河童社會的混亂與扭曲后能夠聯系起現實社會,如河童社會中,資本家河童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為了火災保釋金縱火,肆意解雇職工河童送去屠宰場,在“職工屠殺法”的操控下,被解雇的職員被屠宰食用也不會反抗。河童社會的吃人與腐敗現象看似荒誕,卻是現實社會的縮影。
2.“瘋癲”的敘述視角
小說以主人公“我”為第一人稱敘述視角展開,而作為主要人物的“我”卻沒有姓名,唯一涉及對主人公身份的介紹僅是某精神病院的第23號病員。文本內聚焦的敘述視角雖局限了對現實和河童國世界更深入的認識,卻在洞悉主人公的精神狀態上更勝一籌。主人公回到人類世界后被關進精神病院,成為具有社會意義的瘋子,根本原因正是社會壓迫對人的異化。
瘋癲“是一種荒誕的社會騷動,是理性的流動”[2]。瘋癲形象是社會權力對非理性主體的定義與打壓,而理性是統治階級制定的武器,主人公以瘋癲形象敘述回憶河童國是觸怒了統治階級的觀念而被定性的表現,事實上,這些瘋言瘋語不過是主人公經歷河童國與現實世界雙重絕望體驗后的憤怒與痛苦,社會的規訓又逼迫他只能用極端的方式發泄情緒,主人公不僅是在辱罵河童國里殘暴自私的河童,同樣也是在唾棄丑惡的人性,看似如夢境般神秘的理想國度居住著的生物與現實并無兩樣,主人公通過絕望的嘶吼進行無差別抨擊,抒發他對河童國美好夢境破滅的失望,對現實與夢幻世界同樣灰暗的憤怒。
當主人公身為人類在河童國游歷時,體型和思想都與河童大相徑庭,他回到人類社會后,又因為不適應人類社會的生活而顯得格格不入。此時他滿口河童語,與社會脫節,成為異類被警察關進精神病院。這一情節體現出冷漠的社會規則如機械般運作,企圖抹殺他個性的一面,為他的“大腦”治病,將他恢復成融入集體的“正常人”,“受到操控的集體統一性就在于對每個個體的否定,因為個性正是對那種把所有個體同歸于單一集體的社會的嘲諷”[3]。主人公借理想國度逃避現實,但發現理想世界仍是荒誕的,逃離河童國后又看到人類世界的黑暗遠超河童國,他的孤獨與瘋狂是對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雙重諷刺。
二、角色異化的荒誕:形象的解構
河童的妖怪形象在小說中被保留了外形及動物的獸性特征,又賦予其人際關系和社會習性,對河童形象的顛覆與再創造更直觀地體現出社會異化導致的社會群體畸形。理性社會下工業機器無情地碾壓人性,人類也被機械同化,主人公在回到現實世界后變成精神病人是由于社會異化對他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極大傷害,他的瘋狂是理性喪失的表現,是社會過度擠壓的結果,主人公通過無厘頭的語言以精神病人的口吻控訴現實社會帶來的痛苦。
1.河童形象的顛覆
河童是日本神話傳說中著名的妖怪之一,文獻中記載河童腦袋上有短毛,手腳上有蹼,多出現在以九州為中心的西日本地區的河川中,并且會將人拖入水中致其溺亡,河童的傳說在古代引起人的強烈恐慌。隨著古代中國龜長壽、驅邪的觀念傳入日本,18至19世紀河童的形象在文獻記載中發生變化,外形開始向龜形轉變,河童謝罪、報恩的故事也隨之流傳起來[4],河童逐漸演變為福壽安康的象征,受到日本人民的崇拜。
《河童》中的河童形象有別于傳說中的妖怪形象,作者雖保留了河童的體格外觀,將其描述成丑陋的變色動物,卻賦予河童人類的思想與生活習慣,人與動物相互滲透的方式體現出河童形象異化的特點,將神秘的妖怪轉化成具有社會性的群居生物,參與社會勞動分工。河童作為人類的一面鏡子,照出人的虛偽和社會的灰暗,借動物原始自然的獸性特征揭開現實社會的“遮羞布”,諷刺人類世界。
河童比起人類更加直率,不以滿口正義道德偽飾內心真實想法,但這并不是因為河童比人類道德更加高尚,只是作者借河童的動物性特征更直觀地展示社會現象。在主人公與資本家河童蓋路的對話中,蓋路講述河童國每個月會解雇不下四五萬只的河童工人,而這些沒有利用價值的工人在失業后只能被屠宰,做成肉制品被吃掉,不同于魯迅筆下的狂人因感到自己馬上被吃而暴躁、發狂,也不同于魯迅企圖用狂人爆發的情緒點燃讀者的緊迫感,從而喚醒愚昧的國民,芥川龍之介的狂人則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見證河童之間蠶食同類,在幻想與現實同樣骯臟的情況下,狂人難以置信和恐懼的情緒帶給讀者更深的失望和絕望。《狂人日記》中的吃人隱藏在仁義道德的面具之下,而《河童》中的吃人卻能夠成為飯桌上的談資,更襯托人的虛偽。
2.人與動物關系的消解
描寫動物的文學作品中常有借助動物意象指涉人的道德品質的意圖,如借虎豹豺狼代表危害社會的壞人等。芥川龍之介的小說也常通過刻畫動物形象來深化故事內涵。芥川龍之介在《河童》中將動物作為小說描寫的主體,借助動物的行為直指社會的痛點,人與動物的社會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河童主導的世界,人類只是外來者,如“動物”一般被觀賞。主人公對河童的凝視是以一個闖入河童國的外來者身份,審視河童社會與現實社會的奇特之處,而河童對河童的凝視則更能體現出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糾紛。河童與河童之間的關系占據小說的主要部分,動物之間的關系取代了人的主體關系,人則居于旁觀者的地位,不影響、不參與河童的任何行為,只在體驗河童社會后表現出情緒上的喜愛或厭惡。
《河童》中,主人公與河童的關系比他與人類的關系更親密,體現在主人公離開河童國后將河童國視為故鄉,特地強調他“想回去”而不是“想去”河童國,以及被關進精神病院時只有河童經常去看他。精神病人滿口異世界的言論在正常人看來是他發瘋犯病的表現,肯定河童存在的言論更加深了他在旁人眼中的瘋狂形象,而對主人公來說,這是內心的空洞與孤獨在封閉的精神病院中被放大的表現,小說中沒有提及主人公的任何親人朋友對他的關心,只有河童的看望與關照減輕了他的孤獨感,人類喪失了同理心,人類社會失去了歸屬感。動物不加偽飾自然流露出的情感襯托出人類社會的情感危機。
三、生存困境的荒誕:寓言式主題的解構
寓言故事多以動物為主要角色,通過賦予動物人類的思維與行為講述蘊含哲理的小故事,借動物之間的關系影射現實社會,揭露社會矛盾。《河童》同樣是圍繞書寫動物的生活狀況與社會現象批判現實社會的寓言形式,但不同于傳統寓言故事號召讀者學習故事哲理,團結起來反抗壓迫,《河童》只描繪生活在社會中的痛苦,不提及對社會的改變。小說還以狂人為視角展開敘述,狂人象征理性的喪失,他的瘋狂幫助他顛覆社會制度至高無上這一真理,從而認識到社會是罪惡而扭曲的吃人機器。
1.反啟蒙的荒誕情節
啟蒙是一個用知識代替幻想的過程,古代人民用神話啟蒙取代對自然的恐懼,又通過對世界的不斷認識與改造獲得的知識啟蒙取代對宗教神話的迷信。河童國是主人公在現實社會因情感崩塌探索出路的過程中創造出的神話世界,是如避難所一般的逃避現實的空間。但避難所中的生活并非如幻想般美好,主人公認識了象征執法者的警察河童和象征資本家的玻璃公司老板河童蓋路,看到象征統治階層的政治家河童用謊言操縱大眾,從政治、法律、宗教、戰爭、人性等各個方面展現了河童國同樣存在階級剝削與壓迫,資本家以利己主義為導向,吃人作惡卻不以為然,神話中的社會暗示了現代工業發展下人類心靈和主體地位的喪失。
在河童國,嬰兒河童可以選擇自己是否愿意出生到這個世界,嬰兒河童拒絕出生并回答:“我相信河童的存在是罪惡的。”[3]嬰兒未出生時便會說話和做選擇本就荒誕,回答的內容更是直接揭露了河童國的虛偽。面對是否愿意來到這個虛偽丑陋的世界,神話世界給了嬰兒選擇出生的權利,就像也給了主人公進入另一個新世界的機會,而主人公到了河童國依舊無法逃脫烏煙瘴氣的社會氛圍以及社會對人性的摧殘,社會給他的選擇只是痛苦或者更痛苦。除此之外,河童國政府還親自出面用毒氣“解決”被解雇的河童職員,甚至頒布“職工屠殺法”使吃河童肉合法化。面對主人公的驚訝與質疑,資本家河童回答,工人階級的女兒在主人公所處的人類社會當妓女,言外之意指現實世界中下等階層人民的女兒被迫做妓女與河童世界對職工的屠宰并無分別,河童國的荒誕就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折射出社會中的壓迫與不公,以及被社會洗腦的人類面對生存困境的麻木。
2.邊緣人物生命意義的消亡
隨著主人公對河童國的深入探索,這個看似比人類社會的工業更加先進,思想更加開明的“理想國度”仍然存在著階級剝削、殘害生命等丑惡現象,主人公帶著崩塌的理想回到現實世界,卻發現現實世界中制度的剝削、人性的冷漠比令他失望的河童國更加荒誕和丑陋。作者對理想社會的追求諷刺了現實,又用河童國的經歷打破了前期美好的追求,在一次次失望中,主人公沒有了逃避的退路,也失去了前進的方向,最后的希望被打破,對殘酷現實徹底失望,對河童國的態度由厭煩轉為懷念也是一種無奈的妥協。
主人公在河童國感到失望,回到現實又被當作精神病關進醫院,最終他認識到現實社會遠比河童國黑暗,消解了幻想與現實的對立,他腦海中的幻想世界不再是純潔美好的,現實比荒誕的河童國更讓人無法理解,希望的燭火在幻想與現實的雙重打擊下逐漸熄滅,“人已被撕成了碎片,變成了喪失中心地位的、失去了自我的存在,變成了沒有確定意義和歷史延續的表面化了的虛無”[5]。文本借助主人公在河童國與現實穿梭的奇幻經歷控訴人生在失望與絕望下變得毫無意義,對人生意義的探索已經走到盡頭,面對黑暗的現實更無力改變,只能深陷悲觀和虛無之中走向死亡。
四、結語
芥川龍之介通過主人公在河童國的游歷展現河童之間的人際關系與社會現象,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藝、愛情等諸多方面的丑惡現實,繼而對現實社會產生懷疑。河童國是現實社會權力斗爭的縮影,斗爭以底層人民的犧牲為結局,借此諷刺現實中的階級剝削、利己主義等,控訴社會的黑暗、畸形、扭曲和人性的冷漠、自私、滑稽,發泄對日本現實社會的極度憤懣。《河童》是芥川龍之介在自殺前發表的作品,小說中,主人公找不到自己的歸宿與生活的希望陷入迷惘,又被關在精神病院變得癲狂、易怒,主人公不幸的經歷與心路歷程也是芥川龍之介內心苦悶的象征,其借助作品發泄出對人生的絕望。
參考文獻
[1] 蔡曉惠.空間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空間轉向[J].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
[2] 張之滄.走出瘋癲話語——論福柯的“瘋癲與文明”[J].湖南社會科學,2004(6).
[3]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李江龍.日本近世河童形象變化原因初探[J].戲劇之家,2018(8).
[5] 韓雅麗.詹姆遜的后現代主義理論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
[6] 莢婕.從小說《河童》看芥川龍之介的創作思想[J].黑河學院學報,2020(7).
[7] 芥川龍之介.河童[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8] 曹若男.莎士比亞戲劇人物關系的“延異”問題[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
[9] 黃丹.芥川龍之介作品中動物形象研究[D].南昌:南昌大學,2015.
[10] 袁意.世界主義潮流下的自我書寫與價值解體——芥川龍之介《河童》寓言形式探究[J].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
(特約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