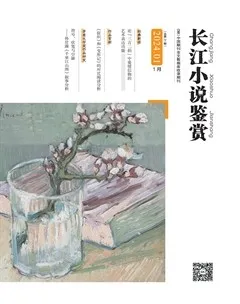《丑聞筆記》中自我危機的拉康式解讀
王瑞林
[摘? 要] 《丑聞筆記》是英國作家卓伊·海勒的小說。國外學者從異常和瘋癲、后現(xiàn)代主義癥候、媒體倫理角度對小說的丑聞事件展開分析。本文則通過分析自我的困境,并運用拉康的三界理論來展示自我如何在想象界和象征界受到束縛,探索小說女主人公陷入的自我危機和建構(gòu)自我合法性的嘗試,以此來揭示異化和規(guī)訓的自我在當代英國社會的困境。
[關鍵詞] 《丑聞筆記》? 拉康? 身份危機? 布克文學獎
[中圖分類號] I106?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1-0077-04
一、引言
卓伊·海勒是英國記者和小說家,著有《你知道的一切》(Everything You Know,1999)、《丑聞筆記》(Notes on a Scandal,2003)和《信徒》(The Believers,2008)三部小說,第二部作品《丑聞筆記》入圍2003年布克獎短名單。
《丑聞筆記》的敘述者是60歲的高中女教師芭芭拉·科維特(Barbara Covett)。芭芭拉以日記的形式,講述了一位42歲新入職的藝術(shù)教師希巴·哈特(Sheba Hart)和她15歲的未成年學生史蒂文·康納利(Steven Connolly)的“丑聞性”戀情。芭芭拉出于嫉妒,在另一位學校老師巴斯(Bath)面前暗示了這段肆無忌憚的秘密戀情。之后巴斯向校長報告了這件事,并以工作威脅芭芭拉,迫使芭芭拉指認希巴的罪行。最終希巴發(fā)現(xiàn)了芭芭拉的日記,了解了芭芭拉對她的背叛,同時遭受史蒂文對她的離棄。芭芭拉和希巴兩人住在租借的房子中深陷窘境,她們沒有收入,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布克獎評委評價《丑聞筆記》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心理劇”。
小說的自我危機和建構(gòu)超越了日記敘述形式的私人領域,探索社會文化對自我的規(guī)訓。不難看出,戲劇化的情節(jié)(師生戀丑聞和窺視欲)、非常規(guī)/邊緣的人物設定(年邁單身女同性戀與出軌學生的已婚婦女)、觸碰道德和法律的情節(jié)發(fā)展與開放式結(jié)局都足夠吸引眼球。作家海勒的記者身份為她提供了組織小說情節(jié)的素材,同時也讓她以小說的形式對其身處的媒體行業(yè)提出質(zhì)疑。在小說當中,媒體對丑聞的大肆報道侵占了兩位主人公的隱私權(quán)和生活,將她們逼上絕路。因此,該小說對媒體行業(yè)的反思和對社會邊緣群體的關注,以及對“愛與欲”“道德與法律”界限的再次探索,都使得小說成為管窺后現(xiàn)代社會的窗口。自我的危機和建構(gòu)與英國社會的文化規(guī)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小說從日記的私人空間出發(fā),反映了這一主題,本文探索小說兩位女主人公陷入的自我危機和建構(gòu)自我合法性的嘗試,以此來揭示異化和規(guī)訓的自我與當代英國社會之間的聯(lián)系。
二、拉康的自我與自我危機
在拉康看來,每個主體都缺乏自主性。換言之,主體對自己的認知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他者的形象來塑造對自己的認知。因此,主體生來就是殘缺的,對自身的認知從一開始就是被異化的。學者丁禮明認為,自我“為了獲得周圍環(huán)境的認同不得不選擇自我的異化,把自我異化在他者的世界里,找尋迷失的主體,在自我和他者之間選擇與掙扎,最后的結(jié)果是徹底的異化,把自己也變成陌生的他者”[1]。拉康提出的“鏡像階段”清楚地闡明了這一點:在最初的幾個月里,嬰兒將自身和環(huán)境作為一個隨機的、破碎的、無形式的群體來體驗;之后6到18個月之間的某段時間經(jīng)歷鏡子階段,嬰兒會在一面真實的鏡子中看到自己的鏡像,這個鏡像和嬰兒形成對比,即身體的形式和嬰兒形成對稱圖像,但鏡中形象是顛倒的,它和嬰兒大小一樣,和嬰兒自身形成連接。但是在拉康看來,這已經(jīng)預示了自我異化的結(jié)局,因為鏡像和自我本就不同[2]。嬰兒也會根據(jù)母親的表情、肢體動作等反應獲取對自身的認知,重要的是,嬰兒在這個階段形成了一種整體的自我意識。然而,這個自我是異化的,因為這個自我來自鏡像,來自他人或者他者。自我的感知因此不直接來自自我,而是來自自我看向他者時,由他者反映的自我。這也構(gòu)成了自我的扭曲感知,以及對自我的錯誤認識。
《丑聞筆記》則充斥著對自我的錯認和自我的異化,這種異化的自我來源于把他者的形象和需求當作認知自我的基準。小說在形式上采取第一人稱的不可靠敘述者,加強了自我認知的偏差與敘述的疑點。而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所講述的內(nèi)容更突出了敘述者對自我、對他者認知的癥候。芭芭拉認為自己是希巴在丑聞被披露后唯一值得信任的人,這是她對自我的錯認。她錯把希巴在丑聞被揭露后的無力和無助的反應,把希巴對康納利戀情的反復演說,當作希巴對自己的依賴和袒露,也就是再一次把他者的反應當作自我的落腳點。在丑聞被揭露前,希巴從未主動向芭芭拉傾訴過她與康納利的戀情。在小說結(jié)尾,希巴發(fā)現(xiàn)芭芭拉也參與到丑聞泄露而勃然大怒,這些都證明芭芭拉對自我的錯認。芭芭拉在小說開篇反復說道,“我們之間沒有秘密,希巴和我”“我膽大妄為,自認為是最有資格寫這則小故事的人。我敢說,我是唯一的人選”“希巴沒有別人可以傾訴這些事情”[3]。然而,在丑聞被揭發(fā)后,希巴和芭芭拉的對話始終圍繞著康納利,而與芭芭拉無關:“跟康納利的那段戀情,沒哪件事希巴不會說上好幾回的。”“這個話題她似乎百談不厭。”[3]也就是說,即使希巴對她的訴說與她無關,芭芭拉仍然把對自我的認知投射在希巴身上,沒有希巴在她面前對康納利戀情的反復回顧和講述,她便沒法確認自己是希巴唯一可以傾訴的人,即使這種對自我的認知不建立于自我,而建立在自我的他者身上,也就是看到希巴對自己講述而存在的自我,因此芭芭拉對自我的錯認也就能夠解釋了。
芭芭拉無法抵達的欲望也是異化的自我的一種體現(xiàn),自我危機與欲望緊密聯(lián)系。在拉康的定義中,嬰兒與母體同一,沒有任何區(qū)別,只存在最基本的需要(need),這種生存需要能夠隨時被滿足的狀態(tài)被稱之為“實在界”(the Real)[4]。芭芭拉錯認的自我在保守的英國社會中進一步被異化,如果想要達到實在界母子一體的關系,就必須舍棄想象界錯認的自我,而錯認的自我不是真正的自我,而是自我的他者,一旦形成錯認的自我便不可能消除,不然就意味著自我的徹底抹除。因此,自我與一個異化的自我/自我的他者之間的隔閡促使了重返一體的欲望,但是重返的欲望永遠不可滿足。在小說最后一章中,芭芭拉和希巴爆發(fā)的沖突以希巴的絕望和無力結(jié)束。芭芭拉日記的最后一句,“到現(xiàn)在,她已經(jīng)了解,不要離我太遠”[3],看似是芭芭拉對希巴的占有,但這句話的中心仍然是關于芭芭拉自己,而非希巴。這其實生動地展示了芭芭拉想要不斷接近一個錯認的自我,一個看到希巴對自身回應而產(chǎn)生的自我,也是如前文提到的希巴和芭芭拉之間是沒有秘密的一體存在。但這種重返一體的欲望是不可滿足的,自我的危機也就不能夠被解決。
自我的危機更是主體在象征界經(jīng)受規(guī)訓和壓抑的過程。語言的習得標志著人向象征界的邁進,在象征界中,“主體受到以‘父為名的規(guī)訓,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規(guī)則都可以是規(guī)訓的一部分。‘父親的名或‘父親的法就代表著一種法規(guī)、一種家庭和社會制度”[4]。小說中,媒體對芭芭拉這樣的年邁單身女性的報道是“那位俏麗的老小姐參謀”。芭芭拉對自己的認知同樣是貶低性的,她認為自己“是那種會被美容院理發(fā)小姐竊笑的女人”“是一個老小姐,必須在星期六晚上一個人在房間里哀哀自憐”[3]。由此可見,英國社會對于單身女性的異樣眼光仍然是社會規(guī)訓的一部分,在象征界中自我很難實現(xiàn)自我的滿足。芭芭拉異化的自我和她想要填補匱乏、重返欲望能夠滿足的實在界之間存在著鴻溝。這種鴻溝折磨著她的內(nèi)心,“我一生都在扮演別人向我吐露秘密的那種人,而且一生都對這角色感到受寵若驚。但這種滿足感逐漸被一股疲倦的憤怒所取代。他們告訴我是因為覺得我很安全。認定我是圈外人”[3]。她扮演的角色便是一種異化的自我。象征界的規(guī)訓和戒律成為她自我危機加劇的推手,芭芭拉永遠也無法擺脫扮演的自我。
三、主體自我的拉康式建構(gòu)嘗試
自我危機分析和自我主體建構(gòu)是剖析人物內(nèi)心的另一個重要手段,這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實際上,自我危機和自我建構(gòu)總是同時存在,與拉康的自我建構(gòu)理論相輔相成。在拉康看來,自我從想象界中形成異化的自我。在獲得語言表達的同時,自我被象征界的符號規(guī)訓,進一步迷失自我。個體成長的過程是自我異化的過程,想要尋找一個不是投射到他人身上的異化自我,但這種嘗試始終失敗。主體嘗試與他者回歸實在界的一體,但無法區(qū)分自我和他者,把他者對自我的印證當作自我,則會淪陷在關于自戀的漩渦中。自我的構(gòu)建始終無法超越拉康所塑造的三界框架,但通過對小說中人物自我建構(gòu)嘗試的分析,依然可以管窺自我異化與自我建構(gòu)、自我異化與他者、自我異化與社會的獨特聯(lián)系。
通過文本細讀的策略,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自我的建構(gòu)始終與他者的存在緊密聯(lián)系。首先,小說的日記體敘述形式,提供了一個不可信的敘述者,也是一個不可信的自我。在主人公芭芭拉的日記中,其他人物同樣是以殘缺自我的形式出現(xiàn)的,也就是自我的他者。這些自我的他者都表現(xiàn)了芭芭拉對自我認知來源的一部分。當芭芭拉談到在他人眼中的自我時,“連像我這樣六十出頭,公認漂亮的女人”[3]的話語是對自我的定義。很顯然,這一自我側(cè)寫,可能來源于學生給老師的綽號,也可能來源于同事間的竊竊私語。芭芭拉對自己的年齡感到羞恥,這是異化的自我受到規(guī)訓的表征,也是把自身形象的投射當作自我的癥候。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芭芭拉和希巴(他者)之間體現(xiàn)了一種想要重回實在界,也就是母子一體的無殘缺狀態(tài)的努力。在希巴的丑聞被揭發(fā)后,芭芭拉對希巴就有父式的監(jiān)護人身份,自覺地成為她的監(jiān)護者。她合理化她的越界行為,“我并不喜歡侵犯希巴的隱私,但身為她的非正式監(jiān)護人,有些責任是我不能逃避的”[3]。在象征界中,個體接受象征界的戒律,使自我區(qū)別于他者。區(qū)別的行為成為建立自我的重要手段。因此,監(jiān)護行為本身就具有拉康意義上的雙重性:第一,建立等級關系,創(chuàng)建上級下級,有無權(quán)力的二元對立。第二,試圖規(guī)訓他者,將他者接近自身,達到一體的無殘缺狀態(tài)。小說中,芭芭拉種種窺視和控制行為,彰顯了自我的匱乏,也是拉康意義上欲望的無法滿足狀態(tài)。而在自我與他者的糾纏中,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自我的建構(gòu)總是離不開他者的存在。
自我的建構(gòu)總是痛苦的書寫,而痛苦的根源是他者的不可接近和不可獲得,這種痛苦是自我建構(gòu)不可或缺的部分。自我辯護、創(chuàng)造虛幻自我形象、自我懷疑,這是芭芭拉持續(xù)痛苦和無意義感的根源。作為一個即將退休的未婚女性,芭芭拉經(jīng)歷了身份危機,她對自我價值的認知被無用和孤獨所削弱:“我曾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管道上和教室的椅子上,感覺大量未被使用的、沒有目標的愛像一塊石頭一樣坐在我的肚子里,直到我確信自己會大叫一聲,摔倒在地。”[3]這種異化的自我和無意義感成為建構(gòu)自我的終點,也是失敗的終點。
自我的建構(gòu)是與社會規(guī)訓抗爭的過程。拉康宣稱,進入象征秩序是一種對兩性的“閹割”形式。在拉康的觀點中,閹割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字面上的,它代表了每個人整體性的喪失,以及他或她對社會規(guī)則的接受。社會規(guī)則的強加決定了個人的心態(tài),并繼續(xù)影響或疏遠一個人存在于想象中的整體性。芭芭拉成為“老小姐”話語結(jié)構(gòu)的犧牲品。在一個強調(diào)單身和怪異毫無價值的世界里,她覺得自己的生活毫無意義。然而,“多余女性”的恥辱仍然存在。芭芭拉遭受著未婚剩女和老齡婦女歧視的雙重壓迫。在這個意義上,她不知不覺地認同這種滲透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卻無法鼓起勇氣與之抗爭。
小說中,希巴的自我建構(gòu)更受到雙重束縛,她嘗試僭越社會的規(guī)訓,打破道德的捆綁,尋求實在界的自由。希巴的自我被她身為母親的身份局限,被社會對于母性的期待所束縛。她追求自我的獨立性,卻不得不屈服于她作為母親和妻子的家庭義務。希巴鄙視自己:“我對為家庭犧牲的一切感到憤怒。我有這樣一個想法,如果我沒有遇到理查德,那么年輕就把自己埋葬在婚姻中,我應該可以有一番作為,做出偉大的雕塑,環(huán)游世界,或者其他什么。一天晚上,我甚至對理查德說,他‘扼殺了我的想象力。”[1]和芭芭拉一樣,她對自我的貶低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也不是感情用事,這種自我困境的“好妻子”形象是現(xiàn)代版“家里的天使”的翻版。此外,一旦希巴試圖脫離社會的結(jié)構(gòu)性權(quán)力,她就會被社會和道德法規(guī)進一步驅(qū)逐,意識形態(tài)機器不能容忍任何越軌行為。希巴的自我經(jīng)歷了進一步的限制,她企圖尋求一個完滿的自我,試圖通過越軌行為打破束縛,但仍然難以超越社會的規(guī)訓。
四、結(jié)語
自我的危機和自我的建構(gòu)是本文的關注點。通過拉康的三界理論,本文對芭芭拉自我的危機進行了闡述。丑聞的暴露揭發(fā)了敘述者自我的缺點,也凸顯了芭芭拉的惡意和嫉妒的本質(zhì),她是被規(guī)訓的,她的自我是異化的,社會的話語建構(gòu)糾纏著她的生活和追求自我的權(quán)利。小說還探討了個人生活與整個社會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后現(xiàn)代社會,客觀現(xiàn)實的問題被奪人眼球的新聞報道所取代,希巴和芭芭拉都是不關心真相的世界的受害者,希巴的越軌選擇是媒體和社會無法容忍的,芭芭拉對自我、對愛和欲望的追求在拉康的框架下是注定不可滿足的。最后,本文試圖探討自我危機與影響自我實現(xiàn)的因素之間的關系。人的欲望追求受到社會、家庭、媒介等各種力量的干涉,因而變得復雜。超越拉康的悲觀結(jié)局,建立起主體性,找到自我實現(xiàn)的位置,是每個人都需要回答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丁禮明.《兒子與情人》中保羅的身份危機與“拉康式自我”建構(gòu)[J].外國文學研究,2012(3).
[2] Lacan J.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M]//Richter D.The Critical Tradition: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Bedford:Bedford Books, 2007.
[3] 海勒.丑聞筆記[M].丘淑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4] 汪震.實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解讀拉康關于個人主體發(fā)生的“三維世界”學說[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
(特約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