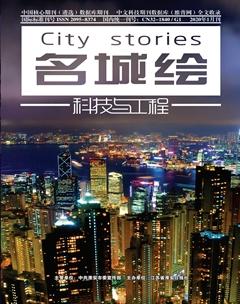廢水水質檢測化驗誤差分析與數據處理
顧威
摘要:在現代,對廢棄污水的檢查誤差監控還有很大難度,因為排放周邊對廢廢棄污水檢測的影響很大,而且部分的項目只可以檢查一次。所以,為了可以降低檢查所產生的誤差,就需要我們在檢測過程中根據控制等不同的方法盡量減少誤差,并對檢查信息進行一系列的分析,以此來保證廢水檢查結果的精準性。
關鍵詞:廢水水質;檢測化驗;誤差分析;數據處理
為了了解水源質量的基本方面,必須及時進行廢水質量測試,以確保有關水質的穩定和可靠性,但在水質測試期間,測試環境、測試工具、測試方法,甚至在進行水質測試時,必須對廢水質量進行測試,檢查人員的專業技術和嚴謹程度這些客觀的原因都會影響到最終結果的科學準確,從而導致在污水質量測試中出現化驗的錯誤,如果不及時加以解決,可能會對測試結果的真實性造成影響,因此,如果在廢水質量測試中會出現這種情況。分析所產生的化驗誤差非常有必要,了解誤差的原因,提高測試結果的科學準確,從廢水質量測試中排除無效化驗,并對檢測方案進行全面提升。
1、廢水水質監測的重要性
目前,由于迅速的城市化發展和經濟的發展所影響,工業和農業生產的廢棄污水排放量較高。當這些廢水進去自然的水域時,其清除能力不足以凈化其中的污染物,從而使水體環境發生退化,其化學和物理特性發生變化,水污染影響到水域的環境,這不僅對生態造成了一些很大的損害,對生態環境的恢復造成了不利影響,但它也嚴重威脅著人類的身體健康,就受污染的水的質量而言,有效管理水質量的根本變化和有效控制水污染的增加,有助于通過對廢水質量和水質進行有效檢查,對有關的環境保護部門能夠更好地保護水資源提供維護生態平衡和環境的保護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信息。
2、水質檢測化驗誤差來源分析
2.1絕對誤差
水資源質量測試中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無論多么精確,都有產生或大或小的誤差的可能。從計算方法的角度看,在測試值和實際值之間存在一個斷層,盡管這一斷層很小,但這是一個絕對的誤差。科學檢查未能獲得適當的設備、容器和操作程序,因此相對誤差是客觀的,雖然相對誤差不能完美的避免,但對試驗結果也沒有很大的影響,這是因為想對誤差是絕對的。通常是恒定的,所有水質數據在被測量出來后都會產生誤差,因此相對誤差作為恒定變量,這可能是控制變量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對每一個測試之間的比較不會產生影響的;另一個原因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相對誤差也正在減少,即使在精確度測量中,誤差也是微不足道的,這是造成誤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2.2廢水水質檢測誤差
在現實生活中,一些測試機構對水質監測不夠重視,因為,水質測試通常是在實驗室進行的,從而降低了某些抽取水樣地點的研究能力,也降低了對收集點的選擇的標準規范。對水樣品的管制不夠,可能會有不合理或不專業的樣品影響到水樣品,廢水質量監測方法很多,目前主要依靠第三方檢測科研機構和環境系統。此外,這一錯誤還可歸因于實驗人員對質量控制缺乏重視,缺乏對水質的控制,以及缺乏對操作的管理。此外,在試驗期間,試驗結果可能受到人體操作的影響。
3、檢測化驗誤差分析與數據處理
3.1間接測量誤差
在廢水檢測過程中,間接檢測是通過公式計算直接測量的數值得出的,所以間接檢測誤差不僅包括直接測量的數據的誤差,而且還包括公式的計算的結果,間接計量與直接計量之間的相關性可能會最終影響到數據的整體性和科學性,在對間接計量誤差進行分析時,如果根據平均計算誤差計算錯誤,則應考慮到所有誤差都是同時發生的,所有誤差都是同時發生的。這兩種方法相互重疊,最不利的結果是,誤差值之間的函數的關系包括啟動等若干交易所產生的相對計量誤差的總和,比如,間接計量值公式只是一個加減乘除的公式。在分析過程中,應當計算出絕對的誤差,然后才計算出相對誤差的分析,因此,分析錯誤是一種更為合理的方法,如果間接計量包括復雜的開方等運算,例如乘積系數,那么在計算絕對錯誤之前,應當對相對誤差進行分析。這樣才能科學合理的分析出結果。
3.2粗大誤差處理
粗大的誤差具體涉及在某些條件下偏離測量值和實際值所造成的錯誤,也被稱為離群的值。所有的誤差產生的原因都因為兩個因素,主觀和客觀。檢查人員的操作失誤是主觀因素,無法避免的錯誤是客觀因素。在檢查方法方面,我們常常采用了《萊達準則》,該方法需要進行10次以上的檢測,但在實際測試過程中,受實際情況的影響,沒有辦法多次檢測。因此,我們認為,在進行測試時,必須考慮到工作人員在操作過程中的疏忽和測試結果的異常情況。在許多情況下,它們都無法做到,因此,在進行實際研究和分析之后,在試驗階段,我們將使用試驗4法和Q方法來糾正粗大錯誤,并采用簡單有效的方法來減少粗大錯誤對測試結果所產生的影響。
3.3直接測量誤差
在物理測量方面與水質測試有關的數據可通過直接和間接測量獲得,直接檢測數據是指在測量過程中根據測試機器所直接獲得的數據,間接檢測是將測量數據納入相關的公式和通過計算得出的數據中,因為,直接測量數據一般有兩種錯誤。在實驗室進行的水質測試有時受到的某些條件的影響只能用一種測量方法進行,而且不能進行反復測量,因此,在實驗室進行的水質測試是一種單一的測量方法。因此,有必要根據實驗數據對其進行修訂:如果出現某些計量中的隨機誤差比較小的情況,可在該工具允許的范圍內加以修改,如果不可加以修改,應將儀器最低限度的一半作為該水質的的誤差最大值,為了獲得準確的測量或使測量盡可能接近現實,應重復多次的進行測量,并對所獲數據進行對應的計算。
3.4系統誤差處理
系統性錯誤是指在偏離測試條件時出現的模式不同的錯誤,這些錯誤主要發生在測試過程中,對結果的影響是一定的,從根本上來看,系統性錯誤可分為方法性錯誤和工具性錯誤。試劑錯誤和操作性錯誤。有以下幾種解決的方法,第一種選擇是將試驗方法與可靠的分析方法或標準的試驗結果樣本進行比較;第二種選擇是對照實驗,主要適用于沒有樣品的存在的情況,以實際結果=樣品結果-空白值表示,就可以得到精確的測試結果。
4、結束語
在廢水質量測試過程中發現了誤差,檢查人員應分析檢測中心的實驗室環境以及測試方法等是否有不正確的地方,分析并解決問題。并根據實際情況處理不合理的數據。
參考文獻:
[1]胡志勇.廢水水質檢測化驗誤差分析與數據處理[J].環境與發展,2018,30(06):174+176.
[2]孔小禹.廢水水質檢測化驗誤差分析與數據處理[J].資源節約與環保,2018(02):50-51.
[3]江珊.廢水水質檢測化驗誤差分析與質控措施[J].中國資源綜合利用,2018,36(01):163-165.
(作者單位:江蘇尚維斯環境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