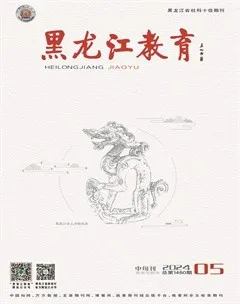看上去是“矛盾”讀起來是“學(xué)問”
趙桂萍 張強(qiáng)
摘要:文本的矛盾是作者筆法奇特、文本內(nèi)容與現(xiàn)實生活情境不同、文本敘事張力、故事對象情感突變等多種因素下,敘述者、文本人物、讀者之間難以在短時間產(chǎn)生在文本內(nèi)容、情感、手法的通路、共鳴,進(jìn)而引發(fā)的文本曲解、誤解或淺表理解———乍看上去是“矛盾”,研讀起來是“學(xué)問”。這樣的矛盾之處,恰恰是教學(xué)的“錨點”。將之作為定位器,師生立足教學(xué)的“錨點”,拉長文本解讀的鏈條,形成古詩文學(xué)習(xí)的網(wǎng)狀知識點互通格局,解讀更加真實合境,閱讀體驗更加豐富,語文教學(xué)更加和雅。
關(guān)鍵詞:初中語文;古詩文教學(xué);文本解讀;文本矛盾處
文本矛盾是敘述者、文本人物、讀者多主體處于信息不對等下的文本解讀狀態(tài),在“似懂非懂”之間,恰是教學(xué)的切入點。語文教學(xué)理應(yīng)聚焦文本矛盾處,在人物答非所問處抽絲剝繭,在情感非常處知人論世,在邏輯相對處重構(gòu)文本,在文化差異中融通品咂:師生閱讀交流,在一個個“錨點”上深度閱讀,在文本的矛盾處爆發(fā)思維活力,探索形成立體化、系統(tǒng)化、統(tǒng)整化的古詩文深度閱讀模式。
根據(jù)艾布拉姆斯的藝術(shù)四要素理論,“矛盾的現(xiàn)實世界,矛盾的觀眾欣賞”是文本矛盾的兩維。針對初中教材中古詩文選篇,可以從如下幾點抓住“矛盾”教學(xué)古詩文:作者敘事裁減、辭格運(yùn)用造成的矛盾;文本人物語言矛盾、行為矛盾和情感矛盾;古今文化差異的矛盾等。抓住這些矛盾,可以釋放文本解讀的張力,發(fā)展學(xué)生形象思維、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
一、在答非所問處激活情境
在一般的語言交際語境中,交際對象之間的互動本應(yīng)自始至終保持同一性[1]。然而有的文本或人物對話看上去答非所問,或人物行為看似前后矛盾;學(xué)生如果不細(xì)心品讀,容易漏掉這“意料之外”的“情理之中”。宜采取情境教學(xué)的辦法,還原文本情境,讓學(xué)生沉浸其中。
以統(tǒng)編版九年級上冊語文教材第三單元中張岱的《湖心亭看雪》為例,“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可以在課堂教學(xué)中,組織學(xué)生進(jìn)行情境模擬:
生1(張岱):閣下尊姓?
生2(亭上人):金陵x氏。
根據(jù)古人見面時自我介紹的習(xí)慣,應(yīng)該是“籍貫+姓氏”,如“瑯琊王氏”。在《湖心亭看雪》中,亭上人應(yīng)該是回答了自己的姓氏,而張岱對其籍貫記憶深刻,或為有意略去其姓氏,在答非所問中,構(gòu)筑了“真實的故國世界”與“理想的故國世界”,顯性與隱性的敘事構(gòu)成了一種內(nèi)部充滿強(qiáng)烈對比的整體和諧[2]。教師再出示“崇禎五年十二月”這個時間矛盾,圍繞兩個矛盾輻射張岱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引導(dǎo)學(xué)生梳理從語言現(xiàn)象的矛盾過渡到語義矛盾,立足天地此湖,理解張岱作為前朝臣子,對明故國的情有獨鐘和深深哀思。
此類還有人物言行的前后矛盾,在《十五從軍征》中,老兵回到家鄉(xiāng)“道逢鄉(xiāng)里人,家中有阿誰”。不問人而問家,問家之狀態(tài)。教學(xué)中組織學(xué)生情境交流,“道逢鄉(xiāng)里人”———你一般會問哪些問題?一位征戰(zhàn)幾十年的老兵會問哪些問題?情境對比中,理解老兵數(shù)十年離家,與家人音信全無,近鄉(xiāng)情怯,求問心切,希望與衷情交織的復(fù)雜情感。
二、在情感非常處知人論世
情到深處不講“理”,初中生對情感的認(rèn)知受限,無法對文學(xué)作品中的人物情感有全面的認(rèn)識[3]。創(chuàng)作者與讀者在信息、情感上不對等,加之文本的敘事張力,基于不同體驗和立場,文本的矛盾之處就會暴露出來。即文本讀起來與學(xué)生的日常經(jīng)驗存在情感沖突———如果拓展作者個人生活經(jīng)歷、時代特征、創(chuàng)作特色,或許能幫助學(xué)生理解作者的思想與行為。
關(guān)于知人論世,胡根林做了較為細(xì)致的課例分析。以“知人論世”為切入點,從詩人的身世背景、人生境遇、生命思考和精神追求角度切入,體會詩詞的情感世界;進(jìn)一步細(xì)化,“知人論世”還要關(guān)照詩人的職業(yè)、代表作品、后世影響等,作為教學(xué)的鋪墊、支架或理據(jù)[4]。
在秋瑾的《滿江紅》中,有一句“早又是中秋佳節(jié)”,明明是“中秋佳節(jié)”,眾人眼里一個皆大歡喜的團(tuán)圓節(jié),秋瑾為何埋怨“早早地又來了”?“矛盾”之意是:中秋來得太快、太勤了。在這種情況下,師生需要結(jié)合課下注釋、補(bǔ)充資料,理解詞人的情感。
本詩寫于1903年,列強(qiáng)環(huán)伺,秋瑾立志救亡圖存。
秋瑾寓居北京期間,接受了新思想。但丈夫以封建思想束之,不允許她外出參加愛國救亡活動。
1904年,秋瑾東渡,積極參加革命組織。
上述助讀資料,充分糅合了秋瑾的婚姻生活、思想歷程、人生重大經(jīng)歷和社會背景、年代信息,形成了一個大的“詩詞解讀意象群”,幫助學(xué)生理解秋瑾現(xiàn)在的“家庭生活不幸”、回憶中的閨中生活漸遠(yuǎn)、眼中的“家國被瓜分而不完整”、心里的自由精神不被理解……因此,“大家的”中秋與“個人的”中秋存在矛盾,豈不是“太早了!”
有的文本存在明顯的邏輯矛盾,需要結(jié)合創(chuàng)作者當(dāng)時的人生境遇、社會現(xiàn)實來分析。比如蘇軾的《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中提到“月有陰晴圓缺”,而在《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卻是“缺月掛疏桐”。蘇軾的月為何“隨意圓缺”?
“丙辰中秋”,月本該是圓的。蘇軾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自求外放,以求離蘇轍近一點。在《水調(diào)歌頭》中,借“問天問月”來表達(dá)對兄弟蘇轍的思念之情,也抒發(fā)出“月有陰晴圓缺”的豁達(dá)樂觀。同期作品《江城子·密州出獵》《祭常山回小獵》等也多以會列神采、傾吐豪氣為主。幾年后,蘇軾因烏臺詩案“寓居”黃州,眼下“缺月掛疏桐”“幽人”“孤鴻”“沙洲冷”,不復(fù)密州時“千騎”“出長圍”的豪壯。這種情感越不被理解,蘇軾心中的寂寞越是厲害,所以缺月孤鴻就“顯身”來寄寓詞人內(nèi)心的孤傲蔑俗之情,是為蘇軾“內(nèi)在心志”與外在自然的矛盾。
三、在邏輯相對處打通文本
矛盾格是利用兩個矛盾項所指對象的同一或包含關(guān)系,將辭面沖突而辭里統(tǒng)一的語義單位組織到一起的一種修辭方式[5]。在語義沖突中,辭面與辭里融合、消解、沖突和疊加,強(qiáng)化表達(dá)效果。邏輯相對在文本層面多表現(xiàn)為前后存在矛盾,或為字面意義上矛盾,或為主題闡釋性矛盾。正因如此,打通這些矛盾之處,有利于充分理解文本的敘述邏輯和抒情脈絡(luò)。
《茅屋為秋風(fēng)所破歌》中有詩句在字面上存在邏輯矛盾:“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上句為寫被子之“冷”,將其比作“鐵”———詩意暗含其“硬”。常理上,布衾多年不拆洗,污垢滿沾,質(zhì)地應(yīng)該較硬。而下句卻緊接提出“里裂”。“似鐵布衾里裂”于邏輯不通,需要反復(fù)咀嚼文本,打通矛盾之處。
教師需要引導(dǎo)學(xué)生找出前后語境中描寫“環(huán)境”的詞語,比如“云墨色”“昏黑”“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喪亂”“沾濕”,然后讓學(xué)生分析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雙重因素下,杜甫自安史之亂以來,遷居之不易,用“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嬌兒需要……但是……因此……”的句式表達(dá)看法,理解內(nèi)外交困下,杜甫一家人長夜難眠、輾轉(zhuǎn)反側(cè),甚至亂中難眠的窘態(tài)。
四、在文化差異中咀嚼味道
文化差異產(chǎn)生文本“用詞”矛盾。因為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的不同,學(xué)生接觸古代、國外文學(xué)作品時,難免有疏離感,對古代或其他民族地區(qū)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表達(dá)習(xí)慣、民族文化等感覺與現(xiàn)代、本民族文化存在矛盾沖突之處。教師采取對比閱讀方法,可以引導(dǎo)學(xué)生深化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理解,理解其背后蘊(yùn)藏的民族文化內(nèi)涵和審美特性的差異[6]。比如《曹劌論戰(zhàn)》中,學(xué)生會產(chǎn)生疑問:衣食都分給人了,為什么還會“民弗從也”,古代的“人”和“民”的兩個概念與現(xiàn)在“人”“民”連用形成矛盾。“人”是魯莊公的近親,“民”則是奴隸:在對比中增強(qiáng)理解力。
在學(xué)習(xí)《行路難》時,學(xué)生讀到“拔劍四顧心茫然”會有疑問:李白“停杯投箸不能食”可以理解,但是在宴會上為什么要“拔劍”?在《送東陽馬生序》中,寫同舍生的優(yōu)渥生活時,介紹“左佩刀,右備容臭”。“同舍生”帶刀上學(xué)嗎?古人佩劍帶刀的習(xí)慣與現(xiàn)代人的生活存在文化差異,單從文本上看,確實存在矛盾。
漢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說:“劍在左,刀在右。”古人佩劍,自周至唐,頗為盛行。帝王佩劍,是為地位、權(quán)力象征;文人士大夫佩劍,是為防身自衛(wèi)、禮儀所需;游俠佩劍,是為見義勇為、伸張正義的載體。而文人劍膽琴心,詩劍風(fēng)流,更有文武雙全、憂國憂民、儒雅孤傲之氣。因此,拓展李白的“詩劍風(fēng)流”,讓學(xué)生理解李白佩劍所獨有的雄心壯志,及劍所寄托的建功立業(yè)豪情。
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贈張相鎬》)
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臨江王節(jié)士歌》)
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塞下曲》)
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勛。(《贈何七判官昌浩》)
文本是作者、編者、文本人物、讀者之間交流的媒介。教師要善于“發(fā)現(xiàn)矛盾”,在多維交流場域中以問題、情境、資源為引子,讓語文學(xué)習(xí)有理有據(jù),有料有樣,有趣有味。在文本矛盾的解決過程中,引導(dǎo)學(xué)生抓住一個個“錨點”,發(fā)展學(xué)生思維,提升和雅語文素養(yǎng)。
參考文獻(xiàn):
[1] 陳楊.答非所問,別有洞天:從語用學(xué)視角分析初中語文課本中人物語言的藝術(shù)效果[J].語文教學(xué)與研究,2018(17).
[2] 曾仙樂.《邊城》的文本矛盾與沖突[J].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學(xué)報,2017(2).
[3] 林楚芬.以文本矛盾解讀人物情感:《群文閱讀:矛盾中的父子情》教學(xué)課例思考[J].師道·教研,2021(2).
[4] 胡根林.知人論世:還原詩人立體的生活世界:高中《語文》必修上第三單元教學(xué)設(shè)計與實施[J].中學(xué)語文,2022(1).
[5] 劉穎.漢語矛盾格的多維觀照[D].合肥:安徽大學(xué),2011.
[6] 李思瀅.對比教學(xué)法在“跨文化專題研討”任務(wù)群中的應(yīng)用研究[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xué),2022.
課題項目:2022年度淄博市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研究項目“古詩詞項目化學(xué)習(xí)提升學(xué)生文化自信實踐研究”(22ZBSKB090)
編輯/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