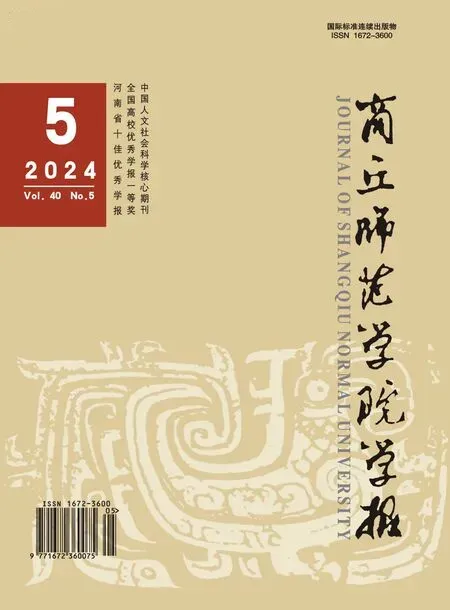《老子》上德、常德、廣德、玄德對價值二元論的超越之疏解
賴 錫 三
(臺灣中山大學 文學院,臺灣 高雄 80424 )
一、名言設制“即成即毀”的價值二元論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1]6—7(《老子》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這一句,可作為理解第二章前半段的綱領,而且關鍵在于“知”字。對于《老子》,“知”就像扮演“樸散而為器”的利刃,意味著把“渾樸整全”切割成為“特定器用”的機制。例如當人們“認知”“判斷”“命名”某棵樹某部分是美善良材時,同時也就意味著將渾樸整全的無名樹木,切割裁剪出“美善良材”的有用部分,離棄掉“不材散木”的無用部分,刻意有為地強取“美善良材”(有價值),刻意有為地拋棄“不材散木”(無價值)而令其成為垃圾。正如《莊子·天地》篇所言:“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于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2]453人們建立在“心知”而來的“有為”,突出了某些用途、樹立了某些價值,但這種犧尊形式的突出和青黃文采的加工之“知”與“為”,同時也是“犧牲”的暴力之“知”與“為”(斷在溝中)。進一步說,“知”與“為”,是通過“名言”的命名與分類來進行,而名言在標定某種善美典范之時,其實只是站在某特定角度或立場的視域下,進行二分切割而造成“破(突出犧尊)”與“斷(離棄溝賤)”的同時成立。例如美、善范疇的成立與突出,同時建立在不美、不善的犧牲與斷離。如此一來,美的肯定和丑的否定,看似相反相離,實又相待而成。
善與不善的關系,也是如此。同樣的道理,“有”與“無”,“難”與“易”,“長”與“短”,“高”與“下”,“前”與“后”,任何二元概念的區分,也都具有類似于“相對又相立”的構造關系。但人們在進行“知”“為”“名”的分類活動時,通常只會歌頌“突出犧尊”的規范框架和價值階序這一面,卻很容易遺忘“離棄溝賤”的規范暴力與制造垃圾的那一面。而《老子》要提醒我們,人類的“有知”“有為”“有言”,既提供“始制有名”的倫理、社會、政治之名制體系,但同時也可能將人們框限在固定而僵化的社會階序中,并將不合“犧尊”(如禮教)價值系統的“他者”拋棄,令其“斷在溝中”而成為無價值的垃圾。換言之,“樸散為器”的人為有用之制作程序,同時也是造成大量垃圾的拋棄過程(1)關于《老子》的垃圾哲學之反諷深義,及其與《莊子》有用、無用的呼應,可參見任博克和筆者的對話《〈老子〉:“正言若反”“不笑不足為道”的“吊詭·反諷”之道》,《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第1—17頁。此文已收入賴錫三主編《老莊思想與共生哲學》,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99—142頁。。
其實善惡、美丑,乃至長短、高下、前后,甚至延伸到是非、福禍、生死,等等,也都具有“相對又相立”的曖昧性。也就是說,“善”“美”“是”“福”等所謂價值范疇,并不能夠自己決定自身的絕對獨立價值,它們必須在區分的對比之下,才能暫時突顯相對性價值。亦即深入其“相生相成”的生產結構,將會發現它們具有“喜怒同根,是非同門”的“不可偏舉”關系(2)王弼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名數也。”王弼《老子王弼注》,收入彭曉鈺校《老子四種》,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頁。。而隨著時空情境的脈絡轉化,這些相對性的價值內涵也可能跟著轉變。問題是,人們在“自知”“有為”的“始制有名”“名以定形”的建構過程中,經常會掉入“有為”所帶來的偏取執著與特定僵化中,以至于走向價值一端的爭奪,從而繁衍出欺世盜名的悖論現象(3)蔣錫昌:“無名時期以前,本無一切名,故無所謂美與善,亦無所謂惡與不善。迨有人類而后有名,有名則有對待;既有美與善之名,即有惡與不善之名。人類歷史愈久,則相涉之事愈雜;相涉之事愈雜,則對待之名亦愈多。自此以往,天下遂紛紛擾擾,而迄無平安清靜之日矣。”蔣錫昌《老子校詁》,東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2頁。。例如《老子》第三章所反諷的尚賢易使民爭賢、貴貨易使民為盜等“現可欲”的詭譎現象[1]8。
面對價值二元論的僵化偏執與爭先恐后,《老子》提出了它的反省之道:一者要覺察價值吊詭的模糊曖昧性(如福禍相倚,孰知其極?),二者要實踐“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然而何謂“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首先,“無為”不是兩手一攤而全不作為,“不言”也不是如聾如啞的純粹沉默(4)焦竑引李息齋語:“圣人知之,必立于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敎,不取善,不舍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焦竑《老子翼》,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頁。。“無為”乃是對“有為主宰”的轉化,“不言”則是對“名以定形”的解放,因為“知”所帶來的“有為”“有言”,造成了“道有封”“言有常”的窄化現象,讓原本“道未封”“言未常”的“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的多元豐富受到片面的揀選與窄化的排斥。例如只將某種路徑定義為“正”(標準典范),勢將無法納受“道并行不悖”的不同路徑。正如《齊物論》對“正”或“同”的反省:
嚙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蝤然乎哉?木處則惴栗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蝤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2]91—93
王倪連番以“吾惡乎知之”回答嚙缺,表面看似回避問題,實是對嚙缺“自知”(自以為知)“自是”(自以為是)的棒喝與擱置。其實嚙缺的三問,都是建立在人類中心的特定認知角度和發言脈絡,“有為”地自以為自己是萬事萬物的標準尺度。而從王倪的回應“孰知正處?”“孰知正味?”“孰知天下之正色?”則是要對“自我觀之”的“同一性”價值判斷(正)進行反思與懸擱,以敞開“非同一性”的視角,以欣納“差異性”的物化。可見,“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并非取消多元差異的形而上同一或絕對沉默之秘境,它只是為了治療人類過于強制性的有為控制與語言分類的價值僵化。治療之后,千差萬別的物化現象,反而能各正其性、各安其命地自然發展。此乃《老子》在“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后,要許諾給萬物的崢嶸風光:“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5)陸希聲:“使萬物各遂其性,若無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萬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為器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功而不居其所。”陸希聲《道德真經傳》卷1,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版,第3—4頁。
呼應人們泰然任之而不為不恃,“萬物作焉”而自賓自化的崢嶸景觀,我們也可再度嘗試以莊解老(6)如王淮以《莊子·大宗師》“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游已”來為《老子》此段注解:“言其天地生,作于萬物之初,而不自為老始……言其生畜萬物,無心施為,而不自恃有德……言其包羅一切,成遂萬有,而不自居功巧。”王淮《老子探義》,商務印書館(臺灣)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2—13頁。。例如《齊物論》言:“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譎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通為一。”[2]69—70在人“自以為知”“自以為是”而給出價值標準之前,萬事萬物原本各有其不同脈絡的合宜性,如所謂“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當人們不去嚴格樹立某種標準或定義來框限多元事物時,萬物的“然”與“可”,就獲得了“各正其色,各正其處,各正其味”的多元差異之正。因此,“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也可以說是解構了“同一之正”而允諾了“萬殊之正”。如此而有“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譎怪,道通為一”的眾聲喧嘩之景觀:小草與大樹,丑婦與美女,都得以松開“美之為美,斯惡矣;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的二元框架,各自回歸“恢恑譎怪”的萬殊差異情境,容許森羅萬象而各顯崢嶸,由此呈現并行不悖的“道通”景觀。
而“道通為一”的“一”,則并不意指任何形而上的同一之道,也不是將萬物的差異都給同化或統一起來,而“道”只是無為無作地敞開最大空間,以便讓萬事萬物“并行不悖”地“各安其位”“各正其性”。換言之,“道通為一”,許諾的是事物并行與價值多元,讓萬事萬物得以在暢通的空間中,相互交流而共生共長。一旦通暢的通道被封閉固定下來,就會墮落為“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的垃圾生產邏輯。因為在“有封有常”的分類標準下,它只允諾某些正典進入價值世界的窄門,而進不去窄門的異類異行,將只能被排擠在門外,而成了無用的垃圾。因此《莊子》提醒我們,通達于道者的真人(達者),不要遺忘“知通為一”的寬廣之門與并行之道,這樣才能避開制造大量垃圾的“即成即毀”之生產邏輯。
二、超越“即藥即毒”的上游療法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1]8(《老子》第三章)
“尚賢”“貴難得之貨”“見可欲”,前提都是先透過“名”(始制有名)與“知”(一偏之知),先崇尚(尚)、先標舉(貴)、先突顯(見)某種價值標準與財貨利潤,然后將人們的“欲望”焦點化地誘導并增強到其所設定的“可欲”對象上。如此一來,也就造成人們對稀少之名的爭取(好賢人之名)、對稀有物資的搶奪(爭難得之貨)。然而《老子》提醒我們一種詭譎現象:當人們刻意樹立某種價值準繩或利益導向時(如善名、美名、賢名、好材、貴貨,等等),除了會產生《老子》第二章“美之為美,斯惡已;善之為善,斯不善已”(7)王弼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老子王弼注》,第2頁。河上公章句:“自揚己美,使彰顯也。有危亡也。有功名也。人所爭也。”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6頁。[1]6,那種對不美、不善的“垃圾排斥”效應,同時也會驅使人們對美善價值的“爭先恐后”。于是,原本以為可以利用美好正典價值來引導或規范人們,但現在卻也因為“有為”而過分標榜“可欲”對象,同時也帶來了“欲望”被集中、被放大的后遺癥。
以上便是《老子》對于“見可欲”反而造成“民心亂”的診斷。因此《老子》才要提出一連串的“不”,來作為除病之藥與轉化之道:“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8)王弼注:“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也曷為;唯用是施,貴之何為。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為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老子道德經注校釋》,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8頁。王淮引憨山語:“尚賢,好名也。名,爭之端也。故曰爭名于朝。若上不好名,則民自然不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利,盜之招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為盜。故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以好名好利者,因見名利之可欲也……若在上者茍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老子探義》,第14—16頁。《老子》的“不”,并不是簡單取消或完全否定。例如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9)王弼注:“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兼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為,不求而得,不為而成, 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93頁。河上公章句:“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氣流行,民德以全也。”《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第147頁。的“不德”,第二章“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10)王弼注:“自然已足,為則敗也。智慧自備,為則偽也。”《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6頁。的“不言”,其真義都不在于簡單否定“德”或取消“言”,而是面對過分僵固的德目規范、過分封閉的名言分類時,要給予柔軟、彈性、流動的治療與轉化之“去蔽”作用。用《齊物論》的話來說,“不”的“去蔽”是想要恢復“未始有封,未始有常”的“際而不際”狀態[2]83。換言之,“不”是一種去固執、去封閉、去單向、去本質的活化作用。而“上德不德”就意味著不固執在道德條目的特定徼向上,所以能夠涌現更真誠更自然的寬容之德(是以有德);而“不言之教”則是不停滯在名言分類、言說標準的特定徼向上,所以能發揮更柔軟更自然的轉化作用(物自賓、民自化)。同樣精神,“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的“不”,一樣指向了不偏執、不停滯、不焦點化的去蔽與療愈(11)“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見可欲”的三“不”,不禁令人想起《莊子·逍遙游》中的三“無”:“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華正書局1991年版,第17頁)“不”“無”,都是一種去蔽的除病工夫。。
接著,《老子》進一步強調:好的療愈或除病之道(圣人之治),在于“虛其心”“弱其志”。面對人們被過分聚焦而轉剛強的“可欲”之心、“常心”之志時,須給予柔軟(虛之)、給予淡泊(弱之)的調節轉化。但這并非取消或否定人們的自然欲望,事實上《老子》也強調“實其腹”“強其骨”,也就是恢復自然生命力以及由此而來的平實需求。可見,《老子》第三章的“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其中的“無-知”“無-欲”“無-為”(不敢為),都不是單向度或簡單化地去取消與否定“知”“欲”“為”,而是針對片面之知、偏取之欲、控制之為,給予“不”固執、“不”偏取、“不”控制的去蔽與活化。“無”和“不”的反思與修養是相通的,都是針對心志增強與欲望擴張的過分突顯之“有為”,給予調節轉化而使其逆返平實而自然的狀態。對此,《老子》認為這種“為無為”的修養與智慧,才真能使人們減少“爭、盜、亂”的后遺癥,而達成“無不治”狀態。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1]43(《老子》第十八章)
對于儒家來說,仁義、智慧、孝慈、忠臣等道德價值或行為范式,是理所當然的好東西,而且也是用來救治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藥物良方。就一般人的道德直覺與社會規范而言,儒家這種以“正”(美善的正確價值范式)來救導“不正”(不善不美的價值異化)的主張,似乎很自然地被一般人視為應該積極追求與自我認同的價值觀,《老子》如何可能反對它呢?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老子》這種看似很激進的批判呢?這種對仁義、圣賢的批判,會不會掉入反倫理的價值虛無主義?這也是一般人對第十八章的擔憂與質疑所在。
對筆者而言,比較好的理解方式,先不必簡單化地將《老子》這類批判反省視為純粹的完全否定,反而適宜將其視為“除病不除法”的病理診斷,并由此提出另類的辯證藥方。對于《老子》而言,儒家對仁義、忠孝、圣賢等的倡導,是站在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等禮崩樂壞、橫行叢生的亂象上,因此很直接很焦慮的用心用力所在,就是站在“不正”的對立面,要以“正”的典要來直接、強力地救治“不正”。這種以“正”挽救“不正”的導正或救治,當然也有它的合理性和迫切性(因此老莊對儒家也有相當同情成分在),但是否是“最好的”或“唯一的”治療方式呢?顯然《老子》有相當不一樣的想法,而這個“不一樣”,帶有對儒家提出的救治方式的再治療。如果說儒家的救治之道也是一種對社會異化病態的第一序批判(治標),那么《老子》的拯治之道則帶有“批判的批判”那種“第二序”的反思性格(治本)。用個比喻,《老子》想提醒儒家的是,若想要海晏河清地治其根本(而不是治標不治本),就不能只在下游做工夫,因為下游的混雜污穢是撈不完、除不盡的,因為上游還一直在制造污染源。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儒家的“以正導不正”,不但不能帶來河清海晏,《老子》甚至以反諷思維來提醒儒家,其藥方本身也可能帶有毒性,亦即“正”也可能導致更加“不正”的繁衍。
當人們愈需要強調仁義忠孝的時候,除了反映現實上更處在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詭譎境遇外;當人們愈標舉某種仁義忠孝的行為規范和舉止典要,這個動作也可能愈具有排他性和壓抑性,因而造成人們在心態和行事上的“恢恑譎怪”。例如貪好仁義忠孝之善名而實多偽善,例如以仁義忠孝來純化自己或強求他人而造成道德的同一化暴力,例如以自以為的道德判斷而擇善固執地嚴分善惡而造成裁判他人的不寬容等其他可能性的異變演化。而《老子》開出的另類辯證藥方,則在于想要同時思考“即藥即毒”的吊詭性,不想要等到生了重病(大道廢,六親不和,國家昏亂),再去思考開立特效藥的救治方式(高倡仁義、大舉忠孝、強名圣賢),而是先去預防性思考如何讓病癥還未演變成病入膏肓之前,那種較自然、較平淡、較少副作用的,也就是“藥性不強,毒性稀少”的“上游”療方。而這個“上游”療方的基礎就在于,“大道”還未被“有封有常”地給固定下來(大道未廢),“智慧(人心)”還未被復雜的機心欲望給雕刻的支離破碎(智慧未出),“六親”的人倫親密關系還沒有被比較與競爭給過分增強與壓抑(六親未不和),國家機器還沒有被過分操控而造成權力傾軋與爭奪(國家未昏亂)。換言之,《老子》的激進療方,乃在于上游的釜底抽薪,而不是下游的抽刀斷水。這不必視為完全否定儒家第一序治標的用心良苦,而是嘗試提出第二序治本(治療的再治療)之辯證藥方。
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1]45(《老子》第十九章)
其實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可以和第三章一起來建構出融貫的解讀脈絡。而將《老子》這幾章加以歸納,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通主題:即對儒家思維的價值系統和救世方式(如仁義圣智、孝慈、忠信等),表達后設性或第二序的再反省。牟宗三曾強調儒、墨、道、法諸家思想,都是針對“周文疲弊”禮崩樂壞的秩序崩解與價值失落而來的回應與救治。而在牟宗三看來,儒家最重要的回應與拯治之道,就在以“仁”疏導并活化周代禮樂的虛文危機,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而孔子“攝禮歸仁”,不但承繼周代文化遺產的傳統形式,更是注入了“仁”的內在性價值根源。因此牟宗三對于儒家的回應之道給予了最高禮贊:“開辟價值之源,挺立道德主體,莫過于儒。”[3]62
而《老子》上述諸章句所提及的“仁、義、智、忠、孝、賢、圣”等價值概念和人格典范,便是儒家“開辟價值之源,挺立道德主體”的救世法寶,牟宗三顯然認同先秦儒家面對“周文疲弊”所端出的藥方具有普遍性的價值意義。但《老子》卻認為儒家端出的尚圣尚賢、尚仁尚義、尚忠尚孝等救世作為,仍然不免“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簡單地說,這些藥方看來很莊嚴、很誠懇、很積極、很正向,帶有撥亂反正的用心和力挽狂瀾的使命。但《老子》卻認為儒家那些看似深入人心、挖掘道德主體的價值活源,仍然還不是釜底抽薪以治療文明異化的最好藥方(為文不足),還必須進行第二序反思“即藥即毒”的吊詭性結構,以便提出更激進于儒家的辯證藥方。《老子》想要回到“藥性毒性交錯相攻”之前的“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的上游狀態,這也就是第十九章所謂“令有所屬”的用心所在。
《老子》絕非簡單地否定“仁、義、智、忠、孝、賢、圣”,而妄想退回前人文的動物原欲般的存在,更非否定一切價值而鼓勵妄行妄為。否則我們無法理解《老子》為何再三強調,它對儒家價值概念的“除病(不除法)作用”(如“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反而可能具有超越“仁、義、圣、智”的功能或效果,例如“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等等。可見,面對周文疲弊的大危機,《老子》不能完全認同儒家的藥方(為文不足),乃是因為它認為自己的“藥中之藥”,更為治本、更加有益。對于這一點,牟宗三也曾提出“作用的保存”來描述或定位《老子》的詭辭智慧。言下之意,《老子》并非在“實有層”否定儒家的仁義圣智等主張,只是想在“作用層”的方面去思考:“如何”把仁義圣智更好地呈現出來。牟宗三這種說法,頗有幾分觸及《老子》“無”的吊詭理趣,但他最終目的卻還是為了推舉儒家(牟先生認為儒家同時擁有實用層和作用層,而道家只有作用層而缺乏實有層),而且說到底,他認為老莊對儒家的批判與反省,還是可以被解消(因為儒家也具有“無”的智慧),而道家卻由于未在實有層所有建立,因此無法像儒家那樣“開辟價值之源,挺立道德主體”。如此一來,《老子》所提出的周文藥方便不真具效用,而《老子》對儒家的反省亦不真具意義。牟宗三的觀點,屬于典型“以儒觀道”的立場前見,有為了張揚儒家而低估道家之嫌(12)牟宗三對道家的“作用保存”之相關討論,參見氏著《中國哲學十九講》之第七講《道之“作用的表象”》,第125—154頁。。
《老子》不能全然認同儒家尚賢圣、尚仁義的關鍵原因,正如筆者在解讀第三章時所指出:價值觀念的高舉、財貨貴物的標榜,會誘導人心對“可欲”的增強與聚焦,很難不造成爭名奪利、爭先恐后等后遺癥的演化增生。詭譎地說,在《老子》看來,儒家提出的解藥本身同時就具有毒素成分。這并不是說儒家拯救周文的道德動機(出發心)有問題,而是點出儒家施用的解藥本身,會連帶引發它未能預期的反效果或后遺癥。首先,這是因為人心不全是道德仁心,人心還有種種臥虎藏龍而且具有滋長變異的各種可能性。例如當儒家宣揚它認為的正向價值為救世之道的同時,便會與不同的觀點形成是非對立(所謂“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儒墨是非’之爭論現象”)。其次,不合于儒家美善價值規范的正名系統之言行,容易被視為“不美不善”而遭受拒斥,如《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的善惡對立[1]6。第三,仁義圣賢的高舉與標榜,也很容易被濫用和盜取,滋生欺世盜名的偽君子,甚至“竊國者侯”的大政客。另外,仁義忠信等德行也容易墮化為成規成矩的形式規范,導致人的情性在回應多元差異的感受力時受到干擾與抑制(13)林希逸:“圣知之名出,而后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后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于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后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也。圣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林希逸《道德真經口義》卷1,收入陸國強等編《道藏》第12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703頁。。由上數端反思,約略可知《老子》并非只是想以牟宗三所謂“作用的保存”(“無的詭辭智慧”),來促使儒家的仁義圣智等所謂“實有層”的價值規范得到最好發揮,他的這種解釋簡化了《老子》“非藥非毒”的思想激進性格。讀者可以先不急著認同《老子》的主張,甚至可以對《老子》的主張保留疑惑和探問,先回歸“以《老子》觀《老子》”,這樣才能善察《老子》對儒家的針砭用意。例如孝慈與忠信的道德呼吁,可能正好反映出家庭和國家的失序實情;而此時此刻,愈去標榜孝慈忠信、仁義圣智的矯治方式,愈有可能演變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觀點沖突和權力斗爭。這就好像儒家和法家,其人性觀、道德觀、政治觀、權力觀,雖然有著相當大的差異(甚至位于對立兩端),但儒法之間的沖突與斗爭,卻經常呈現出“相立又相生”的詭譎局面。這也是政治史上,儒法兩邊經常在政治體制的實際運行過程中,扮演好人與壞人總是同臺合演政治劇的詭譎現象。所以就《老子》的激進立場來說,仁義圣智從來都未能消滅血淋淋的權力斗爭,也不會終結政治權力的矛盾傾軋,它只是扮演權力游戲中的天使角色,這個角色看似對立于魔鬼,甚至一心想要終結魔鬼,但在《老子》看來,它卻可能秘響旁通地助長了魔鬼氣焰,吊詭地促進了魔鬼演化。
因此《老子》的激進藥方(以藥解藥),在于反諷地煉制出了“解藥之藥”(解開藥毒的非藥之藥)。那就是:要殺死魔鬼的最好方法,不是一味朝魔鬼殺去,反而是殺死自以為天使般的自己。或者說,殺死自己心心念念想要殺死魔鬼的天使心(常心)。因為魔鬼的力道和天使的力道,剛好相反相成,一邊太使力,會醞釀另一邊反作用力的增生。因此一味用天使去打擊魔鬼,反而可能造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鬼越殺卻越多而且越厲害的詭異邏輯。這就像病毒吸收了藥性,而演化出具有抗藥性的超級病毒那樣。所以《老子》建議,不如“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釜底抽薪地解開“魔/道”相斗又相生的糾結。讓天使與魔鬼“和光同塵”地相互淡泊,而這種“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的淡泊作用,才能化除兩邊都過分剛強的戲劇張力,由此希望恢復人們原初互動中的自然情性。此正如《莊子·天地》篇所呼應的,人們自然而然的端正、相愛、實誠、穩當,卻不必在意念上刻意知曉或標榜“以為義,以為仁,以為忠,以為信”:“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2]445
《老子》強調在互動關系中恢復人的自然情性(如“民復孝慈”等),表面看似有幾分類于牟宗三的“作用保存”,實則骨子里有所不同。因為《老子》的“民復孝慈”“民利百倍”,并不是在儒家的思考框架中來進行,而是跳出其思維框架往更根源的上游去進行第二序的治本思考,因此《老子》才會批評儒家“為文不足”,并強調自己的主張才是“令有所屬”(14)焦竑:“圣智、仁義、巧利三者,繇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老子翼》,第48頁。。正如《莊子·馬蹄》篇所指出的,“文”對“質”的析離與破壞,會進而產生“析文忘質”的后遺癥:“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廢,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2]336而老莊所以敢直指“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主要是為了提出“返質以救文”“返樸以救器”的藥中之藥(15)關于道家“返質以救文”的想法,可參見拙文《質文辯證與倫理重估:〈莊子〉對禮之真意的吊詭反思》,收入《道家的倫理關懷與養生哲學》,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219—290頁。。
三、化除前識暴力的上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1]93(《老子》第三十八章)
《老子》將“上德”和“下德”作對照,并透過否定性的“不-德”(不據德),來辯證彰顯它所要呈現的肯定性表達“是以有德”。換言之,“是以有德”是透過對“不-德”的除病,或者對“下德”的治療,來呈現其“是以有德”的倫理關懷。“上德”的提出,代表《老子》的倫理關懷是批判后的辯證肯定,而不是單純的直接肯定。而一般“下德”直接肯定的“不失德”(據德)模式,行事上斷然表現出“為善去惡”的積極作為(為之),內心里又帶著“擇善固執”的強度意向性(有以為)。然而《老子》卻批判這種“為之”(外有為)又“有以為”(內刻意)的“據德”狀態,并不是與他人興發原初倫理關系的最好方式。在《老子》看來,原初性倫理關系的“上德”(上善之德)實現方式,需要對自我的道德裁判(為之)和道德意志(有以為)之“前識”,給予“無為”和“無以為”的“雙無”之轉化修養。
第三十八章所謂“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意指“下德”乃不脫“為之”和“有以為”的“前識”做主,這是一種“以自為前、以自為識、以自為光”的自為之、自以為。而《老子》認為“前識”(也可說是“常心”)做主的道德意志優越感,在鑿破了原初素樸的倫理關系之后(道之華),卻反而走向了“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愚昩(愚之始)(16)河上公章句:“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言前識之人,愚暗之倡始也。”《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第150頁。林希逸:“前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為智,則非道之實矣。華者,務外也。若以此為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道德真經口義》卷3,第710頁。。《老子》的“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大致相應于《齊物論》的“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的成心自師[2]63。而“前識”(“常心”或“成心”)正是鑿破渾沌、裁判是非的利刃,從此讓“知白守黑”與“和光同塵”的渾沌上善,變成善惡分明、是非兩端的下德裁判。《齊物論》言:“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其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2]83顯然《莊子》所嘲諷的“八德”(左右,倫義,分辯,競爭),契近于《老子》所批判的“下德”(17)《莊子·齊物論》的“八德”之說,應是對“仁、義、禮、廉、勇、忠、信、(孝)”等用法的“反諷”。亦即道德條目在《莊子》看來,反而屬于“道封”“言常”的產物或標示。原本“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的狀態,屬于《老子》“道德”未失的原初狀態,一旦“道有封”“言有常”,便墮化為“失道”“失德”而后的“仁、義、禮、廉、勇、忠、信、孝”等,具有明確條目性的價值判斷與行為規范。對于這種定義相對明確、分辯相對清楚的儒式道德倫理,《齊物論》便以反諷口吻指出“八德”的核心本質不脫于“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簡言之,這種“有左有右,有倫有義”的規范秩序,它建立在“有分有辯”的名言分類與區辨的基礎上,同時也脫不開“有競有爭”的價值競爭與排斥的命運。這就像《人間世》對“德”“知”“名”的反諷與反省:“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莊子集釋》,第135頁。。《莊子》提醒我們,不要只看到“有左有右,有倫有義”的秩序規范,也要留心它所帶來“有分有辯、有競有爭”的“樊然淆亂”之后遺癥,也就是類似《老子》第三十八章所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后遺癥。
《老子》批判以自為前、以自為識、以自為光的“前識”,稱這種自我篤定與自我優越的成見心態,其實是對于“道”踵飾增華的“余食贅行”,所以才要有返璞歸真的“不自”“去自”的修養工夫。而為了對治“余食贅行”的“前識踵華”,乃有第二十九章的“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也就是將自我的“甚、奢、泰”,轉化為“敦、儉、樸”的柔軟平淡(18)林希逸:“甚、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余食贅行之意。圣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為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道德真經口義》卷2,第707頁。另外,河上公章句:“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第119頁。。
《莊子·齊物論》所嘲諷的“八德”,除了呼應《老子》第三十八章的“下德”,進一步說,“八德”或“下德”都涉及了道德之光的暴力,尤其和語言概念的二分切割密切相關。如《老子》第二章所分析:“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19)王弼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6頁。因為語言的二元特性,使得人類經由命名、分類所建立的道德規范與倫理尺度,產生出肯認價值而排斥非價值的分斷現象(其斷在溝壑)。就像美、善的被高抬,和丑、惡的被賤斥,是同時成立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一連串對比概念,都不免于肯定與否定的“相較相成”。換言之,對有價值的追求與無價值的賤斥,屬于“即肯定即否定”的一體兩面。由此很容易造成肯定一邊而犧牲另一邊,如《齊物論》所分析的現象:“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3]70肯定這一邊(成此一端)、否定那一邊(毀彼一端)的道德裁判,在老莊看來,則屬于“鑿破渾沌”的下德處境。這種肯定部分生命、部分行為,排斥其他生命、其他行為的八德處境,使得原本“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的接納差異、欣賞多元,墮化為“有分有辯,有競有爭”的特定追求而賤斥他者。
對于下德或八德的“有分有辯,有競有爭”之倫理成毀現象,《老子》曾針對周文體制的價值體系,提出一連串的批判性觀察,例如第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20)陸希聲:“夫情所貴尚,則物徇其欲。徇則生偽,偽則生奸。故尚賢則爭奪之心萌,貴貨則盜賊之機作。夫唯以性正情者,不見貴尚之欲,從事于道而無奸偽之心。”《道德真經傳》卷1,第4頁。林希逸:“尚,矜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為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于為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道德真經口義》卷1,第698頁。、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21)林希逸:“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后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后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之時,而后有忠臣之名。”《道德真經口義》卷1,第703頁。、第十九章“絕圣去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22)林希逸:“圣知之名出,而后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后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于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后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也。圣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道德真經口義》卷1,第703頁。。除了批判這種“有分有辯,有競有爭”的二元性道德倫理之成毀亂象,《老子》也指出道德優位性的一偏之見,容易產生“光之暴力”,因而《老子》的原初倫理要以“襲明”來加以柔和,并走向“和光同塵”的寬容與諒解。此如《老子》第五十六章:“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23)陸希聲:“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故大丈夫去彼辯說,取此心悟,塞其嗜欲之端,閉其云為之路,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糾,上和光而不皦,下同塵而不昧,是謂微妙玄通,與物大同者也。”《道德真經傳》卷3,第20—21頁。第四十九章:“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24)陸希聲:“圣人體道無為,物感則應,應其所感,故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茍百姓有好善之心,圣人亦應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輔之。茍有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化而為善,則天下無不善,百姓皆得所欲之善矣。至于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化之,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無不信矣。”《道德真經傳》卷3,第13頁。
《齊物論》亦有言:“圣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2]83《莊子》對“八德”的反諷,意不在取消道德倫理,而是經由批判而重返“圓”的包容并蓄(圣人懷之),而不是“方”的沖突對立(辯以示之)。換言之,“圓”具有圓納萬端、圓轉無方的包容性與轉化性。“方”看似有了更明確的方向性,卻是在對立性、對比性的基礎上,弱化了“和光同塵”的曖昧玄同性格,才產生相對明晰的徼向性。“示之”(現可欲),就是樹立某種行為規范、突顯某種價值判斷,這種“樹立”與“突顯”的“示”與“辯”,很容易同時產生爭奪性和排斥性的暴力。所以《莊子》強調:過分顯示單一道路的正當性,會減損其他方向道路的可能性(道昭而不道)。過分黑白分明而強辯是非,會降低與不同立場的對話能力(言辯而不及)。過分執著某種特定行為實踐才是仁行,會阻塞對于多元事物感同身受的能力(仁常而不成)。認定某種標準而清廉自高,也就很難虛懷若谷地接納別人(廉清而不嗛)。以某種血氣行為來定義勇氣,將會變得狹隘而看不到差異情境下所展現的勇氣(勇忮而不成)。
老莊的上德(或者大道、大仁、大廉、大勇),其中的“上”和“大”,不是以“一行一德”而排斥“它行它德”,而是以“道生、德畜”的兼容并蓄,來圓懷容納不拘一格、各有差異的德行。而且為了對治黑白、明暗過于二分對立的“方”德(亦即“裁圓為方”的“偏向倫理”),《老子》乃以“襲明”(25)《老子》第二十七章:“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70頁。來批判之,《莊子》則以“葆光”來轉化之。“襲明”和“葆光”,都是為了治療“偏向倫理”的光之暴力,改以“知白守黑”“知雄守雌”(26)《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73頁。的非二分對立的“玄德”態度,欲將“方德”所排除的其他可能性,納入“圓德”的慈柔圓懷中。“襲明”“葆光”所隱喻的“玄德”,就是讓“有”的徼向,連通“無”的妙用,正是這種“知有守無”的“玄德”,不讓一德一行的特殊顯示被固執焦定下來。老莊也經常將這種“無”的除病治療,運用“不”的去蔽作用來表示,故有“上德不德”“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等一連串“不”的除病治療之表述。但這種“不”并非簡單的“否定”,而是要還原或成全“上德”的“大道”“大仁”“大廉”“大勇”。而“大”之為“大”,在于能將偏執于定向的“方德”(偏向倫理),轉化為包容而廣納的“圓德”(包容倫理)。
然而“圓德”的包容倫理,若要能被體現,則需有類似《老子》“致虛日損”的工夫,或《莊子》“坐忘”“心齋”的喪我還虛的修養。《莊子》的坐忘、心齋可視為對上德、圓德的再肯定,只是這種肯定必歷經一番批判治療、逆轉收回的“忘仁義”“忘禮樂”,甚至更深層的“喪我”。呼應于《老子》第三十八章,“忘仁義”“忘禮樂”大約相應于忘卻外在倫理規范的“為之”,而“喪我”則相應于忘卻內在道德意志的“有以為”。也就是說,坐忘更深層的修養工夫涉及自我的封閉內核之轉化與敞開,如此才能“同于大通”“無好無常”。而這種“喪我”的主體轉化、自我淘空,在心齋的描繪里,則被表達為:“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亦即顏回原先的道德自我中心感、重要感“消失”了,從此“實自回也”逆轉為“未始有回”。也只有這種“以自為光”的道德中心性、優位性之忘卻與虛心,才能產生出最大的容納空間與最柔軟的回應能力,此即“同于大通”“虛懷若谷”,才能產生的無偏好、無常心的上德容量。
四、知白守黑的常德不割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1]73—74(《老子》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章主要由三個對應句子來構成,而且意義結構相一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
基本上,這三個句子的意義相契,首先都在描述不落入“雄/雌”“白/黑”“榮/辱”等二元對立的兩端(但可稍為再作細微區分,“雄/雌”或涉及性別或動靜的兩端,“白/黑”或涉及“道德”與“非道德”的兩端,“榮/辱”則涉及“聲名”與“非聲名”的兩端(27)焦竑引李息齋語:“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為天下溪。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于人,辱者人加于我。我加于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于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老子翼》卷3,第63頁。)。其次,超越“價值”與“非價值”的兩端對立方式,乃在于回到“為天下溪”“為天下式”“為天下谷”的會聚之地。尤其“溪”“谷”更是表達道的負抱、容納意象,如第三十二章“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第四十一章“上德若谷”、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顯然“溪”“谷”的處下、容納、不爭,經常被《老子》用來譬喻柔軟包容的上德、廣德、常德(28)《老子》經常交互使用“上德”“廣德”“常德”“玄德”等概念,來對照善惡對分的“下德”。基本上,它們都意味著超越二元對立的另類德行模式。這是因為老莊的“道”不固定、不占據某特定之道,因此其“德(上德不德)”也具有了包容差異的廣納特性。。
也唯有處卑、就下、不爭、廣納的“常德”性情,能做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既能知道“價值”(有用)如何被焦點化地突顯出來,也能守護未被焦點化而隱沒在“無-價值”(無-用)的廣大場域。亦即“溪谷”的“中央”之地、“渾沌”之玄德(常德、上德、廣德),能夠促使原本對立的兩極(“雄與雌”“動與靜”“白與黑”“榮與辱”),重新遇合于“溪谷”(無極)之地,展開“知有用,守無用”的相知相守之兩行共生、平等對話(29)至于“為天下式”的“式”,除具有法式的模范意義外,它可能具有早先“式盤”所象征的“中心與四方”“天圓與地方”“中心與兩行”的統合意味:它的天圓地方形象,圓的中心有一空洞,可懸掛而圓轉不息,象征天行運動的周行不殆。放在本文的脈絡乃涉及“負陰抱陽”的“沖和”意義,“式(盤)”的具象本身,也帶有“雄雌負抱而不二”“黑白負抱而不二”的意味。有關“式盤”的考辨,可參看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第二章,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89—174頁。式盤的樣式與說明,也可參考Sarah Allan, “The Great One, Water, and the Laozi: New Light from Guodian,” T’oung Pao 89 Fasc. 4/5(2003): 246—253.。《莊子·應帝王》的“中央”之地,呼應于《老子》的“溪谷”之地,都具有“中而空”“中而下”的虛位、謙下之意涵(30)據任博克的觀點,第二十八章的“溪、谷、式”三項,都具有處“虛、下、中”的特性:“三者合起來則有共同意思:虛而處中心位置或下方位置,無為而萬物自然歸的象征。因為所有中間轉的歸向也在其中。所以此章等于說:如果能夠知道被肯定為有價值的事物都在那兒,而不拋棄被否定為無價值的事物,就會變成無為而萬物自然歸的那個中心。”參見任博克、賴錫三《〈老子〉:“正言若反”“不笑不足為道”的“吊詭·反諷”之道》,《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第4頁。此文已收入賴錫三主編《老莊思想與共生哲學》,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106頁。。而“渾沌”之善,則呼應于“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的“常德”之善。而復歸“嬰兒”(雄雌未對立),復歸“無極”(陰陽無住兩極),復歸“素樸”(原木未裁割),其中的嬰兒、無極、素樸,這三者在《老子》和《莊子》的思想脈絡下,都具有“即有即無”“渾而為一”的二邊交織而“中道不偏”的特質,可見《老子》的所謂“常德”具有調中而不偏的玄同意味。例如成玄英對《莊子·應帝王》“渾沌”中央帝的注解,便很能保握這種“即無即有”“非有非無”的調中特質:“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為有。北海是幽暗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渾沌為非無非有者也。有無二心,會于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之心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2]309—310
因此第二十八章要提醒我們“樸散則為器”,并總結在“大制不割”(31)王弼注:“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也。”《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75頁。。“樸散”意味著原先一體流通、多元交流的渾沌、抱樸狀態,現在被割裂成為價值和非價值的對立兩邊,使得原先的渾樸被支離破碎了,而“常德”也就被破壞了。原本可為天下范式(式)的“常德乃足”(32)焦竑引王純甫語:“此圣人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圣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焉往?所以為溪為谷為式,而天下歸之者正以此真常之德未之離焉耳。”《老子翼》,卷3,第64頁。,現在被“樸散為器”(33)王弼注:“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老子王弼注》,第25頁。的特定框架與硬性規范給取代了。因此《老子》要提醒我們,唯有重新“復歸于樸”而善用“大制不割”的圣者,才能成為好官長。因為好的導引者要能實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的“常德”包容之道,而不是讓百姓掉入“各得一偏”卻“不能相通”的定用之器。
對于“不割”“抱樸”等狀態,除了呼應溪谷的中空、處下的容納特性,《老子》還運用了嬰兒“專氣致柔”的身心狀態來比擬(“嬰兒”是雄性與雌性氣質,尚未單向定型化的原初可能性);也用了陰陽流轉而兩行無礙的無極來比擬(“無極”是“無偏于陽極亦無滯于陰極”的兩行可能性);還用了樹木尚未被制成特定器具前的原樸可能性來比擬(一旦鑿成特定器物,可能性就被固定的現成性給代換了)。總之,“樸”乃處于曖昧兩可、渾然為一的可能性,一旦進入“樸散為器”的割裂狀態,人們就很難不掉入“雄/雌”“白/黑”“榮/辱”的有封、有常,并且由此產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對立斗爭。所以好的帶領者(官長),要能善于守護“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的“常德”“不割”之道。值得提醒的是,“不割”只是不決裂為絕對分離的兩邊(“于二而無二”),而不是全然無用的“純粹同一”。亦即官長作為人類文明的守護者,不可能不適度“用器”而走向一定程度的“樸散”,但也要“知有守無”“知器守道”,才不會掉入“用器忘樸”的一邊之見。當然,《老子》的還樸之道,也不是簡單地回歸“純然無用之樸”的另一邊見。而是“知其器守其樸”的“即器即樸”之兩行相即、中道調節。
總結地說,《老子》第二十八章明白告訴了我們,“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下的所謂“返樸歸真”,絕不在于退回全然“無名、無分、無欲”(絕對名詞狀態),而是要在“名、分、欲”(有之徼)的不可逃離之認取活動中,不斷進行“無-名、無-分、無-欲”(無之妙)的調節轉化之守護運動,以促使“價值的焦點作用”(知雄、知白、知榮)和“非價值的敞開作用”(守雌、守黑、守辱),進行“即有即無”(知有用守無用)的兩行調中運動。由此可見,返璞歸真之中道諦,既不能停在“純割”一邊之極端,也不能停在“純樸”一邊之極端,而是同時保有“否定兩邊”(非割非樸)又“肯定兩邊”(即割即樸)的中道創造性。以上這種思維方式,任博克曾經透過“垃圾”的深刻隱喻(雌、辱、下、嬰兒等無用隱喻),把《老子》對“價值”和“非價值”的“非形上學式”“非二元論式”的“遍中論”思維給闡明得十分精彩(34)“你挖出那個器物的時候,同時一劃就有兩段,一段是肯定有價值的,就是器,你不要的那一部分就變成廢物,就是垃圾。但是你創造價值之物的時候,同時在創造垃圾,一挖出一個善,就破壞原來非善非惡的樸,而同時產生了惡。”換言之,建立一套特定價值體系,它所付出的犧牲代價或后遺癥,遠比我們想象的多。參見任博克、賴錫三《〈老子〉:“正言若反”“不笑不足為道”的“吊詭·反諷”之道》,《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第4頁。此文已收入賴錫三主編《老莊思想與共生哲學》,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107—108頁。。
五、不棄人不棄物的廣德襲明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1]70—71(《老子》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七章雖使用一連串“善”字,如“善行”“善言”“善數”“善閉”“善結”“善救人”“善救物”,但從具體內容看來,顯然具有不同凡響的吊詭性質。尤其從一連串“善”字底下的“否定性修辭”,亦即一連串動詞化的“無”來觀察:“無-轍跡”“無-瑕謫”“無-關楗”“無-繩約”“不用-籌策”,顯然《老子》的“善”,不同于一般正面指涉的“善”,反而是要經過“無”的去執去固的除病作用,才能調適上達于“不病之善”。從《老子》看來,一般意義的“善”只是透過與“不善”的對立來突顯自己,例如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但是這種“善/惡”嚴然分明的“邊見之善(或偏見之善)”,也很容易留下后遺癥:一者容易產生自我確信的道德固執,二者容易產生賤斥他人的道德暴力。換言之,一般意義的“善”,可能會帶來擇善固執的不柔軟、不寬容。所以第二十七章一連串的“去病之善”(才可謂“上善若水”的“上善”),正想透過“無-轍跡”“無-瑕謫”“無-籌策”“無-關楗”“無-繩約”的“無”之除病或解蔽作用,來柔化一般善行容易產生的固執與對立,調節轉化出“無棄人,無棄物”的柔軟之德、寬容之善。
第二十七章的“善”,若用第三十八章“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來呼應解讀,乃屬“上德”之善,而非“下德”之善。“下德”的“善”,處于善與惡對抗的一偏之善,它只能位于蹺蹺板兩端對立的其中一極。但第二十七章的“善救人”“善救物”的“(上)善”,并非取一端、棄一端的“下德”模式,而是“無棄人”“無棄物”的廣大包容之“上德”(或廣德)模式。這種能讓兩端和解、兩行相化的“上德”之善,第二十七章又將其稱為“襲明”。何謂“襲明”?“襲”,具有含藏收斂、因循調節意味。也因為能含藏并節制自是自見的“明”,所以才能因循對方的脈絡而“和光同塵”。透過“襲明”,才能“知白守黑”,才能夠兩行對話而調節極端,以防止掉入單邊的道德裁判。簡單說,“襲明”是為了轉化同一性視域的光之暴力,讓不同視域所帶出來的差異性明暗光譜,具有“黑白相守”“光塵和同”的交互對話性和廣德包容性。
若以莊來解老,《莊子·應帝王》的“渾沌之善”,約可呼應《老子》第二十七章的“上德之善”:“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2]309
中央之帝渾沌,對比于南帝之儵與北帝之忽,象征不落“南北兩端”“是非兩邊”“善惡兩極”,而是位于“和光同塵”“知白守黑”的“中央”之地,也因此中央帝才能促使“自是非他”的南北兩帝,重新遇合于渾沌之地而進行“兩行”交流。在這則寓言中,“渾沌待之甚善”的“善”和南北兩帝的謀報之“善”,兩善的性質相當不同。中央渾沌的“善”,正可謂“無棄人”“無棄物”的包容差異之上善(上德之善);而南北兩帝的謀報之善,卻是回到“自我觀之”的一端之善(下德之善)。而當故事總結在:渾沌的“上德之善”,被南北兩帝的“下德之善”給取代了(給謀殺了),也就暗示著“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取代了“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如此看來,第二十七章的一連串“善”之修辭,其實是要呼吁我們重新回歸“襲明之善”“上德之善”“渾沌之善”。只有這種經過“無”的去固去執之除病作用,才能轉化“兩極對立”而重新打開“兩行交換”。正是這種化“兩極”為“兩行”的吊詭修養,讓第二十七章對“上德之善”的描述充滿了詭辭意味。如何說呢?一般的善行不只會留下善跡,甚至想留下善跡來作為被傳揚歌頌的典范。但《老子》主張的善行卻是“無-轍跡”,就像《莊子·人間世》的“以無翼飛者”,它像春風化雨而潤物無聲,難以稱揚也難被仿效,不得而榮也不得而辱(35)成玄英:“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跡之可見也。”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7,收入《道藏》第13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頁。。由于吊詭智慧不讓自己停住在一偏之見,因此無法輕易使用社會俗眾的善惡體系、榮辱標簽,來簡單地將其定位、固定、追蹤、計算。
我們或許可以嘗試模仿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吊詭表達,將第二十七章表達為:善行無行(善行不固行)是以“無-轍跡”;善言無言(善言不定言)是以“無-瑕謫”;善閉無關(善閉不封閉)是以“不可開”;善結無結(善結不打結)是以“不可解”(36)王弼注:“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跡也。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謫可得其門也。因物之數,不假形也。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70—71頁。焦竑引呂吉甫語:“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轍跡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于不行,故曰善行無轍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唯得一而忘言者為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算。天門無有,辟闔在我,我則不辟,誰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纆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無轍跡;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筭而亂,雖有關楗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存于己者不能無敝,何暇人物之救哉?”《老子翼》,第68頁。。這樣的詭辭表達,看似曖昧難解,其實它只是運用“無”和“不”的除病作用,去極端化、去偏執化,以便保持“流動不居”“變化莫測”的無住狀態。換言之,吊詭之所以吊詭,正因為它在兩端之間而不住兩端(本書謂之“調中之道”),并且能不斷促成兩端調中地進行兩行對話(37)《老子》的上述觀點和表達,約可相應于《莊子·德充符》的觀點:“故圣人有所游,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圣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莊子集釋》,第217頁。筆者將其譯解如下:圣人處于“化而不固”的游化狀態(圣人有所游)。“知巧”經常異化成是非爭端的折磨,“誓約”經常墮化成脫開不了的黏膠,“德目”經常變成社交應酬的工具,“手藝”經常淪為販售自我的商品(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由于圣人不先謀略,所以不必依賴成心知見(圣人不謀,惡用知);不先砍傷破壞,所以不必事后黏合縫補(不斲,惡用膠);不去斲傷他人,所以就不必再用德澤去做額外的彌補(無喪,惡用德);不把人我關系當成利益工具,所以就不必去做商業利益的計量(不貨,惡用商)。。
也由于具備“無棄人,無棄物”的“襲明”態度,它才可能讓“善人”與“不善人”,從兩極互斥的對立斗爭,轉化為“和光同塵”的兩行對話,甚至變成“相師”又“相資”的互助互化。所以第二十七章總結在“善與不善”的“相師”又“互資”的共榮景觀:“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所謂的“善人”與“不善人”,如果能暫時松開固定化的標簽,轉從故事化的脈絡去嘗試同情理解,那么他們便可能具有互照功能,可以成為提醒彼此的好教材,甚至成為雙向學習、雙向轉化的共生資產。正是這種“善/不善”的“相師相資”,才真正顯現了兩行共生的玄同妙義(是謂要妙)。然而一旦只是一味地自是非他,一味地固執一邊之見,那么我們將舍棄“相師互資”的大好學習機會(不貴其師),也遺忘了雙向轉化的共生資產(不愛其資)。然而這種持一偏之見卻自以為是的小聰明(雖智),其實也是困在自我成心的大迷宮而走出不來(大迷)(38)關于此章的解讀,也可以從政治哲學的隱喻角度來詮釋,而把轍跡、瑕謫、關楗等視為政令聲教的過度規范,從而產生秩序體系管控下的棄人棄物之后遺癥,而《老子》的“無轍跡、無瑕謫、無關楗”等批判反省,則是為了思考更根源的療愈之道:“對《老子》來說,善救人者有一個很重要的脈絡:無人需救。善救物者,無物待救,這是《老子》對于所謂救人、救物背后脈絡的反省前提。當這個社會不再去制造‘什么人該救?什么人不該救?’時,是否它就是一個讓人可以自化自生的、完善周延的政治前提呢?”這種詮釋觀點和本文相通,但更強調它的政治性解讀。參見林明照、陳赟、賴錫三《〈老子〉:“無棄人,無棄物”的“和光同塵”之道》,《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第22頁。此文已收入賴錫三主編《老莊思想與共生哲學》,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154頁。。
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1]129(《老子》第四十九章)
道家的圣人,不從“自見、自是、自明、自矜”的自我角度和固常之心,來面對他人。正好相反,道家的圣人轉從“不自見、不自是、不自明、不自矜”的“無-自我”和“無-常心”,柔軟地回應他人與世界。以《莊子》的概念來呼應,一旦變成“常心”,就表示“心”被堵塞為“有蓬之心”,固著而成了“成心”(成見之心)。而《莊子》的“心齋”工夫,便在逆轉“成心”返回“虛心”,這樣才能“虛而待物”地讓一切差異性存在,獲得被納受的最大空間(“虛室生白,吉祥止止”[2]150)。大體說來,《老子》的“常心”與“無-常心”,相應于《莊子》的“成心”與“虛心”。而老莊圣人希望轉化“以我觀之”的成心之見,松解“常心”的一偏之見與一端之執,以百姓的思考為思考、以百姓的需要為需要,這樣才能容納百姓的差異角度和多元意見(以百姓心為心)(39)河上公章句:“圣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第188頁。朱謙之:“各本‘無’下均有‘常’字,敦煌本、顧歡本無。……圣人不私心自用,唯以百姓之心為心而已。”朱謙之釋、任繼愈譯《老子釋證》,里仁書局1985年版,第194頁。。“無-常心”的圣人,不高高樹立自以為是的美善標準,不硬用善惡二元的價值體系來框限并裁判百姓。由于不輕易黏貼“善”與“不善”的價值標簽,所以更能夠聆聽差異的眾多聲音(善者,不善者,皆能善之),也更能夠廣泛接納多元的不同故事(信者,不信者,皆能信之)(40)《老子》這種和光同塵、知白守黑的觀點,顯然不同于孔子“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的觀點:“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卷十六《子路第十三》,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46頁。換言之,孔子認為,君子對“好之”與“惡之”的價值標準是不宜含混模糊的。。
一般人視為善惡對立的同一性價值標準范式,如今被轉化為立場差異的價值多元之共生對話。對此,四十九章稱呼這種非二元對立、非道德裁判為“上德之善”(德善)與“上德之信”(德信)。這也呼應了第三十八章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關鍵在于,“上德”不固執(無常心)于自以為是、自以為對的道德標準,因此才能如“上善若水”般“善利萬物而不爭”。而“下德”太固執(有常心)于自是自見的道德框架,自以為能決斷價值的主流方向,結果造成與萬物爭善,反而難以避免道德裁判的光之暴力。《老子》的“德善”(真正“得善”)與“德信”(真正“得信”),提供了“和光同塵”“知白守黑”的廣德包容力道,它讓不同立場與脈絡的百姓們,可以找到自然自在的生長空間(41)有些版本作“德善”與“德信”,但有些版本也作“得善”與“得信”,即“德”與“得”相互假借。焦竑引蘇轍語:“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老子翼》,第121頁。焦竑引呂吉甫語:“猶之鑒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為形而已。圣人之視己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老子翼》,第122頁。。因此圣人回應世界或治理百姓的方式,必先將自己“有為有欲”的成心、常心,給予逆轉收回(歙歙焉),回歸于無作無欲的素樸之心(渾其心)(42)王弼注:“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于上,魚亂于下。是以圣人之于天下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130頁。焦竑引蘇轍語:“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圣人憂之,故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老子翼》,第121頁。。如此無為而“不見可欲”的素樸情境,也讓百姓的耳聰目明和機心機伶適可而止(不“注其耳目”)(43)河上公注:“注,用也。”陳鼓應指出:“指百姓競相用智,即王弼所注的:‘各用聰明。’”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及評介》,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71頁。焦竑引蘇轍語:“彼方注其耳目,以觀圣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老子翼》,第122頁。,自然回歸“為腹不為目”的素樸天真。
六、不主不宰的玄德上善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生、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1]136—137(《老子》第五十一章)
“道”雖然生畜、長育、亭毒(成熟)(44)高亨:“亭,當讀為成。毒,當讀為熟。皆音同通用。”高亨《老子正詁》,臺灣開明書店1987版,第109頁。另外,河上公本,亦作“成之熟之”。、守護萬物,卻又“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一方面,“莫宰其命”地化除自恃心態;另一方面,“常任自然”地信任萬物各隨環境形勢去展現自身。“道”對待萬物的“玄德”方式,呈現出尊重、信任、放開的“無為”與“無以為”(45)王弼注:“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是以謂之玄德也。”《老子王弼注》,收入《老子四種》,第44頁。河上公章句:“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見。”《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第197頁。林希逸:“然造物不有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道德真經口義》卷3,第715頁。。而在《老子》看來,這才真正能呼應于道的宏大無私、闊然容納,如第三十四章所謂:“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萬物歸焉而不為主。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1]85—86
“玄德”是去自我、去中心、去偏私、去宰制的修養。正是玄德這種“莫之命而常自然”的“泰然任之”,讓萬物(含百姓)擁有千姿百態的差異之美,讓萬物自然而然地自發生長去多元發揮。如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1]90—91(46)林希逸:“無為無不為,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道德真經口義》卷2,第709頁。如第三十二章:“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1]81也就是說,道與萬物最理想的狀態乃是道無為讓開而萬物自賓自化。也可說,道的莫宰莫命之“無為”玄德,最能“無不為”地任讓萬物自然而然的生生景觀。可見,玄德的精神在于讓萬物生機盎然地實現自身,而不是將世間萬物收攝于統一之道而只為彰顯道之權柄。事實上,《老子》的玄德不是為了榮耀道的主宰性,而是為了榮耀萬物的自發性。尤其只有在解構道的主宰性與控制性之后,反而才能讓萬物繽紛多彩地自賓自化。而人(侯王)最為可貴的“上德”倫理態度,宜效法大道玄德的“無為而無不為”,并將這種包容差異、欣賞多元的玄德倫理,運用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如此而能成就第五十七章所呼吁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1]150
另外,第十章最后也總結在:“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對此,王弼注得精彩:“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1]24經過一連串“抱一”“致柔”“滌除”“無知”“為雌”“無為”等自我轉化后,人才終于將自是、自見、自明、自伐、自有功等有心有為的甚深習性,給予“泰然任之”地松解開來。而王弼的“不塞其原”“不禁其性”“不吾宰成”,特別能對愛之適足以害之的“以愛之名”之“宰成”,給予批判轉化,以使“物自生”“物自長成”的“玄德”漸自浮顯。“玄德”者,“和光同塵”之玄同之德也。以其無偏愛,故能成其大愛;以其不私仁,故能成其大仁。玄德者,乃可呈現出“大愛不愛”“大仁不仁”“上德不德”的廣大包容與寬宥之德。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1]85—86(《老子》第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是用“水”來喻道,尤其運用流水無心無意、不分左右地開闊于四方而流敞滋潤,來比擬“大道”無作無意、不偏左右,卻能讓萬物無所分別地在大道遍泛、四方流溢中,獲得最大的適性自長(47)王弼注:“言道泛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86頁。河上公章句:“言道泛泛,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第136頁。。大道“生而不辭”“功成不有”,其謙卑而無言,從不夸大宣稱“榮耀歸于我”。《老子》這種“衣養萬物不為主”的表述(48)王弼注:“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85頁。蔣錫昌引成疏:“衣披者,覆育也……言道蓋覆萬物而不為其主也。”《老子校詁》,第227頁。,相當不同于榮耀歸于耶和華、歸于主耶穌的說法(49)王淮:“道創生萬物,但卻不自以為先天超越;愛(衣)養萬物,但卻不對萬物支配主宰,此與西方上帝之先天超越,對萬物可任意支配主宰如舊約中所述者,精神迥然不同。”《老子探義》,第137—138頁。。《老子》的“大道”像是無名英雄,它“無名”“無欲”“不為主”,它放開有心有意、有作有為,任讓萬物自賓自化、自我做主。可以說,這是把榮耀歸給萬物,而不是歸于自己。這也呼應于第五十一章的“玄德”:“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老子》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無為,體會人宜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玄德,并將其實現在人的政治倫理、生命倫理中,將“為之而有以為”的“下德”,轉化成“無為而無以為”的“上德”(50)《老子》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93頁。另參見筆者對第三十八章之疏解。。
以“道法自然”來說,道之所以“大”,不是它高高在上地突顯出主宰性,相反地,是在于它無作無為地“泰然任之”,讓出天高地闊的最大空間,讓萬物去自生自長。吊詭地說,道之“大”在于不自以為大、不自居為大。由于“不主宰”“不偏愛”,任讓萬物去自發生長、適性發揮,“道”才真正實現了既“可名于小(無為)”又“可名為大(無不為)”的吊詭性。為何用“小”來描述“道”呢?這是因為道雖“衣養萬物”,卻“常無欲”“不為主”,故“可名于小”。換言之,道的無作無意(無欲)、任讓無為(不主),正是“道”謙柔退讓地自居為“小”(51)林希逸:“泛兮其可左右,無所系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于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圣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谿之意。”《道德真經口義》卷2,第709頁。陸希聲:“大道之用,其猶鬼神之德乎。泛泛乎可在乎左,可在乎右。洋洋乎若在其上,若在其前后。為萬物之母,故恃之以生。與天地合德,故其功易成。以其親之至,故不謝厥德。以其大之極,故不稱有功。慈育萬類,長而不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則可以名其樸為小。萬物歸之不為其尊主,若川谷之與江海,則可以名其道為大。夫川谷之赴江海,受之而不厭,是未嘗自尊。天下皆歸圣人,圣人容之而不倦,是終不為大。圣人守無名之小樸,終不自以為大,所以為萬物之所賓,卒能成其大。”《道德真經傳》卷2,第16頁。。但這樣的“小”同時又屬于“正言若反”的“大”,因為“道”的這種“無欲”“不主”的“不自為大”(“可名于小”),反而才真正成全了萬物隨境而適性生長的最大可能性。如此一來,“不自為大”(自居為小),反而“能成其大”。所以三十四章要總結在“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可以這么說,愈能把自己縮小而愈加無我,反而愈能成全他人而包容廣大。《老子》第三十四章這樣的結尾,既顛覆了常人的小大之辯,也印證了“愈小愈大”的“正言若反”。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1]20(《老子》第八章)
《老子》喜愛“以水喻道”“以水喻德”,透過水意象來隱喻道與德。例如借由“水”的非實體性、可靜可動、流變、混融、就下、潤澤、柔軟等物之性情,來善喻“道”的流變不居、混融為一,來善譬“德”的不爭處后、潤澤包容(52)河上公章句:“水性善喜于地,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于牝動而下人也。水心空虛,淵深清明。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無有不洗,清且平也。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第29—30頁。。而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就是典型的透過“水”的“不爭”“就下”“處后”等“柔軟”性情,來啟發人們對“上善”的思考(53)林希逸:“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于道矣。”《道德真經口義》卷1,第700頁。。然要把握《老子》的“上善若水”,則需玩味其吊詭思維的“正言若反”。類似“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否定辯證,“上善”也要經過“不-善”的否定辯證,才能呈現真正的“上善”。唯經過對有心有意的“有為之善”(可謂“下德之善”),給予“不”或“無”的否定作用(除病去蔽),才能真正呈現自然無為的“上德之善”。為了避免“下德之善”造成“見可欲”的反效果(爭先恐后而民心更亂)(54)“上德”與“下德”的批判區分,語出《老子》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93頁。,第八章“上善若水”的“上德之善”,則轉而效法“水德”的“不爭”“處惡”,透過柔軟、接納、滋潤,讓事物在被環抱、被容受的共在情境中,自然自發地體現出生命風采與自在姿態。
由于“正言若反”的否定辯證與除病性格,“上善若水”或“上德之善”的“善”,其體現方式將不同于“下德之善”或“規范之善”的“善”。因此第八章所謂“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55)陸希聲:“上善之人若此水德,其居世若水之在地,其用心若水之淵回,其施與若水之潤澤,其言語若水之信實,其為政若水之清靜,其行事若水之任器,其變動若水之應時。”《道德真經傳》卷1,第7頁。的一連串“善”字,應該會與一般儒家所強調的“善仁,善信,善治,善能,善時”之“善”,有所差異。相較而言,先秦儒家的“善”,具有道德意志使命感在背后推動,欲將“心之所之”的仁心擴充至人、事、物,這種“善”既要真誠有心,也要勉勵有為去實踐擴充。換言之,儒家的仁心善端所實踐的善行,基本上建立在“志于道”的意志性、“據于德”的意向性等更為有心有為的明確支點上,期盼以我仁愛之心為支點來推擴仁愛之政的王道世界。但是《老子》的“上善若水”的“上善”,卻將“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的“為善去惡”,判為“下德之善”,因為那種“善”與“不善”的黑白分明,既可能導致善行規范的僵化,也可能造成對他者的差異性不夠寬容。而《老子》借由“水”不分東西、不別方圓,總是順隨情境而柔軟地環抱、納受各種差異情境中的事物,以讓不同脈絡的紋理得以被“廣德”納受,再暗示我們宜將“方向倫理”“判斷之善”,調節為無私無執的“差異倫理”與“慈柔之善”(56)有關道家的差異倫理,參見拙著之詮釋。《道家的倫理關懷與養生哲學》,第1—218頁。。
對于“上善若水”的柔軟之“善”,或許可用第四十九章的“德善”“德信”來呼應:“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也。”[1]129第四十九章的“德善”可解為“上德之善”,“德信”可解為“上德之信”。而“上德”所表現出來的寬容之善與寬容之信,不同于“取善棄不善,取信棄不信”的“一取一棄”之二元判斷,反而要對一般明確規范的“善/不善”“信/不信”的二分價值取舍系統,進行“和光同塵”“知白守黑”的兩行對話與調節轉化(57)林希逸:“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故曰得善矣。……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道德真經口義》卷3,第714頁。陸希聲:“茍百姓有好善之心,圣人亦應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輔之。茍有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化而為善,則天下無不善,百姓皆得所欲之善矣。至于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化之,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無不信矣。”《道德真經傳》卷3,第13頁。。對于《老子》,善體“上善若水”者,宜暫緩心中的道德意志和價值判斷,不預先將個我意志固化為“常心”,更不將個我“常心”加諸“百姓心”,反而宜效法“無常心”的水,柔軟、不爭、處下而“善利萬物”。此乃呼應于第四十九章的“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1]129。正因不固化的“虛心”“無我”之德善,才更能敞開“上德”的慈柔與“廣德”的容量(58)河上公注:“圣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百姓心之所便,〔圣人〕因而從之。”《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第188頁。陸希聲:“圣人體道無為,物感則應,應其所感,故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道德真經傳》卷3,第13頁。林希逸:“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我者無心矣。”《道德真經口義》卷3,第714頁。。
根據上述精神,“上善若水”的“居善地”,或可解讀為居下、居后的不爭之地,也就是讓自己柔軟退居于無為不爭、虛懷包容,而讓出最大的余地。而“上善若水”的“心善淵”,則是讓自己的“心”處在“淵兮似萬物之宗”的淵谷狀態,那是百谷匯聚諸水的“虛心若懷”之深淵,也是活水滾滾的涌泉淵源。而“上善若水”的“與善仁”,并非有心有意的一偏之善、一端之仁,而是讓“善者與不善者”皆獲得包容體諒的上德之善、無偏之仁。而“上善若水”的“言善信”,亦非有心有意的一偏之信,而是讓“信者與不信者”皆能獲包容體諒的上德之信、寬諒之信。至于“上善若水”的“正善治”,則非私心有為的強治管理,而是屬于“我無為”則民自化、民自正的“無為而治”。至于“上善若水”的“事善能”,將如水之柔軟無我而“能于不能”,放下自知自是的能,泰然任之地任讓百姓自發自能。至于“上善若水”的“動善時”,則是指水柔軟無我、流動不居,與時俱變而沒有固而不化的封常定則。由于“上善若水”有上述種種水德,而沒有“自是、自見、自明、自有功”(59)《老子》第二十二章:“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圣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55—56頁。的“爭先”“爭勝”“爭賢”,也就不會落入傷人傷己、患得患失的“咎尤”了(故無尤)。
《老子》上德之善和下德之善,我們還可用《莊子·應帝王》的渾沌寓言來呼應解讀: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2]309
寓言中,中央渾沌之帝的“待之甚善”,也是屬于“玄德之善”“上德之善”“上善若水”的善,屬于無心無為、忘仁義忘禮樂的包容之善。而南帝和北帝謀報給渾沌的善意,則已經淪為“下德之善”,屬有心有為、雕刻仁義的意向性之善,落入了《大宗師》所謂“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而中央帝的渾沌則是渾身是水的柔軟意象,而且渾沌所居的“中央之地”,也暗喻著:處谷、處淵、處下的虛懷不爭之地(“居善地”“處善淵”),因此渾沌的“待之甚善”,便可相應于“上善若水”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寬容上善,才能促使原本各自據德、各以為善的南帝與北帝(二元對立),重新相遇于渾沌的“環中”善地。我們可嘗試將南帝和北帝的兩邊對立,視為《齊物論》“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針鋒相對(如儒以厚葬為善,墨以薄葬為善;儒以禮樂教化為善,墨以節樂節用為善等),而渾沌中央帝則象征著“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的“環中”修養。此一環中(守中)狀態,不顯“自是、自見、自矜、自有功”,而能放開自我中心而轉為虛心、中空之玄德狀態,如此“虛其常心”的虛懷若谷,才能同時包容、聆聽不同的是非立場,并重新促成雙方展開“兩行”的共生對話。然而一旦中央帝被南北兩帝鑿了七竅,則代表落入了和南北兩帝相同的意志性活動和意向性思維,那也就代表渾沌離開“居善地”的“守中”狀態,如此也就喪失以“環中”轉化“兩端”的“上善”能力了。換言之,渾沌之死,代表著“上德之善”的失去,而漸被“下德之善”給取代了。從此以往,“善”與“不善”的相傾相軋,會逐漸失去“和光同塵,是謂玄同”的調節空間之轉圜余地。原來,渾沌所居的中央之地(居善地),是可以讓“光”(善者)與“塵”(不善者),都獲得被“善待”的“玄同”境地。一切的兩邊對立者,皆可獲得兩行轉化、調節更新之地,是謂“玄同”之“常德”(廣德),而可打開兩行共生的生機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