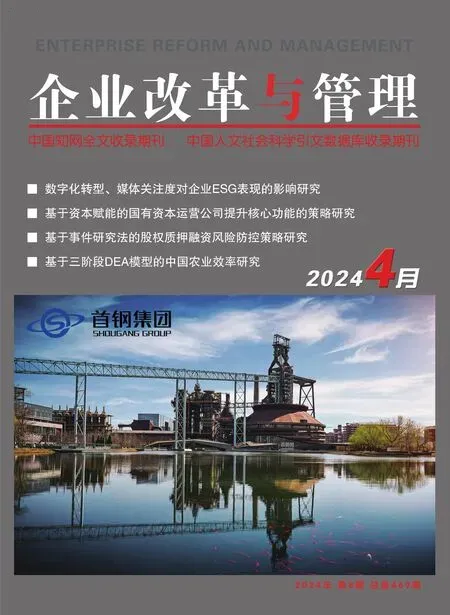企業知識轉移演進邏輯研究
——以湖南省衡陽市南岳區鄉村旅游企業為例
張靈丹 羅 芬
(1.湘潭理工學院商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0;2.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旅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4)
知識轉移作為促進知識重構和有效利用的重要方式,是鄉村旅游創新發展的重要動力[1],能夠有效激發鄉村旅游企業的創新活力[2],提高鄉村旅游企業的競爭力。實踐證明,高效的知識轉移有助于實現鄉村旅游區域內企業“增智”“增收”,對實現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貢獻。
鄉村旅游企業作為鄉村旅游區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知識轉移的主要主體。然而,鄉村旅游企業之間的知識轉移在現實環境下往往受生動力不足、流動頻繁、活動分散、信任缺乏、能力有限等問題制約[3,4],因此,研究鄉村旅游企業的知識轉移對促進鄉村旅游區域的創新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一)知識轉移
知識轉移是知識從發送方流動到接收方的過程,知識轉移的內容包括文字、圖像等易于表達和編碼的顯性知識,以及需要進行編碼否則難以表述的隱性知識。具體而言,知識發送方具有較強的發送意愿與目的,通過知識編碼、教授、交流等實現知識外部化;而知識接收方通過學習、感悟來實現知識接收,并轉為自身隱性知識,進而實現知識的內化與擴散。知識接收方通過獲取新知識來增加知識儲量,同時改變自身行為,實現行為創新。
(二)鄉村旅游企業知識轉移
近年來,大量鄉村旅游企業之間存在激烈競爭,但企業之間的知識轉移行為愈加頻繁,包括分享行業政策、設計產品、升級服務和管理經驗等知識實現轉移與共享。本文從知識發送方、知識接收方、知識特性、知識轉移情境四個方面來分析鄉村旅游企業的知識轉移。
知識發送方的發送意愿、發送能力、激勵因素、知識存量是知識轉移的主要影響因素。其中,知識發送意愿是知識轉移開始的重要步驟,與知識轉移的啟動呈正相關。知識發送能力由豐富的經驗、開放的溝通以及較高參與度等要素構成。激勵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干預、經濟回報、價值實現等對知識轉移效率的影響因素[5]。知識存量會影響發送內容,較高的知識存量能夠顯著提升知識轉移的成功率。
知識接收方的接收意愿、接收能力、激勵因素、知識存量是知識轉移的主要影響因素。其中,接收意愿包括接收意向、認可程度以及主動程度,與知識轉移效率呈正相關。接收能力是識別、評價、消化、轉化、整合和應用知識的能力,進一步可以分為適應性學習和主動性學習能力[6]。接收新知識需要付出時間、人力和物力等成本,激勵會提升知識轉移效率,缺乏激勵將導致拖延應付、虛假接受或公然反抗等行為[7]。
知識特性是影響知識轉移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從復雜性、內隱性、異質性三個方面研究知識特性對知識轉移的影響。復雜性是由于構成知識的元素數量多、結構組成復雜、各要素相互關聯程度較高,使企業內或企業間產生專業差距、知識儲量差異、知識理解能力差異。內隱性是由于隱性知識在組織間所占的知識構成比重高于顯性知識,知識的內隱性越強就越難以被發現和編碼,其可表達程度就越差,也就越難以轉移。異質性指在特定領域中知識的獲取與掌握必須依賴專業人士或專業技術人員操作和引導,與特定產業的知識積累過程密切相關。
當前,對鄉村旅游企業知識轉移研究的成果較少且散落于各類文獻之中,呈碎片化分布,大多聚焦于單一要素對旅游企業知識轉移或者企業創新發展的影響,對現代鄉村旅游企業的特殊性、鄉村性與知識轉移成效等方面缺乏系統的分析,但上述研究成果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與借鑒。
二、研究設計
(一)案例地簡介
本文選取湖南省衡陽市南岳區為案例地,原因如下:一是南岳區因旅游建區。南岳衡山和南岳大廟是南岳區的立區之本,1984年5月中央設立縣級南岳區,當年接待游客達66萬人次,旅游收入350萬元。二是南岳區靠旅游立區。多年來,南岳區大手筆、高標準實施文旅融合戰略,推出“旅游+非遺、演藝、鄉村、文創”等文旅融合新業態,旅游發展格局從“一山一廟”向“全域旅游”轉變,2022年接待游客1001.03萬人次,旅游總收入110.26億元,旅游業已成為南岳區的主導產業。
基于政策文件、關鍵事件的梳理,本文將南岳鄉村旅游企業的創新發展過程分為探索起步期、發展壯大期、提質升級期,重點關注創新發展過程中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探討知識轉移演進的內在邏輯。
(二)數據收集與處理
1.數據收集:從2021年4月至2022年7月,對區域內80家企業及10個村干部進行訪談,每人訪談時間約2小時以上,獲得有效訪談材料100萬余字,獲得比較豐富的一手資料。另外,搜集相關報道、文章、政府和各企業的文件、手冊、出版物等,收集到豐富的二手資料。
2.數據處理:首先,采取質性研究的主題句編碼方式,對資料進行主題句提煉與編碼,進行匹配性驗證。其次,利用Nvivo12 Plus對無效數據進行篩選,將有效數據進行細化、比對、整理。最后,通過開放式編碼形成高頻詞,主軸編碼系統概念化,在此基礎上,提煉概括性詞語得到核心類屬。
三、研究發現
(一)探索起步期(1984—2011年)
在探索起步期,區域內的企業大多剛剛起步,知識轉移和創新都處于初級階段。區域內的知識轉移的內容主要是政府主導的生態保護和發展鄉村旅游理念為主的隱性知識,并沒有形成良好的知識轉移網絡。
知識發送方。較高的知識存量是政府作為知識發送方的一個重要因素,南岳區委、區政府秉承生態保護理念,對基礎設施進行專項設計,堅持生態立村,把生態文明建設視為發展鄉村旅游的基礎。知識發送意愿是影響知識轉移的重要參考條件,為了加快美麗鄉村建設,南岳區政府積極組織自上而下的鄉村旅游相關知識轉移。這一階段,南岳區委、區政府較高的知識發送意愿、較強的知識發送能力、較強的知識存量為生態治理、發展鄉村旅游營造了良好氛圍。
知識接收方。該階段旅游企業大多規模較小,以小型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為主,是主要的知識接收方。接收意愿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資金短缺、人力資源不足、學習積極性不高、理念不認同或覺得實現難度大、思想保守致使對知識轉移內容不認可、自我滿足而不愿意承擔轉型升級風險等情況,導致知識接收意愿較低。接收能力方面,不同的企業對相同知識轉移內容的接收效果明顯不同,整體以被動適應性學習為主。由于存在分配機制上的矛盾,部分村民認為發展旅游是政府和旅游企業的職責,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知識的吸收效果。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鋼鐵積累不斷增加,廢鋼重鑄將逐漸增多,特別是表面鍍鋅等金屬回爐重鑄,高爐粉塵及灰渣中會含有鋅元素。因此,在高爐粉塵和灰渣中富集、提取氧化鋅逐漸成為關鍵固廢資源回收的熱點問題。我國鋅資源儲備豐富,分布廣泛,品位主要集中在1%~7.5%之間,品位大于等于6%以上的已探明鋅礦資源量僅全國總量33.3%[2]。高爐粉塵中回收鋅元素對低品位鋅礦的利用也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知識特性。此階段鄉村旅游知識轉移大多為隱性知識,主要是灌輸和傳播生態發展理念,知識隱性特征明顯,體現在日常的溝通交流中未形成正規的書面顯性知識。區域內采取參觀學習、會議討論、集中培訓、人員交流等多種措施來促進知識轉移。同時,區域內的企業或個體戶大多由農業轉型為鄉村旅游,存在知識水平不一、知識落差較大等知識差異,企業內上下級之間的知識異質性明顯。
知識轉移情境。許多旅游企業主住在城區,較近的地理距離降低了經濟、時間等成本,有利于知識轉移的實施。而在關系距離方面,主要表現為大型農業項目對政府的交易信任,主要形式為政府主導的點對點幫扶、指導和優化,而各企業主體之間的合作建立在物質契約信任基礎上,主體之間的交互程度與交互效率不高。
(二)發展壯大期(2011—2016年)
知識發送方。由于區域內各企業之間的聯系不夠緊密、自身實力限制等因素影響,知識轉移效率較低,不利于鄉村旅游產業的區域化發展。對此,南岳區委、區政府全面實施“旅游+扶貧”戰略,打出規劃引領、政策扶持、產業融合等組合拳,積極搭建區域知識平臺促進知識轉移,加強區域內各企業之間的聯系。該階段的知識轉移中傳奇文旅發展集團等企業積累了部分成功經驗,開始轉變為“知識發送方”角色,向準備產業轉型的企業和村民提供管理經驗。
知識接收方。本階段的專業知識轉移主要存在于企業骨干之間,骨干的個人素養對知識接收能力有較大影響,發揮“主人翁”意識,發展鄉村旅游促進脫貧致富的理念得到企業骨干的認可。從管理者層面來看,返鄉創業或學歷較高的個體經營者的知識存量比較高,知識接收意愿較強,吸收效果較好。知識接收方激勵因素主要表現為追求經濟效益、實現企業發展。各知識接收方為更好地適應發展趨勢,抓住“旅游扶貧”政策機遇以提升效益、實現企業轉型升級。從接收能力方面看,區域內的整體接收能力水平受主動性學習氛圍影響不斷提高,企業骨干成為知識轉移吸收的主體,區域內個體普遍形成主人翁意識,開始存在明顯的專業知識轉移,且企業骨干對專業知識的吸收效果良好。
知識特性。此階段的知識內容從上一階段的隱性知識逐步滲透到顯性知識,以隱性知識為主、顯性知識為輔,具體表現為從鄉村旅游概念轉變到具體的經營管理專業知識。同時,知識的發送和接收開始具備雙向依賴、雙向賦能的能力,龍頭企業開始轉移自己的成功經驗,知識的內隱性、復雜性特征明顯。隱性知識大多通過觀察模仿、研討培訓、區域會議、參觀學習和人員交流進行傳遞,而顯性知識主要通過產品手冊、活動策劃、品牌設計方案等顯性文件傳遞以及門戶網站、媒體等信息平臺傳遞。
知識轉移情境。在區域內旅游企業的關系距離影響下,知識轉移情境具體呈現為正式社會網絡和非正式社會網絡兩種形式。在正式社會網絡中,南岳區委、區政府深化旅游扶貧工作,以扶貧為抓手促進區域內社會網絡的規范化、緊密化,發揮黨員干部的帶頭作用,提升企業主及村民的學習熱情,促進知識轉移的實施。在非正式社會網絡中,主要包括家庭關系、鄰里關系以及由合作演變的友誼等,企業間的知識轉移主要通過企業主之間的非正式交流和相互模仿。總之,關系距離逐漸由企業對政府的交易信任轉變為企業之間的情感信任,從政府對企業的“點對點”幫扶進階到企業之間“線與線”的交流。區域內企業獲得了較高的經濟效益,強化了管理人員對脫貧致富理念的認同感。
(三)提質升級期(2016年至今)
知識發送方。傳統的經營方式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加之受新冠疫情的影響,逐漸出現游客數量下降、附加值低、回收周期長、市場波動影響大等瓶頸問題,企業的知識轉移意愿迅速增強,外在的政策支持也極大地激勵了區域內企業的知識轉移。2020年,南岳區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扶持獎勵政策,支持旅游新業態項目發展,激勵企業轉型升級。同時,就企業內部來看,企業內部采取日常考核、獎金激勵等相關措施促進員工在工作過程中運用新知識。
知識接收方。經過探索起步期和發展壯大期的知識積累,區域內企業的學習積極性不斷提高,進一步認同全域旅游發展理念,加深了鄉村旅游企業家和員工對服務、產品等類型知識轉移的認可,這一階段知識接收方的接收意愿較高,有利于知識轉移成果向創新演化。同時,區域內存在產業區域發展水平不均、市場匹配程度低以及專業人才短缺等三個關鍵問題。在知識接收能力方面,在濃厚的知識轉移氛圍中,形成了對新知識互助理解、共同消化的良好風氣,企業對知識的吸收已經轉變為主動性學習過程。
知識特性。區域內的知識轉移內容轉變為全域旅游理念體系化的專業知識轉移,包括以營銷方式、品牌建設、產品服務升級為代表的顯性知識和以理念認同為代表的隱性知識,知識的內隱性、復雜性、異質性明顯。具體表現為企業內外部之間知識元素構成眾多、結構較為復雜,各企業的人員、技術、資源等相互關聯程度較高,包括企業內部研發團隊、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外部供應商、政府政策等。因此,為克服知識特性帶來的影響,南岳區委、區政府采取了“人才輸送”“團隊支持”等轉移形式,如開展培訓沙龍、創客論壇、青年友好沙龍、屋場懇談等活動。
知識轉移情境。在關系距離方面,逐漸由對政府的“交易信任”轉變為對全區發展的“情感信任”再到對全區發展的“認知信任”。區域內的傳奇文旅、星域投資有限公司、貴妃凰菊等頭部鄉村旅游企業能高效吸收和轉化外來知識,帶來穩定的創新收益,使區域內的其他主體主動追隨。在知識距離方面,不同產業之間的企業主體逐步尋求合作、促進產業融合。全區在進行知識轉移可行性評估和知識轉移對象選擇時,大多以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為對象,其自身具備開展鄉村旅游活動的條件和知識儲備,同時部分第二產業企業也被邀請參與知識轉移過程,有利于增加知識轉移效果、促進產業融合。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南岳區鄉村旅游企業的知識轉移伴隨著創新過程的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理念上的知識轉移表現為從“走鄉村旅游發展道路”到“主人翁精神”再到“全域旅游”的進階,知識轉移效果逐步提高;專業知識上的轉移表現為從“鄉村旅游概念”灌輸到“企業經營經驗”的傳遞再到“體系化專業知識”的交換與接收,知識轉移的內容和類型影響了區域創新的類型;知識發送方主要是政府,隨著知識轉移的不斷深化,部分龍頭企業也逐步擔當知識發送方的角色;知識接收方主要是企業,企業的接收能力經歷了從“適應性學習”到“主動性學習”過程的轉變;知識特性中的異質性從剛開始的上下級異質過渡到跨產業、跨級別的異質;知識轉移情境從地理距離轉變為關系距離再到知識距離,其中關系距離經歷了“交易信任”到“情感信任”再到“認知信任”的強度變化。
(二)對策建議
針對湖南省衡陽市南岳區鄉村旅游產業,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政府層面的知識轉移策略。南岳區委、區政府作為推動區域發展的重要力量,應繼續發揮其引導和推動作用,從區域及企業層面制定更為具體的知識轉移計劃和制度,通過政策支持、資金扶持、稅收優惠等手段,引領區域區內的企業家、管理層及員工共享智力資源;同時,政府還可以搭建平臺,促進企業、高校、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交流,圍繞知識轉移進行深度合作,推動知識的流動和創新。
2.構建多方參與的知識共享平臺。構建“政府+企業+員工”的南岳鄉村旅游知識平臺,有效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和智力,分享鄉村旅游的最佳實踐、市場動態和創新理念,實現知識共享。此外,充分利用高校的教研優勢,鼓勵師生積極為南岳鄉村旅游發展建言獻策。
3.加強有利于知識轉移和創新的組織文化建設。南岳區旅游企業應從內部激勵機制著手,培養員工的知識管理意識,鼓勵他們分享知識、交流經驗。同時,企業也可以從外部聘請專業團隊,幫助企業進行知識重構與制度化建設。內外舉措緊密結合,確保知識轉移的效率和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