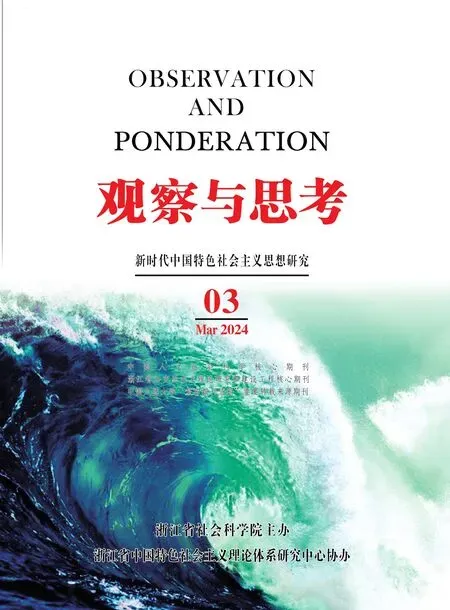“內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流行的成因與應對策略*
李鍵江 張子怡
提要:探究“內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流行的成因與應對策略,對于引導青年正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意義。在“內卷化”背景下,青年社會獲得感的缺失是青年“躺平”思潮流行的內因,主要體現為“習得性無助”降低青年的自信感、“主動污名化”宣示青年的抗議,以及階層焦慮導致青年斗志消沉。而亞文化中部分消極文化的流行與擴散是外因,主要體現為“喪文化”下青年情緒消解方式的扭曲、消費文化下青年認同危機的加劇、網絡文化下核心價值觀對青年引導作用的削弱。為了應對青年“躺平”思潮的不良影響,亟待加強心理健康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建立健全青年社會經濟保障體系,甄別研究青年合理社會利益訴求,強化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引領。
伴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網絡技術的躍遷式發展,人們的現實生活與網絡環境相互滲透,尤其在當下,“內卷化”與“躺平”之類的網絡熱詞備受媒體與社會大眾關注,關注者以正廣泛參與社會勞動的青年群體居多。縱觀上述網絡熱詞的發展軌跡可知,“躺平”因其傳播廣度、與青年群體關系密切性及對青年群體的影響深刻性等特征,或許能被理解成一種社會思潮,且“躺平”思潮的流行有其獨特的現實基礎與形成原因。此外,“躺平”也與當今的“內卷化”社會背景關系匪淺。具體而言,“內卷化”可用來指稱一種無實際發展的社會形態,即社會呈現出一種“惡性斗爭頻繁”“高度內耗嚴重”的現實狀態,在“內卷化”的現實背景下,“躺平”成為了青年在互聯網上熱議的主要話題之一,甚至不少青年在互聯網平臺公開發表“躺平”宣言,青年“躺平”正成為繼“佛系”之后的又一潮流。但青年作為國家和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主力軍,如若選擇“躺平”,終歸不利于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因而必須對“內卷化”與“躺平”的現狀、成因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系加以深刻審思,以找尋矯治的正確方法。
與此同時,有關“內卷化”與“躺平”的研究在不斷增加,有的研究將“內卷化”與“躺平”當作有著鮮明網絡文化特征的青年亞文化形態,表明它們正以趣味性的調侃方式昭示對主流社會和文化的抗爭與挑戰,①參見付茜茜:《從“內卷”到“躺平”:現代性焦慮與青年亞文化審思》,《青年探索》,2022 年第2 期。有的研究將“內卷化”與“躺平”都理解成時代變遷過程中青年群體的不同社會心態。其中,較多學者的觀點認為,青年群體選擇“躺平”是由于“內卷化”作為低水平、無意義的社會競爭形態消耗了自身的奮斗意愿與精神,導致青年群體的發展動力與精神內驅力不足,“躺平”實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反抗。②參見林龍飛、高延雷:《“躺平青年”:一個結構性困境的解釋》,《中國青年研究》,2021 年第10 期;令小雄、李春麗:《“躺平主義”的文化構境、敘事癥候及應對策略》,《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2 期。也有學者認為“躺平”與“內卷化”之間具有重要的因果關聯,破除社會“內卷化”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躺平”對于青年群體的不利影響。然而,目前很少有研究將“內卷化”作為社會形態、“躺平”作為社會思潮進行拓展與分析,因此,筆者試圖對“內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的形成原因及其應對策略展開深入研究,以期為其他學者針對青年“躺平”思潮的研究及尋求治愈之策開拓思路,提供有益借鑒。
一、“內卷化”與“躺平”的內涵與聯系
(一)“內卷化”:無實際發展社會形態的客觀反映
“內卷化”,即Involution,也譯為“過密化”。根據其特定含義,“內卷化”狀態是對無實際發展社會形態的一種客觀反映,也可用來描述社會發展的停滯現象或某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基于“內卷化”是社會形態的視角看,社會發展水平與個體能力發展水平是不同步的,社會由于對高質量發展目標的追求表現了對發展與競爭的迫切性,個體在有限能力水平的約束下也渴望融入當下的競爭形態以促進自身發展,由于社會競爭是社會群體的全面參與,有些個體在奮力向前與追趕不及的雙重影響下,會普遍選擇不斷提升競爭水平進而抬高自己的價值和地位,以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速度與趨勢,促使公眾的工作與生活形成一種尤為激烈的社會競爭狀態,而這一社會形態即稱之為“內卷化”。由于社會資源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均衡特性,社會大眾的日常工作與生活過程中存在著過多的競爭,且這種競爭大多是一種無意義的自我消耗,并未使得個體的社會生活產生實際性的發展與進步,因此可以說,當下的社會發展狀態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內卷化”的社會形態。
關于“內卷化”概念的起源,其最早由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提出,他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將“內卷理論”與“演化理論”進行了區分,并指出內卷是與進化完全區別開來的事物演進方式。①參見[德]康德:《判斷力批判》,宗白華、韋卓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年版,第85 頁。此后,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Alexander Goldenweiser)將“內卷化”用來描繪“某種文化模式在達到某一特定形態后既無法保持穩定狀態又無法突破自我,只能在內部變得更加精細化與復雜化的文化現象”②Alexander Goldenweiser,“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6,pp.99-104.。隨著之后的發展,“內卷化”真正成型于格爾茨針對瓜哇島農業發展的相關研究,他以“農業的內卷化”用來概括“農業因條件受限無法向外拓展,勞動力卻不斷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產中,為使人均收入不至于下降從而實現自我戰勝,只能使得耕作不斷趨于精細和復雜化”③GEERTZ C,“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p.80-81.的過程,此定義對后續關于“內卷化”的研究和解釋具有奠基作用。黃宗智則基于中國社會情境對“內卷化”展開研究,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指出“內卷化”的要旨在于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單位勞動的邊際報酬減少,④參見[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版,第65-124 頁。其又在后續對小農經濟的研究中,把“增長”和“發展”區分開,說明了“內卷型增長”即“無發展的增長”。⑤參見[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版,第 21-93 頁。劉世定和邱澤奇將土地和資本類比作畫框、畫布和可以使用的繪畫要素,指出受畫框和顏色種類限制,繪畫只能通過增加色彩調配使畫作更加復雜化和精細化,生動形象地講明了格爾茨所講的“農業的內卷化”的深刻內涵。⑥參見劉世定、邱澤奇:《“內卷化”概念辨析》,《社會學研究》,2004 年第5 期。美國學者杜贊奇則通過對國家政權的“內卷化”現象的研究,提出了“政權內卷化”的概念,指明國家機構通過對舊有的國家和社會體系及其職能的重復、延展與精致化,借此實現行政職能的擴大。⑦參見[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09-211 頁。
總之,“內卷化”雖外在表現為數量的增長,實質上卻并未實現發展水平的提升。從發展系統角度理解“內卷化”,可以看出,“內卷化”社會形態下的社會發展系統表面呈現的是一種“虛假的進步”狀態,實際是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發展系統內各要素所謂復雜化、精細化的發展,只是系統在某一發展水平上的不斷重復與延展,是無意義的重復,受系統本身發展規模和條件的限制,系統最終無法真正提升自身發展水平。因而,結合社會發展情形來看,“內卷化”是對無實際發展社會形態的客觀反映,精確描述了一種社會中存在普遍無效競爭的社會發展形態。
(二)“躺平”:青年“低欲望”社會思潮的現實呈現
關于“躺平”,學界尚未對其進行明確界定與概括。現實生活中“躺平一族”“躺平主義”“躺平學”的出現與流行,使得現今“躺平”在網絡上極具熱度,一度成為談論的焦點。一般將“躺平”定義為:一種青年群體以無所作為的方式反叛裹挾,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外在環境對個體規訓的順從心理。教授儲殷認為,“躺平”可以與生活中的頹廢、消沉和玩憂郁相提并論。白巖松指出,“躺平”是青年個體一種缺乏動力、不焦躁的生活狀態。范榮認為,“躺平”是指一種無欲無求、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的狀態,與“喪”“宅”“佛系”等異曲同工,并且有悖于中國傳統文化推崇的“自強不息、奮斗向上”的精神品質。①參見范榮:《莫用“躺平”誤讀奮斗著的年輕一代》,《北京日報》2021 年6 月2 日。客觀地看,“躺平”并非完全消極且一無是處,“躺平”是青年“低欲望”社會思潮的現實呈現,描繪出青年一代降低自身欲望、反抗“內卷化”的姿態,其所處的狀態暫且可稱為一種“無欲無求”“就地而安”且遠離競爭與壓迫的處世狀態。大部分青年群體面臨無效率、無實質進步的“內卷化”競爭,察覺到自身的勞動投入最終并不會獲得理想的回報,不能使自己的獲得感與幸福感得到相應的滿足,于是選擇了適合自己生存的“躺平”方式。他們面對外界刺激,會堅持自己所思所想,不會任意更改,會順從本心,不再執著追求眾人眼里的優質生活,暫時放棄追求上進與艱苦奮斗,盡量降低自身欲望,依靠適當的物質條件,甘愿享受低標準的生活,在自我降低負擔和壓力的過程中獲得內心的舒緩與安寧。
在內涵概括的基礎上,對“躺平”的深層意蘊進行剖析。“躺平”可作為一種社會思潮進行理解,其是對當前廣泛存在的、特有的社會現象的反映。社會群體中青年個體因為自身生活情境的驅動與外部群體情緒的渲染,不約而同地選擇“躺平”這一在社會中日漸流行的生活姿態,并利用群體力量在“躺平—族”中實現群體的自我強化與壯大,最后“躺平”通過網絡的傳播與發酵,逐漸在青年群體中形成一種廣泛流行的社會思潮。社會思潮是指某一時期內在某些社會群體中廣為流行,并對社會群體內成員的社會生活產生深刻影響且以一定的思想理論為核心的思想趨勢、價值理念或者理論體系;②參見浙江省團校課題組:《青年和社會思潮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04 年第1 期;佘雙好:《當代社會思潮對青年學生影響的新趨勢及應對策略》,《中國青年研究》,2015 年第11 期。社會思潮也可理解成反映某些特定階層或群體的利益訴求、為廣大人群所知曉和掌握、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對主導社會價值觀起消解作用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觀點。③參見佘雙好:《當代社會思潮的內涵、特征及其研究意義》,《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1 年第19 期。“躺平主義”雖缺乏深厚的文化內涵和理論基礎,但它在以青年群體為主的社會大眾間廣泛傳播,也鮮明地表達了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對青年群體的社會生活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如:使青年拒絕無效奮斗、選擇低消費,并且其所蘊含的消極的價值理念,也對主流價值觀起到了消解作用。因此,基于以上角度,“躺平”可被理解為一種社會思潮。作為與“內卷化”社會背景關聯頗深的一種社會思潮,“躺平”反映了青年群體“反感無效奮斗”“拒絕無意義內耗”的心理狀態,同時它也是青年群體的一種情緒宣泄與保持群體共鳴的重要方式,允許青年個體通過自身行為進行思想表達與行為抗爭。此外,“躺平”作為一種對青年群體具有深遠影響且趨同作用明顯的思想趨勢,與已知的消費主義、自由主義等社會思潮聯系密切。
值得強調的是,“躺平”社會思潮并非突然爆發形成的,而是有其漸進發展的演變過程與邏輯。就“躺平”的社會發展軌跡與文化發展趨勢而言,“躺平”是“喪文化”、消費文化及其他主流亞文化的一種最新的表現形式,其基本內涵與上述文化既相互關聯,又有所區別,因為“躺平主義”帶有時代賦予的新意,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若將“躺平”與早年間日本學者描述日本社會時所用到的“低欲望社會”或者“無欲望社會”相對照,可以發現“躺平”與“低欲望”有著幾乎一致的行為表現,且此行為表現貫穿于個體衣、食、住、行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不穿名牌、不吃大餐、不買房以及不生子。然而,“低欲望社會”是日本獨特的社會現象,受日本當時特殊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影響而產生,“躺平”則是中國社會發展情境下的特殊現象,在差異顯著的社會背景下,兩者各有其獨特的內在發生機制,因此,雖然表現形式幾乎一致,但在成因方面有著很大的區別。
(三)“內卷化”與“躺平”的聯系
“內卷化”是時代變遷和社會綜合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具有當下時代特征的社會形態,“躺平”社會思潮則是“內卷化”社會形態下的時代產物,“內卷化”的社會形態是滋養“躺平”思潮形成的土壤,兩者之間縱橫交錯的復雜聯系,最終發展成為一種顯而易見的因果關系。實際生活中存在的、與競爭相關的高度“內卷化”特征,會使社會群體不滿于參與無意義的內耗斗爭,容易引發社會大眾內心的浮躁與焦慮情緒,廣大青年群體是不愿被迫融入和適應“內卷化”的社會形態的,在身體與內心兩個層面都拒絕卷入無效斗爭當中,也會相繼選擇“躺平”的心態或者姿勢,進而在全社會形成一種“躺平”的社會思潮。“躺平”社會思潮與“佛系”“喪文化”等亞文化在青年群體中的滲透息息相關,最后由于受到“內卷化”社會形態這一誘因的激發,從而實現了自我的擴散與成熟發展。“內卷化”的社會大環境下,個體有時會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種競爭當中,并遭受競爭失敗的頻繁打擊,不僅身心容易受到嚴重損害,還可能導致其徹底喪失向上拼搏的斗志,主動選擇“躺平”或許是對個體身心的一種自我保護,可以幫助個體在內心建立牢固的“圍墻”,以抵制外界不利社會環境的侵害。
同時,從積極的角度來看,“躺平”也是一種個體抗擊“內卷化”的方式,通過減輕自身壓力對抗社會不斷施加的“壓迫”。當下,中國正處于經濟與社會發展轉型期,開始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發展階段,因而進入一個同質化競爭激烈的過渡期,此時,中低水平的供給過剩,在社會總體資源一定的情況下,使得生產與就業等社會活動因要維持競爭力而造成個體壓力過大。①參見張立偉:《應該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讓年輕人不再無奈“躺平”》,《21 世紀經濟報道》2021 年5 月27 日。通過實施青年勞動教育培育具有持續奮斗精神的青年一代,是黨在新時代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迎接新形勢下社會勞動環境改變帶來挑戰的需要,②參見常宏宇:《黨的青年勞動教育:演進邏輯、基本經驗及未來展望》,《重慶社會科學》,2021 年第8 期。現實勞動環境賦予青年群體較大的壓迫感,青年作為勞動主體無力改變大環境的影響,但也不會一味地被迫接受,因此無奈之下只能選擇自我回避,其選擇“躺平”看似不爭氣、沒志氣,實則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據此可知,應秉持客觀態度正確,理性地看待“躺平”,需明白選擇“躺平”有時不是出于青年群體的內心意愿,而是受到社會大環境的驅使,尤其是容易受到當前激烈競爭的“內卷化”環境的影響。在實際生活中,少數人的力量難以抵抗大勢,“內卷化”的社會形態短期內難以被改變,它造成的消極后果也在不斷侵害著當代青年群體。在萬物皆可卷的“內卷化”社會形態下,競爭不可避免,個體不免會被卷入各種競爭中,其中不乏無情且殘酷的惡性競爭,青年不畏懼競爭,但會厭倦個人的諸多努力只能得到微薄的回報,也會不甘于參與競爭的結果是無效或是失敗的,以致于產生深深的無力感、無奈感,由此會覺得心累、迷惘、沮喪,從而變得屈服和順從現狀,且容易逐漸喪失上進心與拼搏斗志,最終青年個體的消極情緒利用網絡平臺在群體間不斷擴散,并在青年群體間滋生“躺平”思潮。
二、“內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流行的成因
(一)內因:青年社會獲得感的缺失
1.“習得性無助”與青年的自信感降低
“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這一現象或機制,最初由美國心理學家賽利格曼在研究動物行為的實驗中發現,該心理學家隨后證實人的行為表現也具有并適用此種現象。賽利格曼將人在經歷諸多失敗與挫折之后,察覺自身對事物失去掌控力并對改變事情結果無能為力,造成的面臨問題時會表現出無所適從、喪失信心、消極無望的特殊心理狀態與行為定義為“習得性無助”。①參見Seligman,M.E.P,&Maier,S.F,“Failure to escape traumatic shock,”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Vol.74,No.1,1967,pp.1-9.
聚焦個體實際生活來看,競爭的失敗、自我提升無望、實現自我價值不得,由此造成的習得性無助會帶給個體較大的負面影響,讓個體感到沉重的無力感與灰心感,甚至挫敗一個人的自信心,使其消極地面對現階段的人生。習得性無助不同于非習得性無助,后者雖然外在表現為“無助”,實則是以“無助”為外殼從而實現對社會現實的反擊,前者則是真切的、實在的“無助”。②參見杜駿飛:《喪文化:從習得性無助到“自我反諷”》,《編輯之友》,2017 年第9 期。就事物的原因而言,有著習得性無助心理的個體,通常傾向于將自己經歷的失敗歸咎于自身內部因素,如:素質能力低下,而不會歸因于外部情境或人員。就結果而言,習得性無助個體面臨無論怎樣努力都不能獲得理想結果的情形,會變得失落、失去信心與斗志,以致進行自我懷疑和否定,最終通常會選擇放棄奮斗和逃避現實。“內卷化”時代的到來,帶給多數人的不是競爭與成功的喜悅,而是種種失敗感和隨之而來的頹廢感,如若青年失去了對多數事情的控制力,是“事”戰勝了“人”,“人”敗倒在“事”的腳下,青年在降低自信感的同時,也會拒絕去努力、去奮斗,從而選擇“躺平”。
2.“主動污名化”與青年的無聲反抗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界定的概念可知,“污名”(Stigma)代指個體在人際關系中具有的某種社會不認可的、令人丟失臉面的特征,其提出的另一個概念“污名化”(Stigmatization),則用以重點強調某群體被不斷貼上負面標簽,群體或群體成員具有的某個或某些負面特征被擴大化,以致身份接連受損的動態過程。③參見Goffman E.,“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63,p.68.盡管被污名化的程度或高或低,但都會對所指群體自身聲譽、社會地位等造成一定損害,群體成員會因為自身帶有的不同于常人的不光彩的特性而遭受社會排擠或隔離,且除了受到社會大眾的歧視與排斥以外,成員也會進行自我貶低與唾棄。
而就青年“躺平”與“污名化”之間的關聯而言,青年“主動污名化”是指青年群體選擇主動貼上“躺平一族”的標簽,以此宣示青年的抗議,重點并非自嘲與“污名化”。實則“躺平”被污名化的程度并不深,帶有的否定與鄙夷的色彩不如以“葛優躺”等為代表的“喪文化”濃烈,社會群體對“躺平”的態度不一,否定與鄙夷有之,默許、贊成與鼓勵也有之。青年選擇貼上“躺平”的標簽,更可能是想將自身納入“躺平一族”的群體中,因為基于某些意義“躺平主義”是在宣示青年對“內卷化”社會形態的抗議。而一般來說無論是資源還是話語權,群體的力量更為強大,所以,此種舉措也可被看成是一種戰術,摻雜自嘲、戲謔與宣泄的成分,體現的是青年群體一種看似屈服而又不甘屈服的反抗方式。且正如蕭子揚等定義“主動污名化”時指明,“主動污名化”區別于“污名化”的特點是其屬于自我的主動接受、主動選擇,它的初衷和目的,更多的是一種自我的叛逆表達。①參見蕭子揚、常進鋒、孫健:《從“廢柴”到“葛優躺”:社會心理學視野下的網絡青年“喪文化”研究》,《青少年學刊》,2017 年第3 期。
3.階層焦慮與青年的斗志消沉
焦慮是夾雜著煩躁、不安、憂愁、空虛等情感體驗的一種心理狀態,焦慮多出現在個體心理落差大、對事物掌控力低、選擇機會多和重大不確定性等條件下,主體內在地感受到力不從心又無法放棄的一種狀態。②參見張艷麗、司漢武:《青年群體的社會焦慮及成因分析》,《青年探索》,2010 年第6 期。處于焦慮狀態的個體對困境、風險等情形高度敏感,有關研究結果表明,在社會轉型期,青年群體的壓力最大,因此,他們的焦慮程度也最為嚴重。其中,當代青年群體的階層焦慮表現得極為突出,究其緣由,向上流動的生存需求和困境造成的不確定性,是青年焦慮產生的個體心理機制,快速的社會變遷與轉型、社會流動渠道狹窄、少子時代青年的壓力和焦慮的迅速傳播則是青年的階層焦慮癥候不斷顯現的社會根源。③參見朱慧劼、王夢怡:《階層焦慮癥候群:當代青年的精神危機與出路》,《中國青年研究》,2018 年第11 期。
尤其是社會轉型期內及“內卷化”社會形態下,青年群體所擁有的階層焦慮感還可能導致種種消極后果,容易引發青年對社會與社會制度的不滿,“求而不得”的挫敗感和“高不可攀”的焦慮感會消解青年的奮斗意愿,使青年喪失向上流動的蓬勃熱情,其會主動降低自身欲望,甘愿停留在自身目前所處階層,變得斗志消沉,甚至選擇主動“躺平”,與當初努力奮斗的自己形成鮮明的對比。青年群體本是有著滿腔熱血的群體,理應充滿赤忱之心與拼搏斗志,并且會因為不滿于一直停留在低層或底層,從而希望拼盡全力向上游的中層和上層挺進,對財富和地位有著更大的向往與期待是青年群體所獨有的特性,因此,巨大心理落差下青年的階層焦慮顯得更為嚴重與突出。此外,社會階層固化容易加劇階層焦慮對當代青年的影響,社會階層固化表現為上等社會青年階層的“世襲化”、中間社會青年階層的“下流化”、社會底層青年階層的“邊緣化”,絕大多數沒有背景或者關系的青年想要依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愈加增大,最終只能無奈地停留在底層或者中低層社會,④參見熊志強:《當前青年階層固化現象及其原因探討》,《中國青年研究》,2013 年第6 期。由此激起社會中部分普通青年的階層焦慮感,使其喪失斗志,最終選擇“躺平”。
(二)外因:亞文化中部分消極文化的出現與擴散
1.“喪文化”下青年情緒消解方式的扭曲
“喪文化”曾因“廢柴”“葛優躺”等話語成為大眾熱議的話題,具有很高的辨識度和感染力,也是青年群體所熟知的一種流行文化,無形中為社會個體的人生選擇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向。“喪”帶來的比較突出的好處,如:舒適、壓力小,慢慢誘導青年選擇此種生活方式及人生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躺平一族”的產生。同時,“喪文化”在誘導青年以錯誤方式去宣泄或釋放負面情緒,促使其選擇用消極行動化解自己的內心矛盾以及自己與社會的矛盾沖突。
“喪”,顧名思義,是一個相當消極的詞匯,多用來指不知理想、無所作為。“喪文化”散發出的喪氣、不思進取等負能量,對主流文化所倡導的價值理念是一種顛覆性毀壞,不利于青年建立健康、正確的價值觀。青年或許剛涉足社會但也遭遇了不少打擊,或許已在競爭激烈的社會浸淫許久,正處在精神崩潰的邊緣,而亟需一種功能強大的精神藥劑以治愈其內心創傷,并幫助其振作精神重新迎接生活的挑戰。而有的青年可能自我信念本就不堅定,個人的辨別能力薄弱,尚未形成成熟的世界觀、人生觀,非常容易受到消極文化的錯誤誘導。若不論及“喪文化”的價值取向問題,其是相當契合當代青年的精神需求的。因此,“喪文化”發揮了自身獨特的“優勢”,用它的“彩衣”蒙住了青年的雙眼,迷惑青年,使其選擇了消極的、錯誤的方式去釋放自己的負面情緒。更有甚者,部分青年不僅態度上表現相當頹廢、萎靡,還在行動上完成了“喪”的自我升級,選擇了“躺平”的生活姿態,對賺錢、晉升、消費、娛樂等活動都不再熱衷,只是一味地堅持己見,盲目地追求自由和自我解脫,看似掙脫了社會與倫理加于其身的沉重枷鎖,實則也游離在集體、社會之外,游離在現實世界主流價值觀之外。
2.消費文化下青年認同危機的加劇
消費文化是指特定時期和社會背景下,人們在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生產活動中綜合表現的、與消費有關的思想理念和行為方式。①參見黃智君:《消費文化與青年認同危機》,《青年探索》,2006 年第5 期。消費是社會個體的一種經濟行為與生活方式,在當今社會,消費商品的風格和種類在快速變化,時尚消費品日新月異,消費主流支柱卻未發生較大改變,并在此方面表現趨向同一的消費主義傾向,即房、車等標記個人社會地位與價值的物品仍持續地受人吹捧。所謂認同危機,重點是指人的一種內在的自我認同,在個體對自己過往經歷進行深度反思的過程中形成,并最終內化于心,②參見王成兵:《消費文化與當代認同危機》,《江海學刊》,2004 年第2 期。而出現危機代表著人的自我價值感、自我意義感的喪失,③參見[美]羅洛·梅:《人尋找自己》,馮川、陳剛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45 頁。即說明人在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過程中,慢慢地失去了對自我的定位,找不到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現代消費現象和消費文化正醞釀著當代多數青年的認同危機,消費不起的高檔商品或房、車等高昂商品使得青年的自我價值感逐漸降低。在“內卷化”背景下,部分青年只能從自我消費中獲得少量的滿足感和自我認同感,恰逢某些較為偏激的消費心理或消費理念甚囂塵上,使青年的認同危機逐漸加劇,有時甚至達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當今社會常以“高薪”標榜“能人”,多數個體潛意識里認同“消費得起”代表著“能力出色”的觀念,所以,社會個體也時常通過各種消費來展現自己的生活格調與品質、社會地位及價值,雖然高檔消費不可與高社會地位劃上等號,但社會大眾對此種消費行為趨之若鶩。過分追求時尚用品和高檔消費反映公眾比較畸形或偏激的消費心理,不僅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悖,同時也體現了個體價值觀的扭曲,在一定意義上引發并加劇了青年的認同危機,導致青年進行自我否定與懷疑,最終促使其選擇“躺平”。
3.網絡文化下核心價值觀對青年引導作用的削弱
網絡文化主要指網絡青年亞文化,是青年群體受自身面臨的突出現實問題和社會矛盾所影響,不斷在網絡空間發表顯示自身個性的觀點,逐漸形成的一種獨特的話語表達體系和價值判斷邏輯。④參見平章起、魏曉冉:《網絡青年亞文化的社會沖突、傳播及治理》,《中國青年研究》,2018 年第11 期。2023 年11 月8 日,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發布重要成果性文件——《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23》和《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3》兩本藍皮書。藍皮書表明,截至2023 年6 月,我國網民規模和互聯網普及率分別達到10.79 億、76.4%。①參見《2023 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發布藍皮書: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達76.4%》,《中國證券報》2023 年11 月9 日。互聯網的普及與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網絡文化提供了廣闊的塑造與傳播空間,接踵而至的網絡流行文化在網絡空間形成一種亞文化的狂歡,“宅文化”“喪文化”“佛系文化”等不同形態的網絡亞文化皆可歸納其中。
而“宅文化”“喪文化”等盛行的網絡青年亞文化,卻在某些意義上削弱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青年群體的積極引導作用,致使互聯網的主要使用者即廣大青年群體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出現偏差,較大程度上催生了“躺平一族”的出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全體人民共同價值追求的精華和結晶所在,長期占據中國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對社會風尚和公眾自身的良好向上發展具有重大引領作用,且可以幫助青年群體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顯而易見的是,受某些不積極或不健康的亞文化影響而產生的“躺平”社會思潮,其所傳達的“追求安逸和享樂”“厭倦努力和競爭”的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弘揚青年正能量”“樹立堅定且遠大的理想抱負”的價值理念相背離,可見,某些流行的網絡青年亞文化雖不占據主流地位甚至是處于邊緣化地位,仍能依靠自身的傳播力與感染力在網絡世界創造一種“文化狂歡”,替代主流價值觀影響力的同時對青年群體的價值取向造成消極的負面影響,其破壞力之大也不言自明,值得警惕并應著力加以矯正。
三、“內卷化”背景下青年“躺平”思潮的應對策略
(一)加強心理健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網民、學生……都容易產生心理健康問題,包括心理壓抑、心理自卑、心態失衡、焦慮癥、強迫癥、抑郁癥、孤獨癥等。……要引起高度重視。要加大心理健康問題基礎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識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規范發展心理治療、心理咨詢等心理健康服務,加強心理健康專業人才培養。”②習近平:《論黨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8 頁。這就為新時代我們進一步加強心理健康公共服務及其體系建設指明了方向。
“喪”“頹廢”“佛系”等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描述性詞匯,說明當下的青年群體有著較差或者非常差的心理狀態,也表明他們迫切需要專業的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服務。因此,國家和政府亟待加強心理健康公共服務及其體系建設,包括但不限于社區、共青團、社會團體等組織的心理服務設施建設,因為青年群體更需要一種免費的公共服務產品,在緩解其經濟壓力的同時幫助解決自身出現的不良心理狀態問題。心理健康公共服務是指可以被廣大社會公眾所享有,負責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咨詢、教育、治療、輔導等活動的總稱,③參見吳衛東:《論和諧社會建設中心理健康服務體系的構建》,《繼續教育研究》,2011 年第10 期。其中所指的心理健康,若說是一種特質,不如說它更像是一種會因為個體生活的外界環境和時代背景發生改變而變化的心理狀態。④參見師保國、雷靂:《近十年內地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回顧》,《中國青年研究》,2007 年第10 期。當今時代各種消極亞文化的流行,無不反映青年群體焦慮、絕望、頹廢等較差的心理狀態,青年群體面臨著買房、買車、結婚、生子等巨大壓力,因渴望突破階層牢籠而自發向上奮斗,卻遭遇了不少的挫折和打擊,他們內心煩躁、苦悶、無奈等情緒無法消解,以致青年群體選擇以在網絡上自嘲、自諷的方式來宣泄和化解負面情緒,或者選擇加入“躺平一族”的隊伍來消極地應對生活。
政府作為社會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需發揮自身優勢對青年更廣泛地提供高質量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務。例如:可以適當建立線上或者線下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務專業機構,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形式,擴大服務的受眾面,提升針對性,可以完善或健全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立包含心理咨詢、心理治療、心理輔導和心理教育在內的,針對多種服務對象的多層次的服務機制。①參見張華:《青年壓力來源與社會支持系統優化策略》,《當代青年研究》,2012 年第3 期。最終能夠幫助青年群體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和意志品質,強化青年自身的健康心理建設機制,促進青年身心健康向上發展,有益于幫助其發揮自身潛能,提高青年適應和融入社會發展的能力。
(二)建立健全青年社會經濟保障體系
社會發展轉型期內社會結構及體制變遷與青年發展的個人軌跡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使得經濟壓力成為現階段青年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并具有普遍性和持續性。隨著時間推進,青年自身壓力在不斷累積,卻不能得到社會機制與政策體系的有力保障,更多時候只能依靠自己微弱的力量去化解壓力。②參見王小璐、風笑天:《青年何以“暮氣沉沉”——基于轉型期青年壓力的分析與反思》,《中國青年研究》,2014 年第1 期。青年群體正處于社會財富積累與社會地位創建的關鍵時期,同時肩負家庭與社會的期盼,他們面臨的壓力有時會比較大,且因為是自我奮斗時期,家庭能給予的幫助有限。青年群體雖不屬于經濟水平低下的弱勢群體,但在“內卷化”社會形態影響下的青年社會經濟保障問題依舊值得關注。由青年群體社會經濟保障難題所引發的心理、生理等問題,需要得以妥善解決。
為改善青年群體的生存環境,在一定程度上遏止青年“躺平”思潮的傳播,政府需要建立健全青年社會經濟保障體系,逐步改善以青年民生為重點的住房、醫療、就業、養老保障體系,加快住房保障體系向新生代中低收入青年的覆蓋,優化青年住房公積金和住房補貼制度,強化城市長租公寓的管理與監管,積極推動“租購同權”政策落到實處,保障青年群體“住有所居”進而實現“安居樂業”;擴大青年醫療保障的覆蓋面,增強青年的健康保障感和身心安全感;加大就業培訓并提高青年的就業創業能力;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以減輕青年養老負擔和壓力。③參見聶偉、蔡培鵬:《讓城市對青年發展更友好:社會質量對青年獲得感的影響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21 年第3 期。
(三)甄別、研究青年合理社會利益訴求
“躺平”社會思潮的盛行以及“宅文化”“喪文化”“佛系文化”等的流行,都從側面反映了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位于中低階層的青年個體的話語權有時實在薄弱,青年群體發聲需要利用一定的技巧以匯聚話語力量,才能使其利益訴求被社會所識別和關注。由此,利用網絡平臺表達利益訴求成為青年開展訴求行動的主要方式,此種方式也使得青年訴求的表達和實施變得更為快捷、有效。“內卷化”背景下青年的利益訴求,可以具體概括為需要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和合理的向上流動渠道、希望機會和資源能夠被平等享有、渴望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和惠及廣大群眾的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青年群體在內心有著多種訴求的同時,也希望訴求能早日得到滿足,其心理和思想狀態會因為社會壓力的激增而變得更加脆弱,若他們切身、合理的利益訴求不能實現,將不利于青年成長,容易使其走上錯誤的發展道路。
政府需要加強網絡空間的監管力度,依托現有先進的網絡技術,盡力甄別青年群體多元、合理的利益訴求,政府也需要團結社會整體力量和善于利用社會組織的力量,幫助厘清和解決青年群體正當的利益訴求,同時建立適合青年利益訴求表達的更為適當、便捷、有效的渠道和途徑。隨著中國社會制度的日趨完善和成熟以及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中國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方式開啟了變革之路,從前社會運動的街頭動員、全民參與模式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時代的帶動下,青年群體利益訴求行為開始轉向網絡平臺,并實現了向網絡轉型。①參見曾曉彬:《中國青年利益訴求的網絡嬗變與統戰路徑分析——基于網絡化創新治理的視角》,《北京青年研究》,2019 年第3 期。網絡平臺為青年群體提供了廣闊的情感表達、經驗交流以及學習討論的空間,活躍的網絡平臺成為當代青年最大的聚集地,從而方便青年在群體間產生強烈的群體認同感,也滿足了青年集聚力量為群體利益發聲的需求。
(四)強化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引領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沒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難以自立自強,一項沒有文化支撐的事業難以持續長久。青年是引風氣之先的社會力量。一個民族的文明素養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準和精神風貌上。”②習近平:《論黨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 年版,第21 頁。新時代,我們必須強化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引領作用,使廣大青年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有效抵御和克服“躺平”等錯誤社會思潮的不良影響。
在“內卷化”社會形態下,亟待加強社會主流價值觀對社會風尚和青年價值追求的引領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能反映國家的發展愿景和國民全體的共同價值追求,能極大地推動國家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并發揮中流砥柱的核心作用,也有利于青年群體思想道德素養的提高和健康向上發展,能夠幫助其堅定理想信念與實現價值追求,從而在物欲橫流的現實社會中堅強、勇敢地向前發展。因此,不僅應根據形勢需要對價值觀的實質內涵進行完善,也需注重價值觀宣傳的形式,若宣傳形式較為單一,將致使價值觀倡導的內容因為形式枯燥等原因易被公眾所忽視。此外,亟需實現主流價值觀對青年自身存在價值和多元利益訴求的引導、認可和滿足,加強主流價值觀對青年群體的吸引力,進而引導青年樹立正確、適當的價值取向。
青年社會思潮的動向,反映的是當代青年的群體心態、利益訴求與價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③參見雷開春、楊雄:《我國青年社會思潮新動向及政策建議》,《當代青年研究》,2015 年第6 期。青年社會思潮或者青年亞文化并不會因為與主流價值觀存在沖突而自動消失,它們中既蘊含消極成分,也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因素,消極成分需要徹底否定和摒棄。其中,“躺平”社會思潮、“喪文化”等對主流價值觀有著顛覆與抵制的一面,對青年群體的行為思想、人生觀和價值取向有著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應徹底批判。在展開批判的同時亟待不斷完善社會主流價值觀,加強其對國民尤其是青少年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等方面的引領作用。④參見符明秋、孫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喪文化”治理》,《重慶社會科學》,2020 年第2 期。部分社會成員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定位與社會主流價值觀有所偏離,需要社會建立健全正確的價值引導機制,同時,社會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理應與時俱進以切實滿足青年群體需求和社會發展需要,并能夠善于利用青年社會思潮或青年亞文化的存在進行有效引導,對相關制度進行相應補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