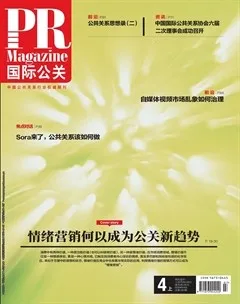自媒體視頻市場亂象如何治理
蔣楠
如今,互聯網的發展仍然如火如荼,并進一步深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據2023年8月28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10.79億人,其中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到10.44億人,用戶使用率達96.8%。互聯網不僅影響到社會公眾的吃穿用行等,還開始展示出其復雜、詭譎和難以控制的特性,尤其是公眾喜歡觀看的視頻產品,越來越多地出現一些低級、庸俗、乏味的片段或表演。在突發公共事件時,一些表達觀點的視頻產品變得十分活躍,發揮了不良的輿論誤導作用,如沖擊傳統價值認知,刺激社會情緒,攪動原本清晰的事件,翻云覆雨,顛倒是非,給公眾對事件的判斷帶來較大難度,不僅影響了公眾的情緒,更有顛覆公眾價值認知、攪亂社會公序良俗、影響青少年健康成長以及解構政府公共治理成效、破壞知名企業品牌形象、影響全社會長治久安等較大隱患。面對龐大的網絡視頻用戶市場,政府與平臺對網絡視頻產品的管理與規范面臨著巨大挑戰。
自媒體視頻市場呈現出特有的分類
在本世紀20年代,互聯網已經蓬勃興盛到人人皆可“自產自銷”的“視頻為王”時代。一些普通人經常把日常生活的點滴傳到網上,大量商家在視頻平臺上直播售貨,一些機構制作特別的視頻節目自話自說等等。今天,人們打開手機,在不進行通訊、信息溝通或購物的情況下,一般都會選擇點擊視頻作為消遣,網絡視頻產品每日的消費量極為龐大。總的來看,網上的視頻產品一般分為如下三類:
1.生活類,主要有推銷購物、講授生活技藝、分享育兒經驗、分享養生體會及生活瑣事等等;
2.信息類,如傳播時事新聞、高科技發明、突發事故、旅行見聞、奇聞軼事等;
3.評論類,對熱點事件、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社會名人、國家、國際大事等的評說。
前兩類的視頻產品盡管存在商業氣息濃厚、魚目混珠,難辨真偽的情況,但其對社會公眾的生活影響尚較小,相對來說比較為大眾接受,點擊率變化不大:愿意看的多看一些,不愿意看的也就直接翻頁過去。而第三類的視頻產品,則有些不同。它們看似沒有什么商業氣息,具有一定的傳播知識功能,內容貌似公允,但這些視頻產品中的一部分,內容上具有明顯的指向性,語言往往帶有一定攻擊性,內含社會煽動性,散布的信息有時比較驚悚,內容的真實性難以確定,甚至有杜撰、造謠、甚或網暴傾向,近年還出現了以“愛國”“公平”“正義”等名義來攻擊社會名人、知名企業或突發事件當事人等視頻產品。對于這些視頻產品,公眾的點擊率往往變化較大,有些內容比較極端的視頻產品點擊率可能在很短時間達到10萬+。這類視頻就是視頻市場中的“垃圾”產品。它們往往十分吸引公眾眼球,但其實內容空洞,子虛烏有,經不起推敲,但卻傳播力強,社會蠱惑性大,具有極大欺騙性,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嘩眾取寵,吸引社會公眾關注,挑起社會對立或不安,搞黑他人或企業,追求流量最大化。這種“按鍵傷人”的視頻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已經引起越來越多公眾的心理不快,也令一些企業擔心憂慮,并對今后視頻產業的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自媒體垃圾視頻已然成為社會公害。
自媒體垃圾視頻何以肆無忌憚?
今天,社會公眾看到的一些自媒體視頻產品,在一些突發事件背景下,往往橫空出世,興風作浪,呼風喚雨,故意與官方媒體逆反發聲,為追求流量無所不用其極,話不驚人死不休,標新立異,努力出格,甚至達到故意顛覆價值認知、毫無道德底線、無法無天的地步。自媒體垃圾視頻產品的制作者意欲何為,其真實目的昭然若揭。自媒體垃圾視頻何以在今天異常活躍,其原因有三:
第一,龐大的用戶群滋養了海量的自媒體視頻產品,幾乎每一秒鐘都會層出不窮地涌現出來,僅靠國家監管機構的抓取審查和平臺的常規監督是難以完成的。
第二,自媒體垃圾視頻產品具有一定的偽裝性,制作者在不斷地變換“馬甲”,改頭換面,以貌似合法合規的面目出現,令監管部門難以馬上識別出,平臺的監管更容易百密一疏。
第三,這些自媒體垃圾視頻在內容方面表現出伸張正義的模樣,選擇的話題往往直擊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迎合某些社會群體的心理痛點,致點擊率很快躥升,點擊和轉發的量短時間里可能達到巨大的數據。
陳立丹在《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中指出,“輿論是一種群體意見的自然狀態”。但是,“輿論有時十分憤青,有時又十分保守,并非時時代表社會的良知和發展方向。”在傳統社會環境中,輿論趨向于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監督的權力。但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能是電視臺,個個都是播音主持人。輿論的生態環境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傳統媒體的優勢被社會化媒體的喧囂消解到微不足道或驅趕到角落的程度,官方正規的信息渠道被無形中屏蔽或淡化,無數人打開手機,直奔視頻平臺,本來是要獲得信息、尋求快樂或消磨時間,殊不知無形中也把時間交給了視頻制作者,自己的大腦“被安排”了各種信息——你本想刷點笑話,但送到你面前的卻是魚目混雜的海量信息轟炸。
祭出市場淘汰機制,把垃圾視頻清理出局
現在,對于自媒體視頻產品的監管機制主要來自兩個方面:政府監管部門和播放視頻的平臺。每天海量的自媒體視頻產品,依靠政府的監管機構和平臺的自律審查,從力量上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在視頻市場上應該推出第三種力量,那就是公眾自我評判的力量,讓公眾對那些垃圾視頻產品點差評。
德國學者伊麗莎白 · 諾爾 · 諾依曼在《沉默的螺旋》中指出,在公開場合持有不同意見的人總是會保持沉默,他們往往是“大多數”人,傳播學上把這種現象表述為“沉默的大多數”。在一些公開或比較敏感的議題上,發聲的往往是叛逆的、浮躁的、或者喜歡顯露的一些人,而守法的、沉穩的、比較智慧的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數人,他們不愿意表達,不喜歡被人關注。然而今天,面對海量的視頻產品,這些“大多數”是視頻產品的受眾,他們拿著手機觀看,完全可以不再“沉默”,因為在視頻的播放平臺不再是一個完全公開的平臺,他們可以默默地表達自己的取向態度而不必擔心被人關注。但是,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的視頻播放平臺都僅僅設置了只允許他們表達贊成態度的按鍵,而沒有表達反對或排斥的按鍵:即只可以點紅心、點贊、關注、轉發或評論,這樣,社會公眾無法對一些虛假、低俗、惡劣的視頻產品表達明確的反對態度。盡管一些公眾在評論區可以闡釋自己的負面評價意見,但在視頻播放的界面基本上是看不到這一負面評價的,也完全不影響那些視頻產品的傳播,這是不公平的,其潛在后果也是嚴重的。
1.有“贊”而無“差”,會對社會輿論環境帶來不良影響。今天一些別有用心的視頻產品制作者正是利用平臺只有“贊”的正向功能設置在瘋狂獲取流量,他們完全無忌大量網民對垃圾視頻產品的反感或排斥,蠱惑一部分人賺取點擊量或制造刷量,任他們在平臺上興風作浪,制造事端,營造虛假的民意輿論形態,形成對健康社會輿論生態環境的侵襲,造成一種輿論假象,實則強奸民意,盜用民心取向,這種視頻平臺設置的缺陷該改一改了。
2.設置“差評”符號,讓“沉默的大多數”發聲。在網絡時代,每個人都能夠極為便捷地獲取社會信息,個體既是親歷者也是旁觀者,公眾發出自己的聲音已經不再變得困難,也不會有所顧忌。網絡輿論環境的公平性與低風險性,恰好便于讓那些原來的“大多數”發出自己的聲音,對于制作精良的視頻產品點贊或打紅心,對于垃圾視頻產品點差來表達自己反對的態度,讓它們從眼前消失,不再危害他人。如果一個視頻產品平臺只能允許用戶點贊,而不能點差,那對廣大的視頻用戶來說無疑是一種權利的剝奪,也不符合市場優勝劣汰的基本規則。
3.設置“差評”級別,對垃圾視頻產品進行市場懲戒與淘汰。目前,社會對于垃圾視頻產品的管理仍然用的是“看得見的手”:即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管與平臺的審查,其實市場早就該采用“看不見的手”來規范視頻產品的守法合規了。平臺可以通過“差評”淘汰機制的設置,以“紅牌罰下”的公眾監督力量,讓那些制作粗陋、虛假產品廣告宣傳、無聊低俗表演、以及懷有險惡用心的所謂知識傳授、熱點問題分析、歷史事件解讀等視頻產品退出平臺。具體做法如:公眾差評達到十萬加的視頻產品應永久禁入平臺;差評達到五到十萬萬的可直接退出平臺,并禁入3個月;差評達到五萬的,將不再出現在平臺,也自動禁止轉發。這樣,市場自動淘汰機制就會對那些垃圾視頻制作者形成一種制約或震懾力量,也能對政府監管、平臺審查形成一種積極的補充,三股合力打造清朗網絡空間,一定會讓中國的網絡視頻市場更加健康發展。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打一場網絡視頻市場的人民保衛戰,網絡垃圾視頻的危害與猖獗就一定能夠得到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