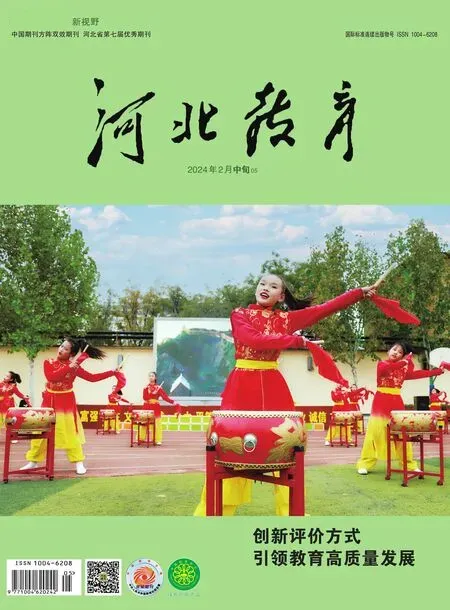生存與生命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呈獻
○ 邯鄲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李風林
“我的整個生命,只是一場為了提升社會地位的低俗斗爭。”
這句話出自意大利著名女作家埃萊娜·費蘭特所著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失蹤的孩子》,它被中文版出版社的編輯們選中,印在了腰封上。就憑這一選擇,本書中文版的編輯們就值得讀者多為他們點一個贊。這句話如霹靂當空,振聾發聵。無論是經過艱辛努力最終完成了社會地位的提升從而備感快慰的成功人士,還是得過且過活到哪兒算哪兒因而老大徒傷悲的庸碌小民,在回溯、檢視自己寫就的生命史時,如果發現自己根本未曾思考過生命的意義這一命題,都難免會產生一些“此生有點俗”的不安,用一個書面語來說就是“汗顏”。
忽視主旨的人生。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主人公萊農,生于貧寒之家,父親是一個政府部門的卑微門房,母親是家庭婦女,夫婦兩人要養育4 個孩子。按照貧民模版平安度過一生,代際間小有改善,就是這類家庭出身者的典型人生理想。這樣的理想可以濃縮成幾個字:一切為了更好地生存,或者,一切為了生存得更好。
在萊農人生的60 多年中,她對生命意義的基本解答也是這樣的,改善生存狀況就是她向前走的最大動力。比起許多同齡人,她很幸運,她的智商較高,又遇到了愛才并且執意督促、幫助她超越她所在階層的老師。最終,她接受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并發揮自己的寫作特長,成為擁有一定社會地位和知名度的作家。
她一度很滿意。小時候,她以為自己的一生會困在那不勒斯,甚至是困在那個落后的城區:貧窮的生活,粗俗的家人,同樣貧窮的玩伴,同樣粗俗的玩伴的家人,黑惡勢力的籠罩,小康階層洋溢的優越感的刺激……而后來,她成為暢銷書作者,四處參加讀者見面會,侃侃而談,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被社會名流認可,去過博洛尼亞、米蘭、羅馬、蒙彼利埃、巴黎,嫁入名流之家……
但等她有足夠的智慧總結自己的大半生時,她終于發現了她的貌似飽滿而富有光彩的生命史的空虛之處——缺乏高貴的靈魂,她把這樣的人生視為低俗。
如果不是主人公毫不留情、血淋淋地自我錐心,作為讀者,陪同萊農走過她瑣碎紛亂、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的人生之路,你很難給出低俗的結論。但當她把你提升到局外審判者的高度,你又不得不同意她的結論,哪怕她有過為了營救好友、改善底層勞工境遇而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向黑惡企業主“開炮”的正義之舉。因為,這畢竟是零星的、偶發的行為,也并不是生發于一個偉大的人生主旨。從上世紀40 年代到本世紀初,在意大利或者整個世界的宏大背景中,主人公只是一個微觀的存在,這不是她的錯,很多人都是如此。錯的是,她并沒有試圖將自己與這個宏觀背景聯系在一起,她甚至并不關心時代的前進,她關心的只是自己的私域生活。
主人公或者作者,是通過寫作完成更高層面自我教育的人,她在人生后半段才有了對人生價值較為苛刻的衡量。而沒有完成高層次的自我教育,甚至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對人生意義的劃線會在哪個高度?
不求主旨的人生。
莉拉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主人公,或者是并列主人公。萊農與莉拉相愛相殺(萊農自己這樣認為),在愛恨糾葛中一同書寫著自己的歷史,并且深入影響著對方的歷史。
與萊農擁有階層跨越的長遠目標不同,莉拉更愿意拿當下開刀。只要自己覺得有能力做點什么,就勇猛操作,就去冒險,窮盡思維。她有超高的智商、非凡的決斷力,敢作敢當,能享天堂的福,也能吃地獄的苦。她令萊農著迷,令黑社會家族的公子著迷,更令投機鉆營的知識分子著迷。
莉拉讓萊農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哪怕莉拉只上過小學。莉拉在學習、寫作、經營公司方面的天賦,在社區的影響力,讓萊農自感望塵莫及。莉拉的光彩激勵著萊農不停地向前。而莉拉卻并不珍視自己的天賦,她將自己的智商、創意、勇氣肆意揮霍,喜歡就千方百計去獲取,覺得無價值了就毫不猶豫地拋棄——無論是男人還是生意。
也許,這就是她讓周圍很多人著迷的原因,也是讓萊農自慚的根源。萊農在爭取社會地位、嫁人、移情別戀、育子等一系列人生環節中,都加入了戰勝莉拉的元素,以至于無視莉拉的忠告,不顧一切地投入到尼諾的懷中。而這個尼諾,也曾是莉拉不顧一切委身的渣男。
在萊農的心中,莉拉的人生并不低俗,因為她的人生出發點不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而只要一份灑脫。但莉拉的生命也沒有什么主旨。她甚至不如萊農,因為她自始至終都沒有想到要總結人生的主旨。
莉拉不多的公益行動,也許就是想利用萊農的影響力對抗社區黑勢力,但最終失敗了。失敗便失敗,這并不在她的人生計劃之內。
她說消失便消失了,是刻意的。在寫作藝術上,這樣的結局沒什么不好。作為讀者,我很失望。因為,她本來能為改善這世界做得更多,能給混沌的人群更多亮光。
主旨無法飄在空中。
我們沒法不原諒萊農和莉拉的無主旨人生,對書中的其他人物,恩佐、阿方索、艾達、吉耀拉、卡門……一大堆所謂的人畜無害的小人物,難以觸摸到生命主旨線的社會一員,我們也只能原諒他們的庸碌。
因為,人首先要生存。人生主旨是滲透在一塊塊的生活拼圖中的,而不是飄在整個拼圖的上方。在掙得每一塊人生拼圖的過程中,教育或多或少發揮了一些作用。
教育讓萊農實現了階層跨越,擴大了生活版圖,有能力給三個女兒正確的人生啟蒙,也有能力做些有益于社會進步的事。
教育讓萊農的前夫獲得了大學的教職和社會聲譽,幫助三個孩子步入較高的社會階層。
教育讓莉拉和恩佐成立了計算機公司,改善了生活,幫助了一些窮苦朋友。
教育讓尼諾有了混跡于社會和女人間的光鮮外衣,讓他成為議員,擁有了相當大的話語權。
歸根結底,他們的人生停留在物質進步的階段,而沒有精神境界的提升。因此,他們會陷入迷茫,甚至蛻變為蛀蟲。
讓受教者擁有改變生活的技能,這只是教育的低階目的,有些人沒有受過科班教育,也成功地改變了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水平、社會地位。教育應該有更高的目標:讓受教者明白改變是為了什么——微觀改變是為了改變宏觀。
低階的、高階的目標,單獨實施似乎都不難,難的是將它們融在一起。沒有低階,高階將無以附存,就如萊農的無奈;而沒有高階,低階也將陷入低水平循環,就如萊農的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