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有質量的師幼互動有跡可循
谷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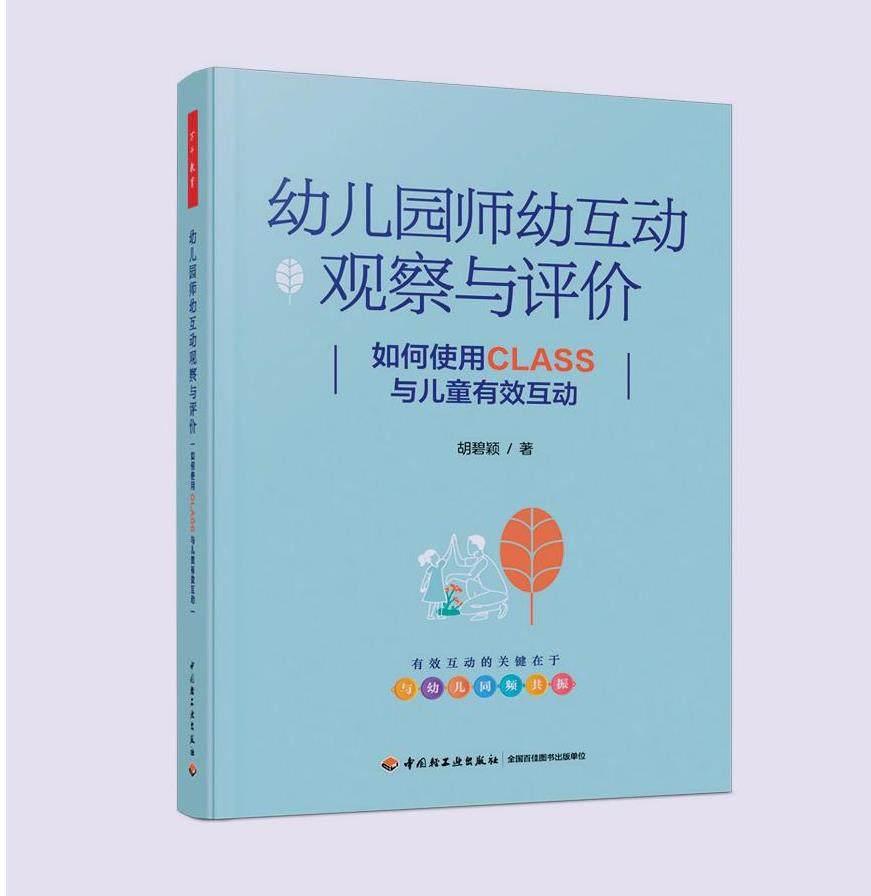
什么樣的師幼互動才是有質量的?近年來,隨著幼兒園質量評價與提升掀起熱潮,師幼互動愈發獲得重視,對于“有質量”的追求成為題中之義。然而,盡管師幼互動存在于幼兒園的每時每刻,卻也有些飄忽不定,不少教師都感覺難以把握。怎樣幫助一線幼兒教育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師幼互動質量的內涵,并以此指導具體實踐?澳門大學教授、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常務理事胡碧穎,帶著她的新作《幼兒園師幼互動觀察與評價:如何使用CLASS與兒童有效互動》,如同一陣撥云見日的清風而來。
研究學前教育質量評價與提升多年,胡碧穎深諳高質量的師幼互動,首先源自科學理念和科學目標的引領,以CLASS這一系統作為抓手,嘗試引領這場兒童觀和課程觀的變革。同時,教師也需要操作性方法作為參考。胡碧穎特別強調從實踐中去反推和檢驗理念,在書中詳細分析了CLASS各指標的應用場景,并做了本土化詮釋。她相信,當教師真正理解了尊重兒童的價值,在科學的理念指引下不斷訓練有效的教學方法,良好的師幼互動就在不斷向教師招手。
足夠重視師幼關系,才能自然而然地反思
《教育家》:您曾有過四年一線帶班經歷,關于師幼互動在實踐中的重要原則,您認為主要有哪些?
胡碧穎:在美國讀完本碩博之后,我在當地的一線幼兒園跟孩子們打了四年的交道,而后在大學工作,培養實習生,也繼續和孩子接觸。從本科學習期間,美國的師資培養就非常注重evidence-based practice,也就是以循證為基礎的實踐。它要求教師必須使用高效的、促進兒童發展的教學策略,并且教師要能證明自己的教學策略是有效的——我很清楚孩子發展的目標是什么,用了什么樣的教學策略,這些策略是基于哪些科學依據制定的,使用策略后孩子的反應如何,是否達到預期效果等。因此,在走上工作崗位以后,我非常注重跟孩子的互動,互動就是教師怎么教的過程,并且根據孩子的反饋來判斷教學的成效。目前,國內的師資培訓在這方面的意識還相對薄弱,處于逐漸推廣的階段。有些策略可能是教師之前學習的,或者是成長中跟父母、教師互動時自然習得的,比如重復對方說的話是促進孩子語言發展的一個很有效的策略,那么此后如何回應才能進一步提升孩子的能力呢?這就需要教師有意識地練習,甚至要反復訓練,才更易于教學策略的實施。
此外,我在本科階段的老師非常強調建立良好的師幼關系,這是教學的基石。任何知識的習得都是基于師生關系的情境展開的,教師絕不能對學生帶有任何偏見。因此我會特別注意反思,自己對孩子的要求是過高還是過低?有沒有因為孩子的背景對他產生偏見?當教師對師幼關系有足夠的重視,就能夠自然而然去反思。
《教育家》:您在前言中指出,有學者認為我國幼兒園文化特色太強,不適應于CLASS的質量評估,其實不然。在大班額狀況較為普遍的情況下,教師如何應用CLASS量表?
胡碧穎:關于本土化,我認為更恰當的理解是,究竟什么是高質量的學前教育。在最新版的《0-8歲兒童發展適宜性教育》中,提出了教育要具有情境適宜性,也就是與兒童的生活環境、生活經驗、家庭或社區的文化價值相匹配。探討本土化,其實也是需要遵循這樣的規律,做到年齡適宜、發展適宜、情境適宜。我在剛開始做質量研究的時候,用的工具是《學習環境評估量表》,它在美國的質量評估體系中廣泛使用。我和浙江師范大學的李克建老師、秦金亮老師一起對量表做了非常系統的本土化研究,因為我們認為這個工具很多指標與本土的文化情景是不匹配的,最后修改了一半以上的內容。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在進餐的時候是鼓勵教師與孩子開展社會性交流的,所以將它列為一個考察指標。而我們的教師在進餐時多半是在看管幼兒,不讓大家說話。這其實跟文化有關,在評估的時候并不是要探討哪個更好,于是我們將它修訂了,改成可以不計分,當然現在幼兒園的觀念在不斷更新,所以很多事情也無法使用同一套標準。
CLASS量表的使用其實并沒有規定班額,也沒有要求必須是個別化交流、小組交流還是集體活動。CLASS量表關注的是怎么教、關注過程中師幼互動的質量。大班額班級中教師引導的集體活動會多一些,是淺層地讓孩子死記硬背概念知識,還是深度地拓展孩子的學習思維,教師的引導至關重要。CLASS中融入大量兒童心理學、教育學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幫助教師組織好活動,因此我覺得它是每位教師必備的工具。
在日常了解和觀察孩子的積累中提升敏感性
《教育家》:為何師幼互動如此重要,但一線培訓中的反饋并不熱烈?作為一種過程性評估,它的評估難點在哪里?
胡碧穎:對師幼互動的認識發展需要時間。2008年我到內地來做博士論文時,感覺學前教育整體處于剛剛完成規范性辦園的狀態,等級評估雖然已經有轉入更合理評估方式的期待,但多是在結構性評估內容上調整,只有個別學者在倡導過程性評估。到了2022年,《幼兒園保育教育質量評估指南》頒布,開始將師幼互動作為二級指標加以突出,證明通過這十幾年的努力,我們的教育理念已經跟國際越來越接軌。而相應培訓的跟進或是體制里結構化的制度改變,還需要一個過程。比如對師范生的培養要求,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是實習,檢驗的是學生得到學校和教師專業輔導和支持的程度,但很多學校就是走流程,這種培養方式肯定是不行的。許多大學教師自己從來沒有帶過班,又怎能有實踐經驗指導學生帶班呢?我認為這是政策應該匹配和跟進的,現在更多依靠自覺行為。
過程性評價的難點在于它不是簡單的有或無。這個區角有多少類型的玩具、教師有沒有組織相關活動等,是相對容易判斷的,只要稍微留意下教師的語言,遇到相關表達記錄一下就差不多。而師幼互動是高度基于過程性的。比如判斷分析推理能力的培養情況,不光要去看他有沒有問“為什么”“怎么樣”,有沒有讓兒童分析對比,還要關注教師提出問題以后兒童的反應——兒童有沒有高水平的反應,還是根本沒有反應,然后教師又怎樣繼續給出暗示。它是一個隨時觀察和充分思考的過程,需要我們不斷地、大量地練習,以及自身豐富的互動經驗做基礎。
《教育家》:幼兒園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師幼互動,但有時候教師并不敏感,比如沒有意識到不回應其實也是在互動。教師應該如何提升敏感性?
胡碧穎: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敏感性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醒教師,孩子在情緒情感、社會性發展、認知能力等方面是有需求的,教師要有明確的意識,同時能夠良好地回應和幫助孩子解決問題,用與孩子個性發展特點相匹配的方式提供個別化支持。無論是兒童的發展特點還是心理成長規律,對教師而言,都要在帶班觀察中積累經驗,注重學習,才可能產生敏感性,知道如何支持孩子。比如面對害羞的孩子,可以說“我能跟你一起玩嗎”,通過語言起到提示和示范的作用,甚至要陪伴在孩子身邊,他才有底氣敢于嘗試。這樣的判斷是基于日常的了解和觀察的。
教師的敏感性水平發展是循序漸進的,也是反映教育理念和水平的一種指標。在書中我舉了一個例子,孩子們和教師一起觀察班級飼養的倉鼠,到了倉鼠進食的時間,教師將倉鼠放回籠子,孩子們也準備進行下一環節的活動。這時有個孩子告訴教師,自己想要抱抱倉鼠。教師當然可以答應孩子,這似乎是最簡便的做法,但這位教師沒有這么做。教師首先拒絕了孩子的要求,并給予充分的解釋:“現在不是一個抱倉鼠的好時機,因為我們剛剛抱完它,它正在吃東西。”到這里,教師的回應并沒有停止:“就像你在吃午飯的時候,突然媽媽來接你了,你會不會覺得困惑,我是該吃完飯還是該跟媽媽走?我是不是要把飯打包?小倉鼠也一樣,所以我們不適合打擾它,但明天早上你來的時候,我可以讓你抱抱它。”不難看出,這位教師的敏感性極高,她知道孩子理解“不能抱倉鼠”的困難性,遭到拒絕孩子也會不開心,于是從同理心建立的角度,幫助孩子以倉鼠的視角去理解這件事,那么以后孩子遭到拒絕的時候,就容易換位思考,而不是馬上感到失望或者生氣。有智慧的教師,策略都是有跡可循的。
《教育家》:在關注兒童觀點維度的解讀中,您提出“高水平的教師允許兒童把自己的想法帶入課堂,不會要求兒童按照教師的指示完成任務和游戲”,當兒童的想法和教學目標的達成出現沖突時,應該如何取舍和調整?
胡碧穎:作為教師,我們接受的熏陶和教育就是要以兒童為中心,但并不是所有教育活動都要以兒童為主導,一定會有以教師為主導的活動。生成也好,預設也罷,實質跟教師的理念和課程模式相關,跟教師教學的方式和特點相關,本身沒有高低之分。當然,隨著教師水平的逐漸提高,對課程的掌握程度也越來越高,更能隨時隨地接受生成課程。而新手教師比較緊張,往往更喜歡預設的課程,這是非常正常的。究竟讓兒童來主導還是教師主導,并沒有標準答案,教師要按照自己的節奏來,即便走出舒適區,也不能走太遠,一下子無所適從。從小的靈活性來說,每位教師都可以做到,比如今天天氣比較好,讓孩子們在外面多玩一會;孩子們對材料感興趣,那就多給五分鐘來擺弄。從大的靈活性來說,就是課程的主題。比如帶孩子在戶外觀察螞蟻,孩子對外面的廣告產生了興趣,一直在談論。雖然廣告主題是下學期的安排,但教師捕捉到孩子的興趣,就可以提前安排,在班級里設立廣告公司的區角,讓孩子從門衛、廚師處模擬接廣告業務。幼兒教育中多多少少都會有靈活性,包括集體活動的環節,可以提供機會讓孩子多表現,促進孩子學習動機的生發,培養孩子強烈的自主性和責任感,真正從內在點燃自己。
教師需要關于教育策略的大量練習
《教育家》:您提到,在使用CLASS量表對廣東省60所幼兒園180名教師的半日活動進行評分時,結果表明在認知發展維度上的整體平均分很低,而且顯著低于其他維度。為何出現這樣的情況?應該如何改善?
胡碧穎:我曾做過一個幫助教師提升師幼互動技能的干預研究,教授了CLASS的維度和指標,在不到一個學期的時間里,其他領域的提升相對較快,但是教學支持領域下面的一些策略,教師的提升幅度的確沒有達到顯著水平,說明維度相關策略的學習是需要時間的,而大部分教師需要更多的練習。對于教師而言,首先要有意識,這也是訪談中教師自己的感觸。比如認知發展維度中的分析推理策略,可以與布魯姆的教育目標相匹配,包括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創造六個層次,由此開展教學設計。我常以《好餓的毛毛蟲》這本受孩子歡迎的繪本為例來說明,教師可以圍繞上述六個層面來設計問題。第一個層面是記憶,教師很容易提出“毛毛蟲星期一吃了什么、星期二吃了什么”的問題;第二個層面是理解,很多人都會想得出“為什么毛毛蟲肚子會痛”;但從應用層面開始,多數教師就無法思考出“如果你吃了很多東西以后會怎么樣”之類的問題了。如果教師自己都無法設計出問題,又怎能通過提問促進孩子的發展呢?因此,培訓中真的需要刻意訓練,教師才能夠問得出有水平的問題。而且問題是通過一步步鋪墊,來引導孩子在記憶、理解的基礎上逐漸深入,培養孩子的分析能力,而非直接提出評價、創造層面的問題一蹴而就。
《教育家》:對于教師來說,如何在實踐中有效地利用CLASS,真正地在教育教學行為中將之融會貫通?
胡碧穎:我們可以從學習和有效教學的四個部分來考量。第一部分是“你要知道”,包括對孩子和對教學策略的了解。比如看了這本書,知道了什么樣的策略,你要能舉出例子來,否則可能還沒有理解,需要繼續學習。第二部分是“你要能識別”,比如看到別的教師互動,你能夠馬上判斷使用了哪種策略,說明能將理論和現實匹配起來。第三部分是“你要能做”,可以拍攝下自己使用策略的場景,記錄下在什么場景中如何引開話題、如何與孩子互動。第四部分是“你要反思”,教師通過自己評估反思,再與培訓專家一起交流。比如我真的在培養孩子的思維能力嗎?我是如何培養的?每天用了哪些策略?當我們反思之后,發現很多策略其實自己已經掌握了,那么還欠缺的就自然明確了,就可以在日后著重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