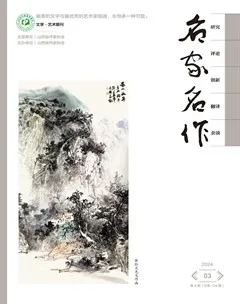“圓 舞”符號的文化解讀
王媛媛


[摘 要] 岷縣“巴當舞”是一種源自古代的民間民俗舞蹈,其舞蹈形態以“圓舞”為核心。作為中國舞蹈特有的運動模式與形態特征,“圓”成為中國舞蹈的根本形態與符號標志。在“巴當舞”表演中,無論是舞蹈動作、道具形制還是場地布局,都充分體現了“圓”這一典型的中國舞蹈形態特性。旨在從“巴當舞”的樣態特征、道具形制、隊形等多個方面對其“圓”的形和義進行深入解讀,分析“巴當舞”中“圓”的形態的具體呈現,以及所承載的文化內涵。
[關 鍵 詞] 圓舞;符號舞蹈;文化解讀
基金項目:2022年度甘肅省人文社會科學項目“岷縣‘巴當舞的樣態研究與文化認同”(項目編號:22ZZ20);2022年度甘肅中醫藥大學科學研究與創新基金項目“臨洮羊皮鼓祭禮樂舞的文化樣態解析”(項目編號:2022KCYB-15)。
任何藝術形式都有其最本質的規律,決定著該藝術的基本風貌和體系。中國舞蹈的形式規律就是“圓”。“圓”作為中國舞蹈具體的運動模式與造型原則,是中國舞區別于世界上其他民族舞蹈的根本標志。[1]
在物質世界中,宏觀星體或微觀粒子的自旋和公轉都是“圓形化”的,因此“圓,是從微觀到宏觀一切物質的基本形式和運動方式”[2]。我們不得不承認,“圓”是一種極其基本且重要的形象符號,它在自然界中隨處可見,同時也是人類認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圓”作為人類認知的方式,它在自然界和人類文明中都有著廣泛的應用和豐富的內涵。
作為一種最古老的文化符號,“圓舞”以其獨特的形態和結構,成為舞蹈藝術中的一種基本類型。這種“圍圓而舞、舞而成圓”的舞蹈方式,不僅體現了舞蹈的基本樣態,構成了此類舞蹈最基本的結構形態,還是原始先民群居性生活方式的重要體現,反映出他們團結互助、共同生活的精神面貌。
1937年,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上孫家寨出土了一件馬家窯文化類型的彩陶盆,其上繪有“手拉手舞蹈紋樣”,這將中國的舞蹈發展史追溯到了5000年前。這一發現打開了中國舞蹈新的一頁,讓我們對古代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這件彩陶盆上的舞蹈紋樣,描繪了人們穿著統一、手拉手圍圈而舞的場景,這既是當時人們舞蹈方式的真實寫照,也是他們現實生活的生動反映。這種圍圈而舞的方式,充分體現了原始先民群居生活的特點,揭示了舞蹈藝術在他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是以“舞蹈符號學”和“舞蹈形態學”角度劃分舞蹈形式類型的重要依據。所以,“圓”是“圓舞”核心藝術價值的基本體現。鑒于此,我們有必要以非常理性的態度重新審視“圓”在幾何中的基本定義及屬性。[3]
一、岷縣“巴當舞”概況
岷縣“巴當舞”是一種傳統的民間民俗樂舞,這種舞蹈在定西地區的岷縣、漳縣以及甘南地區的卓尼縣等地廣泛流傳。它起源于古老的“祭山會”,并被認為是最原始、最尊貴的樂舞禮儀活動。在表演中,當地群眾會一邊唱詞曲,一邊手搖“巴當鼓”,腳踏節奏,圍圓而舞。這是一種古老的民俗禮儀活動,當地居民通過這種方式祈求來年風調雨順、人畜興旺、五谷豐登。同時,這也是各民族群眾在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智慧結晶。
二、岷縣“巴當舞”圓舞符號的形與義
岷縣“巴當舞”堪稱當地最具特色的傳統集體舞蹈之一,它的獨特魅力在于其廣泛的群眾性。以岷縣中寨窗兒崖村為例,該村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每一戶人家每年都必須派出一名成年男子參加民俗活動。這項活動通常在農歷臘月農閑時啟動,由春巴(“巴當舞”核心人物,需熟練掌握“巴當舞”的唱詞、動作、步伐及儀式的各項流程,并負責教授村民跳“巴當舞”)帶領舞蹈隊員開始練習。正月來臨,民俗活動隨之進行。
(一)巴當鼓的圓形符號特征
“巴當舞”因其舞蹈所持道具“巴當”一詞而得名。
“瞽蒙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周禮·春官·瞽蒙》)
樂官掌管播鼗、柷、敔、塤、簫、管、弦等樂器。
“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論語·微子》)
擊鼓樂師方叔進入黃河邊,搖小鼓的樂師武進入漢水邊。
古籍中關于“播鼗”一詞的記載比比皆是,“播”,即手搖,“鼗”即鼓、手鼓。“《大濩》的文獻中描述了類似于今天‘撥浪鼓的鼓器‘鼗鼓。”[4]
“播鼗”實為“撥浪鼓”,是一種古老的樂器,依靠手搖鼓柄敲擊鼓面發聲,也是古代樂舞中使用的道具之一。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的樂舞多具有民俗性質,因此可以推測,巴當鼓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民間民俗舞蹈道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形制與“撥浪鼓”頗為相似,是一種雙面手柄鼓。在岷縣的民俗活動中,巴當鼓既是舞蹈道具,也是重要的精神載體。
巴當鼓的構造主要由鼓身、手柄和鼓穗組成,其形狀為圓形。這種圓形的設計不僅構成了“巴當舞”的重要形象符號,還與其舞蹈中的圓舞符號特征相輔相成,共同塑造出了一種以圓舞為主、手持圓形符號道具的特色舞蹈。這種舞蹈形式不僅富有深厚的文化內涵,還充滿了獨特的藝術魅力。
(二)“巴當舞”的圓形符號特征
“巴當舞”是一種重要的民俗樂舞儀式,傳說是為了祭拜“業力總督山神”。相傳業力總督帶領十萬兵馬西行,最后在甘肅岷縣中寨鎮窗兒崖村大山梁(岷縣中寨鎮窗兒崖村東北方向的一座山,海拔約3300米,此山山頂被稱為“營盤頂”)的營盤頂遭遇困境,并在那里離世。為了紀念這位英勇的武將,人們尊奉他為“業力總督山神”,以表達對他的敬仰之情。這一民俗活動每年都會如期舉行,不畏嚴寒,旨在祈求靠天吃飯的土地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保佑當地四季平安、人畜興旺。
岷縣“巴當舞”無論從表演道具的形制還是從其表演場圖來看,均以“圓”的形態呈現。舞蹈以“圍圓轉圈”為主,在圓形隊形的基礎上進行轉圈、繞圓等,具有獨特的地域特色,凸顯了“圈舞”特征。
三、岷縣“巴當舞”圈舞符號的文化解讀
(一)岷縣“巴當舞”圈舞的典型舞疇
“舞疇,這一概念是由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學博士生導師資華筠先生在《舞蹈生態學導論》一書中提出的。所謂舞疇,就是在直觀上可以感受到的具有同一審美表意機制的一簇舞動。”[5]舞疇,“疇”即類,同類的、相似的,意指在舞蹈中涵蓋舞蹈元素的諸多等同、同類、相似因素的合集。關于舞疇,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博士生導師馮雙白曾說:“在舞蹈觀察中,不必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動作精確值差的采集上,而只要注意那些能為舞蹈特征作出表征的‘舞疇即可,因為‘舞疇是一個由多種因子組合而成的復合單位(含節奏型、呼吸型、步伐、顯要部位動作等)。”[6]在研究和理解民間舞蹈的特征時,觀察者需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成簇出現的舞疇上。這不僅要求觀察動作的表面形態,還要求深入理解動作背后的意義,并將二者結合起來。僅僅關注舞疇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關注舞疇序列(舞疇序列是依時間順序組合的兩個以上的舞疇)中基本節奏型①、典型性顯要部位動作②、基本步法③這三個要點,這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民間舞蹈的整體特征和表現形式。
岷縣“巴當舞”圈舞的典型舞疇在其12種“腳步”中得以充分展現。這12種“腳步”的名稱均為藏語音譯,其中昂樣樣、打謝謝、沙愛為9句唱詞,其他則都是6句唱詞。所有“腳步”在舞蹈過程中呼吸自然,體態自然放松、下沉,重心在兩腿之間自然轉換,頭部動作自然,手臂動作自然上下、開合,腿部自然彎曲,步伐大小適中。
岷縣“巴當舞”在表演過程中,舞者的呼吸自然、體態下沉、步伐穩健。他們的頭部動作會隨身體的轉動而變化;手臂動作自然伸直或彎曲、上舉或下撤,使“巴當舞”的動態特征協調統一。舞者的上身體態自然,腿部自然彎曲,體態下沉,步伐穩健且動作流暢。整個舞蹈具有獨特的韻律感,充滿神秘的氛圍。
(二)岷縣“巴當舞”的表演場圖
為了更清晰地解讀和模擬再現舞蹈過程中的動作要領,我們加入了舞蹈方位和角度注解,以便于明確隊形變化并掌握個人在隊列中的位置。通過這些詳細的說明,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舞蹈動作的關鍵點,從而更好地模擬和再現舞蹈表演。此外,我們還可以借助這些信息了解舞蹈表演中的隊形變化和個人在隊列中的位置,從而更好地掌握整個舞蹈表演的節奏和韻律。
“巴當舞”是一種富有神秘色彩的舞蹈,共有七個環節。其中,安場、行腳步和攢山神這三個環節包含舞蹈表演的場圖。這些場圖以八人一組為例進行標示,旨在為我們提供一種理解和模擬舞蹈表演的方式。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舞蹈動作的布局和順序,以及舞者在表演中的位置和角色。此外,這種標示方法還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掌握舞蹈節律,從而更好地模擬和再現舞蹈表演。
1.“安場”表演場圖
2.“行腳步”表演場圖
“行腳步”與“安場”的表演場圖相同,在舞蹈表演中,舞者通常會以場地中心位置的圓圈為舞臺,進行各種動作的展示。這種圍圓完成的動作不僅具有獨特的視覺效果,還能夠充分展現舞者的技巧和舞蹈風格。在圓圈上做動作,意味著舞者需要在一個相對固定的空間內,利用圓圈的邊界創造出無限的舞蹈可能。
3.“攢山神”表演場圖
由此可見,岷縣“巴當舞”的“圓舞”符號構成為連環型、缺口型、虛線型、多環型等類型,符號特征明顯。舞蹈形態以集體圍繞某個圓心進行圓形軌跡上的移動為主。這種形態不僅傳承了古老的舞蹈形態,還代表了一種文化符號。在整個舞蹈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舞蹈“圓舞”的運動模式符號,同時也體現了當地居民緊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得益于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與推介,岷縣“巴當舞”在2011年5月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不僅是對這種古老民間民俗舞蹈的認可,還是對其所蘊含的深厚歷史文化和當地居民智慧的肯定。這種舞蹈具有極大的研究意義和社會價值,也為相關舞蹈形態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
我們期待岷縣“巴當舞”能夠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到該舞蹈的挖掘和研究工作中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傳承岷縣“巴當舞”豐富的文化內涵,從而為舞蹈“符號學”的理論研究提供更多的依據。
參考文獻:
[1]袁禾.舞蹈與傳統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4.
[2]李希凡,劉駿驤.中華藝術通史:原始卷[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57.
[3] 海維清.有意味的形式:舞蹈符號視覺下的中華“圈舞”舞蹈文化遺存研究[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116.
[4]海維清.論鼓舞并非“農耕舞蹈文化”之先河[J].青海社會科學,2008(3):114-117,195.
[5]鄧小娟.吾舞·吾歌·三叩首:甘肅秦安羊皮鼓祭禮舞蹈的文化解讀[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23.
[6]馮雙白.青海藏傳佛教寺院羌姆舞蹈和民間祭禮舞蹈研究 [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03:44.
作者單位:甘肅中醫藥大學定西校區學前與體藝教學部
注釋:
①即在舞疇序列中反復出現的、不發生改變的節奏型和作為變奏基礎的原型節奏型。見資華筠、王寧:《舞蹈生態學導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第93頁。
②包含兩方面內容,即在舞疇序列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活動或者超常度極高的特異動作。見資華筠、王寧:《舞蹈生態學導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第94頁。
③即與典型性顯要部位動作相配合的步伐類型。見資華筠、王寧:《舞蹈生態學導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