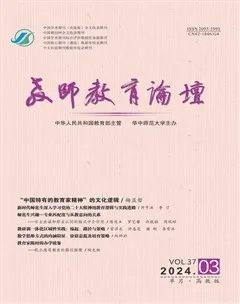教育家陳時的辦學鏡鑒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8年度教育學重大招標課題“建設教育強國的國際經驗與中國路徑研究”(項目編號:VGA180002).
作者簡介:
陶光勝,男,湖北襄陽人,教育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教育史和教育政策研究.
(華中師范大學 國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武漢 430079)
摘要:陳時是私立武昌中華大學的創辦者,是中國近代民辦高等教育的先驅。陳時在40年的辦學過程中沉淀了一套寶貴的辦學經驗,以士志于道的使命自覺固大學之本,以業精于勤的精神建構塑大學之魂,以苞桑之固的制度磐石立大學之治,以和而不同的差異方略謀大學之特,以風不鳴條的時代氣候筑大學之基。陳時的辦學歷程為研究中國近代民辦高等教育史提供了有益參考,也為推進當今民辦高校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歷史智慧。
關鍵詞:教育家;陳時;民辦高等教育;民辦高校;辦學啟示
中圖分類號:G52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5995(2024)03009008
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致全國優秀教師代表的信中,深情希望“大力弘揚教育家精神”。辦好一所學校,關鍵是校長和教師。教育家辦學既是一種高尚的價值追求,也是一種迫切的社會需求,更是建設教育強國的客觀要求。陳時(1891—1953),是我國近現代著名教育家,中國私立大學的先驅,周恩來總理稱其為“清苦的教育家”。1912年5月,陳時與父親陳宣愷一起,毀家興學,創辦了私立武昌中華大學,這是中國第一所不依靠官府、不依靠外國人、純粹由國人自己創辦的大學。1932年,蔡元培在參觀考察中華大學時曾經贊譽到:“常常聽到陳校長在武漢辦了一個中華大學,并設有大、中、小學三部,像這樣完善的學校,中國確實罕見。中華大學的名稱是和中華民國相同的,年齡亦一樣,所以中華大學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的大學代表者。我們知道陳校長辦這所學校的動機和目的,以及慘淡經營的情況,兄弟對于陳校長熱心教育的精神特別佩服!”[1]中華大學在1912年至1952年的40年辦學歷程中,培養了惲代英、林育南、陳昌浩、余家菊、馮友蘭、王亞南、光未然、萬國權、陳慶宣等一大批人才,取得了卓越的辦學成就,成為中國近代私立大學教育史上一座無法繞過的豐碑。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卡爾在《歷史是什么》里寫道,“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2]過往的歷史是現實發展的鏡子,現實走向是研究過往的引子。陳時興辦中華大學的40年,是中國教育大開大合、風云際會的40年,是中國教育從傳統逐步走向現代的40年,也是與中國近現代民辦教育心手相牽的40年。陳時作為中國近代民辦高等教育的先行者,既為我們研究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提供了絕佳樣本,也為我們探尋教育家引領助推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民辦大學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歷史智慧。
一、固大學之本:士志于道的使命自覺
毛禮銳認為“中國是具有數千年文明的國家,有豐富的教育史料,有悠久的大學教育的傳統,應注意挖掘整理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土特產。這些‘土特產也具有世界意義。一部中國大學發展史,是一幅自從有了文字以來中華民族創造和傳遞精神文明的歷史畫卷。”[3]這些“土特產”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近代大學校長群體的“士志于道”。孔子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在余英時看來,“士”的價值取向必須以“道”為依據,士要“能夠超越他自己個體的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4]如北宋張載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士志于道”不但是先秦時代儒家知識分子的行為準則,而且也同樣適用于后世各派的知識人,成為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符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中國近代大學校長是中國傳統‘士人與近代知識分子的結合。”[5]他們對于“道”的堅守和追求,他們在辦學中注入的深厚家國情懷和強烈社會責任,成為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經驗。大學是社會的良心,是文明的燈塔,其本質是一個關于知識的特殊學術機構。傳播知識、創造知識、運用知識,作育人才、闡揚學術、傳承文明、服務社會是大學的使命,也是大學興辦者應有的初心。
陳時傾其所有,勞碌一生,辛辛苦苦治理中華大學,擔任校長累計長達26年,其最樸素、最直接、最強烈的想法就是為國育才,挽救危亡。他說:“處在20世紀的年代里,一切是宜適應時代的需要,何況是次殖民地的中國,若不陶鑄人才來彌縫補缺,挽救危難,國家前途更屬不堪設想。所以本校就于民元應運而生。”[6]正是這種崇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鞭策著陳時為振興中華而興辦教育,培養人才在陳時的心中重逾千鈞。他曾殷切希望,“當先生的負起當先生的責任。做學生的要做個像讀書的學生。先生負責任,學生肯努力,互相勉勵,教學認真,校譽日上,……這樣才盡到大學的使命。”[7]1933年1月,《東方雜志》刊登了國內各界名流的新年夢想,陳時寫道:“我的個人生活完全為武昌中華大學活動,我的幸福亦純粹為此校犧牲。我夢想此校在五十年以內,能夠達到牛津、劍橋、哈佛、耶路、巴黎、日內瓦、慶應各大學規模,并發揮一個最高的大同思想,來造就許多未來世界的先鋒勇士。”[8]辦一所世界著名的好大學,是陳時畢生的追求和夢想。1937年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中華大學演講時說:“我和陳校長相比,自愧不如。辦南開,我只是出點力。陳校長辦中華,既出力,又出錢。我在北方……想到中華,就想到陳校長,中華大學有惲代英,南開大學有周恩來,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們兩校的光榮!我們兩校有許多共同點,正如陳校長所說,中華南開是親如姊妹。”[9]
做事情總有一個出發點。陳時創辦和發展中華大學的歷程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最為寶貴的經驗:士志于道的使命自覺是興辦大學的根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再光輝,也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對于教育管理者而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抑或是將來;無論是創辦大學,還是發展大學,都應該時刻牢記大學所擔負的使命,都應該時刻反省自身從事教育工作的初衷。方向性的錯誤,最后會發展為南轅北轍。特別是對民辦高校的發展而言,無論是營利性民辦學校還是非營利性民辦學校,時刻將辦學的公益性放在首位,是確保學校可持續發展的至關重要的戰略決策。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民辦教育進入發展的快車道。1993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國家對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依法辦學,采取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2018年12月最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再次強調,“民辦教育事業屬于公益性事業,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國家對民辦教育實行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依法管理的方針。”2021年4月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詳細指出,“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依法支持和規范社會力量舉辦民辦教育,保障民辦學校依法辦學、自主管理,鼓勵、引導民辦學校提高質量、辦出特色,滿足多樣化教育需求。”截止到2022年,我國有民辦高校764所,占全國高校總數的比例2536%。其中,普通本科學校390所,本科層次職業學校22所,高職(專科)學校350所,成人高等學校2所,民辦普通、職業本專科在校生92489萬人,占全國普通、職業本專科在校生的比例2527%。[10]
民辦學校這些年的快速發展也暴露出很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辦學的方向性問題。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一些民辦大學將學校的公益性拋至九霄云外,在一味追求辦學利潤的路上越走越遠。這些學校盲目擴大規模,倉促開辦專業,急于多招學生,樂于多收學費,自律精神不足,甚至將辦學經費挪作他用或遭遇資金鏈斷裂,在內涵建設上著力不多,辦學質量低下。有的學校因此而難以為繼,最終走向倒閉。早在1919年,陳時與惲代英談及教育家問題時,就直言不諱的指出,有些教育家并非真心熱衷教育,沽名釣譽、斂財獵官的大有人在。惲代英在日記中對此詳細寫道:“叔澄師談及目前教育家之劣跡,或因黷財,或因獵官,或因漁色,積德終身,隳于一旦,令吾戰兢。蓋棺以前知成就何等人耶。”[11]德不孤,必有鄰。陳時興學的案例昭示我們,民辦高校要想做大做強,做長做遠,無論是舉辦者、出資人,還是管理者,都一定要有崇高追求和戰略考量,一定要尊重和敬畏教育規律。當前,高等教育市場供給相對過剩,民辦高校的社會信任還在進一步構建、辦學格局還在進一步調整,此時更應該拋棄短視的利益觀,搶抓機遇把質量建設放在極端重要的位置,把學校辦出境界,辦出水平。
二、塑大學之魂:業精于勤的精神建構
“在任何社會中,高等教育機構都往往是一面鮮明反映該國歷史與民族性格的鏡子。”[12]大學是復雜的有機組織,根植于獨特的社會文化土壤。每一所大學都有自己的文化符號,都有屬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大學精神既是大學與大學之間相互區別的重要表征,也是大學發展重要的內驅力。辦大學,圖書、設備、建筑等物質設施必不可少,理念、文化、信仰等精神層面也不可或缺,要特別注重對大學精神的建構。
1930年元旦節,中華大學舉行喜迎元旦暨大學立案批準慶祝會,陳時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蓋私立學校若非精益求精、實事求是,則不克成立。本校雖不能驟與英國之牛津、劍橋,美國之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相比,然我總理有云‘有志竟成,心竊向往,希望其實現于將來。”[13]中華大學之所以能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一路前行,并取得較大的辦學成就,跟陳時營造的堅韌進取、成德達材、兼容并包的大學精神密不可分。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學校師生顯現出蓬勃的創造力、強大的凝聚力和驚人的戰斗力,也因此得到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中華大學的精神建構是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物質設施的不足和匱乏,成為驅動學校發展的重要力量,為現今辦學提供了寶貴經驗。大學管理者要善于立足教育的本質和規律,廣泛借鑒全校師生和社會的智慧,對學校辦學思想、辦學目標、發展路徑、文化特色、精神風貌等進行高度概括和抽象凝練,并根據時代發展和校情變化,與時俱進做出調整。要高度重視校歌、校訓、校史、校儀等工作,善于對學校文化元素進行整合優化,創造富有深刻精神內涵的、個性化的、規范化的校園形象符號系列,打造包括理念文化識別系統、視覺文化識別系統、行為文化識別系統等在內的一整套學校形象識別系統SIS(school Identity system),使大學精神有載體、有內涵,易識別、易傳承。
陶行知曾說,“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要評論一所學校,首先要評論它的校長。”校長是大學精神的培育者、象征者、弘揚者和傳承者,在大學精神的塑造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如果說大學精神是大學的靈魂,校長就是塑造靈魂的靈魂人物。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許許許多民國著名大學校長的經歷啟示我們,教育家辦學是學校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回顧中華大學的辦學歷程,陳時做到了溫度與力度的共存、職業與事業的統一、底色與特色的融合,在實踐中成長為一位當之無愧的教育家。陳時對中華大學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引領和助推作用,成為中華大學的“晶核”。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任何一種組織都是以某種形式的權威作為基礎的,權威能消除混亂、帶來秩序,沒有權威的組織是無法實現組織目標的”[14]。他認為,權威與權力是有區別的,權力是無視人們的反對,使人們被迫服從的能力;權威則意味著人們在接受命令時是出于自愿,而非強迫。韋伯又把權威分為三種類型:“傳統型權威源于歷史,克里斯瑪型(即超凡魅力型)權威來自個人的非凡品質,法理——理性型權威則建立在一套非人格化的規制基礎上。”[15]中華大學薪酬微薄、經費困頓,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劉鳳章、嚴紱蘋、鄒昌熾、魯濟恒等一批學者仍然愿意與陳時一起同甘共苦、共舟共濟,從某種程度上講,是陳時用自己一心向學的教育情懷和真誠待人的人格魅力,感召了一批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為建設中華大學和實現教育救國的夢想而努力,其事跡可歌可泣。陳時作為校長,僅僅依靠其身份和崗位所帶來的制度性權力是無法讓這些老師心甘情愿地留在中華大學的,他所能仰仗的其實正是他自己的超凡魅力。陳時在中華大學建構了一種個人魅力型權威,他的品格、能力和威望贏得了師生的擁護,特別是他教育救國的理想信念、毀家興學的感人壯舉、堅韌不拔的苦心經營、以誠待人的高尚品格、超越私利的服務和犧牲引發了巨大的情感共鳴,帶來了較高的價值認同,在中華大學這個特定的“場域”樹立了一種自然的威信,贏得了廣泛的尊重,獲取了深切的同情,并在客觀上帶來了一批認同陳時行為理念的堅定追隨者,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中華”現象、“中華”文化、“中華”人格,最終達成了陳時所期望的“師生們聯合起來,作一種發揚‘中華精神的運動”,把學校建設好發展好。
作為教育家,要有崇高的教育理想、堅定的教育信念,深厚的教育情懷、執著的事業追求,科學的教育認知、清晰的辦學思路,高尚的人格品質和開創性的事業建樹。當今時代,無論是公立大學還是民辦大學,推行教育家辦學,既是學校所需,更是時代呼喚。對于民辦大學而言,與公立大學相比,起步較晚,歷史較短,積累較少。劣勢也可以轉換為優勢,民辦大學的體制較為靈活,包袱相對較輕,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以市場化機制延聘一批熱愛教育、尊重教育的教育家作為學校校長、院長。在時間、空間、環境上給予充分的信任、充足的耐心和鼎力的支持,支持他們依法獨立行使教育教學和行政管理職權,支持他們大膽探索,創新教育理念,革新教育模式,變革教育方法,形成教育特色和辦學風格,最終助力民辦高校辦出特色、辦出水平,實現彎道超車。
此外,“面對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世界一體化的新形勢,教育的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機遇和挑戰,作為學校發展的領航者,明確校長的角色定位和職責權利非常必要。”[16]陶行知曾指出,“國家把個整個的學校交給你,要你用整個的心去做個整個的校長”[17]。一所好學校必然離不開一個好校長,甚至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校長就有什么樣的學校。校長的職業化在當前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校長的職業化或者任職期間的職業化,將有助于校長成為“好校長”。這的好處在于,“可以發展專業的精神,增進職務的效率”[18]。陳時校長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職業性,他是一個職業化的校長,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地做好學校的管理和服務工作。現如今,大學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校長的辦學理念、管理方式、治理成效等將直接關系到學校競爭力的高低。對于民辦大學而言,更是如此。民辦大學在校長的選任、聘用、考核、薪酬上,擁有比公立大學靈活很多的體制機制,一個能夠有效處理來自于市場、同行、家長、學生甚至出資人等各方面的壓力,能夠運用專業的管理思維、運營策略治理學校的職業化、專業化的教育家型校長,對學校的發展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立大學之治:苞桑之固的制度磐石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在《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中指出,“制度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穩定的環境,使我們至少可能達到微弱的理性……靠著制度環境的這種穩定性,以及其他許多沒有什么疑問的穩定性,我們就可能對自己的行動后果進行合理而穩定的規劃了。”[19]制度對組織發展的促進和保障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制度是關系大學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在大學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章開沅指出,“任何優秀的校長總有自己的任期(或長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續數十年。校園譬如軍營,師生如同士兵,老師(包括校長)、職工和學生一批一批來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連綿不絕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鐵打的營盤,歷經世變滄桑而長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須遵守的合理制度。”[20]
中華大學正反兩方面的教訓昭示著制度建設對于大學的重要性。一方面,在陳時積極主導下,中華大學建立了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1943年,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群發文指出,“私立大學能存在發展之條件有四:一為校董會,一為教授,一為畢業校友,一為肄業學生”“校董會為學校之主體,依照民法所組織之團體,……只要校董會健全,學校即能順利存在和發展”[21]。這套源自于西方的現代大學制度,開啟了中華大學的現代管理模式。董事會制度的穩定運行,使學校辦學有了一個制度化的支撐。與此同時,陳時把自己的辦學理念和經營思路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來,體現在中華大學從董事會章程、組織大綱到學生管理、教學管理等的一系列校內規章中。正如德國學者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言,“大學只能作為一個制度化的實體才能存在。在這樣一種制度里面,大學的理念變得具體而實在。大學在多大程度上將理念轉化成了具體實在的制度,這決定了它的品質。倘若將它的理念剝離出來,大學就一文不值了。”[22]在董事會的支持下,陳時按照現代大學的組織模式、管理架構、決策體系、院系設置等,于1928年復校后迅速重新建構了中華大學的整個管理體制,使其成為一個形式上具備現代大學框架、管理上浸潤現代大學理念、運行上貼近現代大學實踐的現代化大學,為中華大學日后多年的辦學打下了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中華大學法人財產權制度、“收支兩條線”財務管理制度等的不健全,為學校的健康運行帶來了隱患。從現代法律視角來看,民辦學校對舉辦者投入民辦學校的資產、學校獲贈的財產、辦學過程中的積累以及政府投入的資產,是享有法人財產權的。民辦學校的所有資產都應該由民辦學校依法進行管理和使用,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占。陳時家族不僅是中華大學創辦之初的注資者,也是中華大學發展壯大的維系者。陳時一身兼著兩種身份:他是中華大學的校長,是學校的法定代表人,爭取辦學資源,尋求經費支持,是校長的本職工作,而且自1912年創辦中華大學以來,陳時就沒有在學校拿過工資,擔任大學校長20多年都是義務工作,心系學校,甘于奉獻;陳時又是中華大學最大出資人的代表,陳家的各種資金、捐助都是經過陳時注入中華大學。在現代企業管理或現代私立大學制度體系中,這兩種身份都有清晰的法律地位和職責權限,也有規范的行為準則。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社會民眾的認知水平有限,民國時期法律制度也不健全,中華大學的這種特殊出資結構以及陳時兩種身份的疊加,成為被人詬病“公私不分”的重要原因,也是現代大學加強內部控制建設所應竭力避免的財務風險。
“大學是在一個制度架構之內完成它的任務的:科學研究、教學、學術訓練、溝通。它需要建筑物、原材料、書籍、院系,還需要對所有這些進行規范化的管理。”[23]當前,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的偉大征程中,制度建設被擺在了至關重要的位置。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加快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成為“雙一流”建設的重要內容。對于占全國高校數量四分之一的民辦高校而言,制度建設同樣萬分重要。中華大學在制度建設上的得與失,同樣值得當今的民辦高校深思。在宏觀治理結構上,民辦高校要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完善董事會(理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加快建立現代民辦學校制度,妥善處理行政權力、學術權力、民主權力、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在微觀管理制度上,要健全內部管理體制,特別注重加強財經制度的建設和執行。要依法建立健全財務制度、會計制度,加強財務監管體制、機制和制度建設,在成本審核、學費收取、經費使用等環節上,加緊補齊制度漏洞。要加強和規范法人資產管理,建立和健全資產管理制度,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設置會計賬簿。通過完備的制度建設,以規范辦學行為,確保學校良性發展。
四、謀大學之特:和而不同的差異方略
潘懋元指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結構必須主動與現代經濟、社會的人才需求結構相適應。社會需要的人才是多層次、多類型的,因此,每一所高校都應在高等教育的分類中找準自己的位置,明確自己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戰略,突出自己的特色,為社會培養高素質的人才。”[24]在高等教育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走特色強校之路,更應該成為高校發展的選擇。國內國外概莫如此,比如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學院和藝術學院享譽全世界,其校長賈瑞德·柯亨曾說:“我們沒有像哈佛、牛津那樣雄厚的資金支持,因此在確定學校發展方向時必須找出自己的比較優勢,用有限的資金發展自己的強項。”[25]
中華大學在辦學過程中,主動對接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調整和完善辦學思路,在保持優勢專業相對穩定的基礎上,使學校走上了一條以特色謀發展、以質量鑄品牌的道路。陳時注重學校的學風建設,中華大學“學風淳樸,為人所稱道”,成為學校特色發展的重要保障。他曾說:“本校正要培養良好風氣,向學問方面努力,將來到社會上去,獲得好的觀感,社會因此感應,校譽日向光榮之途前進,以創造學校久遠歷史。”[26]陳時注重延聘高質量師資隊伍,精心設計課程體系,加強學生日常管理,高度重視實習實訓,努力提高學生的培養質量,使學生具備較強的就業競爭力。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數學、化學、教育學等傳統專業開辦多年,經久不衰,累積了許多建設資源,形成了相對優勢。會計學、法律學、經濟學、銀行學、工商管理學、農藝學、師范專修科、會計專修科、應用化學科等專業,應用性很強,迎合了區域和行業發展的迫切需要,社會認可度很高,口碑很好,畢業生大受歡迎。除中華大學外,民國時期立信會專、湘雅醫專、無錫國專、東亞體專等,雖然都只是專科層次的高校,但因為辦學特色鮮明,教育質量較高,而在社會上聲名卓著。
由此可見,每一種高校、每一所高校都可以辦出水平、辦出影響,關鍵在于能不能辦出特色。現在許多高校同質化嚴重,區分度減少,千校一面的現象普遍存在。
不同地域、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不同歷史、不同文化的高校,卻在辦學定位、發展目標、培養模式、專業設置、課程體系等方面高度趨同,引發學校生存危機,帶來學生就業壓力。對于民辦高校而言,很多是新建本科院校或高職高專,正處于學校發展的起步階段,更應該以戰略眼光做好統籌規劃。美國著名高等教育學家伯頓·克拉克提出:“實施高等教育的最差的辦法就是把所有的雞蛋往一個籃子里裝——高等教育最忌諱單一僵化的模式。”[27]特色就是質量,特色就是生命,特色是學校核心競爭力的基礎。民辦高校的舉辦者、管理者要實事求是地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所處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社會需求狀況、辦學條件、資源結構等,明確自身定位,明晰辦學目標,凝練辦學風格,科學合理地制定發展戰略,揚長避短,有選擇地追求卓越。要有辦學定力和發展活力,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打造“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特色專業,不能盲目攀比,也不能冒然追求大而全的專業設置,以至于攤薄有限的辦學資源。要加強學校內涵建設,在師資隊伍、實驗設備、圖書資料、實習實訓、政產學研用結合等方面舍得花功夫,下成本。要搶抓中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和創新型國家發展對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巨大需求的機遇,以培養適應市場需要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為突破,密切關注社會需求和市場反饋,不斷完善培養舉措,不斷創新培養模式,力爭在各自的層次和類型中成長為一流的高校。
五、筑大學之基:風不鳴條的時代氣候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是中國古代對社會安寧、天下太平的一種理想描述。教育不是萬能的,教育更不是超政治的。教育不可能離開經濟社會條件而單獨存在,必定會受到一定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離開特定的社會條件談教育,只能是一種美好的幻想。一方面,教育建立在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基礎之上,教育的內容、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目的、教育的規模、教育的組織形式、教育的物質基礎、教育的人文環境等等,都深受其影響。另一方面,“自古以來,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要想得到實現、鞏固與發展,必須有一定的人才作支柱,而這些人才的培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學校教育。”[28]1931年,魯迅在《友邦驚詫論》中犀利而悲哀地寫道:“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于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1935年,抗日救亡的“一二·九”愛國運動爆發以后,運動的參與者文立征在寫給弟弟的信中,不無凄涼地嘆息道:“偌大的華北已不允許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烽火連天的舊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國家羸弱、民族衰亡,教育缺少和平穩定的外部發展環境,宛如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漏水扁舟,在仁人志士的支撐下,勉力維持。陳時主持下的中華大學亦是如此,在經濟落后、社會動蕩、民眾生活慘淡的情形下,辦理一所從小學到大學的私立學校異常艱難,單單是因為戰爭原因,中華大學就幾乎于1928年、1938年、1946年三次“重辦”,備嘗艱辛。
經費問題是關乎私立高校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動蕩的社會環境加劇了經費籌集的不易。教育作為具有公共屬性的準公共物品,投入周期長,產出效益具有滯后性和外溢性,資本投入的積極性不高。民國時期,資本市場尚不健全,社會公益事業尚不發達,政府對私人或私人團體投資教育或捐資教育的政策機制還不完善,捐資助學的社會風氣遠不如歐美發達國家那樣濃厚,私立大學的經費來源渠道有限,無外乎學費、捐贈、私產收入、政府補助等。經費短缺成為私立大學揮之不去的“噩夢”,中華大學情況尤甚。中華大學既不屬于以學養學型,也不屬于民辦官助型,而是捐贈為主型。中華大學的捐贈收入占當年學校總收入的比例基本維持在50%以上,是學校最為重要的資金來源渠道。中華大學的捐贈又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陳時家族不斷拿私產來補助學校,陳家的補助主要是變賣田產、房舍和收取地租,這種補助在辦學初期奠定了學校的發展基礎,當學校日益壯大以后,僅靠陳家的私產已經遠遠不能維持一所大學的日常運營,而且陳家已經毀家興學,財產所剩無幾。另一種是通過社會募捐來籌集經費。中華大學1912年剛剛成立之時發起募捐,有一名對中華大學抱有深切同情,對教育救國充滿期望的熱血人士,當場慷慨捐贈400銀元而不留姓名,該志士“下臺逕去,或追問其姓名,曰:‘我無名氏也,惟望貴校此舉有成爾。”[29]滿腔熱情令人感慨。但是,總的來說,1926年前,中華大學還處于起步階段,社會聲譽還不像日后那么聲名顯赫,“學校在社會上的信用,沒有建立,募捐工作,無法進行;縱然進行,收獲不多。學校的開支,除了學費和田租收入一部分外,不足的部分,就靠借債來維持。”[30]1928年學校董事會正式成立后,伴隨著學校的快速發展,董事會在募集經費方面起到了較大的作用。社會捐贈特別是湖北工商業人士的捐贈,極大地緩解了中華大學經費緊張的局面。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約,募集的額度并不穩定,與浩大的開支相比,辦學經費仍然經常捉襟見肘。陳時不得不拆東墻補西墻,繼續向銀行借債度日。抗戰期間,學校經費更為短缺,在校董的大力支持、陳時的四處奔走和政府的些許補助下,勉強維持。辦學后期,社會環境持續動蕩,經濟形勢不斷惡化,中華大學的收入來源更窄,經濟困難更甚。可以說,自中華大學成立以來,陳時就一直在為經費奔走,幾乎沒有停歇。經濟困難到極致的時候,“于寒舍中,羅雀掘鼠以供校用,同事見舊衣銀屑,送入質庫,有相顧垂涕者。”[31]為了籌集辦學經費,把學校辦下去,陳時不僅變賣家產,還像武訓興學一樣,四處“化緣”,苦行“乞討”,極為艱辛。
教育的發展離不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轉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奮斗,中國綜合國力今非昔比,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萬美元,教育發展擁有了雄厚的經濟社會基礎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黨和國家旗幟鮮明地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充分凸顯教育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作用,為教育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社會保障,創造性地提出“三個優先”戰略,即“在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上優先安排教育、在財政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教育、在公共資源配置上優先滿足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需要。”目前,我國建成了世界最大規模的教育體系,世界最大規模的教師隊伍,各級教育普及程度均達到或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保障了億萬人民群眾受教育的權利,從2012年起連續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教育總體發展水平躍居世界中上行列。民辦教育也擁有了更完備更系統的政策環境,多部促進民辦教育發展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法人屬性不明、財產歸屬不清、內部治理結構不順、政府扶持不到位等問題從制度上陸續得到解決,民辦教育迎來發展的黃金期。
六、結語
我們研究歷史人物,應該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以唯物史觀全面地看待歷史,注重歷史的連續性和整體性。習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32]對于陳時,我們要看到歷史的主流和本質,要準確把握歷史的主題和主線。陳時為了“興學”不惜“毀家”,四十年如一日,堅守了初心,保持了氣節,舍棄了功名利祿,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崇高的教育事業,探索了一條社會力量辦教育的艱辛之路,贏得了社會的尊敬和稱頌,立下了光未然所言“為中華育才,為江漢增光”的豐功偉績。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克紹箕裘,踵武賡續。陳時興學的經驗是我們辦教育特別是民辦高等教育的寶貴財富,陳時辦學的教訓發人深思,讓人警醒。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的繁盛為中國教育開啟了發展的快車道。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久經磨難的中國人民走過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征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指日可待。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步伐越來越快,中國教育逐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影響力與日俱增,離教育現代化的目標日加接近。包括民辦教育在內的各級各類教育,理應牢牢把握住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的戰略機遇,努力推動自身實現更高質量更高水平更有特色的發展,為教育強國的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
[BT4]參考文獻:[HT5”XH][STXFZ][WTXFZ]
[1]孫中岳、趙伯英.蔡元培先生1932年5月28日在中華大學演講原文[N].中華周刊,19320604(01).
[2] (英)愛德華·霍列特·卡爾.歷史是什么?[M].吳柱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28.
[3]曲士培.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2.
[4]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5.
[5]吳立保.大學校長與中國近代大學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376.
[6][7]陳時.本校成立25周年答記者問[A].婁章勝,鄭昌琳.陳時教育思想與實踐[C].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32.
[8]陳時.新年的夢想[J].東方雜志,1933(1):79.
[9]吳先銘.陳時與中華大學的幾個片段[J].武漢文史資料,1983(3):114121.
[10]教育部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N].中國教育報,20230706(03).
[11]惲代英.惲代英日記[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522.
[12](美)勞倫斯·A·克雷明.美國教育史(3)[M].朱旭東,王保星,張馳,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422.
[13]陳校長致詞[N].中華周刊,19300118(01).
[14]丁煌.西方行政學說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59.
[15]李國正.公共管理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164.
[16]鄔志輝主編.現代教育管理專題[M].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8:256.
[17][18]陶行知.整個的校長[J].新教育評論,19260205:45.
[19](美)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M].楊礫,徐立,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162.
[20]章開沅,余子俠.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7.
[21]王伯群.私立大學存在和發展的條件[N].大夏周報,19430125(01).
[22][23](德)卡爾·雅斯貝爾斯.大學之理念[M].邱立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8.
[24]潘懋元,董立平.關于高等學校分類、定位、特色發展的探討[J].教育研究,2009(2):3338.
[25]馬德秀.變革與超越:走中國特色的一流大學之路[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44.
[26]陳時.十月一日在第三次總理紀念周報告[N].中華周刊,19341010(05).
[27](美)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王承緒,徐輝,殷企平,蔣恒,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307.
[28]王道俊,王漢瀾.教育學(新編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67.
[29]國民愛國史[N].申報,19121222(10).
[30]陳時.我的檢討:195104[Z].華中師范大學檔案館(LS1259).
[31]陳時.弁言[Z].武昌中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特刊.
[32]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31227(02).
Educationalist Chen Shis Enlightenments on Running Education
——Exploring the Path of Nongovernmental Higher Education
Tao Guangsheng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Governance Studi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9,China)
Abstract:Chen Shi is the founder of the private Wuchang Zhonghua University and a pioneer in modern nongovernmental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Over the course of 40 years of running the university, Chen Shi has accumulated a valuable set of experiences in education. Guided by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a commitment to virtue, he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university. Driven by the spirit of diligence and excellence, he has shaped the soul of the university. Building upon a steadfas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he has established the governance of the university. Employing a strategy of embracing differences harmoniously, he has sought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university. Grounded in the zeitgeist that does not boast loudly like the wind through bamboo, he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Chen Shis educational journey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nongovernmental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offering historical wisdom for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oday.Keywords:
educationalist; Chen Shi; nongovernmental higher education;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enlightenment
(責任編校:周文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