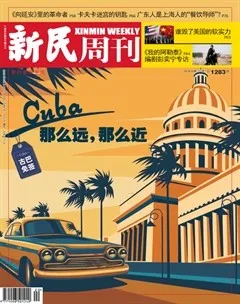山野的國(guó)王
春末,我收到了一網(wǎng)兜新蠶豆。一看留下的字條,樂了。這個(gè)老盛,果然是一個(gè)老農(nóng)詩(shī)人啊,他的字體往一邊傾斜,還分段:
“蠶豆還沒有長(zhǎng)出黑嘴子/松鼠就來偷吃盛宴/莢果上的細(xì)絨毛掃著它的鼻子/松鼠一定被我種的蠶豆迷倒了……”
老盛是我20多年的同事,退休前兩年,他在遠(yuǎn)郊荒山上租了一處廢棄的水塔,開始耕讀生活。中國(guó)人都有半耕半讀的夢(mèng)想,但很多人只是嘴上說說而已,老盛卻付諸行動(dòng),特意與村里簽了15年合同,準(zhǔn)備在水塔上層做一個(gè)玻璃房觀景臺(tái),好讓自己面對(duì)莽莽蒼山讀書。他還買回電動(dòng)卷?yè)P(yáng)機(jī),把它改造成能拽引重物上山的“電梯”,方便運(yùn)送裝修材料。
清理山上的垃圾與石頭,運(yùn)來腐殖土與肥料,改善荒山的土壤。過了大約一年,老盛已經(jīng)在山間種起菜蔬與十幾棵杏樹、櫻桃樹。果樹開花時(shí),老盛的水塔書房仿佛就像船的桅桿,浮漾在粉白色的浪頭中。他親自到地里扯了韭菜、掐了菜苔,又去雞窩摸了雞蛋,招待前來探訪他的朋友,老盛說:“住得如此荒僻,從被油菜花田包圍的地鐵站鉆出來,還要走半小時(shí)才能上山,能來的人,都是知己。”
耕讀生活也不可能永遠(yuǎn)一帆風(fēng)順。老盛的收獲,被山里不招自來的野生動(dòng)物們吃掉相當(dāng)一部分。秋天的花生、山芋、土豆,招來了一小隊(duì)昂首闊步的野豬,老盛觀察到,那是野豬夫妻帶著自己的頭胎與二胎寶貝,有時(shí),它們彼此親密地翻滾嬉戲;春天,剛結(jié)出的蠶豆與豌豆,又招來了捧著豆莢啃噬的小松鼠。村民小組長(zhǎng)上門統(tǒng)計(jì)老盛的損失,說要給他申請(qǐng)一定的補(bǔ)助,老盛謝絕了:“這就不用了吧,野豬和松鼠吃剩的,我也一樣能吃。”
除了野豬和松鼠,還有鳥,杏子由綠變黃時(shí),鳥們就嘩啦啦地來了,哪一只杏子甜,調(diào)皮的鳥就在上面啄一口。老盛說,若把這些剛啄破的果子摘下來,挖去啄破處,及時(shí)熬成杏子果醬,也就不算浪費(fèi)了。
春夏之交,山野蔥郁又遼闊,正在涂果醬的老盛,聽見空中有鳥兒在歡叫,抬頭望去,原來是一只白頭鵯在杏樹上來回跳躍,它的灰色背羽上,間錯(cuò)泛著橄欖綠色,頭頂有一撮白色的羽毛,像是梳著帥酷的莫西干頭。老盛遂賦詩(shī):“白頭鵯的叫喚/如老木門被敲響/此時(shí)我就是山野的國(guó)王。”
一個(gè)富足如國(guó)王的人,當(dāng)然不會(huì)計(jì)較山野中的小生靈們,搶吃了他一把蠶豆和幾只杏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