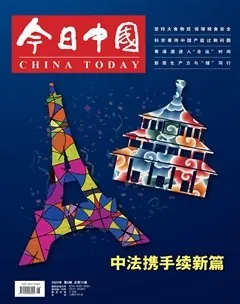科學看待中國產能過剩問題
近來,美西方一些政客和媒體頻繁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論”,無理指責中國以不公平的價格向全球市場大量傾銷太陽能板、鋰電池和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品,破壞全球商品供需平衡狀況,并導致新能源產品價格螺旋式下降,扭曲了全球產品價格機制,損害了全球制造業的可持續性。
對于中國而言,這些言論實際上是老調重彈。十多年前,美國也抱怨中國鋼鐵和鋁行業產能過剩沖擊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就業機會。按照美西方國家慣常的行事邏輯,“產能過剩論”事實上是其對中國新能源產品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所尋找的一個借口。
“產能過剩”是什么
產能過剩通常指某個產業的產能大幅超過需求,導致產品供給明顯過剩和價格大幅下跌。顯然,這一定義將產能過剩與供需不平衡聯系在一起。
從市場經濟運行規律角度看,生產者(供方)和消費者(需方)相互分離且行為方式差異巨大,宏觀經濟周期波動、消費者偏好改變、技術進步、自然災害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因素均會導致供需出現大的變動。從而,供需平衡是瞬時、相對的,供需不平衡是常態、絕對的,價格機制的作用正是通過價格漲落來引導供需走向平衡。因此,不能將供需不平衡輕易認定為產能過剩。
從產業發展生命周期角度看,新能源行業作為新興產業,具有技術創新迭代快、技術路徑多元的特征。一些企業在完成初步的技術積累和市場培育后,為搶占市場進行大量投資,造成供給暫時性超過需求。但隨著行業步入成熟期,技術先進的優質產能會替代落后產能,供需不平衡狀態會得到改善。所以,將當前一些新能源產品暫時性供大于求認定為產能過剩是不正確的。
在當今全球經濟深度一體化的情形下,評估某個產業供需是否失衡或產能是否過剩,需要跳脫國別層面的限定,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按照經濟規律,一國的產業結構和特定行業的產能規模由其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科技水平等因素決定。各國依據自身比較優勢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分工合作,是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途徑,如發達國家出口科技產品和金融服務,資源豐裕的國家出口初級產品,中國出口工業制成品。顯然,我們不能將各國出口量大的優勢行業認定為“產能過剩”,即既不能將美國的金融業和科技行業稱為產能過剩行業,也不能將中國的新能源行業和沙特的石油行業稱為產能過剩行業,否則就是違背了經濟學基本認知,開逆經濟全球化的倒車。
是否過剩不能一概而論
美國政客和媒體此輪炒作“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的所謂核心證據,是中國的工業產能率下降和工業品價格下跌。
宏觀經濟波動周期和國外需求變動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的工業產能利用率產生明顯影響。作為世界工廠和最大的工業制成品出口國,中國確實長期備受產能過剩問題的困擾,這促使中國不斷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
一般而言,衡量一國產能狀況最常用的指標是產能利用率。產能利用率數值介于0與1之間,0表示工廠完全閑置,1表示產能滿負荷運轉,80%表示產能利用處于正常水平。在2014-2016年期間,受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政策的滯后影響,鋼鐵和鋁等行業的產能嚴重過剩,帶動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降至72.9%的歷史低位。這推動中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22-2023年期間,因新冠疫情、中美經貿摩擦和房地產行業投資低迷等因素,中國的工業產能總體利用率降至76%左右,處于2016年以來偏低的水平,但仍比2016年的產能利用率高約3個百分點,且與美國78.9%和歐盟78.8%的產能利用率相差不大。這一數據顯然不足以證明中國當前出現了明顯的產能過剩。
評估中國工業產能問題需要做具體的行業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無須諱言,中國目前一些傳統行業確實出現產能過剩跡象,如玻璃、水泥行業因房地產市場拖累,產能利用率僅為30%左右。并且需要承認的是,中國的光伏產品和鋰電池確實出現了較突出的供需不平衡問題。其表現在:中國硅片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從2019年的78%降至2022年的57% ;中國電動汽車鋰電池2022年產量是國內需求量的1.9倍,2024年產能預期將達4800吉瓦,但中國國內需求量1200吉瓦,意味著75%的電池產能要出口;鋰電池主要原材料碳酸鋰的價格已從2022年峰值水平下降了80%,太陽能板價格也比上年下跌了50%左右。
然而,并不能據此判定中國的光伏和鋰電池行業出現產能過剩。從全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與能源轉型進程來看,中國的光伏產品和鋰電池的產能實際上不能滿足未來全球市場需求。要實現巴黎氣候協定目標,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預測,2030年全球光伏累計裝機量將超過5400吉瓦,分別是2023年全球、中國累計裝機量的約4倍、9倍;國際能源署(IEA)預測,2030年全球動力電池需求量將達3500吉瓦,分別是2023年全球、中國產量的4倍多、5倍多。另外,光伏產品大幅降價也是技術不斷進步的結果,這極大推動了光伏發電成本的下降和新能源行業的發展。
對于中國電動汽車行業來說,無論從產能利用率還是出口價格角度衡量,均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目前,中國電動汽車行業的產能利用率達到80%的正常水平門檻。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純電動車和油電混合動力汽車市場,國內銷售量在2023年同比增長36%,預計在2024年將同比增長25%左右。并且,盡管中國在2023年首次成為汽車出口量最多的國家,但出口量占產量的比例遠低于德國、日本和韓國。此外,中國出口的汽車特別是電動汽車,價格是上漲而不是下降的,中國電動車價格在歐洲、墨西哥市場的售價相當于國內市場價格的2倍左右。而且,目前中國電動汽車產能尚不能滿足未來全球能源轉型的需求。據國際能源署(IEA)測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需求量將達4500萬輛,是2023年全球銷量的3倍多、2023年中國產量的近5倍。這表明,中國電動汽車在價格和質量上均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警惕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競爭優勢主要可歸結為規模龐大且充分競爭的國內市場、領先的科技創新能力、勤奮且高素質的工程師和產業工人隊伍、完備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完善的充電樁設施、較低的能源成本。中國新能源行業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依靠美國政客所污蔑的“不公平競爭”得來的,而是中國企業努力奮斗的結果。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引導和財政補貼確實推動了新能源行業的發展,但相對于技術迭代創新而言居于次要地位。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在新能源技術領域的論文發表量已領先美國和歐盟。
需要指出的是,支持新能源行業發展和鼓勵綠色轉型,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和實踐。世界各國均通過各種方式支持新能源行業發展。例如,美國的《通脹削減法》規定向在北美組裝的電動汽車提供每輛至多7500美元的稅收減免。
美西方國家之所以頻繁炒作“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是因為其無奈地認識到難以與中國新能源企業進行競爭,被迫采用“產能過剩”這一話術或“語言陷阱”來粉飾其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以限制中國新能源行業的發展。
當前,世界各國紛紛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并加快能源轉型步伐,預示著光伏、風電、電動汽車等新能源行業將迎來巨大的發展機遇,并有望成為引領21世紀科技進步和經濟繁榮的前沿新興產業。
在當前中美大國博弈的背景下,美國寧愿犧牲其能源轉型的速度,也要不遺余力地打壓中國新能源產業,遏制中國的良好發展勢頭,削弱中國在產業領域的競爭優勢。
歐盟計劃在2024年7月完成對中國電動汽車的反補貼調查,并將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關稅。當地時間2024年5月14日,美國白宮宣布,進一步提高對自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關鍵礦產等產品的加征關稅。增幅最大的是電動汽車,關稅稅率翻了兩番。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是典型的政治操弄。美方提高301關稅違背了拜登總統“不尋求打壓遏制中國發展”“不尋求與中國脫鉤斷鏈”的承諾,也不符合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精神,這將嚴重影響雙邊合作氛圍。
面對美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中國政府和企業應做好應急預案。一是在美國的“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和“在岸外包”政策作用下,以及對中國產品征收高額關稅的情景下,中國新能源企業將難以在本土向美國市場大量出口光伏、鋰電池和電動汽車等產品,對此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準備;二是鼓勵中國企業對外開展新能源投資,特別是去墨西哥等拉美國家以及東南亞國家投資,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產能,適當規避美國關稅限制措施。但與此同時,中國企業應考慮墨西哥、越南、泰國等國家的承接能力,盡量避免一窩蜂地扎堆投資;三是鑒于歐美市場進入門檻不斷提高,中國企業應適當控制國內光伏、鋰電池等產量投資規模,避免因外部市場進入壁壘升高而引起供需不平衡問題。
王永中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大宗商品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