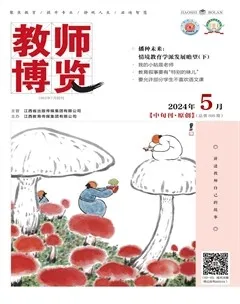我的小姑是老師
朱盈旭
一
我11歲那年,小姑當(dāng)了我的老師。
聽爹說,小姑那年沒考上大學(xué),落榜后,就被村里聘為民辦老師了。
彼時,我心里暗暗為她叫屈。我覺得小姑這樣一個人,在四壁漏風(fēng)的小教室里,在十幾張缺胳膊少腿的高桌子矮板凳前,在一群衣衫襤褸、鼻涕邋遢的鄉(xiāng)下臟兮兮的孩子堆里,軟語溫聲地教我們唐詩宋詞,太委屈她了。她應(yīng)該在綠窗下捧讀詩書,她應(yīng)該在城里明亮的辦公室里喝茶看報。
可她卻成了一群鄉(xiāng)下猴孩子的老師。她在荒園似的小破學(xué)校里,像一朵露水洗過的蘭花,清澈地明媚著,不動聲色地瀲滟著,叫人生起依戀與向往。
二
一向淘氣的猴孩子們突然乖極了,很聽話,也許都喜歡美人老師吧。
她說一口流利標(biāo)準(zhǔn)的普通話,聲音清甜,含一點點的軟糯,分外迷人。
她的語文課,我們一群十一二歲的鄉(xiāng)下孩子聽得如癡如醉,以至于常常聽不到鏗鏘的鈴聲。
小姑還擔(dān)任我們班的音樂老師、美術(shù)老師。她給我們上音樂課時,男孩子比我們女孩子還高興。他們爭先恐后地跑去老師辦公室或者別的班級,簇擁著去抬那架學(xué)校唯一的老舊的風(fēng)琴,一路上嘰嘰喳喳。
那架風(fēng)琴據(jù)說還是小姑向校長申請的。校長知道小姑是怎樣來到他這所破學(xué)校的。
三
彼時小姑落榜的事情最早被鄉(xiāng)里知道了。
鄉(xiāng)里唯一的中學(xué)奇缺這樣的才女啊!中學(xué)校長自掏腰包買了好煙好酒,連夜與鄉(xiāng)里管教育的干部一起,深一腳淺一腳地冒雨趕到三爺爺家。
好不容易叫開了門,一生清骨凜凜的三爺爺,對桌上的煙酒與眼前摔了一身濕泥巴的年輕校長眼皮子都不抬。一幫人磨破了嘴皮子,好話說了一籮筐。
最終,三爺爺還是拂袖而去,把一干人等訕訕地晾在了八仙桌前,未得其果。
聽娘說,彼時我們村小的校長,二話沒說,挽褲腿卷袖子,抄起一把糞勺跳進了糞坑。連著干了三天,直到把三爺爺一坑糞全出了,又撒進了田。
三爺爺手執(zhí)油黑發(fā)亮的小煙嘴,緩緩立在一截籬笆墻邊,不緊不慢地說一句:“就讓花妮去咱村小吧!”
其實,村里人都知道,三爺爺心里裝著一村的讀書娃呢。他不慕虛榮,不懼權(quán)貴,清白剛正,在村里一直德高望重。
四
小姑一下子替村小擔(dān)起了半壁江山。
音樂課與美術(shù)課也開起來了。村小校長樂呵呵地去鄉(xiāng)里中學(xué)討要風(fēng)琴,中學(xué)校長心懷妒意,未免惆悵,說了句:“唉,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便宜了你小子。”最終,他給了一架淘汰的風(fēng)琴。臨了,還說是看在小姑的面上。
小姑一點也不嫌棄,讓人把風(fēng)琴抬進她潔凈的小宿舍里,連著幾個有白月亮的晚上,搗搗鼓鼓,居然把舊風(fēng)琴修理調(diào)試好。
音樂課開起來了。
一群十一二歲的鄉(xiāng)下少年,在溪水般的歌聲里,漸漸衣衫白了,骨骼硬實了,像一群從莊稼與草木的莽莽蕩蕩中鉆出的小鷂子,要翻身了!
三爺爺瞇著眼睛,看門前經(jīng)過的上學(xué)放學(xué)的孩子們,像看著村里的寶貝。他呵呵笑著與荷鋤而歸的娃兒們的爹娘說:“這些娃兒,要出息了。”
要出息了!要出息了!娃兒們憨厚樸實的爹娘激動地笑,每一道粗糲的皺紋都閃著希望與喜悅。
五
我們像一株株生機蓬發(fā)的雨后小樹,在小姑的修理下,清新,有朝氣,神清氣爽,眉目有神。
每天清晨,衣衫清爽帶香氣的小姑,在干凈明亮的教室里巡視一圈又一圈,像山大王巡視自己的地盤。
爹娘在壟上直起腰身,沖彎彎的小路上雄赳赳氣昂昂的學(xué)生娃兒們,喜愛地喊一嗓子:“喲!那不是咱們的大學(xué)生嗎?”
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爹娘,掄起鋤頭也似乎更有力氣了。他們昔日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猴孩子,突然就讓三爺爺家的花妮老師給改頭換面了。
彼時,他們從自家孩子煥然一新的精氣神里,似乎看到了一條光明大道,正從草木葳蕤的村里延伸到村外更廣闊的天地去……
娃兒們的爹娘把平時母雞下的蛋,攢起來,悄悄地送到三爺爺?shù)脑钗堇铩?/p>
六
彼時的村子貧瘠,家家戶戶的籬笆院不上鎖,吃飯也端著碗串門。
小姑也不知道竹籃子里的雞蛋是哪家送的。干紅棗、焦花生、辣紅豇豆、腌蘿卜……零零碎碎,更不必說。
小姑給我們上音樂課,給我們的小臉蛋涂油彩。我們個個都唱得小臉紅撲撲,像雞冠子花一樣艷,小鼻頭上汗津津的。小肚子出了力氣,癟癟的,咕咕叫,像小布衫里各揣了一只小青蛙。
她挨個給我們擦汗,用她的花手絹,含著一股茉莉花香。然后從課桌下變戲法似的提出一籃子個頭大大的熟雞蛋,每人一顆,發(fā)給我們吃。
小姑看我們吃雞蛋,溫溫柔柔地笑著說:“慢點吃,別那么大口,當(dāng)心噎著……”當(dāng)時,她也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細心的我,看見她悄悄地咽口水。
彼時,我心里一酸。小姑偷偷吞咽口水的小動作,印在了我的腦海里,多少年了,鮮明深刻,未曾褪色。
七
小姑帶著我們開荒。
勞動課上,小姑輕衣短衫,黑發(fā)繞在腦后,挽了厚而圓的高髻,斜斜地插一支明晃晃的銀簪子,帶流蘇。那是三奶奶留給她的。
我們沿著村小矮矮的土墻,翻土、撒籽、種蔬菜,把扯下的長長的蔓生的野藤投到矮墻外的小水溝里去,漚肥。野生的綠藤,把小姑的手劃得血口子交錯橫生,讓人看著觸目驚心。
校長跑來幫忙。墻外的農(nóng)人隔著低矮的墻看過來,丟下手里的農(nóng)活也過來幫忙。
清理了野草的土地裸露出原始的肌膚,黝黑而泛著濕氣,像壯實的漢子。土膏松軟,我們把從家里帶來的種子放進去。胖胖的種子在泥土里涼涼軟軟地翻個身,一定會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八
美術(shù)課上,茹奶奶的孫女,一個瘦小單薄的小女孩,畫了張小姑的像。簡簡單單,甚至有點粗糙。
可小女孩給畫取了個妙極了的名字:我的小姑是老師。幾個稚氣清嫩的鉛筆字,寫在大辮子旁邊,歪歪斜斜,像小螞蟻爬過。
不料,畫被校長送到鄉(xiāng)里,鄉(xiāng)里送到縣里,居然得了三等獎。縣里點名讓小姑領(lǐng)著畫畫的學(xué)生去領(lǐng)獎。那天,校長不知從哪里借了一輛手扶拖拉機,興沖沖帶著她們?nèi)チ丝h里。
“突突突……”他們黃昏才回來。
小姑臉兒紅紅的,像一朵木芙蓉。小女孩捧著大紅的獎狀,小臉笑成了喇叭花。
大紅的獎狀,端端正正貼在了教室黃灰剝落的墻上,正前方,不偏不倚。
后來,我寫了一篇和那張畫同題的競賽作文:《我的小姑是老師》。結(jié)果得了個全縣一等獎。
當(dāng)然,我得的獎狀也和那張獎狀一起貼在了教室正前方。它們像兩盞明晃晃的燈,照進每個孩子的心中。
九
如果茹奶奶的孫女,那個畫小姑的小女孩沒有突然輟學(xué);如果小姑沒有每天夜晚去小女孩家替她照顧生病的娘和奶奶;如果那個冬天雪下得不那么大……也許,小姑會頂著紅蓋頭,做嬌羞的新娘;會被評為鄉(xiāng)里、縣里的優(yōu)秀教師,披紅戴花;會生兩個可愛聰明的娃娃,那金童玉女一樣的娃娃會拉著三爺爺?shù)氖郑搪暷虤獾睾巴夤H隣敔敃腋L鹈鄣匾皇掷鹨粋€,笑盈盈地跟荷鋤而歸的左鄰右舍打招呼……
可是,那年冬天,我的小姑,也是我的語文老師、我的音樂老師、我的美術(shù)老師、我的勞動老師,卻永遠地走了,把十八歲的青春定格在了那個大雪的冬天。
茹奶奶的兒媳婦,畫畫小女孩寡居多年的娘,在那個冬天第一場雪來臨時,突然中風(fēng)了!
照顧病人與年邁老人的重擔(dān)一下子壓在了一個小女孩的肩上。女孩默默收拾小書包,悄悄流著淚離開了課堂。
小姑知道了,心急如焚啊!她怎能舍得讓孩子輟學(xué)呢?她竭盡所能也要讓孩子重回課堂。
她與三爺爺拿出了多年的積蓄,給孩子的娘求醫(yī)問藥。她白天有繁重的課,抽不開身,就在每天晚上改完一天的作業(yè)后,急急忙忙趕回村子里去。
那個冬天雪下得驚心動魄,胖雪壓得瘦瘠的村莊東倒西歪。小姑批改完作業(yè)就冒著大雪,踩著幾乎齊膝的厚雪,打著手電筒往村子里趕。
那一晚,大雪像給大地扯了一床巨大的白棉被,兜頭蓋臉鋪下來,溝溝洼洼與田野全被掩蓋在了下面。改完作業(yè)的小姑往村里趕,也許有點累、有點怕。她一個人在雪地上迷了路,大雪之下再也分辨不出那條彎彎的熟悉小路在哪兒了。
她一步步踏進了白茫茫的田野,一步步走近了白雪覆蓋下的那眼枯井……
小姑被打撈上來的時候,已經(jīng)是出事后的第七天了。那一天,我們圍在她身邊。只見她微闔雙眼,兩排長睫毛像兩排溫柔的小梳子。她是睡著了嗎?
她叫朱蘭花。18歲,那年尚未涉情事,正美得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