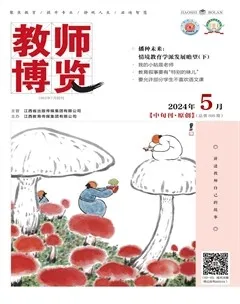父親的獨(dú)輪車(chē)
吳小街
我一直想給父親的獨(dú)輪車(chē)換個(gè)皮輪胎。
20世紀(jì)80年代,農(nóng)村里家家戶戶都有獨(dú)輪車(chē),人們用它來(lái)推谷、推牛糞、推石頭、接人等。開(kāi)始的時(shí)候,獨(dú)輪車(chē)的輪子都是木頭制作的。為了減少磨損,有人在輪子周?chē)描F皮包起來(lái),好處是耐磨,缺點(diǎn)是費(fèi)力,推到爛泥地里需要費(fèi)很大力氣才能推出;還有就是聲音大,“吱呀吱呀”的聲音非常難聽(tīng)。
14歲那年暑假,家里的早稻曬干了,父親要交公糧,就用獨(dú)輪車(chē)推到鄉(xiāng)糧管所。為了減輕父親的負(fù)擔(dān),祖母讓我用繩子綁住獨(dú)輪車(chē)車(chē)頭,遇到溝溝坎坎的地方就往前拉。
父親那個(gè)時(shí)候正值壯年,身體素質(zhì)好,推起四袋稻谷來(lái)健步如飛,根本就不用我拉,我反而覺(jué)得是父親在我身后催我快跑似的。只是進(jìn)了鄉(xiāng)糧管所門(mén)口水泥地就討厭了:鐵皮輪子跟水泥地摩擦的聲音太大,且不說(shuō)鐵皮跟水泥地摩擦發(fā)出的刺耳雜音,單聽(tīng)那個(gè)木軸轉(zhuǎn)的“吱呀吱呀”的聲音就讓人受不了。
那個(gè)時(shí)候好多人都換成皮制的輪胎,這樣推起來(lái)特別輕松。
像我家這樣的獨(dú)輪車(chē)非常少見(jiàn)了,街上有人見(jiàn)了父親,不知道是嘲笑還是同情:“老哥,你把民國(guó)時(shí)期的獨(dú)輪車(chē)換成輪胎的唄。”
那“吱呀吱呀”聲和鐵皮跟水泥地摩擦發(fā)出的巨大聲響深深刺激了我的神經(jīng),感覺(jué)那是路人鄙夷的眼神和嘲笑。我不知道父親當(dāng)時(shí)心情怎樣,因?yàn)槲也桓彝罂矗桓铱此难劬Α?/p>
到了糧管所門(mén)口,前來(lái)交公糧的車(chē)子都排了兩里路了,很多人熱得敞開(kāi)衣服,邊用草帽扇風(fēng)邊說(shuō)話,隊(duì)伍緩慢地往前移動(dòng)。鄉(xiāng)糧管所工作人員戴著麥帽,左手拿著一個(gè)小板板,右手拿著尖銳的糧食扦樣器。那時(shí)不知道那玩意兒怎樣弄的,插進(jìn)蛇皮袋子里再往回收,倒置扦樣器,糧食便會(huì)從手柄處的出料孔流出。工作人員把糧食倒在小板板上,又將幾粒稻谷放在嘴里啃瓜子一樣,然后說(shuō)一句:“到門(mén)口去稱!”這戶主人一聽(tīng),歡天喜地地等著去稱谷了。
戴著麥帽子的工作人員走到哪里,別人對(duì)他都是笑臉相迎。大家都遞煙點(diǎn)火,一個(gè)勁說(shuō)著奉承話,用前呼后擁來(lái)形容一點(diǎn)都不為過(guò)。
轉(zhuǎn)來(lái)轉(zhuǎn)去,終于到了父親這里,父親早就備好了熱忱討好的笑容,就差拱手作揖了。我到今天還記得那張冷漠的臉,工作人員面無(wú)表情,好像極不情愿地用扦樣器深深插進(jìn)蛇皮袋里,再抽出,倒了幾粒稻谷放在手心,啃了幾個(gè)。
“回去再曬兩天過(guò)來(lái)!”
這句話讓盛夏蒸籠一樣炎熱的天氣瞬間降到零度,父親頓感寒氣從頭蔓延到全身,就像站在南極的冰川上。
父親趕緊將笑容在臉上緊急集合:“同志,我家稻谷已經(jīng)曬了三天了,都是烈日下一天曬到晚,什么就不熟呢?”
“叫你推回去曬就推回去曬,我覺(jué)得還不夠。”
每一個(gè)字在父親心里結(jié)成了厚厚的寒冰。
父親張了張嘴,滿臉通紅,似乎想說(shuō)什么,但沒(méi)說(shuō),只能默默地掛好肩襻,推著他的鐵皮獨(dú)輪車(chē)返回。“吱呀吱呀”的聲響刺穿了我的耳膜。
回到家,祖母看著父親垂頭喪氣坐在凳子上抽煙,忙問(wèn)怎么回事。父親一五一十說(shuō)了,最后又說(shuō):“村里××家的稻谷跟我家一起曬的,他的都收了,我家的就不收?”
“能跟他比嗎?人家會(huì)來(lái)事。你沒(méi)看到,就在收公糧前一周,他家就請(qǐng)來(lái)鄉(xiāng)糧管所的人吃飯喝酒。”祖母說(shuō)。
“他們是狗眼看人低,可能看到我推著落后的土車(chē)子,一下就判斷出我們家的情況。”父親狠狠抽了一口煙。
兩天后,父親的獨(dú)輪車(chē)又上路了。
還是上次的那個(gè)人,依然是那張冷漠的臉。等了半天,他才慢騰騰到了父親這邊。啃了幾粒稻谷后,他讓父親把稻谷推到一角,那里有好幾臺(tái)風(fēng)車(chē),要父親再扇一次稻谷。
父親一肚子的不愿意,但沒(méi)辦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他叫我站在原地不動(dòng),自己一袋一袋扛到風(fēng)車(chē)那邊。我看到父親扛著一袋谷在送糧大軍里左穿右轉(zhuǎn),一會(huì)兒工夫,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等待的時(shí)間格外漫長(zhǎng)。
熱浪一陣一陣襲來(lái),我的耳邊只有眾人的喧鬧。
好不容易才等到父親把四袋稻谷扇完了,他走到那個(gè)驗(yàn)谷員那邊請(qǐng)示。驗(yàn)谷員把嘴里的稻谷吐了吐,手一揮,意思是讓父親把稻谷推過(guò)去稱。
父親高興極了,幾天來(lái)難得一見(jiàn)笑容的臉上恢復(fù)了往日的紅潤(rùn)。
父親再有力氣,碰到獨(dú)輪車(chē)就沒(méi)脾氣。天晴路好還好說(shuō),碰上刮風(fēng)下大雨,那又笨又重的車(chē)子陷進(jìn)淤泥里沒(méi)辦法推,有時(shí)累得滿頭大汗都推不起來(lái)。除了費(fèi)力,那獨(dú)輪車(chē)車(chē)軸發(fā)出的聲音特別難聽(tīng),“吱呀呀”“吱呀呀”“吱吱呀呀”“吱吱呀呀”,半里之外的人先是感受地面的微微顫動(dòng),然后是聽(tīng)到刺耳的聲音。
“什么時(shí)候能換個(gè)皮輪胎的車(chē)子呢?”有一次吃晚飯時(shí),父親揉揉肩膀跟家里人說(shuō)。
“家里兩個(gè)書(shū)包就夠你受的了。除了公糧外,賣(mài)不了多少稻谷,家里兩個(gè)書(shū)包,要花錢(qián)的地方太多了,還是勒緊褲帶過(guò)日子。”母親說(shuō)。
1990年,我家迎來(lái)最艱難的時(shí)刻。
這年暑假,祖母生病去世;中秋節(jié)前,我得了急性闌尾炎,經(jīng)過(guò)學(xué)校班主任努力,在鷹潭中醫(yī)院做了手術(shù),因?yàn)榧依餂](méi)錢(qián),我提前一周出院……寒假回家第二天,為了迎接春節(jié),父親用獨(dú)輪車(chē)將牛糞推到田野去,經(jīng)過(guò)村后碾子邊時(shí)突然暈倒,獨(dú)輪車(chē)撒手滾到一邊去了。村里人趕來(lái),七手八腳把父親抬到村醫(yī)家。醫(yī)生聽(tīng)了聽(tīng)父親的心臟,說(shuō)沒(méi)事沒(méi)事,就是缺乏營(yíng)養(yǎng),加上勞累過(guò)度,一會(huì)兒就醒了。
果然,過(guò)了二十分鐘后,父親睜開(kāi)了眼,看到哭得滿臉是淚的母親和我,連連說(shuō):“我怎么在這里?我不是推著牛糞嗎?車(chē)子呢?”
也就在那個(gè)時(shí)刻,我暗暗發(fā)誓:等我工作后第一個(gè)月的工資一定給父親換一個(gè)皮輪胎。
窮人家的生活每一分鐘都是那么漫長(zhǎng)!
黑夜漫漫,也有東方發(fā)白的時(shí)候。1992年8月,我?guī)煼懂厴I(yè)并走上工作崗位,10月下旬終于迎來(lái)我發(fā)工資的日子。我留了一點(diǎn)錢(qián)吃飯,其余的全部交給母親。我再三交代母親:欠的債慢慢還,父親的獨(dú)輪車(chē)胎一定要換!
“換,換,苦都苦過(guò)來(lái)了,不差這一兩個(gè)月。”母親緊緊捏著那筆錢(qián),瘦弱的腰桿好像挺直了不少,說(shuō)話中氣十足。
最開(kāi)心的是父親,推著皮輪胎的獨(dú)輪車(chē)回家,開(kāi)心得像個(gè)孩子一樣:“特別輕呢,感覺(jué)走路都輕快了好多!”
母親嗔罵他:“窮人沒(méi)得財(cái)主人家的碗見(jiàn),一個(gè)皮輪胎車(chē)子就高興成這樣!”
父親說(shuō):“你曉得什么,這車(chē)子再也沒(méi)有聲音了,轉(zhuǎn)起來(lái)人輕快了好多!”
那輛獨(dú)輪車(chē)從此伴隨父親的晚年生活。1992年,父親66歲,農(nóng)村人這樣的年齡還能干很多事情,捕魚(yú)、撿牛糞、種田……那輛獨(dú)輪車(chē)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2016年元月21日上午9點(diǎn)一刻,離春節(jié)還有半個(gè)月,父親再一次昏迷。我和母親一次又一次呼喚父親,希望能像20多年前一樣出現(xiàn)奇跡。
可是親愛(ài)的父親這次再?zèng)]能睜開(kāi)眼睛。
父親走后,那輛獨(dú)輪車(chē)沒(méi)有使用價(jià)值,幾年前被大哥放到老屋里去了,再過(guò)幾年也許就成為歷史文物了。
去年,母親帶著我和大哥翻修老屋時(shí),看到那輛獨(dú)輪車(chē)靜靜地待在一個(gè)角落里。看到它,我就想起父親,還有那個(gè)艱難困苦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