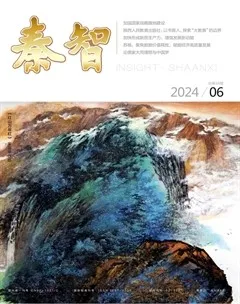淺析延安時期紅色經典聲樂作品價值研究
[摘要]延安時期的紅色經典聲樂作品是老一輩藝術家在戰火紛飛、物質艱苦的條件下所創作出的寶貴精神食糧,記載著艱苦的歲月中努力奮斗的歷史,具有極高的育人價值。1942年5月,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延安時期的文藝界具有強大的鼓舞作用,涌現出更多經久不衰的文藝作品。在新時期通過對延安時期的紅色經典聲樂作品的學習、傳唱、演出以及對作品的價值探究,可以培養新青年通過音樂更生動的走入延安時期的點點滴滴,不忘歷史、不忘初心,帶著老一輩不怕苦不怕累的紅色精神更加堅定的建設美好明天!
[關鍵詞]“一帶一路”;中外合作辦學;教學管理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4.06.030
一、“紅色經典”價值論述
(一)“紅色經典”在音樂領域的價值體現
“紅色經典”在音樂領域是至關重要的題材,是近代以來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先進音樂文化體系。提到紅色音樂就不得不提到延安時期的紅色經典音樂,其音樂作品不同于其他時期的紅色經典音樂作品。抗日救亡歌詠運動時期著名音樂家張寒暉以抗戰為背景創作了聲樂作品《軍民大生產》,著名音樂家馬可以抗戰為背景創作的《南泥灣》形象的記錄了在陜甘寧邊區在黨的領導下有序的領導、組織、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強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物質福利。1943年,音樂家安波根據陜甘寧邊區勞動模范馬巫恩與馬杏兒父女的事跡為原型創作的《兄妹開荒》,是秧歌劇運動中產生的第一個秧歌劇,它的主要內容是反映了當時的解放區大生產運動。1944年,誕生于黃土高原地區、由李有源作詞的民歌曲調《騎白馬》,李渙之作曲的《東方紅》,用樸實的語言傳遞著人民群眾的感恩之情。反映出了延安時期的紅色經典聲樂作品緊貼人民群眾,其創作源于群眾源于真實生活,音樂藝術不僅作為藝術欣賞的一種重要途徑,同時音樂藝術直觀的反映了中國近代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歷程[1]。
(二)“紅色經典”聲樂作品的特殊性
“紅色經典”以歌曲、合唱乃至民族歌劇等聲樂范疇的藝術作品為突出代表,其作品數量多、代表性強、傳播力度廣。特殊時期依靠歌詞傳播思想的革命歌曲,體現了用音樂傳播革命精神、增強革命信念、獲得革命力量的便捷性,很多革命的原理、精神通過深入淺出的歌詞和通俗好記的旋律深深的刻在革命軍民的心中。延安時期的音樂并不追求陽春白雪,而是要讓音樂貼近群眾,反映群眾的生活,并能讓群眾都參與進來;于是,文藝工作者們便發起了群眾歌詠活動。[2]
二、延安時期“紅色經典”聲樂創作的歷史價值
(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具體實踐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是實踐和認識的主體,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紅色歌曲源自于中國革命歷史,同時也反映了中國近代的革命歷史,通過演出傳唱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反響,成為黨中央和群眾之間的一座橋梁,形成了堅固的民族精神。藝術創作不是空中樓閣,而是現實的抽象映射;以藝術創作書寫革命歷史,真實地反映了特殊歷史時期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洋為中用”的音樂創作道路的具體實踐
延安時期的合唱是傳播革命思想、群眾歌詠活動的有機結合,其中以《黃河大合唱》最為著名。《黃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以黃河為背景,熱情歌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光榮歷史和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斗爭精神,痛訴侵略者的殘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災難,廣闊地展現了抗日戰爭的壯麗圖景,并向全中國全世界發出了民族解放的戰斗宣言,從而塑造起中華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3]共有八個樂章:第一樂章《黃河船夫曲》(混聲合唱),第二樂章《黃河頌》(男高音或男中音獨唱),第三樂章《黃河之水天上來》(配樂詩朗誦),第四樂章《黃水謠》(齊唱),第五樂章《河邊對口曲》(男聲對唱),第六樂章《黃河怨》(女高音獨唱),第七樂章《保衛黃河》(輪唱),第八樂章《怒吼吧,黃河》(混聲合唱),每個樂章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在樂曲開始前都會有一段朗誦作為導引以使樂章之間具有連貫性。它的創作技法豐富,音樂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配器采用“中西合璧”的寫法,運用交響樂團+民族樂器的形式,體現了黃河岸邊的英雄兒女抗日救亡的英勇精神[4]。
另外,《白毛女》是詩、歌、舞三者融合的民族新歌劇,采用北方的音樂語言、中國的唱念結合的戲曲形式、中國戲曲的分場方式;配器采用西方的管弦樂隊與中國樂器相結合的手法,融合了管弦樂編制的戲劇化的音響效果與民族樂器音色的獨特情緒表達;借鑒了古典戲曲的歌唱、吟誦、道白三者結合的傳統,糅合了若干民歌的旋律如河北民歌《青陽傳》、山西民歌《撿麥根》、河北民歌《小白菜》等,唱段念白吸收山西梆子的韻味,在西洋化的歌劇形式基礎上具有鮮明的中國風味。《白毛女》在秧歌劇的基礎上創造了新的民族藝術形式,是中國新歌劇集大成、開先河的重要奠基石[5]。
三、延安時期“紅色經典”聲樂創作的當代價值
(一)體現民族音樂精髓的傳承價值
歌劇是歐洲近代一種綜合性的大型藝術體裁。上世紀二十年代,黎錦暉曾寫了《麻雀與小孩》《小小畫家》等兒童歌舞劇為中國新歌劇的誕生打下重要基礎。再到后來,音樂工作者通過深入人民群眾的斗爭生活,通過開展新秧歌運動和進行秧歌劇的創作實踐,才逐漸找到了使歌劇這種藝術體裁在我國得以廣泛發展的正確途徑。延安時期的新歌劇創作內容緊貼人民大眾,創作風格上多是對地方民歌的改編但又在此基礎上借鑒西方歌劇的創作原則,尤其《白毛女》的誕生對中國以后自主創作歌劇具有一定的開辟意義,先后在延安演出30余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白毛女》逐漸走向世界,將中國“新歌劇”帶向全世界[6]。
(二)當代聲樂創作及表演的指導價值
延安時期的紅色經典聲樂作品,不僅是一段光輝的歷史記憶,也是一筆寶貴的藝術財富,它們對于當代聲樂創作及表演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1.經典作品對于聲樂創作的拓展和指導意義
①突破了傳統的音樂形式和風格,探索了多種新的音樂語言和表現手法
延安時期的聲樂創作,不拘泥于既有的音樂范式,而是根據不同的創作目的和對象,采用了多種音樂形式和風格,如大型合唱、歌劇、歌曲、詩朗誦等,實現了音樂形式的多樣化和豐富化;在音樂語言和表現手法上也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和實驗,如融合了中西方音樂元素,運用了多種調式、節奏、和聲、配器等技巧,創造了一種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氣息的新音樂風格。
《黃河大合唱》為當代聲樂創作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在音樂語言上既吸收了西方交響樂和合唱的結構和技巧,又融入了中國民間音樂和戲曲音樂的旋律和節奏,形成了一種獨特而鮮明的音樂風格;在表現手法上既運用了對比、變奏、復調等多種手法來增強音樂的張力和層次感,又運用了詩朗誦、歌頌、呼喊等多種方式來增強音樂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②緊密地聯系著時代主題和人民生活,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追求
延安時期的聲樂創作,是在抗日戰爭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它與時代的主題和要求密切相關,體現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情感,表達了人民的精神和理想;既有歌頌革命、抗日、建設的樂觀主義的歌曲,也有描繪人民生活、苦難、渴望的現實主義的歌曲,構成了一幅豐富而真實的音樂畫卷[7]。
《保衛黃河》為當代聲樂創作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在歌詞上運用了大量的比喻、擬人、夸張等修辭手法,如“黃河是我們的母親”“黃河怒吼著”“黃河水漲起來”等等,使得歌曲具有了強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在旋律上采用了高亢而激昂的調式和節奏,如“保衛黃河,保衛黃河”“打倒日本鬼子”等等,使得歌曲具有了強烈的激勵力和動員力。
2.經典作品對于聲樂表演的拓展和指導意義[8]
①突出了歌唱者與聽眾之間的互動和感染力,強調了歌唱者對作品內容和情感的理解和表達
延安時期的聲樂表演,是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下進行的,它與聽眾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和共鳴,體現了歌唱者與聽眾之間的同心同德、共同抗敵;不僅要求歌唱者具有良好的嗓音和技巧,更要求歌唱者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情感,能夠準確地理解和表達作品的主旨和精神,能夠用真誠和熱情的態度去感染和鼓舞聽眾[9]。
《白毛女》為當代聲樂表演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它要求歌唱者不僅要有優美而富有表現力的嗓音,還要有精湛而富有變化的演技,能夠根據不同的場景和情境、運用不同的唱法和表情來展現喜兒復雜而多變的心理變化。
②注重了歌唱者與舞臺、道具、服裝等視覺元素的結合,增強了歌唱者的表現力和藝術感染力
延安時期的聲樂表演,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的,它沒有豪華的舞臺和燈光、沒有精美的道具和服裝,但卻能夠充分利用有限的視覺元素,與歌唱者的聲音和動作相結合,形成了一種獨特而富有表現力的藝術效果;既有利于突出歌唱者的主體地位和作品的主題意義,又有利于創造出一種富有象征意義和審美價值的藝術形象[9]。
《黃河大合唱》為當代聲樂表演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在舞臺上運用了各種不同的服裝、道具、布景等視覺元素,與歌唱者的聲音和動作相結合,形成了一幅生動而震撼的抗日畫卷;這些視覺元素不僅增強了歌唱者的表現力和藝術感染力,也增強了作品的主題意義和象征意義。
四、結語
延安時期的紅色經典聲樂作品,不僅具有深刻的歷史價值,反映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英雄主義和斗爭精神;也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展現了中國音樂家在音樂創作和表演方面的創新和探索,融合了中西方音樂元素,體現了中國音樂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對于當代聲樂創作及表演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形式、風格、內容、技巧等方面的選擇,鼓勵我們在繼承和發展傳統音樂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大膽的創新和實驗,關注社會現實,反映時代精神,以人民為中心,增強歌唱者與聽眾之間的互動和感染力[10]。
延安時期的紅色經典聲樂作品,是我們學習音樂、熱愛音樂、傳承音樂的重要資源,不僅能夠豐富我們的音樂知識和審美情趣,也能夠激發我們的愛國情感和革命意識。在當下時代背景之下,我們必須更加珍視并傳承這些經典作品,充分發揮其在現代社會和音樂領域的深遠影響,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應有的力量。
參考文獻:
[1]項筱剛.論“延安時期”音樂創作[J].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21(3):15-21+165.
[2]趙宇濤.延安時期音樂創作的歷史考察及其當代啟示[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3(4):38-43.
[3]潘勛.紅色經典音樂的文化闡釋——以《黃河大合唱》為例[J].商洛學院學報,2012,26(1):73-75.
[4]文曉園.古箏重奏《黃河》藝術特色與演奏分析[D].江蘇:揚州大學,2022.
[5]漆欣欣.淺談歌劇《白毛女》的創作特點與藝術成就[J].明日風尚,2019(7):90.
[6]蘇丹.延安時期(1935-1948)延安地區音樂文化的傳播研究[D].陜西:西安音樂學院,2016.
[7]鞠宏馳.“小魯藝”到“大魯藝”的精神內核與啟示[J].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23,42(4):143-147.
[8]石蘇平.延安時期音樂藝術的價值研究[D].陜西:西安石油大學,2012.
[9]楊陽,黃蓉.延安魯藝時期陜北民間音樂美學研究[J].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綜合版),2021,21(5):148-152.
[10]黃斯綺.冼星海三首不同時期抗戰聲樂作品音樂與演唱探析[D].廣西:廣西師范大學,2017.
基金項目:遼寧省教育廳高等學校基本科研項目(青年項目),項目名稱:論延安時期“紅色經典”聲樂作品的價值與意義(項目編號:LJKQR2021029)
作者簡介:錢京濤(1982.6-),男,漢族,山東淄博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聲樂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