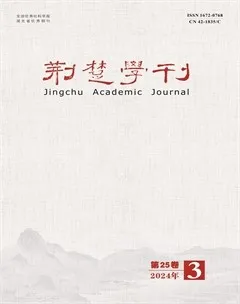《紅樓夢》中玉石鏡像與幻設情境的儀式特征
潘淼
摘要:《紅樓夢》整體框架符合神話-儀式的“結構性原理”,而“無材補天”之頑石的“石—玉—石”和“幻形入世”之寶玉的“空—色—空”的歷程呈現明顯的“過渡禮儀”特征。女媧補天棄用的頑石通靈后被一僧一道幻化為“鮮明瑩潔的美玉”,“銜玉而生”取名寶玉進入“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的賈府。他既不是賈寶玉又不是甄寶玉,或者既是賈寶玉又是甄寶玉;他既不在石頭城又不在長安城,既不在大觀園又不在太虛幻境。這個“假作真時真亦假”的閾限人、邊緣人或臨界人無法在“無為有處有還無”之“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安身樂業”,經歷了情感糾葛的“離合悲歡”,嘗盡了賈府盛衰的“炎涼世態”,“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乃隨一僧一道重返大荒。玉、色的世界以及大觀園和賈府“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生活終是“太虛幻境”般的過眼云煙,唯鑄刻于石上之文成為永恒。
關鍵詞:《紅樓夢》;儀式;神話;頑石;寶玉;大觀園;太虛幻境
中圖分類號:I207.411?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2-0768(2024)03-0014-06
方克強指出,《紅樓夢》“存在著兩個互滲互補的子系統,即現實系統與神話系統。”[ 1 ] 143楊義以為《紅樓夢》是“人書與天書的詩意融合”[ 2 ] 591-593;陳維昭也認為《紅樓夢》“從真實性與邏輯的觀點看,這個象征實體分為兩個敘述層次,即超驗敘述與寫實敘述”[ 3 ]。其實,“現實系統與神話系統”“人書與天書”“超驗敘述與寫實敘述”均指向愛彌兒·涂爾干所說的“信仰和儀式”之關系:“信仰是輿論的狀況,是由各種表現構成的;儀式則是某些明確的行為方式。”[ 4 ] 45或如克拉克洪所說的“神話和儀式”之關系:“神話與儀式都是象征的程序,并極緊密的因此(也因其他事實)而聯系起來。神話是一個語詞構成的象征系統,而儀式是對目的和行動組成的象征系統。兩者都是針對同一類型和情景,而以同一感情形式來對待的象征過程。”[ 5 ] 151如此,彭兆榮談及神話與儀式的關系問題時,涉及到的“結構性原理”對我們頗有啟發。所謂結構性原理,“即傾向于把神話視為信仰的、理念的、理性的、理論的表現;而儀式則成了行為的、具體的、感性的、實踐的配合……人們很容易地可以通過一個儀式回顧一個相對應的神話傳說;同理,神話傳說也經常可以推衍出具有儀式性色彩的行為和實踐。”[ 6 ] 24《紅樓夢》的結構設計巧合神話-儀式的“結構性原理”,其石頭之記文引出的女媧補天、絳珠還淚、太虛幻境神話自有其深層的背景意義;“無材補天”之頑石的“石—玉—石”和“幻形入世”之寶玉的“空—色—空”的歷程則呈現明顯的儀式特征,且與人類學家范熱內普“過渡禮儀”理論暗合。
范熱內普認為一切過渡禮儀有三個階段:分離、邊緣(或閾限)、聚合。儀式主體在居間的閾限時期不具有過去的或將來的狀態的任何特性在第三個階段轉化完成。閾限時期的“過渡者”,“它們既不是這種東西又不是那種東西;或者既是這種東西又是那種東西;它們的位置既不在這里也不在那里(按照公認的文化地志);甚至無處可安置,它們最低限度是介于所有公認的結構分類的時空固空點之間的‘模棱兩可的東西。”[ 7 ] 517維克多·特納在《模棱兩可:過關禮儀的閾限時期》提出的最具理論特色的“兩可之間”或“模棱兩可”,正對應著“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副在“太虛幻境”中的對聯。“天上人間諸景備”,石頭記乃“人間”戲劇精要的神話說明,紅樓一夢是“天上”神話繁復的儀式表演。作為個體的棄用的補天頑石通靈而為寶玉,“銜玉而生”取名寶玉進入集體賈府,經歷了事業與情感的磨難即所謂“離合悲歡”,嘗盡了賈府盛衰的“炎涼世態”,“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重返大荒。
一、賈寶玉和甄寶玉:玉石鏡像與過渡者
女媧氏煉石補天所棄之石因聽一僧一道“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便有思凡之想,于是僧人便念咒書符大展幻術,將這塊大石登時縮變成一塊扇墜大小一般、可佩于身可玩于掌的鮮明瑩潔的美玉。那僧人便托這美玉于掌上,笑它形體雖是寶物,但要讓人覺得奇物方妙,還須鐫上數字再攜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 8 ] 2-3這“一僧一道”在甄士隱夢中將“蠢物”“交割”于“太虛幻境”的警幻仙子,讓其夾帶在一干“尚未投胎入世”的“風流冤家”之中去了結“一段風流公案。”
“無材可去補蒼天”是《紅樓夢》“書之本旨”[ 9 ] 103。賈寶玉在神話世界里即“無材可去補蒼天”的一塊“頑石”,癩僧跛道口中的“蠢物”。我們認識凡俗世界的賈寶玉由賈雨村的朋友“冷眼旁觀人”古董商人冷子興率先介紹:因銜玉而生,其祖母便愛如珍寶。因抓周時只抓脂粉釵環,其父賈政便大不喜悅,以為“將來酒色之徒耳”。長到七八歲,便說了特別驚奇的話,“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所以冷子興也以為“將來色鬼無疑了”(第2回),這本是下人的看法,因為冷子興的情報來源于他的岳母周瑞家的。同是下人的傅秋芳家里的兩個老婆子到怡紅院見識了寶玉,都以為“果然有些呆氣”“千真萬真的有些呆氣”,因為“他自己燙了手,倒問人疼不疼”“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第35回)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當十分熟悉寶玉,他向尤二姐、尤三姐介紹寶玉說他不喜歡看書,雖然外頭大家都看著好一個清俊的模樣,卻是個外清內濁的人,每日不習文、不習武,又畏見人,唯喜愛跟丫頭玩鬧。
寶玉的奶奶賈母卻不這樣看,說從沒見過這樣的孩子,這般同丫頭們好,實在是難懂得不得了。賈母因此也時常擔心,經常冷眼旁觀,以為他與丫頭們嬉戲,必是人大心大,男女之事皆知,故愛親近。可細查又不是如此,只覺令人詫異,想必本來就是個投錯胎的丫頭!賈雨村也不以為寶玉是“色鬼”,并舉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為例:甄家有這么一個學生,深得祖母溺愛,也有些奇怪的話,什么“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什么“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凈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癡,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因此,被他的父親“下死笞楚過幾次”,都無可奈何地改不了。每次打到痛得不行時,他都會“妹妹”“姐姐”般亂叫。活脫脫又一個賈寶玉,不過人叫甄寶玉。
其后的甄寶玉,總若隱若現地存在,到第56回江南甄家進宮朝賀,到訪賈府的人說到甄、賈寶玉模樣、性情都相仿佛。賈寶玉不見甄寶玉,心中念想,不知不覺到了園子里。寶玉詫異于除了大觀園更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間,從那邊來了幾個丫環,寶玉又詫異于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那些丫環以為是她們家的寶玉,一聽寶玉說話,原來不是她們家的寶玉。寶玉忙問這里也更還有個寶玉?丫環們則不許他叫寶玉二字,罵他是遠方來的臭小廝,把她們都熏臭了。
寶玉納悶著,難道真有個如此相像的人不成?一邊想著,一邊往里走。走到了一個院子里,又驚道:“如此庭院,除怡紅院外,更甚矣。”再往里走,只見榻上有個人躺在那,旁邊有幾個做針線的女孩兒,嬉笑嬉鬧著不亦樂乎。只見那榻上少年仰天長嘆,一位侍女笑著說:“寶玉,何言不寐?想必是為了妹妹抱病,把你愁得焦頭爛額。”寶玉聞之,心驚不已。又聽到榻上少年說:“聽聞長安亦有寶玉,性情與吾同,吾唯不信。竟夢見到了都中的一個花園里,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里頭,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寶玉聞之,忙說道:“吾因尋寶玉而至。原來你才是寶玉?”榻上少年急忙一把拉住了寶玉說:“原來你是寶玉?這可不是夢中的情景?”寶玉說:“這怎么能是夢呢?”一語未盡,來了個人說老爺想見寶玉,嚇得兩個人都慌了神!一個寶玉趕緊離去,一個寶玉忙不迭地叫著:“快回來,快回來!”
原來不過鏡像。襲人說了實話,“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里照的你影兒。”卡西爾說:“在亞爾噶阡印第安人部落里,一個人的名稱若與另一人相同,他就會被看成是那個人的另一個自我,他的‘另一個我。”[ 10 ] 74賈寶玉、甄寶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甄寶玉只是賈寶玉的影子。是影子,就有看不真切的,“空有皮囊”;及見“真性”,賈寶玉大失所望。
江南甄家蒙圣恩起復,甄寶玉千呼萬喚始出來。賈寶玉“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想到夢中之景,并且素知甄寶玉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為得了知己。”然一番談論之后,寶玉“詫異”莫名,以為“祿蠹的舊套”。寶釵問賈寶玉:“那甄寶玉果然像你么?”“雖然外表看起來很像,但在交談中發現似乎也是個祿蠹”,寶玉說道,“可惜他也生出如此模樣,這樣我甚至不想要我那樣的相貌。”也是真假孫悟空的一場爭斗,周春《閱紅樓夢隨筆》有“甄賈兩寶玉,從《西游記》兩行者脫胎”一說[ 9 ] 530。浦安迪亦認為“真假寶玉人魂并現的情節——‘真(甄)寶玉緬懷自己南京的家園,‘假(賈)寶玉在京中真真假假的夢幻——似乎是一種明顯的游戲筆墨,甚至可貶為俗氣的謔頭。然而,仔細分辨一下,可以看出作者是在認真地對待其中的哲理的,因為‘真假情節開場而追出全書的寓意,實在是經過一番苦心策劃的。”[ 11 ] 159-160
“后人有《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恰”:“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第3回)既不知“安身”,又不知“樂業”,充滿維克多·特納所說的閾限人、邊緣人或是“臨界人”所擁有的顛覆社會性和逆反儀式性的行為。他認為這些人充滿熱情和激情,要設法從生活中除去那些與“占有地位”和“扮演角色”掛鉤的陳詞濫調,以便無論這種關系是真實存在的,還是假想出來的,都能融入到一種生機勃勃、與他人結成的關系中去。不過,好在有僧道托底。一僧一道將女媧補天棄用的一塊頑石幻化為寶玉攜入警幻仙姑所主之太虛幻境并墮入紅塵,時刻以引路人或保護者的身份指導其在“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安身樂業”。寶玉“為聲色貨利所迷”遭逢五鬼時,僧道入賈府祝玉,想“頑石”之時,“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卻因鍛煉通靈后,便向人間覓是非。”看今日“寶玉”,“粉漬脂痕污寶光,綺櫳晝夜困鴛鴦”;并告誡教導:“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孽償清好散場。”還提出希望:“塵緣滿日,若似彈指!”而當寶玉失玉癡傻瘋癲,到了預備后事的時候,那僧將玉送還,寶玉便隨僧到了“真如福地”——太虛幻境,見大門對聯也換成“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似乎暗示假寶玉回歸真頑石了,那僧亦教導他“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點醒寶玉“來處來去處去”。到了寶玉該還玉的時候了,寶玉未認同甄寶玉的仕途經濟之路而是印證了黛玉的“無立足境,是方干凈”的“悟徹”,舍棄了與襲人、寶釵的終老白頭,決然遁入空門,“劫終之日,復還本質。”還玉之后,他就是頑石。“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劫的”,經過閾限期的歷練,塵緣已滿,“那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峰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云游而去。”“我所居兮,青梗之峰。我所游兮,鴻蒙太空。誰與我逝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頑石”幻化為“美玉”是賈寶玉而非甄寶玉,而“美玉”復還“頑石”則是甄寶玉而非賈寶玉。作為閾限時期的“過渡者”,脫離過去固有的“頑石”狀態,進入到體量、品質、價值——身份、地位、處境等都存在巨大差異的“美玉”狀態,心理落差也大,相互之間的特征體認并不是非常的清晰。所以在玉石、真假的鏡像中,他既不是賈寶玉又不是甄寶玉,或者既是賈寶玉又是甄寶玉。有一僧一道的加持,他自帶仙氣,不同凡響;投身世俗,無拘無束;標新領異,“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如王希廉所說:“《紅樓夢》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為作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 12 ] 568
二、太虛幻境和大觀園:夢幻現實皆閾限
寶玉夢中忽見“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司掌人間之風情月債、塵世之女怨男癡的警幻仙姑,邀其一游“太虛”。寶玉欣然隨往,到了個石牌上書寫著“太虛幻境”四個大字的地方,石牌兩側有對聯一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寶玉曾作為“蠢物”被癩僧跛道帶入警幻仙子宮中,故此番系再入“太虛幻境”。警幻仙姑帶寶玉經過書有“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對聯的“孽海情天”門,來到書有“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對聯的“薄命司”,寶玉先展開“金陵十二釵又副冊”,看了晴雯和襲人的畫面預示及判詞,不悟;遂開“金陵十二釵副冊”,看了香菱的畫面預示及判詞,仍不悟。寶玉直取“金陵十二釵正冊”,看了寶釵、黛玉、元春、探春、湘云、妙玉、迎春、惜春、熙鳳、巧姐、李紈、秦可卿的畫面預示及判詞,仍欲細看。警幻仙姑恐泄了天機,遂領寶玉游玩奇景,讓寶玉聞“群芳髓”香,喝“千紅一窟”茶,飲“萬艷同杯”酒,然后十二舞女演唱新制《紅樓夢》十二支曲。
“《紅樓夢》寫夢境乃至以‘紅樓之‘夢命名全書,并不在于小說中寫了多少個夢,或夢長或夢短,而在于立意寫法別開生面——引神寓意,托筆夢幻,以夢說破千古事。”[ 13 ] 255太虛幻境神話與現實世界的大觀園遙相呼應,互為鏡像;寶玉夢游太虛幻境,乃后之在“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生活的彩排。整部太虛幻境神話規定了寶、黛、釵等主要人物的一生遭際和命運走向及賈府的衰亡。悲劇的調子已定,“人間”大觀園開演在即。
王希廉《紅樓夢總評》曰:“《紅樓夢》雖是說賈府盛衰情事,其實專為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作。”[ 9 ] 537《紅樓夢曲》[引子]即托出大綱:“懷金悼玉”;緊接著[終身誤]概括到位:“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黛玉有“木石前盟”,寶釵有“金玉良姻”。“木石前盟”即“還淚神話”,乃甄士隱夢中聽“一僧一道”之“一僧”說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絳珠草,一面靠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一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后來得以脫卻草胎木質,修成個女體,終日游于離恨天外。恰在近日,這位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世之機,意欲下凡造化幻境。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倒可了結。那絳珠仙子說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第1回)
“木石前盟”似乎任何外在力量都無法破壞和摧毀。寶黛初見就似曾相識:“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而寶玉見林妹妹素未謀面,竟脫口而出:“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定然“眼熟”,確是“舊相識”,“還淚”的新神話正式登場。
到第8回寶玉去看寶釵,寶釵說要細細地賞鑒他“落草時銜下來的寶玉”,“寶釵托于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癩僧所鐫”正面有“通靈寶玉”四個大字,下面是“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八個小字,反面為“一除邪祟;二療冤疾;三知禍福”三行字。寶釵若有所思地念了兩遍“莫失莫忘,仙壽恒昌”,還是她丫頭鶯兒說得直白:“我聽這兩句話,倒象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當然要賞鑒賞鑒,“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字,共成兩句吉讖:“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寶釵說:“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上了,叫天天帶著。”這個人是誰呢?又是丫環鶯兒說了出來,“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原來還是那僧,且將“一對兒”許給了寶釵和寶玉。薛姨媽曾對王夫人等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第28回)有薛蟠埋怨寶釵的話為證:“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第34回)
黛釵均有自娘胎帶來的病。第3回林黛玉初進賈府回答眾人的關心:“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日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在黛玉三歲的時候,家里來了個瘋瘋癲癲的癩頭和尚,說要帶她出家,黛玉爹娘不肯。那癩頭和尚便說:“既不舍其身,惟恐其病平生不得好也。若要好時,除非從此再也不哭,且所有外姓親友也都不能見了,這輩子才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
第7回薛寶釵回應周瑞家的關心:“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呢。憑你什么名醫仙藥,從不見一點兒效。后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癥,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里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還不相干;若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藥倒效驗些。”藥名“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
黛玉之病無藥可治,除非出家;即使不出家須“不見哭聲”,“除父母外”不見外姓之人,實與出家無異。做不到,病“一生也不能好。”寶釵之病則有藥可醫,雖一時難制得天時地利人和的“冷香丸”,居然“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癩頭和尚也偏愛如此,不過也不怪他,誰讓林黛玉是絳珠草呢,入世只是還淚,“淚盡”再回神界。
黛玉有“奇香”,寶釵有“冷香”。第19回寶玉在黛玉處“只聞得一股幽香”“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欲知究竟,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么‘羅漢‘真人給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弟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制。”進而問寶玉有“暖香”沒有,寶玉不解,黛玉點頭嘆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直指第8回寶玉在寶釵處“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系何香氣”,原來因吃過“冷香丸”的緣故。
寶玉實難取舍,“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太虛幻境中警幻仙姑許配給他的“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的“乳名兼美字可卿者”似乎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庚辰本四十二回回前脂硯齋即評曰:“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但寶玉還是有所取舍,當寶玉聽到興隆村的大爺賈雨村來要他陪話時老大不樂意,湘云勸說寶玉,不愿意讀書考舉人、進士也就罷了,也該會會那些為官做宰的人們,別成天跟著姑娘們玩鬧。結果遭到寶玉毫不客氣地驅離:“姑娘請別的姊妹屋里坐坐,我這里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寶釵有時見機導勸,他也生氣,說“好好的一個清凈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后世的須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第36回)即使美麗聰慧如寶釵、湘云,寶玉也深為痛恨,再不見女兒的“清爽”,而是男子的“濁臭逼人”,因為她們喜歡男人喜歡的“仕途經濟”。所以寶玉夢中大呼:“僧道之言,何以信之?金玉良緣為何物,我偏說是木石姻緣!”(第36回)明確無誤地選擇了林妹妹。
當然還有家族的選擇、家長的選擇。“任是無情也動人”“艷冠群芳”(第63回)的薛寶釵因其逢迎有術不僅深得皇妃元春的喜愛,還深獲賈母、王夫人的好評。況且寶釵因其豁達與親和“大得下人之心”,相比于黛玉的“計較”“有心”和“孤高自許”也是占盡上風。所以黛玉雖有寶玉的心心相印,到底敵不過家族家長們的同心協力。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說:“賈母愛寶釵之婉嫕,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王夫人故親于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第81回)之語,懼禍之及,而自同于鳳姐,亦自然之勢也。”[ 14 ] 158于是在寶玉失玉后的瘋癲中,“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而“薛寶釵出閨成大禮”(第97回),“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第98回)然正如成就寶玉、寶釵“金玉良姻”的通靈寶玉上的“莫失莫忘,仙壽恒昌”、辟邪金鎖上的“不離不棄,芳齡永繼”之“仙壽”“芳齡”,寶玉的出家,“癩僧”已有安排;寶玉掛在口邊的只對林黛玉說的玩笑話“你死了,我做和尚”,無意中已自我設定(第30回、第31回);亦如寶釵自作元宵燈謎《更香》所示:“朝罷誰攜兩袖煙,琴邊衾里總無緣”“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孤凄寡居已命中注定(第22回);第62回探春為平兒慶生,寶玉寶釵射覆,“寶釵覆了一個‘寶字”,寶玉“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又加香菱神補刀,說李義山七言絕句有“寶釵無日不生塵”,似乎也暗示了寶釵婚后的孤寂。
西湖散人《紅樓夢影序》說“《紅樓夢》一書,本名《石頭記》,所記絳珠仙草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修成女身,立愿托生人世,以淚償之。此極奇幻之事,而至理深情,獨有千古。作者不惜鏤肝刻腎,讀者得以娛目賞心,幾至家弦戶誦,雅俗共賞,咸知絳珠有償淚之愿,無終身之約,淚盡歸仙,再難留戀人間;神瑛無木石之緣,有金石之訂,理當涉世,以了應為之事。此《紅樓夢》始終之大旨也。”[ 12 ] 623絳珠草修成女身為黛玉,黛玉又為芙蓉花,而寶釵為牡丹、探春為杏花、湘云為海棠、李紈為梅花、麝月為荼蘼花、香菱為并蒂花、襲人為桃花(第63回)等等。花的命運是注定的,黛玉《葬花吟》領悟透徹:“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漂泊難尋覓……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感花傷己”,凄涼的身世和淚盡而亡的情感袒露無遺(第27回)。即如寶玉聽后由黛玉推之寶釵、香菱、襲人等這些花們的命運,無非“春殘花漸落”“春盡紅顏老”。甲戌本回末總評說:“埋香冢葬花乃諸艷歸源,《葬花吟》又系諸艷一偈也。”[ 9 ] 416“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眾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餞花神,第62回記黛玉二月十二生日恰與花神同,歡快中早埋下《葬花吟》悲情。
“絳珠還淚”呈現出一種時序儀式,時序的遞嬗與人的生命生存休戚相關。范熱內普說:“將人類生命階段與動植物生命之存在相聯,以一種類似前科學預示之方式,再將它們與宇宙之偉大節奏聯系起來,這無疑是個劃時代的觀念。”[ 15 ] 140-141春去秋來,四季交替,萬物枯榮,生命亦隨之興盛衰亡。季節之變更,物候之不同,感之深者花草也。草木的世界,絳珠是代表;花兒的世界,芙蓉是代表;女兒的世界,黛玉是代表。草木易凋,花兒易謝,“女兒命薄”,正是“太虛幻境”之“薄命司”命意所在。“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葬花吟》)所以“三春去后諸芳盡”(秦可卿死前贈鳳姐話),原(元春)應(迎春)嘆(探春)息(惜春)。
“太虛”似無實有,似有實無,正是“無為有處有還無”;“幻境”,似真實假,似假實真,正是“假作真時真亦假”。女媧補天遺棄的“蠢物”“頑石”,被移除到已經構建的秩序之外,在“人間”大觀園浮沉,在情感、情愛的花花世界蕩漾。閾限中的賈寶玉既不在石頭城又不在長安城,既不在大觀園又不在太虛幻境,在習俗、傳統、規范等之外的模棱兩可的“固空點”上,歷經“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磨難;伴隨著他“木石前盟”“金玉良姻”的愛情以及“人間”大觀園的毀滅,他所依附的“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賈府的“樹倒猢猻散”,終至“懸崖撒手”割斷情緣,“棄而為僧”“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神話中的“頑石”“蠢物”,不甘“無材補天”,有幸“靈性已通”,得愿人間從頭再來;然即便是“通靈”“寶玉”,在神圣與世俗間自由往來,到頭仍“萬境歸空”。“在通過儀式中,人們從結構中被釋放出來之后,仍然要回到結構之中,而他們所經歷的交融,已經為此時的結構重新注入了活力。”[ 16 ] 130大觀園的生活終是“太虛幻境”般的過眼云煙,唯鑄刻于石上的文字成為永恒。
參考文獻:
[1]方克強.文學人類學批評[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2]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3]陳維昭.《紅樓夢》的敘事結構[J].紅樓夢學刊.1991(2):113-129.
[4]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東,汲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5]克萊德·克拉克洪.神話和儀式:一般的理論[C]//史宗.20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金澤,宋立道,徐大建,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
[6]彭兆榮.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7]維克多·特納.模棱兩可:過關禮儀的閾限時期[C]//史宗.20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金澤,宋立道,徐大建,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
[8]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9]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G].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
[10]恩斯特·卡西爾.語言與神話[M].于曉,等,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11]浦安迪.中國敘事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12]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13]胡文彬.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M].北京:中國書店,2005.
[14]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下[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15]阿諾爾德·范熱內普.過渡禮儀[M].張舉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6]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M].黃劍波,柳博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