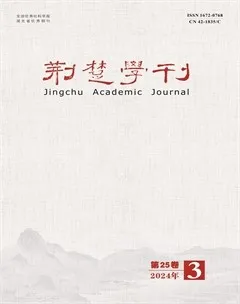健康環境權實有化的實踐檢視與路徑探析
李想
摘要:健康環境權的實有化趨勢方興未艾。現有國際法規范的發展困境和新型全球環境治理關系的現實需要對健康環境權保護提出新的挑戰。實踐中,聯合國系統對健康環境權的保護路徑借助大會決議由“綠化”現有人權向創設基本人權轉化,歐洲和美洲則通過司法實踐在區域人權公約體系下助推健康環境權實有化。然而,當前國際法實踐對于健康環境權實有化具有理念引領不足、規范效力有限和治理體系分散的缺陷。中國在全球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通過價值引領、法治保障和國際合作等方式,為健康環境權保護提供優化路徑。
關鍵詞:健康環境權;實有人權;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環境治理;人權保護
中圖分類號:D912.6?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2-0768(2024)04-0063-06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人類應該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朝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不斷邁進,共同創造更加美好未來”[ 1 ]。全球環境問題的嚴峻趨勢,特別是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日本推進核污水排海等事件,敦促國際人權話語聚焦至健康環境權(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作為新興的第三代人權,健康環境權勾連著環境與人權兩大熱點議題,將各國可持續發展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李步云先生曾提出,人權的三種形態包括“應有”“法定”和“實有”[ 2 ]。聯合國大會已于2022年7月通過第76/300號決議,在全球層面首次承認健康環境權以一種自主(autonomous)形態的基本人權立于人權之林,歐洲和美洲的人權司法實踐亦對該命題展開了一定闡釋,其實有化趨勢方興未艾。然而,全球尚未形成以國際公約為核心的健康環境權保護法律制度,區域性保護機制的發展呈現出碎片化、不平衡的樣態,一些國家更任性地以自身利益為根本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忽視環境保護長期效益。面對健康環境權的理論供給不足和現實發展困境,以及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新型全球環境治理關系的現實需要,本文通過梳理健康環境權實有化的國際法實踐,審視并分析該權利保護的法律缺位,展望其實有化進程中的中國闡釋和貢獻。
一、健康環境權實有化的實踐考察
健康環境權暫無統一學理定義。代表性觀點如馮慶旭認為,健康環境權即每個人有權生活在有一定品質保證的環境中[ 3 ];簡·漢考克則認為健康環境權主要是享有自然資源和不受有毒污染環境的權利[ 4 ],他們主要是從健康環境權的實體層面來討論的。實踐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8/13號決議稱之為“享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環境的權利”(the? right? to? a?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1988年《圣薩爾瓦多議定書》第11條則將它定義為“每個人應有權在健康的環境中生活,有權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但它們還不足以達到創造一種國際習慣法或國際法原則的程度。本文認為,健康環境權是實體權利和程序權利的有機統一。在權利實有化的進程中,程序權利如信息知情權和參與決策權的實現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它是實體權利的保障,也有助于確定實體權利的具體權能。健康環境權也必須與“環境的權利”(rights? of? the? environment)所區分,后者是一些法律規范授予自然環境及其造物的權利,如維持其代際結構和進化過程等[ 5 ],這是生態中心主義影響下的結果。
(一)聯合國系統:從“綠化”到“獨立”的健康環境權
在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中,有四項均與防止環境惡化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但健康環境權在聯合國系統內從派生性權利走到基本人權的路程十分漫長。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通過的《斯德哥爾摩宣言》首次正式將人權與環境保護聯系起來。程序權利則是1992年《里約宣言》對健康環境權最重要的補充,該宣言原則上承認了公眾參與決策權和獲得救濟權的重要性。傳統的解釋路徑認為,健康環境權的內涵包含于其他基本人權(如生命權、健康權)的范圍之中,環境保護應基于現有人權框架開展,即人權的“綠化”。1994年5月,人權和環境保護問題國際專家組基于上述兩份宣言起草了一份全面聯系人權與環境的《人權與環境原則宣言草案》,明確指出所有人都有權享有安全、健康和無害的環境,且這項權利與其他人權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6 ]。然而,該文件并未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掀起波瀾。直至2012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定任命獨立專家負責研究健康環境權問題,全球層面環境權與人權的互動開始由“綠化”現有人權向創設獨立的健康環境權轉化,健康環境權由派生性權利走向獨立權利,由存留于紙面上的權利走向被實際享有的權利。
2021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第48/13號決議,以43票贊同、0票反對、4票棄權在全球層面首次肯定了獨立形態的健康環境權。2022年,聯合國大會在此基礎上通過了第76/300號決議,呼吁各國、國際組織和其他利益攸關方以更大力度確保人人享有健康的環境。前述兩個決議的通過,反映了聯合國系統五十年來環境權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它們雖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卻為健康環境權保護走向成文法規范提供了有力支撐。但是,聯合國系統內部仍然缺乏制定統一且有約束力國際法律文件的合意,上述行動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各國將健康環境權納入國家憲法和區域條約。當前全球性健康環境權保護實踐仍然主要通過人權兩公約進行,但沒有全球性人權協定明確承認獨立的健康環境權。
同時,人權理事會第48/13號決議未明確說明健康環境權的具體內涵,只是以高度概括的語言說明了其實質性要素,即“清潔、健康和可持續”,并特別強調了弱勢群體“對環境損害后果的感受最為強烈”。聯合國人權與環境特別報告員約翰·諾克斯在2018年提交的最終報告中包含了一份《人權與環境框架原則》,提出實際的環境標準應包括空氣質量、全球氣候、淡水質量、海洋污染、廢物、有毒物質、保護區、養護和生物多樣性方面的標準[ 7 ]。然而,統一剛性規范的缺位,使各國可以擁有自己的標準,這對跨境污染等環境問題的解決造成困擾。雖然健康環境權的一般定義是困難的,但這不應成為否認該權利存在的理由,“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的判斷仍然是客觀的,具體技術標準則需要國際法實踐進行列舉和闡明。人權理事會第48/13號決議還強調了與健康環境權相關的一些程序權利,包括尋求、接收和傳播信息的權利,切實參與政府治理與公共事務和切實參與環境決策的權利,以及獲得有效救濟的權利,但這一部分只是對《里約宣言》相關內容的再述。
(二)歐洲人權法院:健康環境權的間接保護
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本身并未規定健康環境權,但是歐洲人權法院已通過判例實踐擴大解釋公約第8條的規定來解決與環境有關的糾紛,只是不認可其基本人權的譜系定位[ 8 ]。法院認為,考慮到相關社會問題和技術難點,國家才是最適合對健康環境權問題做出決定的主體,法院只能充當國家補救措施適用后的最后手段,即“國家裁量原則”。國家裁量原則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成員國各不相同的環境保護狀況,但法院內部未形成統一標準的現實進一步加劇了它對于健康環境權實有化態度的模糊性。來自法院的判決更多時候是以間接的方式推動國家自行采取措施來加強對健康環境權的保護,例如在2017年Jugheli等人訴格魯吉亞案中,法院判決格魯吉亞違法,并被動地等待該國改善其環保措施。誠然,法院委托部長委員會跟進判決的執行以及相關國家嗣后立法和行政行為的舉措,有力推動了權利保護的實效。但是,這種間接保護的路徑會帶來這樣一種困擾,即運用何種規則來控制擴大解釋的范圍以及公約成員國在判例基礎上自由裁量的幅度范圍。在過去環境問題尚不嚴峻時,該路徑有效地維護了既有體制,但放在環境沖突日益激烈的當下,則顯得過于保守。這一機制的缺陷業已面臨反思。在聯合國大會通過相關決議之后,歐洲委員會已在其2022年《關于人權和環境保護的建議》中呼吁成員國在國家一級頒布類似的立法和政策。歐洲人權指導委員會在《人權與環境手冊(第三版)》中總結道,法院可以不受以往判決的拘束,在解釋公約的問題上采取一種漸進式的方法[ 9 ]。換言之,歐洲人權法院對權利的解釋并非一成不變,它能考慮到社會背景的變化,應當也正在尋求改變過去間接保護的方法。
(三)美洲人權法院:權利區域實有化的激進突破
《美洲人權公約》以《歐洲人權公約》為藍本,也無明確條款規定健康環境權。在OC-23/17號咨詢意見發布以前,雖然美洲人權法院承認環境保護與享受其他人權之間存在關系,但只限于土著和部落人民的領土權利方面,特別是與公約第4條生命權和第21條財產權等權利相連結[ 10 ]。法院在2012年薩拉亞庫的克丘亞土著人訴厄瓜多爾案中便強調了類似的觀點( 1 )。但是,健康環境權并未被作為一項實有基本人權來看待。
隨著區域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美洲人權法院的態度發生了重要轉折。2017年11月,法院發布了OC-23/17號咨詢意見,該意見是為了回復哥倫比亞于2016年提交的關于大加勒比海地區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能危及圣安德烈斯群島居民人權的請求。法院承認,環境退化會對人類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因此享有健康環境的權利是一項自主的基本人權,必須得到保護。法院創造性地指出,《圣薩爾瓦多議定書》第11條的健康環境權應被視為公約第26條所規定的漸進式發展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法院還指出,享有健康環境的權利甚至把森林、河流和海洋等環境組成部分作為法益本身來保護,即使在沒有確定證據表明對個人有風險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2 ),由此搖擺于生態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除了豐富權利內涵,法院還指出健康環境權是個體權利與集體權利的統一,前者強調它與其他基本人權(如生命權)的不可分割性,后者則基于人類整體和代際利益。
由于美洲人權委員會向美洲人權法院移送爭議案件的動力不足,以及提請咨詢的主體更具有廣泛性,美洲人權法院咨詢意見的影響力并不遜于其判例[ 11 ]。OC-23/17號咨詢意見允許依據環境損害提出索賠,不再需要依靠其他人權[ 12 ]。在美洲人權法院第一個關于健康環境權的訴訟案件——2020年拉卡本哈特(我們的土地)組織土著部落訴阿根廷案的判決書中,法院也回顧了OC-23/17號咨詢意見的基本觀點,認為被告應為它并未采取有效行動防止對環境的有害活動負責( 3 )。在法院提起訴訟的案件類型也得以豐富,受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一方可以利用這一咨詢意見來提起氣候訴訟。法院強調,當有合理的跡象表明一項活動可能會對環境造成嚴重和不可逆轉的損害時,即使存在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各國也必須根據預防原則行事。美洲人權法院的咨詢意見還對美洲人權委員會產生一定影響。2022年3月,美洲人權委員會第3/21號決議承認健康環境權是一項可以為法院審理的基本人權。
美洲人權法院對健康環境權區域實有化的態度是較為激進的。首先,法院運用多種解釋方法認定公約第26條的經濟、文化及社會權利隱含健康環境權,將《圣薩爾瓦多議定書》的相關內容與公約本身進行了統一解釋,為其他區域提供了示范的同時,也面臨許多討論和批判。特別是法院是否不當擴大了它解釋公約的權力,或者至少是超出法院在本案可以審理的范圍,即違反了“未經其同意,不得將任何國家帶入國際法庭”的原則。其次,法院認為,各國有義務保證可能受源自其領土的跨界損害影響的人訴諸司法時,不因國籍、居住地或環境損害的地點而受到歧視。不僅如此,法院指出健康環境權和其他經社文權利之間沒有等級制度,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進行審判。進而,法院結合公約第1條,要求國家應承擔“尊重”和“確保”兩類義務。其中“尊重”要求國家避免“采取任何做法或活動以在平等條件下拒絕或限制獲得有尊嚴生活所需的必要條件”等行為;“確保”則要求國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護相關權利,并避免第三方在私人領域違反相關權利。這是法院將健康環境權權能進一步細化的結果,但相關義務的覆蓋情形過于廣泛,也沒有列明損害尊嚴生活的具體標準,對國家實際上形成較重的負擔。在亞洲這樣一個地域廣闊、發展極不平衡且仍未形成自己的人權法院和人權保護機制的區域,完全參照適用可能導致國家抵觸和利益失序。再次,法院較為強調生態中心主義,但人權最終要回到以人為本的闡述方式當中。最后,美洲人權法院自身不能完全解決的問題是,它關于健康環境權的主張能否在實踐中得到維持,為國家設定明確的積極義務并得到遵守,以保護其人民在環境退化中的人權。
二、健康環境權實有化的規范審視
(一)理念引領不足
聯合國系統將健康環境權確立為一項基本人權,符合當前環境矛盾突出現狀和國際法實踐迫切要求,但是在具體的理念選擇和制度架構上,缺乏行之有效、公平合理的安排籌劃。全球和區域法律規范制定實踐偏好使用概括性術語來定義健康環境權,也是出于復雜的政治考量,根源則是缺乏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引領理念。與此同時,國際司法實踐正在加速推進,環境判理正走向統一,不同人權體系的觀念正交叉融合[ 13 ]。在具體路徑選擇上,歐洲人權法院與美洲人權法院走向殊途。權利思維慣式下,有兩條途徑解決新問題,一種是創設新的權利,一種是對現有權利進行新的解釋[ 14 ]。歐洲人權法院選擇后者,通過擴大解釋《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為健康環境權提供間接保護,而美洲人權法院則以咨詢意見和嗣后判例的方式確認獨立的健康環境權,這足以被認為是權利實有化司法實踐的一個里程碑,但并不適于推而廣之。另外,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彼此碰撞,要求我們必須將健康環境權相關訴求納入到一個能夠將環境固有價值、代際需求和國別需求統籌考慮的開放性決策框架[ 15 ]。健康環境權實有化進程不能被當作國家之間推諉責任的手段或是政治斗爭工具,這亟須一個能夠激發大多數國家共識、統合大多數國家利益的價值理念。
(二)規范效力有限
健康環境權從一開始就遭遇到“硬法”和“軟法”的二元差序化劃分甚或對立[ 16 ]。從硬法規范來看,聯合國系統主要沿用以人權兩公約為核心的保護框架,但軟法層面的宣言、決議和指南等文件則不斷涌現。這些文件不僅多為彼此之間的復述,還面臨諸多爭議,難以達到預期的保護效力。歐洲和美洲人權保護機制中,區域人權機構或者區域決策機構躑躅于制定統一的立法或政策,雖有各自人權公約規定,但較保守的制度設計促使兩人權法院不得不尋求突破,但終究是一時之計。兩法院本質上均采用了法律解釋方法,不同案件處理結果具有不確定性,相關公約框架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擔這樣的突破頗受疑問。以歐洲人權法院為例,法院管轄健康環境權事務還受到“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約束,法院也不是國內法院的上訴機構。與國內法院不同,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監督機制通常以組織建設性對話來進行,并且在具體執行措施上給當事國留下了較大的自主權,甚至可能會被該國無視[ 17 ]。司法實踐通常具有被動消極的特征,區域性人權法院面臨健康環境權這樣一個敏感且涉及復雜政治利益的議題,通常保持更加審慎的態度。因而司法實踐能夠扮演“助推器”卻無法擔任“發動機”。總的來說,現有硬法體系已顯僵化,而軟法則恣意生長,卻還未有形成新硬法規范的契機,二者之間的動態互動也需要得到良好協調。
(三)治理體系分散
保護人權的主要責任在于國家,但人權保護也應融入一種超越國家秩序之上的法律秩序,即以聯合國為核心、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戴維·博伊德在提交給理事會第四十三屆會議的報告中指出,就法律承認而言,80%以上的聯合國會員國現已通過憲法、立法、法院裁決和區域條約保護健康環境權這項基本人權[ 18 ],但若是據此斷定全球已形成健康環境權保護路徑的共識還為時過早。雖然美洲人權法院在OC-23/17咨詢意見案中多處引用歐洲人權法院健康環境權判例,但從規范路徑和法庭結論來看,兩者觀點迥然相異,這與兩洲環境保護發展差異是緊密相關的。聯合國系統之中的分歧亦無法完全解決,在人權理事會48/13號決議表決中,中國、印度、日本和俄羅斯聯邦均投了棄權票。一些國家強調健康環境權的獨立,其目的在于追究政府責任而非有效保護環境、維護人權,也漠視了不同國家經濟發展和環保能力的差異。人權理事會決議對健康環境權含義以及與其他人權關系的闡述不夠明確,更未提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在聯合國大會上,即便是對決議投了贊成票的巴西、巴基斯坦、牙買加等國家,也分別從對發展中國家支持力度不夠、對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國家的關注不突出、一些術語使用過于主觀等層面提出批評( 4 ),可見該決議的通過尚顯草率激進。用過于標準化、統一化的規則去套用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權利保護實踐,無益于促進國際合作和推動全球環境治理。
三、健康環境權實有化的路徑探析
(一)價值引領: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背景下,生態文明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最大公約數[ 19 ]。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是國際秩序堅定捍衛者,并為國際規則制定、完善和發展提出中國方案和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處于政治共識向國際法律制度規范轉化的過程,具體到健康環境權領域,應在以“綠色發展”為核心的理論基礎上,構筑富有中國特色、包容多元的健康環境權體系。首先,深刻把握“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論邏輯和實踐方向,積極從法律和政策上承認健康環境權是自主的基本人權,持續鞏固健康環境權的道德應然性和法律應然性。正如我們談到生命權、居住權等傳統基本人權時,并不會將保護它們對于保護其他人權具有重要意義作為支撐它們實有化的依據。其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健康環境權保護體系,并非謀求統一的國際和國內法律制度,而是最大化求同存異、合作共贏。聯合國將健康環境權的內涵確定為“享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的環境”,對此每個國家都有基于各自現實基礎的闡釋,這要求必須建立最低限度的標準,否則權利只是一紙空文。同時,環境氣候變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并不相同,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視域下堅持并細化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揮聯合國多邊平臺作用,厘定人權路徑下環境保護因國而異的義務區分,保障各國走符合自己國情的權利保護之路。再次,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多層次一體化的價值理念,必須將權利保護納入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之中進行謀劃,以和平護環保,以發展促環保。
(二)法治保障:積極融入全球環境治理
環境議題的普遍重要性意味著我們不能獨善其身,而應積極行動融入全球環境治理進程,在完善自身法治保障的同時,運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導國際法規則的創設和發展。從實體權利維度來看,健康環境權實有化能整合原本分散在其他基本人權中的環境需求,增強統籌保護實效。健康環境權實有化的意義不單在于宣示該權利的重要性,更在于推動一個權責明確、強有效性法治保障體系的形成和完善[ 20 ]。應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中國2021年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21—2025年)》將環境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并列,在政策層面肯定健康環境權的獨立屬性。在法律層面,應積極推動環境權入憲,推進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持續加快環境法律規范制度更新,制定新型環境保護技術標準,以實際行動率先垂范。“訴權是現代法治社會中第一制度性的人權。”[ 21 ]在程序權利維度,當應然權利向實然權利轉化的可能性受到挑戰的時候,司法是保障人權實現的最終救濟防線。應加快建設中國環境司法專門化專業化體系[ 22 ],一方面通過完善公益訴訟制度和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制度為其他國家提升健康環境權司法效能提供示范;另一方面通過開展國際司法協助、舉辦司法合作論壇等方式推動世界環境司法交流,增進中國法治傳播影響力和國際司法共識,積極展現中國融入全球環境治理的大國責任擔當。
(三)國際合作:有力推動健康環境權實踐
國家間、區域間的人權保護機制受全球層面人權實踐發展的影響,又反過來與全球機制的演變形成互動,從而實現曲折的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要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者,中國可就健康環境權保護的關鍵問題,如發展中國家和受環境變化影響特別嚴重國家的人權訴求、相鄰國家的環保合作、國際環境糾紛解決機制等籌劃區域內、國家間法治合作體系,落實落細區域環境保護共同體建設,以聯合宣言等軟法形式甚至是多邊公約等硬法形式建構典型,促進國際健康環境權實踐的正確發展。對于其他區域健康環境權實踐,應加強交流借鑒、去蕪存菁。其次,在國際合作實踐中適當解釋和運用無害原則等國際環境法基本原則和習慣法規則[ 23 ],在合理限度內規范國家對環境損害的負責范圍,細化分類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助推健康環境權進一步實有化。再次,在與健康環境權密切相關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層面,秉持“地球生命共同體”理念拓展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深度參與雙邊、多邊特別是與相鄰國家合作的自然生態共管共治體系。健康環境權是個體權利與集體權利的統一,在其實有化進程發展到一定水平后,應對該權利的對世性(obligations? ?erga? omnes)進行展望( 5 )。
四、結語
人權兼具固有性和根本性。人權的固有性并不意味著一成不變,隨著社會意識不斷發展,許多新興的權利也逐漸被認識到具有人權屬性。基于國際社會對于環境問題與人的生存和尊嚴密切關系的認識,健康環境權逐漸成為一項不依賴于其他權利而存在的基本人權。推進全球健康環境權保護事業,需要中國闡釋與中國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健康環境權保護提供新的視角。應在全球充分發揮該理念供給作用,從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和人類整體命運出發,在尊重各國實情的基礎上,推動健康環境權實有化進程與環境保護國際實踐同頻共振。
注釋:
(1)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the Kichwa Indigenous People of Sarayaku v. Ecuador, Judgment of 27 June 2012, Series C No. 245, para. 171.
(2)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Advisory Opinion 23/17? of? ?15? November? 2017, Series? A No. 23, para. 62.
(3)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f the Lhaka Honhat(Our Land)Association v. Argentina,Judgment of 6 February 2020,Series C No. 420, para. 289.
(4)UN Doc. A/76/PV.97, General Assembly official records, 76th session: 97th plenary meeting, Thursday, 28 July 2022, New York.
(5)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Judgment,I.C.J. Reports 1970, p. 3, p. 32.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EB/OL].(2021-10-25)[2023-03-10].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10/25/c_1127992532.htm.
[2]李步云.論人權的三種存在形態[J].法學研究,1991(4):11-17.
[3]馮慶旭.環境人權概念的倫理解讀[J].理論月刊,2012(2):42-46.
[4]簡·漢考克.健康環境權:權利、倫理與法律[M].李隼,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173.
[5]Lewis B.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M].Berlin:Springer, 2018:5.
[6]Ksentini F Z.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Final report prepared by Fatma Zohra Ksentini, special rapporteur[R]. Geneva:UN,1994:74.
[7]Knox J H.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lssue?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relating to the enjoyment of a safe, clean,healthy? and? ?sustainable? ? environment[R]. Geneva:UN, 2018.
[8]胡婧.環境權與《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的司法適用——以歐洲人權法院對格拉案的判決為視角[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6(11):89-95,162.
[9]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Manual?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3rd edition)[M].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2022:19.
[10]Pinto-Bazurco J F.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cognizes a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in recent advisory? ? opinion[EB/OL].(2018-02-23)[2023-04-09]. https://blogs.law.columbia.edu/climatechange/2018/02/23/the-inter-american-court-of-human-rights-recognizes-a-right-to-a-healthy-environment-in-recent-advisory-opinion/.
[11]谷盛開.國際人權法:美洲區域的理論與實踐[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314
[12]Siwior P.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OC-23/17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J]. Review?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2021, 46(3):177-188.
[13]Boyle A.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Wheres next[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2,23(3):613-642.
[14]劉衛先.環境人權的本質探析[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09,11(2):91-96.
[15]李尊然.環境權與人權的協調——以歐洲人權法院的實踐為例[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1):91-94.
[16]郇慶治.環境人權在中國的法制化及其政治障礙[J].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3(1):14-21,30.
[17]聯合國.人權專家:土耳其無視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將開創危險先例[EB/OL].(2022-10-31)[2023-03-10].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10/1111922.
[18]Boyd D R.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Good practices[R]. Geneva:UN, 2019.
[19]龔維斌.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引領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N].光明日報,2022-08-26(011).
[20]Knox? J? H,Pejan R. The human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5.
[21]莫紀宏.論人權的司法救濟[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學院學報),2000(5):84-89.
[22]呂忠梅.邁向中國環境法治建設新征程[J].地方立法研究,2023,8(1):1-13.
[23]Beyerlin U, Marauhn 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 Oxford:Hart? Publishing,201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