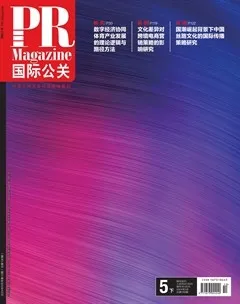內卷化視角下重負社區治理困境及破解路徑研究

摘要:基層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和重心。受內部制度制約、外部治理主體力量不足等多方面影響,基層治理陷入一種簡單自我循環和自我重復的狀態,即內卷化困境。本文立足基層治理的現實情況,探討基層治理內卷化的表現,深入分析形成的根本原因,為基層減負和去內卷化提供破解對策,以期改變基層治理 “改而不變”和陷入重負的現狀,為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提供問題聚焦與理論思考。
關鍵詞:基層治理;基層減負;內卷化
國家治理,關乎利益,要害在基層,基層工作事關群眾福祉與社會穩定和諧。然而,受制度環境、治理主體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目前基層治理的公共服務實踐已經呈現 “重負荷”和 “改而不變”的狀態,即陷入內卷化的桎梏,面臨 “大有作為”的機遇和 “以何而為之”的挑戰。政府開展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治理現代化建設,尚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一、治理內卷化研究回顧
“內卷化”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最初應用于哲學和人類學,由康德在 《判斷力批判》中首次提出,指代內卷、內纏、糾纏不清的事物。[1]時至今日,內卷化理論被廣泛應用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領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關于內卷化的研究分析,國外學者更著重于立足宏觀角度,如文化、農業、國家權力,較少將其引入基層社區治理困境的分析。
目前,國內關于 “社區治理領域的內卷化現象”的研究成果日趨豐富,從不同角度對治理內卷化進行探索性研究。何艷玲、蔡禾 (2005)最早借用內卷化的概念,從組織學角度出發,指出中國基層自治組織在創新組織形式后仍未脫離原有發展路徑的束縛,依然強烈地依附基層政權,內卷化由此產生。[2]陳寧 (2010)從國家權力的角度出發,認為社區建設的實質是國家權力對基層的過度滲透,基層治理行政化顯著,則內卷化特征明顯。[3]許寶君、陳偉東 (2017)從治理主體的角度指出內卷化的原因是居民主體性缺失,[4]李利文 (2016)等從個體認知的角度出發,指出人的主觀是 “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內卷化”的重要成因。[5]馬衛紅 (2016)從發展目標、行為主體和環境三個方面指出內卷化與基層治理的 “改而不變”的差別。[6]
在基層治理去內卷化的研究中,張付強 (2009)構建了社區自治改革的內卷化分析框架。[7]張立等 (2019)構建了 “政策壓力—目標替代—集體經濟內卷化”的解釋機制。[8]韓志明 (2020)基于案例調研,指出可以通過外在賦權和自我賦權將治理權力由政府讓渡給其他治理主體,提高社區主體的治理意識,在合法性和效率性之間尋求平衡,解決內卷化困境。[9]
二、基層治理內卷化的表現及其成因
(一)基層治理內卷化的表現
在基層治理領域,內卷化指在既定結構下,社區治理趨于復雜化和精細化,社區發展脫離事物發展或運行規律,公共服務實踐呈現出循環往復卻 “改而不變”的現象,以及資源投入與治理產出不對稱的 “邊際遞減效應”等表現。
1.社區行政化色彩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政府試圖通過職能結構的改革來帶動基層社區向有效自治轉型,然而受原有行政模式的剛性制約,社區治理模式無法擺脫行政化、官僚化,進而出現無限政府管理和無效自治的內卷困境,使社區治理遲遲無法真正過渡到更理想、更高級的狀態。
2.形式主義作風
基層治理的形式主義是對上級規定的表面遵守,但與實質價值背道而馳,被視為治理復雜性與組織程序化、標準化矛盾碰撞的必然結果。[10]例如,面對上級檢查督導,基層工作人員加班加點補材料做臺賬;面對上級巡查觀摩,安排 “演員”,分配 “臺詞”;日常工作中,創建結束寫創建收獲,活動辦完寫活動新聞,領導發言寫發言稿,負擔沒減還要寫減負心得,社區的功績成就依靠表格數據來判定。弄虛作假成為體制內潛規則,表演成為工作表現形式,基層組織陷入 “內卷化”困境。
3.痕跡主義
痕跡主義在基層治理實踐中,表現為通過齊全的痕跡掩蓋行動的不作為,通過過濾性執行以自保來躲避潛在的問責風險。產生原因之一是面對大量的行政性任務,痕跡生產的投入、效率大于實際 “作為”,成本遠低于實際 “作為”,故基層相比于 “最終效果”更注重 “行為過程”本身;原因之二是上級對基層進行績效考核,面對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偏向于 “一刀切”地將痕跡信息作為判定標準,“過程留痕”的好壞成為基層組織考核成績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基層治理內卷化的成因
1.制度層面
(1)關系形態錯位
當前社區治理面臨的一項普遍難題是:社區承擔政府下放的大量行政性工作任務,無暇開展自治、回應居民訴求。政府與基層組織之間原本 “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被 “調控與服從”所代替,出現了職責關系的錯位。具體表現為政府通過嚴峻考核指標和不定時督查來調控基層,為了通過考核,規避風險,基層可能會采取作假、推諉、變通等消極策略,行動模式轉為 “按規辦事”“服從命令”。如何扭轉政府與基層社區的關系錯位,成為基層治理實際工作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2)公職人員思想跑偏
長期以來,中央與地方的縱向關系呈現 “行政發包制”特征,基層組織 (承包方)處于行政發包制的末梢,上級政府 (發包方)對基層組織的激勵方式以負向激勵為主,這關乎基層工作人員的晉升和評優。大多數基層隊伍的晉升周期長、晉升空間有限,面對高風險弱激勵機制,主動 “干實事”通常可能獲得領導口頭表揚等非實質性回報,卻意味著承擔更大的責任,影響 “鐵飯碗”工作穩定和日后的晉升發展,造成基層極端個人主義風氣的泛濫。
2.多元主體層面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加快建設 “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但在現實中,企業、社會組織、社會公眾等治理主體治理力量薄弱,面臨自治困境,參與治理意愿不高。
(1)居民參與不足
一是認知不足,居民大多處于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狀態,只有涉及自身權益問題時,才被動選擇非合規的參與方式,如集體上訪;二是基層治理 “私人化”色彩濃厚,為 “避責、求穩”而很少敢有作為,久而久之,社區中存在 “為民做主”的包辦思維,導致大部分居民被排斥在治理場域之外。
(2)企業參與意識變化
我國企業參與治理的內容和形式多樣,但治理潛能并未充分發掘。究其原因,一是傳統觀念上企業治理主體的社會屬性未被廣泛認知,很多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都以提高績效為前提,履責意識不強;二是制度環境尚未完善,使企業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和社會生態系統不協調,企業無法在治理中獲得正向、積極的反饋,打擊積極性;三是企業參與渠道障礙重重,無法實現 “市場賦能”。
(3)社會組織無力參與
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和實踐者,但在 “強國家—弱社會”制度前提下,社會組織的作用無處發揮。國家對于社會組織缺少實質性的支持,其自我造血能力不足,所以整個社會組織系統長期處于孤立化、彌散化的狀態,無法有效參與。此外,“官本位”思想嚴重,忽視了社會力量。公眾 “有事找政府”的思維慣性十分普遍,較少對社區組織表達利益訴求,社會組織參與 “無門”。
三、基層治理去內卷化的路徑
去內卷化是幫助基層減負、提高基層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徑。要解決目前基層治理內卷化的問題,一方面要組織內部需要進行改革,重構優化原有的體制;另一方面要凝聚多方主體力量參與治理。
(一)基層減負賦能
1.優化問責機制,改變行政考核的指標體系
基層工作的重負主要來源于上級下放大量的行政性任務,基層形式主義、痕跡主義、避責傾向的不良風氣也是由壓力型體制下超高壓 “泛化問責”制度和超強度負激勵造成的。為基層減負,要避免 “一刀切”“欺軟怕硬”等問責督查方式,問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建立科學民主的容錯糾錯機制,讓基層人員愿干、敢干、能干;要創新考核激勵機制的方式、內容和理念,注重動態管理和結果評估,破除因工作難度大而導致的 “不想干事”困境。
2.權力下放,權責匹配
長期以來,基層處于權責嚴重不對等的狀況,表現為 “責大權小”,基層陷入權責不匹困境,致使基層干部想作為但實際上卻 “無法作為”。政府應以 “放管服”為抓手,由管理、控制手段向服務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持續優化和厘清自身職能,加快權力下放,讓基層工作人員感受到權責相匹配,另外也要注重加強配套措施建設,以保障基層人員有充分的作為條件。
3.合理規范技術治理邊界
數字化智慧技術手段引進社會治理,初衷是更好地服務社會,提高辦事效率。但就現實看,技術治理的理性色彩掩蓋了治理對人本價值的重視,呈現以結果為導向的工具理性傾向。因此,政府要辯證看待技術以及技術治理,正視其局限性。界定技術的功能及使用邊界,將其作為有力的使用工具,明白治理成效不能單靠數字與指標來衡量,注重基層人員的治理能動性。
(二)專業基層隊伍建設
基層人員的素質水平高低關乎基層服務質量。在招聘環節,可采取直接考察等方式招聘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人員,建立防范公開招聘突出問題的有效機制。入職后,要做好培訓工作,一是加強工作人員業務能力和服務意識培訓,二是加強業務能力、崗位知識的培訓和現代信息技術培訓,有效提升綜合素質,以群眾為中心,使隊伍人員具備科學的觀念、專業的知識,能夠幫助居民解決實際問題。
(三)對外賦權,推進協同治理
受原有政治體制影響,政府 “一家獨大”的治理局面使社會治理出現內卷化困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1.社會公眾
通過創新社區教育的方式,凝聚社區力量,在社區教育過程中通過情感互動培育參與意識,強化社區認同,激發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熱情。培養參與能力,提高社區治理的效率;優化參與路徑,積極為居民開辟建言獻策、表達訴求、參與服務評價的渠道,構建新型鄰里關系,實現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2.企業
企業在傳統觀念上只被視為營利性商業組織,但中國企業在市場化、國際化的長期發展中,已經具備社會、政治、道德等多維屬性和多元化的價值追求,實現了充分的社會化發展。在企業有履責意愿和能力的前提下,一方面,政府通過拓寬、創新購買服務的方式,引導企業參與社會養老、助殘、扶貧等社會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繼續完善企業參與治理的制度環境,明確治理的邊界和 “義利”關系,以保障企業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和持續性。
3.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本身的非營利性、自治性、民間性在深入基層、貼近現實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專業優勢。要發揮社會組織的治理效能,首先,政府應大力支持社會組織的發展,放寬政策管制;其次,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提高治理積極性和造血能力;最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界定履責行為的邊界,營造規范有序的法制化環境,助力社會組織行穩致遠。
四、結束語
本文立足基層治理的現實情況,研究了基層治理 “內卷化”的表征,從制度層面和多元主體層面對治理內卷化形成邏輯進行歸因分析,并提出從制度層面入手,改革機制,建設專業基層人才隊伍;多元主體入手,實現基層減負,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治理共同體。
值得注意的是,減負并不是減責。減負是為了基層人員擺脫煩瑣復雜的形式主義任務,能夠有足夠精力為社會公眾做實事,謀福利。政府要明確自身職責邊界,發揮好監督與管理的功能,不越位不缺位,積極引導多方主體發揮自身優勢,共同破除內卷化困境,提高社區治理效能。
參考文獻:
[1] 韓江風.政府購買服務中第三方評估的內卷化及其優化:以Z市S區社會工作服務評估項目為例[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4(02):20-37.
[2] 何艷玲,蔡禾.中國城市基層自治組織的 “內卷化”及其成因[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5):104-109.
[3] 陳寧.國家—社會關系視野下的社區建設:走向內卷化的權力秩序:基于對長春市J社區的研究[J].蘭州學刊,2010(07):109-113.
[4] 許寶君,陳偉東.居民自治內卷化的根源[J].城市問題,2017(06): 83-89.
[5] 李利文,申彬,彭勃.城市基層治理創新中的 “認知內卷化”:以上海X區物業管理深化改革為例[J].社會科學研究,2016(02): 39-51.
[6] 馬衛紅.內卷化省思:重解基層治理的 “改而不變”現象[J].中國行政管理,2016(05):26-31.
[7] 張付強.我國社區自治改革的內卷化分析:一種空間模型的視角[J].公共管理學報,2009,6(03):77-83+126.
[8] 張立,郭施宏.政策壓力、目標替代與集體經濟內卷化[J].公共管理學報,2019,16(03):39-49+170.
[9] 韓志明.小心翼翼的行動者:社區治理的內卷化敘事:以S市Y區 “睦鄰門”案例為例[J].中國行政管理,2020(12):69-75.
[10] 顏德如,張玉強.基層形式主義的生成機理及其韌性治理:一種組織學的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21(05):68-78.
作者簡介: 李暉,女,漢族,山東臨沂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