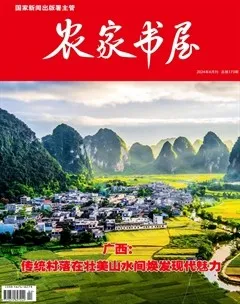《游隼》: 自然主義者的孤獨吟唱
張向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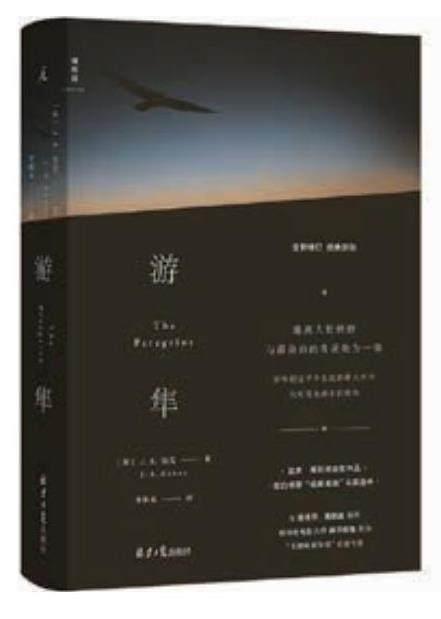
灰白的天空中,游隼在孤傲地飛翔,大地上一個孤獨的背影在執(zhí)著追隨。天高地闊,游隼像天空中的黑點,那個背影像踽踽獨行的螞蟻,而在地平線的遠方,大海蒼茫。
這是一幅令人震撼同時也令人心碎的畫面,給我們描繪這幅畫的人是英國作家約翰·亞力克·貝克。他連續(xù)十年執(zhí)著地追隨著游隼的身影:“整整十年,我將我所有的冬日都用于尋找這漂泊不定的光芒,尋找游隼掠過天空時生命迸發(fā)的霎時熱情。”他的眼光時刻聚焦在游隼的身上,直到它消失在地平線的盡頭。
在作家的眼里,天空的王者,自然界最強大的掠食者——游隼就是他所尋找的生命的光芒。在寧靜的河灘,濃霧包裹的河谷,閃爍著金光的田野,溪水潺流的濕地,茂密的樹林等地方,他追隨游隼,觀察它的眼睛、翅膀、羽毛、鳥喙、利爪;觀察它恣意的飛翔,血腥的捕獵;贊賞它的自信、威嚴、霸氣。
作家不吝筆墨地贊美游隼,將他的生命形容為一場孤單的死亡,認為游隼所做的一切就是將他們的榮耀帶向天空。正是作家對游隼的癡迷和投入成就了他的作品——《游隼》。
一方面,這是一本觀鳥筆記。作家以精準、唯美、流暢的筆觸描繪了博大的自然界的物態(tài)。林中的榆樹、梣木、橡樹、山楂樹、雪松,以及斑尾林鴿、麥雞、赤頸鴨、山鶉、田鶇、黑水雞,無不體現(xiàn)了自然的純粹之美與物種的豐富性。
作家的目光冷峻鋒利,流連自然山水,體察以游隼為主角的鳥類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認同自然物種的存在法則。他筆下的自然有一種不假雕琢的唯美,可以讓他在冬日追逐游隼時忘記了寒冷霜凍。在他眼中,鳥的飛翔也是一種美的呈現(xiàn),甚至鳥的死亡也是壯美的:“他(翠鳥)像一顆死去的恒星,綠松石般冷峻,微弱的星光,穿透漫長的光年,終傳至我的眼中。”
另一方面,《游隼》又并非單純的觀鳥日記,而是一位自然主義作家心靈和思想軌跡的記錄,是一曲以吟唱游隼而影射自身的哀歌。
約翰·亞力克·貝克一生都生活在英國鄉(xiāng)下的小鎮(zhèn)切姆斯福德,他患有類風濕關(guān)節(jié)炎,飽受疾病折磨,后因服用緩解關(guān)節(jié)疼痛的藥物而患上癌癥去世。“我一直渴望成為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到最外面去,到所有的事物的邊緣。”作家把心靈的孤獨以及去遠方的渴望寄托于游隼,追隨它而步履不停。作家毫無保留地袒露了他的心跡,仿佛一個自然的夢游者在孤獨囈語。
在書的結(jié)尾中,在作家的潛意識里,他已經(jīng)被游隼這個物種接納,儼然已經(jīng)成為一只脫離了人類世界的游隼。這是一種深刻的隱喻,暗示作家已經(jīng)抵達了游隼的內(nèi)心和精神世界,完成了不可能的蛻變。游隼,成了頑強生命的象征,作家渴望著成為具有游隼生命力的所在。
閱讀《游隼》時,像在讀一部詩集,作家詩一樣流暢優(yōu)美的語言有著詩歌節(jié)律的美感,使一部幾乎沒有情節(jié)、人物單一的書籍讀起來毫不費力。書中作家對游隼進行了近乎虔誠的禮贊,表達了他對自然的深沉的熱愛。同時在書中的字里行間,我也讀到了作家對自然的敬畏和對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思考,類似于梭羅在瓦爾登湖邊的思索。
作為一個自然主義者,作家有著博大寬廣的情懷,他對自然的熱愛,顯得偏執(zhí)而執(zhí)著。除了作家本人,作品中有關(guān)人的描寫只是一個“他”或者一個背影,作家刻意淡化了“人”。他認為“我們(人類)都是捕殺者,我們渾身都是死亡的氣息”。他和游隼一樣“厭惡人類的聲音,憎惡這聲音”。他對人類世界充滿厭棄和疏離,認為人類的捕獵殺戮超出了自然法則,是欲望的驅(qū)使和放大。
作家以謙卑和敬畏心對自然的摹寫,聆聽著純粹的自然之音,窺見了純粹的自然之美,讓我們對人類和自然的未來始終懷著美好的愿景。隨著人類對自然認識的加深,更多的人加入保護環(huán)境和生物物種的行列,自然主義者不再是孤單的吟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