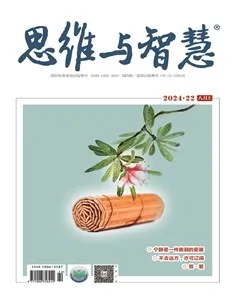閱讀的環境
每一頁書都是一個地平線,都是一田疇,文字是上面的花草。閱讀者的目光是太陽,花草因目光而生機蓬勃。書是要人讀的,只有被人讀才會鮮活,而閱讀的環境在不斷變化,讀書的環境不同,同樣的文字會讓人感受迥異。正如吃飯,時間不同,地點不同,食者饑餓程度不同,一樣的菜肴有時讓人吃得津津有味,也有時讓人味同嚼蠟。
讀書是在汲取精神食糧,吃飯是在獲得物質食糧。兩種食糧的獲取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是食糧就不可斷餐。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一日不吃餓得慌。”古人又說,“一日不讀書,塵生其中;兩日不讀書,言語乏味;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一天不讀書,如同一餐不吃飯,在身體和精神層面上皆有著很大的反應。
年少時,物質食糧的缺乏讓人饑不擇食,精神食糧匱乏也如此。一次,表叔偷偷地給了我一本他的密藏書籍《賦》。雖然勞累了一天的我極度疲乏,但晚上依然在蚊帳里燃起一盞熒熒如豆的煤油燈,饕餮地讀著。佶屈聱牙的駢體古文實在難懂,但我也硬著頭皮直讀到深夜。饑不擇食讓當時只念完小學的我食古難化。
人吃東西香甜與否,與所處環境和當時自身情況有關。《芋老人傳》里說,一位書生在饑寒交迫中飽食老人之芋,為相國后依然不忘當年的“美味”,可再食老人之芋時味道已迥然,簡直是難以下咽。時位移人,閱讀也這樣,一本書的閱讀體驗,在于讀者的個人經歷以及翻開書的地點和時間。年少時的我很幸運地成為生產隊的“看田人”,可以一邊看田一邊看書。每當肚中無食,饑腸轆轆時,我都以閱讀療饑。雖然腹中無食,閱讀的知識卻進入了胃中,穿肝入肺,成為營養,長在了身體中。饑餓中讀書所獲得的知識是其他時候閱讀獲取的好多倍,且能終生不忘。
無論歲月怎樣更迭,當年閱讀時的環境只要再現,閱讀的記憶便能被辨識出來。如“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這是在春日中一個雨天讀到的,爾后只要在野外遇到淅瀝春雨時,這句話就會滴滴答答浮現在腦海。閱讀能彎曲與拉直空間和時間,對于時空的流轉有著加速或減緩的效用。閱讀是一種現實與超現實旋轉環繞強有力的運動,它可以強腦健身,可以改變日子。
年少時閱讀的場景很凌亂,這時空的“凌亂”卻因各有特點,連同所讀的知識一起刻在了腦子里。早上放牛時,天蒙蒙亮,才見到一絲絲曦光,便將眼睛睜到最大,收獲到盡可能多的光亮,讀《紅燈記》《杜鵑山》等樣板戲劇本;炎炎夏日,在村里撿拾一個個桃仁時,于各戶的墻壁上讀村里“老先生”寫上去的毛主席語錄;在村前東荊河灘陰涼的柳林下讀唐詩宋詞,讀米蘭·昆德拉的《生活在別處》,讀馬丁·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常常處于動態喧鬧與恒常寧靜的交叉跑位之中讀書,這樣的“奔跑”越快,記憶便越深刻。
年少時閱讀的環境,不同空氣的溫度與濕度,陽光或雨水的傾斜度,風與雨水聲響的大小,在身邊的人的密度與運動的速度……所有的不同,哪怕是細微的差別,皆能將當時所讀到知識刻入這一環境中,就像留聲機將聲波轉化成金屬針振動的能量,當某一情景因金屬針“回放”時,當時的知識便又“播放”出來。如在風雪中的草棚里讀《水滸傳》:“銀迷草舍,玉映茅檐。數十株老樹杈枒,三五處小窗關閉。疏荊籬落,渾如膩粉輕鋪;黃土繞墻,卻似鉛華布就。千團柳絮飄簾幕,萬片鵝毛舞酒旗。”每逢風雪天氣中有草棚,這些字便排著隊清晰地跳入眼簾。
(編輯 兔咪/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