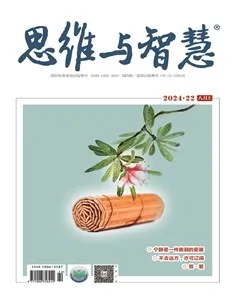今朝好涼快
愛讀詩詞由來已久,炎炎夏日也不例外。游弋在浩瀚如海的詩詞中,儼然忘卻了酷暑。每每際遇精妙處,便頓生“今朝好涼快”之感。
你看,1200多年前的盛夏,狂狷不羈的李白,攜三五好友,拎著美酒,頂著烈日,不顧斯文“裸袒青林中”,干脆“脫巾掛石壁,露頂灑松風(fēng)”,有清風(fēng)陣陣,清涼爽快,便“懶搖白羽扇”。而1000年之后的清代袁子才,瘋狂仿效詩仙太白,似乎更是無羈無絆,稍勝一籌,為了貪涼,竟然半年不穿衣服,索性來了一個(gè)驚世駭俗的“不著衣冠近半年,水云深處抱花眠”,真是神仙的清涼境遇。
李白和袁枚的納涼頗具儀式感,在熱鬧中尋求清涼。詩人錢起則別有另一番情趣,他格外悠然淡漫,完全不顧“木槿花開畏日長(zhǎng)”,而是“時(shí)搖輕扇倚繩床”,那種清涼自得的模樣,仿佛與炎炎夏日毫無干系。“知足隨緣,安時(shí)順命”的白居易,更是少有狂妄和灑脫,只是安詳?shù)亍岸司右辉褐小保?dú)享清風(fēng)徐來,怡然其樂,自顧自地沉吟“熱散由心靜,涼生為室空”。東坡先生主張“靜故了群動(dòng),空故納萬境”的“以靜消暑”。陸放翁則用“竹梢露滴驚殘夢(mèng),荷蓋風(fēng)翻送早涼。暑用酒逃猶有待,熱憑靜勝更無方”的詩句啟迪人們神寧氣靜,方能自然涼。而宋代的周邦彥則一個(gè)人靜靜地“燎沉香,消溽暑”,在“鳥雀呼晴”的嘈雜中,調(diào)和一劑清涼,心定自然涼。
優(yōu)雅的高駢獨(dú)愛自家小院,躲在“綠樹陰濃”里,欣聞“滿架薔薇一院香”。最解風(fēng)情的楊萬里喜歡月下獨(dú)步,掬一縷月光,和著清風(fēng)吟唱“竹深樹密蟲鳴處,時(shí)有微涼不是風(fēng)”。參禪的梅堯臣鐘愛花木蔥蘢的禪房,納涼品茗,煩熱全消,自然有了“不須河朔飲,煮茗自忘歸”的感嘆。而一生顛沛,游離千山萬水的東坡先生則把山洞視為消暑佳地,用“自清涼無汗,水殿暗香滿”的詩句把水殿乘涼的愜意寫得頗有情趣。
與他們相比,北宋秦少游則顯得急促許多,他一旦遭遇炎夏,便急匆匆地“攜杖來追柳外涼”,趕緊覓一處“畫橋南畔”的清涼之地,于是,閑“倚胡床”,怡神閉目,享受著這份難得的清涼。勤勞的劉禹錫則自己動(dòng)手,利用竹管將冷水傳輸?shù)酵ろ數(shù)乃拗匈A存,然后讓水從房檐四周流下,形成雨簾,避暑降溫,為此吟詩一首:“千竿竹翠數(shù)蓮紅,水閣虛涼玉簟空。琥珀盞紅疑漏雨,水晶簾瑩更通風(fēng)。”
打開塵封的詩詞,掠一縷清涼,拂過盛夏,萬種風(fēng)情的千年詩詞里,儼然躲著一個(gè)清涼的自我。
暢讀詩詞吧,不為“詩讀百遍,其義自見”,不為“腹有詩書氣自華”,也不為“口吐蓮花,字字珠璣”,只為與心靜自然涼的心境撞個(gè)滿懷,讀出一個(gè)“今朝好涼快”!
(編輯 高倩/圖 雨田)
- 思維與智慧·上半月的其它文章
- 河水與堤岸
- 風(fēng)吹麥浪滿地黃
- 樂山樂水
- 蝶夢(mèng)翩躚
- 船
- 豆色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