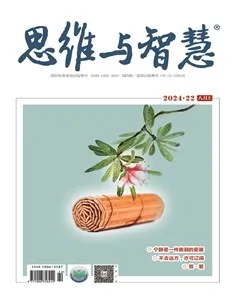十六歲那年的綠皮火車
那個時候,小城通向省城的交通工具除了看上去笨笨的大客車,還有綠皮火車,火車一天只在小城和省城之間來往一趟,進站時總鳴著長長的聲響,在那資訊和交通都不發達的上世紀90年代,聽到火車的鳴笛聲,就好像聽到來自外界的喧囂的訊息,總讓人有莫名的振奮感。
那年我十六歲,因為偏科嚴重沒有考上理想的高中,生性倔強的我不準備復讀。父母跟我講了很多道理,但終究還是沒有說服我,于是他們商量了一下,既然我選擇不再讀書,那么我就不再是個孩子,我必須要出去找工作,要開始面對紛雜的社會。我點頭答應了。
于是那個夏天,父母安排我跟著堂姐去省城打工。
知道出行的日期后,我心里有些忐忑,從小到大我都沒有離開過家,外面的世界雖然充滿誘惑,但對那個年紀的我來說,它更像一扇關著世事百態的門,我想打開看看究竟,又怕門后的世界太洶涌,瞬間吞沒了我。
但我們出行的工具是火車,這又讓我有些期待。我沒有坐過火車,總是聽坐過的人說起火車的各種好,比如速度快,窗外的景物都是一閃而過;比如平穩,人可以在過道上如履平地;比如熱鬧,還有推著小車賣食品的人……所以對火車,我是抱有熱切期待的,想親自體會一下坐火車的感覺,而且隱約覺得坐過火車之后,我就變得比周圍同齡人更有見識,有了可以跟朋友吹牛皮的本錢,因為他們都沒坐過火車。
離開家的那天,我哭了,父母淡定地看著我,提醒我可以改變主意繼續復讀。聽到這話,我擦干眼淚,跟在堂姐身后,拎著大大的行李堅定地走了。
小城的火車站很簡單,但是很干凈很美,一排紅頂瓦房,白色墻壁,候車室里是一排排長椅,椅子上人并不多,我和堂姐坐在一起。堂姐因為出過很多次門,姿態是過來人的安然,而我,一顆心浮在半空,周圍的一切對于我都有新奇的吸引力。
等待的時間總是特別漫長,檢過票之后走上站臺,第一眼就急著去看火車和那兩條長長的軌道,對于十六歲的我來說,這一切都是那么神奇。
火車是綠色的,和郵筒一樣的顏色,而火車和郵筒都是屬于遠方的工具,所以那種綠深刻地印在第一次離家的我的腦海里,從此以后看到那樣的綠色,就莫名有了離愁與遙想。
堂姐帶我找到車廂和座位,車廂里人不算多,看到我們兩個女孩拎著大大的行李,有人熱心地幫我們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陌生人的熱心讓我感到溫暖,連帶著覺得火車真是個溫暖的地方。
火車上的座位也是綠色的,堂姐說這是硬座,這個火車上還有臥鋪,不過票價很貴。堂姐說這些時我并不在意,因為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這個車廂的人身上。我的目光掃過視野內每一個人的臉,他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受到自己心情的影響,我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張漂泊的臉。
火車啟動后,有人打開了座位旁邊的窗戶,風灌進車廂,之前彌漫在空氣里的煙味一掃而光,整個車廂都是大自然植物的氣味。
火車上果真有人推著小車賣食物,但很少有人買。大家和我一樣,多數時候都扭頭望向窗外。盛夏的車窗外,植物都呈現著最飽滿的狀態,在秋天到來之前,努力地伸展枝葉。
火車并不像之前聽說過的那樣穩,它時不時發出咣當咣當的聲音,走在過道上還會因為一個轉彎險些滑倒;也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快,它走不遠就要停下來,有人上車又有人下車,是一個不斷遇見與別離的小世界。度過起初的好奇、驚喜等種種情緒后,火車就變得不那么神秘了。
到了省城,才發現省城火車站人真多,這種人山人海的畫面直到今天都未曾改變過,而綠皮火車隨著時代的發展,漸漸被淘汰,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但我始終忘不了十六歲那年的綠皮火車,它帶著懵懂的我,離開家鄉,為我閉塞的眼界打開一扇多彩生動的門。同樣是那一年,一個月后,綠皮火車又帶著我回到家鄉,外面的世界諸多不易,我重又回到課堂,為自己積蓄可以面對紛雜社會的力量。
(編輯 高倩/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