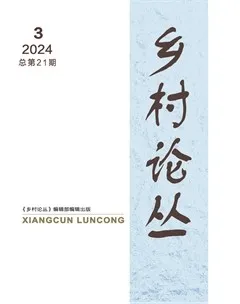鄉土中國視角的江村研究:地方知識、現代特征及未來愿景
摘要:鄉土文化是中華文明呈現、傳播、傳承的核心要義。隨著當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現代化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斷滲透到鄉土文化的肌理中。研究發現,鄉土文化變遷主要表現為從封閉性同質化到開放性異質化、從“生存理性”到“生活理性”、從“熟人社會”到“利益社會”等現代特征轉向。這種變遷對“鄉土中國”的“鄉土本色”產生影響,但鄉土文化實質并未改變,仍以“形散而神聚”為特點而存在。當前,鄉土文化仍然是構建村落共同體的情感基礎,也是構筑鄉村社會“精神家園”的核心要素,應深入分析鄉土文化現狀,推動鄉土文化與鄉村振興相結合,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鄉土文化建設,以此推動鄉土文化實現現代化轉型。
關鍵詞:鄉土文化 地方性知識 文化變遷 《江村經濟》 《鄉土中國》
*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般項目“清代改土歸流后酉水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1735—1911)”(編號:23BMZ016);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項目“新時代中國成立以來婚姻交往促進民族‘三交’實踐研究”(編號:2023-GMI-120)的階段性成果;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民族學專業本科導師制實施方式與實踐研究”(編號:2023GJJG447)的階段性成果。
引言
鄉土文化是中華文明呈現、傳播、傳承的核心要義。推進鄉村文化振興、新時代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豐富人民精神文化世界,理應充分認識、挖掘和利用鄉土文化價值。鄉土社會是富于地方性的,具有“鄉土本色”的概念特征,同時“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因此,一定程度上造就了鄉土社會是“有機的團結”的“熟悉”社會,鄉土民眾在“熟悉”的空間場域內通過內在禮俗秩序與外在“差序格局”進行交往交流。在數千年的歷史與文化積淀下,鄉土社會的信仰習俗、生活習慣、人文特質及社會風格與農業生產渾然一體,共同形塑了特色鮮明的地域性鄉土文化。但是,在社會流動加快的今天,鄉土社會面對著現代性的沖擊,現代化的生活生產方式不斷侵蝕鄉土文化肌理,那種以“己”為中心的一圈圈向外推延的同心圓波紋狀社會基層結構出現裂痕,“離土又離鄉”成為鄉土社會變遷最為顯著的常態現象,鄉土文化原有內核功能趨向式微。
現代化沖擊導致鄉土社會急劇變遷的事實,吸引了大量學者開始關注社會變遷問題,相關成果產出頗豐。甚至僅以“江村研究”作為個案研究得到的成果,亦不絕如縷。目前,相關研究的啟示成果著重體現在較為宏觀的學科探索和實證啟發,很少將江村鄉土文化整體變遷作為研究對象,從江村“地方性知識”的理論角度來闡釋鄉土文化,并進行現代性的學術理論思考。有鑒于此,本文嘗試結合以往學者研究基礎,具體從《江村經濟》與《鄉土中國》兩部著作出發,從格爾茨“地方性知識”理論角度解構江村鄉土文化的內容建構以及鄉土文化變遷的主要現代特征表現,并闡釋現代化沖擊下江村鄉土文化所傳遞的主要意涵,揭示所蘊含功能價值,以期更好地理解鄉土文化變遷所帶來的影響。
一、地方性知識:江村鄉土文化的內涵解讀與內容建構
鄉土文化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的象征形式,凝結了廣大民眾地方性生產生活經驗、智慧,具有深厚的價值意蘊。
(一)鄉土文化的內涵解讀
“鄉土”一詞最早見于《列子·天瑞》,從原文理解,鄉土有故土、家鄉之意,其地方性被予以論證。“鄉土”概念生成和“鄉村”有著渾然緊密的關聯。而“土”字也象征表達了“鄉土”的應有之義。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鄉村社會的“鄉土本色”進行了深入的描繪。因而,作為一個日常生活用語,“鄉土”往往成為指代個體長期生活居住并與自身聯系緊密的地方。在現實生活中,“鄉土文化”通常被視為植根于土地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并由此孕育出相應的“鄉土意識”和“安土重遷”的民族心理特征。費孝通對文化有簡短概括:“‘文化’是一個民族,或者群體,共有的生活方式與觀念體系總稱”,并“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共同經驗”。參考費孝通“中國的傳統文化是鄉土性的文化”及“五谷文化”對鄉土文化的解讀,結合學者對于鄉土文化的界定。茲僅就管見所及,鄉土文化是以土地為根基,進而衍生出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鮮明獨特而相對穩定的地方性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綜合知識系統。一言以蔽之,鄉土文化是扎根于社會土壤的文化,既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也是中華文化的根脈。
(二)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江村鄉土文化內容建構
“地方性知識”是美國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構建的核心概念,反映了人類學發展的“普遍主義”與“歷史特殊主義”之間的張力,其核心是回答“知識是在何種情境條件下形成的”之疑問。對于“地方性知識”而言,如果將演化其產生的具體情境和文化客觀主體抽離,其產生的理想和意義價值便難以明確認知。故而,地方性知識“是事情發生經過自有地方特性并與當地人對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聯系”。因此,地方性知識是在特定環境下,人類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積淀的智慧產物。可見,“地方性知識”與鄉土文化二者有種密切的聯動。
1.物質文化層面。物質文化構成了鄉土社會的具體形態,反映了鄉土文化所蘊含的深層內涵,其主要包括該地域的自然環境、建筑、農產品、服飾等。結合《鄉土中國》與《江村經濟》,可以窺見江村民眾在鄉土文化物質文化層面的地方智慧。例如,江村民眾根據自然或社會環境,相應采取了“男性耕田,女性編織”的農業生產組織結構,即“吃靠土地,用靠副業,男耕女織,農工相輔”,這種結構組成展示了江村民眾為謀求生活生計,所激發顯現的創造力和主動性。再如,村莊的布局規劃方面,由于江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計方式,以致每家每戶都備有船只,一方面是方便進行交通運輸,另一方面則是部分生計需要。故而,“為便利起見,房屋必須建筑在河道附近,這就決定了村子的規劃”,形成了村莊大部分建筑沿河而起的現狀,是為“開玄弓”地名之由來。此外,水進入江村的入口處裝著柵欄,夜間柵欄關閉,成為防止壞人進入江村“對村民的生命和財產進行威脅”的重要手段。又例如,江村因氣候和生計方式,形成了獨特的穿衣風格。夏季,男性常穿短褲,遇正式場合則穿裙,女性則穿無袖上衣和長裙。從另外一種角度看,衣服除了保護身體外,還便于社會身份區別。這些方面反映了江村民眾的地方智慧,構成了江村鄉土社會的具體形態,并體現了鄉土文化所蘊含的深層內涵。
2.精神文化層面。精神文化形成了聚落空間的意象和氛圍,故而往往只能通過感官感知,如當地民眾性格、風俗習慣、宗教信仰、道德情操、價值觀念等。在此,本文以敬谷為核心的傳統宗教信仰為切入點,對該信仰進行簡要概述。據費孝通所記述,江村禁忌總體可分為三類:其一,以敬谷為基礎。其二,與有關性的事物都是臟污的意識聯系在一起。其三,以尊敬知識相聯系。這很大一部分是鄉土社會對長期以來人民生產生活實踐的客觀現實反映。僅以敬谷為案例具體分析:一方面,農業在江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每年有8個月種植作物,稻谷是最普遍的產品。由于人均土地和產量有限,村民無法接受糧食浪費。另一方面,江南地區民眾歷來對稻谷格外重視,在吳越地區,不僅對谷神的信仰很普遍,而且谷神的形態多種多樣,有的還保留著較原始的形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谷神形態發展的歷史軌跡。因此,江村的道德觀念來源于對宗教的誠意和信賴,并影響其行為規范,成為穩定社會秩序的核心力量。可見,江村將浪費稻谷作為禁忌,是警醒后人尊重糧食、節約糧食的地方性知識的重要體現。
3.制度文化層面。制度文化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規范體系,它不僅促進了人類行為習慣和規范的生成,還促進或制約人們精神與物質文化的轉型。其主要包括道德準則、社會約定、民間組織等。例如,在江村的婚姻制度方面,提親通常由女方家庭主動,但因母女情深,母親難以接受與女兒分離。因此,母親前往男方提親并不普遍。故而,在江村有一個制度化的習俗,就是由中間人代替母親提親,這種做法既避免了母親直接參與提親的尷尬,又保證了女兒能找到合適的伴侶。此外,由于一些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及夫妻關系不穩定,達不到“經濟互惠”,有可能存在家庭不和睦,選擇表親聯姻成為江村民眾解決此類問題的辦法。再如,在財產繼承制度方面,一般按繼嗣系統進行,無嗣時依據江村獨特規則進行領養。領養過程中,養父需邀請同族見證,并與生父母簽訂契約。契約包括兩部分:養父保證領養孩子有財產繼承權,生父母保證與孩子斷絕關系,并讓孩子承擔對養父母的贍養義務。從江村的收養制度中,該地區形成了一種名義上看似收養的文化現象。費孝通認為,名義上的收養是指個人并未通過生育和婚姻關系,而被接納到另一個群體中去的制度,又稱為“過房”“過寄”,“過寄”的意思是依附。江村嬰兒的高死亡率導致村民認為鬼魂會侵擾嬌養的孩子。因此,孩子需“過寄”給有力量的人以求保護。這種地方性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社會互動方式。
4.行為文化層面。行為文化指人類在生產生活中創造的有價值的、促進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的經驗及活動。行為文化構成了聚落空間的社會交際行為,主要包括廣大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例如,在人口控制方面,江村人都認識到后代的重要性,但現實中由于土地面積限制、養蠶業的生產規模等,必須限制人口數量。因此,他們會按照當地的“智慧”有意識地去限制人口的擴張,預防貧困甚至破產。再如,在傳統的江村鄉土社會中,普遍采用陰歷作為歷法記錄時間,但這種陰歷系統以記月為基礎,導致不能準確反映季節性氣候的變化,對農事造成影響。由此,廣大民眾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種以“節”為系統單位的節氣歷法,即紀日系統。這種紀日系統能夠準確標記各時期地球與太陽的相對準確位置,從而彌補了陰歷的不足。加之,西方陽歷計時系統的傳入,江村地區逐漸形成了三種歷法并行的現狀。再比如,江村民眾從小就被灌輸了節儉的思想,因此節儉的生活方式成為他們的習慣,如不能浪費一粒米、衣物必須穿壞為止等。這種節儉思想,一方面反映了江村村民自我約束和珍惜資源的態度;另一方面,如果農民把收入全部消耗完,遇到欠收的年份就不得不借債,這可能導致失去土地。
在江村鄉土社會中,這些鄉土文化的要素成為維系原生態鄉土社會“靜態”發展的核心內容,而“地方性知識”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鄉土文化能夠起到規范秩序的功能,穩定鄉土社會;另一方面,鄉土文化作為包含鄉土民眾智慧的載體,能夠幫助改善民眾的生產生活,進一步維系“靜態”的鄉土社會。
二、現代特征:鄉土文化現代變遷下的集中表現
鄉土文化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過程,亦是其文化本質屬性的變遷歷程。在當前的鄉土社會中,鄉土文化的痕跡并未消失,而是呈現出“進化演變”趨勢,并與現代性、多樣性文化交融共存。
(一)破土而出:由“封閉性同質化”邁向“開放性異質化”
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人們依據地緣和血緣關系建立起固定的波紋形社會關系網絡,這種關系網絡構成了鄉土社會的生活交往基礎。鄉土民眾堅守在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上,形成了相對靜態的“熟人社會”,人們通過世代相傳的習俗規范鄉土社會的生活秩序,這構成了“鄉土本色”。一方面,從其優點而言,由于群體成員同質性程度較高,具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共性的集體記憶,進而聯結村落內部成員,能夠形成較強的村落共同體意識。這形成了亨廷頓對鄉土社會的描述:“鄉間社會的特點就是道義和情感義務、人與人之間親密無間、社會凝聚和持久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傳統農業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亦有可能造就了鄉土文化社會的封閉守舊,形成“坐井觀天”、自我封閉、遵循傳統等價值觀念。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差序格局”,進一步強調了同質文化形態和價值觀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鄉土社會的進步,使其無法跟上時代步伐。
在全球化背景下,現代文化與鄉土社會產生了緊密的接觸和碰撞,對傳統鄉土文化造成了巨大沖擊。這種沖擊打破了鄉土文化的封閉性,使其融入了現代文化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特質。在江村,異質性多元化的特點就是現代化變遷影響導致的多元技術引進和改革,進而導致鄉土社會新產業、新職業、新機構、新社會組織的出現。例如,近年來,江村積極推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絲織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逐漸減弱。為實現鄉村振興,江村已將工作重點轉向文旅產業,致力于打造“江村”文旅品牌,并圍繞文旅產業,發展現代農業和養殖業。與此同時,江村的現代文化產業中也涌現出諸多新興業態,如中西餐廳、涼茶鋪、果汁店、咖啡館等。此外,老菜場經過投資改造,現已發展成為融合文化創意與手工藝品的“江村市集”。這些新興產業為江村鄉土社會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在這個過程中,鄉土文化也在與現代文化的交融中不斷創新,煥發出新的活力。因此,江村村民盡管依然身處鄉村,承襲了部分傳統習俗,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已經趨近于城市居民。在審視江村近八十年的演變歷程時,可以清晰地看到,變革是絕對的,而穩定是相對的,兩者共同構成了鄉村發展的歷史脈絡。
(二)理性超越:從“生存理性”到“生活理性”
“生存理性”指人們為了生存而采取的理性行為。在生存的壓力下,人們會選擇最直接、最簡單、最有效的手段來獲取生存所需資源,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存權利。因此,這種理性行為具有功利性和實用性特征。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廣大農民基于土地限制、人口因素等,將“生存理性”放到第一位。因此,在面臨人多地少的壓力時,必須精打細算,同時對得失進行權衡。《江村經濟》中介紹,江村對于農田的安排是有講究的,一般而言,該村的主要作物是水稻、小麥、油菜籽,每年6月到12月,水稻種植結束后,其高地亦可種植小麥和油菜籽,在田地的邊緣種植桑樹。江村農民將土地視為自己“命根”,如果失去土地,其生存基礎也將會被剝奪。可見,江村農民奉行的“生存理想”,以“生計第一”為原則。隨著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生存壓力不再顯得那么緊要,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基本保障,他們在這種語境下形成了更高層次的追求,即“生活理性”。
“生活理性”,主要指在村民的日常世界中,他們所不斷追求的不僅僅是生活的意義以及個人在社會中的價值,而是一種超越了“生存理性”和“經濟理性”范疇的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江村村民開始更加注重生活品質和對精神文化的追求。他們不僅關注自己的生存需求,還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體驗。在這種背景下,江村村民開始積極參與各種文化活動,如文藝演出、書法比賽、攝影展覽等。例如,作為公共文化服務示范村,開弦弓村自2010年起便著手打造江村文化園,并在2018年對其進行了擴建改造。如今,村內設有江村文化弄堂和文化禮堂,對村民開放,具有兩百年歷史的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木偶昆曲定期展演。再如,江村女性傳承并發揚了具有百年歷史的“茶花形式”。昔日農閑時節,村民偶爾相聚一堂,議論鄰里瑣事。然而,這種狀況現在已發生轉變,村民們不僅交流家庭教育心得,分享對社會現象的見解,為彼此提供了一個展現自我、交流思想、提升精神文化素養的平臺,甚至還“經常會聊聊什么花好看,如何種植”等。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還進一步增強了村莊的凝聚力和歸屬感。同時,江村村民也開始注重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他們積極參與村莊環境整治和綠化美化工作,努力打造美麗宜居的鄉村環境,彰顯美美江村風貌特色。這種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正是“生活理性”在鄉土社會中的具體體現,它超越了簡單的生存需求,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滿足和文化傳承。
(三)結構裂變:從“熟人社會”到“利益社會”
在江村鄉土社會中,人們通過“地緣”“血緣”組建了趨向一致的生活共同體,并形成了相對靜態的,具有共同的價值理念、慣例習俗的“熟人社會”或“禮治(倫理)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遵循著傳統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彼此之間形成了穩定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在傳統鄉土社會中,社會的秩序需要以“禮”來維持,進而能夠有效應對生產生活的各方面,在這樣的社會關系人際網絡結構中,并不需要“法”,“無訟”是其特征。然而,鄉土社會在現代化和城市化沖擊下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社會結構的裂變上,從原先的“熟人社會”逐漸轉變為“利益社會”。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原本基于地緣和血緣建立的人際關系開始松動,傳統的價值理念和慣例習俗逐漸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鄉土民眾從“生存理性”轉向“生活理性”,導致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動機發生相應變化。以“禮”為核心的倫理秩序不再占據唯一地位。此外,廣大民眾為追求各類經濟因素,進而實現自身價值利益,具有血緣關系的“親人”關系不斷“外化”,地緣關系的“熟人社會”逐漸“陌生化”,倫理色彩日漸淡化,社會的交往規則開始擺脫“禮”,轉向以“利”為目標的共識規則體系,這類變化深刻影響原有的家庭組織結構和社會倫理秩序,并重塑了鄉土社會的社會結構模式。
例如,21世紀初,我國推行農村土地流轉政策,江村成立經濟合作社,村民以耕地作為股份,由合作社進行集體經營,從而使越來越多的村民脫離土地,推動合作社實現規模化經營,發展養殖產業。然而,傳統的魚蟹養殖業為了追求“利”,也帶來了導致集體受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系統破壞等問題。此外,隨著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江村村民絕大多數從事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活動。在這樣的變革下,江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不可否認,這種變化的最大原因是廣大民眾受現實經濟利益吸引再加上現代文化的影響,失去了對過去“鄉土本色”的信仰和追求,他們的生活執著于追求“個人利益”而忽略“禮”。盡管當前鄉土文化受到利益本位影響,但鄉土文化中的“倫理”仍制約著“利益”意識的影響。因此,鄉土社會民眾當前的價值觀念長期受到“倫理”和“利益”本位二者的影響,正如孫慶忠所言,鄉土社會按照內在的慣性邏輯延續,其文化在不斷變遷的過程中被建構和發明。
三、未來愿景:鄉土文化現代變遷的價值意蘊與理性思考
在現代化沖擊下,鄉土文化不可避免地經歷著由“慣性”帶來的與現代文化混合沖突、相互滲透、相互涵化的過程。在這“閾限空間”,鄉土文化面臨著諸多機遇與挑戰,應該運用辯證的觀點進行剖析。同時,在充分認識鄉土文化變遷存在的價值意蘊的基礎上,引導并實現鄉土文化變遷向理想方向發展。
(一)價值意蘊:鄉土文化變遷的理性思考
鄉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構件,具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和價值底蘊。在現代化的沖擊下,鄉土文化變遷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鄉土文化變遷改寫了鄉土社會的“鄉土本色”,但“形散”而“神聚”才是現代鄉土文化的本質特色。
1.鄉土文化依舊是構建村落共同體的情感基石。費孝通在分析“文化的生與死”時,認為文化能夠對人發生“功能”時就是活的。此外,“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共同經驗”。當下的鄉村社會相較于過去的鄉村社會生活共同體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即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最后向“陌生人社會”讓步。不可否認的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內核的鄉土社會文化仍然存在,面子、輿論等元素在維系社會秩序方面仍發揮重要作用,“法”相對“禮”而言,仍暫時起著補充功能。因此,民眾在處理日常事務時,更傾向于通過傳統的治理方式解決問題。
鄉土文化中,鄉村的制度、精神文化主要體現在鄉村社會的價值觀和規范制度中,同時也反映在鄉村社會的民風、習俗、輿論等方面。因此,鄉村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共同價值觀在社會變遷中起到了彌補“裂痕”的作用。在轉型期,鄉土民眾尤其是年輕群體脫離“熟人社會”步入“陌生人社會”。因此,他們在城市中接觸到新的價值觀所帶來的各種道德滑坡事件在鄉村社會也屢見不鮮,并對鄉村社會的共同價值觀提出新挑戰。然而,鄉土社會有其自身運轉的規則和價值體系,這種價值觀念的挑戰,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鄉村社會的內在運轉邏輯,鄉土社會的秩序運轉核心仍在于“倫理”和“禮俗”。這些以“禮”為基準的“非正式規范”雖然需要村民自覺遵守才得以發揮作用,但通過長期的實踐和學習,鄉土民眾達到了源于內心的自覺遵守狀態。例如,在鄉村社會中,人們注重傳統禮儀和家庭觀念,尊重長輩和親戚,重視鄰里之間的互助合作。這些傳統觀念和行為方式,已經深入村民的內心,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鄉土社會的分解和“非正式規范”的忽視并非同時發生,它們之間也不是簡單的對立關系,而是需要在相互作用的情境下進行觀察。在這兩者逐漸減弱的背景下,遵守和傳承“非正式規范”對于鄉土社會的鞏固至關重要。因為“非正式”規范的有效發揮需要鄉土民眾彼此熟悉、認可規則、懷念鄉土情感以及對鄉土記憶場域需求等因素的支撐。
2.鄉土文化依舊是構筑鄉村社會“精神家園”的核心要素。“中國文化以鄉村為本,以鄉村為重,所以中國文化的根就是鄉村。”鄉土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根基,即便歷經長久變遷,也無法忽視其作用。對任何社會現實的認知,都擺脫不了傳統的框架。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認知和重d0c633aecb5f643d2be0440074545aa1視程度愈為顯著,鄉土文化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保護。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傳統的文化元素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生活的需求,需要進行適當的改革和創新,在這個過程中,鄉土文化變遷成為“文化進化”的揚棄過程。
同時,人們迫于生計壓力,外出謀生,離開“生于斯,長于斯”的“熟悉鄉土”,來到陌生地域,并與陌生人建構一種新型短暫的契約關系,這種契約關系雖然可以帶來物質上的滿足,但難以填補人們內心深處的精神空虛。因此,鄉土文化的獨特價值在于,它不僅是歷史的積淀,更是人們情感、信仰、價值觀的源泉,扮演著“精神家園”的角色,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情感寄托和精神支撐。在現代社會中,盡管科技和經濟飛速發展,但鄉土文化依然能夠給予人們內心的安寧和歸屬感。在城市化浪潮中,鄉土文化成為了一種獨特記憶,一種對過去的懷念,也是一種對未來的期許。它不僅僅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精神寄托,一種心靈的歸宿。故而,在“陌生的社會”,鄉土文化以其獨特的魅力,成為人們的精神寄托,它以民俗節慶、村落建筑、歷史文化遺跡等物質文化的儀式形式存在,構建了寄托鄉土情感意識的“記憶之場”,使人們能夠回憶過去的生活,尋找自我歸屬感與認同感。這些富有回憶性、儀式感的民間習俗文化不僅承載和傳播了鄉土文化,亦是“離土又離鄉”村民存留鄉土情結的表達方式。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民間習俗、節日慶典等形式也展現了鄉土文化的特色,這些民俗文化活動不僅豐富了村民的業余生活,更讓他們在異鄉也能感受到家的溫暖。對于外出務工的村民而言,“夸富”只是一種尋求“他者”認同的行為手段,但無法真正解決個人對歸屬的需求。鄉土社會的民俗文化則填補了村民漂泊他鄉時的無助感,滿足了他們對鄉土情結的渴望,同時增強了村民之間的凝聚力。通過共同參與民俗活動,村民能夠重建與鄉土的聯系,找到歸屬感,并以此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系和認同。這些活動不僅為村民提供了一個交流互動的平臺,更讓他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心靈寄托。在這個平臺上,村民們共同分享彼此的故事和經驗,相互關心和支持,從而構建了一個充滿溫暖和團結的“精神家園”。
(二)未來愿景:鄉土文化未來走向的理性思考
在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鄉土文化變遷成為大勢所趨。面對這一變革,應當積極尋求鄉土文化價值的再定位,從而引導并推動鄉土文化朝著更加理想的方向發展。
1.推動鄉土文化與鄉村振興相結合。優秀傳統文化是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基礎,也是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軟實力”。文化振興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構件,應高度重視鄉土文化的價值和功能在推動鄉村文化振興過程中的作用。當前,鄉村社會面臨著對優秀傳統文化保護意識淡薄甚至缺失的困境,鄉土文化的衰落使鄉村社會生活的共同體精神逐漸消散,進一步導致鄉村社會民眾精神層面陷入普遍“失位”的窠臼。如果不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推動鄉村文化振興,鄉村全面振興便會步履維艱。正如梁漱溟曾言:“外力之破壞鄉村尚屬有限,我們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應,自動地破壞鄉村,殆十倍之不止。”因此,鄉土文化的保護和傳承顯得尤為重要。需要重新審視鄉土文化的價值,挖掘其深厚的內涵和獨特的魅力,使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同時,還應引導廣大村民樹立正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增強對鄉土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激發他們保護和發展鄉土文化的熱情和積極性。
此外,鄉村振興的目標并非讓城市取代鄉村,而是通過優化鄉村地區的發展環境,提升鄉村的綜合競爭力。在這個過程中,鄉土文化作為鄉村地區獨特的文化資源,在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下實現“再生產”成為必然趨勢。目前,隨著鄉村旅游業的日益繁榮和城市居民對鄉愁情結的日益凸顯,整個社會正逐漸從物質需求向文化情感需求轉變。因此,需要根據時代的要求,對鄉土文化進行改造、改良與傳承,不能將現代文化與鄉土文化對立起來。文化作為一套幫助人們適應特定處境的產物,當處境發生改變時,這套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可能無法繼續提供有效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堅持舊有的價值體系已經變得不再有意義。故而,為了在新時代實現鄉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必須將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相融合,進行“再生產”。
因此,在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今天,要從鄉土文化中汲取先輩的智慧和知識,進而推動鄉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鄉土文化在新時代語境下煥發出嶄新的生命活力,為鄉村振興提供持續的理論力量和精神動力。例如,江村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政界、企業界和文化教育界等各行各業的“新鄉賢”為其出謀劃策。由此可見,“新鄉賢”群體已成為推動鄉村治理新格局形成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此外,在傳承和發揚鄉土文化的過程中,要注重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充分挖掘和保護鄉土文化資源,包括歷史文化遺跡、民間民俗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建立完善的文化保護體系。二是要推動鄉土文化的創新性發展,將傳統鄉土文化與現代文化相結合,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三是要加強鄉土文化的教育普及工作,提高農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例如,江村秉持創新原則,促進江村文化禮堂、知源小院、廟港繅絲廠等場所的建設,構成了江村的教育科普文化基地,并成為“社會學圣地”。僅在2022年,村集體收入達到1000余萬元,開弦弓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超過4萬元。
2.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鄉土文化建設。堅守鄉土文化是維護中華文化根基的必要條件。然而,由于鄉土文化的鮮明特性,其發展往往會受到限制。正如克利福德·格爾茨所強調:“文化存在于貿易點、山岬上的城堡、牧羊場……”可見,鄉土文化并不是一種可以輕易移植或標準化的現象,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地理、歷史和社會環境之中。鄉土文化往往與特定地域緊密相連,具有濃厚的、相對穩定和連貫的形態。不過,這種穩定性也往往導致鄉土文化在面對現代化沖擊時顯得滯后和脆弱。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先進優秀文化的凝練,亦是民族文化和時代精神的基本內核,更是社會成員在判斷社會現象和利益關系時所依據的根本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基于此,需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鄉土文化守正創新。鄉土文化在守正創新的階段過程中,難免引發民眾精神文化信仰層面的“失位”,這種“失位”可能會表現為對鄉土文化價值的迷茫、對現代價值觀的盲目追求,甚至是對傳統文化的否定和遺忘。加之,部分地域文化在迎合市場需求的過程中,表現出一種快餐式的拜金、媚俗傾向,這種傾向對鄉土文化造成了嚴重沖擊,使得鄉土文化變得支離破碎、弱不禁風。因此,處理鄉土文化開放性、多元性特征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間的關系成為傳承發展新時代鄉土文化的迫切所需。
為此,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作為指導鄉村文化整合的核心,以加強鄉土文化在轉型“閾限空間”的向心力。同時,還應深入挖掘鄉土文化的基因脈絡和精神實質,把握鄉土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在互動關聯。這樣做可以將鄉土文化中優秀向上的價值觀念融入時代主流文化,又可以將鄉土文化中人們長期遵守的具有自我約束并對社會產生穩定秩序的道德觀念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此,不能僅關注鄉土文化物質表征的“形似”,更要深入把握鄉土文化精神內涵的“神似”。通過促進鄉土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雙向內外聯動,推動鄉土文化的現代化轉化與發展,同時補充和完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價值理論底蘊。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能夠促進鄉土文化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實現與現代文化的有機融合,進而形成獨具特色的現代鄉村文化體系。“現代性脫離不了各個社會的文化傳統”,進行尋覓甄別,選擇利用優秀與先進的文化元素,對于鄉土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在傳承鄉土文化的過程中,還需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鄉土文化,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全盤否定。此外,還應該積極推動鄉土文化的創新,鼓勵廣大農民群眾發揮主體作用,結合現代文化元素和科技手段,挖掘、保護和傳承優秀的鄉土文化,在新時代使其再次煥發出蓬勃的生機活力。
四、結語
鄉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今社會的發展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應該在保護和傳承鄉土文化的同時,積極推動鄉土文化的創新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鄉土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良性互動,既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又推動鄉土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同時,這也有助于提高農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和道德水平,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鄉土文化作為彌足珍貴的精神和物質財富,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今天,要重視從鄉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動鄉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鄉土文化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精神動力和理論支撐。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
[2]楊潔著.地域文化視角下的《詩經》思想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3]費孝通:費孝通九十新語[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4]格爾茨.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M].王海龍,張家瑄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5]費孝通.江村經濟[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公司,2021.
[6]牛震乾,朱夢佳.文化自覺與鄉土文化的價值重塑[J].鄉村論叢,2022,(06):21-27.
[7]劉曉峰.我國鄉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轉型[J].理論與現代化,2014,(01):66-71.
[8]徐輝,王儒年.鄉土文化促進農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阻滯與疏解[J].鄉村論叢,2023,(06):80-86.
[9]趙霞.傳統鄉村文化的秩序危機與價值重建[J].中國農村觀察,2011,(03):80-86.
[10]李玉雄,農藝.鄉村書店助力鄉村文化振興的現實邏輯與實踐研究——基于云南“先鋒沙溪白族書局”的考察[J].廣西民族研究,2023,(01):147-155.
[11]陳宏偉,史小建.鄉村振興背景下鄉土文化的當代價值[J].鄉村論叢,2023,(03):62-68.
[12]孟凡麗,郭妍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記憶建構:內涵、價值及實踐路徑[J].廣西民族研究,2023,(06):141-148.
[13]董磊明,陳柏峰,聶良波.結構混亂與迎法下鄉——河南宋村法律實踐的解讀[J].中國社會科學,2008,(05):87-100+206.
[14]孫慶忠.離土中國與鄉村文化的處境[J].江海學刊,2009,(04):136-141+239.
[15]費孝通.文化的生與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6]趙倫.從自治到管治:鄉村糾紛的類型變遷、化解失靈與權威重構[J].鄉村論叢,2023,(01):96-102.
[1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第1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
[18]宋靖野.從“跨文化比較”到“跨自然比較”——人類學比較研究的方法、類型與范式轉換[J].廣西民族研究,2023,(04):123-131.
[19]索曉霞.鄉村振興戰略下的鄉土文化價值再認識[J].貴州社會科學,2018,(01):4-10.
[2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第2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21]格爾茨.文化的解釋[M].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作者單位:東北大學民族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