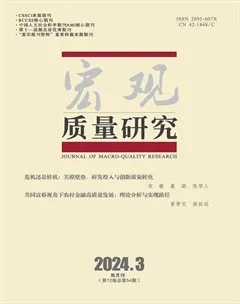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與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契機與困境













摘 要:
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農(nóng)民工高質(zhì)量就業(yè)注入了新動能,為其轉(zhuǎn)型升級提供了契機,但同時也帶來了新困境。基于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diào)查(CFPS)數(shù)據(jù),采用HLM模型從多層視角剖析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及其內(nèi)在機制,并揭示了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各個維度的實際問題。研究結果表明,數(shù)字經(jīng)濟在宏觀層面優(yōu)化了就業(yè)結構,在微觀層面促進了弱關系社會資本以及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而顯著改善了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尤其是在收入水平提升和勞動合同簽訂率方面;但也存在部分低收入農(nóng)民工無法享受“數(shù)字收入紅利”以及“靈活化”勞動合同的問題。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工作時間的影響表現(xiàn)出雙向效應,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所催生的新型職業(yè)崗位和勞動關系模式,也暴露出勞動保障缺失的制度漏洞。異質(zhì)性分析進一步表明,數(shù)字經(jīng)濟會對具有某些特征的農(nóng)民工群體產(chǎn)生偏向性,會加劇農(nóng)民工內(nèi)部的不平等。最后針對性地提出了改善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數(shù)字經(jīng)濟;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多層線性模型
DOI:10.13948/j.cnki.hgzlyj.2024.03.004
許清清,青島大學經(jīng)濟學院,電子郵箱:xuqingqing@qdu.edu.cn;王麗云,四川大學經(jīng)濟學院,電子郵箱:leeyun1218@163.com;江霞,青島大學經(jīng)濟學院,電子郵箱:xiajiang02@hotmail.com。本文受教育部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9BSH085)的資助。感謝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的意見,文責自負。
一、引言
數(shù)字經(jīng)濟這一核心生產(chǎn)要素,已經(jīng)滲透到了就業(yè)領域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戚聿東等,2020),成為就業(yè)領域的新增長點,并對就業(yè)結構、規(guī)模、質(zhì)量等諸多方面產(chǎn)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據(jù)《中國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與就業(yè)白皮書(2019年)》顯示,2018年我國數(shù)字經(jīng)濟領域就業(yè)崗位為1.91億個,占同年全國總就業(yè)人數(shù)的近1/4,同比增長率為11.5%,明顯高于同期全國總就業(yè)規(guī)模增速。在這一背景下,數(shù)字經(jīng)濟被社會寄予厚望,通過數(shù)字經(jīng)濟帶動和賦能高質(zhì)量就業(yè)成為中國政府托底就業(yè)大盤和提振經(jīng)濟增長的重要政策選項(孟祺,2021)。然而,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中占據(jù)著重要份額的農(nóng)民工群體的就業(yè)質(zhì)量狀況并不樂觀。根據(jù)《2021年農(nóng)民工檢測調(diào)査報告》顯示,農(nóng)民工的收入水平僅為同期城鎮(zhèn)就業(yè)人員的一半左右,非穩(wěn)定就業(yè)比例高達61%,而且面臨著工作時間長、社會保障缺失、工作權益難以維護等問題。因此,在數(shù)字經(jīng)濟時代,農(nóng)民工的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那么,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改善帶來了何種新契機,以及農(nóng)民工的高質(zhì)量就業(yè)又遇到了哪些困境?這是本文探討的核心議題。
對于數(shù)字經(jīng)濟能否助力農(nóng)民工高質(zhì)量就業(yè),學界一直存在著悖論與爭議。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通過創(chuàng)造新的就業(yè)機會、提升勞動效率等方式為農(nóng)民工的高質(zhì)量就業(yè)提供了契機。數(shù)字經(jīng)濟為中小企業(yè)的成長和新興產(chǎn)業(yè)的壯大創(chuàng)造了有利環(huán)境,激發(fā)了“蒲公英效應”。這不僅為農(nóng)民工提供了更多傳統(tǒng)與新興就業(yè)崗位(林龍飛和祝仲坤,2022),也為農(nóng)村勞動力、女性和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提供了更多參與市場競爭和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機會,從而推動了就業(yè)環(huán)境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普及為農(nóng)民工提供了獲取就業(yè)信息的便利,同時也為其技能提升提供了有效途徑,為獲得更高質(zhì)量的就業(yè)機會奠定了基礎(張廣勝和王若男,2023)。此外,數(shù)字技術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chǎn)效率,使他們能夠在更短的時間內(nèi)完成更多工作,這能夠縮短工作時間并提高收入(朱統(tǒng)和馬國旺,2022;程虹等,2020),有助于緩解過度勞動的問題(郭鳳鳴,2020)。已有研究表明,數(shù)字經(jīng)濟在提升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綜合指數(shù)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林龍飛和祝仲坤,2022;彭麗娜等,2023;王若男和張廣勝,2023;張廣勝與王若男,2023)。然而,另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也給農(nóng)民工帶來了技能要求提高、就業(yè)市場邊緣化風險增加、勞動市場結構性變化等方面的問題。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正在重塑勞動市場的需求,對農(nóng)民工提出了更高的專業(yè)技能和數(shù)字素養(yǎng)要求(鄧悅和蔣琬儀,2022)。難以適應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農(nóng)民工可能會面臨被淘汰或邊緣化的風險,這不僅會加劇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等,還可能形成“數(shù)字鴻溝”。隨著對勞動密集型和中技術密集型職位需求的減少,以及對高技術密集型職業(yè)和服務業(yè)工作需求的增加(孟祺,2021),結構性失業(yè)的現(xiàn)象可能會出現(xiàn)。此外,數(shù)字化的發(fā)展也可能導致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限模糊,使工作時間無形中被延長(戚聿東和劉翠花,2021)。在數(shù)字化的大背景下,就業(yè)人員尤其是農(nóng)民工可能會面臨權益模糊和福利保障滯后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會加劇他們的不穩(wěn)定性,從而不利于他們在勞動市場中的表現(xiàn)(林龍飛和祝仲坤,2022)。
隨著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就業(yè)質(zhì)量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單一的基礎維度,而是包含勞動者的就業(yè)保障、勞動強度、勞動收入等多個方面,綜合反映了勞動者在就業(yè)過程中的整體福祉。特別是在數(shù)字經(jīng)濟浪潮下,這種多維度質(zhì)量分析尤為重要,數(shù)字經(jīng)濟滲透到了經(jīng)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勞動力市場產(chǎn)生了多維度的影響,引發(fā)了包括就業(yè)形態(tài)變化、工作內(nèi)容升級以及勞動關系重構等多方面的變革。然而現(xiàn)有研究大多關注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或數(shù)字技術應用對農(nóng)民工收入、工作時間等單一方面的影響(郭鳳鳴,2020),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綜合性分析不足。鑒于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可能成為提升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重要契機,本研究進一步探究了以下問題:數(shù)字經(jīng)濟具體改善了就業(yè)質(zhì)量的哪些方面?其作用又是通過何種機制得以實現(xiàn)?在如今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大背景下,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仍面臨哪些挑戰(zhàn)?厘清這些問題,對于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優(yōu)化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環(huán)境,以及提升其整體生活質(zhì)量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梳理上述文獻,學者們雖從不同層面和角度探討了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然而,現(xiàn)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幾點不足:首先,關于數(shù)字經(jīng)濟與就業(yè)質(zhì)量的研究大多基于單一的宏觀層面或微觀層面,缺乏宏微觀相結合的分析框架和方法,難以全面揭示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就業(yè)質(zhì)量影響的內(nèi)在機制。其次,關于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這一特殊群體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現(xiàn)有研究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通常只關注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就業(yè)質(zhì)量綜合指標的整體影響,大多反映數(shù)字經(jīng)濟給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帶來的契機;而未對構成就業(yè)質(zhì)量的各個具體維度進行深入分析,難以揭示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存在的實質(zhì)性問題。鑒于此,本文從多層視角探討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及其各個維度的影響和作用機制,識別潛在的質(zhì)量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以期為促進農(nóng)民工高質(zhì)量就業(yè)和實現(xiàn)城鄉(xiāng)共同富裕提供學術參考。
本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更細致地考察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各個維度的影響,并識別了其中存在的質(zhì)量問題。二是充分考慮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影響的多維性和復雜性,采用多層線性模型,將個體家庭層面和地區(qū)層面的因素納入統(tǒng)一的分析框架,有效地處理了數(shù)據(jù)中存在的層次結構和嵌套關系,避免了估計結果偏誤和效率損失。三是從個體層面和省級層面分別探討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路徑,并分析了其影響的異質(zhì)性特征。
二、理論假設
數(shù)字經(jīng)濟作為一種基于信息技術和數(shù)據(jù)資源的創(chuàng)新型經(jīng)濟形態(tài),使生產(chǎn)要素的配置和組合方式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推動了生產(chǎn)效率的提高、市場競爭的激化、就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勞動關系的多元化等。這種變革對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水平和特征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既有利于提高農(nóng)民工的收入和福利,也可能增加農(nóng)民工的不穩(wěn)定性和不平等性等。
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改善帶來了契機。數(shù)字技術為農(nóng)民工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工作方式,減少了重復性和低附加值的勞動,減輕了他們的身心負擔(孫繼國和柴子涵,2023)。同時,勞動生產(chǎn)率和附加值的增加也提高了他們的收入水平。數(shù)字經(jīng)濟還拓寬了就業(yè)新領域,為不同地區(qū)、不同群體、不同勞動層次的農(nóng)民工提供了更多樣、更靈活、更智能的就業(yè)選擇(郭鳳鳴,2020),有助于緩解農(nóng)民工的過度勞動問題,同時滿足他們多元化的就業(yè)需求和發(fā)展期待。此外,互聯(lián)網(wǎng)為農(nóng)民工提供了獲取信息和維權的渠道,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反映訴求與困境,尋求解決方案和支持,進而提高就業(yè)質(zhì)量和福利水平(宋林和何洋,2020)。
另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也給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與困境。首先,數(shù)字技術的發(fā)展和應用改變了農(nóng)民工的勞動環(huán)境和勞動方式,使他們不僅需要適應更復雜的勞動條件,還要應對更加不規(guī)律和不確定的工作時間所帶來的勞動風險(胡京,2020)。靈活的工作方式使工作與生活的界限變得模糊,導致隱性工作時間延長,進一步增加了工作壓力和勞動強度,對農(nóng)民工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質(zhì)量產(chǎn)生了負面影響(戚聿東和劉翠花,2021)。其次,工作內(nèi)容的多變性使農(nóng)民工難以保持技能和知識的及時更新,這影響了他們的競爭力和收入水平。最后,工作地點的不確定性和分散性導致勞動關系變得模糊且脆弱,這加劇了勞動關系主體間的利益沖突,并對勞動權益保護、勞動爭議處理和勞動標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zhàn)(戚聿東等,2021)。基于此,提出假設1:
H1: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產(chǎn)生了多維度的影響,既包括正向的促進效應,也包括負向的抑制效應。
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路徑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在宏觀層面,數(shù)字經(jīng)濟有助于優(yōu)化就業(yè)結構,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提高農(nóng)民工的收入水平。在微觀層面,數(shù)字經(jīng)濟能夠促進農(nóng)民工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提升他們的就業(yè)能力。
從宏觀角度來看,數(shù)字化技術在第三產(chǎn)業(yè)的高度滲透,推動該產(chǎn)業(yè)成為經(jīng)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這一過程引發(fā)了產(chǎn)業(yè)結構的變換,并使不同產(chǎn)業(yè)對就業(yè)的拉動能力呈現(xiàn)顯著分化(崔巖,2023),帶動了就業(yè)結構的轉(zhuǎn)型。一些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和低端制造業(yè)等勞動密集型、中低技術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空間受到壓縮(Acemoglu和Restrepo,2018),而一些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以及消費性服務業(yè)等新興產(chǎn)業(yè)存在對勞動力的旺盛需求。這些新興產(chǎn)業(yè)的出現(xiàn)為農(nóng)民工提供了獲得更高收入的工作機會(崔巖和黃永亮,2023),為他們實現(xiàn)高質(zhì)量就業(yè)提供了契機(戚聿東等,2020)。同時,為了適應就業(yè)結構升級的要求,農(nóng)民工會主動或被動地參加相關的教育與培訓(Wu和Yang,2022)。這種教育與培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nóng)民工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增強了他們的就業(yè)競爭力和靈活性,有利于他們向更高效率和更高技能要求的就業(yè)領域流動。隨著教育和技能水平的提高,農(nóng)民工也能夠享受到更高的收入、更穩(wěn)定的職位、更完善的社會保障和更良好的職業(yè)發(fā)展前景,從而獲得更高水平的就業(yè)質(zhì)量。基于此,提出假設2:
H2:數(shù)字經(jīng)濟通過優(yōu)化就業(yè)結構改善了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
從微觀角度來看,數(shù)字經(jīng)濟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等技術手段,促進了農(nóng)民工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一方面,互聯(lián)網(wǎng)的使用拓寬了農(nóng)民工的社會網(wǎng)絡(丁述磊和劉翠花,2022),有助于他們獲取高質(zhì)量的就業(yè)信息,提高其個人能力與崗位需求的匹配程度(鄧睿,2020a);另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倒逼農(nóng)民工提升自身綜合素質(zhì)(韓艷旗和郭志文,2022),包括數(shù)字技能、信息獲取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等。同時,數(shù)字經(jīng)濟也降低了農(nóng)民工的人力資本投資負擔,使他們能夠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等數(shù)字技術更有效地學習(方福前和田鴿,2021)。這些因素促進了農(nóng)民工人力資本的提升,增強了他們的競爭力和勞動生產(chǎn)率,進而使其收入、社會地位等方面得到改善(叢屹和閆苗苗,2022)。因此,提出假設3和假設4:
H3:數(shù)字經(jīng)濟促進了農(nóng)民工社會資本的積累進而改善了其就業(yè)質(zhì)量。
H4:數(shù)字經(jīng)濟促進了農(nóng)民工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而改善了其就業(yè)質(zhì)量。
三、研究設計
(一)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基準回歸所采用的微觀實證數(shù)據(jù)來源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diào)查中心(ISSS)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diào)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選取男性16~60歲、女性16~55歲從事非農(nóng)工作的農(nóng)業(yè)戶籍人口作為研究對象。為了排除極端數(shù)據(jù)的干擾,對連續(xù)變量進行了1%的縮尾處理,并剔除了異常樣本,最終得到有效樣本5386個。此外,本研究還引入了宏觀層面的變量,相關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統(tǒng)計年鑒》。
(二)指標選取
1.就業(yè)質(zhì)量
就業(yè)質(zhì)量是反映農(nóng)民工就業(yè)狀況的綜合性概念,本文沿用Erhel等人(2014)提出的客觀就業(yè)質(zhì)量測量模型從收入、工作強度、工作穩(wěn)定性、工作保障四個維度構建農(nóng)民工的客觀就業(yè)質(zhì)量評價指標體系。各指標的具體含義以及相關的描述性統(tǒng)計如表1所示。另外,借鑒鄧睿(2020b)等人的做法,在對各維度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工作強度進行了正向化處理),采用等權平均法來獲得客觀就業(yè)質(zhì)量指數(shù)。
如表1所示,2018年,農(nóng)民工的平均年收入為36047.60元,這一數(shù)值顯著低于城鎮(zhèn)職工的平均工資。農(nóng)民工的平均周工作時長為55.81小時,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guī)定的44小時法定工作時限。在調(diào)查樣本中,有54%的農(nóng)民工未能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61%的農(nóng)民工在工作中未獲得任何形式的保險保障。綜合以上數(shù)據(jù),可以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工群體的就業(yè)質(zhì)量整體較低,這一現(xiàn)狀亟需通過相關政策和社會支持得到改善。
2.數(shù)字經(jīng)濟指數(shù)
數(shù)字經(jīng)濟的概念最早由Tapscott(1995)提出,隨著諸多機構以及學者的深入研究,其內(nèi)涵也不斷得到完善與發(fā)展。目前,國內(nèi)普遍接受的是G20峰會中對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定義:數(shù)字經(jīng)濟是以數(shù)據(jù)為核心要素、以網(wǎng)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訊技術為關鍵推動力的一系列經(jīng)濟活動。
結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數(shù)據(jù)的可得性,本文基于劉軍等人(2020)的方法,從信息化發(fā)展、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數(shù)字交易發(fā)展三個維度對數(shù)字經(jīng)濟進行了分解,并采用熵權法進行賦權。表2詳細列出了數(shù)字經(jīng)濟的指標選取及權重分布。
3.控制變量
影響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因素有很多,但過多或不恰當?shù)目刂谱兞咳菀滓l(fā)過擬合和多重共線性等問題,造成估計偏誤。為了提高控制變量選取的科學性,本文借助Lasso算法從個人層面、家庭層面、省級層面進行了控制變量的篩選。表3展示了經(jīng)Lasso回歸篩選后保留的控制變量及各指標的具體含義。此外,為了消除異方差帶來的影響,本文對連續(xù)變量進行了對數(shù)轉(zhuǎn)換。各變量的定義及描述性統(tǒng)計情況如表3所示。
(三)模型選擇
由于省級數(shù)據(jù)與農(nóng)民工個體數(shù)據(jù)之間存在明顯的嵌套關系,即一個省份對應多個農(nóng)民工個體。這往往導致個體間隨機誤差的獨立性假設難以滿足,使傳統(tǒng)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不再準確(Raudenbush和Bryk,1992)。因此,本文擬采用Lindley等(1972)提出的多層線性模型(HLM)進行實證研究。HLM適用于具有嵌套結構的數(shù)據(jù),更適合本研究的情形。經(jīng)檢驗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組內(nèi)相關系數(shù)ICC(1)為0.072,大于0.059,表明存在層級效應,需要使用多層線性模型(Cohen,1988)。
為分析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構建如下基準模型:
Level-1 Model:Yij=β0j+∑βZij+eij
Level-2 Model:β0j=γ00+γ01(DEj)+∑γXj+μ0j
Mix Model:Yij=γ00+γ01(DEj)+∑βZij+∑γXj+eij+μj
其中,Yij為被解釋變量,分別包括j省農(nóng)民工i的就業(yè)質(zhì)量指數(shù)(EQij)、收入的對數(shù)和工作時間的對數(shù),DEj為數(shù)字經(jīng)濟指數(shù)變量,Zij為微觀層面控制變量的集合,Xj為一系列宏觀層面的控制變量。β和γ為系數(shù),其中,γ01是本研究關注的核心變量系數(shù),反映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客觀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eij和μj分別為個體層面和省級層面的隨機誤差項。
另外,當被解釋變量為是否簽訂勞動合同和工作保障時,考慮到該變量為二分變量,采用Probit模型進行回歸,構建模型如下:
Level-1 Model:Probit(pi)=lnpi(yij=1)1-pi(yij=1)=β0j+∑βZij+eij
Level-2 Model:β0j=γ00+γ01(DEj)+∑γXj+μ0j
Mix Model:lnpi(yij=1)1-pi(yij=1)=γ00+γ01(DEj)+∑βZij+∑γXj+eij+μj
其中,yij為j省個體i的工作穩(wěn)定或工作保障變量,pi表示個體i工作穩(wěn)定或社會保障變量等于1的概率,其余變量設置與前文一致。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4報告了基準回歸結果。列(1)顯示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就業(yè)質(zhì)量綜合指數(shù)的影響,列(2)~列(5)則進一步報告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就業(yè)質(zhì)量各個維度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數(shù)字經(jīng)濟不僅能夠改善農(nóng)民工的收入,還能夠提高其勞動合同簽訂率,從而顯著提升其就業(yè)質(zhì)量。然而,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工作強度和工作保障的影響并不顯著。H1得以驗證。這是因為,數(shù)字經(jīng)濟能為農(nóng)民工提供更多的就業(yè)選擇,增加他們的收入來源。同時,數(shù)字經(jīng)濟促進了整體就業(yè)生態(tài)的改善,增強了農(nóng)民工的權益保護意識,進而促進了他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通過對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進行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男性農(nóng)民工的收入水平、工作保障和勞動合同簽訂率都高于女性農(nóng)民工,盡管他們面臨更大的勞動強度,但是他們的綜合就業(yè)質(zhì)量指數(shù)仍然高于女性農(nóng)民工。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對于提高農(nóng)民工的工作收入、勞動合同簽訂率和工作保障程度,以及降低工作強度都有積極作用,因此教育對于改善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至關重要。生活滿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生活的積極態(tài)度,生活滿意度較高的農(nóng)民工更傾向于享受生活并減少長時間勞動的可能性,同時他們更注重工作的保障程度,更有可能選擇提供保險的工作。集體土地的擁有能夠提高農(nóng)民工的生活保障,但也一定程度上牽制了農(nóng)民工的發(fā)展空間,降低了農(nóng)民工的工資性收入,從而降低了他們的就業(yè)質(zhì)量。家庭支出高的農(nóng)民工有著較高的家庭經(jīng)濟水平,更容易找到收入高、工作強度相對較低,勞動合同簽訂率高、保障也更好的工作。相較于戶外工作,室內(nèi)工作的就業(yè)質(zhì)量更高,但在車間工作的農(nóng)民工其工作時間往往更長。工作地點離居住地越遠,表明求職范圍更大,就業(yè)機會更多,更容易找到收入高、勞動合同簽訂率高和保障完善的工作,這有助于提高整體就業(yè)質(zhì)量,但通常也意味著更長的工作時間。
上述結果僅分析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總體影響,未能深入剖析具體問題。為此,本文進一步探討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就業(yè)質(zhì)量及其構成維度的作用模式,并嘗試揭示潛在的質(zhì)量問題。
1.農(nóng)民工高質(zhì)量就業(yè)契機與局限
本文選取10%、25%、50%、75%、90% 分位點作為回歸節(jié)點,運用分位數(shù)回歸分析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規(guī)律。如表5所示,研究發(fā)現(xiàn)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綜合就業(yè)質(zhì)量的正向影響并不是均勻的,而是呈“倒U”形變化。其原因可以從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結構和技能需求變化的雙重影響來分析。
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在對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和崗位產(chǎn)生替代效應的同時,也催生了許多新型產(chǎn)業(yè)和新型崗位,為農(nóng)民工提供了更多樣化和靈活化的就業(yè)選擇;另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提高了對農(nóng)民工的技能要求。對于就業(yè)質(zhì)量較低的農(nóng)民工而言,盡管數(shù)字經(jīng)濟擴大了他們的就業(yè)機會,但由于教育程度、培訓機會和數(shù)字技能的限制,處于“數(shù)字洼地”的他們往往只能從事技能要求較低的新興職業(yè),導致就業(yè)質(zhì)量提升效果有限。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指數(shù)的增加,意味著他們在勞動報酬、工作時間、工作穩(wěn)定性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得到了改善。這通常伴隨著農(nóng)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數(shù)字化技能水平的提升,農(nóng)民工更可能享受“數(shù)字紅利”并將之迅速轉(zhuǎn)化為“就業(yè)質(zhì)量改善優(yōu)勢”,實現(xiàn)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個體就業(yè)質(zhì)量效應的邊際遞增。然而當就業(yè)質(zhì)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50%分位點之后),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就業(yè)質(zhì)量的作用效果出現(xiàn)遞減趨勢。這是因為隨著就業(yè)崗位的質(zhì)量不斷增加,勞動力市場逐漸趨于飽和,競爭壓力增加,此時農(nóng)民工個體的數(shù)字技能已得到發(fā)展,數(shù)字鴻溝得到大幅度彌合,數(shù)字技能提升對就業(yè)質(zhì)量的改善邊際效果也逐漸降低。
2.數(shù)字收入紅利與邊緣化風險
本文進一步采用分位數(shù)回歸探討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收入的影響,結果顯示(見表6),其正面效應隨收入分位數(shù)提高而遞減,表明數(shù)字經(jīng)濟在提升農(nóng)民工收入上存在分配不均。具體而言,數(shù)字經(jīng)濟對低收入農(nóng)民工的效益大于較高收入的農(nóng)民工。值得注意的是,在10%分位點上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這表明有一部分低收入農(nóng)民工被邊緣化了。盡管數(shù)字經(jīng)濟創(chuàng)造了更多較低就業(yè)門檻的新型就業(yè)崗位,如外賣員、快遞員等,這些崗位對學歷和技能要求不高,但仍需要掌握基本的數(shù)字技能。而對于部分收入較低的農(nóng)民工而言,他們已經(jīng)無法跟上數(shù)字經(jīng)濟快速變革的步伐,無法掌握基本數(shù)字技能,從而可能無法享受到數(shù)字經(jīng)濟帶來的紅利。而對于大部分能夠掌握基本數(shù)字技能的低收入農(nóng)民工,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不僅極大地增加了他們的就業(yè)機會和收入來源,也提升了他們的數(shù)字技能和數(shù)字素養(yǎng),大幅縮小了其在數(shù)字領域與其他群體的鴻溝,從而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和勞動報酬。然而,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農(nóng)民工面臨的職業(yè)競爭壓力增加,數(shù)字經(jīng)濟提升其技能水平進而影響其收入的正向作用也逐步減弱。這一結果與就業(yè)質(zhì)量綜合指數(shù)呈現(xiàn)出“倒U”形的影響規(guī)律不同,反映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復雜影響機制。
3.數(shù)字經(jīng)濟的雙向工時效應
通過對工作時間進行分位數(shù)回歸,我們發(fā)現(xiàn)(見表7),盡管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工作時間的整體作用并不顯著(見表4),但在25%分位點及其之后,數(shù)字經(jīng)濟能夠顯著降低農(nóng)民工的工作時間。這一現(xiàn)象可歸因于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工作時間所產(chǎn)生的雙向效應。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能夠提供更靈活的工作模式和更高效的工作流程,縮短工作時間,緩解過度勞動。同時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也增加了農(nóng)民工的收入水平,產(chǎn)生補償效應,促使他們增加休閑消費,從而進一步降低工作時間。另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也存在增加工作時間的傾向。對于工作時間不足的隱性失業(yè)群體,數(shù)字經(jīng)濟提供了更多工作機會,從而能夠增加該部分勞動者的工時。例如,在10%分位點上,這些農(nóng)民工的實際工作時間往往低于他們的期望水平,存在不充分就業(yè)問題。此時,數(shù)字經(jīng)濟有增加農(nóng)民工工作時間的趨勢。但由于該部分農(nóng)民工通常是技能水平較低的簡單勞動力,且數(shù)字化素養(yǎng)不高,這抑制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工作時間的提升作用,最終使得這一效果并不顯著。同時,數(shù)字經(jīng)濟還會模糊工作與生活的界限,無形中延長了勞動者的工作時間。這一現(xiàn)象在工作時間較長的勞動者群體中尤為突出,因此在90%分位點上,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工作時間降低的邊際效果有所減弱。正是由于這種方向相反的雙向工時效應,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工作時間的整體影響不再顯著。
4.勞動合同“靈活化”困境
通過對農(nóng)民工的勞動合同簽訂狀況進行統(tǒng)計分析,我們注意到有21.27%的農(nóng)民工在與工作單位簽訂的合同中并未明確約定合同期限(見表8)。這種情況下的“靈活性”對于資本方而言,意味著可以根據(jù)需要自由設定就業(yè)條件。然而,對于雇用工人來說,這種“靈活性”卻轉(zhuǎn)化為不得不接受企業(yè)提出的任何條件,包括但不限于隨時面臨被解雇的風險。這種對勞動力的“靈活”運用,導致了工會力量的削弱、工資增長的停滯、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公司高層收入的急劇上升(Kotz,2015)。這些后果不僅反映了資本對工人的控制,也凸顯了當前勞動市場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穩(wěn)定性問題。因此,必須審慎考慮,在保障勞動者權益和促進經(jīng)濟靈活性之間找到平衡點。
5.勞動保障缺失困境
最后,表4中列(3)的結果表明數(shù)字經(jīng)濟并沒有改善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保障,這是因為數(shù)字經(jīng)濟催生的新型靈活就業(yè)崗位吸納了大量的農(nóng)民工群體,如外賣行業(yè)等,而在這些崗位中勞動者通常沒有與雇主直接簽訂勞動合同,而是與第三方機構簽訂所謂的“合作協(xié)議”。這種協(xié)議形式上看似提供了靈活的工作安排,實際上卻使得勞動者處于一種不穩(wěn)定的就業(yè)狀態(tài),因為這些協(xié)議并不構成正式的勞動關系,第三方企業(yè)也就無須為這些工人繳納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福利。這也表明技術進步雖然創(chuàng)造了就業(yè)機會,但同時也可能引致勞動保障的缺失。
(二)內(nèi)生性處理
1.工具變量法
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可能受到不可觀測因素的干擾,進而存在遺漏變量導致的內(nèi)生性問題。為此,本文采用1984年各省份的人均郵電業(yè)務總量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內(nèi)生性處理(趙濤等,2020)。表9報告了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在考慮了可能存在的內(nèi)生性問題后,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正向影響仍然顯著,這與前文的分析結果相符。
2.Heckman兩步法
由于選擇效應的存在,農(nóng)業(yè)戶籍人口是否從事非農(nóng)工作并不是一個隨機事件,因此農(nóng)民工樣本也不具有隨機性,導致存在樣本選擇偏誤問題(張廣勝和王若男,2023),使估計結果偏離真實值。同時,樣本選擇偏誤會導致解釋變量與隨機誤差項之間存在相關性,因而也是造成內(nèi)生性問題的來源之一。為此,本文采用了Heckman兩步法來糾正這一偏誤。表9中的結果顯示,在加入逆米爾斯比率糾正了樣本選擇偏誤問題后,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依然表現(xiàn)出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驗證了本文主要結論的穩(wěn)健性。
另外,本文還將逆米爾斯比率納入了工具變量回歸分析中,從而同時處理了樣本選擇偏誤以及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導致的內(nèi)生性問題,相關結果如表9列(3)所示。將兩種可能的內(nèi)生性來源同時處理后,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仍顯著為正。
(三)穩(wěn)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模型估計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從更換被解釋變量、更換核心解釋變量以及更換樣本三個方面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穩(wěn)健性檢驗。
在原有客觀就業(yè)質(zhì)量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將農(nóng)民工對工作的主觀心理感受也納入其中,構建了包括收入、勞動強度、工作穩(wěn)定性、工作保障以及工作滿意度的就業(yè)質(zhì)量指數(shù),并將該就業(yè)質(zhì)量指數(shù)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
借鑒趙濤等人(2020)的方法,從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和數(shù)字金融普惠兩個維度,重新構建數(shù)字經(jīng)濟綜合指數(shù)的指標框架,并運用熵權法計算得到數(shù)字經(jīng)濟指數(shù)進行回歸。
選取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diào)查(CFPS)數(shù)據(jù)中的農(nóng)民工樣本,并結合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相關數(shù)據(jù),計算2016年數(shù)字經(jīng)濟指數(shù)和其他變量的指標值對模型進行重新估計上述穩(wěn)健性檢驗結果均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說明本文主要結論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限于篇幅,穩(wěn)健性檢驗結果在此不做報告,讀者可向作者索要。。
五、機制分析
(一)就業(yè)結構
本文分別從產(chǎn)業(yè)就業(yè)結構和技能就業(yè)結構兩個維度檢驗就業(yè)結構在數(shù)字經(jīng)濟就業(yè)質(zhì)量效應中的機制作用。產(chǎn)業(yè)就業(yè)結構采用第三產(chǎn)業(yè)就業(yè)占比來衡量(戚聿東等,2020),技能就業(yè)結構則通過高技能勞動力占比來衡量。其中,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勞動力被定義為高技能勞動力(孫文遠和周寒,2020)。
表10列(1)、列(2)顯示,數(shù)字經(jīng)濟顯著推動了勞動力向服務化和高技能化轉(zhuǎn)型,進而提升了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這一轉(zhuǎn)型得益于數(shù)字經(jīng)濟催生的新產(chǎn)業(yè)和業(yè)態(tài),增強了服務業(yè)的就業(yè)吸納力,為農(nóng)民工提供了更高收入的就業(yè)機會(崔巖和黃永亮,2023)。同時,數(shù)字經(jīng)濟優(yōu)化了勞動力需求結構,并降低了農(nóng)民工的人力資本投資成本(方福前和田鴿,2021),為農(nóng)民工的人力資本積累創(chuàng)造了條件,促進他們從低技能向高技能就業(yè)的轉(zhuǎn)變。
(二)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是與個人所擁有的關系網(wǎng)絡相關的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Bourdieu,1986),能夠為個人或組織提供信息和支持,具有顯著的經(jīng)濟效益。人力資本則是勞動者工作能力的表征,體現(xiàn)為蘊含在人身上的各種生產(chǎn)知識、勞動與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質(zhì)的總和(邢敏慧和張航,2020)。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都是影響勞動者就業(yè)質(zhì)量的重要因素。
其中,社會網(wǎng)絡是社會資本的重要載體,可分為基于親緣和地緣的強關系網(wǎng)絡(如親友和鄰里網(wǎng)絡)以及基于職業(yè)、行業(yè)或興趣的弱關系網(wǎng)絡(如同行和專業(yè)組織)。隨著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農(nóng)民工的社會網(wǎng)絡也不再僅局限于強關系,而是逐漸突破空間距離的約束,拓展了更開放的弱關系網(wǎng)絡。本文借鑒張笑寒和李金萍(2022)的方法,采用“每月郵電通訊費”和“人情禮支出”作為社會資本的代理變量,分別衡量弱關系和強關系社會資本,以反映農(nóng)民工在不同社會網(wǎng)絡中的信息交流和情感投入。
為了測算人力資本增量,本文運用Cobb-Douglas形式將人力資本增量設定為教育投資和健康投資的組合(楊建芳等,2006;余長林,2006),其中教育投資以教育培訓支出表示,健康投資以保健支出表示。
表10列(3)分別展示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的強關系社會資本和弱關系社會資本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在數(shù)字經(jīng)濟背景下,農(nóng)民工的社會資本結構經(jīng)歷了顯著的轉(zhuǎn)變。具體而言,數(shù)字經(jīng)濟在拓展了農(nóng)民工弱關系社會資本的同時,削弱了他們對強關系社會資本的依賴。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大部分農(nóng)民工長期遠離家鄉(xiāng)務工,與基于親緣、地緣的強關系網(wǎng)絡聯(lián)系不夠密切,且強關系社會資本往往具有較高的同質(zhì)性和局限性,難以提供有效的職業(yè)發(fā)展資源;另一方面,弱關系社會資本的資源相似性較低,信息重疊少,價值更高(Granovetter,1973)。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農(nóng)民工能夠建立更廣泛的弱關系網(wǎng)絡,有效降低了他們獲取信息的障礙和成本,使他們不再處于信息孤島,從而增加了他們接觸到創(chuàng)新性、高價值或稀缺資源的機會。綜上所述,數(shù)字經(jīng)濟可以通過促進農(nóng)民工弱關系社會資本的積累,幫助他們優(yōu)化決策過程,減少機會成本和風險,提高機會收益,從而提升他們的就業(yè)質(zhì)量(楊政怡和楊進,2021)。H3得以驗證。
此外,表10列(4)顯示,數(shù)字經(jīng)濟對人力資本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這意味著數(shù)字經(jīng)濟能夠促進農(nóng)民工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而改善他們的就業(yè)質(zhì)量。H4得以驗證。這是因為通過網(wǎng)絡平臺和移動應用,農(nóng)民工獲得了豐富的學習與培訓機會,增強了其人力資本,進而拓寬了就業(yè)選擇,改善了就業(yè)條件(邢敏慧和張航,2020)。
六、異質(zhì)性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改善效應是否會受到農(nóng)民工個體特征和工作特征的影響,進而存在異質(zhì)性,本文基于四個維度對農(nóng)民工樣本進行分類分析,即新生代與老一代、高技能與低技能、高國際聲望職業(yè)與低國際聲望職業(yè)、遠距離與近距離農(nóng)民工。具體劃分依據(jù)為:出生日期(以1980年為界)、受教育年限中位數(shù)、國際職業(yè)聲望量表得分中位數(shù)、務工地點與家鄉(xiāng)的距離中位數(shù)。據(jù)此,本文對不同類型農(nóng)民工進行分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1所示。
1.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代際差異
表11列(1)展示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新生代農(nóng)民工與老一代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結果。研究結果顯示,數(shù)字經(jīng)濟對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老一代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并不顯著。產(chǎn)生這一差異的原因在于,新生代農(nóng)民工與老一代農(nóng)民工在數(shù)字化技術的接受程度方面存在一定的“數(shù)字鴻溝”,新生代農(nóng)民工對互聯(lián)網(wǎng)等數(shù)字經(jīng)濟技術的利用度和熟練度要高于老一代農(nóng)民工,因此更能夠在數(shù)字化浪潮中抓住機會和利益,提高自身的技能和競爭力,改善自身的工作條件和收入水平。相反,老一代農(nóng)民工由于個體現(xiàn)代化程度較低,對新的思想觀念和信息技術的接受能力較弱,因此在數(shù)字經(jīng)濟浪潮中難以適應和受益,甚至可能面臨被邊緣化和淘汰的風險。
2.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技能水平差異
表11列(2)為數(shù)字經(jīng)濟對高技能農(nóng)民工和低技能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影響的分組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數(shù)字經(jīng)濟顯著改善了高技能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但對低技能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改善作用并不明顯。這是因為,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就業(yè)創(chuàng)造效應是影響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數(shù)字經(jīng)濟催生出許多新興就業(yè)形式,其中既涵蓋了技能要求較高的崗位,如互聯(lián)網(wǎng)、軟件開發(fā)、電子商務等,也包含了技能門檻較低的崗位,如外賣員、快遞員等。然而,這些不同技能層次的崗位在就業(yè)質(zhì)量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高技能農(nóng)民工更可能從事技能要求高、收入水平高、發(fā)展空間大的崗位,而低技能農(nóng)民工則更傾向于進入就業(yè)門檻較低,但工作強度大、社會保障缺乏的崗位。
3.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職業(yè)特征差異
表11列(3)呈現(xiàn)了從事高聲望職業(yè)與從事低聲望職業(yè)農(nóng)民工的異質(zhì)性分析結果。結果表明,數(shù)字經(jīng)濟對高國際聲望職業(yè)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對低國際聲望職業(yè)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影響不顯著。這是因為高國際聲望得分的職業(yè)意味著該職業(yè)在人們心目中的社會重要性、價值或貢獻,以及人們對相應從業(yè)者給予的尊重和贊許較高。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高國際聲望職業(yè)農(nóng)民工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平臺,使他們能夠更充分地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技能和社會價值,從而提升他們的收入水平、福利待遇和工作滿意度。而從事低國際聲望職業(yè)的農(nóng)民工往往面臨著較低的技能要求和較高的替代性,數(shù)字經(jīng)濟對他們就業(yè)質(zhì)量的改善作用較弱。此外,從事低國際聲望職業(yè)的農(nóng)民工往往缺乏足夠的數(shù)字技能和資源,難以充分利用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優(yōu)勢。
4.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務工距離差異
表11列(4)為數(shù)字經(jīng)濟對不同務工距離農(nóng)民工的分組回歸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數(shù)字經(jīng)濟對遠距離務工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近距離務工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沒有顯著影響。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在于,遠距離務工的農(nóng)民工更傾向于在城市就業(yè),而城市的數(shù)字化發(fā)展水平更高,數(shù)字技術的應用更廣,數(shù)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更完善,數(shù)字人才的需求更旺盛。這些因素都為遠距離務工農(nóng)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時,城市的數(shù)字化也改善了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環(huán)境和福利待遇,例如,通過數(shù)字平臺,農(nóng)民工可以更方便地獲取就業(yè)信息、進行在線培訓、享受社會保障、維護勞動權益等。相反,近距離務工的農(nóng)民工往往在鄉(xiāng)鎮(zhèn)從事非農(nóng)工作,相對城市而言,數(shù)字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發(fā)展滯后,數(shù)字技術應用有限,數(shù)字基礎設施建設落后,數(shù)字人才供給不足。這些因素都限制了近距離務工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選擇和收入增長,數(shù)字化對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環(huán)境和福利待遇的改善作用也相對弱化。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diào)查的微觀數(shù)據(jù)以及31個省份的宏觀數(shù)據(jù),運用多層線性模型,探究了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1)數(shù)字經(jīng)濟顯著改善了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尤其是在收入水平提升和勞動合同簽訂率方面;但也存在著部分低收入農(nóng)民工無法享受“數(shù)字收入紅利”以及“靈活化”勞動合同的問題。(2)盡管數(shù)字經(jīng)濟對工作時間的整體影響并不顯著,但它仍能緩解工作時間較長農(nóng)民工的過度勞動問題,并顯示出雙向效應;數(shù)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催生了新型崗位和新型勞動關系,這一進程也暴露出勞動保障體系中的缺陷。(3)在宏觀層面上,數(shù)字經(jīng)濟可以通過優(yōu)化就業(yè)結構促進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提升;在微觀層面上,數(shù)字經(jīng)濟能夠促進農(nóng)民工弱關系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提升他們的就業(yè)質(zhì)量。(4)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存在明顯的異質(zhì)性特征,即數(shù)字經(jīng)濟更傾向于改善新生代農(nóng)民工、高技能農(nóng)民工以及從事高國際聲望職業(yè)和遠距離務工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啟示:
首先,數(shù)字經(jīng)濟在賦能農(nóng)民工高質(zhì)量就業(yè)方面展現(xiàn)出強勁勢能。政府應該把數(shù)字經(jīng)濟作為助力農(nóng)民工實現(xiàn)高質(zhì)量就業(yè)的關鍵抓手。具體而言,要強化數(shù)字基礎設施建設,并適當降低收費標準或提供網(wǎng)絡費用補貼,進一步提高農(nóng)村勞動力的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降低他們獲得數(shù)字信息的門檻。此外,要加強對農(nóng)民工特別是低收入農(nóng)民工的數(shù)字就業(yè)培訓,構建開放的數(shù)字基礎入門培訓平臺,充分利用現(xiàn)代化數(shù)字技術,根據(jù)農(nóng)民工群體的特點,創(chuàng)建靈活多樣的學習方式,并積極引導農(nóng)民工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從而提高他們的數(shù)字化素養(yǎng)水平。
其次,政府應當鼓勵支持數(shù)字技術在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中的廣泛應用,以此促進數(shù)字經(jīng)濟與傳統(tǒng)行業(yè)的深度融合。這不僅能夠為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注入新動力,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還能顯著提升生產(chǎn)效率。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在解決就業(yè)不足、隱性失業(yè)以及過度勞動問題上獲得雙贏,實現(xiàn)勞動力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和社會經(jīng)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此外,完善勞動保障體系至關重要,特別是針對數(shù)字經(jīng)濟領域新興崗位和勞動關系,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guī),確保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避免他們因技術變革而面臨就業(yè)困境。在此基礎上,對于新興職業(yè)形態(tài),應當規(guī)范靈活的工作安排,在勞動者權益保障與經(jīng)濟靈活性之間尋求平衡。
再次,就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升級、弱關系社會網(wǎng)絡的拓展和人力資本的提升在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就業(yè)質(zhì)量效應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政府要預先考慮可能出現(xiàn)就業(yè)結構快速變化導致的農(nóng)民工失業(yè)問題,鼓勵支持基層組織和企業(yè)對農(nóng)民工開展有針對性的專業(yè)數(shù)字技能培訓,通過精準高效的培訓幫農(nóng)民工突破發(fā)展瓶頸,提升其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力,從而使農(nóng)民工適應數(shù)字化背景下經(jīng)濟結構不斷轉(zhuǎn)型調(diào)整的需要,降低“結構性失業(yè)”的風險。除此之外,還要關注農(nóng)民工弱關系社會網(wǎng)絡以及自身綜合能力的發(fā)展。依托數(shù)字技術建立全國性與地區(qū)性的農(nóng)民工通訊互助交流平臺,擴大他們的交往半徑,以打破農(nóng)民工社會網(wǎng)絡的空間局限性。同時,為農(nóng)民工提供培訓和健康投資補貼,降低其人力資本投資成本,促進他們?nèi)肆Y本的提升。
最后,厘清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就業(yè)質(zhì)量效應在不同群體中的特殊表現(xiàn),有針對性地加以改善。特別是要關注老一代、低技能、從事低國際聲望職業(yè)和近距離務工的農(nóng)民工群體的就業(yè)質(zhì)量改善情況,加大對這些群體的數(shù)字化培訓支出和政策傾斜力度,緩解農(nóng)民工內(nèi)部的不平等問題。同時,加強宣傳引導,提高處于數(shù)字劣勢農(nóng)民工群體對數(shù)字技能培訓的認可度和接受度,提升其數(shù)字化融入水平。此外,要定期對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質(zhì)量進行評估檢測,及時發(fā)現(xiàn)問題并修正,不斷縮小不同特征群體間的數(shù)字化差距,進而加快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
參考文獻:
[1] 程虹、王澤宇、陳佳,2020:《機器人與工資:基于勞動力質(zhì)量中介效應的解釋——來自中國企業(yè)綜合調(diào)查(CEGS)的經(jīng)驗證據(jù)》,《宏觀質(zhì)量研究》第3期。
[2] 崔巖,2023:《宏觀因素多維共振背景下的就業(yè)結構變遷和就業(yè)質(zhì)量分化研究》,《學海》第3期。
[3] 崔巖、黃永亮,2023:《就業(yè)技能與職業(yè)分化——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差異及其社會后果》,《社會學研究》第5期。
[4] 叢屹、閆苗苗,2022:《數(shù)字經(jīng)濟、人力資本投資與高質(zhì)量就業(yè)》,《財經(jīng)科學》第3期。
[5] 鄧睿,2020a:《農(nóng)民工社會資本的就業(yè)質(zhì)量效應分異——基于回報差異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雙重視角》,《宏觀質(zhì)量研究》第5期。
[6] 鄧睿,2020b:《社會資本動員中的關系資源如何影響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經(jīng)濟學動態(tài)》第1期。
[7] 丁述磊、劉翠花,2022:《數(shù)字經(jīng)濟時代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研究——基于社會網(wǎng)絡的視角》,《經(jīng)濟與管理研究》第7期。
[8] 鄧悅、蔣琬儀,2022:《智能化轉(zhuǎn)型何以激發(fā)企業(yè)創(chuàng)新?——基于制造業(yè)勞動力多樣性的解釋》,《改革》第9期。
[9] 方福前、田鴿,2021:《數(shù)字經(jīng)濟促進了包容性增長嗎——基于“寬帶中國”的準自然實驗》,《學術界》第10期。
[10] 郭鳳鳴,2020:《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能緩解農(nóng)民工過度勞動嗎?》,《浙江學刊》第5期。
[11] 胡京,2020:《我國新業(yè)態(tài)從業(yè)人員職業(yè)傷害保障問題及其解決》,《廣東社會科學》第6期。
[12] 韓艷旗、郭志文,2022:《數(shù)字經(jīng)濟賦能家庭創(chuàng)業(yè):理論機制與微觀證據(jù)——基于CFPS2018的實證分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
[13] 林龍飛、祝仲坤,2022:《“穩(wěn)就業(yè)”還是“毀就業(yè)”?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民工高質(zhì)量就業(yè)的影響》,《南方經(jīng)濟》第12期。
[14] 劉軍、楊淵鋆、張三峰,2020:《中國數(shù)字經(jīng)濟測度與驅(qū)動因素研究》,《上海經(jīng)濟研究》第6期。
[15] 孟祺,2021:《數(shù)字經(jīng)濟與高質(zhì)量就業(yè):理論與實證》,《社會科學》第2期。
[16] 彭麗娜、徐家鵬、姜志德等,2023:《數(shù)字經(jīng)濟對農(nóng)村流動人口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人口與發(fā)展》第4期。
[17] 戚聿東、丁述磊、劉翠花,2021:《數(shù)字經(jīng)濟時代新職業(yè)發(fā)展與新型勞動關系的構建》,《改革》第9期。
[18] 戚聿東、劉翠花,2021:《數(shù)字經(jīng)濟背景下流動人口工時健康差異問題研究》,《中國人口科學》第1期。
[19] 戚聿東、劉翠花、丁述磊,2020:《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就業(yè)結構優(yōu)化與就業(yè)質(zhì)量提升》,《經(jīng)濟學動態(tài)》第11期。
[20] 宋林、何洋,2020:《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中國農(nóng)村勞動力就業(yè)選擇的影響》,《中國人口科學》第3期。
[21] 孫繼國、柴子涵,2023:《數(shù)字普惠金融對地區(qū)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宏觀質(zhì)量研究》第4期。
[22] 孫文遠、周寒,2020:《環(huán)境規(guī)制對就業(yè)結構的影響——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的實證分析》,《人口與經(jīng)濟》第3期。
[23] 王若男、張廣勝,2023:《數(shù)字經(jīng)濟與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就業(yè)質(zhì)量:促進或抑制》,《農(nóng)業(yè)技術經(jīng)濟》第2期。
[24] 邢敏慧、張航,2020:《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農(nóng)村勞動力就業(yè)的影響——基于CFPS2018數(shù)據(jù)的實證分析》,《調(diào)研世界》第2期。
[25] 楊建芳、龔六堂、張慶華,2006:《人力資本形成及其對經(jīng)濟增長的影響——一個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內(nèi)生增長模型及其檢驗》,《管理世界》第5期。
[26] 楊政怡、楊進,2021:《社會資本與新生代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研究——基于人情資源和信息資源的視角》,《青年研究》第2期。
[27] 余長林,2006:《人力資本投資結構及其經(jīng)濟增長效應——基于擴展MRW模型的內(nèi)生增長理論與實證研究》,《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經(jīng)濟研究》第12期。
[28] 張廣勝、王若男,2023:《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何以賦能農(nóng)民工高質(zhì)量就業(yè)》,《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第1期。
[29] 張笑寒、李金萍,2022:《社會交往內(nèi)卷化、數(shù)字經(jīng)濟與進城農(nóng)民工創(chuàng)業(yè)》,《南京審計大學學報》第4期。
[30] 趙建國、任冠宇、王凈凈,2023:《數(shù)字化嵌入對農(nóng)民工就業(yè)質(zhì)量的影響及規(guī)律研究》,《財經(jīng)問題研究》第5期。
[31] 趙濤、張智、梁上坤,2020:《數(shù)字經(jīng)濟、創(chuàng)業(yè)活躍度與高質(zhì)量發(fā)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jīng)驗證據(jù)》,《管理世界》第10期。
[32] 朱統(tǒng)、馬國旺,2022:《數(shù)字技術、人力資本與雇員過勞——基于實際工作時間和工作評價的研究視角》,《山西財經(jīng)大學學報》第8期。
[33] Acemoglu, D. and Restrepo, P., 2018,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6): 1488-1542.
[34] Bourdieu, P., 1986.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Greenwood Press.
[35]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L. Erlbaum Associates.
[36] Erhel, C., Guergoat-Larivière M. and Leschke, J., et al., 2014, Trends in Job Quality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for the EU, HAL SHS.
[37]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38] Kotz, D. M., 2015,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9] Lindley, D. V. and Smith, A. F. M., 1972, Bayes Estimates for the Linear Model,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 (Methodological), 34(1): 1-18.
[40] Raudenbush, S. W. and Bryk, A. S., 199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41] Tapscott, D. (ed.), 1995,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42] Wu, B. and Yang, W., 2022,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Chinas Employment Structure,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49: 103047.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Opportunities and Dilemma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Based on CFPS 2018 Data
Xu Qingqing1, Wang Liyun2 and Jiang Xia1
(1.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2.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injected new energies into th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posed new dilemma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e HLM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ntrinsic mechanisms from a multilayered perspective, with an attempt to reveal the potential problems involv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optimizes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t the macro level and promotes the accumulation of weak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at the micro level, thu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income level and labor contract signing rat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in that some low-income migrant workers are unable to enjoy the “digital income dividend” and the “flexibility” of labor contracts. Th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working hours shows a bidirectional effect. Moreover, the new types of occupational positions and patterns of labor relations creat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contained obvious deficiencies in labor secur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bias towards groups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which will exacerbate inequalities within migrant workers.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re proposed.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責任編輯 王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