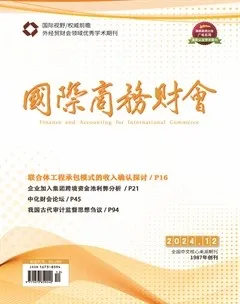聯合體工程承包模式的收入確認探討
【摘要】聯合體工程承包是工程行業采用的模式之一,其牽頭方收入如何確認是會計實務中關注的重點。文章首先介紹了聯合體工程承包模式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采取聯合體模式的動因。其次,根據聯合體成員的工作內容,分析了牽頭方與其他成員方各自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牽頭方不對其他成員履約義務承擔主要責任,但需要承擔連帶責任。在此基礎上,根據收入準則關于主要責任人與代理人的規定,結合具體案例,探討了聯合體牽頭方收入確認問題,牽頭方應當采用凈額法確認收入,并進一步對聯合體其他方代收代付款項及管理費收入、承擔連帶責任會計處理進行了探討。最后,列舉了實務中聯合體牽頭方收入確認的相關案例。
【關鍵詞】工程承包;聯合體;收入確認;連帶責任
【中圖分類號】F275;F235.3
一、聯合體工程承包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1999年版)》規定:“兩個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組成一個聯合體,以一個投標人的身份共同投標”,這是“聯合體”術語最早出現于相關法律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規定:“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結構復雜的建筑工程,可以由兩個以上的承包單位聯合共同承包”。從工程特性明確了聯合體工程承包的情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規定:“兩個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可以組成一個聯合體,以一個供應商的身份共同參加政府采購”。明確了政府工程可以采用聯合體模式建設,如PPP項目。聯合體工程承包投標,通常應當滿足下列條件:一是聯合體各方均應當具備承擔招標項目的相應能力;二是工程項目有資質要求的,聯合體各成員需要具備相應的資質,如果同性質工程(如建筑施工承包工程不同標段)由同一專業承包商組成聯合體,應當以資質較低的承包商確定資質等級;三是聯合體成員需要簽訂共同投標協議,中標后與發包方(業主)共同簽訂工程項目合同;四是涉及政府工程的,聯合體各方應當滿足政府采購活動相關條件。本文主要探討聯合體牽頭方相關責任及收入確認問題。
工程承包總分包模式下,發包方對承包商是“一對一”的垂直關系,即只與總承包商簽訂總承包合同,總承包商再與分包商簽訂分包合同,將部分工程分包給其他承包商,分包商可繼續往下分包,下一級承包商對上一級承包商負責。聯合體模式下,發包方對承包商是“一對多”的扁平關系,發包方直接與兩個或以上承包商簽訂承包合同,所有承包商直接對發包方負責。采用聯合體工程承包模式,主要基于以下動因:
(一)從發包方角度,確保工程質量。工程建設往往較為復雜,尤其是大型工程項目,既包括前期的勘察、設計,又包括與工程建設有關的設備、材料投入,還涉及建筑物或構筑物的施工活動。發包方選擇相關領域的專業承包商組成聯合體,可降低總分包模式下總承包商為獲取高收益違規分包、轉包給履約能力較差分包商的風險,有利于保證工程項目質量。此外,聯合體模式“一對多”的關系,減少了總分包模式的層層分包鏈條,可降低工程造價。
(二)從承包商角度,組建聯合體有利于增強競爭力,互補各自技術力量的不足,適應大型或復雜工程項目對專業技術高水平的要求,分散承包經營風險。同時,減少聯合體各方因支付履約保證而產生的資金負擔。
二、聯合體相關方權利義務與法律責任辨析
(一)法律法規關于聯合體相關方法律責任規定
聯合體不是一個法律民事主體,聯合體成員必須簽訂共同協議,列明各方需要承擔的工作和責任,強調“共同”與發包方簽訂合同,承擔連帶責任。合同的共同簽訂方式和連帶責任特征,決定了聯合體各方權利義務的設置需在責任連帶的前提下約定,聯合體各方權利義務與法律責任見表1。

此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礎設施項目工程總承包管理辦法》《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等規范性文件也對聯合體各方的權利和責任進行了規定,明確要求聯合體應當共同與發包方簽訂合同,并承擔連帶責任。
(二)聯合體牽頭方的法律責任
關于聯合體牽頭方的法定責任,相關法律法規規定較少。《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聯合體各方應當指定牽頭人,授權其代表所有聯合體成員負責投標和合同實施階段的主辦、協調工作,并應當向招標人提交由所有聯合體成員法定代表人簽署的授權書”;第四十五條規定:“聯合體投標的,應當以聯合體各方或者聯合體中牽頭人的名義提交投標保證金。以聯合體中牽頭人名義提交的投標保證金,對聯合體各成員具有約束力。” 目前,聯合體牽頭方是否承擔主要責任并無明確規定,需結合業務合同以及聯合體協議中的約定判斷。
作為牽頭方,除了履行自身約定的工程任務及承擔相應責任外,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既包括“對上”連帶責任,即對工程發包方承擔連帶責任,也包括“對下”連帶責任,即對聯合體其他成員因履行合同產生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該等連帶責任的性質,類似于擔保責任,屬于次要責任、補充責任,只有在聯合體其他方違約時承擔責任。
(三)聯合體模式與總分包模式法律責任區別
總分包模式是總承包商對工程項目進度、質量、安全等向業主承擔責任。對于分包給其他承包商的工程部分,其他承包商應當對總承包商負責,按照分包合同約定完成相應工作內容。站在業主角度,總承包商對分包商工程質量承擔當然責任,但分包商與業主并無法律責任關系,不承擔連帶責任。也就是說,總承包模式下,業主、總承包商、分包商三者之間的法律責任,是“直線型”的單向法律關系責任,而聯合體模式下,則是“網絡型”的互相法律責任關系,總承包商、分包商均需要對業主承擔責任,聯合體牽頭方與其他成員各方需要相互承擔連帶責任。
聯合體模式牽頭方與總分包模式的總承包商,雖然都需要對整個工程項目承擔連帶責任,但前者承擔的為擔保責任,是次要責任;后者承擔的為直接責任,是主要責任。實務中,聯合體牽頭方承擔連帶責任的合理性尚存在一定爭議,實際發生承擔連帶責任的情形較為少見。
(四)聯合體工程承包案例
某港口智能倉儲基礎設施配套EPC項目,發包方(建設單位)為甲公司,承包方為乙公司、丙公司組成的聯合體,乙公司為聯合體牽頭方,簽署三方協議《設計施工總承包合同》《聯合體協議書》(合同相關條款見表2)。

三、聯合體牽頭方收入確認
(一)總額法與凈額法
聯合體牽頭方是按總額法,還是凈額法確認收入,關鍵是判斷牽頭方是主要責任人還是代理人。《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規定:“企業在向客戶轉讓商品前能夠控制該商品的,該企業為主要責任人,應當按照已收或應收對價總額確認收入。企業在向客戶轉讓商品前能夠控制該商品的情形包括:企業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資產控制權后,再轉讓給客戶;企業能夠主導第三方代表本企業向客戶提供服務;企業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權后,通過提供重大的服務將該商品與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組合產出轉讓給客戶。”
以前述案例為例,逐條分析聯合體牽頭人乙公司在某港口智能倉儲基礎設施配套EPC項目承包中,就聯合體成員丙公司負責的部分工作是主要責任人,還是代理人角色進行分析:
1.在職責分工中,乙公司負責總體協調和工程設計、設備供貨,聯合體成員丙公司負責建筑安裝工程,各自向發包方交付工作成果并對發包方負責。乙公司不對建筑安裝工程承擔主要責任,僅承擔連帶責任。因此,乙公司并未承擔整個項目主要責任和整體風險,不屬于取得控制權后再轉讓的情形。
2.乙公司作為設計和設備供貨單位,與丙公司組成聯合體投標,以聯合體名義共同向客戶甲公司提供服務。因此,乙公司無法主導第三方代表本公司為客戶提供服務。
3.乙公司負責設計和設備供貨,丙公司負責施工,彼此相對獨立,各方工作成果直接交付給發包方,乙公司不需要將其工作與丙公司施工整合或組合后轉讓給客戶。
關于主要責任人與代理人的認定,《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還從公司是否承擔向客戶轉讓商品或提供服務的主要責任、在轉讓商品或提供服務之前是否承擔存貨或服務的風險、是否能夠決定商品或服務的交易價格,以及是否承擔款項收回的風險等方面,提供了進一步的實務操作指引。前述聯合體工程承包案例,乙公司僅對自身工作任務承擔主要責任,而不對整個工程項目承擔主要責任;聯合體各方自行負責采購、制造和交付存貨或勞務成果,并承擔相應的存貨風險;從收費情況看,乙公司收取設計費、設備費和管理費,該等費用僅構成工程項目總報價的59%,乙公司無法自主決定整個工程的報價。
綜上,乙公司雖然是聯合體工程承包牽頭方,但主要承擔設計、供貨和管理工作,與施工單位丙公司各自交付成果,未承擔項目全過程各環節的主要責任和交付前后主要風險,也未提供重大服務將產品整合成組合產品轉讓給客戶。因此,乙公司對聯合體其他成員承擔的工程任務,應為代理人角色,不應當確認為自身收入,即就工程項目整體而言采用凈額法確認收入,僅應將自身承擔的合同金額12 400萬元確認為收入。
仍以某港口智能倉儲基礎設施配套EPC項目為例,假設采用總分包工程承包模式,發包方將工程總包給乙公司,乙公司再將其中建安施工部分分包給丙公司,雖然乙公司實際仍僅負責設計、設備供貨和管理工作,但由于總分包模式下,乙公司需要就工程項目整體承擔主要責任和風險,且能夠自主決定分包價款,故屬于主要責任人,應當采用總額法確認收入,即確認收入20 900萬元。
(二)時段法與時點法與履約義務
新收入準則對采用時段法確認收入進行了嚴格限定,減少了原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確認收入的情形。以工程領域較為普遍的EPC(設計、施工、采購總承包)為例,既可能采用時段法,也可能采用時點法。因滿足“合格收款權”采用時段法的情形實務中較為少見,采用時段法主要看是否滿足“客戶能夠控制企業履約過程中在建的商品”這一條件,需要根據合同條款具體分析判斷。
對于聯合體模式履約義務,較總分包模式發生了變化。仍以EPC為例,總分包模式下,不論設計、施工、采購是分開簽訂合同,還是簽訂一攬子合同,均不滿足履約義務分拆條件,應當作為一項履約義務確認收入。而聯合體模式下,設計、施工、采購被分離,分別由聯合體成員各自履約,那么,是否可分拆為不同履約義務?前述案例中,聯合體牽頭方乙公司負責設計、采購,是作為兩項履約義務分別確認收入,還是合并為一項履約義務確認收入?筆者認為,由于乙公司設計、采購是可明確區分的商品或服務,滿足準則識別為單項履約義務的條件,宜作為兩項履約義務確認收入。但是,假設乙公司負責施工、采購工作,兩者需要經過重大整合才能轉讓給客戶,則應當作為一項履約義務確認收入。
(三)代收代付款項核算及管理費收入

聯合體合同中,牽頭方在從發包方收取的款項中,可能包含了代第三方收取的金額,該金額與牽頭方提供的服務無關,為其他聯合體成員對應的合同價款,不屬于牽頭方日常經營活動產生的經濟利益總流入,應當作為代收代付款項核算。前述案例中,工程款由牽頭方乙公司統一收取,再轉付給聯合體成員丙公司,系代收代付款項。在現金流量表列示時,按代收代付處理,通過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或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列示。
乙公司因履行牽頭人職責向丙公司收取的管理費200萬元,系代理人角色獲取的勞務報酬,應單獨確認為代理費收入。由于負責聯合體管理事務能夠與牽頭方從事的具體工程承包內容區別開來,應當識別為一項單獨的履約義務,不應將其收入并入牽頭方工程承包收入。
(四)承擔聯合體其他方違約責任會計處理
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聯合體成員可能因為項目核心人員變動,或資金發生困難,導致難以按照承包協議履行合同義務。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工程承包協議,聯合體牽頭方應當就聯合體成員違約行為給發包方造成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如墊付資金繼續工程建設,承擔聯合體成員尚未完成的工程任務,或承擔質量索賠等。類似于對外擔保責任,聯合體牽頭方承擔的連帶責任系或有事項,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3號——或有事項》第四條規定,在或有事項相關的義務同時滿足下列條件的,應當確認為預計負債:在該義務是企業承擔的現時義務;履行該義務很可能導致經濟利益流出企業;該義務的金額能夠可靠地計量。
當聯合體牽頭方可能承擔聯合體其他成員違約責任時,應當確認預計負債,其金額應當按照履行相關現時義務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計數進行初始計量,如為聯合體成員繼續履約墊付的資金、承擔其尚未完成工程預計需要發生的成本,以及承擔聯合體其他成員履行合同產生的債務等。需要注意的是,牽頭方承擔的聯合體其他方違約責任發生的支出,與當前或預期取得的合同無關,也不能增加公司未來用于履行合同義務的資源,不應作為合同履約成本確認為一項資產或計入營業成本,應當在發生時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可計入管理費用或營業外支出科目。
四、聯合體收入確認實務案例
實務中,采用聯合體工程承包模式的,通常按凈額法確認收入。如表3所述,以設計行業為例,如華藍集團(SZ301027)、深城交(SZ301091)、奧雅股份(SZ300949)等采用凈額法確認收入。
責編:夢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