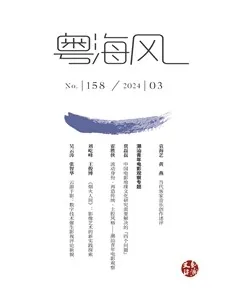舞臺之上的詩意演繹
摘要:話劇《索愛》的詩意演繹由劇本和舞臺兩部分共同完成,內容和形式有機地構成了話劇的詩意敘事。劇本追求詩意真實,蘊含詩性智慧,對生活進行了詩化提煉,奠定了話劇詩意敘事的基調。舞臺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從視覺和聽覺上對劇本的詩意指令進行了準確傳達與補充闡釋。話劇《索愛》改編自同名電影劇本,此次編創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對傳統詩性的強化,也是對當代戲劇藝術的探索。
關鍵詞:話劇《索愛》詩化現實主義 劇本指令 舞臺敘事 雙重意義
話劇《索愛》由張欣編劇、王筱頔導演,優秀的主創團隊保證了話劇的文學性和舞臺性。話劇講述了一個追求愛、學習愛的故事,討論了當代人如何塑造自己,它關注的是愛、尋找和成長等人類永恒的母題。當代人面臨的精神困境觸動了張欣,她滿懷感情又竭力理性地觀察生活,對現實生活進行了提煉,創作出具有詩化傾向的現實主義劇本。舞臺接受劇本的指令,綜合運用多種技術手段,充分再現了生活的詩意幻象,將觀眾帶入到詩意的情感與氛圍中。劇本的詩意真實與話劇表演的“詩核”本質顯然十分契合,文本與動作有機地生成了《索愛》的詩意敘事。話劇《索愛》既實踐了傳統戲劇美學,又進行了一次將電影改編為話劇的藝術實驗,它的詩意演繹對話劇藝術的當代探索極具啟發意義。
一、詩意的劇本
劇本是一劇之本。蘇珊·朗格認為,劇本提供指令,它對富于想象的思維所造成的混亂進行約束,并把所有人員——導演、演員、布景、燈光和服裝設計——都引向一個基本概念,一個準確無誤的“詩的核心”。[1] 編劇張欣追求“詩意真實”,劇本創作融合了西方理性精神和中國抒情寫意傳統,在描摹現實的基礎上注入情感的真誠與真實。《索愛》在現實反映、劇情結構、人物塑造等方面呈現出詩意抒情化傾向。詩意的劇本奠定了話劇詩意敘事的基調。
首先,《索愛》是一部蘊含詩性智慧的社會問題劇。
詩性智慧是維柯在《新科學》里首先提出的概念。維柯認為,“智慧是一種功能,它主宰我們為獲得構成人類的一切科學和藝術所必要的訓練”[2],而人類最初的智慧就是詩性智慧,“這些原始人沒有推理的能力,卻渾身是強旺的感覺力和想象力”,他們認識世界并非依靠“理性的抽象的玄學”,而是通過“感覺到的、想象出的玄學”,“這種玄學就是他們的詩,詩就是他們生而就有的一種功能(因為他們生而就有這些感官和想象力)”。[3]《索愛》的劇本創作起因于張欣對現實的困惑:“為什么成功催生出來的是抑郁,是無愛無性無感的清明世界。”[4] 所以,張欣在《索愛》里談論了諸多當下的社會問題,關注到了人們普遍面臨的人生困境,并尋找到解決人生困境的辦法——愛。愛來自人們的感覺力和想象力,它是一種詩性智慧,擁有強大的力量。
話劇開始,恐婚、心理問題、原生家庭創傷、離婚等社會問題便在主人公初英華的女友薛貝凝和母親初照的對話中接連出現。人物面臨的“無愛無性無感”的人生困境呈現在舞臺之上。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和人生困境帶給觀眾生活的真實感。話劇中,即將邁入婚姻殿堂的初英華產生結婚恐懼癥,無法進入兩性關系。對此,醫生給出的診斷結果是,長期缺失父愛給初英華造成了心理創傷,最終誘發了初英華的心理和生理障礙。于是,初照找到前夫陳泥,與陳泥“做生意”,試圖用錢買他對兒子初英華的愛與陪伴。就這樣,劇情圍繞著“索愛”展開,劇中人物都在“索愛”中獲得成長、得到救贖。張欣給出一種答案:物質并不能完全解決人類的“無愛無性無感”的生存困境,但愛所產生的動力和能量卻有可能破解這一人生難題。
當現代文明破壞了“詩”的神圣,鈍化了人的感覺力和想象力,愛將如何復現?張欣借劇中人物之口表達:“愛是一種能力,需要一輩子去學習。”劇作將阿德勒個體心理學的基本觀點貫穿始終,強調個體的能動性。愛仍存在人們生而就有的感官和想象力之中,只是過往的經歷弱化了對愛的感知。學習是讓愛重新煥發能量的辦法。劇中人物尋愛的經歷表達了一種積極追求,即過往不被愛的經歷并不能剝奪個體學習愛的能力。《索愛》始終洋溢著個體精神強大的理想情愫,它對人生困境破解路徑的思考蘊含著詩性智慧。
其次,《索愛》中“發現”與“突轉”情節結構的結合,既制造了戲劇性,也描摹了“詩意真實”。
田本相將曹禺的戲劇真實觀概括為“詩意真實”。所謂“詩意真實”,是在似乎脫離寫實的“狂肆的幻想”中,達到更高的真實,包含著理想情愫以及對現實生活中的詩意的捕捉、感悟、提煉和升華。[5]《索愛》的劇情結構精巧,編劇除了設置引人入勝的戲劇沖突,更是借助情節的“發現”與“突轉”制造強烈的戲劇性,創作了一部不那么現實的現實主義劇作。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闡釋:“發現”指從不知到知的轉變;“突轉”指行動的發展從一個方向轉至相反的方向,這種轉變必須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則;最佳的發現與突轉同時發生。[6] 《索愛》里將“發現”與“突轉”結合得最妙的情節要數陳泥的“發現愛”和“突然死”。起初,陳泥將陪伴兒子當成是一場生意,后來,陳泥不知不覺間對初英華真正萌發出父愛,他“發現”后主動返還“賣父愛”的錢。就在這“渣爹”醒悟的時刻,陳泥突遭車禍離世。陳泥的死看似是偶然的,但從戲劇節奏來看卻有著必然性——他的死加強了話劇的戲劇性,并推動新沖突的發生。話劇不著重渲染陳泥的死亡,觀眾還未沉浸于死亡帶來的哀痛,便立馬被新的沖突——劇中其他人物的行動——吸引。應該說,陳泥在劇中的功能,決定了他必死的命運。
陳泥初出場,編劇便借初照之口預言了他的死亡。初照提出用錢買陳泥對兒子的陪伴與愛,兩人有這樣一段對話:
陳泥:你這是打算付到什么時候啊?
初照:我可以付到你死!
此處情節與后來陳泥的死亡形成互文。確實如初照所言,她付錢付到了陳泥死亡為止。雖然止付的原因是陳泥的悔過自新。悔過、止付、死亡,這幾個情節被巧妙而又合理地編織到了一起。陳泥的出場和退場被戲劇化了,換句話說,他的命運被戲劇化了,他的死承擔著重要的戲劇使命。此外,陳泥的死還包含著個體生命必將走向死亡的母題——這雖然非《索愛》的核心論題,但卻是對現實的詩意呈現。總之,陳泥“發現愛”與“突然死”的情節本質上具有戲劇性,屬于“詩意真實”。
最后,張欣找到寫實與寫意的平衡點,使劇中人物既具有深切的真實感,又飽含抒情寫意特質。
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7] 劇中人物有著所屬時代的普遍共性,又有著所屬社會群體的特性,同時還擁有自身獨特的個性。張欣嚴肅的創作態度,使其能夠理性看待人與社會的關系。通過正確把握劇中人物與社會環境的關系,《索愛》的人物及其行動得以成立,話劇因此有了現實感和時代感。張欣明確表明《索愛》中的人物都是正面形象,這并不是說劇中人物是完美的道德楷模。就拿主人公初英華來說,他處理與薛貝凝的感情問題時采用的冷暴力方式并不恰當。但劇中人物的人格底色是明亮的。初英華雖不夠成熟,但他赤誠單純。劇中人物因為身上的缺點顯得鮮活,因為人格魅力而顯得動人,他們是立體的,富有生命力的。
編劇塑造話劇人物時,敘事性的行動刻畫,塑造出具有“詩意真實”的人物形象,而具有特定含義的名字則進一步確定了人物的形象和功能。張欣運用象征手法,給劇中人物以符合身份形象、話劇功能的名字。通過語言符號強化了人物抒情寫意的詩化特質。第一,人物名字突出表現人物個性特質。陳泥和初照的名字屬于第一類。“泥”字本身包含著多種釋義,能激發人們的多重聯想,也象征著“陳泥”不同階段的形象色彩和個性特質。“初照”一名帶有中性色彩。從社會層面看,初照的個性特質已經區別于芮塔·菲爾斯基所說的“史前女人”,她自主地,并成功地參與到現代化社會的文明進程中。從家庭角色看,性別決定家庭角色的規則在她身上消解了。第二,人物名字對人物的劇情功能進行了詩意體現。“陳可渡”一名光從字面上看,包含著渡人渡己之意,對劇情發展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戈”的象形字模擬的是古代的兵器,因此,“侯小戈”一名象征人物的工具性。侯小戈“劇情NPC”的屬性明顯。
二、詩意的舞臺
戲劇是以動作為形式的詩歌,屬于舞臺表演藝術。話劇的主要表現手段是語言和動作,而演員講話也是一種特殊的動作。舞臺為虛構的動作提供“天地”,舞臺美術設計將布景變為“場所”。[8] 舞臺的音效音樂具有說明性功能和語匯性功能,參與了話劇的敘事抒情。話劇《索愛》的舞臺表演、舞美語匯和音效音樂給予觀眾感官上的審美感受,構成話劇舞臺整體性的詩意敘事。
首先,演員的表演營造了話劇舞臺的詩意氛圍。
詩意的劇本指令影響著演員的舞臺動作。舞臺動作是舞臺表演的基礎,講臺詞又是重要的舞臺動作之一。話劇《索愛》的臺詞擇取了中西方經典詩作,通過演員的動作詮釋表現了劇作的題旨與情感。話劇臺詞選用了莎士比亞的抒情詩。話劇開幕,作為“劇情NPC”的侯小戈在舞臺上朗誦《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的第116首:
我絕不承認兩顆真心的結合會有任何障礙;
愛算不得真愛,
若是一看見人家改變便轉舵,
或者一看見人家轉身就離開。
決不!
愛是亙古長明的塔燈,它定睛望著風暴卻兀不為動;
愛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顆恒星,你可量它多高,
它所值卻無窮。
愛不受時光的播弄,
盡管紅顏和皓齒難免遭受時光的毒手;
愛并不因瞬息的改變而改變,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盡頭。
我這話若說錯,并被證明不確,
就算我沒寫詩,也沒人真愛過。
演員張祎心正確處理語言節奏,運用重音、停頓和氣息等舞臺語言表現技巧,伴隨著外放的肢體動作,充分地傳達了詩歌中勇敢、激昂、明亮的情緒,給予觀眾強烈的感官沖擊,將觀眾引入詩意的劇場氛圍中。《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116首關于愛的闡釋也點明了話劇“索愛”的題旨。
話劇臺詞還選用了陳毅所作的近體詩《青松》。《青松》中的“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兩句經由陳泥之口念出。陳泥的扮演者陳志榮結合表演情境,自然地將這兩句詩融于“講話”之中。這種“生活化”的表演方式,既有效地在臺詞中融入了人物感情,揭示陳泥的人物性格和命運,也避免了朗誦腔與生活化劇情之間產生割裂感。同時,《青松》描述的料峭情境構造起劇情發生發展的抒情空間,青松體現的頑強精神再次強化了話劇明亮的基調,賦予話劇詩意的藝術美感。
其次,《索愛》的舞臺美術設計以表現劇本精神意蘊為基礎,服務于演員及演出,偏重于寫意,打造了富有象征性的舞臺空間和服裝造型。
話劇需要以舞臺作為敘事空間。《索愛》具有象征意味的舞臺空間主要通過幾何圖形進行構建。舞臺設計簡約,兩個碩大的三角板作為舞臺布景道具,一黑一白,一大一小。利落的線條和冷冽的顏色烘托劇作的都市背景。黑色大三角板立于上場門處,白色小三角板立于舞臺中央。黑色大三角板固定不動,白色小三角板可以在舞臺平面上旋轉。隨著白色小三角板的轉動,兩個三角板會出現或平行或相交的幾何關系。白色小三角板具有功能性作用,除了可以提示時間、空間的轉換,還可以進行時空分層。更重要的是,白色小三角板能夠配合演員表演和劇情發展,對話劇的藝術表達進行闡釋補充,它的象征作用正在于此。
兩個三角板的幾何關系表征著人物關系。開幕時,黑白三角板呈現平行的狀態,象征著多組人物的平行關系——陳泥和初英華、初照和花峰秀、初英華和陳可渡,等等。而隨著演員轉動白色小三角板,黑白三角板的平行關系改變為相交關系,象征著人物相遇,故事開始。變化的三角板傳達出劇本的詩性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碰撞。
機動的布景道具拓展了舞臺空間的表現力。布景道具三角板全程參與舞臺表演,轉動變化的形態配合演員的情緒以及劇情的發展。轉動白色小三角板是演員的重要表演動作。這一動作具有四層含義。第一,三角板由演員親手轉動,象征著人具有塑造自身的主觀能動性。舞臺語言對劇作“我命由我”的主題思想和亞里士多德《詩學》里“人的行動決定命運”的詩學觀念進行回應。第二,轉動三角板的力度、幅度反映出人物的情緒,或激烈或徐緩的轉動動作體現人物不同的心理狀態。第三,變化的三角板表征著人物的成長變化。《索愛》中主要人物的成長軌跡是非常清晰的,人物從缺乏愛到獲得愛,從不會愛到學會愛。旋轉的三角板像時鐘的指針,刻錄著人物的成長變化。第四,轉動的三角板指向不同的方向,既指向人的不同側面,也寄寓著人生的無限可能性。《索愛》是一部社會現實問題劇,但它的情感基調明亮。白色三角板與黑色三角板形成對立,象征著人性的光明面和陰暗面,以及人生的理想與現實。轉動的白色三角板形成的舞臺語匯仿佛在補充闡釋:面對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只要找對解決的角度和方向,就能走出困境。
色彩是象征符號。《索愛》舞臺美術設計的色彩運用,既打造了詩意的舞臺空間,也渲染了話劇的抒情詩意氛圍。演員的舞臺服裝整體上用白色打底,再點綴鮮亮的色彩。舞臺布景道具的黑色三角板和白色三角板構成一幅巨大的、潔凈的畫布。隨著演員的動作和表演,彩色服裝宛若彩色顏料,點染于黑白色調的“畫布”之上,舞臺成為一幅幅躍動的水彩畫。明亮、活潑、清新的色彩點亮了黑白色調的舞臺,營造了劇作積極向上的詩意情調。
最后,適當使用音效音樂這一舞臺手段,增強了話劇的敘事效果,傳達了話劇的詩意情緒,營造出《索愛》的詩意氛圍。
《索愛》的音效音樂使用頻率是節制的,并未打破話劇“講話”為主的戲劇形式。音效運用上,除了敘景音效(陳泥車禍場景的剎車聲),便是簡潔的抒情音效——用來烘托劇情氛圍、營造意境美。話劇選擇具有音樂性的抒情音效烘托劇情,器樂蘊含的緊張感成為故事情境的補充說明,現代編曲技法帶來的都市感構建起話劇世界的詩意時空。音樂使用上,《索愛》的終幕表演與歌曲《有生之年》的演唱相結合,音樂語言產生表情作用和認識作用。歌曲《有生之年》旋律優美,歌詞溫暖,以“有生之年,愿你……”的唱詞結構表達美好祝愿。話劇中,初英華走出困境,與薛貝凝結婚生子。隨著劇中人輪流對新生兒唱出“有生之年,愿你……”《索愛》的故事迎來結局。歌曲《有生之年》的主題不僅與話劇的情感基調契合,還塑造出富有詩意的聽覺幻想。同時,劇情表演和歌曲演唱的有機結合,增強了劇作的寓意性——孩子代表的是希望,話劇指向處是美好的理想和未來。
三、詩化的意義
詩意演繹使《索愛》這部現實主義題材的社會問題劇具有明顯的詩化傾向。《索愛》的詩意演繹既源于對詩化傳統的追求,也是對當代戲劇藝術的探索,具有美學意義和現實意義。
首先,《索愛》具有濃烈的抒情性,體現了話劇詩本體的強化。
話劇的詩本體屬性是公論。但排斥話劇的詩本體地位的情況在現代“戰斗傳統”和“現實主義傳統”話劇、當代“實驗戲劇”和“探索戲劇”中不算少見。[9] 田本相認為,詩的弱化,即情的弱化,真情隱沒,虛情假設,就談不到“詩本體”,“詩本體”說到底是“情本體”。[10]《索愛》的劇作與舞臺都流露出極強的抒情性。編劇張欣對社會現實熱切關注,她注意到了看似非常小但又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人生話題,主創團隊對愛的遙想與渴望為話劇的創作提供了蓬勃的詩情。《索愛》優美的、積極的情感氛圍遠遠背離了當下流行的要么“爽文”要么“擺爛”的浮躁表達。在明亮的情感氛圍下,人生難題不再可怖,連死亡也不令人哀痛,因為有情,舞臺上的一切都成了詩。
當莎士比亞的詩作和簡約冷冽的舞臺布景相碰撞,遙遠的詩意在劇場里激蕩。舞臺美術設計配合話劇演出,賦予圖像和色彩人的情感,借用象征手法將其上升至美學層面。最終,話劇《索愛》的舞臺演出不僅帶給觀眾視覺和聽覺上的審美體驗,還給予觀眾心靈的感動與思想的啟迪。《索愛》從故事架構到舞臺技法都是現代的,劇作卻呈現出古典的詩意。《索愛》的美學風格彰顯了現代創作與詩本體的藝術融合是可行的。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現實需要和審美追求,但話劇的創新不能忽視詩本體的基本準則。縱觀古今中外的優秀劇作,創作手法、形式表現等或許各有不同,但對詩意的追求始終是共性。換言之,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對以“情”為根本的詩本體的堅守能激活話劇的藝術生命。
其次,話劇《索愛》的美學風格是對中國話劇詩化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
在西方新浪漫主義和中國傳統戲曲的影響下,“五四”時期許多現實主義或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話劇都具有詩化的特色。[11] 田本相從曹禺、夏衍等人的杰出現實主義劇作中提煉出“詩化現實主義”的美學概念,將中國話劇的戰斗傳統和藝術傳統概括為“詩化現實主義”。田本相認為,中國話劇的“詩化現實主義”是中國人的詩性智慧、詩化手段同西方現實主義戲劇的結合。詩化現實主義話劇熔鑄著時代亮色和民族藝術精神,表現的生活具有“詩意真實”,還特別注意戲劇意象的營造,追求真實的詩意、意境的創造和象征的運用。[12]
編劇張欣早年觀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保留劇目的體驗,培養了她關于話劇的藝術審美。導演王筱頔更是擁有豐富的導戲經驗,曾多次獲得各種榮譽,其中包括中國專業舞臺藝術領域最高獎“文華導演獎”。編劇、導演等優秀主創人員的藝術判斷力,共同呈現了詩意的《索愛》。《索愛》的落腳點是當下和現實,指向處是理想和未來。《索愛》的人物和故事都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然而又不只是對現實的復制粘貼,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詩意真實”。《索愛》擁有很強的目標感,始終懷抱著理想的情愫在殘酷的現實中尋找出路。話劇《索愛》注意象征手法的運用,劇作人物的名字、舞臺美術設計等被有意識地賦予象征意味。《索愛》的故事在詩意的感情里發生、生長、呈現,而詩意的情境又在劇本指令和舞臺表演中被創造。
最后,《索愛》以舞臺的方式呈現,是一次藝術的詩化實驗。
《索愛》的劇本原先是電影劇本,后來改編為話劇——編劇張欣和導演王筱頔試圖解決電影和戲劇創作的沖突。一般來說,戲劇沖突是戲劇的基本特征。雖然話劇和電影都講求戲劇沖突,但舞臺上的沖突不同于放映在銀幕上的運動中的沖突。話劇《索愛》的改編創作中,劇本的主旨和故事架構沒有改變,依然保留了“索愛”的主線,但詩化傾向更加明顯。
將話劇改編成電影的情況并不少見,并且歷來都有許多成功的嘗試。莎士比亞、莫里哀、易卜生、曹禺、老舍等劇作家的話劇作品都曾被改編成電影。就近幾年的華語電影而言,2015年改編自同名話劇的電影《夏洛特煩惱》叫好又叫座,掀起了一股話劇改編潮。相對來說,將電影或電影劇本改編為話劇,算是一種新鮮的藝術的詩化實驗。J.H. 勞遜曾對這種不平衡感到遺憾:“不幸的是,舞臺劇作家從電影中學習得很慢,而電影劇作家卻又過分倚賴戲劇,以至往往忽視他所從事的藝術形式的潛能。”[13]
電影不受舞臺空間的限制,觀眾觀看表演的角度取決于攝像機所能制作呈現的角度。同時,電影劇本可以有許多分段,電影的鏡頭語言可以消化掉這些分段,譬如,運用淡入和淡出進行場景的切換,通過控制攝像機鏡頭運動拍攝出近景、遠景、外景、特寫等畫面。反之,話劇的演出場所是一定范圍的舞臺空間和劇院,觀眾觀看表演的視角是固定的。話劇劇情主要通過演員的動作進行表現,話劇舞臺上的每一幕所呈現的故事都是要富有戲劇張力的。如果還機械地照搬電影劇本的分段,試圖在話劇舞臺上頻繁地切換場景顯然不符合話劇演出的實際。所以,重新組織舞臺上的戲劇沖突是話劇《索愛》的創作關鍵,也是其詩化的關鍵。
從話劇《索愛》的舞臺演出來看,每一幕都充滿了戲劇沖突,蘊含著巨大的戲劇張力。譬如,花峰秀在整場戲中出場不多,其中一場是她與女兒陳可渡的爭執,兩人的對話幾乎已經完全勾勒出了人物未來的“戲劇命運”。這場爭執表明了花峰秀價值觀的轉變,揭示了她與陳泥婚姻的破裂,暗示了她此后“棄女”尋找第二春的選擇。此外,導演創造性地利用布景道具設置故事場景的方式,也打破了舞臺的時空局限。舞臺上的小三角板切割了時間和空間,陳泥遭遇車禍死亡的場景與親人們得知陳泥死訊的場景并置,有效地避免了頻繁切換場景對話劇的詩意造成破壞,多個場景的舞臺共時呈現也更大限度地表現出戲劇張力和舞臺魅力。
張欣文學創作的啟蒙是話劇,所以她的小說故事性很強,電影劇本《索愛》同樣充滿戲劇性。電影劇本《索愛》的戲劇性為話劇的詩化改編提供了可能性。話劇結構和電影結構固然不同,但它們的內在組織有許多相似的地方。質言之,話劇和電影這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可以對同一個故事進行演繹,它們各自的獨特創作手段會帶來不同的藝術效果。導演王筱頔喜愛《索愛》的故事,也充分地理解了故事的主旨和戲劇架構。所以,導演王筱頔對劇作的準確把握,以及對戲劇沖突的巧妙設置,使《索愛》以舞臺的方式詩意呈現。《索愛》的劇本詩化特征明顯,而舞臺表演將劇本的詩意以一種更純粹、更理想化的方式進行了演繹。
結 語
《索愛》首先是作為電影劇本被創作出來,話劇的編創有一定的難度,但不失為一次令人期待的藝術實驗。劇本表現的生活經過了詩化提煉。觀眾若將之與現實對標,可能會產生諸多懷疑。譬如,原生家庭創傷是否能真正被治愈?毫無疑問的是,即使《索愛》里討論的社會問題有朝一日消散殆盡,但劇中被形容為“鬼”的“愛”,仍會以堅不可摧的形式存在著。《索愛》蘊含的理想情愫和詩性哲理從現實生活提煉而得,具有永恒的價值。話劇的成功編創既得益于劇本的詩意表達,又憑借獨特的舞臺手段增強了劇本的詩意主旨。話劇《索愛》的所有舞臺表演和舞美設計都圍繞著表現劇本主旨展開。以劇本為中心的創作原則不僅沒有淹沒話劇舞臺藝術的“個性”,還使舞臺上的演員、聲音、色彩和幾何圖形等擁有了超越日常生活的美,成為《索愛》這首“劇之詩”的構成因素之一。現代元素的融入豐富了話劇的舞臺敘事,舞臺語匯對電影劇本的轉化強化了話劇的詩意內涵,《索愛》的成功編創對當代話劇的藝術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注釋:
[1] [美]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傅志強、周發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頁。
[2] [意] 詹巴蒂斯塔·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頁。
[3] 同[2],第188—189頁。
[4] 張欣:《話劇〈索愛〉:直指心深深處》,微信公眾號“歲月無敵問張欣”,https://mp.weixin.qq.com/s/vpC6Fk8GV2wwvvxbAAWpdA,2024年1月6日。
[5] 田本相:《中國話劇的詩化傳統》,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20年版,第98—100頁。
[6] [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9頁。
[7] [德] 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頁。
[8] 同[1],第372—373頁。
[9] 朱棟霖:《論戲劇的詩本體》,《學術月刊》,1991年,第10期。
[10] 同[5],第31頁。
[11] 柯漢琳:《五四時期話劇的詩化現實主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
[12] 田本相:《論中國現代話劇的現實主義及其流變》,《文學評論》,1993年,第2期。
[13] [美] 約翰·霍華德·勞遜:《戲劇與電影的劇作理論與技巧》,邵牧君、齊宙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