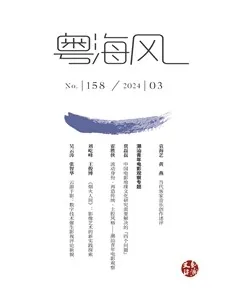流動身份?再造傳統?土腔風格
摘要:近年,南方電影不斷涌現,通過地方性知識生產為今天全球化語境下逐漸凸顯的現代性困局提供另類方案。而潮汕青年電影是其中一支值得關注的新生力量。它們通過對于“都市—城鎮”“陸地—海洋”之間流動主題的持續關注和書寫,試圖翻轉既定的“中心—邊緣”關系,重塑潮汕自身的主體性。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再造潮汕的家族主義傳統,使其在新的語境下煥發生命力,成為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同時,與內容主旨相一致,潮汕青年電影正在形成一種區別于主流商業電影的土腔風格和土腔制作模式。
關鍵詞:潮汕 青年電影 流動 家族主義 土腔
引言:望向“南方中的南方”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有關發展主義、經濟至上的現代性神話面臨崩解的危機,對于現代性的反思與重估成為世界范圍內的一股文化思潮,中國也不例外。表現在近期的電影、電視等大眾視覺媒介中,一是時間上的“重返九十年代”,一是空間上的“回到地方”。前者以電影《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以及根據“東北文藝復興三杰”作品改編的《平原上的摩西》《漫長的季節》等影視劇為代表,它們不約而同地通過懸疑的敘事范式,重揭改革開放初期社會體制轉型過程中被遮蔽的時代隱痛和創傷記憶;后者則將視野從“北上廣深”等一線國際都會移向小城,通過地方性知識的生產,曾經被忽視甚至被否定的前現代傳統重獲生機,從而試圖提供解決當下現代性危機的另類方案。
正是在這一波“回到地方”的電影熱潮中,“南方”成為眾多電影創作者的共同選擇,例如成都(《宇宙探索編輯部》)、重慶(《火鍋英雄》《少年的你》《刺殺小說家》)、杭州(《春江水暖》《郊區的鳥》《漫游》《她房間里的云》),以及貴州的凱里(《路邊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都勻(《無名之輩》)、獨山(《四個春天》)、貴安(《送我上青云》)等等。有關南方電影的討論也因此變得熱鬧。[2] 一個日漸形成的共識是,“南方”并不僅僅意味著具體的地理位置、空間物候或人文環境,更意味著溢出中心性的“北方”之外的異質性和邊緣性空間,并與之形成或補益、或對話、或超越的關系。
而在一眾南方電影中,嶺南/廣東電影是一個稍顯特別的存在。廣東是中國現代性發軔區域,也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擁有經濟實力雄厚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落,以及廣州、深圳這樣的一線都市,因此雖然位處南方卻具有一定的中心性/北方性。但是,在引人注目的珠江三角洲之外,粵西、粵東、粵北仍然存在著經濟上較為遲滯、文化上較為“無聲”的廣大區域,它們在與珠江三角洲的權力關系格局中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成為“南方中的南方”[3]。近年來,這些“南方中的南方”卻顯露新的文化萌芽并呈現勃興之勢,潮汕青年電影即是一例。它不僅突破和拓展了既往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廣東電影面貌,也與其他區域的南方電影形成呼應和對話,嘗試為面對和處理當下的現代性危機提供自己的在地化方案,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探討的案例。
所謂“潮汕”,是指粵東以汕頭、潮州、揭陽三個地級市為核心區域的,由講潮汕話的民系所創造的一個文化共同體。其邊緣性首先體現在語言文化分區上。廣東文化由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組成。按照柯漢林的觀點,廣府文化“無疑是嶺南文化的代表,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已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屬于“文化中心”,而潮汕文化與客家文化則屬于“文化邊區”。[4] 此外,潮汕地區在廣東的經濟體系中也處于相對落后和邊緣的位置。根據2022年廣東各地市的GDP統計數據,潮汕四市皆排名靠后,其中汕頭、揭陽、潮州的排名分別為11、13、19。[5]
雖然在文化和經濟上長期位處邊緣,但近年來潮汕青年文化卻有崛起之勢,屢有亮眼表現。具體來說,在文學方面,一批“80后”潮汕青年作家涌現,成為近年引起廣泛探討的“新南方寫作”[6] 的中堅力量。例如陳崇正的《半步村敘事》《碧河往事》、林培源的《小鎮生活指南》、陳楸帆的《荒潮》《人生算法》、陳再見的《回縣城》《天橋》《魚生》等,都以故鄉潮汕為原型,通過現實書寫、歷史鉤沉、科幻想象等不同形式,塑造了紛繁多元的潮汕文學世界。在音樂方面,因2020年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2》進入公眾視野的“五條人”樂隊引起了熱烈討論,其音樂中反復吟詠的“城市不像城市,農村不像農村”的海豐縣城也隨之浮出歷史地表。[7] 需要說明的是,“五條人”故鄉海豐所在的汕尾市并不隸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潮汕地區,但是由于汕尾與潮汕存在地域上的臨近性和方言上的交叉性,“五條人”的爆紅客觀上推動了潮汕文化的大眾普及。與“五條人”同時期成立,觀照潮汕現實并使用潮汕方言演唱的青年獨立樂隊,還有“六甲番”“玩具船長”“雷猴樂隊”“一指團體”等。而在電影方面,一批“80后”“90后”青年導演開始集體亮相,其創作兼有短片與長片,既取得不錯的商業票房成績,也獲得專業影展的藝術肯定。對此下文將進行詳述。有意思的是,潮汕文學、音樂、電影的發展并非“各自為政”,而是頗多互文與勾連之處。例如在潮汕青年文學中反復出現的“離鄉—返鄉”敘事和潰敗、衰落的小鎮風貌,在“五條人”音樂和潮汕青年電影中也同樣可以看到。而“五條人”和“玩具船長”的音樂也作為配樂和插曲,分別出現在潮汕青年電影《之后的一周》和《爸,我一定行的》之中。可以說,潮汕青年文學、音樂與電影之間的互動聯結,共同生成了獨特的潮汕青年文化生態。但限于筆力和篇幅,本文將僅僅聚焦于近年的潮汕青年電影,嘗試分析其發展原因和具體表現,探討其在南方電影譜系中的價值與意義。
一、潮汕青年電影的興起及其原因
綜合來看,推動近年潮汕青年電影發展的創作力量大概來自三個方面。
首先是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影視制作相關專業的在校學生及畢業生,他們的學生作品、畢業設計和藝術創作大多通過參與地方性、全國性以至國際性的藝術影展得到放映渠道,甚至以此獲得繼續創作的資金扶持。這是促進潮汕青年電影發展的主要生力軍。部分青年導演已有長片作品,例如蔡杰的《人海同游》(2023),陸曉浩的《之后的一周》(2022),藍燦昭的《女德》(2021)、《動物世界》(2018)和《狗》(2015),陳堅杭的《潮州熱》(2015),吳博平的《捂著眼睛看紅光》(待上映)等。此外,已有短片作品的青年創作者還有黃剛、郭嘉琳、楊哲霖、陳柏麒、陳功銘、溫柏高、林齊穎、趙八斗、鄭康、林旭茂、許哲涵、莊燦杰、陳冠丞、黃文禮等。
其次是非科班出身的業余創作者,在機緣巧合之下轉向潮汕電影行列。較早的典型案例,是2012年時任廣東新聞頻道法制欄目編劇的業青,跨界執導以潮汕為故事背景的青春題材影片《鮀·戀》。這部電影在低成本制作和無商業宣傳的情況下,在廣東各個高校的巡演展映中掀起熱潮,尤其獲得潮汕學子的熱情支持。影片于次年在騰訊視頻上線,獲得突破百萬次的點擊量,并一度成為新浪微博熱搜話題。在《鮀·戀》中擔任監制的藍鴻春,原本畢業于華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并長期擔任鳳凰衛視紀錄片編導,或許正是由此看到了潮汕本土觀眾的巨大市場潛力。2015年他辭職后自組廣告制作公司,并在2018年和2020年先后推出了院線電影《爸,我一定行的》和《帶你去見我媽》。《爸,我一定行的》以700萬元投資斬獲4700萬元票房,至今仍保持著廣東本土電影的最高票房紀錄。
第三是海外潮汕籍的電影導演,這部分的導演數量雖然不多,卻構成潮汕電影的一道異色。潮汕地區作為廣東著名的僑鄉,自明清之際就不斷有人“下南洋”并分散至世界各地,形成規模龐大的海外潮人社群。近年亮相國際的不少青年導演,如陳哲藝(新加坡)、楊毅恒(新加坡)、張吉安(馬來西亞)、歐詩偉(馬來西亞)、杜來順(法國)等,都具有潮汕的祖籍背景。他們中亦有部分人將視野朝向遙遠的故土,拍攝潮汕題材影片。例如法國動畫導演杜來順的近作《陳小姐的森林》(2023),就是以其父輩從潮汕“過番”到柬埔寨的經歷為原型而創作的潮汕家族史故事。影片從籌資到放映都獲得了法國青年潮州人協會的支持,眾多潮汕移民參與眾籌,影片的配音亦由移居法國的潮汕素人完成,體現了潮汕群體極強的文化凝聚力和身份認同感。
綜上來看,近年潮汕青年電影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是多方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結果。高校影視藝術專業教育的深耕與人才培植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潮汕本地而言,汕頭大學2003年成立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2007年新傳學院設立融合媒體實驗室,并聘請海外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業界人士擔任導師。陳堅航、溫仕培、陳功銘等都是在汕頭大學完成本科學習后進入電影業界或繼續專業深造。而近年也有不少潮汕青年選擇在廣東(如深圳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北京(如北京電影學院、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戲劇學院等)、港澳臺地區(如香港浸會大學、臺灣藝術大學等)和海外(如美國紐約大學、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等)的高等學府接受影視、傳播、藝術類專業教育,為潮汕青年電影發展儲備了潛在人才。
第二個重要因素在于,近年蓬勃發展的各類藝術影展為潮汕青年導演提供了學習、展示、聯結的平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FIRST青年影展等具有全國和國際知名度的影展組織,以“觀潮影展”為代表的潮汕地方性青年影展十分活躍,在潮汕青年電影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觀潮影展”創辦于2016年,是由一群潮汕青年電影人策劃舉辦的本土影展,也是目前潮汕地區規模最大的影展。“觀潮影展”在發掘和幫助有潛質的青年影人方面做出持續努力,不少青年導演如蔡杰、陸曉浩、藍燦昭、溫仕培等在其創作生涯之初就參與到“觀潮影展”,而后陸續在國內外各大影展和電影業界嶄露頭角。除了組織展映,“觀潮影展”更將觸角延伸至學術論壇、主題展覽、駐地創作,積極凝練和生產有關潮汕電影的文化論述和學術話語,試圖在中國乃至世界電影版圖中錨定潮汕電影的獨特位置,成為推動和形塑潮汕青年電影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潮汕社群強烈的身份認同和互助意識為潮汕青年電影的投資、制作、放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上述藍鴻春和杜來順導演的創作案例已經充分顯示,基于本土情懷的投資和票房支持,是其能夠抵御商業風險并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這在其他區域的本土電影生產中,極少看到類似的例子,也因此構成潮汕青年電影發展的獨特優勢。當然,正如一枚硬幣的正反面,這也同時使得部分潮汕電影招致消費本土情懷的營銷非議,同時面臨突破本土觀眾圈層、獲得更大受眾群體的困境。如何權衡與取舍其中利弊是未來潮汕電影仍需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流動中的身份協商
隨著潮汕青年電影的興起和發展,其在內容主旨和形式風格上的共通之處逐漸開始明晰。最為顯見的是,這些電影文本中普遍存在著“流動”的主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潮汕地區在當下和歷史上都是人口流動性很強的區域。民間俗語“本土一個潮汕,國內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就是對其流動性特征的高度提煉。就當下的現實語境而言,隨著改革開放之后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快速崛起,以及潮汕地區的相對滯后,發展的不平衡導致“虹吸效應”出現,潮汕地區的人口長期外流珠江三角洲地區。根據一項2006—2015的統計數據顯示,揭陽、汕頭的人口減幅都在30%以上,是廣東各地市中人口外流較為嚴重的區域。[8] 如此的現實境況反映到電影文本中,就體現為“離鄉—返鄉”流動敘事的反復出現。但倘若仔細探究,可以發現在這一流動敘事內部存在著變遷和差異。
我們將2012年業青執導的《鮀·戀》與該片監制藍鴻春后來執導的《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作為有趣的對讀文本,來觀察其歷時性的主題變遷。《鮀·戀》講述了一個汕頭青年和一個外省女孩在廣州相愛,卻受困于家鄉傳統思想而被迫回歸汕頭、放棄愛情的故事。不難看出,廣州是主人公向往的、美好的“外面的世界”,汕頭卻是禁錮主人公的樊籠,廣州與汕頭之間存在著“中心—邊緣”“現代—保守”“向往—否定”的二元對立關系。而到了《爸,我一定行的》和《帶你去見我媽》,“深圳—汕頭”的二元空間并置雖然仍在,但影片對于汕頭的價值取態卻發生極大逆轉。汕頭固然還存在著排外、保守等值得商榷的問題,但已經不再是阻礙主人公自由意志的否定性力量,更不再是與一線都市拉扯、互搏的對峙性存在。恰恰相反,汕頭所持守的小城鎮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補救了都市生活的缺失與弊病,使主人公重獲心靈慰藉與歸屬。例如《爸,我一定行的》中的汕頭青年369在深圳創業成為“網紅”,在浮躁的流量世界逐漸遭遇價值迷失。在家鄉的父親所堅持的誠信經營的傳統理念最終幫助369走出迷津并在深圳成功立足。在《帶你去見我媽》中,“潮汕仔—外省女”的愛情模式設定與《鮀·戀》十分相似,但不同之處在于,汕頭密切的家庭溫情、家族聯結和社群情誼對主人公而言既是束縛,也同時是在外孤獨漂泊中的重要情感支援。從《鮀·戀》到《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的主題變遷,我們看到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以及現代都市問題的逐漸凸顯,“都市—城鎮”之間“中心—邊緣”的權力位階發生某種翻轉,小城鎮中曾經被否定和忽視的價值系統和生活方式重新獲得一定接受和認可,從而顯現了一種“去中心化”的文化趨勢。
這種“去中心化”的趨勢在陸曉浩的《之后的一周》中同樣有所彰顯,但其背后的文化邏輯又與《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存在很大差別。《之后的一周》中,在廣州打工的女孩漫如回到故鄉汕頭見好朋友燕婷,而燕婷正計劃輟學跟隨漫如去廣州,影片就圍繞著兩人動身前在汕頭的一周漫游生活展開。片中出現了豐富的“小鎮青年”群像,他們呈現了多樣的流動軌跡和生命狀態:有的正準備去往廣州并懷揣向往,有的已經在廣州打工卻逐漸感到困頓,有的浪蕩在汕頭街巷無法離開,有的在外打工后選擇回歸汕頭生活。與《爸,我一定行的》和《帶你去見我媽》相似,廣州及其所代表的現代都市生活在影片中被一定程度“祛魅”,不再是神往的中心與彼岸。但與之不同的是,汕頭并沒有因此成為主人公心之所屬和安身立命的所在。城鎮里凋敝、潰敗的生存景象,以及重男輕女等傳統積習的留存,使主人公極欲逃離。因此,兩位女主人公在街頭巷尾、渡口碼頭的終日漫游,傳遞出一種非常復雜的況味:一方面,這是從庸常的日常生活中短暫的抽離,在夾縫時間中借由投身大自然獲得片刻的輕盈和快慰;另一方面,這漫游本身也正如“小鎮青年”命運的隱喻——看似可以自由流動,事實上卻無以為家。如果說《爸,我一定行的》和《帶你去見我媽》是在都市與城鎮之間友好協商并終得圓滿的成功故事,那么《之后的一周》則在左右圍閉的困境中感到悵惘與失落。《之后的一周》與之形成這樣的差異,可能源于導演敏銳的女性意識和個人的價值判斷,也體現了非商業電影與商業電影不同的敘事范式和文化取向。
《之后的一周》中流連于不同渡口的散點式漫游,以及對“廣州—汕頭”關系的“去中心化”處理,某種程度上暗合了近年興起的海洋論述。法國學者蘭尼·湯普森(Lanny Thompson)以加勒比海島嶼為研究對象,提出“群島化邏輯”(Archipe-logic)[9] 的概念,即以一種去陸地中心主義的思維,重新思考和搭建海洋空間的交叉網絡。在聚焦邊緣海洋空間的同時,《之后的一周》又規避了將其“再中心化”的傾向。影片通過“離鄉—返鄉—再離鄉—再返鄉”的持續循環模式,在二元結構之間反復游移,從而越出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這種審慎的思辨方式,幽微體現出流動性的海洋意識。正如巴斯威特(Barbadian Kamau Brathwaite)的“潮汐辯證”(tidalectics)所指出的,海洋潮流在陸地與海洋之間往復循環、持續不斷,強調時間的循環而非線性前進,從而動搖了以陸地為基礎的線性、二元論述框架。[10]
從這個意義上說,《之后的一周》曲折地體現了潮汕地區的“海洋性”文化特征。[11] 而更為直觀地彰顯潮汕海洋屬性的,則是“流動”主題影片的另一支脈——它們聚焦潮汕歷史上的海洋互動與離散身份。潮汕地區處于海上絲綢之路中繼站的重要位置。明清時期,潮汕的漳林港就是粵東沿海交通要沖,外海可達東南亞諸島,大量潮汕人從這里搭乘紅頭船“下南洋”。清末汕頭開埠之后,潮汕地區的海上貿易活動更為活躍。民國時期,潮汕又經歷三次大規模海外移民潮。[12] 據統計,現有潮汕籍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臺同胞約1500萬,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70%以上集中在東南亞。[13] 但是,潮汕地區悠久的海洋流動史與龐大的海外移民群體,卻長期在中國影像中處于缺席的狀態,這未嘗不是陸地中心主義思維的一種體現。直至近年,在潮汕青年電影中才萌發了一些新跡象和新突破。
在這類影片中,杜來順的《陳小姐的森林》和陳堅杭、陳柏麒聯合執導的《Dear Chang Lin》(2021)恰可形成微妙的對話,體現了處理潮汕人離散身份的不同視角和策略。如上所述,杜來順的父輩從潮汕“過番”到柬埔寨,之后又輾轉移民到法國。《陳小姐的森林》就是以此為原型,講述了一個潮汕家庭從清末到千禧年后橫跨六代人的歷史。在一百余年的光景中,這個潮汕家庭不斷與柬埔寨發生各種聯系,有時是貿易往來,有時則是“下南洋”謀生求存。影片隱晦地傳遞了一種從海洋而非陸地的角度重思潮汕的位置,及其在“南海世界共同體”[14] 中的作用的努力。同時,正是由于不斷有人離開故鄉、奔赴海外,這個潮汕本土家庭成為維系血脈、存續傳統、生生不息的“根”的象征。這個“根”的象征特別集中地體現在影片中的家庭空間里。雖然時移事遷,家庭成員也不斷迭代,但是家庭中的生活習慣(如吃飯、飲茶)以及日常器物(如衣柜、手串、盆栽)卻代代傳承,延續至今。導演似乎想要表達,即便潮汕群體不斷離散,但仍有穩固的家園和原初的身份根植在本土。
《Dear Chang Lin》流露了與之相似的鄉愁,但是對于穩固的家園和原初的身份是否依然存在,態度卻是遲疑的。貫穿影片的是同為潮汕后裔的一個德國女子和一個深圳男人由于尋找一處潮汕老宅而發生的書信往來。但正如片名所示,影片其實是寫給漳林的一封家信或情書。漳林港作為明清以來幾代潮汕人離家出海的起始地,已經成為潮汕離散族群的家園象征。然而,兩人找尋的行動卻是無果的。加之影片最后,導演的個人主體現身,坦陳因為潮汕老建筑“人去樓空”而導致自己陷入調研困境,以及影片中一個猶如導演分身的神秘女子不斷出現的尋覓身影,都在顯示經過歷史風煙與代際離散之后,試圖尋找原初身份是困難重重的。由此看來,影片選擇“書信體”的結構還帶有另一層深意:書信本身就同時意味著連結與分離、在場與缺席,正與潮汕離散群體糾葛的懷鄉情緒和身份處境吻合。
潮汕青年導演在“流動”主題的影像表達中,普遍彰顯了一種試圖從邊緣處翻轉既定的權力結構,進而形塑潮汕主體性的努力。這在現實題材影片中體現為對“都市—城鎮”關系的“去中心化”處理,而在歷史題材影片中則表現為對“陸地—海洋”關系的調整和重置。值得肯定的是,這種強調和爭取并沒有走向一種本質主義的論述,而是在各抒己見的多元話語場域中保持了探討的開放性。
三、再造“家族主義”的傳統
正是基于上述建構潮汕主體性的內在驅力,如何重思、重估、重塑潮汕自身的傳統就成為潮汕青年電影的一個重要議題。而在潮汕文化傳統中,“家族主義”是關鍵性的組成部分。有關潮汕地區家族主義傳統的探討,可以追溯到1925年美國社會學家葛學溥的《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村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葛學溥通過對一個潮州鄉村的社會學調查,提出了核心概念“家族主義”(Familism)。“他認為家族主義是一種社會制度,所有的行為、標準、思想、觀念都產生于或圍繞著基于血緣聚居團體利益的社會制度。家族是所有價值判斷的基礎和標準。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務、行為,都會被采納、推行;而反之,就會被視為禁忌,加以修正和限制。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會控制、宗教信仰、親屬制度都是圍繞家族主義這一核心的。”[15] 而人類學家周大鳴通過對鳳凰村的追蹤研究,指出家族主義至今仍然頑強地存在于潮汕地區。[16]
家族主義對于血緣、宗族、地緣關系的強調,以及與之相關的復雜的節慶、民俗、宗教儀式,長期被視為潮汕地區保守、落后、迷信的表現。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中,家族主義傳統有沒有可能被重新再造,生長出幫助人們應對當下困境的新的價值?從潮汕青年電影的創作實踐來看,它們提供了兩條不同的路徑。其一,不將家族主義視為鐵板一塊的、具有本質主義意涵的概念,而是將之置于復雜的文化場域,還原其內在的多義性,進而從中提煉可以為今所用的有益成分。上文提及的《帶你去見我媽》即是一例。它既批評并試圖修正家族主義的排外性,同時也強調當人們在都市生活中越來越“原子化”,家族主義傳統中緊密的人際聯結和濃厚的人情味具有一定的療愈作用。陳堅杭的紀錄片《潮州熱》則是將潮汕地區的民俗儀式——“鬧熱”(又稱“營老爺”)置于具體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中,重新審視它的社會意義。在歷史上,“鬧熱”有利于離散潮人搭建互助網絡,并為本土民眾宣泄民間情感提供了渠道。而在今天,“鬧熱”仍然發揮著增強社會人際網絡的作用。特別有意思的是,影片還提到“鬧熱”民間信仰中對于神的敬畏,以及對于人類有限性的承認。這在某種程度上正與今天方興未艾的“后人類”思潮暗合,是對“鬧熱”傳統在當下語境中的價值的重新發掘。
但需要指出的是,《潮州熱》在試圖重寫“鬧熱”民俗儀式的當下意義時,有意無意間忽視了它的局限與問題。以科大衛為代表的人類學家已經指出,潮汕以至華南地區紛繁復雜的宗族儀式,自明清時代出現之始就是當地居民宣稱自己的入住權和社會政治地位,以排斥、區分、涵化其他群體的手段。[17] 而這種排他性顯然仍是今天潮汕宗族儀式的題中應有之義。此外,影片將“鬧熱”視為區別于國家體系的民間系統的論述,也過于簡化了宗族儀式背后國家與地方之間的曖昧聯系。宗族信仰儀式中其實滲透著帝國隱喻和政治禮節(例如“營老爺”中的“老爺”就喻指官僚體系的權威)。本地居民通過將自己整合到國家政治體系以確認自身權力并排斥他者,國家與地方之間事實上存在著協同與融合的關系。僅列舉以上兩點,我們希望說明的是,在再造傳統的過程中,《潮州熱》存在著將地方傳統浪漫化的跡象,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自我批判的力度和審慎思辨的深度。而這種將地方傳統浪漫化的現象,不唯潮汕青年電影存在,也是近年很多“回到地方”的青年電影中共有的問題。
第二條路徑是在當下語境中對家族主義傳統做出新的自我書寫和闡釋,從而翻新了家族主義傳統的意涵。我們試舉吳博平的《勝嵐的秘密花園》(2015)和蔡杰的《歸省》(2014)兩部短片為例。《勝嵐的秘密花園》的片名和內容都指涉了潮汕地區的一項家庭儀式——“出花園”。它是潮汕家庭為虛歲年滿15歲的孩子舉辦的成人禮,意在提醒孩子即將擔起責任走向社會,同時也寄托了長輩的殷切期盼。但影片所聚焦的,卻是正值青春期的女主人公性意識的萌生和覺醒,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交織的憧憬、恐懼、失落、接納等復雜感受。換言之,《勝嵐的秘密花園》弱化甚至剝離了“出花園”儀式對人的家庭身份和社會身份的強調,反之“向內轉”地洞察人的身體性和心理性感知,從而將“出花園”原本的社群主義取向置換為更具現代性的個人主義意涵。
《歸省》也運用了相似的“向內轉”的策略。影片講述一個遠嫁日本的女孩回到故鄉看望父母和親人時產生的復雜情緒,以及父親的心境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微妙變化。歸省作為傳統習俗,所強調的是對父母長輩的尊敬以及對家庭、家族關系網絡的重視,但是影片所關切的卻是個體和家庭面對“故鄉—異域”的跨國流動所產生的內心波瀾。片名巧妙地借用了“省”字的多義性,它既指涉省親的社會習俗,也同時意指內心的省思和省察。對于遠嫁日本的女兒來說,原生家庭既是親近溫情的,又是隔膜疏離的。而對于父親來說,他從抗拒到逐漸接受女兒遠嫁的心理過程,既體現了家族主義的排外性,也同時表明傳統家庭具有接納他者、包容異文化的豐富彈性。特別是影片最后,父親為未出世的外孫取名“山中泉”,既使用了日本姓氏,也包孕了中國古典意象和傳統審美趣味,正是對于這種接納、融合他者的豐富彈性的具體呈現。《歸省》雖然將故事背景設定在廣州,但是影片對于家庭和家族主義的復雜性的細致表達,仍可看出導演潮汕文化背景的深刻影響。
“華南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人類學家蕭鳳霞曾經從《傳統的發明》一書獲得啟發,借以考察華南地區的民間儀式和宗族傳統如何在新的語境下被不斷再造,從而實現循環再用。[18] 而通過對于潮汕青年電影的觀察我們發現,再造傳統的工作在影像文本中也同樣存在。潮汕青年電影將家族主義傳統置于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下,置于與其他文化的互動和碰撞之中,從而不斷發掘其內在的張力與再造的可能。
四、土腔風格與土腔模式
潮汕青年電影對于“故鄉—異地”流動故事的不斷書寫,以及由此形成的對于故鄉主體性的不斷回身審視,是否使其生成某種獨特的電影美學風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嘗試性地借鑒和引用“土腔電影”的概念。“土腔電影”(Accented Cinema)由生于伊朗、任教于美國西北大學的哈米德·納菲斯(Hamid Naficy)提出,指的是由第三世界流動到第一世界的“一批以流亡、移民、離散、難民、族裔或跨國之名的導演們,在西方的社會形構、主流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夾縫中打造出一種新跨國電影、一種新全球在地化”[19] 的電影。而執教于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臺灣學者林松輝進一步延展了土腔電影的概念,他認為土腔電影不必局限于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等級結構,也可以包括亞洲內部之間的移動路徑。[20]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進一步,提出土腔電影也不需要僅限于國別之間的流徙,還可以指涉一個國家內部從欠發達的較邊緣區域向發達的中心區域的流動方式。那么,潮汕青年電影可以被包含在這個擴展后的土腔電影概念之下。而納菲斯對于土腔電影的論述亦可對我們觀察潮汕青年電影具有適用性和啟發性。
納菲斯將土腔電影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敞開式與封閉式的視覺風格;碎片、多語、書信體、自我反思,以及批判性并置的敘事結構;含混、雙重、越界、迷失的人物形象;關涉旅程、歷史、身份、移居的主題內容;焦慮、愉悅、懷舊、通感、邊緣化和政治化的情感結構;夾縫式和集體式的制作模式;以及導演個人的自傳色彩和影像標簽。”[21] 上述特征又可以劃分為土腔風格和土腔模式兩個面向,而潮汕青年電影都恰好與之契合。
就土腔風格而言,首先,潮汕青年電影中多見“離鄉—返鄉”的“行旅”主題和敘事模式。與之相關地,影片中經常出現摩托、渡輪、汽車、火車等交通工具,以及車站、渡口、旅館等過渡性空間。正如納菲斯所指出的,主人公的物理空間位移背后,其實隱含著對于身份的流動性、跨界性、去畛域化的思考。[22] 其次,潮汕青年電影大多流露出懷鄉的情感結構。這一方面體現在某些故鄉空間的高頻出現。例如自然風物往往象征穩定性、永恒性和可靠性,從而安撫主人公的鄉愁,[23] 又如家庭空間常常成為個人記憶的載體和懷舊情緒的容器[24]。另一方面,懷鄉情感的表現方式并不僅限于視覺,還借由通感、聯覺,全方位地喚起對于故鄉日常生活經驗的記憶。[25] 在潮汕青年電影中,吃飯場景和食物意象極其豐富(如《之后的一周》《帶你去見我媽》《陳小姐的森林》《歸省》等),正是通過聯合視覺、嗅覺與味覺來共同激發懷舊情感。第三,潮汕青年電影在以潮汕方言為主體的同時,時常雜糅粵語、普通話和英語,而這種多語共存的情形,通過人物對白、書信旁白、歌曲配樂、電影電視媒介等多元形式呈現出來。最后,潮汕青年電影帶有強烈的導演自傳色彩。這些青年導演大多離開潮汕,散居于廣州、深圳、香港和海外各地,與其影片人物的流動軌跡重合。而導演在自身流動中產生的個人體驗,也往往被投射于電影文本的肌理中。
有意思的是,潮汕青年電影的土腔風格與臺灣電影之間有著較強的相似性和關聯性。有的導演在電影中明顯借鑒臺灣電影的情節設置、場景配樂和美學風格,有的則在訪談中自覺明確地指出臺灣電影導演侯孝賢、魏德圣等對自己的深刻影響。[26] 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強聯系,除了因為潮汕與臺灣兩地同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和閩南語文化區而存在地理和人文上的親緣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臺灣電影是土腔電影的重要生產地。一方面,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臺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歷了快速的經濟騰飛和城市化進程,“都市—鄉土”之間的流動成為當時臺灣新電影的一個重要主題,并在此后的臺灣電影中不斷續寫和延展;另一方面,臺灣的殖民和后殖民歷史促使它在與中國大陸、日本的不斷互動交流中處理自己的主體身份問題。臺灣電影作為華語文化圈中土腔電影的先行者,令潮汕青年電影產生了跨越時空的共鳴,并成為后者學習與效法的對象。由此可見,在土腔電影的譜系內部存在著影響與共振的關系。
而所謂土腔模式,是指土腔電影導演大多游離于主流商業電影的制作體系之外,夾縫中求存。他們常常身兼導演、編劇、攝影等多重身份,以一種低成本的、集體手工作坊式的方法完成電影。納菲斯因此將土腔電影納入第三電影美學的譜系之中,認為它是區別于追求專業、完美、炫目的好萊塢商業電影的“不完美電影”,訴諸低成本、業余、粗糙的“貧窮美學”[27]。如果說在納菲斯的論述中,土腔模式的對照面是好萊塢商業電影制作成規,那么潮汕青年電影的對照面則是國內大制作、明星制、類型化的主流商業電影模式。具體來說,潮汕青年電影的土腔模式又可以細分為兩種。一種以《之后的一周》為代表,創作者自籌經費拍攝獨立電影,然后通過參與地方性、全國性、世界性的影展活動獲得傳播渠道,在商業電影體系之外找到生存空間;另一種則以《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為代表,雖是具有商業類型元素的院線電影,但能夠以較低成本在潮汕文化族群內部實現自產自銷,而無需參與到主流商業電影的運作模式之中。而無論是《之后的一周》還是《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都曾經得到“粗糙、業余”的負面評價,這種負面評價甚至被導演本人接受和認可。但事實上,潮汕青年電影的土腔模式,不僅使影片的美學品格與片中的人物和主題形成緊密的同構關系,也有利于在主流商業電影體系的夾縫處提供有關潮汕的多元文化話語。因此,我們希望借由土腔電影的概念,為這種無論在電影制作體系還是文化評價體系中都處于邊緣位置的電影模式賦權。
結 語
在今天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國南方電影版圖中,潮汕青年電影是一個既有共通性又有獨特性的存在。與其他地區的南方電影相似,潮汕青年電影將視野朝向邊緣處,試圖重塑地方的主體性。而其獨特之處首先在于,由于潮汕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及其與珠江三角洲這一“中心”的鄰近關系,潮汕青年電影往往更側重于表現“邊緣—中心”之間的復雜流動,從而有利于從更多元的角度、更深刻的層面發掘“邊緣—中心”之間的豐富張力,并由此形成獨特的美學風格。其次,重審與再造家族主義傳統是潮汕青年電影的一個重要議題,而家庭倫理觀以及以家庭為基礎生成的社群意識是中國(乃至東亞)最為重要且根深蒂固的傳統之一。因此潮汕青年電影在家族主義問題上所能探討的深度和闊度,具有相當普適的價值和意義。而從目前的成果來看,潮汕青年電影既進行了一些開創性的工作,也暴露了一定的局限和問題。
因此,潮汕青年電影有沒有可能通過地方性知識的生產為處理今天的現代性困境帶來獨特的方法論?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尚無法給出確定的答案。潮汕青年電影仍處于“剛出發,在路上”的狀態。目前的電影文本已經顯露出一定潛力和萌芽,而更多的青年創作者和作品正陸續走來。我們以問號作結,既是對潮汕青年電影當下未完成性的概括,也是對其未來可能性的期許。
本文系廣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電影理論與批評”(2024SFKC_060)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廣州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
注釋:
[1]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觀潮影展”主理人陳柏麒、陳功銘以及導演藍鴻春、蔡杰、陸曉浩的幫助,在此一并致謝。
[2] 霍勝俠:《南方影像:中國電影與城市空間》,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
[3] Shih Shu-mei:“Race and Relation:The Global Sixties in the South of the South”,Comparative Literature,2016(2).
[4] 柯漢林:《嶺南文化研究的三個問題》,《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5]《2022廣東各市GDP出爐:湛江反超中山,深圳排名第一,惠州增速第一》,網易,https://www.163.com/dy/article/HTS1TCFA055325G5.html,2023年2月18日。
[6]“新南方寫作”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提出,區別于以江浙滬江南地區為核心的傳統南方,“新南方”指涉的地理位置是中國的海南、廣西、廣東、香港、澳門,同時輻射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南洋”區域。詳見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7] 霍勝俠:《近期大眾文化中的廣東圖景——以〈隱秘的角落〉、“五條人”音樂、〈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為例》,《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8]《廣東十年人口變遷:誰人口流失過半?誰增長最為迅猛?》,21財經,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171115/herald/f8b9491d197c8ef7fd42b64fb8f107d9.html,2017年11月15日。
[9] Lanny Thompson:“Heuristic Geographies:Territories and Areas,Islands and Archipelagoes”,Archipelagic American Studies,eds. Brian Russel Roberts and Michelle Ann Stephens,Duke UP,2017,pp57-73.
[10] Barbadian Kamau Brathwaite,Contradictory Omen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in the Caribbean,Savacou Publications,1974.
[11] 鄭松輝:《近代潮汕海洋文化特征的形成與發展》,《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12] 何東霞、易順、李彬聯、郭維:《宗族制度、關系網絡與經濟發展——潮汕地區經濟落后的文化原因研究》,《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13]《華僑華人》,汕頭市人民政府網,https://www.shantou.gov.cn/cnst/yxst/gk/hqhr/index.html,2022年3月30日。
[14] 許紀霖:《農耕、游牧與海洋文明視野中的南北文化》,劉志偉:《廣州三重奏:認識中國“南方”的一個視角》,《知識分子論叢》,2018年,第1期。
[15] 周大鳴:《譯者序》,載丹尼爾·哈里森·葛學溥著,周大鳴譯《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村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16] 周大鳴、黃鋒:《家族主義的傳承與發展——紀念鳳凰村研究100周年》,《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17] David Faure: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8] 蕭鳳霞著,余國良編:《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19] 許維賢:《華語電影在后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67頁。
[20] Lim Song Hwee:“Speaking in Tongues:Ang Lee,Accented Cinema,Hollywood”,Theorizing World Cinema,eds. Lucia Nagib,Chris Perriam amp; Rajinder Dudrah,I.B.Tauris,2012,pp129-144.
[21] Hamid Naficy:An Accented Cinema,Exilic and Diasporic Filimmak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4.
[22] 同[21],p5.
[23] 同[21],p156.
[24] 同[21],p169.
[25] 同[21],p28.
[26] 導演藍鴻春在2023年7月17日與筆者的訪談中提到,臺灣電影導演魏德圣的《海角七號》對其創作產生影響。此外,蔡杰在多次媒體訪談中提及侯孝賢對于自己的重要影響,參看《廣州青年報》:《導演蔡杰:從小島影像到國際電影節》,https://www.gzyouthnews.org.cn/index/view/id/71,2015年3月15日。
[27] Hamid Naficy:An Accented Cinema,Exilic and Diasporic Filimmak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31.方言喜劇電影類型的本土化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