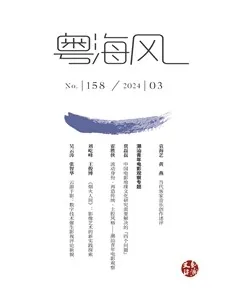《之后的一周》:漫游作為辯證性的現實書寫
摘要:潮汕青年導演陸曉浩的長片首作《之后的一周》在第十六屆FIRST青年電影節上展映并獲獎。影片聚焦潮汕地區的三個小鎮,既有看似沉重的地方現實觀察,又有輕盈閑散的“漫游”敘事,在“中心”與“邊緣”之間找到了巧妙的辯證。這種辯證得益于影片充滿活性的虛構方法論,以及在這種方法背后一種同樣在“私人”與“虛構”之間實現了微妙平衡的創作理念。在近年華語青年導演拍攝關于自己故鄉電影的熱潮中,充滿審慎與辯證的《之后的一周》提供了獨到且頗具借鑒意義的視角和觀念。
關鍵詞:潮汕地區 邊緣 辯證性 現實主義 虛構性
一部成本僅7萬元的潮汕電影《之后的一周》在2022年第十六屆FIRST青年電影節上亮相,并獲得“第一幀”評審團特別提及和“學者之選”最佳影片。該片是潮汕青年導演陸曉浩的長片首作,小團隊低成本的創作自然難以避免技術水準上的瑕疵,但影片仍然因這份“野生”而保存了難得的獨立性和辯證性。同樣是聚焦于潮汕地區地方性的呈現,橫向對比近期在主流院線上映的潮汕電影,如《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等,都是采取鄉土情結感召和強調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創作策略;《之后的一周》卻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切入這片地區的視角和觀念:以看似散漫飄逸的“漫游”敘事,直切地審視故鄉。但與此同時,影片對“地方”的批判并沒有導向對“中心”的向往,對地方性社會議題(如“重男輕女”現象)的討論也并沒有陷入偏激的二元論桎梏中,而“漫游”則成為調和極與極之間的辯證法。由此,本文試圖探究的便是這樣一種辯證法如何建構著整部影片的表達,以及這種創作方法反映出怎樣的創作觀念。在這重意義上,看似“業余”的《之后的一周》恰好能夠為近年卷入拍攝故鄉故事熱潮中的華語青年導演們,提供可借鑒的啟示。
一、“現實”與“漫游”的雙重時間
導演陸曉浩曾表示自己原本想將影片命名為《半島一周》[1]:將影片的三個主要故事發生地在地圖上連起來,會得到一個半島的形狀。有趣的是,“半島一周”的“一周”令人容易聯想成空間意義上的“一周”,即“環繞一圈”。從字面的更迭上我們可以辨認出這樣一個變化,片名由對空間的興趣轉換為對時間及其不確定性的描述——“一周”為什么是“之后的”,在什么“之后”?它仿佛位于某段時間的末尾,又像是另一段時間的開端,一個沒有來由的“之后”將電影的時間懸置在一種臨界、過渡、邊緣的狀態中。盡管這未必是導演所考慮到的,但它卻提供了一個進入這部年輕的、沒有歷史包袱的“潮汕電影”的抓手。
《之后的一周》講述了高三女孩林燕婷,在距離高考僅剩一個月的那天逃課去接一位早已輟學打工的好友黃漫如,隨后迅速被這位好友所“策反”,決定放棄無望的高考轉而追隨黃漫如在一周之后前往廣州打工。在這樣一段夾縫中的時間里,兩個女孩對自己從小所生活的這片地區展開了漫游。電影的主線故事(即“漫游”)肇始于一次時間上的變動,但這種時間上的變動并不是單純地在數字上由30天變為7天,而是整條時間軌道的變化,人物直接駛入了另一條時間線中。
在兩個女孩剛見面不久的對話中,逃課的林燕婷說:“我覺得那串數字特別搞笑,明明沒有人在為高考這件事努力,然后他們還弄得很緊張一樣。我覺得那串數字根本不是什么高考倒計時,應該是進廠倒計時、成為大專生倒計時。”影片在此處借人物之口指出了一個巨大的斷層,即中心性時間與欠發達地區學生實際生活的地方性時間之間的巨大撕裂。而兩位女主角所遭遇的便是由這兩重時間的錯位所導致的特殊境況。這兩重時間在現實之線性時間上形成了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而這種選擇又并不是積極意義上的個體的自主選擇,它的結果更多地導向一種無可奈何的被迫和妥協之舉。
影片中的角色并不具有掌控自己時間的主體性(此處特指女性角色,而關于其中的性別政治,筆者將在后文詳述),而是在另一種更高的秩序之下成為被迫流動的和被排擠于邊緣的,總是被無窮的期限推著走,沒有停留和喘息的余地。在陳柏麒對潮汕地區的觀察中,我們可以尋到人物處于這種邊緣境況的現實根基:“潮汕地區與其說是幾座城市或一個區域,不如說是一個過渡的空間。由于經濟的衰退和產業轉型緩慢而被迫在一個高速發展的大環境中長期處于過渡期……潮汕自古以來是一個帶有顯著港口氣質的區域……而生長于港口城市的人,便也習慣了某種‘港口心態’:一切都是流動的,暫時的,包括了人口、貨物和人際關系。”[2] 在此,如果我們要為影片片名作一番解讀的話,“之后的”,即是“邊緣的”“過渡的”,總是位于一重時間與另一重時間的裂隙和撕扯之中,被接踵而至的期限追趕著,無法停下運轉的步伐。“之后的一周”,正如鏡頭所對準的這片地區——“一座位于某一段時間的末端的城市”[3],是關于這些生長在邊緣的、位于某段時間末端的人們的一周。
不過,在兩位女主角身上,中心性時間與地方性時間的錯位僅僅是作為敘事的前提而存在,而影片敘事的展開,依靠的則是不同于這兩重現實時間的另一重時間——漫游的時間,也即片名中的這“一周”。通過將原本來自中心性時間的“高考倒計時”直接指認為地方性時間的“進廠倒計時”“成為大專生倒計時”的偽裝,女主角林燕婷得以獲得從其中脫身而出的決心,而這反而使她獲得了在另一重時間,即漫游的時間之中的自由。也正因為這個決定,她首先將打工歸來的好友黃漫如從短暫的有著明確期限的假期時間中解放出來,進入到漫游的時間中——不需要去完成任何事情,不需要為期限的臨近而做任何努力,這是一個可以暫且假裝自己擁有無限時間的一周。
“現實”的無始無終和接踵而至的種種期限,讓我們總是將時間描述為一條無情的直線,一股一去不復返的洪流,這種錯覺乍看上去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人們不假思索地遵循著“現實”的場面調度。但自柏格森以來,我們知道時間經驗之于我們當下從來不是線性的——對過去的追憶總是在瞬時到場,我們并不需要循著一條假想的時間“線”去慢慢回溯,“過去作為一個潛在的整體是現實事件得以現在發生的條件”[4]。在這個意義上,德勒茲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用“逃逸線”來指代一種新的生命進程,“一種在緩期之中的持存,一種無限的延期”[5],也就是說,一種中斷。
正如在影片中,主角放棄對未來期限的努力,轉而投入到對過去生活的地區所展開的漫游中一樣,“漫游”首先不是一個行動,而是行動的休止,它并不處于“時間之中的某個時刻,而是某種讓時間導向新的進路的東西”[6]。這種“漫游”帶來了有別于“現實”之線性時間的另一種時間經驗(下文詳述),而經由漫游的時間,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林燕婷也愈發清晰地意識到出走的意義。
影片在此區分出了兩種時間,即作為“現實”之線性的、期限的時間,和在休止中持存的、綿延的漫游時間。
二、“中心”與“邊緣”的辯證性
中心性時間與地方性時間在現實之線性時間上,形塑了一種“中心”與“邊緣”的二元結構,人們在大部分時候都只能在二者之間被迫選擇其一——正如打工女孩黃漫如一樣。那么,兩個女孩是如何逃逸出這個二元結構的呢?
影片開頭,兩個女孩碰面后先去了一家奶茶店,剛翻開飲品單,黃漫如便感嘆與廣州相比小鄉鎮的物價之便宜,但隨后又很快翻轉了對家鄉的態度,向店員抱怨旁邊客人手機聲音外放的行為,而“廣州就不一樣,廣州就明令禁止這種行為”,儼然是將這種現象與家鄉的某種落后捆綁在一起進行批評。接著,兩人談論到對未知未來的感嘆,由此,林燕婷作出了一周之后和黃漫如一起去廣州打工的決定。
在影片這樣一個前情交代性質的小段落里,我們其實看到了角色心理在“中心”與“邊緣”之間的迂回。與作為經濟中心的廣州相比,潮汕自然屬于邊緣,角色雖然一方面懷念故鄉的低消費生活,一方面又向往都市現代性的公共文明素養——而這又同時包含了兩層相反的態度,即一方面清楚都市的經濟發達帶來的高生活成本,一方面亦明白家鄉的欠發達往往又意味著民眾普遍素質的落后。
這種反復在影片接下來的情節發展中指向了角色關于“走出去”還是“留下來”的抉擇、“投靠中心”還是“留在邊緣”的抉擇,但她們并不是一邊倒地傾向于二元中的某一方,而是呈現出一種迂回而又保持開放的心態。在兩人開始為期一周的漫游途中,每度過一段輕松散漫的時光之后,影片都會向角色拋出關于這個抉擇的疑問和勸阻,黃漫如說:“廣州可沒有在這里輕松哦。”偶遇的外地學生劇組導演說:“這個年代沒有學歷是很難混的。”以前的老師也勸她也許可以找助學貸款,但林燕婷只說:“反正我也不想待在這兒了。”既非貪戀故鄉也非向往中心,而是抽離出二元之外,保持著自身在這短暫的一周中難得的主體性,由此,“漫游”才成為可能。正因為脫離了這種二元論,漫游者才得以以更加審慎的視角來觀察自己的故鄉,既非自上而下的憤世嫉俗,也非一廂情愿地投射自我感懷和鄉愁——這兩者都滑向將這片地區再度他者化和“邊緣”化的危險,因為它們都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一種平視與靜觀的態度。
正是這樣的視角和態度才令漫游者的時間從現實的線性中逃逸出來,將她們以及她們所歷經的旅途帶入到隨遇而安的綿延之中,電影從而也重新恢復了它自身和角色對日常的感知和好奇:將昔日埋頭苦讀的校園變成嬉戲的場所,把摩托車的車燈當作電影打光的光源,遠遠觀察偶然路過的一支聲勢浩大的送葬隊伍,攝影機在江邊等待一艘大船緩緩駛過江面,以及所有那些隨機抓取到的街景……而每一樣食物都有自己的特寫鏡頭。“漫游”以一種抽離于日常本身的視角,帶我們逃逸出現實無始無終的線性時間,制造出停頓和休止,并借此重新回望和關注那些我們原本身處其中的日常。對日常的解放首先發生在對身體的感知上,一個典型的段落是:女孩們在學校的房頂發現先前騷擾林燕婷的兩個男生正好在樓下,想要用手中的西瓜給對方一個教訓,但又不舍得浪費食物,于是兩人開始埋頭猛吃,這個動作的變化隨后很快演變成某種游戲性的比賽,兩人也因此而互相嘲笑對方的狼狽。在這個過程中,“吃西瓜”這個簡單的動作被不斷地打斷,又不斷開發出新的面貌,并沒有一個單一的目的,這樣的過程正需要足夠松弛的身體在動作的每一次變化中意識到它自身的存在方式。漫游將身體從那些理所當然的日常之中解放出來,重新關注它在日常之中運動的呈現與形變。在漫游中,如同過去之于我們是一個同時到場的整體,當下的時間也被重新經驗為一個綿延的、“開放的整體”[7]。
如果說漫游的開始是由于角色在內心中對都市與家鄉的體悟脫離了“中心—邊緣”的二元論桎梏,那么漫游本身,則是角色通過自己具身的行動來實踐著從“中心—邊緣”的框架中逃逸出來的方法論。這種無拘無束的能量在某個時刻亦有輻射到他者的可能:兩個女孩在逛一間不賣當季衣服的服裝店時——一間不屬于任何季節的服裝店,多么有趣,仿佛是從線性時間里逃逸出的另一個停滯的時空一樣——遇到了同樣喜歡“五條人”歌曲的老板娘,對方心照不宣地放下了工作,與女孩們一起沉浸到一首歌的綿延之中,獲得了日常之外的短暫的解放。
需要指出的是,女孩們漫游的實現不僅是對“都市—鄉鎮”二元關系的超逸,還基于對“男性—女性”傳統關系的辯證。潮汕地區普遍存在重男輕女現象,而教育的不平等是這一現象的具體縮影,“一些經濟較為困難、兒女又較多的家庭,當其經濟只夠支撐一人上學時,不管孩子的成績誰優誰差,退學打工的必然是女孩”[8]。在影片開頭的奶茶店對話中,林燕婷放棄高考的底層原因其實被她自己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了:“我弟說他要去讀什么藝術,光學費就得兩萬塊。”但她沒有將弟弟指認為自身命運的對立面,而只是自己勸自己:“反正高不高考我也無所謂了。”這種釋懷也是漫游得以實現的原因之一。
影片特別設置了兩個男孩無所事事的游蕩作為女孩們漫游的對照。兩組角色在影片的各處都發生著偶遇、行程的重疊和不經意間的擦身而過。但與女孩們從日常的線性中逃離出來尋找解放性的漫游不同的是,男孩們無所事事的游蕩本身就是他們的日常。比起女孩們所需要經歷的接踵而至的期限,男孩們的時間顯然有著過分的盈余,男孩談話的內容也常常是關于“泡妞”“把妹”這類帶有明顯性別歧視意涵的話題。在這片重男輕女的地區,兩人理所當然認為相比起同年齡的女性,自己是處于某種“中心”地位的。影片一開頭,便是兩個男生對女主角林燕婷的騷擾,到臨近結尾時,兩組角色又在臺球桌前產生了正面的沖突。但影片并沒有停留在表面的對立上。若仔細觀察兩個男孩在出入當地各種場所時的姿態和行動,我們會發現他們總是比女孩們表現出更多的自如和游刃有余:他們在腸粉店扯下店面的帳篷捉弄外地人(同樣在腸粉店形成對比的是,女孩們只會私下抱怨腸粉難吃)、在學校樓下高聲大罵朝他們丟西瓜的女孩們、面對牛肉粿條漲價直接要求店家“料放少點就行啦”……他們在行動中似乎處處在彰顯自己作為這片地區的主人身份,而相比之下兩個女孩在空間中則常常顯得局促和拘謹。但男孩們也正因為如此而被困在了這個他們誤以為自己具有主體性和支配權的地區:影片中段,當被問到未來的打算時,男孩說自己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去當地高鐵站載客;影片結尾,男孩們賴以行動的摩托車無端開始自燃,誤認為自己處于“中心”地位的兩人被丟棄在空間的“邊緣”,喪失行動力,看不到走出來的希望。
當我們談及重男輕女現象時,它指的是一種父權制“由性進行的統治”[9] 的派生品,在其中,不僅女性承受著系統性的不公,年少男性事實上也承受著來自年長男性集團的宰制,只是其形式更加隱蔽,盡管兩者有著“性階級”的差異,但在父權制“由世代進行的統治”[10] 之下他們都同屬于一個階級。
受困于時間的女孩們正因感受到身處這片地區的格格不入,于是才通過漫游和出走來尋求心靈與身體在空間上的解放;然而時間自由的男孩們卻在與女孩們“性階級”差異的優越地位上忘乎所以,最終丟失了尋找更廣闊空間的可能性。影片獨具洞見地揭露了重男輕女社會所呈現出的“男性—女性”即“中心—邊緣”的二元結構表象,雖并沒有直接指出其背后的父權制根源,但也暗示了在更為巨大的系統性力量下,無論男女,兩組角色未來的命運也許都將不可避免地被拖入到未知之中。
三、“現實主義”的道德平衡點
當然,我們也并不否認,電影中的現實書寫總是來自導演以其個人生活視角出發所作出的一種主觀化的呈現。因此,電影與現實的相遇,如同吉爾·德勒茲在談到電影與哲學的相遇時指出的:“并不是用其中一方來反思另一方,而是當其中一方意識到它必須以自己的方式為自身解決一個同樣也內在于對方之中的問題的時候,雙方就相遇了……因為任何作品在其領域內本身都是具有可比性的。”[11] 電影創作者的任務是電影化他/她所理解的現實,當社會現實向個體經驗提出了問題時,它便將創作者“引至電影之中去尋找答案”[12]。
需要指出的是,《之后的一周》帶有主觀色彩的現實書寫并沒有采取一種說教性的方式。影片將兩組角色進行對照組設置,也并不是為了以褒揚一方貶損另一方的方式,來兜售某種關于“走出去”的“成功學”(事實上,再也沒有比“漫游”更反“成功學”敘事的了)。漫游從來不試圖“表達”什么,也從不試圖推銷什么,或者說,在漫游中,“不做什么”總是比“做了什么”更重要。甚至,在影片對兩個男孩的呈現中,鏡頭也始終以一種與拍攝女孩時同樣平和的方式注視著他們,即便在拍攝他們性別歧視的對話和騷擾女孩的橋段時,鏡頭的視角也并沒有采用任何剝削式的技巧來刻意丑化他們,而更多的是一種溫和的戲謔姿態——兩個處處惹事卻也處處碰壁的角色,本就有著某種喜劇潛質。這一切的前提是,創作者為影片找到了一種介乎于現實批判的沉重和虛構敘述的輕盈之間的道德平衡點。
此處暫且借一個簡短的題外話來引入影片中書寫現實的虛構力量。《之后的一周》在2022年FIRST青年電影節上映時,許多媒體和評論者提到此片與法國新浪潮大師埃里克·侯麥電影的某些親緣性[13],也許因為兩者都有男男女女的鄉間漫步和日常之中的奇遇這樣的共同點,但這些只是表層敘事的相似。若真要嚴肅分析“奇遇”,相比起侯麥通過奇遇來開啟角色之間新的聯結和情感空間,《之后的一周》中兩組角色的交集甚至很難算得上是“奇遇”——除了開頭與結尾的正面交鋒,他們在更多的時候僅僅是擦身而過,或是前后腳分別光臨同一個場所。“奇遇”,沒有預謀的相遇,作為一種典型的虛構手段,在這部影片中,并不致力于展現兩組角色之間的聯結,而是關注在兩組角色與空間之間的關系上。
這種虛構的技巧一方面的確帶來了它應有的奇趣。從影片一開始我們便看到了男女角色雙方的對立,但他們卻又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不斷地造訪這片地區相似乃至相同的場所,營造出某種冤家路窄的喜劇感。而攝影機也常常以客觀于兩組角色的視角來展示這種不經意的交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女孩們在便利店門口討論著要買什么帶去廣州,隨后騎著車子出畫,須臾,兩個男生從便利店買完東西出來,騎車往另一個方向駛去,這一切被街對面的一個長鏡頭拍下。通過全知視角對兩條故事線近乎游戲般的編排,影片呈現出一種被虛構手段所提純了的主觀現實——不僅在于家鄉之小,幾天內就能逛完,還在于即便是看似水火不容的兩組人,也是被家鄉如此相同的空間所孕育出來的。
而在這種輕盈、戲謔的主觀現實的表象下,“虛構”亦暗示了一個沉重的假設:兩組角色在家鄉漫游行程的重合,亦是個體命運和境況的重合。陸曉浩在采訪中表示:“他們去的很多地方都是同一個,想表達的是就算是重男輕女,不管是出去還是留下,他們的人生都差不多。”[14] 影片結尾處,女孩們已經遠離故鄉,抵達了廣州的某個城中村,此時,林燕婷的臉上突然被映上了一道暖光,當我們試圖為其賦予某種希望的象征時,一個相似性剪輯掐斷了積極意義的生成,暖光化作了男孩們的摩托車自燃的火焰。電影的剪輯,這一“游戲時間”的虛構力量,在創造著游樂園般的空間和巧合的同時,也提示我們那個晦暗的地方性時間的無處不在——它在結尾以一種更加勢不可擋的形式卷土重來,而角色無論身在廣州還是故鄉,都難以幸免。地方性時間的殘酷性在這樣一種虛構手段中亦被提純了。
關于電影如何才能呈現“現實”的問題,也許是一個無解的、需要被永恒地追問的問題,但面對某一部具體的電影,我們也可以退回到對個體經驗意義上的“現實”的探究中。因為,一部電影不可能也不必去摹寫那個大寫的“現實”,一部電影只是如晶體般吸納并折射著創作者以其個體經驗所理解的“現實”。如此,我們所謂的“現實主義”才不至于成為一類創作的陳規和對某種“真實”的客觀主義潔癖,而是一種能夠創造性地編織那些帶有個人生命印記的“現實”的虛構方法論。因為,如果只論一重時間對另一重時間的壓迫,“現實”永遠比電影所呈現出的更為殘酷;重男輕女的觀念在現實中給個體帶來的傷害也一定比電影中所呈現的要更多。但是,呈現苦難并從中剝削出說教的道理,并不是電影的目標,也不應該是“現實主義”的目標。正如在漫游中我們可以暫且忘記所有的期限,在《之后的一周》這一被創作者主觀建構出的電影世界里,也有辯證的虛構力量將角色以及他們所身處的現實帶來超出那個大寫的“現實”之外的可能性,也即綿延的、游戲性的漫游時間。它選擇了從虛構出發,因此它從來只為自己所觀察到的和所想表現的主觀現實說話。
的確,影片在多處批判了這片地區的許多頑疾,也呈現了對男性角色的許多負面的刻畫,但這并沒有令影片成為創作者憤世嫉俗的發泄口,因為這些表達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以不容置疑的姿態指明一個絕對化的“現實”,而恰恰相反,它們都由兩個女孩逃逸出現實之線性時間的漫游作為視角的基點,也在漫游的過程中被作為一種虛構強力的“奇遇”情節編排和游戲性的剪輯收束在創作者自身的主觀現實之中——換言之,所有批判的出發點都基于影片所展現出的對自身虛構屬性的自覺,以及創作者對影片于他而言的私人屬性的自覺。
是的,真正從頭到尾支撐《之后的一周》在表達主題上的諸多辯證(“中心—邊緣”“都市—鄉鎮”“男性—女性”),是這樣一種關于創作機制的辯證:私人性與虛構性。能夠作為影片私人性佐證的是,陸曉浩在自述中表示角色們漫游的三個小鎮其實就是自己“從小到大去的不同地方”,“第一個官埠鎮是我出生的地方……第二個是金玉鎮,我上高中之后會經常去金玉鎮……最后一個炮臺鎮對我意義比較大……小學我最期待的就是爸媽帶我到那邊玩,初中之后是和朋友去玩,所以炮臺鎮是我在家鄉唯一開心自在的地方”。[15] 可以說,導演正是將自己在家鄉的生命經歷壓縮進了女孩們一周的漫游之中。
即便拋掉這種先驗的對導演本人經歷的認知,僅憑影片文本我們也能發現這種“私人性—虛構性”的張力。回到影片開頭,盡管表面上看是林燕婷“投靠”已經有打工經驗的黃漫如,但實際上是林燕婷通過這樣的一個決定,才將被束縛在有明確期限的時間中的黃漫如解放出來,進入到充滿虛構魔力的漫游之中。如果說被擠壓在城鄉之間、中心與地方之間的黃漫如的身上所表征的是一股地方現實的向心力,那么跳脫出線性秩序之外的林燕婷則是將影片引領至虛構之地的離心力(相比起影片花費篇幅來交代黃漫如的前史和家庭,林燕婷仿佛憑空而來,永遠在路上,唯一與這個角色的來歷有關的母親,也只在電話中說出寥寥幾句話,從影片的第一刻起,林燕婷就已經騎著車出現在路上了)。通過超離于現實時間的虛構性的漫游,電影與角色得以獲得清醒的辯證視角;她們所游歷的也都是那些她們曾經生活、學習、玩樂的地方,電影的漫游因此呈現為角色對自身私人經歷的一次追憶——而正是虛構所帶來的辯證視角讓這種追憶成為一次從“現實”、從私人史中收獲警醒和汲取繼續前行的能量的行動。
借此,我們能夠結合導演自身的經歷來分析這種“私人性—虛構性”的創作機制是如何發生的。在創作者關于故鄉現實的私人經驗中,缺乏的是“虛構”;而在電影虛構角色的漫游中,所缺席的又恰恰是作為被“追憶”的對象的私人史。于是,前者的私人經歷填補進了后者的空缺中,并回溯性地生成了后者的虛構之下更根本的一重虛構:作為追憶活動的漫游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有著創作者根據其私人經驗虛構而來的角色前史作為底本以供影片對其展開追憶。在這重意義上,創作者的私人經驗化作了影片敘事中最原初的虛構,而影片則通過對這一原初虛構進行虛構性的展現(以追憶展開漫游,以漫游提純主觀現實),來向我們提示創作者私人視角的在場。
這種“私人性—虛構性”的創作機制的辯證,同時維系著兩種距離:私人性持存著電影與“現實”的距離,虛構性持存著電影與創作者自身的距離。前者讓影片不會過分剝削“現實”的苦難來為自己的說教背書,后者讓影片也不至于成為創作者發泄內心憤懣的出氣筒或是一味投射鄉愁與自哀的景觀符號。
這也是為什么這種創作機制的辯證首先并不是用來服務于某種美學追求或主題表達的,而是一種自覺的創作者道德,既是與那個大寫的“現實”保持距離的道德,也是與自身私人經驗與情感投射保持距離的道德。也許這對于我們這個影像泛濫的年代是一個難以想象的事實:距離,而非“沉浸”,才是電影的美德。
結 語
在《之后的一周》這部看似簡單、輕巧,乃至“業余”的影片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它通過多重時間的辯證思考來打破城鄉、男女等傳統意義上的“中心—邊緣”二元結構,看到了它如何創造性地將私人經驗與虛構的方法相結合,而更重要的則在于支撐這一切的背后,是一種關乎創作道德的辯證視角和距離感。
回望近年華語青年導演拍攝的關于自己故鄉的作品,辯證視角和距離感的缺乏常常導向對欠發達地區的詩意景觀化和對私人情結的過分投射,從而令影片容易陷入到符號化現實和自我感動以至令觀眾產生隔膜的危險之中。不應否定的是,創作者們拍攝關于故鄉故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出于自身對故鄉豐沛而真摯的情感,但如何為私人情結注入虛構視角的活性、如何令虛構故事辯證地討論現實議題、又如何道德地維系上述的距離,并不是創作者情感足夠真誠便能迎刃而解的。在這些問題上,《之后的一周》為如今的年輕導演們提供了一種解決的可能。
基金項目:2023年度汕頭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潮汕電影生產與城市發展研究”(ST23ZX19)。
(作者單位: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
注釋:
[1] [14] [15] 陸曉浩:《FIRST需要這樣的電影,本屆最大驚喜》,微信公眾號“深焦DeepFocus”,https://mp.weixin.qq.com/s/Y7UmyD93lxZcrIvFQVE2ow,2022年8月3日。
[2] [3] 陳柏麒:《時間末端的城市:潮汕新浪潮電影當中的文化空間和景觀》,觀潮檔案,2017年。
[4] [美] 尤金·W. 霍蘭德:《導讀德勒茲與加塔利〈千高原〉》,周兮吟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頁。
[5] [法] 吉爾·德勒茲,菲力克斯·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頁。
[6] [7] [英] 克萊爾·科勒布魯克:《導讀德勒茲》,廖鴻飛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頁。
[8] 陳友義:《潮汕地區重男輕女社會現象探析》,《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8月,第3期。
[9] [10] [日] 上野千鶴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鄒韻、薛梅譯,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77頁。
[11] [12] [法] 吉爾·德勒茲:《什么是創造?》,載李洋:《要么去愛,要么孤獨:法國哲學家論電影續編》,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92—193頁。
[13]《少數派意見: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學者之選》,微信公眾號“耐觀影”,https://mp.weixin.qq.com/s/OZvl5ROikaIzV__OB_KtAw,2022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