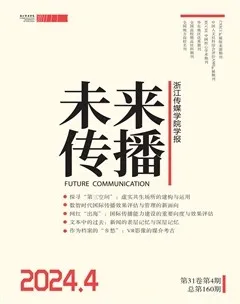網紅“出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向度與效果評估






摘 要:研究選取阿木爺爺YouTube官方賬號觀看次數前10的作品,爬取26361條非中文留言(含表情符號)作為分析樣本,借用“認知層面—情感層面—意動層面”的經典框架,剖析網紅“出海”在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方面的效果。研究發現,在認知層面,網紅“出海”的政治符號淡化,生活化個體符號凸顯,“他者”類比提供了國外網友探知中國符號的視角。與此同時,身份模糊、語言歧義、觀念沖突等認知障礙影響了網紅“出海”的觀感和評價;在情感層面,精湛的中國傳統技藝、老當益壯的工作狀態、以親情為紐帶的代際傳承喚起了國外網友的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占比較小,其中亦不乏建設性的批評言論。在意動層面,“亂言”與糾錯的線上交鋒隱喻著國家間敘事話語權的激烈爭奪,扭轉原本負向的行為傾向和表達對中國文化體驗的向往,代表了國外網友線下意動的兩個方向。
關鍵詞:國際傳播;短視頻;網紅“出海”;重要向度;效果評估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4-0053-10
近年來,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無論在國家頂層設計的藍圖,抑或在學術研究的知識圖譜中,皆成為顯性的戰略議題。這一議題的凸顯源于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與現有國際話語權的不相匹配。正如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話語即權力”,長久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依憑發達的大眾傳媒業,在國際傳播的信息流動中占據“順差”高地。它們精心“編織”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元敘事框架,并在“進步主義”的西方現代話語的標榜下,將其撒播至世界各個角落。[1]這是一個“一體化的整合過程”[2],內置著隱性的權力控制。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使用“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的概念對此加以批判:“(文化帝國主義)以引誘、壓迫、強制乃至賄賂為手段,驅使一個社會的主導階層塑造出與現代世界體系的主流意識形態相匹配的社會體制,強化了現代體系的統治結構。”[2]此種話語框架及其表征的權力落差使得中國等后發國家在全球話語權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即是此種境況的寫照。
尋覓因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差異而遭遇西方國家話語圍堵的突圍路徑,成為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使命。[3]網紅“出海”因應社交媒體,成為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的可選方案。本文選取“網紅”出海的成功案例,借用說服研究“認知(cognitive)層面—情感(affective)層面—意動(conative)層面”的經典框架,考察國外網友對網紅“出海”所建構的中國話語的接受情況。以“出海”網紅為媒,國外網友形成以及如何形成對中國的何種認知?評論區的情感地圖如何分布?國外網友對中國的行為傾向呈現何種特點?在回應上述問題的基礎上,本文將總結網紅“出海”的經驗啟示,以期為網紅“出海”在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方面的效能添磚加瓦。
一、文獻綜述
2009年6月,中共中央《2009—2020年我國重點媒體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總體規劃》出臺,明確提出“把我國重點媒體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納入國家社會發展總體規劃”[4]。同年,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開始為學界所關注,出現了以《堅持科學發展 提升傳播能力 努力建設影響廣泛的國際一流電視強臺》為代表的第一批研究文獻。此種時間上的重疊反映了學術研究的敏銳性。此后,發文量雖偶有波動,但基本呈現遞增之勢(如圖1所示)。“經驗—啟示”框架和“問題—對策”框架成為主流研究框架。
“經驗—啟示”類研究主要分析從事國際傳播的相關機構的建設運營、內容生產,總結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成果及蘊含的經驗啟示。這可分化出不同的研究路徑:其一,從歷史的、政治的、全局的高度擘畫國際傳播矩陣的外在輪廓,著力分析國家在政策環境、資金投入等方面對媒體機構的支持,指出“以外宣旗艦媒體為引領,中央和地方媒體協同參與的外宣格局已然形成”[4](297),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形象自塑能力有了很大提升。[5]其二,“解剖麻雀”,以個案研究小切口折射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大問題。云南亞洲象北遷南歸報道、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報道等成為研究熱點,表征著中國國家形象符號的拓展與更新。[6]
“問題—對策”類研究則致力于揭示現階段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存在的問題,繼而探討提升國際傳播能力的可行方案。研究的問題反思如下:在理論建構層面,理論的有效性面對世界地緣政治版圖位移和全球傳播生態變革“捉襟見肘”[7],內在批判力、闡釋力、供給力亟待升級[8];在戰略思維層面,西方話語“二傳手”的頑瘴痼疾猶在[9],媒介話語生產“自我東方主義”傾向亟待扭轉[10];在實踐操作層面,對外議程設置能力不強[5](15)、說教式宣傳效果不佳[11]、受眾分析不足致使傳播失焦[12]等皆是現實痛點。研究從“道”和“術”兩個層面建言獻策:“道”的層面重在制定基本原則,提出布局智能全媒體國際傳播戰略體系[3](8)、建構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9](1);“術”的層面則針對實操問題提出具體對策和建議,例如,推動“政府+媒體+智庫”多元主體融入國際傳播大格局[13];打造頭部賬號和爆款產品,推動黨的創新理論成果形象化、可視化、國際化[8](8)等。
綜上所述,圍繞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這一重大議題,學術界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其理論觀點、行文框架、資料整合等對本研究有啟發借鑒意義。與此同時,有研究基于對CSSCI期刊論文的文獻計量學考察指出,多數研究僅對國家級媒體保持高關注,分配給人際傳播、網絡傳播的注意力有限,這與媒介“下沉”至社會“元場域”的傳播生態相脫節。[14]此種研究現狀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所處的網絡化的時代語境。一直以來,互聯網都在“固化”與“流動”兩大作用力的此消彼長中影響著國際傳播版圖的型構。在“固化”方面,對全球社交媒體權力流動的實證分析表明,線下權力結構不僅可能被挪至線上,還可能因應某些要素的催化,借助線上實現擴張。[15]在“流動”方面,互聯網分布式的網絡結構天然攜帶去中心化的基因。它賦權個體成為傳播基站,驅使國際傳播從媒體機構為主體的“象陣”傳播轉向基于個人的“蟻群”傳播[16],提供了撬動“固化”權力結構的新變量。
考察網紅“出海”在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方面的效果,既是扭轉“重大眾傳播,輕人際傳播和網絡傳播”這一研究取向的題中應有之義,又呼應了國際傳播從“象陣”傳播邁向“蟻群”傳播的時代大勢。現有研究以個案分析為主。其中,探究作為國際傳播樣本的李子柒成功“出海”的機理密碼構成學術研究的主線,涌現出文化“間離”效果說[17]、“直通車”模式說[18]、“超文化回聲室”說[19]、后現代語境說[20]等學術觀點。與如火如荼的李子柒研究形成對比,許多頗具國際影響力的“出海”網紅尚未進入學術研究考察的視野。換言之,現有研究存在結構性失衡,既不利于準確把握網紅“出海”的整體態勢,又鉗制了構建豐富而立體的中國形象的路徑探索。本文基于實證研究范式,考察國外網友對阿木爺爺鏡頭下的“影像中國”的認知、情感和意動,是補充和豐富現有研究的一種嘗試,有助于透視海外網友群體內部的差異性,助力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分眾化傳播。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文將阿木爺爺YouTube官方賬號網友留言作為分析對象。阿木爺爺名叫王德文,山東聊城人,現跟隨兒子生活在廣西梧州市屯兩村。他13歲學習木工,至今已有50余年。2018年底,他因一段采用中國傳統的榫卯工藝制作魯班凳的短視頻走紅網絡,被外國網友稱為“真正的魔術師”(true magician)。阿木爺爺YouTube官方賬號由王德文的兒子負責運營,賬號內容主打木匠工藝,同時涉獵美食制作、捕魚技巧、中國功夫等。值得注意的是,王德文主演了阿木爺爺賬號下的大部分作品,其余作品的主角則是另一位不具名的老人。王德文的兒子、兒媳、小孫子等亦作為配角亮相。在這個意義上,阿木爺爺賬號是團隊協同,共筑內容矩陣。選取阿木爺爺作個案“深描”,案例的代表性是主要考量因素:一方面,阿木爺爺的身份特征和視頻文本皆具有鮮明的中國鄉村特色;另一方面,阿木爺爺在海外具有一定影響力。其YouTube粉絲數達178萬,視頻播放量超4億次,有4條視頻播放量超1000萬次,單條最高播放量達5861萬次。
(二)樣本選取
截至目前,阿木爺爺YouTube官方賬號共發布556部視頻作品。按“熱門”排序,選取觀看次數位列前10位的作品(如表1所示),評論區的全部網友留言構成初始分析樣本。在本文語境下,留言囊括了評論(comment)和回復(reply)——前者的客體是視頻,后者的客體是評論和其他回復。
(三)數據爬取
使用基于Python語言的Selenium框架自動化模擬人工瀏覽操作,爬取動態加載的所有評論和回復。數據爬取過程中引入檢查點(checkpoint)機制和容錯(fault tolerance)機制,以保證程序運行穩健。檢查點機制即每進行200次數據請求,緩存當前頁面作為檢查點,提高數據獲取的魯棒性(robustness)。容錯機制即在請求數據時,一旦觸發數據獲取結束條件(即當前滾動是否達至最底端),程序反復滾動并睡眠5次,避免因網絡延時造成的數據獲取不完整。
(四)文本解析
使用XPath表達式“//ytd-comment-renderer”,定位div標簽下包含留言的標簽“ytd-comment-thread-renderer”;使用XPath表達式“.//*[@id=\"content-text\"]”,定位留言文本,濾除html標簽后,獲得文本數據。其余元數據(如作者、時間等)經由類似解析獲取。由于本文考察的是國外網友的認知、情感和意動,因此使用正則表達式“[\u4e00-\u9fa5]”濾除中文留言,剩下的26,361條非中文留言(含表情符號)構成了本文的最終分析樣本。
(五)數據可視化
1.制作詞云圖
使用賓州樹庫(Penn TreeBank,TextBlob默認實現)算法對留言文本進行分詞(tokenization);使用NLTK框架下的stopwords子模塊去除停用詞(stop-word);使用pyecharts中的WordCloud子模塊渲染詞云圖。
2.制作情感分析直方圖
使用TextBlob默認的PatternAnalyzer(來自Pattern庫)逐條分析留言的極性(polarity)和主觀性(subjectivity),將極性區間[-1.0, 1.0]按步長0.1分桶(bin),將全部留言的極性值劃分到對應桶中,繪制情感分析直方圖。
3.制作極大會話關系圖
記1條評論和該評論下的所有回復為1個會話(thread),遍歷10個視頻中的全部會話,取每個視頻中條數最多的會話,記為極大會話。統計每個極大會話中的用戶和留言次數,以用戶為節點,留言次數為節點權重。逐條解析回復文本,若文本明確指向會話中的用戶,則以該文本用戶為起點,所指向用戶為終點,繪制一條有向邊。否則,以該文本用戶為起點,評論用戶為終點,繪制一條有向邊,以此描述會話關系。另外,使用Gephi渲染極大會話關系圖。
三、研究發現
(一)個體認知的形塑
認知即理解,是感知者在刺激(stimuli)和反應(responses)、輸入(inputs)和輸出(outputs)之間進行調解(mediate)的內部過程。[21]中國主流媒體的海外傳播受困于“偏見”和“異化”的藩籬——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分野下,它們被西方利益集團貼上政府“傳聲筒”的標簽[22],鉗制了中國聲音向海外網友觸達的廣度和深度。特別是伴隨“后真相政治”于西方社會的彌散,此種刻板成見愈加根深蒂固——西方政客精心炮制、編織、操控話語敘事,使“客觀”“真相”讓位于“情感”“身份”,左右著西方受眾的信息接觸與價值研判,制造意識形態對立的風險。[23]
相較之下,阿木爺爺等“出海”網紅或許無法在作品厚度和藝術審美上達至主流媒體的水準,卻擁有政治傳播色彩淡化的先天優勢,因而更容易被異文化場域的全球網友所接納,成為其認知真實中國的重要媒介。本文對網友留言的實證研究亦證明了這一點——僅有少量留言提及冠狀病毒(corona-virus)、種族主義(racialism)等政治議題,大部分留言均與政治無涉。主要內容包括贊美阿木爺爺的高超技藝,高頻詞有amazing(1228次)、wow(762次)、good(759次)、incredible(199次)等;分享觀看視頻的美好體驗,高頻詞有like(1022次)、beautiful(579次)、awesome(392次)等;表達對古老技藝傳承的期盼,高頻詞有skills(381次)、craftsmanship(351次)、grandson(157次)等;提出視頻優化的方向,高頻詞有music(269)、videos(237)等(如圖2所示)。此種認知的形成離不開視頻制作者對認知符號的取舍和組合。
第一類符號是視聽符號。多年前,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J.Boorstin)在其代表作《圖像》中提出了“圖像革命”的概念,“19世紀中期,照片和其他插圖突然大量侵入符號環境,它們在美國文化中橫沖直撞,看圖片而非讀文字成為人們信息判斷的基礎”[24]。如今,這場“圖像革命”因應泛視覺化時代的到來程度尤甚。羅蘭·巴特甚至斷言“言語已降格至圖像的寄生物”:“言語升華圖像,使之感人或理性化,而圖像并不闡明或實現言語。”[25]阿木爺爺的視頻以大量中近景和特寫鏡頭直觀展示阿木爺爺做木工的全過程,甚少出現對話和字幕,降低了國外網友理解作品的難度。降低難度不等于沒有難度,認知具有區隔性。對于跨文化傳播而言,這是地理、文化、制度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文本梳理發現,作為“他者”的國外網友在面對陌生的視聽符號時,慣于采用類比完成認知由陌生化向熟悉化的“轉譯”。例如,將阿木爺爺類比成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悟飯爺爺(Grandpa Gohan,出自日本漫畫《龍珠》,筆者注);將榫卯工藝比作林肯積木(Lincoln logs)、變形金剛(Transformers);李子柒、中國功夫、中國制造等亦成為國外網友認知新的中國符號的中介物,“阿木爺爺是李子柒的爺爺嗎”“爺爺一定會神秘的中國功夫”,諸如此類的留言獲得眾多網友點贊。
第二類符號是手工木制品符號。如表1所示,在觀看次數前10的作品中,7個視頻的主題是手工木制品,涵蓋了木拱橋、小水車、烏篷船、魯班凳等。國外網友被中國傳統的木工技藝所折服,“沒有設計圖紙,只有最基本的工具,(但)這座橋的比例非常完美”,“好可愛的(烏篷)船,我真希望能和阿木爺爺一起劃船”,“魯班凳的復雜性(complexity)和質量(quality)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干得漂亮”。在夸贊之余,制作手工木制品的材料、工具、技藝等備受關注。有網友詢問:“這用的是什么木頭?它的顏色如此鮮艷(vivid),我還以為上過油(oiled)了。”“請問這個竹子鉆(bamboo drill)是怎么做的?”還有一些網友心疼阿木爺爺只能純手工勞作,表示要給阿木爺爺寄錘子(hammer)、手套(glove)、3D打印機(3D printer)。這類跨文化線上交流拓寬了國外網友的認知視域。
第三類符號是空間符號。有研究者將地方空間視為一種“語境假定物”,認為它是物質的客觀形式,兼具物質性和社會性雙重屬性。[26]物質性強調作為地理坐標的地方空間。“秀甲天下,壯美廣西”的山山水水給國外網友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個生活環境真是太棒了!每個搬到大城市的人都在尋找已經存在的東西。”社會性則強調地方空間的生活社交和文化色彩,它“既提供各類資源,又提供記憶和行為的暗示”[27]。阿木爺爺含飴弄孫、村里人幫忙伐木造橋等場景,展現了鄉土中國“熟人社會”的生活日常。網友們紛紛留言:“喜歡看爺爺和小孫子在一起,太溫馨了!”
身份模糊、語言歧義、觀念沖突等認知障礙客觀存在,影響了國外網友對阿木爺爺的觀感和評價。具體而言,“身體”這一意象在社會學研究中擁有豐富的意涵。它既可指代此在化的實在肉身,又可指代權力和文化形塑的社會身體。在后一種語境下,身體被賦予了符號標識的功能,反映了一個人的生存狀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國學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才有了如下論斷:“身體并非簡單實體,而是被體驗為一種應對外部情景和事件的實踐模式,對身體保持規訓是社會行動者固有的一種能力。”[28]對于國外網友而言,阿木爺爺的身體是其點擊視頻后獲取的第一印象,是認知“阿木爺爺”賬號所承載的中國符號的開端。阿木爺爺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其真實職業是什么?是否存在兩位阿木爺爺,誰為真,誰為假?圍繞上述問題,觀點交鋒激烈,滋生了“阿木爺爺是日本人”等錯誤引導言論、“阿木爺爺受中國政府秘密資助”等“陰謀論”,以及“主角身份變換(6號和8號作品的主角不是王德文,是不具名老人,筆者注)是因為博主從別處盜用了視頻”的揣測。
語言歧義通常出現于視頻標題和視頻簡介的翻譯上。以“魯班凳”為例(4號作品),博主將其翻譯成Luban Stool。Stool有“凳子”之意,也有“糞便”之意。有國外網友一開始以為“這是一段某人上‘大號’的視頻”。無獨有偶,阿木爺爺賬號曾用名“功食道”,英漢對譯時使用了esophagus一詞。但esophagus專指“食道”這一人體器官,顯然語義不符。
觀念沖突則源于價值觀念和文化禁忌的差異。例如,8號作品致敬金庸武俠和香港喜劇電影,以“鏡頭倒放+五毛特效”塑造了不具名老人“口吐棗核即可射殺一只兔子,扔片樹葉即可捕殺一只飛鳥”的世外高人形象。然而,獵殺動物的行為和略帶血腥的特寫鏡頭引發國外網友聲討:“這太令人痛心了,人類暴力是最嚴重的罪惡!”“我不喜歡!奇怪的是,它沒有因為不恰當的內容而受到審查。”
(二)情感極性的構成
在社會認知語境下,情感反應是由目標的特異性(specificity)區分的,包括喜歡/不喜歡的評價、愉快/不愉快的經驗等。[29]圖3展示了國外網友留言的情感分布情況,極性區間[-1.0)代表情感負向,(0.1]代表情感正向,0代表情感中立。有1299條留言情感負向,8996條留言情感正向,另有16,066條留言情感中立。整體而言,持負向情感的國外網友占比較小(4.93%)。這表明阿木爺爺視頻的認可度較高。
研究發現,正向情感主要來源于如下三個方面。其一,精湛的中國傳統技藝。如圖2所示,點贊、鼓掌等表情符號,amazing、great等形容詞,genius、master等名詞皆是高頻詞,反映了國外網友對阿木爺爺業務能力的高度認可。以業務能力為中心點,網友的討論話題向多方向延伸:或撫今追昔,講述自己小時候,自己的爺爺做木工的溫馨場景;或“以小見大”,借阿木爺爺表達對中國的認可:“為什么中國制造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東西?阿木爺爺的視頻說明了這一點。”
其二,老當益壯的工作狀態。勤奮(diligent)、專注(devoted)勾勒了阿木爺爺在國外網友眼中的另一面,傳遞了人生正能量:“我40多歲了,如果能有阿木爺爺一半甚至四分之一的力量和活力,我會很激動!時間的流逝沒有使你靜待衰老,而是讓你每天都變得更棒!”
其三,以親情為紐帶的代際傳承。阿木爺爺與小孫子之間的親情牽絆跨越了文化隔閡:“阿木爺爺不給孫子買玩具,而是親手給他做。我相信,他的孫子長大后會非常感激他。”“中國人世世代代都在為下一代籌謀,希望他能把這些技能傳給下一代,這些不可思議的技能不應丟失。”
負向情感的色彩光譜并非“非黑即白”,僅有少量留言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它們因襲認知慣性,基于對中國的既有偏見畫延長線,給阿木爺爺的視頻貼上propaganda的標簽。Propaganda曾被翻譯成“宣傳”,但基于語言學和傳播觀念史雙重視域的考察表明,它和中文語境中的“宣傳”并非一回事:“在西方,propaganda是一種利用象征符號操縱社會大眾的技術,且專指敵方的傳播和說服活動。它因蘇俄宣傳部和納粹德國大眾教育和宣傳部的成立而徹底淪為一個負面詞匯。”[30]
負向情感的留言中亦不乏建設性的批評言論,它們或針對視頻內容提出疑問,或意在指出視頻制作存在的瑕疵。前者以1號作品為例,有網友對木拱橋的穩固性表示擔憂:“這座橋沒有地基(foundation),豈不是一下雨就會搖晃?”“護欄太低了,不是防止人摔倒,而是讓人摔倒。”“木頭上有這么多切口,這座橋老化程度如何?”后者則涉及鏡頭穿幫、背景音樂與畫面不匹配等:“阿木爺爺的麥克風(mic)掉了。”“音樂太可怕(terrible)了,我寧愿聽自然的聲音。”兼聽則明,及時對網友疑問加以回復,并根據網友意見提升視頻制作水準,應是提高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手段。
進一步梳理可知,一些留言雖然使用了不喜歡(dislike)、令人厭惡的(nasty)等表負向情感的詞語,但文本內容是對發表“差評”網友的回擊:“我敢打賭,‘踩’視頻的人在嘗試任何事情時都是無能的,因為他們看不到老人嫻熟的工藝。”“為什么這些評論一定要令人厭惡呢?只要欣賞工藝就好了。”還有一些留言將“吐槽”的矛頭對準美國和美國政府:“與日本或中國相比,美國是懶惰的。”“如果是在美國,政府會雇傭一個承包商拆掉這座橋,然后花10倍的錢造一個使用期限只有(現在這座橋)二分之一的橋。”站在阿木爺爺的立場,其情感表達實則正向。
(三)線上意動與線下意動的交織
“認知—情感—意動”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過程,傳播效果于其間發酵、疊加,而對受眾意動施以影響構成了傳播的終極目的。[31]國外網友在阿木爺爺視頻評論區的留言構筑了多層次對話的網絡社區。雖然此種虛擬社區將身體留在電腦后面,不可避免地造成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區隔,但作為一種單向與雙向、廣播與窄播、同步與異步并行的交流渠道,它契合了社會黏性化、濕向化的方向——“以社交媒體為紐帶,人類社會變成富有人情味的、濕乎乎的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組合方式(例如,組建群體、尋覓同道)是以自由連接而非制度捆綁實現的,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32]。網友的自由言說提供了“亂言”在網絡社區滋生和蔓延的條件。圖4是10個極大會話關系圖中的一例,“榫卯技藝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成為會話中“引戰”的導火索。“挺日派”如是寫道:“傳統的日本木工非常了不起,他們不用一件硬件(a single piece of hardware)就能蓋房子。”“挺中派”則甘當“自來水”,向不知情的“吃瓜群眾”科普榫卯技藝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亂言”與糾錯的對壘隱喻的是國家間敘事話語權的激烈爭奪。遺憾的是,無論是此種較大規模的會話,還是單條問詢類留言,視頻博主均未現身回復。
除卻線上話語權的爭奪,網友“意動”還混雜了線下傾向的改變。心理學中的“光環效應”(halo effect)描述的是人們傾向于依據對某一事物的初始印象,推斷它其他方面特征的心理狀態。[33]依循這一視角,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實際上承擔著兩項殊途同歸的任務:一方面,強化國外網友對中國“優勢符號”的認同;另一方面,策略性地扭轉國外網友對中國的負面認知。后者雖然道阻且長,但可喜的變化正悄然發生,“我正要開個玩笑說‘中國病毒’,但我改變了主意。我想,如果那是我爺爺怎么辦?如果發生這種事,我會有什么感覺?”與此相交織的另一條線索是,表達對中國文化體驗的向往。有網友想登門拜訪:“這家伙太棒了,我想和他一起喝茶。”有網友想拜師學藝:“我很想去亞洲,向像他這樣的老人學習。我的木工技術定能突飛猛進(through the roof)!”有網友想雇傭阿木爺爺:“我怎樣才能與他聯系?我想請他來美國,幫我建造一個木屋。所有費用由我支付,薪水豐厚。”還有網友因阿木爺爺的視頻重塑了對中國符號的想象:“這是一段如此美麗的視頻,它確實打動了我的心。用這樣簡單的工具創造了這一切,多么驚人的知識和天賦!我喜歡你生活的環境,真希望能夠和你們住在一起。”
四、結 語
本文選取阿木爺爺YouTube官方賬號觀看次數前10的作品,爬取26361條非中文留言(含表情符號)作為分析樣本,借用“認知層面—情感層面—意動層面”的經典框架,剖析網紅“出海”在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方面的效果。“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本文認為,應繼續從認知、情感、意動三個維度增強網紅“出海”效果,以更好地服務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大局。
在認知層面,深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開掘,以平民化的視角、日常化的場景,形塑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中國傳統文化符號是國外網友體認中國的一扇窗口,多元文化符號的呈現有利于建構出相對完整的文化地圖,提供整體而真實的東方圖景。“出海”網紅應加大對具有中國特色的視聽符號、文化符號、空間符號挖掘的力度,激發國外網友的求知欲;加強對“出海”作品的細節把關,避免出現語言翻譯導致的歧義,規避因爭議性選題和爭議性呈現形式引發的理念沖突,減少文化折扣。
在情感層面,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探索異文化場域網友的共鳴點,輸出正向的情感力量。雖然文化隔閡客觀存在,但是共通性情感依然流動于人類的審美活動之中,“它是一個動態的、方向性的人際互動中的社會心理過程,是相似或相同情感的形成與擴散”[34]。植入國外網友可類比“轉譯”的文化符號是激發共通性情感的一個可行方案,這既能降低解碼門檻,又容易觸發話題討論。除此之外,亦可增加“故事模式”的報道比例。美國政治傳播學學者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將新聞報道區分為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前者純粹用來傳遞信息,后者則通過篩選、修飾事實來引導大眾生活。”[35]以阿木爺爺這一個案的考察為參照,“故事模式”擅長講述普通人微觀而鮮活的生活,能夠平衡國際傳播多采用信息模式而留給國外網友嚴肅、正統的刻板印象,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離。
在意動層面,建立常態化的互動機制,擴大“喬哈里視窗”的開放區。“喬哈里視窗”將人的內心世界比作一扇窗戶,并依據個體對自身信息和對他人信息的開放程度,劃分出開放區(自己和別人都知道)、盲區(別人知道但自己不知)、隱藏區(自己知道但別人不知)和未知區(自己和別人都不知)四個象限。其中,開放區劃定了互動雙方愿意自我表露和共享信息的邊界,它的擴大能夠減少互動雙方因信息缺位產生的不安全感。[36]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應以“售后維護”思維取代“作品發布”思維,針對國外網友問詢、評論區不實言論等作出及時回應,既解疑釋惑,又以正視聽,推動多元文化在交流互鑒中走向“民心相通”。
參考文獻:
[1]虞鑫,崔乃文.從“走出去”到“走進去”:全球史敘事視野下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路徑[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19):90-94.
[2]李智.國際傳播(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42.
[3]段鵬.當前我國國際傳播面臨的挑戰、問題與對策[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8):1-8.
[4]程曼麗.國際傳播學教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291.
[5]余江,李文健.新作為、新論斷與新路徑:新時代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再思考[J].求是學刊,2021(6):12-19.
[6]程曼麗.中國國家形象符號的拓展與更新[J].新聞與寫作,2022(6):1.
[7]李思樂.三個“面向”與六個“維度”:邁向新時期的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J].湖北社會科學,2022(6):161-168.
[8]余遠來,孫亦祥.黨的創新理論國際傳播:新理念、新路徑和新方法[J]對外傳播,2022(8):4-8.
[9]李韜,林經緯.中國軟實力提升:問題與出路[J].紅旗文稿,2013(13):24-28+1.
[10]劉耀輝,張璇.姚明的陰影:“自我東方主義”的中國媒介話語生產——基于《中國青年報》對姚明的報道[J].國際新聞界,2010(5):56-62.
[11]劉繼南,何輝.當前國家形象建構的主要問題及對策[J].國際觀察,2008(1):29-36.
[12]周霖.面向東盟的新媒體傳播問題與策略——以廣西廣播電視臺構建新媒體國際傳播為例[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2(9):133-135.
[13]鄭亮,高同同.交往理論視角下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與國際傳播能力提升研究[J].全球傳媒學刊,2023(2):45-59.
[14]胡曉菲,胡翼青.破界、融合、創新:“講好中國故事”研究的現狀與展望[J].傳媒觀察,2021(9):5-16.
[15]周翔,吳倩.場域視角下“一帶一路”推特傳播網絡結構分析與反思[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09-125.
[16]周翔,丁敏玲.信息生態視角下我國對外傳播中網絡用戶的核心生態位問題[J].對外傳播,2018(11):48-51.
[17]趙暉,李曠怡.短視頻對中國文化海外形象的塑造與傳播[J].中國電視,2021(2):74-78.
[18]程思琪,喻國明.享樂感與幸福感:跨文化傳播中的“直通車”模式構建——基于李子柒短視頻評論的分析[J].新聞大學,2022(5):36-49+119.
[19]姬德強.李子柒的回聲室?社交媒體時代跨文化傳播的破界與勘界[J].新聞與寫作,2020(3):10-16.
[20]李小華,華凱純.后現代語境下中國傳統文化傳播新向度——基于李子柒的短視頻分析[J].中國出版,2020(22):62-66.
[21]Fiske,S.T.(1993).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perception.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44:155-194.
[22]張雨龍,駱正林.網紅出海:商業景觀與國際傳播的耦合機制[J].新聞愛好者,2023(3):22-26.
[23]鄭亮,夏晴.媒體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中“國際—國內”議題互構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2(9):83-88.
[24]劉瑞一.中國網絡視頻的緣起與流變(1996-2020)[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1:1.
[25]朱莉,徐可意.中國大象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的跨文化接受研究——基于YouTube短視頻評論的分析[J].傳媒,2022(14):56-59.
[26][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M].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20-121.
[27]邵培仁,楊麗萍.轉向空間:媒介地理中的空間與景觀研究[J].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69-77.
[28][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中的自我與社會[M].夏璐,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52-53.
[29]Brewin,C.R.(1989).Cognitive change processes in psychotherapy.Psychological Review,96(3):379-394.
[30]劉海龍.漢語中“宣傳”概念的起源與意義變遷[J].國際新聞界,2011(11):103-107.
[31]Sim,S.(2006).Demystifying Asian values in journalis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6(2):429-432.
[32][美]克萊·舍基.人人時代:無組織的組織力量[M].胡泳,沈滿琳,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IV-V.
[33]喻國明,潘佳寶.試論我國國際文化影響力傳播的路徑與策略[J].傳媒觀察,2021(4):11-18.
[34]薛可,李思晨.守正創新:新時代中國對外傳播再思考[J].對外傳播,2023(6):58-62.
[35][美]邁克爾·舒德森.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M].陳昌鳳,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79.
[36]高潔.思想政治理論課對話式教學的“喬哈里窗”機制探索[J].思想教育研究,2019(8):112-116.
[責任編輯:高辛凡]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我國農村地區移動短視頻的生產、呈現與社會影響研究”(21CXW020)。
作者簡介:劉瑞一,男,編輯,博士;矯立斌,男,講師,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