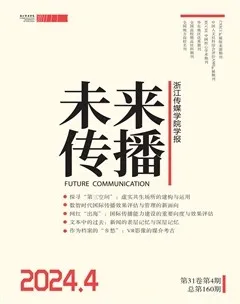作為檔案的“鄉愁”:VR影像的媒介考古
摘 要:從媒介考古到電影媒介考古,“回溯—前瞻”式的新電影史研究路徑認為,電影史是非線性的、斷裂的,電影的概念也是多樣的、異質的。媒介考古學不僅從過去的媒介中尋找新媒介的可能性,更是通過新媒介回溯歷史現場,而VR可以被視為是一份回溯性的媒介考古學“檔案”。將VR放在媒介考古學回溯性的系譜中考察,沉浸感、全景空間以及物質媒介等早期媒介形態,都為VR在史前史及早期媒介中找到了家族相似的媒介線索。VR屬于電影史的“斷裂”時刻。作為一種新型的技術媒介,VR卻不斷地從過去得到材料印證,它使散落在歷史各處的媒介被重新拾取,在諸多物質媒介與虛擬媒介上找到了歷史的幽靈,在新媒介中重拾過去的影子。因此, VR影像作為檔案的“鄉愁”,是重要的考古媒介。
關鍵詞:媒介考古學;新電影史;VR影像;檔案;數字化
中圖分類號:J9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4-0100-08
一、媒介考古學作為方法
作為一種極具生產力的方法論,“媒介考古學”(Media Archaeology)自20世紀80年代興起至今,展示出清晰的反線性歷史的研究面貌。[1]媒介考古學打破傳統的線性歷史觀,強調歷史的斷裂敘事,為學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關于反線性歷史,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1928)中早已提出“星叢”(Konstellationen)概念,認為“理念與物的關系就如同星叢與群星之間的關系”[2],歷史事件之間存在其獨特性,但又通過復雜的方式組成星叢,事件與事件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這是一種非線性的、斷裂的歷史觀念,打散了主體歷史,揭示了主流歷史敘事之外被忽略的時刻。
媒介考古學考察歷史上被遺忘或忽視的媒介形式,其理論資源豐富,代表學者有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Siegrfied Zielinski)、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等。盡管齊林斯基從未正式使用過“媒介考古學”這一術語,但他的研究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啟發,側重研究知識發展的不連續性及其“話語”(discourses)分析。在福柯那里,話語分析是知識考古學的核心——“我的目標不是語言而是檔案(archive),即話語(discourses)的累積存在。考古學,正如我所理解的,它并不類似于地質學(作為對底層的分析)或譜系學(描述開始與繼承);它是對其檔案形式的話語的分析(analysis of discourse in its archival form)。”[3]
福柯揭示了話語如何構建歷史。作為一個堅定的尼采主義者,福柯認為歷史是話語實踐的結果,而非連續的歷史進程。為了尋找被塑造的歷史中那些不連續的、異質的聲音,需要確立耐心的譜系學研究方式。循著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脈絡,福柯在《尼采·譜系學·歷史學》(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考察“起源”(Ursprung)一詞的語義,[4]反對將“起源”視為唯一的歷史開端,即反對本質主義的歷史觀;相反地,“出身”(Herkunft)和“出現”(Entstehung)強調斷裂,拆解了傳統的歷史敘述,強調歷史由眾多偶然與多樣的“事件”(event)構成。也是在這個維度上,后來的新歷史主義與媒介考古學找到了方法論支撐。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生成”(becoming)理論也在這一維度上提供了解釋,強調歷史和現實的不斷變動和生成過程。
另一種媒介考古方法強調技術對媒介的作用。以基特勒為代表的媒介考古學,突出了媒介的物質性,強調技術在媒介演進過程中的作用。基特勒的媒介考古方法是基于物質媒介的考古,將媒介視為物質性的檔案,認為是媒介決定我們的處境。[5]福柯關注話語和權力的關系,基特勒更傾向于挖掘留聲機、電影、打字機和計算機等“物質”線索,考察不同時期的媒介技術對歷史文化的影響。[5](5)基特勒的理論為媒介的物質技術性提供了方法論支撐。而在新物質主義的框架下,媒介考古學被視為一個由物質構成的網絡。媒介考古學將電影視為“物質檔案”[6],這是媒介考古在電影領域的嘗試。
可以看到,媒介考古學的理論資源并非單一,加之它容納了“視聽技術的深層時間”(齊林斯基)、“屏幕考古”等充滿冒險精神的研究對象,媒介考古學的線索已經很清晰了:它是回溯的,也是斷裂的。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提出“失敗一直是媒介考古學的核心”[7],正是基于發現了歷史中那些異質的、被湮沒的聲音。媒介考古學需要返回到那些被遺忘的媒介現場,挖掘一度被冷落卻重要的媒介實踐。通過這種方式,不僅能思考過去與當下的媒介是否存在被忽視的聯系,而且有助于重估電影史觀。
也是因此,媒介考古學研究又展現出熱鬧與不安的一面。胡塔莫(Erkki Huhtamo)與帕里卡指出“對于媒介考古學的準則或術語,沒有達成共識”[8],這也是學界的基本態度。媒介考古學沒有一個標準的定義,它更不是一個學科概念,其理論來源、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方法是多元的。這令人聯想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方法各異的文化研究,還有喬納森·卡勒(Jonathan D.Culler)打破經典文學路徑的“野草文學觀”。有意思的是,媒介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與德勒茲在某種程度上不謀而合——作為創造概念的哲學家,德勒茲從未對“游牧”“塊莖”等概念下過定義;媒介考古學也可以被視為是一座解轄域化的高原,對于新/舊媒介亦沒有命名沖動,它不過是拾獲了主流歷史中那些被忽視的碎片。
媒介考古學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在挖掘被忽視的歷史的同時,不意味著要制造新與舊的對立。關于新舊媒介,有學者提出“蒸汽朋克”(steam punk)概念,認為這是一種“用‘過去媒介的主題、創意與思想’來研究當下所謂的‘新媒介’”[8](2)的藝術實踐。技術與媒介形式的變化影響電影語言的演進。然而,傳統攝像機屬于舊媒介,VR技術與AI技術屬于新媒介,VR技術創造VR影像,AI技術則生成AI影像——變化的是講故事的媒介形式,并非故事本身。相反,媒介的演進會更新電影語言與媒介展現形式,它們或許會為早期電影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如果能在新近的電影元素中發現過去媒介的“幽靈”。這也是福柯譜系學令人振奮的地方:那些斷裂的時刻,找到了。為了反對電影史的“敘事—樹根”系統而去尋找散落在電影史中的碎片,是為了解轄域化的“轄域化”。目的不是要生成新的霸權,而是連接當下與過去那些晦暗的地圖,一如德勒茲的塊莖“制圖”(map),強調一種開放和流動的生成思路。媒介考古學作為一種方法,展示了歷史的非線性和斷裂特性,也能在影像領域找到方法論的實踐。將媒介考古置于電影史的理論坐標中,可以發現,從媒介考古到電影媒介考古,新的電影史研究路徑正在生成。
二、“回溯—前瞻”的新電影史路徑
實際上,在媒介考古學的術語出現之前,媒介考古的實踐就已經存在了。早期電影媒介考古并不是從1895年開始的,需要我們考察19世紀往前的脈絡。[9]經典電影史沿著早期電影(19世紀末期的電影發明與早期實驗)、有聲電影到彩色電影的研究脈絡,而媒介考古學者認為還有多種進入電影史的方法,以此拓寬電影研究的廣度。媒體考古學將電影放在不同的脈絡,且證明這些不同的系譜學如何找到不同的出路。[10]
學者托馬斯·艾爾塞瑟(Thomas Elsaesser)把媒介考古學視為考察新電影史的方法。[11]當我們跳出當下電影史的框架,重新思考19世紀之前的電影發明,可以發現“電影”的概念一直處于生成之中,它是多樣的、異質的。在“作為作品與文本”的電影研究模式之外,還存在“電影作為事件和體驗”的早期電影實踐,它也需要被納入到電影研究中。首先,媒介考古學的早期電影研究路徑支撐得住電影史研究路徑;其次,這種路徑可以有效地理解新舊媒介之間的各種互動(融合或自我區分)。[11]經典電影以格里菲斯以來的敘事中心為主導,忽視了其中的“差異性”,而它們是電影史中不易被察覺的“刺點”。新電影史研究主要是從反對經典電影史的書寫方式開始的。
那么如何重寫電影史?艾爾塞瑟、湯姆·岡寧(Tom Gunning)、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等學者不約而同地將視線投向了早期電影。艾爾塞瑟認為,“通過展示早期電影的異質性(alterity)和差異性(otherness),同時也堅持其復雜性,就有可能證明標準電影史中存在的幼稚、不太有把握的或無資格的隱含概念”,湯姆·岡寧提出了“吸引力電影”(cinema of attractions 1986)[12]。新電影史研究打破了經典敘事傳統,使線性的歷史開始受到質疑。長期以來,敘事內核被認可為電影史研究的內在邏輯,而媒介考古學制造了斷裂的方法——它重返早期電影現場,試圖挖掘那些被遮蔽的、落滿歷史塵埃的媒介——以往的本體論前提是將電影視為一種非物質性(immaterial)的媒介,在新物質主義興起的當下,物質媒介被重新考量。福柯的“起源”幽靈勾勒了偶然的媒介與必然的返回,讓“運動—影像”(moving image)在早期電影的視覺吸引與雜耍中去尋找自己的位置。
關于媒介考古學視野下的新電影史,埃爾塞瑟提出三個維度:首先,介于目的論轉向與追溯因果關系之間的電影史(Media Archaeology I: Film History between Shifting Teleologies and Retroactive Causalities)[11];其次,家譜還是家族相似?(Media Archaeology II: Family Tree or Family Resemblance?)[11];最后,“電影是什么?”或“電影什么時候誕生?”(Media Archaeology III: What is Cinema or When is Cinema?)[11]。第一個維度是對媒介考古學方法論的考察。傳統電影史認為電影是一種有完整敘事能力的藝術形式,往往忽略了構成電影的諸多偶然性。當下的新電影史正處于從線性敘事到裝置/技術媒介/美術館的轉向,為電影史的家譜增加了多樣的闡釋空間,需要我們用反主體的方式看待電影史,用新媒介視角重估過去的電影史。
在第二個維度,艾爾塞瑟辨認了“家譜”與“家族相似”的概念。“家譜”承認電影史以線性敘事主導的本體論傳統,關注電影史中的因果關系,但面對數字化轉型下的影像生產,面對不斷壯大的媒介景觀,傳統電影史的論述是否穩固?于是,埃爾塞瑟用“家族相似”替代“家譜”的說法,電影并不起源于單一的源頭,電影史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物質網絡。福柯認為事件形成譜系,艾爾塞瑟接續了福柯,強調新電影史的重點不在“起源”(origin),而是更多地屬于“家族相似”(family relations)——事件屬于彼此,但從不隨意地或有目的地與彼此關聯[11]——因為電影史中還有圖像、聲音技術、巨型屏幕、3D眼鏡這些琳瑯滿目的媒介[11],它們被如今的電影史遺忘了。新電影史的任務是尋找這些“失敗”的媒介。除了福柯,我們還能在德勒茲和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那里找到解釋。德勒茲的“樹狀系統”[13]可以與“電影史”接上,而“塊莖”則與“新電影史”連接。黑格爾以后的現代哲學不再尋求主體與庇護,新電影史也對傳統電影史提出了質疑——德勒茲與媒介考古學的聯系竟然如此密切,恰是說明了媒介考古學“反對起源”的訴求(福柯與德勒茲的相遇)。艾爾塞瑟將組成電影的其他媒介當作電影家族的一部分,其實是強調了它與敘事傳統處于并列的位置。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放在這里恰如其分,即媒介與媒介之間有相似之處,卻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屬性(維特根斯坦與媒介考古學的相遇)。
第三個維度辨析“電影是什么”“電影什么時候誕生”,在前兩者基礎上引申出一個問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電影史?隨著技術的發展,“電影”的含義變得復雜,它不再僅僅作為影院電影出現,更是包括了視頻論文、VR影像、AI影像等多種媒介形態在內的影像。新電影史將電影視為一種不斷演進的媒介,勾勒出電影是一個超越敘事電影框架的生成過程。用經典電影時期的敘事模式理解早期電影是一種“誤讀”,“重新發現早期電影是繁復的視覺文化的一部分,有著自己的傳統、規則與邏輯。”[14]回顧19世紀早期電影時期,非線性敘事探索只是其中一部分內容,早期電影時期還包含實驗剪輯、視覺實驗、觀眾體驗等內容。譬如,喬治·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的作品經常呈現停機再拍、多重曝光等技術手段,以此創造斷裂的實驗敘事方式和令人驚奇的視覺創新效果。早期電影為后來以敘事為主流的電影史提供了靈感,也成為當代VR等媒介技術的先驅探索。“數字電影復蘇且重新建立了 19 世紀的生理光學,‘回到’魔術幻燈秀、全景畫和西洋鏡……”[10],以此為基點,返回考察早期電影及史前史中的光影實驗、幻影燈幻術、全景畫、立體鏡乃至活動電影放映機(Kinetoscope),它們解釋了電影的源頭可能是作為視覺文化的早期實踐。
最后,媒介考古學沿著“從現在追溯過去”而非“從過去到現在”的回溯路徑,是一種“回溯—前瞻”(analeptic- proleptic)式的關系。[15]從當下的新媒介視角回溯過去被遺忘的媒介現場,挖掘當下與過去的聯系,“回溯性地為過去之物賦予一種對當下的遠見”[14]。在電影數字化轉型的當下,媒介考古作為方法具有重要意義。媒介和技術的發展,膠片電影、引擎電影、VR影像和AI影像的應用,促使電影的語境變得更加開闊。我們在新的媒介形式中找到了早期電影的諸多影子。VR作為沉浸式媒介,對應了史前史中沉浸性的視覺文化;VR的非線性敘事結構,又指向早期電影實踐的循環結構、平行蒙太奇、超現實敘事等。
媒介考古學不僅關注媒介的演進,更關注媒介的創造,需要我們回到電影的“童年時期”去尋找散落在歷史中的早期媒介。以上論述媒介考古學的理論路徑、媒介考古學與電影考古學的關系,繼而論述媒介考古學視野中新媒介與舊媒介的關系,為論述VR作為新媒介去電影史尋找“舊媒介”做好了準備。
三、媒介演進:VR作為征兆
埃爾塞瑟設想了“數字化”(digitisation)的電影史轉向路徑。媒介考古的電影史,將“數字革命”視為一個電影史斷裂的時刻,它首先是一個技術甚至是美學問題。[11]影像不僅局限于古典敘事范式,更可容納多類型敘事以及作為身體在場的觀眾體驗——“虛擬現實”“互動性”“沉浸感”或許可以闡釋媒介考古觀念中的“電影”。[11]
VR的全稱是“virtual reality”,中文翻譯成“虛擬現實”。威廉·舍曼(William R.Sherman)曾作出定義:“VR是由交互式計算機模擬組成的媒介,可以感知參與者的位置與行動,并替將反饋代或增強為單一或多種感覺,從而給予人(虛擬世界的)沉浸式體驗或呈現在模擬中的感覺。”[16]史前史與早期電影為我們展示了物質/非物質的媒介雛形,而VR影像可能與它們存在著電影誕生以來最相似的家族關系。如果將VR媒介視為敘事工具之一,通過新媒介重新定義電影敘事,那么這不僅能挑戰傳統的古典敘事結構,而且也能建立一個以觀眾體驗為核心、意義連貫的新電影世界。VR作為考古征兆,可以沿著“回溯—前瞻”的思路尋找VR與史前史以及早期電影的聯系。于是我們發現,“早期電影”并沒有消失,只是以新的形式“存檔”下來。
首先,VR通過視覺機制營造沉浸感,它和早期視覺文化有相似的視覺邏輯。當我們重返巴贊,發現巴贊對于“完整電影”的預言是準確的,“一切使電影臻于完美的做法都無非是使電影接近它的起源”。[17]電影何種程度上是最接近現實?其實是對電影的真實性提出了要求。巴贊認為,19世紀以來至今,從照相術到新現實主義電影,所做的努力都是在復現一個“真實”的現實,這里面暗示了一個重要信息:沉浸感通過視覺機制建立。
從史前史到VR影像,沉浸感是視覺文化非常重要的體現,而現代電影體驗是一次“斷裂”,它用銀幕阻隔了觀眾身體與影像內容的聯系。VR的出現,繞開了作為偶然事件的現代電影,聯結了同樣作為偶然事件的數字時代新媒介與早期電影及史前史的視覺話題。
視覺文化在歐幾里得(Euclid)時期已經被提出,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出現了透視法(perspective)——在二維空間營造出三維空間的視覺層次。1662年,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發明了“魔術燈籠”(Magic lantern)(作為早期發明者之一),魔術燈籠是暗箱(camera obscura)、顯微鏡等多種光學裝置的結合,是現代電影的“鼻祖”之一。[18]1769年,施羅德費爾將他的萊比錫咖啡館改造成了一個“多媒體的、沉浸式的恐怖劇場”[19](151),主要制作方式是“用魔術燈籠將幽靈般的圖像投射到煙霧的窗簾上”[19](154),并且創造了一個不嚴格的觀影“劇場”,模擬出了與傳統電影的影院以及VR觀影場地相仿的觀影空間。1798年,埃蒂安·加斯帕爾·羅伯特(tienne-Gaspard Robert)首次表演了幻影展覽(Phantasmagoria)[20];保羅·菲利多(Paul Philidor)更新了魔術燈籠的觀看方式:將魔術燈籠放在輪子上,再將投影儀移到屏幕上,從而形成前所未有的視覺“幻影”(phantasmagoria)[19](156),視覺形象多以驚悚的幽靈影像為主,與VR影像強調的“沉浸感”不謀而合。
“全景”(Panorama)的發現為VR影像找到了新的視覺媒介支撐。最初的全景圖是360度的圓柱畫,觀看者身處其中,可以看到全方位的“虛擬世界”。[21]1787年,蘇格蘭畫家羅伯特·巴克(Robert Barker)在愛丁堡的卡爾頓山山頂眺望城市時忽然意識到,如果以一個固定點為中心軸,畫多幅360度角度下的局部風景畫,然后拼貼成整體,利用視覺差形成一個立體的全景畫[19](163),這是全景概念的最初實踐——盡管再早幾年,倫敦已經出現了全景單幅畫展。[22]
VR中的全景如何生成?觀眾戴上VR頭顯,便可以在虛擬空間與影像進行互動,獲得沉浸體驗。18世紀全景的發現,可被視為是VR全景的早期實踐,它們都通過全景空間的確立、視覺沉浸機制的建立將觀眾帶入作為體驗的世界。如果說CG技術還停留在數字電影制作層面,UE、Unity引擎已經創造了一個逼真的虛擬世界/環境。至此,VR與史前史中兩個重要的視覺元素產生聯系——沉浸感與全景,兩者在視覺機制層面達成了共識。
在媒介譜系中,兩個媒介或許可被視為VR眼鏡的“鼻祖”,其中一個是立體鏡(stereoscope)。巴贊援引電影史學家波托尼埃,認為立體鏡的發明(而不是照相術),將“立體感”放進了活動影像中。[16]立體鏡由查爾斯·惠斯通(Charles Wheatstone)發明,原理是利用兩個透鏡制造視覺差,形成虛擬的三維空間;VR眼鏡也有兩片中間厚、兩邊薄的凸透鏡,利用視覺差增強畫面的縱深感,且依賴于飽和梯度與表面飽和度。[20](49)VR是早期立體鏡的三維成像技術演進。另一個媒介是西洋鏡(peepshow),它按照光學原理在一個空間內重疊畫面形成縱深效果,與VR追求的沉浸感是一致的。不過,和立體鏡360度環繞的空間感不同,西洋鏡是在單一平面制造出三維效果。作為與電影誕生息息相關的早期媒介,盡管它們在技術上沒有到達巴贊認為的足以支配電影發明的程度,沒有像照相術與留聲機那樣機械復制現實的能力,但無論是從視覺機制這樣的虛擬媒介還是物質媒介考察,早期媒介與VR技術的關系,似乎比傳統電影有更多的家族相似屬性。
其次,從VR影像內容創作來看,它和早期電影存在相似的“吸引力”。湯姆·岡寧(Tom Gunning)將1907年之前早期電影的觀念命名為“吸引力電影”(Cinema of Attractions)。岡寧發現,奇觀元素較之敘事元素在早期電影中占據更大的作用,而它一直都被后來的電影史忽略了。到了愛森斯坦這里,“吸引力蒙太奇”(Montage of Attraction)可以視為是梅里愛“停機再拍”的演進,它將隨機的、獨立的段落組合成新的段落,與VR的表達是相同的:營造驚奇感,給觀眾帶來視覺上的吸引力。如湯姆·岡寧所言,“最早的電影研究出現在政治激進的電影俱樂部和先鋒藝術雜志上,為的是探詢新媒介蘊含的潛力”[23],史前史中的“幻影”與VR的沉浸感相似,早期電影的奇觀特征與VR早期的奇觀特征相似,這不禁讓人思考,VR是否能通過吸引力建立與早期電影的聯系,繼而成為媒介考古學的材料之一?
齊林斯基認為,“有一種可能性開辟了一種非常特殊的實驗空間,這種可能性是能夠通過對過去的‘現時’進行思考、夢想、草擬和配置,使之進入未來的‘現時’(through past presents into those of the future)”[24],他稱其為“未來考古學”(prospective archaeology)。[23]“未來考古學(prospective archaeology)重構古老的媒介機器以期獲知過去以及可能的未來。”[9]假設VR加入,將產生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隨著越來越多新媒介的涌入,我們是否要重估電影史?VR是電影史的延續還是“延異”(德里達)?
由于新技術(VR技術)的出現,那些散落在歷史各處的媒介重新被當下拾取,進入了一個非線性書寫的歷史中。換句話說,VR作為面向未來的技術,卻不斷地從過去得到材料印證,它拾取了過去的“檔案”,讓我們在一次次“電影終結論”的哀調中找到了一絲感知過去的信心。然而,這不代表我們必須無盡地從過去尋找資源,從更長遠的未來回望,或許VR本身還會成為未來技術緬懷的“鄉愁”,成為一份重要的考古媒介。
VR用數字化(digitisation)生成新的檔案,是否也暗示了,這份檔案同時要承擔某種“遲緩”的衰老?“數字化”不僅意味著當下,也意味著將有更新的“當下”取代當下。首先,在技術上,老生常談的“電影之死”話題,展現了影像本體論層面的焦慮,格林納威(Peter Greenaway)感性的發言自不用說,桑塔格(Susan Sontag)、弗朗西斯科·卡塞蒂(Francesco Casetti)等學者不斷地提示著同時代的人們,技術發展是技術自身最大的“敵人”。他們無法預料如今的影像已經要進入三維空間討論了——同樣地,我們也無法預料未來的影像技術將朝向何方發展。
VR尋找的不是電影發明至今的觀影姿態,它穿過了線性的塵埃,與20世紀初期的某種短暫的觀影儀式遙相呼應。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出現了全景與電影技術融合的觀影方式,被稱為Cine’orama,具體表現在用人工的方式,同時將10卷70mm的膠片投影到圓形的天花板上,以形成一個人工拼貼而成的360度圖像。[25]再往后的媒介檔案中,Cine’orama幾乎是消失了,某種程度上Cine’orama屬于“失敗的媒介”,但VR的觀影方式與其竟有相似的聯系。桑塔格的傷感還停留在對電影院迷影氛圍的眷戀上,這份質樸的儀式感放到當下依然是成立的,但缺少了無可避免的局限性。尼采在提出“以身體為準繩”[26]時,不會預料到科技將與身體產生如此密切的聯系。身體在遭遇幾千年的冷落后,由尼采塑造了它的理論姿態,現在身體又在科技的進階中獲得了新的闡釋空間。由于影院物質空間與周圍觀眾的存在,人與傳統電影形成了自覺的觀看關系的阻隔,并且傳統電影的銀幕制造的是二維空間;然而,VR讓作為觀影主體的人與VR技術互為融合。在觀看一部VR作品時,觀眾帶上VR眼鏡,如果有需要調整畫面與人眼的觀看比例,并在系統提示中按下“開始”按鍵。被固定在電影院的觀眾,與坐在椅子上/站立旋轉360度的觀眾,最明顯的區別在于身體的伸展程度。VR技術前所未有地將身體推向了數字身體。在這個層面上,VR比Cine’orama多了一層身體美學的遞進:身體超越物質身體,成為一個可以被塑造的主體事件,完成了從理論賽博格到實踐賽博格的轉向。
最后,回到媒介考古學。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投射了人對世界的認識不過是幻象,從壁畫、雕塑到后來的電影,創造的也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巴贊所言的“現實的漸近線”。VR能創造一個最接近真實的世界嗎?在數字時代回應這類問題總是顯得著急。VR暫時不會“完成”,它在諸多物質媒介與虛擬媒介上找到了歷史的幽靈,也會因為親緣性被后來者考據——雖然我們無法準確給出未來影像的發展形態。
綜上所述,19世紀的光學原理、史前史早期電影中,藏著VR的媒介、媒介雛形或媒介設想,因此存在從VR進入媒介考古的可能性。在此意義上,重新書寫電影史變得可行。VR作為媒介考古學的征兆,或許會為媒介轉向提供更多啟發。
四、結 語
媒介考古為電影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VR作為新媒介去電影史中尋找“舊媒介”,代表了媒介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VR技術通過其沉浸式體驗,將觀眾帶入一個全新的視聽世界,但我們也看到過去媒介技術的影子——早期電影的敘事技巧、鏡頭語言、觀眾互動方式,都在新媒介中得到了延續和重構。將VR視為媒介考古的一環,我們找到了魔術燈籠、全景原理、立體鏡、西洋鏡乃至“吸引力”等物質媒介或設想,這些給了VR一種可建立且可被辨認的家族“血統”。如果說VR的媒介考古學路徑存在必要,那就是既能用“懷舊”的方式確立VR影像的身份坐標之一,也為媒介考古學提供一個回溯的思路:我們往往在舊媒介中尋找新的可能性,也能在新媒介中重拾過去的影子。更進一步,我們或許會提早感知到VR作為檔案的“鄉愁”。
參考文獻:
[1]施暢.視舊如新:媒介考古學的興起及其問題意識 [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7):33-53.
[2][德]瓦爾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 [M].李雙志,蘇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33.
[3]Foucault, M.(2019).On the ways of writing history In James,D.F.(eds.).trans.Robert, H.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2.New York: New Press, 289-290.
[4][法]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學 [A].尼采在西方 [C].蘇力,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279-305.
[5]Kittler, F.A.(1999).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US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楊北辰.“新物質主義”視野下的電影媒介考古學 [J].電影藝術,2018(3):11-17.
[7]Parikka, J.(2013).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New Jersey: John Wiley amp; Sons.
[8]Huhtamo, E.amp; Parikka, J .(2011).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唐宏峰,楊旖旎.媒介考古學:概念與方法——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訪談 [J].電影藝術,2020(1):125-132.
[10][德]托瑪斯·埃爾塞瑟.媒體考古學作為征兆(下)[J].于昌民,譯.電影藝術,2017(2):117-124.
[11]Elsaesser, T.(2004).The new film history as media archaeology.Cinémas,14(2): 75-117.
[12][美]湯姆·岡寧.吸引力電影:早期電影及其觀眾與先鋒派[J].范倍,譯.電影藝術,2009(2):61-65.
[13]Deleuze, G.amp; Guattari, F.(1977).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4][德]托瑪斯·埃爾塞瑟.媒體考古學作為征兆(上)[J].于昌民,譯.電影藝術,2017(1):75-83.
[15][德]托馬斯·埃爾塞瑟.媒介考源學視野下的電影——托馬斯·埃爾塞瑟訪談 [J].李洋,黃兆杰,譯.電影藝術,2018(3):111-117.
[16]Sherman, W.R. amp; Craig, A.B.(2018).Understanding virtual reality: Interface, application, and design.San Francisco: Morgan Kaufmann.
[17][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 [M].崔君衍,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16.
[18]Vermeir, K.(2005).The magic of the magic lantern (1660–1700): On analogical demonstration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invisible.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38(2): 127-159.
[19]Johnson, S.(2016).Wonderland: How play made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Pan Macmillan.
[20]Castle, T.(1988).Phantasmagoria: Spectral technology and the metaphorics of modern reverie.Critical inquiry,15(1): 26-61.
[21]Hillis, K.(1999).Digital sensations: Space, identity, and embodiment in virtual reality(Vol.1).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2]Huhtamo, E.(2013).Illusions in motion: Media archaeology of the moving panorama and related spectacles.Cambridge: Mit Press.
[23][美]湯姆·甘寧.現代性與電影:一種震驚與循流的文化 [J].劉宇清,譯.電影藝術,2010(2):101-108.
[24][德]齊格弗里德·齊林斯基.未來考古學:在媒介的深層時間中旅行 [J].唐宏峰,呂凱源,譯.當代電影,2020(4):42-48.
[25]Grau, O.(2004).Virtual art: From illusion to immersion.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6][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權力意志 [M].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56 .
[責任編輯:華曉紅]
基金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虛擬現實影像賦能上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2023ZWY003);上海師范大學青年跨學科創新團隊校級培育項目“生成式AI的多模態藝術實踐和本體問題研究”。
作者簡介:鐘芝紅,女,講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