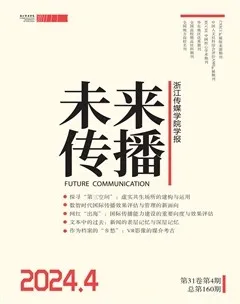何以為記:微博逝者空間的中介化記憶生產




摘 要:媒介技術更迭使生與死之間出現新的連接可能性,從數字記憶中介化起點出發,文章擺脫把研究對象瞄準為公眾人物或普通人物等某個群體的窄化視角,轉向探究逝者賬號空間的網絡悼念和記憶生產的普遍性邏輯。當技術可以協助逝者實現某種程度的“在線永生”和數字來世時,如何理解這些存在于媒介中的“數字幽靈”和平臺可供性下悼念觀念及儀式的變化,如何闡釋網民在紀念逝者過程中的社區形成及其規則。研究發現:微博平臺使個體悼念面臨“中介化記憶”下的新型生產方式和呈現樣態,在數字化的助記意象、協商式的記憶生產、新記憶景觀下的悼念等級和悼念社區規則等方面重構了“記憶之場”,進而獲得挑戰傳統記憶代理和模式的巨大潛力。
關鍵詞:中介化;社交媒體;悼念;新靈媒
中圖分類號:G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4-0091-09
一、問題的提出及研究方法
“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哲學命題尚未迎來答案,我們如何“被記憶”“被復活”卻有了新的討論方向。社交媒體平臺上現存大量逝者賬號并呈現蓬勃的增長趨勢,[1]從中介化視角來看,平臺正在“充當勾連生死疊合的技術通道”[2],國內外社交媒體如微博、B站、微信小程序、Facebook、Insgram等,正在改變我們的死亡哀悼文化及記憶方式。盡管公眾人物的數字哀悼研究對于理解公共議程和大眾文化有其獨特價值,但媒介可供性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成為哀悼空間的主體,[3]社交平臺每一個逝者賬號構成了賽博時代荒原上一個個“數字墓碑”[4]。在此意義上,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這些存在于媒介技術之中的“數字幽靈”?如何勾連人類死亡、在線悼念與數字媒介的深層關系?如何闡釋被技術中介化后了的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如何把握悼念社區內的交際行為及情感規則?
立足于特定案例的相關性和對研究的預期貢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對“中介化記憶生產”的理論視角提供輔助,本文對新浪微博逝者賬號采用“強度抽樣”方法,[5]最終確定對20個逝者賬號最后一條博文的網民評論數據進行采集。方法路徑為:基于網絡爬蟲獲取網頁內容,將非結構化數據通過網頁解析庫進行結構化保存,最終對數據清洗后得到有效數據2,739,755條數據。熱度趨勢按照回復時間進行分組統計評論數量;熱詞分布對所有評論內容基于前綴詞典實現高效的詞圖掃描,生成句子中漢字所有可能成詞情況所構成的有向無環圖(DAG),找出基于詞頻的最大切分組合;表情量化基于標簽識別庫對結構化后的文本實現掃描并識別出所有表情符號,并按出現頻率由高到低輸出。
二、文獻綜述
(一)生死關系及哀悼儀式的演變
漫長的歷史演變使中西方形成各自包含有死亡觀念、樣式、哀悼、禮俗、喪葬等在內的死亡文化。但不管哪種文化語境里,普遍推崇借助某種“巫”或“靈媒”讓生者與死者要保持精神聯系的同時,給予生者走出當下現實困境的方向和路徑指引,人們的死亡觀念和哀悼儀式在社會文化的深層結構也在發生變化。西方對生死關系的態度方面在過去兩千年里有若干重大轉變,有學者[6]認為首先是“馴服死亡”階段。中世紀早期的西方人認為,死亡對于生者來說是熟悉友善的。晚近時期,死亡成為一種只能在特定場合、特定時間甚至特定人群中談論的“禁忌話題”。而到互聯網時代,人們對待死亡的態度再次發生轉向。Walter就生死關系延展提出傳統、現代和后現代三階段,他認為在現代社會,私人和公共生活相對孤立地存在,對喪親的悲傷被定義為私人經歷導致哀悼者身份被隱藏,成為其他人可以“支持”但難以分享的東西,而后現代社會中,喪親者的私人感覺成為可共享的內容。[7]如Kern等人發現Facebook R.I.P.頁面逐漸成為一個在公共空間里生者與死者進行交流的地方,[8]以往這種在社區內私下進行的哀悼變得更為公開,在線哀悼的出現打破了維多利亞時代對死亡和悲傷的隔離。[9]
中國圍繞廣博深邃的死亡觀念衍生出各類圍繞死亡進行的活動、制度和操作,共同構成豐富獨特的死亡文化[10]。古人常把生死關聯起來的觀念依然影響今人,儒家所倡導“生生不息”的精神內核中向來推崇生死相通、以死為安的生命哲學,如“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王充,漢代,《論衡》卷八《道虛》)。在儒家死亡哲學中,“死亡”本就被包容在生死接續的脈絡中,它是衡量宇宙本體、社會秩序和人生法則的重要尺度。儒家之外,我國生死文化中還融有道家“死而不亡”和佛教“死后新生”的關系視角,這些觀念所推崇的道德價值、精神意識和個體品質,指導國人用有限的生命完成對死亡的超越和連接之外,更強調通過一系列死亡禮俗/儀式使生者與死者進行對話,不僅通過“遵禮成服”等相關儀式表達哀思,更是用以社會教化、明晰等級秩序。到近現代,我國一系列繁復的喪葬悼念習俗儀式深受西方影響,諸多象征性悼念方式也大大簡化,但旨在與死者亡靈保持和建立一種特殊密切關系的努力依然存在于文化基因里。
(二)媒介技術基礎之上的“記憶術”變遷
與死亡觀念、悼念儀式不斷發生演變的動態軌跡類似,人們的記憶技術也隨媒介技術更迭而發生變化。勒高夫[11]確定了記憶歷史上4個不同時期,分別是史前口述記憶、文字系統記憶、印刷機時代的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記憶,以及20世紀電子媒介的系統記憶。諾拉從“記憶地點”的概念出發討論某些物體或事件在某些群體記憶中可能具有的特殊意義,其中記憶場所(sites of memory)成為“記憶結晶和隱匿自身”的地方。[12]考慮到當下網絡的普遍性,有學者認為日常交流和長期記憶空間可能會強烈地交互,并且兩者之間的界限也會變得更加模糊進而出現“浮動的間隙”(floating gap)[13]。這意味著附著在平臺的社交媒體除了可以發揮記憶存儲場所的作用之外,還可以促進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的溝通、談判和協商,個體不同的網絡回憶甚至可以重塑其所承載的集體記憶,從而改變記憶的生產方式。
當前國內對網民利用社交媒體表達哀思、形成記憶等現象的研究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領域。有學者論及社交媒體如何成為公眾人物集體悼念的空間,通過悼念內容分析人們的哀痛過程;[14]也有學者側重分析公眾人物的遺留性社交媒體賬號如何成為一個獨特的集體哀悼空間,提出基于特定時間生成的“集體哀悼空間”在熱點時刻結束后的延續如何成為一種“延展性情感空間”(extended affective space),考察此種“持續性聯結”對記憶主客體影響的新意涵。[15]但值得注意的是數字公墓不僅“安葬”社會名流,也“安葬”普通人[16]。這必然會帶來一個繼續追問的契口,即在更加普遍意義上,社交媒體如何通過中介化重構在線悼念和情感公眾的日常行為。換言之,社交媒體如何借助平臺可供性潛入日常悼念和個人記憶實踐中,并促使聯結行為的發生。
(三)個人墓志銘的“中介化”書寫
繼民族國家、大眾媒體之后,社交媒體平臺成為新型的記憶代理。雖然數字化的記憶研究剛剛起步,但對快速發展的中介化記憶和哀悼領域的拓展在近年來一系列成果[17]中得到最好的體現。如媒體中的數字記憶、數字中介的連接行動、自拍文化與紀念等。埃爾等學者[18]認為不存在普遍記憶,并強調了“記憶社區”(communities of memory)的多元性,當代社會中每個群體都可以借助某種中介構成或被構成不同的記憶,當前的記憶文化是高度中介化的,因為生活的所有維度,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的都是中介的。[19]在此意義上記憶與媒介之間的關系都建立在媒介與紀念過程之間關系的基礎之上。與面對面的社會交往和互動不同,中介化傳播作為經由媒體所中介的人類交往過程,促使人類思考當死亡被數字媒介所中介,其為數字化死亡打開的諸多學術想象,[20]考慮到社交媒體造成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在空間和時間中的結構化變遷,已有不少關于中介化記憶方面的成果:[21]在研究主體方面側重主導敘事及記憶的民族國家,研究客體側重重大歷史事件、創傷事件等,研究落腳點側重媒介對記憶建構、身份認同的影響。而事實上,網民對普通逝者個體的在線悼念及所產生的記憶現象層出不窮,但相較而言國內學界理論關注卻顯不足。對于本文研究初衷而言,不論是普通公眾還是公眾人物,當個體死亡之后并未真正完全消失,而是脫離“沉重的肉身”繼續出現在傳播實踐中,雖然無法真正作為主體與生者進行交流,但其仍在被不斷被建構、被延伸。因此,本文秉有這樣一種好奇心,即生者在對逝者追憶過程被社交媒體平臺中介化之后,“他者”是如何續寫逝者的“數字墓志銘”?
三、在線哀悼中的“中介化記憶”生產實踐
(一)樣本采集情況
從表1可以看出采集20個微博逝者賬號的年齡分布在17—76歲,微博粉絲數最少的不到一萬,最多的有一千多萬,根據微博數據可獲得性角度出發,爬取時長從1年到6年不等。20位逝者死因主要有四類:一是因突發意外導致死亡,如KobeBryant、高以翔Godfrey等。二是因某種難以治愈的疾病導致死亡,如xiaolwl、熊頓XD、姚貝娜等。三是自殺,樣本中多數自殺逝者都患有抑郁癥,雖然抑郁癥也屬于一種疾病,但是采取自殺方式主動結束生命的逝者死因與因癌癥不治導致去世存在很大不同,其中會牽涉網絡暴力、工作或學習壓力等,如劉學州a、鹿道森、雪莉_official、旅行的孤獨風等。第四類死因不詳,筆者并未能從公開文件進行判斷,如本兮等。總體而言,20位逝者職業、年齡、粉絲數都存在較大差異,相似之處在于這些賬號最后一條微博評論都能引發網民大量的自發悼念。
(二)數據處理及研究發現
從2014年11月27日到2022年1月24日,20位逝者最后一條微博發布時間不一。從圖1可以看出,不管原有粉絲量多少和身份職業為何,每個逝者賬號最后一條微博的評論區基本都會面臨至少一次留言量的陡增、延續和平緩。隨時間推進,網絡緬懷與悼念的網絡評論逐漸減少,這一現象也回應了學者們的既往研究。Savin Baden[22]提出演化性聯結(evolving bonds)的概念來表明生者與逝者的持續性聯結實踐會隨著時間及媒介使用方式的變化而變化。哀悼者的評論頻率會隨時間推移而下降,但評論數量又會在逝者的死亡紀念日、生日等特殊節日顯著增加,這意味著粉絲“突然想起你(逝者)”的悼念行為會遵循一套記憶觸發的獨特邏輯和機制。在這一意義上,無論逝者主體是公眾人物還是普通小人物并無明顯區別。一般而言,網民對微博逝者賬號的記憶觸發有以下幾種類型:如情感觸發(高興、憤怒、郁悶等不同的心情都會刺激對逝者的回想);事件觸發(通常是日常生活中正在經歷的某件事使生者想起逝者);事物觸發(通常指粉絲看到某種有形事物想起逝者);他人觸發(通常由與逝者去世原因相關相似的其他人引發粉絲對逝者的追憶);時間觸發(通常在生日、清明節、周年忌日等時間節點對逝者進行悼念)。Kanhabua等人[23]曾就觸發重溫過去事件行為的過程進行研究,發現不同的觸發類型具有不同的記憶特征。但記憶的遺忘機制依然在起作用,隨著時間流逝網民對逝者的留言不斷減少。即便如此,在線悼念依然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持續性聯結”,不管何時何地,一旦記憶的觸發機制開啟,生者幾乎可以通過網絡與逝者進行“單向對話”、與“同圈”進行交流分享。
1.數字化的助記意象
2015年,《牛津詞典》把笑哭表情包評選為“年度熱詞”,有學者認為這標志著人際交流甚至人類認知范式已發生徹底轉變。[24]社交媒體催生了作為數字實踐之一的表情符書寫行為,個人可以利用表情符號在不同社交場景中創造新意義。從構成性上來看,作為一種新“溝通語言”的表情符,是悼念空間中介化記憶的重要組成元素,也是對感覺、想法、實體、狀態或活動的一種視覺呈現方式。[25]從設計角度和功能角度來看,表情符通常分為兩類:日常溝通用語,如謝謝、愛心等,常用來調節對話節奏,能夠代替面對面交流時的面部表情或者文字交流時相應的標點符號;另一類是用于特定場景的符號,如悼念、生日快樂、節日祝詞等,可以輔助傳遞更多情緒。此外,表情符使用還受代際、文化、地域和平臺差異的影響具有多元的“解碼”版本。作為表達情感的有力方式,同一表情包在微博逝者悼念區展現出與其他社交場景不同的意涵,如鮮花、愛心等表情符在悼念場景中獲得了思念、祈禱的視覺隱喻。在273萬多條評論內容中,使用表情符數量排名前十的表情包如圖2所示,分別為愛心、淚、蠟燭、鮮花、悲傷、愛你、抱抱、月亮、失望、傷心,這十種表情符多是粉絲為表達對逝者去世的哀傷與思念,網民使用數量最多的Top10表情符也享有更多共同的情感承載功能。
即便在文字詞語中夾雜不同類別的表情包,留言者們通常會擁有對悼念場景共通的意義理解空間,其他網民也可以對接這種“語碼轉換”。除了Top10表情符之外,網民還利用想象力和平臺可供性創造出更多其他數字化助記符號。那些使用數量相對較少且看似與悼念不相關的表情符顯示出留言者更復雜的心理動機、情感狀態以及個性化的獨特記憶。堅持1072天在@KobeBryant評論區留言的“@小樊今天見到杰杰子了嗎”留言道:(受平臺系統和輸入法影響,還可轉譯為:,意為:科比和女兒Gigi安息),這樣一串主要由表情和英文文字構成的數字悼念符號重新定義了一種新語言,這一“逝者安息”的簡短碑銘透露出關于科比成長、父愛等更為豐富的信息,鮮花、愛心、手勢等常用表情符在此留言區構成了一種只有了解Kobe及籃球的圈層才能“秒懂”其含義的表達。同樣在@“離燈_冬眠mode關閉失敗”評論區,網民@風蕭水微寒在評論區發文“你輕輕的走了,跨過了緊鎖的大門,你應該在自己選擇的自由里永生”,文字末尾配上這樣一串包含蠟燭、蛋糕、禮物盒子、飲料、游戲機和電腦等14個表情符,這些看似平常的符號被有意選擇排列后呈現出“數字挽聯”的意涵,8根蠟燭左右對稱排布,而與年輕逝者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意象(飲料、游戲機、電腦等)擺置其中。這些數字化助記意象通過創造性的語法體系,在生者與逝者、生者與生者之間建立起新的社會關系。多位逝者都擁有與其生前生活或工作密切相關的表情符,并被賦予獨一無二的意義,@熊頓XD的專屬表情為小熊頭,用來呼應其筆名和逝者外貌特征;@趙英俊是瀟灑哥的專屬表情符是小紅花,用來呼應逝者曾創作的歌曲《送你一朵小紅花》。總之,網民可以通過遍布在社交媒體上“各種各樣的助記符產品和實踐(mnemonic products and practices)[18](187)“表情”“達意”,從而完成對逝者的數字悼念和記憶。
2.協商式的逝者記憶生產邏輯
已經去世的人在網絡上“被維系”著自己的形象,而這種形象是生動而豐富的。[26]網民對逝者的追思和悼念凝結為記憶的過程在動態中不斷分離、交織和融合,從而在三個層面上展現出協商式的逝者記憶生產邏輯。從悼念對象來看,逝者形象趨向復調呈現。微博留言者作為一個個“記憶的微光”擁有對逝者不同的映照側面,并拼湊出區別于逝者本來形象的悼念對象。網民在悼念逝者過程中雖然不斷回想和發現過往,但這一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反映網民的當下需求,因為記憶總是重構過去、建構現在,[27]可以說網民在逝者空間不斷討論、重塑的逝者形象和身份,重新構筑了理解過往和當下經驗的基礎。一個來自福建的男孩在2022年12月16日凌晨留言:“霍金,我希望有個能滿足我一切幻想的好女孩出現,結婚生子,幸福一生(雙手合十表情符)”,這樣的訴求將霍金本人從物理學家的身份中剝離出來,抽象為一個可以幫助網民實現愿望的符號和精神寄托載體。個體正是通過各種記憶、經歷、情節等敘事組裝進而生產各種各樣的身份,而恰恰是這種被敘事和表達不斷建構的身份形象與記憶之間存在著隱秘而深層的聯系。[28]從中介功能來看,對逝者的記憶生產趨向“去中心化”。在數字時代,不管是國家記憶還是個體記憶,都要更加依賴網絡,其不確定性和瞬息萬變的特點讓數字記憶擺脫了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傳統路徑,[29]而是以一種流動的、“去中心化”方式模糊個體與集體的記憶邊界,越來越傾向于“協商式”記憶的生產邏輯。不僅僅是李文亮這樣具有很強公共性符號人物的去世會讓網民自發主動留言,文中其他逝者賬號都會匯聚起龐大規模的網民,如雪莉這樣一位生前極具爭議性的女孩,其去世之后的微博評論區得到了粉絲的持續悼念和趨近完美的想象,粉絲毫不保留地在雪莉賬號評論區傾訴愛與思念,但更多的還是分享個人心情、學習和生活狀態,從而構成帶有悼念、分享和討論等多種功能的在線社區。從記憶特征來看,社會短期記憶呈現一種新形態。阿斯曼意義上基于日常交流所有形式的集體記憶都可被視為與同時代人共享的社會短期記憶,它的特點是不拘形式、高度的非專業化、角色的互惠性、無序性和主題的不穩定性。與由民族國家、權力組織等所構筑的長期穩定的集體記憶相比,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所有討論和分享都屬于短期的交際記憶范疇,網民留言動機具有相對隨意性,網民之間安慰分享存在精神甚至實質層面的互惠性。這種看似日常交流形式的群體記憶是基于個體表達自我和社交需求產生的互惠記憶,既針對自己也針對同圈層的其他人,留言者往往能由人到己、推己及人。但這種幾乎沒有秩序引導者的記憶不完全屬于阿斯曼所劃分的類型,緣于在線悼念場景中的主題較為集中,并且看似不拘形式的表達實則受到平臺規則所限,因為所有的意象符號都必須在其可供性前提下進行。
3.新記憶景觀的悼念等級
網絡不斷鞏固自己拓展記憶歷史階段的決定性技術地位,其功能和可供性支持鼓勵新記憶景觀的產生。我國傳統社會中的悼念與祭祀,會根據親屬關系的親疏遠近劃定不同等級的“五服”制度完成對逝者的儀式化哀悼和紀念。但微博悼念社區的親疏遠近等級有其自身獨特的排序邏輯,其悼念社區的親密關系等級主要有兩個評價標準:一是根據評論次數多少來判斷網民對逝者的情感聯結程度。“好久沒來(鹿道森微博),評論區有好多老面孔”(在北還是在南,2022-10-20),而“新老面孔”主要是以網民在評論區的留言頻率進行評價。在20位逝者中,有“鐵粉”平均每天在評論區留下數字痕跡(見圖3),留言最多的是姚貝娜評論區,兩年之間有粉絲留下一萬多條評論。正是成千上萬條的評論幾乎可還原出現實生活中這些鮮活個體的方方面面。除了日常問候,粉絲也會因為心情不好、追劇等日常小事來和逝者分享,在把逝者微博評論區當作“情感樹洞”的同時也和其他網友交流分享。但值得注意的是留言者日復一日的日常問候,雖然偏向日常但并不意味著留言者隨意為之,反之鑒于表達習慣和偏好,反而體現出對逝者更深厚的情感寄托和精神依賴。如有粉絲(@可能如金留言2541次)在Kobe評論區內的粉絲堅持每天在其評論區問候三次:老大早上好、中午好、晚安。鹿道森評論區的兩位高評論粉絲300多天每天不間斷道:早安、晚安。高以翔評論區留言最多的粉絲@本草有情薪火相傳(3年3631條)每天重復同一句表白:我愛你一生一世,早安晚安。二是根據留言者的現實知名度來判斷生者與逝者的親密度。網民會因知名度高的公眾人物或圈內大V在逝者留言者的活躍為其“拓寬樓層”,并判定其悼念或表達思念逝者行為的合理性。如岳云鵬和大鵬是@趙英俊的生前好友,他們的評論常常引來更多網民的圍觀和贊賞。同樣,不知名的網民會因“攀附”與逝者的親近關系而受到粉絲譴責,如一位不見經傳的體育博主貼出和高以翔一起用餐的合影時招致其他粉絲的反感:“請給逝者尊重”“你想表達你很了不起嗎”。不管是根據普通網民留言頻率,還是根據現實社會地位所判定的悼念等級都構成了一種新的記憶景觀。
4.悼念社區規則及“巨魔行為”
Pentzold[30]認為網絡不能被理解為一種一致性媒介,而應該被視作促進不同交流互動形式的潛在基礎,同時記憶工作不能再被分為私人的、小圈子的、無中介的話語。與傳統原始記憶媒介相比,網絡觸發記憶的根本差異在于開放性、公共性和流動性,這些基本規則賦予了記憶行為在既定場所和場合之外的存在。首先,人一旦死去,其符號價值也不再具有個人屬性,而是成為一種“開源代碼”被陌生且悲傷的網民靈活征用。其次,逝者賬號會因為死因契合某種社會情緒或網民心理被延展至公共領域,死亡悼念也不再是私人的、小范圍的,而是可以作為一種社會話題,甚至是流行標簽傳播開去。網民借此從不同層次去討論涉及更大社會范圍的議題,如追星與青年價值觀、抑郁癥如何面對和治療等等。最后,網民對逝者的記憶心理動機會隨時間發生改變,逝者微博賬號評論往往從悲傷共情到情感樹洞再到公域分享,但在這一交織復合的過程中逝者形象和身份得以再建構。因此社交媒體使新的記憶模式發揮作用,它不僅提供詞匯化材料的存檔,而且還提供大量潛在的對話伙伴。這些文本可能不僅是存儲記憶的一部分,也是“功能”記憶的一部分,因為它們被記住并以活的、互文性的形式與其他文本聯系在一起。
逝者評論區作為悼念與記憶社區而存在,留言網民利用評論—回復的方式會圍繞逝者相關信息型塑出一個個次級社區,如“離燈”評論區對親子關系、原生家庭、網絡游戲等進行延展性討論。評論樓層既可以是悼念社區,也可以是協商交際的行動小組。當劉學州最后一條微博發出5分鐘后,覺察到有可能自殺的粉絲開始自發組成“營救小組”,雖然沒有清晰的行動方案和組織流程,但陌生網民在“留言—回復”的互動中構成一種新型集體行動。鹿島森留言區有一位同為攝影博主的“微瀾Mag”一夜未睡,將舟山公安局、地方派出所的動態及時告知其他憂心的網民;“旅行的孤獨風”同樣促成營救行動小組的迅速匯集,微博網友不斷@北京警方,一起行動尋找并試圖挽救其生命,在此過程中意見領袖和普通網民組建起目標一致的協同行動小組。逝者悼念社區同樣會遭到溢出悼念范疇的“巨魔行為”,“出言不遜者”通常會帶來悼念氛圍的消解,引發網民之間的對立與沖突。如鹿道森是劉學州的唯一關注對象,并點贊過鹿島森的微博,有網民將劉學州的死亡視為模仿自殺的“維特效應”,顯然這種說辭觸犯到了鹿島森的粉絲,進而引發兩個群體的對立,繼而有粉絲號召他人一起網暴“網暴者”。面對因催婚和玩游戲自殺的“離燈”逝去,評論區的“理中客”言論受到部分網民激烈反對。又因為“離燈”點贊過兩篇討厭肖戰的微博成為肖戰粉絲攻擊的對象,“不喜歡肖戰的都該死,一個一個排隊等死”,圍繞“追星”評論樓層空間轉而變成“罵戰區”。對悼念空間所蘊含的社會心態、負面情緒生成和傳播以及暴力因素的放大將是值得拓展的研究方向。
四、討論與不足
媒介技術的更新迭代使生死之間出現了連接的更多可能性。空間維度上,社交媒體的逝者存在數字世界中某一“中間地帶”,既不是過去人們想象的天堂地獄,也非肉體存在的現實世界。時間維度上,由于某些共通人類情感的永恒性,這些逝者也會通過網民對賬號悼念區的關注趨向永恒。它們無時不在、隨時可及,這種特性使得當代媒體上具備使人類肉體逝去后維持其精神/靈魂以數據或其他形式永存的功用。[31]Pitsillides等將數字化死亡(digital death)視為生命的死亡及其影響數字世界的方式或數字對象的死亡及其影響生者的方式,[32]這意味著可將數字化死亡分為三個維度:生命的死亡、數字信息的死亡、亡者數字信息對生者的影響。數字媒介的勃興不僅延續了死亡,使得數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成為可能,更是使從古至今的死亡觀念及哀悼儀式得以轉變,進而形塑為當今線上哀悼的“賽博天堂”奇觀。微博逝者賬號的評論區無疑是一種流動、生動的交際記憶,不管是意象還是悼念者都處于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但記憶本身被沉淀下來。從在線哀悼的臨時性社區轉化為常態性的情感表達空間,作為以技術中介的儀式化空間,[33]社交媒體可以補充甚至部分代替曾經標志著終止聯結的傳統喪葬儀式,在這里,人們相信逝者的超自然存在并和逝者進行持續性聯系與儀式性互動。除此之外,逝者微博賬號也成為個體找尋生者意義的反思和行動源。網民不僅可通過互聯網構建對自身親人的數字化哀悼,也可通過與非親非友的已逝人物社交媒體賬號的互動表達自我、溝通他人。網民將逝者的微博空間當作悼念自留地,他們在此探尋生者的意義也分享不經意遇見的善意。
當前對社交媒體逝者記憶的研究對象多聚焦于公眾人物或普通人物的個案分析,此類“管中窺豹”的研究拓展了數字悼念和記憶的邊界,但如何避免流于碎片化、瑣碎化,文章試圖抽離于某一類人群,而是在更普遍意義上從逝者悼念和記憶生產角度延展“中介化記憶”這一概念工具的內涵,但由于樣本數據量、時間等存在結構性差異,數據處理整合時面臨較大困難,還需進一步改進。
參考文獻:
[1]張亞寧.數字時代——生命該如何退場?[EB/OL].https://cul.sohu.com/a/537929570_114819.
[2]劉琴.生死疊合:離場記憶的情感仿真、擬化同在與數字永生[J].現代傳播,2022(9):33-42.
[3]嚴玲艷,陳驍堯.“逝去的歌”:B站紀念賬號的數字哀悼和媒介記憶建構[J].新聞與寫作,2023(11):67-80.
[4]歐陽.打開一個逝者賬號,進行一次賽博時代的掃墓[EB/OL].https://mp.weixin.qq.com/s/NY0ycPowxRx7E73TfK3zLw.
[5]Suri, H. (2011). Purposeful sampl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11(2), 63-75.
[6]伊萊恩·卡斯凱特.在線死亡與云哀悼:社交媒體該如何處理逝者信息?[EB/OL].https://www.sohu.com/a/319995689_313745.
[7]Walter,T.(1994).The revival of death.London:Routledge.
[8]Kern, R., Forman, A. E.amp; Gil-Egui, G. (2013). RIP: Remain in perpetuity. Facebook memorial page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0(1), 2-10.
[9]Walter, T., Hourizi, R., Moncur, W.amp; Pitsillides, S. (2012). Does the internet change how we die and mour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64(4):275-302.
[10]鄭小江.中國死亡文化大觀[M].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1.
[11][法]勒高夫.歷史與記憶[M].方仁杰,倪復生,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64-102.
[12][法]皮埃爾·諾拉.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M].黃艷紅,曹丹紅,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7.
[13]Pentzold, C. (2009). Fixing the floating gap: The online encyclopaedia Wikipedia as a global memory place. Memory Studies, 2(2), 255-272.
[14]Gibson, M. (2007). Death and mourning in 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culture. Health Sociology Review, 16(5): 415-424.
[15]周葆華,鐘媛.“春天的花開秋天的風”:社交媒體、集體悼念與延展性情感空間——以李文亮微博評論(2020-2021)為例的計算傳播分析[J].國際新聞界,2021(3):79-106.
[16]周裕瓊,張夢園.數字公墓作為一種情動媒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2(12):32-52,127.
[17]Bennett, W. L.amp;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amp; Society, 15(5):739-768.; Yang, G. (2016). Narrative agency in hashtag activism: The case of# Black Lives Matte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4(4):13-17; Steir-Livny, L. (2022). Traumatic past in the present: COVID-19 and Holocaust memory in Israeli media, digital media, and social media. Media, Culture amp; Society, 44(3):464-478.
[18][德]阿斯特里特·埃爾,安斯加爾·紐寧.文化記憶研究指南[M].李恭忠,李霞,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3.
[19]Livingstone, S. (2009). 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ICA presidential address 2008.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1):1-18.;Lundby,K.(2009).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consequenc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潘忠黨.“玩轉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討新傳媒技術應用中的“中介化”和“馴化”[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153-162.
[21]李紅濤,黃順銘.一個線上公祭空間的生成——南京大屠殺紀念與數字記憶的個案考察[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1):5-26,126.
[22]Savin Baden, M.(2021).AI for Death and Dying. Abingdon:CRC Press.
[23]Kanhabua,N.,Nguyen,T.N.amp; Niederée,C. (2014).What triggers human remembering of events? A large-scale analysis of catalysts for collective memory in Wikipedia.In Buchanan,G.(eds.).IEEE/ACM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London:ACM Digital Libraries,341-350.
[24][加]馬賽爾·達內斯.占領世界的表情包:一種風靡全球的新型社交方式[M].王沫涵,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1.
[25][英]維維安·埃文斯.表情包密碼:笑臉、愛心和點贊如何改變溝通方式[M].翁習文,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7.
[26][英]伊萊恩·卡斯凱特.網上遺產:被數字時代重新定義的死亡、記憶與愛[M].張淼,譯.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20:44.
[2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81.
[28]Lawler,S.(2014).Identity: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Cambridge:Polity Press.
[29]趙靜蓉.國家記憶與文化表征[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2:780.
[30]Pentzold, C. (2011). Digital networked media and social memor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implications.Aurora, (10):72-85.
[31]Lagerkvist,A.(2018).The internet is always awake:Sensations,sounds and silences of the digital grave.London:Routledge.
[32]Pitsillides.S.,Waller,M.amp; Farifax,D.(2013).Digital death:What role does digital information play in the way we are (re)membered? In Warburton,S.amp;Hatzipangos,S.(eds.).Digital identity and social media.Hershey:IGI Global.,75-90.
[33]Irwin, M. D. (2015). Mourning 2.0—Continuing bonds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on Facebook.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72(2):119-150.
[責任編輯:華曉紅]
作者簡介:賈祥敏,女,講師,博士;應慧,女,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