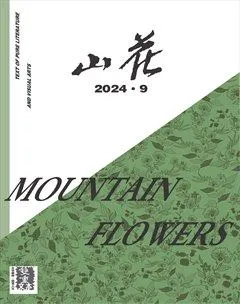為小鎮寫一篇小說
1
馬醫生是十年前回到我們小鎮的。我記得他回來那天是臘月二十八,下著大雪。我是他回來后遇到的第一個人。我告訴他,全鎮的人都在你們家。他點點頭,沒說話。我從他手上拿過旅行箱,幫他拖著,陪他往家里走。
他家在下街,靠近河邊的一個院子。路上我們沒怎么說話。我想起有一年他回來,也是過春節,我們一起在謝大姐的米粉館喝酒,他勸我離開小鎮跟他去省城發展。我說我舍不得這份穩定的工作。他說把工作甩了又怎樣?現在好多小地方的人把工作甩了去大城市發展。我說,我們鎮上也有人跑出去,但都是本來就沒工作單位的,何況郵政所在我們鎮上算好單位,比學校和醫院的待遇都好。他突然把酒杯往桌上一砸,很激動地說,你在這里當個郵遞員算個屁啊,在這個破破爛爛了無生氣的地方,你不管當什么,也就是個屁。見他這樣說話,我也很生氣,也把筷子往桌上一砸,站起來一句話沒說就走了。可能就是這一次以后,我們就開始疏遠了。
走到他家院子門口,看見門上扎的黑布,黑布上的白色紙花,他才問了一句,我哥和我姐他們都回來了吧?我說,都回來了,昨天回的。他沒再說話。我想他問這話也沒什么具體意思,他哥和姐住在縣城,離得比較近,先于他回來是挺正常的。從小我就知道,他跟他哥關系不太好,跟他姐稍微好一點。他哥以前在鎮上糧站工作,糧站倒閉的時候,自己出來做糧食生意,掙了點錢,就把家安到縣城去了。他姐沒正式工作,以前是鎮政府食堂的炊事員,嫁了政府的一個文書,文書高升到縣里當了一個主任,一家人也住到縣城去了。他和他哥除了性格差異大,連長相都不一樣,看不出是兄弟倆。他和他姐要像一些,他姐年輕時也很漂亮。那天我們進了院子后,第一個看見我們的就是他姐。她走過來先跟我打了個招呼,說了句“勞為了”的客氣話,然后就把她兄弟身上的背包卸下來放到一把椅子上,拉著他徑直去到老馬醫生的靈前,對著遺像上香、磕頭。我上午來過一次,給老人家上過香,磕過頭了,就沒再陪著。我把他的旅行箱靠著他的背包放好,自己去茶桶上接了一杯水,就在一桌麻將邊坐下來,看人打麻將。
鎮上死了人,設起靈堂,來吊喪的人送完份子錢,就開始坐下來打麻將。不知情的人進來,還以為進了麻將館。平常沒死人的時候,大家就在茶館或自己家里打。鎮上幾乎人人都打麻將,只有極少數不打的,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我家里有麻將桌,我老婆要打,我有時也坐在旁邊看他們打。我不打麻將是因為才興起打麻將的時候,老婆的興致比我高,常常為爭位子鬧矛盾,為了夫妻和睦,我就宣布不打了;但我不反感打麻將,覺得有這個娛樂還是挺好的,不然鎮上的時間過得這么慢,靠什么打發?對了,老馬醫生生前也是不打麻將的,而且對打麻將這種風氣還有點厭惡。有次我到診所去看病,他就問我,你打不打麻將?我說我不打。他馬上豎起大拇指,很好,年輕人不打麻將很好。然后又關心地問我,平時怎么打發時間?我想了想,還真沒什么上得了臺面的業余愛好,又不好意思說我有時會看人打麻將,只好說自己會看看書。老馬醫生兩眼放光,好,愛看書好,請問都看的什么書?這下我臉紅了。我看的書就是金庸和古龍這樣的武俠小說,便不好意思地說,看看小說之類的,故意省略了“武俠”二字。老馬醫生高興地拍了一下桌子,原來你也愛好文學啊,那我們可以聊一聊。我不記得那天是怎么在老人家面前把“文學”聊過去的,但卻讓我發現了一個秘密,這位平常不茍言笑的醫生居然還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他讓我去他家看他的藏書。他拉開書柜的門,指著里面的書對我說,都是我的珍藏,現在完全對你開放。但是,有個規矩,你要看完一本還一本,才能借下一本。跟他一來二去熟悉之后,我也試著勸他讀一讀金庸和古龍。一開始他不屑一顧地說,武俠小說嘛,以前也看過幾本,作為文學還是不入流的。但當我硬將一套《笑傲江湖》放他桌上之后,他開始上癮了,一發不可收,從我這里又陸續借去《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鹿鼎記》《歡樂英雄》《白玉老虎》《流星·蝴蝶·劍》。他說,你害我廢寢忘食了,讀起來就丟不下手;并評價說,金庸和古龍各有千秋。馬建華(即老馬醫生的兒子,現在的馬醫生)可能萬萬想不到,在我和他疏遠的這些年,我和他家老爺子卻成了莫逆之交。
我正看人打麻將,馬建華過來了。他自己搬了根凳子坐在旁邊,跟著看打麻將。我有點詫異,這種時候,他應該跟他哥和姐坐在一起商量家事,怎么跑這里來看打麻將?打麻將的四個人看他面無表情地坐在這里,也有點不自在。之前搓著麻將還有說有笑的,現在氣氛一下就沉悶起來了。我便拍了他一下說,我跟你去旁邊說點事。
他以為我真要跟他說什么事,面無表情中帶上了一點好奇的神色。我先掏出煙盒,彈出一支來遞給他。他手伸出來,又縮了一下,但還是接了過去。本來已經戒了,他說,現在倒是可以抽一支。我給他把火點上,自己咳嗽了一下說,明天老爺子上山,有你哥和姐,還有這些街坊鄰居,你就放心吧。他吸了口煙說,多虧了你,老同學。可能他聽他姐說,我為他父親的喪事出了不少力,所以才這么跟我客氣一下。我擺了擺手,問他,準備哪天回去?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告訴我,不回去了,準備把父親的診所接過來。
2
跟后來鎮上其他人的反應一樣,當時我也覺得有些蹊蹺。我首先想到的是,會不會老馬醫生留有遺囑,要他回來幫自己把這個診所延續下去?但我這個猜測遭到了大家的否定。他們說,老馬醫生又不是不知道,這個診所根本不賺錢,他兒子在省城大醫院當醫生,是高收入,怎么可能讓他回來做這個無益的事?我說,萬一人家不差錢,就是要回來盡義務呢?大家反駁說,他長期在外面,對這里根本沒感情,盡什么義務?我說,你們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管怎么說,他留下來了,馬醫生診所還在,這就是事實。
我也不知道為什么要替他辯護。其實,越為他辯護,自己越是心虛。我太了解他了。他不僅瞧不起我這個小鎮郵遞員,事實上也瞧不起他父親這個鄉村醫生。說到底,他就是瞧不起我們這個小鎮。他愿意回來繼承這個診所,除了老馬醫生的遺囑,我還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理由。與其說我是在為他辯護,不如說是在為老馬醫生辯護。他肯定是在省城混不下去了,才回來的。不知誰提出了這個假設,一下就獲得了大家的認可。的確,這個假設太符合常理了。一個那么驕傲,條件那么優越的人,要不是走投無路,怎么可能回來?于是,有人又補充說,他一定是在省城犯了錯誤,被醫院開除了。再聯想到他老婆娃兒沒跟著回來,就進一步假設,他老婆也不要他了,離婚了,他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回來。省城離我們實在是太遠了,究竟是不是這樣,誰也無法確認,除非他自己說出來。但誰也不敢去問他,馬醫生,你是不是犯了錯誤被大醫院開除了?或,馬醫生,這么久了沒看見你老婆和娃兒,他們怎么沒跟你一起回來呢?有人就支使我,說這鎮上就你跟他最熟了,你去套套他的話,看我們猜得對不對?我還沒那么傻,跟他再熟我也不可能這樣去問,何況這些年我們已經不那么熟了。
他回來之后,我去過幾次他的診所,他也來我家喝過兩次酒。第一次去他的診所,是他父親的葬禮過后,我想他既然真的把診所開起來了,我還是該去看看。他看見我,第一句問的是,你哪里不舒服?我說,我不是來看病的,我去碼頭辦點事,順便過來看看你。可能他習慣了坐在他對面的是病人,面對一個不看病的人,就一下找不到話說了。為了打破沉默,我問他,看病的人多不多?他環視一下除了我之外就沒其他人的房間說,不多。然后他笑了一下,不多是好事,不是嗎?我也笑了,點頭說,那是,人不生病最好。氣氛稍微輕松了一點。我又問他,還差什么不?他問差什么?是啊,差什么?這是診所,不是家,差什么我又能幫到什么忙?我說,總之,有什么需要盡管說,不用客氣。他點頭說謝謝,但表情卻有些僵硬。我也知道,疏遠了的關系陡然拉近,是讓人有點不習慣。我正準備起身告辭,他突然問我,你還在當郵遞員嗎?我說早沒有了,郵政所都沒了。他笑了一下,這個鎮上不需要郵局。我說是的,醫院也關了,這些年全靠你父親這個診所給大家看病。說完我看著他,看他的表情。他沒有任何表情。隔了一會,他突然問我現在靠什么生活。我說,生活不成問題,有一筆遣散費,拿它當本錢做點小買賣,就是收這里漁船上的魚,再賣到縣城的餐館去,另外每個月還有點社保,生活足夠了。他表情有些凝重,然后說,那就好,差什么,盡管……他看了我一眼,話沒說完,但我懂他的意思。我說,沒事,就是來看看你,我走了。
后來有次,是真去找他看病,也不是什么大病,普通感冒,有點發燒,他給我打了一針,又開了點藥。當時還有其他病人在旁邊候著,不好留下來跟他閑聊,拿了藥準備告辭,他卻招了招手,讓我等一下。我便在旁邊坐下來,等他把病人看完。他要跟我說什么呢?想不出來,只有等著。他看完最后一個病人,便讓我坐過去,問我有沒有認識的女孩?我吃了一驚,莫非傳言是真的?我問,什么樣的女孩?他說,在醫院干過的,沒有的話,衛校剛畢業的也行,長相好一點更好。我試探著問,真的離婚了?他怔了一下,然后笑了起來。他說,是離了,不過不是要你給我找女朋友,是給診所找一個幫手,就是護士。我有點尷尬,但話已說到這里,我不想放棄,就跟著問他,怎么離了呢?他說,這個嘛以后再慢慢說,你先想一想有沒有合適的女孩?我想了一下,說有倒是有,但不是什么女孩了,結過婚,以前也是在鎮醫院工作的,醫院關了就跑出去了,說是在重慶的一家私立醫院做護士,也是今年剛回來。他問,是誰呢,我以前認識嗎?我說,叫蔡春芳,你可能認識。他表情動了一下,以前跟我爸一個醫院的?我說是的。他說,聽說過。我說,但不知道她還出不出去,現在倒是閑在家里的。他說,那你幫我問一下。我突然有點猶豫起來。他察覺到我神色有異,就問,有問題嗎?我趕忙擺了下頭說,沒問題,我可以幫你去問一下。
3
我猶豫那一下,是我有點小心思。但我又覺得,話已經說出來了不好收回去。之前還主動問人家差什么,現在人家就差一個護士,而我剛好就認識這么一個,硬著頭皮也要幫他這個忙。我當然也可以找個搪塞他的理由,說蔡春芳不愿意,另有安排之類的。但這樣撒謊又是我不習慣的。我決定去找蔡春芳。
她算是我的鄰居,我們都住在上街的涼水井旁邊。只不過她家在水井的左邊,我家在水井的右邊,中間還隔著一棵黃桷樹。她離了婚,沒有小孩。我也離了婚,有個兒子在上小學。她雙親健在,兩個姐姐在縣城工作,還有個讀中學的妹妹在家里。我父親去世了,母親健在,兩個哥哥分家出去了,我帶著兒子和母親一起住。她從醫院下崗那一年,我老婆也從郵政所下崗。她跑去重慶,然后跟老公離了婚。我老婆去的是深圳,沒多久也跟我離了婚。她在重慶剛開始并不是在醫院做護士,用她自己的話說,亂七八糟啥都干,就是沒掙到多少錢。掙是掙了些,都用了。鎮上有人說她在夜總會坐臺,也有人說是給一個老板做小三。她中途回來過兩次,一次待半年,一次待了一年,什么事都沒做,就是打麻將。她常去打麻將的地方是“近水樓臺”,鎮上唯一的一家茶館,李二哥開的。他原來是糧站的站長,糧站關了之后,就在碼頭邊開了這個茶館,房子原來是糧站的倉庫,確實是“近水樓臺”。我也愛去茶館喝茶,看人打麻將,所以我們經常碰面。一般都是她在哪一桌打,我就在哪一桌看。打到晚上十二點放手,我們一起回涼水井,走到黃桷樹前,她往左邊回家,我往右邊回家。這樣一段時間之后,有天我就問她,將來怎么打算?
她就笑了,問我是什么意思?我也沒拐彎抹角,直接說,你現在是單身,我也是單身,你沒工作,我在干一點小買賣,我的意思就是,要不我們合起來一起干?她很驚訝地看了我半天,不平哥,你是不是早就在心里打我的主意了?我說,我的確是喜歡你,不然也不會跟你說這些話。她笑了起來,那你老實交待,是從啥時候開始喜歡我的?是不是還沒跟嫂子離婚的時候?這下我就不好干脆地回答她了。我說這個不重要,你只要曉得我現在喜歡你就行了。她一下就變得嚴肅起來,沉默了好久,才說,你是看著我穿叉叉褲長大的,我信任你,叫你哥。但我不值得你信任,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在外面干過些什么;但你又知道我是什么人,鎮上的人都在說,我是個爛人,你跟我會壞了你的名聲。
我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夏天,晚上,打完麻將之后,我陪她回涼水井,走到黃桷樹前,她準備往左邊走,我就說你等一下,我有話跟你說。她那天穿的是一條黑色的吊帶裙,領口開得有點低。她拒絕我的話讓我無從辯駁。我甚至都開始懷疑自己的動機了,究竟是真的喜歡她,還是想找個生意上的幫手,抑或就是看上了她的姿色。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她像是看穿了我在想什么,突然推了我一下,用很做作的輕浮語氣對我說,你是不是想跟我上床嘛?想就明說。我一下有點冒火,就是那種又羞又怒的樣子,畢竟有點被人看穿了嘛。我說,你把你哥看成啥子了,我是那樣隨便的人嗎?她見我變了臉色,就哄著我說,哎呀呀,開個玩笑都開不起,你以為你妹就是那種隨便的人嗎?走走走,我再陪你走一圈,消消氣。我哪還有心情再跟她走一圈,便繼續保持生氣的樣子說,拜拜了,今天的話就當我沒說。
這事過去好多年了。就那次過了沒多久,她突然離開了小鎮,也沒跟我打招呼,我是聽人家說才知道的,她在重慶一家私立醫院找到了工作。今年她又回來的時候,是冬天,比馬醫生回來要晚一個月,即老馬醫生的葬禮之后,春節之前。我開始以為她就是回來過春節的,可春節過了,十五也過了,她還待在家里,我就懷疑她是不是把醫院的工作又耍脫了。所以,當建華說想找個護士的時候,我才一下想到了她。但她這次回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很少見她出門,也不去打麻將。我只是在水井邊碰到過她兩次,一次是中午她和她母親抬著一只大簸箕出來曬鹽菜,那是春節前兩天,她應該是剛回家;一次是她和她妹妹一起在水井邊打水,那是初一的早上。兩次我們都打了招呼,但沒多說話。可能就是上次我的那個表白唐突了一點,使得我們之間有了些尷尬和隔閡。現在要幫建華去問她愿不愿意到馬醫生診所當護士,我還得專門找上門去。
4
我后來才知道,蔡春芳的確是又把重慶醫院的那個工作耍脫了。她也沒告訴我是怎么耍脫的,我也沒問,只說現在有個機會,馬醫生診所差個護士,問她愿不愿意去?我還準備了一些說服她的說辭,沒想到她一聽是馬醫生診所,竟然激動得跳了起來。她說,現在是那個小馬醫生吧,我愿意,我認識他,只是他可能不認識我。我說,他知道你。她又激動得想跳起來。我心里有點不悅,你那么激動干嗎?我還以為你會不愿意呢。她說,怎么會不愿意?我現在正找工作呢,再說,小馬醫生長得還很帥,你們是同學吧?我說是的,他從小就比我長得帥。她看我臉色不對,就呵呵地笑起來,吃醋了吧?我是有點吃醋,這個醋吃得干巴巴的,也沒多大味道。但我又隱隱地有點不安,如果說她是個麻煩,那我把她介紹給建華,這算不算給建華找麻煩呢?
建華為了感謝我給他幫的這個忙,要請我去謝大姐的館子喝酒。我說不用這么客氣,館子里不清靜,就到我家里喝,我自己弄幾個菜。我又問他,蔡春芳也要一起來嗎?他說,你要我喊她一起來嗎?我說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確定下人數,好準備菜。他說,那就不喊她了,就我們兩個,我好跟你說點話。放下電話我就去河邊拿魚。打魚船上的張跛(bāi)子正在曬漁網。他說,你今天運氣好,我剛從羊角灘打到一點青魚回來,你要多少?我說今天是自己吃,三四斤就夠了。他丟下漁網,去船上揭開水箱的蓋子,用網兜先舀了一條起來,我一看差不多有兩斤多,我說你再舀一條,他便又舀起一條,比上一條小一點,我說夠了。他問我,今天看樣子是要招待貴客?我說是老同學,不是外人。他一下就猜出來,是小馬醫生吧?我說是的。他說,聽說那個蔡大姐也到他那里去了?鎮上的人無論老少背地里都喊蔡春芳叫蔡大姐,有點貶義在里面。我說是的。他又說,聽說小馬醫生也離了婚?我說好像是。他就沒再說什么,只說,做這種魚你是知道的,豆瓣啊辣椒啊那些亂七八糟的佐料放不得,就是清煮,放點蔥姜蒜就可以了。
那天我就是按他說的這個辦法做的魚。
5
建華要給我說的事,涉及他回鎮上來的真正原因。他說,他辭職回來接父親的診所,其實是為了寫一部小說。這個說法,比起離婚、被醫院開除、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更讓我驚訝。他什么時候喜歡上了寫作,而且還要辭了職回鎮上來寫?但我沒把我的疑問說出來,因為我一個小鎮上的郵遞員都在寫作,他一個大城市的醫生,又為什么不能呢?回小鎮來寫,也可以說是為了圖個清靜。我問他,準備寫一部什么小說?他只說了是和我們小鎮有關的,至于怎么個有關則不想繼續往下說。寫作是一件很私密的事,他不想說我自然也不多問。其實我也在寫一點東西,我說。他好像并不吃驚,而是平靜地問我,也是小說嗎?我說,只是寫點詩。他想了一下,然后說,詩很難寫。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對我說。很多人聽說我在寫詩,反應都是,好,先從寫詩開始,練練筆,然后再寫散文和小說。建華說詩很難寫,我有種遇到知音的感覺,便多喝了幾杯,話也多了起來。當我提出可不可以請他看看我的詩,提點意見的時候,他卻沒有我期待中那種積極的回應,而是說自己不懂詩,平常也很少讀詩,提不出什么意見來。我當時已經從椅子上站起來了,準備去臥室拿我的詩,但聽他這樣一說,只好又坐了下來。我突然就不知道該說什么了,心里有點難受。
我是真心想聽聽他的意見的。我對自己的詩并無多大把握,曾經給縣里的刊物投過幾次稿,也給省里的刊物投過一次,都沒回音。小鎮上又沒有一個可以交流的人,建華是我老同學,現在又有了寫作這個共同的愛好,本以為可以相互交流和促進,卻發現這只是我的一廂情愿,他并沒有這樣的愿望和需求。但是,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告訴我他在寫小說呢?還特別囑咐我,這事不要外傳。我答應他,一定保密。但心里卻想,小馬醫生回來開診所是因為要寫一部小說,這話即便我說出去了恐怕也沒人會相信的吧?
設想一下,一個生活在省城,事業有成的醫生,突然辭了職,拋妻別子,回小鎮來開一家診所,實際上是以此為掩護,為了寫一部小說。這聽上去怎么都有點不真實,不合一般人的邏輯。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馬建華就不是一般的人,這種有違常理的舉動,在他來說就是正常的。記得毛姆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斯特里克蘭德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本來是一家證券公司的經紀人,事業有成,有家有室,且從沒展露過藝術的才華,卻突然辭去工作,拋妻別子,跑到一個名叫塔希提的太平洋小島上,當起了畫家。雖說是小說,但斯特里克蘭德這個人物卻并非虛構,而是實有其人的,他就是著名的后印象派畫家高更。那么,馬建華是不是也像高更一樣,內心深處一直埋著一顆文學的種子?雖然上的是醫學院,干的是醫生的工作,但寫小說當作家才是他的真正理想(看看他父親的那些藏書,也許最早的種子就埋在那里)。于是,在人生的中途,他給自己來了這么一個反轉。作為老同學,我應該相信他說的是實話。但我又難免多疑,總覺得事情并非表面上他說的那么簡單,其中似乎另有隱情。
6
我繼續有事無事去他診所坐一坐,企圖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但他的診所里看不見一點寫作的痕跡,這也對,既然是隱蔽寫作,就不會把痕跡留在眾人可見的診所。有幾次,我提出到他家里去坐一坐,但都被他以各種理由推脫了。這讓我猜測,他十有八九是利用晚上的時間躲在家里寫的。我問蔡春芳,馬醫生下了班就直接回家了是嗎?蔡春芳說,應該是吧,不回家他還能去哪里呢?她說得沒錯,他自從回到鎮上,除了我這個老同學,別的人一概不往來。即使哪家有紅白喜事請到他,他也只是去隨個份子錢,隨了就走,不吃飯,不打麻將,就好像他不是這個鎮上的人。我又問蔡春芳,你去過他家里嗎?蔡春芳的臉一下就紅了,很羞澀的樣子,這在她來說是很少見的。她說,你想歪了吧,我去他家里干什么?她這一反問,我倒不好再說什么了,也有點臉紅起來。
我承認,我對蔡春芳并沒完全死心,雖然知道已經沒有那種可能了,但心里對她還是存有一定幻想的。無論是正面看見她,還是從背后看見她,我的心臟都會不正常地跳動。當她暗示我想歪了的時候,我才真的往歪處去想了想,她與她老板馬醫生之間是否已走到了那一步?或有沒有可能走到那一步?男人這方面的嫉妒心是本能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嘴上可以說,蔡春芳,你可以跟馬醫生好,你有這個自由;馬醫生,你也可以跟蔡春芳好,你也有這個自由;路不平,你得大度一點,這跟你沒一毛錢關系。但是,心里還是會十分難受,寬闊不起來,過不了這個坎(記得一位叫石光華的詩人說過,人最過不了的關就是情關)。蔡春芳看見我臉紅的樣子就說,你果然想歪了,是不是聽鎮上的人說了什么?我反問她,說什么?她哈哈笑起來,你就裝懵吧。我確實有點裝懵,雖然沒聽到別人說什么,但如果別人說了什么,那一定就是她與馬醫生的那個什么。我說,等他們說,人正不怕影子歪。我本來是想幫她說句話的,她卻似笑非笑地看著我說,可問題是,我這人就不怎么正啊。聽她這話,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她這是在暗示我,那什么未必不是什么了。我想再補一句,人不正也不見得影子會歪,但這種明顯的假話還是說不出口。于是我說,我無所謂。這也是假話,她聽得出來。果然,她低著嗓音(語調嚴肅地)對我說,你有所謂,我的確跟他好上了。
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從介紹她去馬醫生診所那天起,我就知道這事遲早會發生。只是沒想到會是她本人這么輕松地來告訴我。不過想到她一貫的作風,又沒什么可奇怪的了。她就是想看我吃醋的樣子。好吧,我就吃給你看一下。我問,你們,那個……有多長時間了?她哈哈一笑,你問得像我老公一樣,還那個有多長時間了,有意義嗎?我只好說,是沒什么意義。她在我手臂上擰了一下,你又裝懵,說吧,究竟想問什么?我說,還是之前問的那個,你去過他家了嗎?傻瓜,她說,這還用問嗎,當然去過了,不去他家去哪里?這話沒錯,她不能帶馬醫生去她自己的家,家里有母親和妹妹,不方便。我又問,你在他家看見什么了?她不解地看著我,看見什么了?看見鬼了,哈哈。她笑著,以為我發神經,才會問她這么奇怪的問題。但我不這樣問又能怎樣問呢?難不成直接問她,看見馬醫生寫的小說了嗎?我答應過建華替他保密,答應了就得遵守,哪怕問出這樣沒頭沒腦的話,被人當成神經病也不能失信于人。我說,沒什么,就隨便問問,你別往心里去哈。她瞪了我一眼,我往心里去什么去?好啊,我知道了,你們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快說,有什么秘密?這下是她開始好奇起來,扭住我不放,非要問個所以然不可。我當然矢口否認,什么秘密都沒有。她不相信,最后說,我要去問馬醫生,你們倆究竟有什么秘密?
7
第二天,建華就來找我了,坐下就說,你要想看我的小說可以直接跟我說啊。看來蔡春芳那個瓜婆娘真的去問他了。我說,我怕你不愿意嘛。他說,不是不愿意,是還沒寫完,拿出來怕散了氣。他說得沒錯,還沒寫完的小說,就像還沒燜好的飯,中途打開散了氣,就夾生了。有一次我也試著寫過一篇小說,還沒寫完,就迫不及待地拿去給老馬醫生看,他說了幾點意見,我就再也寫不下去了。是要寫一部長篇嗎?我問。他說是的。準備寫多少字?大概四十萬字吧。這么長,寫的是鎮上的事嗎?他沒回答。我們開始喝酒,聊起別的一些事情。他問我這么些年怎么不再找個人一起過?我就直言不諱地說,我追過蔡春芳,但人家不愿意。說到蔡春芳,他神態有點不自然。我覺得兄弟之間,敞開了好說話,就說,我知道你們好上了。他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說了聲謝了兄弟,就自己一干而盡。謝我什么?她又不是我妹。我也一仰頭,喝了杯中的酒。他說這事并不是他主動,他知道我也喜歡她,所以一開始還是有些忌諱,但這女人確實有兩手(主要是太漂亮了),他沒經受得住考驗。對不起了,兄弟。他又自干了一杯。我說,人家沒看上我,把你看上了,不存在對不起誰,我要祝賀你,這杯我干了。他看上去很感動的樣子,自己又拿起酒杯,連干了兩次。
那天我們都喝得有點多了,一直喝到大半夜。人在這樣的狀態下特別脆弱,也特別真誠,容易說出平時不大能說出的秘密。于是,我得知了他回來寫那部小說的具體原因,是因為他父親(老馬醫生)留給他一箱日記,這些日記讓他明白了父親的內心一直隱藏著一個做作家的夢想,父親逐年累月事無巨細地記下小鎮上發生的事情,就是想有朝一日為小鎮寫一部小說。但老馬醫生到死都沒能寫出那部小說,只是記了一箱子的日記。建華覺得這是父親一生的遺憾,他應該替父親實現這一夢想。事實上,這些日記也喚起了他自己內心那個潛在的意識,跟老馬醫生一樣,小馬醫生的內心也一直埋藏著一個作家夢。這也是這么多年他覺得自己活得并不快樂的原因所在。于是他決定回到鎮上來,繼承父親的診所,為父親也為自己,完成一部小說。但是,他這樣的想法并未得到妻子的理解。或者說,她理解他的方式很特別,就是堅決與他離婚,讓他能夠獨自一人安心地回到鎮上寫他想寫的小說。
小說的素材全部來自老馬醫生的日記。素材太多,太龐雜,他又缺少寫作經驗,不懂如何取舍,所以一開始寫得并不順利,起了很多個頭,都只寫了幾頁紙(他堅持用手寫,不用電腦),就寫不下去了。有一次,他似乎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一口氣寫下來竟然寫了四十多頁,中途因為跟蔡春芳談戀愛,中斷了幾天,當他心情平靜下來之后,便重新坐回書桌,翻看前面寫的內容,卻又不滿意起來。完全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那個小說,他說。目前(就是我們喝酒的那天),他又在重讀老馬醫生的日記,想從中發現新的線索,獲得新的靈感。他說,父親的日記像流水賬一樣記錄了鎮上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看上去很詳細,其實很多事情又都不夠清晰和明確,有很多斷點和空白,以及很多隱晦的地方。他覺得自己應該從那些空白處挖掘線索,在隱晦處尋找靈感。小說嘛,就是要大膽地虛構,沒有虛構就沒有真實。這話我不記得是他說的,還是我說的了,那天喝得實在太多。
這之后,他常來找我喝酒,每次都會聊到他正在寫的小說,但我卻不知道他究竟寫了什么。我只知道他這部小說開了幾個頭,哪個時候找到了最終的寫作方向,寫到多少字了,又寫到多少字了,他用了哪些寫作手法,小說的結構借鑒了哪個作家的哪部小說,或哪個導演的哪部電影,以及他如何在老馬醫生的日記里尋找線索和靈感,終于確定了以小鎮上曾經發生的一樁懸案作為主線。是的,小鎮上曾經發生的一樁懸案,這是他透露的唯一與小說內容有關的信息。但究竟是哪一樁懸案他也沒說,害得我連續幾個晚上失眠,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自己在大腦里放電影,把我所知的鎮上那些像懸案的事情過了一遍。我還專門跑去他的診所向他求證,是不是這個,是不是那個?但都被他逐個否定。我說你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告訴我,究竟是哪一樁懸案呢?他說,你為什么要這么著急想知道呢?小說寫完了我自然會給你看的,一定會。
8
但是,小說還沒寫完,他卻先拿給蔡春芳看了。我實際上也很理解,他為什么要把還未寫完的小說拿給蔡春芳而不是拿給我看。因為換作我,也可能會這樣做。不能說這就是重色輕友,是也沒問題。早些年,我曾經跟過一個大哥(郵政所剛停掉那會),他是建筑行業的一個包工頭,對跟著他的兄弟們很慷慨,我們跟他的那幾年,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后來他破產了,生活潦倒,兄弟們想要幫他,卻總是被他粗暴地拒絕。后來得知原因,他把錢財都花在相好的那些女人身上了,也就是說,他對女人比對兄弟更好,更慷慨,所以不好意思接受兄弟們的幫助。我們雖然或多或少有些失落,但還是敬重他。我們一致認為,大哥這樣做是對的,這才是男人。男人用不著對男人那么好。所謂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服,這些話不過是男人之間喝了酒說的。男人更愛女人,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所以,馬建華把尚未完成的小說拿給蔡春芳看,也許是他寫得高興了,寫到特別精彩之處,想要與她分享這種創作的喜悅。又或許是寫得不順,出現了所謂的寫作障礙,自己失去了把握和判斷,于是拿給身邊的女人看看,哪怕她可能不懂文學,對寫作這事也一無所知,但讓她作為讀者給點反饋,喜歡還是不喜歡,好看還是不好看,總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全鎮的人都知道了,馬醫生在寫一部小說。而泄露這一秘密的,就是蔡春芳。她是有天在近水樓臺打麻將的時候,說話說漏了嘴。李二哥說,那天大家在麻將桌上,不知怎么就聊起了婚姻與愛情這個話題,三個麻友就拐彎抹角地套蔡春芳的話,想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和馬醫生好上了。蔡春芳當時剛和了一個暗七對帶自摸的大牌,心里一高興,就承認了,自己的確是跟馬醫生在談戀愛,雖說自己是以結婚為目的在跟他談這個戀愛,但馬醫生是不是也是這樣想的她就不知道了。這樣,大家就又議論起了馬醫生這個人,三個麻友一個是打魚船上的張跛子,一個是蒲大爺的兒媳趙小妹,再一個就是李二哥自己,他們都認為馬醫生是個怪人,二氣,傲西拉秘的,瞧不起鎮上的人。這時候蔡春芳出于對自己人的愛護,就想替馬醫生辯護,他其實不是那樣的人,他那樣不是二,也不是傲,他只是沒時間和大家應酬,因為他除了看病以外,其余的時間都要用來寫一部小說。
9
就這樣,馬醫生在寫一部小說,這事從近水樓臺傳出來,傳遍了整個小鎮。當然還包括小說的內容,由蔡春芳憑著她的記憶和理解轉述出來,再經過張跛子、趙小妹和李二哥的口口相傳,進入到鎮上人的耳朵里,大家都知道了,馬醫生寫的這部小說寫的就是我們鎮上的一些不太好的事。
李二哥對此事的反應還算平和。雖然他說不出作家有創作自由這樣的話,但他說的是,有人來寫一寫這些事總是好的,不然我們這些人死了就沒人記得了。李二哥一輩子都生活在小鎮上,沒出過遠門,但他的思想意識并不保守和狹隘。想當年,他也算得上是個風云人物。
但是,張跛子對馬醫生寫小說這件事的反應就沒那么平和了。他很憤怒。給我說的原話是:都說家丑不可外揚,他馬建華想干什么?什么動機?要達到什么目的?拿這些陳谷子爛芝麻去賺錢?去出名?還是想要報復哪個?他老馬醫生當年被全鎮人孤立,那是他自找的,自己作孽,沒哪個冤枉他。李二哥對他老馬一家那么照顧,他寫這些事對得起李二哥嗎?還有蒲大爺,要不是蒲大爺當年一句話,他老馬醫生活得出來嗎?他那樣寫,對得起蒲大爺嗎?把老子惹毛了,看他姓馬的在這個鎮上還待不待得下去?這一通指責和咒罵中,張跛子只字未提小說里寫沒寫他,寫了他的什么。要說,在當年,張跛子也是僅次于李二哥的人物。
至于蒲大爺,據說是他兒媳婦趙小妹跑回去告訴他的。趙小妹說,爸,你都被馬家那個死娃兒寫進小說了。但蒲大爺聽完整個事情之后,只對趙小妹說了一句話,小說不就是個假東西嗎,他寫他的,關我什么事?蒲大爺 當過主任,后來在鎮政府旁邊開了一個雜貨店。鎮上的人見到他還是叫他蒲主任,直到他六十歲的時候,做了大壽,全鎮的人都被請去吃酒席,這才開始改口,叫他蒲大爺。這之后,他把雜貨店交給兒子和兒媳去打理,自己閑坐家中,不再過問鎮上的任何事情。但實際上,蒲大爺對鎮上發生的大小事情都一清二楚,所謂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鎮上的人有一種說法,就是別看蒲大爺現在啥子官都不是,成天門都不出,但他其實關火得很。事實的確如此,蒲大爺的威望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大,越來越高,到后來近乎一種神的存在了。
現在的李二哥,在威望上比起蒲大爺差遠了。自從糧站關了,他出來開了茶館,大家就已經把他當普通人看待了。李二哥那天就對我說,這個鎮上誰最惹不得大家都清楚。你也知道蒲大爺過去是干什么的,袍哥大爺,那可是真正的大爺。我點點頭,明白李二哥這番話是在暗示我,因為他知道我跟建華是朋友,想讓我去提醒一下建華,自己要多加防范。
10
我去找了建華。我說,這鎮上誰都可以得罪,但蒲大爺你得罪不起。當時是晚飯后,天已擦黑,建華斜靠在他房間的床上,有點背光,看不大清他的表情,我便站起來去找電燈的開關。我還是第一次到建華的房間來。應該說,是建華住進這間房以后我還是第一次來。之前是老馬醫生住的這間房,既是臥室,也是他的書房,我常來這里借他的書。那個大書柜正對著床,床邊就是書桌,這張書桌現在就是建華寫那部小說的地方。書桌上放了一只款式陳舊的臺燈。我還問過建華,是用電腦寫作嗎?他說是用手寫。我問為什么不用電腦?他說他喜歡手寫的那種感覺,并提到了臺燈,說喜歡夜深人靜的時候,臺燈的燈光照在稿紙上的那種氛圍。我說這倒是,過去的作家就是這樣寫作的,只是修改之后,再要抄寫就很費力。我打開房間的燈,建華像是受到了驚嚇,用手擋了一下自己的眼睛。然后我說,這鎮上誰都可以得罪,但蒲大爺你得罪不起。建華依然斜靠在床上,悶了半天,才說,這鎮上我誰都惹不起,蒲大爺只是更惹不起而已。我問他,你是現在才知道的嗎?他搖搖頭,早就知道,從小就知道。我突然想起,他之前就跟我說過,小時候下狠心讀書,就是為了考上大學,離開這個鬼地方。他還說,他恨這里,也害怕這里。他從小表現出來的高傲,不合群,以及長大后與鎮上人的疏遠,都是出于對這里的既恨又怕的心理。我想問他現在打算怎么應對這個局面,但又覺得不合適,也有些多余。我問他,蔡春芳怎么樣?他看著我,有些不明白我問這話的意思。我又說,你現在跟蔡春芳的關系怎么樣?他平淡地說,還是那樣。這次換成我不大明白他話的意思了。我繼續問道,這么說你們還在一起?他點了點頭。我想了想,又問,闖了這么大的禍,她就沒有給你道個歉?他突然很冒火地提高了嗓門說,道歉有什么用,早晚都會發生的事。我也忍不住了,責問道,既然知道這是早晚的事,為啥還要寫那破小說?他吃驚地瞪大了眼睛看著我,鏡片背后的那個眼神既憤怒又很痛苦和失望。你居然也認為那是破小說?他推了推因激動而滑到鼻梁上的鏡框,質問我,你也害怕了是不是?我說,我害怕什么?我是擔心你。你走吧,他說,我們不再是朋友,你放心,這事牽連不到你的身上。
這是我們從小到大發生的第二次爭吵。上一次爭吵之后我們互不理睬長達數年,這一次,我不想那么輕易地與他絕交。我替他擔憂,替他著急,但內心并不認為他做錯了什么,這一點我跟李二哥的認識是一致的。我只是想要幫助他,可能我的方式不對,態度上也有些問題,但就算他接受我的幫助,我實際能做的也很有限。在這個鎮上,我就是一個地位卑微的魚販子,不僅不敢跟李二哥比,連張跛子我都比不了,我在他那里拿魚,維持生計,我得仰仗他,看他的臉色,不然他可以不給我魚,斷我的生路。至于蒲大爺那里,我更沒有與他套得上近乎的那個面子,更不具備與他抗衡的實力。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不拋棄我的朋友,與他站在一起,給予他道義上和心理上的支持。為此,我專門去找了蔡春芳。我要與她談一談這件事情可能的后果,要她堅定立場,不要拋棄馬建華,畢竟,這婁子也是她捅出來的。
但是蔡春芳還沒等我開口說話,就先哭了起來。她說這都是她的錯,她對不起馬醫生,但是現在她也沒辦法,她的壓力太大了,有人親自來找她,給她傳話,要她離開馬建華。還有人去找她母親,讓她母親來跟她說,不離開馬醫生診所,她們全家都會被孤立。現在馬醫生已經被孤立了,她覺得他很可憐,對不起他,但也沒辦法,她也怕被孤立,她母親更怕。以前,很早的時候,她們一家就被孤立過。她的父親死得早,家里沒哥哥沒弟弟,母親特別害怕。現在她的妹妹在上中學,已經在學校被孤立了,還是老師帶頭孤立她的。妹妹回家來都不理她了,不跟她說話。不行,這樣子真的不行,她說,她要到重慶去,壓力太大了非得離開這里不可,只是可憐馬醫生了。她說完后繼續哭,根本不想聽我在說什么。哭了一會,她抬起頭來看著我,真的是淚眼婆娑,臉上的妝容都被淚水弄得有些模糊了,不過模樣依然還是那么好看,竟然使我有了一種沖動,想去幫她擦一擦眼淚。不過一想到這一切都是她那二百五的智商干出來的,徹頭徹尾過去是現在依然還是一個瓜婆娘,我的沖動一下就降落下來。她看著我,突然含淚帶笑地說,不平哥現在的壓力肯定也是很大的吧?我看了她一眼,沒回答我的壓力大還是小,而是說,事情既然是這樣了,你想走就走吧,我也不勸你了。
11
我的壓力確實很大,這一點蔡春芳想得到,也看得出。除蔡春芳外,我幾乎是鎮上公認的與馬醫生最親近的人,甚至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們不認為蔡春芳是他的朋友,女朋友不等于朋友)。他們希望我站穩立場。趙小妹就曾對我說,你當人家是金包卵,人家拿你當夜尿壺。這是很惡意的挑撥離間。我對趙小妹說,男人之間的友誼你不懂。趙小妹拍著手冷笑道,他都把你家的丑事寫進去了,你是傻子嗎?后來我問李二哥,建華的小說里真寫了我家的事?李二哥笑了一下,你家會有什么事呢?意思是我路家在這鎮上無足輕重,沒什么值得寫的。這話回味起來比趙小妹的話還要讓人不舒服。我又問蔡春芳,建華的小說里是不是也寫了我家的事?蔡春芳正在收拾行李,把內衣、襪子和一條絲巾往行李箱里塞。聽了我的問話,她手里拿著一瓶還沒塞進行李箱的洗發水在床沿上坐下來。你讓我想一想,她說。看著蔡春芳沉思的樣子我突然有點想笑,心里冒出這樣一個定義,漂亮的女人是不適合思考的。她皺著眉頭,微閉雙眼,胸脯有節奏地起伏著,就像電影中的女主角,導演說,你現在表演一下思考的樣子,蔡春芳現在就是這樣一種思考的樣子。我有點不耐煩了,就提示說,趙小妹說寫了,但李二哥說沒寫,他們都是聽你說的,寫沒寫你最清楚,還用得著想半天嗎?蔡春芳睜開眼睛迷茫地看著我,不平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記性差,剛看的電影,轉個背就忘記演的是啥子了。她說的是真的,那是好多年前了,那時候她還是鎮醫院的護士,沒結婚,我也沒結婚,有天晚上小學操場要放露天電影,我們是鄰居,她扛著一根板凳出門,在路口遇到了我,就讓我也去家里拿根凳子出來交給她,幫我先去占個位子。那時候我心里已經有人了,就是我后來的老婆,所以我對她沒有想法,跟她坐在一起看電影也就沒什么忌諱。電影是一部外國電影,名字我現在都記得,叫《鴛夢重溫》。看完電影后我們一起回家,走到家門口正碰到她母親,她母親就問她電影演完了嗎?她說演完了。她母親又問今晚演的啥子電影?她回答不上來。她說的就是這一次。所以我對她說,你只是沒記住片名,并不代表你記性差。她說,片名都記不住,記性還不差?我一下火上頭,就直言不諱地說,你是因為不認識“鴛”字,所以才說不出片名。但馬上我就后悔了,真沒必要用這樣的方式去戳她的痛處,以顯示自己認識很多字的優越。蔡傳芳倒是不以為意,自己抱著那瓶洗發水傻乎乎地笑了起來,哈哈,她說,就是嘛,鴛鴦的鴛,合在一起認得到,分開了就不認識了,真是笑死個人。我說,那你究竟想起來沒有,建華的小說里寫沒寫我家的事?她收斂住笑容,用很肯定的眼神看著我說,我敢保證,他沒寫。
其實建華寫沒寫我家的事并不重要,我只是想確認一下,趙小妹是不是在造謠,故意挑撥離間。正如李二哥所說,我家有什么值得寫的呢?那些年,我跟建華一樣還是個娃兒,而且是那種聽話的乖娃兒,沒偷過老師養的雞,沒拿羊油炸彈炸過鎮上任何一家的狗,更沒有做過往水井里撒尿的惡作劇。至于我父親,一個老實巴交的男人,膽子小,兢兢業業的郵差,除了送信,不去招惹任何是非。我母親呢,她就是個最普通的農村婦女,干農活,做家務,不多言不多語,膽子更小。我的父親被吸納進郵政所,做了一名郵政員。這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相信任何一個作家都不會感興趣。但是像蒲大爺那樣的就不同了,家事極其曲折、復雜,極具傳奇性,是上好的文學素材,建華的小說既然寫的是發生在我們這個鎮上的事,不寫蒲大爺,反倒是不正常的了。但問題正在于此,蒲大爺的家事,又是能隨便寫的嗎?記得小時候父親就跟我們兄弟幾個講過,蒲大爺當年做袍哥大爺的時候是如何的威風。那時他才三十歲出頭,個子又高,穿一件青色綢緞長袍,頭戴博士帽,斜挎一只盒子炮,騎在馬上,走哪里都有人圍上去跟他打招呼。我問父親,那究竟蒲大爺是怎么樣的一個人呢?父親說,你只要曉得蒲大爺是個惹不起的人就行了。 一貫沉默寡言的母親當時在旁邊也插了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她說,當年你外公有一次在路上看見了他就因為沒跟他行禮打招呼,哪曉得,晚上我家的倉房就被人點火給燒了。
現在,母親又重提舊事,吃完晚飯的時候,我放下碗,站起來準備出門,她叫住我問我要走哪里去?我本來是想去蔡春芳那里問問她讀過的小說里是不是寫了我家的事,但母親一直反對我跟蔡春芳往來,跟鎮上其他人一樣,她也覺得蔡春芳不是個好女人,所以我就謊稱要去河邊打魚船上問問張跛子明天去不去龍門峽打魚。母親說,你不忙去,我先跟你說句話。兒子聽說我要去河邊,也趕緊丟下飯碗要跟我一起去。我說你先幫奶奶把碗筷收拾進廚房,我跟你奶奶說點事,說完就喊你一起去。母親跟我使了個眼色,我便跟母親去了后院天井里的那棵桂花樹下,我抽了支煙出來,點上,就聽母親說,以前我跟你講的我家的倉房被燒的事你還記得不?我假裝不記得了,就問,我家哪里有倉房?母親說,不是我們現在這個家,是以前你外公的那個家。哦,我想了想,問她,是哪個燒的呢?母親也許看出了我在故意躲避她要跟我說的話,很生氣地甩了一下手說,馬家那娃兒的事我都聽說了,不要以為你媽是聾子,我啥事都清清楚楚,我警告你小平(我的小名是小平),蒲大爺是惹不得的。我說,我從來沒想過要去惹他老人家,躲都來不及。母親說,那得躲遠點,少管閑事,少去馬家晃。
母親說的少去 ,其實就是不去,就是要我斷絕和馬建華的關系。我如果不聽從她的話,讓她看到我還在跟建華來往,她會擔憂,緊張,甚至是恐懼。她比父親還膽小,一直活得小心翼翼,用父親的話說,走路都生怕踩死了螞蟻。現在她已經快滿八十歲了,血壓偏高,心臟也不好,我更不能讓她擔驚受怕。
12
那天我從蔡春芳家出來,不知不覺就走到了河邊。出門時我跟母親說過,要去河邊張跛子的打魚船上看看,但那并不是真話,只是一個借口,不想讓她知道我是去找蔡春芳。蔡春芳收拾好行李之后,我便問她,你準備哪天走?她說今晚就走。今晚就走?我想了想,那只有坐貴州下來的過路船了?她說是的。我說,那都半夜了,我可能送不到你了。她說,就沒想過讓你送。她這樣說話我已經習慣了,照說不會往心里去,但不知為什么,那天我心里還是有點不舒服,就是有點傷心的那種感覺,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從她家出來之后,不知不覺地我就朝河邊走去了。
在我寫的那些詩里,我把這條河稱為墨河,但實際它的名字叫烏江。它發源于貴州威寧的草海,流經我們縣,最后從涪陵匯入長江。我從小在河邊長大,對這條河充滿了感情,所以練習寫詩的時候就拿它做題材。我記得有一天,跟建華在我家喝酒的時候,他突然主動提出想看看我寫的詩。鑒于他上次的拒絕,我一直耿耿于懷,便沒馬上答應,只說寫得不好,沒什么看頭。但那天他不知為什么,執意要看,還說,那就看看不好在哪里吧。我這才起身去臥室把詩稿拿出來,遞到他的手上。他接過稿子就開始看,很投入的樣子。看著別人看自己寫的東西實在是一件很難為情的事情。我就說去上個廁所,起身走了出去。上完廁所我沒有馬上回去,而是站在后院的天井里抽了一支煙。抽完煙,回到屋里的時候,看見建華也在抽煙,我的詩稿則被放在了旁邊的桌上。這么快就看完了?我心里有點疑惑。建華抽煙抽得很認真,是一邊抽煙一邊思考的樣子。我坐回我的座位,沒打斷他的思考,只靜靜地看著他,等他發話。建華終于說,我知道你的詩不好在哪里了,我能說嗎?我說,你必須說。他指了指桌上的那疊詩稿,烏江就是烏江,你非要寫成墨河,問題就出在這里。我一下有點懵,這是什么道理?他沉默了一下,好像下了很大的決心才繼續說道,就是虛假,不真實。
現在看來,他的批評是對的。當我把這條河改名為墨河之后,詩中的所有言辭就開始虛幻起來。而我還錯誤地以為,這是一種升華,是詩意的體現。建華也是在這條河邊長大的,他一下就看出了問題所在,就是虛假。現在我坐在離碼頭不遠的河灘上,真實的河水觸手可及,深吸一口氣,還能聞到從河水中泛起的淡淡的水腥味。碼頭上的躉船已顯出破敗的跡象,因為十年沒有班船停靠了。自從通了公路,大家開始坐班車去往縣城,以及比縣城更遠的地方,航運公司的生意就開始蕭條了,坐船的人越來越少,最后只好停運,倒閉。只有從貴州下來的貨船,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過路船,會在這里停靠一下,順便帶走幾個乘客。過路船一般要在半夜才抵達我們小鎮。從鎮上去縣城每天有早晚兩班車,一次在上午九點,一次在下午三點半,錯過了這個時間,又急于離開小鎮的,像蔡春芳那樣,就只有半夜到躉船上來等貴州的過路船了。
那天我在河邊坐了很久,我想坐到看見蔡春芳拖著行李箱走上躉船,如果我能熬到那個時候的話,就可以目送她一下。這期間,我還猜測,建華會不會也到碼頭上來送別?我開始想的是不會。蔡春芳要離開小鎮實際就是要離開建華,這種離開帶有背叛的意味,她不會讓他知道,所以建華也就不會出現在碼頭。但是,她如果對建華的感情確實很深,臨走之時去給建華道個別,把話說在明處,也是可能的。就我對蔡春芳的了解,她還是一個重情義的人,她的離開,看上去是背叛,但也可以說是一種羞愧,惹出這么大的麻煩,覺得自己對不起建華,無顏繼續待在鎮上。正在我這樣猜測著,又自己反駁自己的時候,就看見一個身影移動到了碼頭上,正是建華。那時候差不多是晚上十點過了,天已完全黑盡,自從班船停運之后,碼頭上的路燈也沒人管了,逐年失修,最終全部熄滅,只有躉船上還殘留了一盞燈。盡管光線暗淡,我一眼就看出那個身影就是建華,我對他太熟悉了。看來蔡春芳真去跟他道過別,他也沒記恨于心,于是深更半夜跑來送她。我內心突然有些感動,便喊了一聲,建華。他有點吃驚的樣子,可能是沒想到我也會在這里。我又喊了一聲,他才動了一下,然后緩慢地走過來,坐在了旁邊的一塊石頭上。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并不知道蔡春芳今晚要離開小鎮,也就是說,他并不是到碼頭來送別的。我問他,那你來干什么?他說,出來散散心,理一理思路。我心里一驚,原來他還在寫那部小說?他曾經跟我說過,這些年只要寫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到河邊來轉一轉,吹一吹河風,頭腦就會清醒很多。我說,可不可以不要再寫那部小說了?他反問道,為什么不寫呢?我當然能說出許多不該寫的理由,但被他這樣一問,我又什么都說不出來了。站在他的角度,要是不寫這部小說,那他放棄一切回到鎮上來又意義何在?他一直企圖掩藏自己寫小說的事情,這說明他知道其中的風險。我忽然又想到他說的真實,即他與我相反,一開始就想好了要真實地寫這部小說,盡管他也提到了虛構。他不會把烏江改為墨河。同樣,他也不會把他寫的那些故事偽裝起來,讓人不知所云。他不怕別人對號入座,而這樣的結果,必然會激怒他小說中寫到的那些人,也就是這個鎮上真實存在的那些人。他也知道,這些人一旦得知他寫的是什么小說,就一定不會放過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他到現在還要繼續寫那部小說的原因,因為他對其可能產生的后果早已心知肚明。
但是,他考慮過我和蔡春芳的處境了嗎?我突然想到了這個問題。我們作為他在這鎮上唯一的朋友,唯一親近的人,必然會因為他這部小說而受到牽連。蔡春芳還可以逃走,我卻只能待在原地,要么與他決裂,以求自保,要么站在他一邊,與他一起被全鎮人所排斥和孤立。他是否知道對這后一種結果我是經受不起的?且不說母親施加給我的壓力,就算她老人家支持我以友情為重,以道義為重,保持與他的朋友關系,但我的生計卻將出現大問題。在這樣的處境下,情義又何以依附?但這些話我不能對建華說。即使我決定了要背棄他,也只能是默默地背棄,無法作任何言語上的解釋。
那天晚上,當蔡春芳終于在碼頭出現的時候,我和建華卻都沒有走出去與她當面話別。我們一直坐在離碼頭不遠的暗處,目送著她拖著那只笨重的行李箱吃力地走上跳板,上了躉船。她在前甲板的一根凳子上坐下來,面朝上游的方向,等待著那艘從貴州下來的貨船。這期間她沒朝岸上看過一眼,顯然她也沒期待過有任何人來為她送行。我們繼續坐在暗處,等到貴州下來的貨船抵達之后,又目送這艘貨船離開碼頭,直至完全在夜色中消失。
13
鎮上孤立馬醫生的行為是在悄無聲息中進行的。首先表現出來的是,無論大病小病,大家都不去馬醫生診所了,寧肯跑遠路,坐班車去縣城的醫院,也再沒人邀請他參加鎮上的紅白喜事了。如果說這兩個跡象都不是建華在意的,即他不在乎有沒有人來看病,開診所本來就只是為了掩護自己寫小說,他對鎮上的紅白喜事也從不感興趣,所以還察覺不了人們孤立他的這種意圖,那么,菜店、肉店以及雜貨店對他的態度,他就不可能感受不到了。先是他去趙小妹的雜貨店買煙,他一直是在這里買煙的,因為只有趙小妹的雜貨店在賣他抽的那個牌子的香煙,但趙小妹不賣給他,先是說沒有那個牌子的了,他愣了一下,就說買其他牌子的也行,趙小妹就干脆地說,不賣。他問為什么?趙小妹說,不為什么,就是不想賣。鎮上有很多家雜貨店,他又去了竇家雜貨店,人家也不賣給他,也是沒任何理由,就是不賣。之后他去的所有雜貨店,都是如此,不賣給他。然后他去菜店買菜,去肉店買肉,幾家菜店和肉店都跟那些雜貨店一樣,不賣。他只好回去給自己下了一碗面條。他后來又去糧店買面條和大米,也是同樣的遭遇。這樣一來,不僅寫作時沒香煙可抽,連吃飯都成問題了。他只得坐班車去縣城采購這些東西。好在蒲大爺的手還沒有那么長,伸不到縣城去,建華也就還能有煙抽,有飯吃。但鎮上這種一致針對他的氛圍,無疑給他的精神造成了極大的壓力。雖然被孤立的滋味他從小就嘗過,但現在不一樣了,他上過大學,當過省城大醫院的醫生,體會過人們的尊敬和熱情,這時候被孤立,被冷遇,其心理落差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一開始,他還每天去診所,把診所的門敞開著,自己穿上白大褂坐在里面,一副隨時準備接待病人就診的樣子,也是在告訴鎮上的人,看看,你們的孤立對我不起作用。但其實大家都知道,他這是在硬撐,用趙小妹的話說,是死要面子。這樣硬撐了一段時間后,大家就發現,診所開門的時間一天比一天晚,有時候都快到中午吃飯的時間,門才打開。同時,關門的時間也越來越早,人們剛吃過午飯,從診所經過,就看見診所的門已經關上了。逐漸地,診所的門不再是每天都打開,有時隔一天開一次,有時要隔上兩天、三天才開一次。有一次,人們發現,隔了一周的時間,都沒見馬醫生打開診所的門。大家開始猜測,他是不是終于撐不住,徹底放棄了?正當人們這樣認為的時候,診所的門又開了一次。
那是一個陰雨連綿的中午,人們剛吃過午飯,就發現診所門口侯了幾個人,看樣子很陌生,應該是從半山上下來的,一問之下果然是半山上的農民,他們專程來找馬醫生看病。病人就躺在一副竹竿綁成的擔架上,是個中年男人,旁邊的兩個男人,一個是他哥哥,一個是他父親,還有一個女人在擔架旁邊撐著一把雨傘,是他的妻子。中年男人躺在擔架上,兩眼緊閉,但嘴巴卻大大地張開著,不停地發出啊啊的聲音。他肚子痛,他的父親對鎮上的人說。大家先是沉默著圍觀,突然,有人喊了一聲,回去吧,診所已經關門了。那個撐著傘的女人用哀求的語調問大家,能不能幫忙去叫一下醫生?有人隨即應道,去縣城吧,縣城的醫生更關火。怕是來不及了,病人的哥哥這樣說。來得及,下午的班車還沒開呢,鎮上的人說。求求你們去叫一下馬醫生吧,女人哭了起來。去縣城吧,鎮上的人說,馬醫生不是好人。聽到這樣的話,病人的父親又哭了起來,我們以前來找馬醫生看過病的,他是好人。這話把鎮上的人激怒了,紛紛指責這位父親分不清好歹,不拿自己兒子的命當回事。病人的哥哥一直蹲在地上,用手抱著頭,這時突然站起來,指著大家喊道,你們去不去,去不去把醫生叫來,不去的話,他環顧了一下四周,看見診所的窗臺下立著的一把鐵鏟,他跑過去拿起鐵鏟,大聲吼道,不然我就把診所的門砸了。大家哄笑起來,想看他是不是真的會去砸診所的門。
就在大家哄笑的時候,建華來了,是我把他叫來的。建華給病人做完手術后告訴我,是急性盲腸炎,幸虧來得及時,再耽誤一個小時就穿孔了。我說,我也是覺得人命關天,才跑去叫你的。他看了我一眼,明白我話中隱含的意思,說了聲謝謝。我們實際上已經斷絕了往來,這次診所救人,是病人妻子的哀求聲給了我勇氣。當我跑去敲建華房門的時候,他還在睡覺。頭發蓬亂,眼袋浮腫,但穿戴卻很整齊,可見那時他心情已糟糕到何種程度,連衣服都懶得脫就那樣躺進被窩不分晝夜地昏睡。我說明了來由,以為他會借故推諉,沒想到他二話沒說,只用手抓了抓頭發,就跟著我到了診所。那聲“謝謝”本該是我說的, 卻讓他說了出來,讓我既羞愧又感動。我甚至想馬上請他去喝一杯酒,但看了看診所外面的那些人,終于還是沒能鼓起這樣的勇氣。
14
那之后,診所就徹底關門了,建華回了省城。他沒來與我告別。長達十年,我們失去了聯系。我一直留意著各種出版信息,但建華的那部小說卻始終沒有出現在這些信息當中。
這十年我一直干著販魚的買賣,除了母親去世,兒子考大學,沒什么特別值得一說的事情。小鎮的情況也一樣,沒多大變化,可說的也不多。兩年前蒲大爺死了,差一天滿九十歲,葬禮搞得很熱鬧,比老馬醫生的葬禮熱鬧多了。全鎮的人都去掛賬送禮,還請縣城的劇團來表演了一個通宵的歌舞,送葬那天炸了一卡車的火炮。李二哥也死了,還死在蒲大爺的前面,突然心梗死的,死前沒任何征兆,吃晚飯的時候還喝了點酒,然后去碼頭邊轉了一下,回來感覺心里不大舒服,李二嫂就說那你去洗漱了早點睡吧,這一睡,就再沒醒過來。張跛子倒是還活著,但這兩年也沒打魚了,類風濕病越來越嚴重,打不動了,所以這兩年我都是在一只貴州漁船上拿魚。蔡春芳自從那次離開后好多年都沒回來過,今年突然回來了,帶了個男人,開的是一輛奧迪。我們在涼水井碰見,打了個招呼,她介紹那個男人給我認識,我們握了下手,但我轉過背就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只記得他頭上套了一頂很明顯的假發。他們在鎮上只過了一夜就走了。我其實這些年對蔡春芳已有些淡忘,看見她時也沒引起我情緒上的多大波動,倒不是因為她容顏的變化,而是我自己在這方面已經心灰意懶。前妻曾經回來過,也是帶了個男人回來,看上去比她小十多歲,我們一起在謝大姐的館子吃了一頓飯,我居然沒覺得尷尬,只是當那個小男人主動要加我微信的時候,被我巧妙地敷衍了過去。
我也沒寫詩了,徹底覺得自己沒那個天賦。倒是有點想寫小說,想把建華沒寫完的小說(也可能他寫完了只是沒有出版)也拿來寫一下,但只起了一個頭,總覺得有什么東西卡在那里,始終寫不下去。前兩年,有三個畫家到鎮上來寫生,引來很多人圍觀,我也去看了看熱鬧。他們對鎮上這些老房子很感興趣,支著畫架畫了一整天,但我卻覺得,他們畫出來的,跟實際的并不一樣。我還聽見其中一個說,這里該打造出來搞旅游,肯定能火起來。我心里不以為然。我問他,誰出錢來打造?他說,找老板噻。我笑了笑,沒問他哪里去找老板?知道他也是說著玩的。沒想到,過了幾天,那個畫家果然帶了一個老板開著一輛奔馳越野來了。我這才知道,那個畫家不光是畫家,還是縣里的旅游局長。因為上次我跟他有過一次對話,算是相識了,就陪著他們一行人在鎮子里轉了一圈,把該看的地方都看了。老板一直面無表情,還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那個局長畫家倒是很興奮,一路上都在給老板作介紹,做導游。我很驚訝,從來沒在鎮上見過他,但他對這個鎮的了解,尤其是對那些老房子的歷史掌故,知道得比我還多。
那天,跟著局長畫家來的還有一個作家。他與我并排走著。他應該是憋了好久,才向我提出了一個他認為不大好開口的問題。他說,這里的落后和窮困他好理解,但這種破敗、骯臟的景象他有點理解不了。人再窮,也是可以把這路上的豬屎和牛糞清掃干凈,把自家院里的雜物收拾整理一下的吧?他不說我都沒意識到這個問題。我趕緊低頭看了看腳下,此時我們正站在鎮北的一個戲臺前,腳下的石板路上,確實就有不少豬屎和牛糞,就好像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不是戲臺前的街道,而是豬圈和牛棚。我有點羞愧,不知該如何回答。想了想,我才含糊其詞地說,這里就這個樣子,清掃干凈了又能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