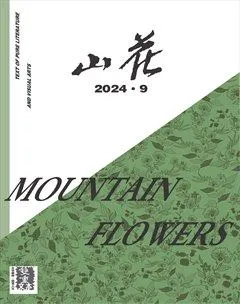花簽
酒柜上擺滿各種酒。納菲站在吧臺(tái)后,身著米色的針織毛衣,正畫(huà)著細(xì)密的圓圈擦拭酒柜。結(jié)婚三周年的時(shí)候,我給紅英買過(guò)一件這樣的毛衣。紅英什么時(shí)候把毛衣送給納菲了?也許,是納菲自己的?
酒吧里一個(gè)客人都沒(méi)有。
“來(lái)杯加冰的。”我坐到吧臺(tái)前,抹抹額頭上的汗說(shuō)。也許是天氣很熱,也許是被困在家里,很久沒(méi)出門,隨便走走我就全身冒汗。
納菲轉(zhuǎn)過(guò)身,好像在確定是我,接著才將毛巾扔在酒柜上,然后拿出兩只水晶杯往吧臺(tái)上一放,其中一只暗暗用力,杯子便“沙——”一聲向我滑來(lái)。我向門口瞟了一眼,門外陽(yáng)光白熾刺眼,柵格窗戶投下的陰影就像一張網(wǎng)將我罩了起來(lái)。我晃了晃身子,試圖從網(wǎng)上掙開(kāi)。
然后,是冰塊扔進(jìn)水晶杯的“咣當(dāng)”聲。
我回頭看著納菲。納菲把開(kāi)瓶器扣在瓶蓋上,手腕稍一用力,啤酒瓶便“啪”一聲打開(kāi)了。為了防止泡沫溢出,她將瓶子緊貼在杯口上,倒得很慢。
“誰(shuí)送的?”我看著吧臺(tái)上的玫瑰問(wèn)。
“你就不能送一次,哄我開(kāi)心開(kāi)心?”納菲把酒瓶放在吧臺(tái)上,不等我端起酒杯,就與我的杯子碰了一下,接著說(shuō),“難道沒(méi)有男人,我們女人連一束花都買不起?”
我端起酒杯“嗞”了一口,杯口的泡沫就像一層細(xì)膩的雪,喝在嘴里蓬松而冰涼。我又盯著淺藍(lán)色的心形花簽發(fā)起愣:“祝菲子開(kāi)心!夏。”清秀的字跡,熟悉的句式,我仿佛在哪里見(jiàn)過(guò),但一時(shí)半會(huì)兒又想不起來(lái)。
納菲并不看我,心不在焉地自個(gè)兒喝著酒。
“再這樣下去,生意只會(huì)越來(lái)越差。”我坐到沙發(fā)上,看著空蕩蕩的酒吧說(shuō)。
納菲沒(méi)說(shuō)話,突然兩眼直直地看著我,看得我心虛地收回了目光。我假裝整理鞋帶。她繼續(xù)盯著我。我感覺(jué)她已經(jīng)看透了我的心緒,便沒(méi)有再遮遮掩掩。
“我真想把她的腦袋砸開(kāi),好好看看她里面裝著什么東西。也許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她在想什么?比如她對(duì)我的感覺(jué)如何?我們對(duì)彼此都做了什么?”我拍著沙發(fā)說(shuō)。若不是納菲久未打掃,沙發(fā)揚(yáng)起的灰塵令我打了一個(gè)噴嚏,我還要繼續(xù)向她傾訴。我還有許多話想說(shuō),但我知道,即使我沒(méi)有說(shuō),納菲也已經(jīng)知道。
“你最好別犯傻。”納菲勸道。
“難道當(dāng)初,你從來(lái)沒(méi)想過(guò)掐死他?”
“掐死他?我愛(ài)他還來(lái)不及。”納菲端起酒杯,想喝,又突然止住,冷笑一聲說(shuō),“也許每個(gè)人結(jié)婚之后,都有過(guò)一兩次想殺死對(duì)方的沖動(dòng)吧。”
我從來(lái)沒(méi)聽(tīng)納菲說(shuō)過(guò)這種喪氣話,從小到大,幾乎任何事,她都抱有耐心。所以我有些吃驚,但似乎也沒(méi)什么好奇怪的,一個(gè)剛被丈夫拋棄的女人,心情能好到哪里?但我和紅英之間的事,除了她,我還能和誰(shuí)說(shuō)一說(shuō)?我打算和紅英離婚。現(xiàn)在,我開(kāi)始猶豫要不要告訴她,她只會(huì)送給我一頓臭罵,我恐怕連一句安慰都討不到。但離婚,也許是我和紅英最好的選擇。
已經(jīng)有人給紅英送玫瑰了!
我真想掐死紅英。每次和她吵架,掐死她的想法有沒(méi)有冒出來(lái),完全取決于那天我的忍受力。二月十四日,紅英精心化了妝,但臉色卻比往日更難看,我知道,因?yàn)橐恢北焕г诩依铮皇窍M@個(gè)特殊的日子能有一點(diǎn)別樣的情趣,但能有什么樂(lè)趣呢?半個(gè)月來(lái),迫于病毒的淫威,我們提心吊膽窩在家里,把防疫阿姨送的洋芋和白菜進(jìn)行煎、炸、蒸、炒,早就倒騰膩了!我和她說(shuō)話,她愛(ài)理不理,我把做飯包了,洗碗包了,把所有家務(wù)都包了,她還想怎樣?總不能出去吃飯吧,據(jù)說(shuō)所有館子都關(guān)著門,真想出去放松,也沒(méi)有可以慶祝的地方。想到花店的老板可以漫天要價(jià),而我的公司卻大門緊閉,我就更加生氣了。晚上,我把紅英摟在懷里,試著吻她,但她一把將我推開(kāi),然后翻個(gè)身,背對(duì)著我,一聲不吭玩起手機(jī)。我心里隱隱作痛,甚至感到屈辱,我不知道自己當(dāng)初怎么會(huì)愛(ài)上她,怎么就和她結(jié)了婚?現(xiàn)在我感覺(jué)我對(duì)她并不了解,陌生得就像一個(gè)陌生人。
自從疫情爆發(fā)以來(lái),公司斷斷續(xù)續(xù)暫停營(yíng)業(yè),我就感覺(jué)自己越來(lái)越力不從心。曾經(jīng)我們對(duì)生活充滿激情,但現(xiàn)在我不止一次夢(mèng)見(jiàn)自己在人群中掙扎。有時(shí)在街上,有時(shí)在醫(yī)院,有時(shí)在海邊,我在人群中尋找紅英,滿心慌亂,但根本找不到。我發(fā)現(xiàn)我對(duì)她根本不了解,似乎一只口罩就掩蓋了我對(duì)她所有的了解。
“她根本不愛(ài)我。”我說(shuō)。
“媽媽活著的時(shí)候,你也這么說(shuō)。”納菲倚著吧臺(tái),端著酒杯說(shuō),“也許你根本不懂愛(ài),也許,你們男人都是絕情的動(dòng)物。”
我斜靠在沙發(fā)上,看著酒柜上母親模糊的照片。如果不是因?yàn)橐咔椋苍S很多人和我一樣,永遠(yuǎn)被妻子或丈夫蒙在鼓里。只不過(guò)公司不能正常營(yíng)業(yè),只不過(guò)欠了銀行一筆錢,貸款快到期,錢還沒(méi)有著落,但紅英就可以整天對(duì)我板著一張臭臉嗎?況且當(dāng)初開(kāi)公司,借錢,我都征得了她的同意。
“你還坐著干嗎?”幾乎每天,紅英都會(huì)像這樣冷不丁冒出一句。
“除了坐著,還能干嗎?”我說(shuō)。
納菲卻說(shuō),我們鬧成這樣,原因不在紅英,而是我不再像以前一樣包容紅英。
難怪紅英把米色的針織毛衣送給了她,兩個(gè)女人已經(jīng)好得可以穿同一件衣服了。因?yàn)橘J款快到期了,每天,我滿腦子想的都是錢,加上對(duì)疫情的恐懼和焦慮,我早已對(duì)親熱失去興趣。而紅英總是揚(yáng)起她白瓷一樣的臉,用冷颼颼的眼神質(zhì)問(wèn)我是不是有了別的女人?自疫情爆發(fā)以來(lái),我們一直被困在家里,我整天活動(dòng)在她眼皮底下。她真會(huì)惡人先告狀啊!
剛結(jié)婚那幾年,我們過(guò)得還算幸福。應(yīng)該說(shuō)開(kāi)公司之前,或者說(shuō)疫情爆發(fā)以前,我們都很幸福,幸福得我把納菲忘到了九霄云外。那時(shí),我和紅英的生活四處充滿了歡笑。我們手挽手一起購(gòu)物,有時(shí)我會(huì)沖進(jìn)廚房,和正在做飯的紅英卿卿我我,有時(shí)我們也會(huì)躲在電影院的最后一排摟摟抱抱。每個(gè)星期一早上,當(dāng)我起床準(zhǔn)備上班,她都會(huì)把修長(zhǎng)而白皙的小腿從被子下面伸出來(lái),用腳背勾住我的小腿,說(shuō)要我別走。
“可是,現(xiàn)在已經(jīng)八點(diǎn)了……”
“給你十分鐘……”
“我會(huì)遲到的。”
“五分鐘,行不行?就五分鐘……”
在那段幸福的日子里,這經(jīng)常成為我和紅英相互調(diào)侃的笑話。我們愛(ài)的電流完全可以為整座城市供電。我們生活無(wú)憂,也許這得益于結(jié)婚之前我買了一套房,到我們結(jié)婚的時(shí)候,房?jī)r(jià)幾乎翻了三倍。相對(duì)于那些剛結(jié)婚就在房貸的苦海中掙扎的夫妻,紅英對(duì)我超前的投資眼光總是贊不絕口。那時(shí)候,我從未擔(dān)心我和她的愛(ài)會(huì)從某一天突然開(kāi)始衰竭。一切似乎已經(jīng)好得不可能更好了,卻偏偏忽然往不好的方向發(fā)展,就像急馳的汽車突然來(lái)了一個(gè)急轉(zhuǎn)彎,然后我被甩出車外。
先是下班回家,飯沒(méi)有做。剛開(kāi)始,我以為這只不過(guò)是百年一遇的偶發(fā)事件。后來(lái),我從紅英的話中聽(tīng)出了微妙的變化。比如每天回家,我已經(jīng)坐在沙發(fā)上,她總會(huì)無(wú)話找話地說(shuō):“回來(lái)了,老公?”語(yǔ)氣中帶著疲憊和失望,好像我不應(yīng)該活著出現(xiàn)一樣。為此,我不得不用類似的口吻反擊:“回來(lái)了,媳婦?”
糖吃多了也會(huì)酸,現(xiàn)在我深有體會(huì)。不過(guò)幸好,不管是不是病,早發(fā)現(xiàn)早治療,長(zhǎng)痛不如短痛,一切總比由內(nèi)而外慢慢糜爛來(lái)得痛快。早上,我和紅英又吵了一架。
“一個(gè)準(zhǔn)備逃走的人,她口袋里總裝著一萬(wàn)個(gè)和你吵架的理由。”我說(shuō)。
納菲不搭話。
口很渴,我讓納菲再來(lái)一杯,沒(méi)想到她突然沖我兇道:“想酗酒,你最好滾去別的地方。”別的地方?當(dāng)然,我知道她這么說(shuō)只是不想讓我成為那個(gè)男人一樣的人,那個(gè)男人經(jīng)常酗酒,她沒(méi)少挨拳頭,有時(shí)候,她還得忍著疼痛幫他處理那些臭氣熏天的嘔吐物,這是我后來(lái)才知道的。那個(gè)男人是突然走掉的,沒(méi)有留下任何信息,所以她對(duì)這段感情心有不甘。她曾經(jīng)在電話里向我哭訴,說(shuō)她不明白,她這么容忍和包容,那個(gè)男人為什么還要走?她開(kāi)酒吧,就是希望那個(gè)男人某天回來(lái),男人不是愛(ài)喝酒嗎?她每天堅(jiān)守在酒吧里,等待那個(gè)男人出現(xiàn)。
其實(shí)不用說(shuō),納菲也知道我和紅英又吵架了。納菲在吧臺(tái)后走來(lái)走去,說(shuō)都怪我們一直沒(méi)要孩子,如果有個(gè)孩子,我和紅英就會(huì)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整天盯著對(duì)方的缺點(diǎn)。
“幸好沒(méi)有孩子。”我差點(diǎn)從沙發(fā)上跳起來(lái),但腿有點(diǎn)酸,腰也用不上力,然后我笑著說(shuō),“你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滾!”納菲指著門外說(shuō),“你是故意來(lái)氣我的吧!”
門外依然陽(yáng)光白熾刺眼。斗爭(zhēng)無(wú)處不在,人與病毒的斗爭(zhēng),人與人的斗爭(zhēng),正變得越來(lái)越劇烈。我從沙發(fā)上站起來(lái),往洗手間走,尿有點(diǎn)急,好像剛才那杯酒不是進(jìn)了肚子,而是直接灌進(jìn)膀胱。洗手間就在酒吧北角,先穿過(guò)一條昏暗的走廊,再拐一個(gè)彎就到了,但門緊鎖著。納菲站在吧臺(tái)后看著我笑,好像我上不了洗手間她非常解氣。她說(shuō)洗手間壞了,手依然指著門外。
可惡的女人!
我懨懨地往家里走。不回家,還能去哪兒?去朋友家?說(shuō)起朋友,我就想到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想到當(dāng)初開(kāi)公司時(shí)向他們借了錢,當(dāng)初說(shuō)短借一年,誰(shuí)知疫情突然爆發(fā),錢遲遲還不上,現(xiàn)在已經(jīng)快四年,其間他們沒(méi)少催我。有一天,我甚至看見(jiàn)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來(lái)到小區(qū)門口,氣沖沖的樣子,若不是進(jìn)不來(lái),他們肯定會(huì)沖上來(lái)給我點(diǎn)顏色看看。所以只能回家,但家里就像一只火藥桶,只要我回去,隨時(shí)可能爆炸。一想到紅英無(wú)辜的樣子和她臉上掛著的鱷魚(yú)一樣的眼淚,我就生氣。現(xiàn)在,紅英喜歡吵架已經(jīng)勝過(guò)喜歡我了,新買的牙膏不是云南白藥牙膏,要和我吵一架;洗衣粉不是立白薰衣草,要和我吵一架;鹽巴不是海藻食用鹽,也要和我吵一架……
曾經(jīng)她是多么善解人意啊。就算我在股市虧得一塌糊涂,她也沒(méi)有責(zé)罵一句,只是提醒我以后謹(jǐn)慎一點(diǎn)。
街道空空蕩蕩,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和從前沒(méi)什么兩樣,紅燈,綠燈。也就是這個(gè)時(shí)候,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忘了戴口罩。幸好路邊的藥店開(kāi)著門,我歪進(jìn)去買了一包。
戴好口罩,轉(zhuǎn)進(jìn)一條巷子,見(jiàn)一家文具店開(kāi)著門,我便鬼使神差走了進(jìn)去。老板懷里抱個(gè)相框,正窩在椅子里打盹。我干咳一聲,男人仿佛從夢(mèng)中驚醒,瞪大眼睛看著我,好像對(duì)突然冒出來(lái)一個(gè)客人非常吃驚。也許他和我一樣,只是跟老婆吵了一架,然后從家里逃出來(lái),躲在冷清清的鋪?zhàn)永镏磺髢啥屐o?
“我想買把刀。”我比了比。
“這么長(zhǎng)屬于管制刀具。”
“是不是除削筆刀,你這里什么都沒(méi)有?”
老板抱著相框,把我?guī)У綌[滿各種美工刀的柜臺(tái)前,然后將口罩拉到下巴上,露出滿臉的胡茬和疲憊。我以為他會(huì)急著問(wèn)我想要哪一款,沒(méi)想到他竟然把相框放到柜臺(tái)上,給我遞了一支煙。這樣我就注意到了相框里的女人,女人眉心落了一顆芝麻大的痣,雙耳戴一對(duì)漂亮的珍珠耳環(huán),站在一片金色的油菜花里。
“你老婆?”我隨口問(wèn)。
“走了。”
“蠻漂亮的。”
“我連她最后一眼都沒(méi)見(jiàn)到。”
看來(lái),老板也想找個(gè)人說(shuō)說(shuō)話。但我想馬上回家,納菲都護(hù)著紅英,我為什么還要跟一個(gè)陌生人絮絮叨叨,說(shuō)不定只會(huì)成為他眼中的笑話。我指指柜臺(tái)里一把刀柄有木質(zhì)桃紋的小刀,讓他拿出來(lái)看看。
回到家,我小心翼翼觀察家里的情況。我非常好奇紅英在干嗎,但我把大臥室和小臥室尋了一遍,都沒(méi)發(fā)現(xiàn)紅英的蹤影。我打開(kāi)衣柜,米色的針織毛衣好端端掛在衣柜里。摸了摸,似乎還有一絲余溫。我躺到沙發(fā)上,將美工刀往茶幾上一扔,心想這下好了,省得我和紅英吵起來(lái),然后用美工刀切開(kāi)她的腦袋,看看她的腦袋里究竟裝著什么東西,什么想法。想到這里,我露出一絲冷笑。
客廳一片狼藉。電視遙控器落在臥室門口,當(dāng)時(shí),紅英就是用遙控器砸在我的額頭上,現(xiàn)在我的額頭還腫得像被馬蜂蜇過(guò);還有那只她經(jīng)常抱在懷里的玩具熊,也被扔在地上;沾滿眼淚和鼻涕的紙巾散落在垃圾桶周圍;而那些被摔碎的玫瑰花,濺得滿地都是。
“滾吧滾吧,最好永遠(yuǎn)別回來(lái)!”我和衣躺在沙發(fā)上,暗罵著閉起眼睛,想睡,卻又睡不著。翻個(gè)身,腦子還是迷迷糊糊。紅英去哪兒了?
為什么我睡著了,還聽(tīng)到窗外垃圾清運(yùn)車的音樂(lè)聲?為什么我沒(méi)有睡著,嘴角卻掛著口水?難道我剛才真的睡著了?
也就是這個(gè)時(shí)候,我突然發(fā)現(xiàn)客廳的窗戶沒(méi)有關(guān)。
紅英會(huì)不會(huì)從窗口跳下去?六樓,雖然不至于把她摔得粉身碎骨,但要她的命還是輕而易舉,曾經(jīng)我就想這么跳下去。我想起紅英仰著頭和我怒目相對(duì)的樣子。“打啊,有種你就打下來(lái)!”她說(shuō)。我掐著她的脖子,把她摁在沙發(fā)里。在此之前,我們先是聽(tīng)到一陣敲門聲。紅英跑去開(kāi)門。談話聲很小,嚶嚶嗡嗡,我想看看門外的人究竟是誰(shuí),然而客廳的隔斷擋住了我的視線。等紅英回到客廳,她的手里已經(jīng)抱著一束玫瑰。這已經(jīng)不是她第一次收到花了,但我從來(lái)沒(méi)有給她訂過(guò)花!最近,她隔三差五就會(huì)收到一束滿天星、百合或者向日葵,現(xiàn)在是玫瑰。
“誰(shuí)……誰(shuí)送的?”我感覺(jué)牙齒有些打顫。
洋溢在她臉上的幸福沒(méi)有任何收斂。
我?jiàn)Z過(guò)花,心形的花簽和以前的一模一樣,字跡清秀:“祝英子開(kāi)心!夏。”送花的人應(yīng)該叫夏吧?應(yīng)該是個(gè)男人吧?他們的關(guān)系絕不一般!
“他到底是誰(shuí)?”我將花摔在地上。
我并沒(méi)有得到紅英的回答,而是額頭上得到了一個(gè)遙控器。我撲上去,掐著她的脖子,把她摁進(jìn)沙發(fā)里,然后我肚子挨了一腳。
我趴在窗戶邊,樓下一個(gè)人都沒(méi)有,更別說(shuō)紅英的尸體了。幾片被風(fēng)扯落的銀杏葉就像幾只綠蝴蝶,在空中翻飛……
天藍(lán)得透徹,云白而豐滿。關(guān)上窗,風(fēng)叫得更歡了,嗚嗚撲打著窗戶。小區(qū)門外像突然落了一朵烏云,哦,不是,是一群人擠在藥店門口,大約二十多個(gè),好像正在吵架。
我感覺(jué)有人在向我招手。會(huì)是誰(shuí)?我瞪大眼睛,想看個(gè)究竟,就真的看見(jiàn)納菲在向我招手。納菲不是在酒吧嗎?怎么突然出現(xiàn)在這里?而且身著黑色的緊身外套。
我并不喜歡湊熱鬧,但我還是站到了人群外。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站到人群外的。反正我遠(yuǎn)遠(yuǎn)躲在人群后,不敢上前。馬春風(fēng)和紅英正在吵架,蔣小兵站在一旁,用耗子一樣的眼睛觀察著周圍的動(dòng)靜,好像正在尋找我的身影。我覺(jué)得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不好好待在家,冒著風(fēng)險(xiǎn)跑出來(lái),不止要賬這么簡(jiǎn)單。納菲推了我一把,我知道,她想讓我上去保護(hù)紅英,但我死死拽著旁邊的行道樹(shù)。馬春風(fēng)把紅英罵得越兇,我就越高興。特別是想到平時(shí)紅英和我吵架,總擺出一副吃人的樣子,我就有種報(bào)仇的快感。
最好再扇她幾耳光!
馬春風(fēng)還真扇了紅英兩耳光。
紅英不甘示弱,反手抽回去,沒(méi)抽到。馬春風(fēng)真的像一陣風(fēng),身子輕輕一晃,就閃到一邊,然后又朝紅英臉上送了幾拳。
見(jiàn)血從紅英嘴里流出來(lái),我突然感覺(jué)胸口有點(diǎn)隱隱作痛,心想這么多年,自從我們?cè)谝黄穑退阕罱[得水火不容,我都沒(méi)有真的打過(guò)她。但又想,她平時(shí)那么霸道,現(xiàn)在我倒要看看她怎么對(duì)付馬春風(fēng)。
她卻突然蹲在地上,捂著臉嗚嗚哭了起來(lái)。
“錢什么時(shí)候還?”馬春風(fēng)朝紅英背上踹了一腳。黃色的腳印就像一條臟兮兮的舌頭,落在紅英的白T恤上。
紅英晃了晃,差點(diǎn)摔在地上。
“依我看,那混蛋是不敢來(lái)了。”說(shuō)著,蔣小兵也朝紅英身上送了一腳。
見(jiàn)紅英鼻子一直流血,我掏一包紙遞給納菲,但納菲生氣地走開(kāi)了。我站在人群后,希望紅英能頑強(qiáng)地站起來(lái),然后用平時(shí)對(duì)付我的潑辣對(duì)付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罵不贏,打不過(guò),總可以跑啊。快跑啊,笨蛋!但她一直蹲在地上,就像一只不倒翁,任由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踢來(lái)踹去。
想到我從來(lái)沒(méi)像這樣打過(guò)紅英,她現(xiàn)在卻被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打得滿臉是血,我就有些生氣。
應(yīng)該住手了。
但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并沒(méi)有住手的意思。他們罵罵咧咧,時(shí)不時(shí)朝紅英身上送出一腳,就算紅英被打得蜷縮在地上,也沒(méi)人站出來(lái)替紅英說(shuō)句話,更別說(shuō)拉她一把了。
還不住手!我氣得咬牙切齒。再這樣下去,紅英可能會(huì)有生命危險(xiǎn)!想到這么多年我從來(lái)沒(méi)像這樣打過(guò)自己老婆,自己老婆可能就這樣被人打死,我突然無(wú)比憤怒。
我握起拳頭,瞅準(zhǔn)時(shí)機(jī),趁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不注意的時(shí)候沖進(jìn)了人群。在人們的驚叫聲中,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各挨了幾拳。我也沒(méi)想到,我竟然這么能打,這么壯實(shí)有力,竟然隨便幾下就把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撂倒在地。然后,我拉起紅英就往人群外跑。沒(méi)人阻攔我們,只有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追在后面,罵罵咧咧。
我牽著紅英,先穿過(guò)一片櫟樹(shù)林,然后是下坡。長(zhǎng)長(zhǎng)的下坡。也許是下坡,我們才跑得那么快,快得步伐差點(diǎn)跟不上腦袋,有幾次差點(diǎn)摔了跟頭。我想起第一次牽著紅英的手瘋跑是在撫仙湖邊,那時(shí)我們已經(jīng)交往了半年,第一次出去旅游,一切都很美,夕陽(yáng)西下,海風(fēng)卷起的浪花親吻著我的短褲和她的裙擺。我瞟了紅英一眼,紅英臉上竟然沒(méi)有一絲血,我有些詫異,但并沒(méi)有問(wèn),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緊追在后面,累得我氣喘吁吁,根本無(wú)法開(kāi)口。
前面就是橋了。很遠(yuǎn)我就看見(jiàn)了那座橋,就聽(tīng)到了嘩嘩的河水聲。紅英以前的家就住在橋?qū)γ妫侥敲妫蚁肫饎傉剳賽?ài)那會(huì)兒,無(wú)數(shù)個(gè)夜晚,我們甜蜜地從橋上走過(guò),有時(shí)是我把紅英接過(guò)來(lái),有時(shí)是我把紅英送過(guò)去。若不是我突然回頭,我?guī)缀跬水?dāng)初為什么會(huì)喜歡紅英。那天陽(yáng)光明媚,我記得她穿一件藍(lán)色的牛仔連衣裙,扎一束高高的馬尾,站在她奶奶家門前,我剛好從門前路過(guò),所以剛好看見(jiàn)她迷人的微笑,就和現(xiàn)在一樣,嘴角微微上揚(yáng),露出兩排潔白晶亮的貝齒。如果說(shuō)她的微笑格外迷人,那么她整齊的貝齒就是能攝人魂魄的神器。我以為,她會(huì)一直把我們的愛(ài)情像珍珠一樣含在她的貝齒之中。后來(lái)當(dāng)我告訴她,令我第一眼就著迷的并不是她高挑的身材,而是牙齒,她根本不信。
“現(xiàn)在怎么辦?”我拉著她的手,站在橋上問(wèn)。
“錢呢?”她說(shuō)。
“哪有什么錢。”
“那就只有跳下去了。”
我瞟了一眼后面,馬春風(fēng)和蔣小兵已經(jīng)追上來(lái)了。但是前面已經(jīng)沒(méi)有路了,只有一座大山擋在前面。前面的路呢?我非常疑惑。以前我可是經(jīng)常沿著山上彎彎曲曲的水泥路把紅英送到山那面。但又能怎么樣?這就是現(xiàn)實(shí),許多路走著走著,突然就沒(méi)有了。而我們卻經(jīng)常陷入“曾經(jīng)”的陷阱,以為曾經(jīng)有路,現(xiàn)在就應(yīng)該有路。
“曾經(jīng)我就想從這里跳下去。”她說(shuō)。
“為什么?”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吵架嗎?就在這里。”
那次我們站在橋上,很久,久得好像彼此都舍不得分開(kāi),手拉著手,就像現(xiàn)在,扶著白色的護(hù)欄,望著波光粼粼的水,聽(tīng)著嘩嘩的流水聲。清白的月光灑在河面。而那樣的夜晚,不知有過(guò)多少次。似乎總是等到那只躲在樹(shù)林里的貓頭鷹發(fā)出咕咕的怪叫,直到紅英突然抓緊我的手說(shuō)害怕,我才送她回家。在這座橋上,有著我們的許多回憶,有我第一次說(shuō)我愛(ài)她,有我和她的第一個(gè)吻,也有我和她的第一次爭(zhēng)吵,她的第一滴悲傷的眼淚。那晚,當(dāng)我和她來(lái)到橋上,當(dāng)她告訴我她有了我的孩子,我竟然充滿恐懼。
“真的?”我希望她說(shuō)的只不過(guò)是從電視劇里學(xué)來(lái)的騙人的小把戲。
“你什么意思?”紅英很生氣。
我還沒(méi)有做好做爸爸的準(zhǔn)備,就連結(jié)婚,我都沒(méi)有準(zhǔn)備好。紅英扶著白色的護(hù)欄,哭得很傷心,眼淚雨一樣落進(jìn)河里。如今,河水已經(jīng)把她的眼淚帶去了很遠(yuǎn)很遠(yuǎn)的地方,但悲傷留了下來(lái)。
“你怕不怕?”我問(wèn)。
“不怕。”紅英說(shuō)。
“我先跳。”
“我們一起跳。”
一個(gè)愿意陪你跳河的人,會(huì)有多愛(ài)你!我鼻子一酸,眼淚差點(diǎn)涌出來(lái)。
“我先跳,然后你再跳,我在下面接你。”不等說(shuō)完,我就跳了下去,因?yàn)轳R春風(fēng)和蔣小兵已經(jīng)追上來(lái)了。但落下去的時(shí)間太長(zhǎng),長(zhǎng)得我以為不等我落到水里,馬春風(fēng)就會(huì)捉住紅英。我感覺(jué)從橋面到河面只不過(guò)七八米高,但為什么我半天落不到河里?就像墜入了一個(gè)無(wú)底的噩夢(mèng)的深淵。我甚至有一種失重的感覺(jué),好像下墜中撲面而來(lái)的風(fēng)把我托住了。我繃直身體,盡量讓自己不會(huì)一頭栽進(jìn)水里。
看著奔騰的河水,我非常害怕。我突然想起來(lái),我并不會(huì)游泳。
我掉進(jìn)河里,砸碎了沉在河底的月亮,嗆了好幾口水,才從水里掙扎出來(lái)。馬春風(fēng)已經(jīng)把紅英按在白色的護(hù)欄上,惡狠狠看著我。我拍打著水,奮力抵抗著水的沖擊,我試圖飛到岸上,把紅英從馬春風(fēng)手里救出來(lái),但我卻開(kāi)始下沉,快速向水底沉去……
我感覺(jué)我就要死了。強(qiáng)烈的窒息感就像一座山壓在我胸口,令我四肢不能動(dòng)彈。我在掙扎中驚醒。我感覺(jué)自己就像真的掉進(jìn)了河里,明明很冷,卻又很熱,全身大汗淋漓。我支起腳,待汗水收了一些,才徹底蹬掉被子,但脊背還是像被火燎到一樣難受,這不是我第一次有這種灼痛感了。我翻了翻身,找一個(gè)舒服的姿勢(shì)繼續(xù)躺著。
天早已黑定。客廳的窗簾沒(méi)有拉,窗外銀月如鉤,月光投進(jìn)來(lái),灑在沙發(fā)和茶幾上,像一層水,白汪汪一片。地上散落著許多東西,但看不清是什么,肯定都是我和紅英吵架的犧牲品。我坐在沙發(fā)上,點(diǎn)一支煙抽了起來(lái)。
我環(huán)顧一圈涌滿月光的客廳,還是不見(jiàn)紅英的身影c491a7ee36c04361292d6d873bfce367。然后,我盯著茶幾上的美工刀發(fā)起愣來(lái),哪兒來(lái)的刀?我將刀扔進(jìn)抽屜。紅英會(huì)在哪兒?我打算去臥室看看。
我站起來(lái),又坐下。
我突然想起納菲的話:難道沒(méi)有男人,我們這些女人連一束花都買不起?我心里一亮,就像突然明白了什么,然后我點(diǎn)燃打火機(jī),開(kāi)始趴在地上尋找。玫瑰已經(jīng)被我摔得七零八落,幾乎只剩花枝,幸好淺藍(lán)色的心形花簽還在。借著打火機(jī)的微光,我看了又看,字跡非常清秀。
我拿著花簽,踩著滿地的花瓣向臥室走去。
門關(guān)著,我輕輕推開(kāi),酒味撲鼻而來(lái)。紅英好像正遭受胃痛的折磨,蜷縮在床上,但已經(jīng)睡著了。也許她已經(jīng)睡著了。我蹲在床邊,入神地端詳著她的臉。她的臉上沒(méi)有一絲淚水,但長(zhǎng)長(zhǎng)的睫毛上還留著淚水曾經(jīng)來(lái)過(guò)的痕跡——所有睫毛粘在一起。我把花簽放在床頭柜上,放在一個(gè)她睜開(kāi)眼睛就可以看見(jiàn)的位置。現(xiàn)在,這枚花簽就像是我親自送給她的。我撿起倒在地上的酒瓶,大口喝起來(lái)。這是她第一次喝酒。我喝著剩下的酒,來(lái)到床的另一邊,這邊有著屬于我的位置和枕頭。
我拉起被子,悄悄鉆進(jìn)被窩,然后慢慢向紅英靠去,直到我的身體與她的身體微微貼在一起。
紅英一動(dòng)不動(dòng)。
我從后面輕輕摟住她,她還是一動(dòng)不動(dòng)。
我長(zhǎng)長(zhǎng)舒了一口氣。剛開(kāi)始,我感覺(jué)床有一點(diǎn)冷,但慢慢就變得暖和起來(l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