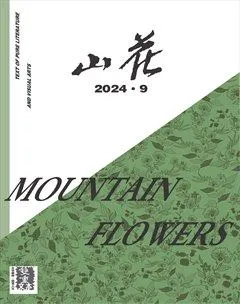珍酒記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時興喝老酒了。這個老,不光指年份,同時還指品牌。年份,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窖藏的。品牌,說起歷史,由今天開瓶之時,上溯幾百年,黃河遠上白云間,甚至上溯到云深不知處。有些是真的,有些就難保沒有幾分杜撰。喝酒當然該是好酒。但當今的酒文化,虛榮心重,要有份,什么都要有個說道。
去年,肖江虹組了個作家團去青藏高原,過成都,邀喝酒,座設黌臺。那家館子高檔,又尋思貴州人肯定帶了茅臺來。立即應了。
去了,卻不是茅臺,桌上擺著的,叫珍酒。沒聽說過,更沒見過。我愛酒,愛好酒,卻沒有擺譜到只喝茅臺的地步。就既來之則安之了。
桌上擺著兩種酒。一種,鼓腹的醬綠瓶子,珍三十。一種,瓶形修長,玻璃與瓶中酒同色,上寫著“2012”。
還有釀酒廠的人隨行,廠方陳國華——有些像四川人的貴州人。兩箸菜后,舉開席的三杯酒。珍三十。遵義來的嘛,醬香型白酒嘛,喝的人明里暗里都在對標茅臺。又像又不像。大多數人,要求是像,就去品咂那像。我以為,可以不像。可以又像又不像。第一杯,第二杯,第三杯。當然有些像,一樣的制曲,一樣的高梁,一樣的流程。一點不像也難。不一樣的釀造地,不一樣的水,有差異的生物環境,又怎么能全像。幾杯入口,唇齒之間,舌與喉頭,還有作為氣息共鳴器的口腔,都感受到一種這酒自己的香。沒有通常的醬香那么厚,那么醬,淺了一點,卻淺出些,多些清冽;回甘也不滯重,而像輕霧,氤氳浮動,持久綿長。無以名之,想起古人談書畫的韻致:“意在有無間”。
這就夠了。還有很多賞酒環節,我只管杯杯入口,一股熱氣直下胃腸,一團香氣回漾口腔鼻腔。我不是鑒酒師,掛不掛杯,不管;空杯留不留香,不管。只管再斟個滿杯。
問這酒的故事,陳國華說,酒廠建得晚,也是兩三代人了,一直努力把酒釀好。有興趣,來廠里走走。
那天席散,主人又贈我兩瓶。光瓶和醬綠瓶。
不幾天,又和朋友喝了。那香味又熟稔了一些,不再那么生分了。世間好多風味,開始陌生,如果真好,就能很快親近起來。
這挺好。我喝酒,醬香、濃香、清香都喝一點。有時還喝一點其它香。世界的多樣與豐富,于酒,也可鑒覽體驗。這多樣性,背后是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地理山河。
這樣過了大半年,今年春天,《山花》雜志李寂蕩來邀,和幾位作家去珍酒廠看看。
遵義。
這片土地上,好多酒故事。其中的茅臺故事,成為當代財富神話。另外的酒故事,漸漸被淡化了。去遵義尋美酒,變成就是去茅臺。這一回,不是去仁懷了。就到遵義近郊的珍酒產地。
典型的貴州天氣。天陰孕雨,云霧中飽含水分子,隨時要灑幾滴的樣子。一會兒又清風徐徐,吹散低云,現幾方藍天。典型的貴州地理。被雨水剝蝕融解的石灰巖和白云巖,造成小山重疊,溝岔交錯,小盆地四布。石子鋪、趙家溝,老廠區新廠區,都在矮山前盆地邊。兩三條溪谷中,七八點雨山前。苔痕上階,草色映窗。能酵能醞,是出好酒的地方。
在趙家溝看了制曲。也是頭一回,酒廠給看制曲。
古人稱曲為酒之始。以前,在鄉下見過家庭釀酒用的小曲。顆顆如大號藥丸。
蘇東坡愛酒,貶謫到廣東惠州,覺得那里酒味薄,以為是制曲的問題,于是親自動手改良。
他把這個過程寫了一篇短文,叫《東坡酒經》:“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汁,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
是說,原先用粳米和糯米,加上花藥制的曲,也算是好。但他加了麥,增酒厚味,加了姜汁,增酒烈味,這才得曲中精品。
但不能按方子照抄,因為那是前蒸餾酒時代的曲,小曲。
這里看的是制大曲。麥為主。蒸煮后,踩踏,入模。有傳說,醬酒端午制曲,踩踏者必是少女,香艷則香艷,我想大可不必。以前的小作坊,產酒量少,制曲也少,或許會如此辦理。今天的大廠,產量都以萬噸為計,怕是沒有那么多少女。
我看見的曲,真是大曲。
從模中翻出,長方形,趁手掂量,餅餅都有二十斤上下。四棱通直,中腹微鼓。這些餅平放在廠房地面,此時都已陰干了,正被男工們一一搬進曲房。曲房里濕熱,充滿發酵的味道。可以說,就是“霉味”。以前,大家不懂科學,怕說這個“霉”字,因為這相當于說是東西壞了。其實說霉味也沒什么不好。霉是真菌,能使谷物變質,散發這種味道,說明真菌們都在努力工作。
古人發現酒,就是因為霉變,飯放壞了,水果放壞了。
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
曲餅搬進來,上架,下面墊稻草,上面也包裹稻草。就是要一塊塊用濕熱的稻草捂著,讓它更熱,讓它發燒,讓它缺氧。這叫高溫制曲。
其實,這還不是制曲流程的全部,其前端還有母曲。母曲如何得來,沒有看見。
《尚書》中就說過了:“若作酒醴,爾唯曲蘗。”
古人說制酒六法:“秫稻必齊,曲蘗必實,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那六法,釀的酒未經蒸餾,濁酒一甕,痛飲三碗,也可過崗,還能打死老虎。今天醬酒制成,還要經高溫堆積,高溫蒸餾。三碗過后,即便是武松,也必躺倒山腳,自己作了肉餌,把老虎也醉了。如果真如此,就把醉老虎捉來,給武大郎泡虎骨酒了。
所以,那六法之中,在今天要緊的只是曲了。
至于喝多一點,遵義的喀斯特地貌,崗不高,也沒有老虎。還有山中清溪小風,清醒也快。有過體驗的,論好酒,就有醒后那個神清氣爽。
那天在釀酒車間,在勾調車間,一杯,一杯,又一杯,各種品嘗。出來,微醺。就想到那崗上找找老虎。幾百年前,徐霞客行于貴北山中,是聽聞有老虎的。
陳國華說,不上去,沒有老虎了。
進庫房,看見蔭涼中蹲著一口口千噸陶壇,深度空間,很安靜,卻恍然覺得,那些壇中酒,似要長嘯低吟一般。
石子鋪老廠。
廠區中一個岔路口,路口三方,建筑各帶鮮明時代風格。不同期的廠房代表建廠史上的三個時代。二十世紀70年代,八九十年代,再就是當下的今天。
參觀出來,我一個人又把三片廠區都周游一番。新廠區,載酒的卡車一輛輛去,又一輛輛來。
最老的車間建于1975年。
新酒廠也有故事。源頭卻在1958年。成都,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那次會在陽春三月,一開二十多天。
以前知道,會議期間,毛主席好整以暇,調看古人四川詩詞,并親手編成一本古人巴蜀詩詞集《詩詞若干首》。這一回,看到當年參會的貴州省省長周林的回憶文章。說:“記得在1958年中共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期間,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問我:‘茅臺酒現在情況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說:‘生產還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毛主席笑著說:‘你搞它一萬噸,要保證質量。’”
這求的已不是曠怡暢情的飲酒之樂,而是謀劃產業發展,意在經綸濟世,壯大國家財力了。早在古代中國,鹽鐵絲布之外,茶課酒稅,也是國家財政的收入重要來源。
于是,為增產擴能,也為探索茅臺酒易地生產的可能性及可行性,貴州省相關部門,決定在自然地理環境與茅臺接近,交通更方便的遵義市北郊建貴州茅臺酒易地試驗廠,進行易地生產試驗。
如今廠內最老的一號車間,就是那時所建。
建廠之初,生產骨干都是從茅臺酒廠精選。那是細胞的增殖分裂,為保證試驗順利進行,還從茅臺酒廠調來廠長、副總工程師、實驗室副主任,以及調酒師等技術人才。今天廠里好些干事的人,也是從茅臺酒廠來的。
建廠十年,都在試生產。經過九個生產周期,六十三輪次,三千多次分析試驗,在全國諸多科研院所支持下,在香味成分分析,微量元素分析,微生物鑒定等方面都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數據。
1985年10月,“易地試驗”項目通過國家科委組織專家鑒定:“該酒色清、透明、微黃、醬香突出、味悠長、空杯留香持久。香味及微量元素成分與茅臺酒相同,具有茅臺酒基本風格……”。“基本風格”,就是似也不似,這是一種新酒,不是茅臺。不獨茅臺,不獨醬酒,但凡中國白酒,同方曲蘗,同流程工藝,遷于異地,水土稍有不同,必有變異,必生新香;不然,中國白酒不會如此豐富,因香分派。
這一回,醬香酒又開新花一朵,方毅副總理為此欣然題詞:“酒中珍品——祝賀貴州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鑒定成功”。
方毅同志題詞,正是那試制茅臺酒定名為珍酒之由來。
廠名也從易地試驗廠改為貴州珍酒廠。珍酒定型生產,供應國內市場,還出口為國家創收外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珍酒廠也一樣經受考驗。改制成功后,更上層樓,如今年產量已經四萬噸了。
珍酒歷史不長,比我都年輕,是酒中少年,一步一個腳印,清清楚楚。不必背要講老故事的包袱,不必上溯千年百年,不必說皇家御用過沒有,地方做過貢品沒有,也不必說遇到神人點化沒有,它就是共和國故事,一個映照時代精神的中國氣派的中國故事。
再飲酒,桌上遇到吳向東先生,珍酒李渡集團董事長,也來陪飲幾杯。
說拿好酒來。酒上來,比珍三十又上一層,更醇香,更清爽。說是正在勾調定型的,明年要上市的珍五十。
明年,珍酒建廠五十周年。年輕的珍酒也有五十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