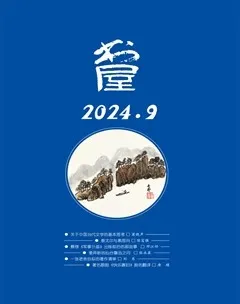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基本思考
關于翻譯文學
中國不但是人口大國,也是翻譯工作者最多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翻譯不僅是個人行為,同時也是單位行為。翻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生活大抵是有保障的(政治運動之大影響除外),年輕人的翻譯工作若被單位認可,往往也能像翻譯家一樣,有時間保障,有工資保障(起碼從前如此)。譯后也不必自己四處推銷,出版一向順利。還可評獎,評上了獎還有獎金,還可升級、升職稱。這使中國的翻譯隊伍一向后繼有人,翻譯事業穩步發展。
而這又使外國名著在中國的出版進行得如火如荼。所譯不限文學類,可謂類類皆有。從小說到詩歌到人物傳記,全集、選集、叢書,曾幾何時,進入書店,目不暇接,非常人所能讀得過來。若某一中國作家對外國文學情有獨鐘,是絕不會愁沒書可看的。外國著名作家的作品,在國內大多不止出版過一兩種版本。數據顯示,某幾年全國出版業的總銷售額中,翻譯書幾占一半碼洋。
我曾讀過一本中外幽默小說選集——第一篇竟是泰國小說,名為什么什么夫人(記不清了),內容是講一位三十歲左右的美婦人,從前幾任丈夫那里繼承了一大筆又一大筆的遺產。當地警察局長起疑,傳之親自細審。原來那美婦人不但深諳房術,還是烹飪妙手,實未加害前夫們,他們皆死于貪享食色。警察局長便不審下去,激動而呼:“我不畏死,我要離婚,向你求婚!向你求婚!”那是我讀過的唯一一篇泰國小說,領略了泰國式文學幽默。
中國也曾有過為數眾多的連環畫畫家,他們的水平堪稱一流。少年時期的我進入任何一家小人兒書鋪,都會從掛在墻上的小人兒書皮兒看出,起碼三分之一是由外國文學作品改編的,當年和現在一樣,所謂“外國”主要指的是蘇聯及西方諸國。1978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外國文學家的故事》,小開本的上、下兩冊薄薄的口袋書。其所屬的《少年百科叢書》此后十余年間累計發行六千萬冊,平均每年發行近六百萬冊。什么概念啊!還被評為1990年的中國圖書獎一等獎。
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人,希望通過書籍了解世界的心愿是何等強烈啊!而青少年們,則首先習慣于通過文學作品及作家們了解世界,當年一旦有新的翻譯書面世,必然可見排隊購買之洛陽紙貴現象。
我們應該承認,西方國家了解中國的意愿遠比我們了解他們國家的意愿小得多——從知識分子到一般大眾莫不如此。這也是為什么從前辜鴻銘將一部分孔、孟、老、莊、騷及唐詩宋詞譯為外文出版后,在國外讀書人中引起一時轟動。那時的老外到了北京,無不以見到辜鴻銘為榮,視他為當時之中國“最偉大的學者”,而他也只不過是譯者,只不過譯了小小一部分。
是不是從此就有很多老外對中國及中國文化、文學感興趣了呢?也不是的。多是多了點兒,卻多不到哪兒去。
這乃因為,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人,渴望快速地先進起來,于是眼睛總是望向西方,必然望向西方,開始以西方為標準,在文學藝術方面也是如此,甚至尤其如此。這種“拿來主義”總體上看,對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是有益的,起到了促進作用,但饑不擇食、拾人牙慧、盲目崇拜,扮作文學和文化方面的“假洋鬼子”,這種情況也是不爭之事實。
那么,西方人到底是怎么看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不得不用到“鄙視鏈”一詞。
在相當長的世紀里,西方人早已習慣了處在文化及文學鄙視鏈的上端。彼們即使也采取“拿來主義”,那也是互相“拿來”,優優互學,優優互補,就近“拿來”,方便“拿來”,相得益彰——是的,這就是他們的“拿來主義”。他們的眼,也是經常望向鄰國的,鄰國一有什么新思潮或新理念弄出了響動,往往很快就在整個西方產生呼應。彼們也不過是人,便也跟風。跟了一陣風后虎頭蛇尾,并無佳品就草草收場的現象不乏其例。
客觀地說,他們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漠然,并不完全由于鄙視,還由于譯者稀少。相比于中國力求語種全面的、水平優秀的翻譯隊伍,在西方諸國那兒,能譯中文者少之又少,而且翻譯是個人之事,出版往往大費周章。即使他們的漢學家,出本什么譯自中文的書亦非易事。在西方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互學互補一向是自給自洽之事,是“內循環”,目光并不望向很多方面落后的東方和中國,實在亦屬自然。好比建設家園,裝修房子,從來都是正要大興土木的一方去向可作樣板家園的一方參觀學習,反過來則不正常。
至于前者曾有怎樣的家風或曰傳統,那不是首先吸引后者的方面。
國與國也像家與家、人與人一樣,總是先看經濟實力后看其他的。
關于魯迅
我這一代作家,包括更多的喜歡文學的人,包括更多的喜歡讀書的人,誰沒崇拜過魯迅呢?
在幾代中國人心目中,魯迅乃是神一樣的存在。
我至今仍認為魯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成就最高。中國將“魯迅文學獎”設立為一項全國性的文學獎項,證明此點仍是共識。
但坦率講,如今的我,已不再將魯迅視為神了。我七十多歲了,已深知一個人間清醒的人,若被神化,等于是對那樣一個人的最大羞辱。
將人神化這一方式,往根子上說,是出于利用之目的。與從前的商家供奉財神、行會供奉關羽、丁口不旺的人家供奉送子觀音,心思相同。
然而以上畢竟還是出于非惡意的利用,魯迅也是每每被懷有惡意者別有用心地利用的。
不久前,我接受過一家外國媒體的采訪,對方是華人。幾番對話之后,他即從所謂“人種學”的角度,對我們中國人大肆侮辱,似乎中國人是地球上天生的劣種人類。
我忍著性子,問其根據為何。
他便抬出了魯迅,理直氣壯地反問:“阿Q、小D、華老栓、紅眼睛阿義,他們不都是典型的中國人嗎?他們身上體現了中國人的國民性,不是中國人自己首先承認的嗎?”
我問:“你是中國人嗎?”
他說:“我已經加入美國國籍了。”連愣都沒愣一下。
我又問:“僅在魯迅所處的時代,中國也有許多優秀人物,你承認嗎?”
他居然聳肩。
“胡適先生曾獲三十幾次博士學位,多數是外國著名大學頒發的,美國頒發的最多,你總該知道吧?”
“這我當然知道!”
“虧你還知道點什么。古代的就不提了,單說魯迅所處那個時代和以后吧。徐錫麟聽說過嗎?秋瑾聽說過嗎?辛亥革命了解嗎?方志敏、葉挺知道嗎?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知道嗎?八女投江之事知道嗎?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中國有千千萬萬的鐵血兒女為國捐軀,你承認他們身上體現的也是中國的國民性嗎?”
“打住,魯迅筆下可沒寫到他們!”
“那首先是因為魯迅死得早。你這個美國人,不是像你剛才自我介紹的那樣,在中國生活的時間長,在美國生活的時間短嗎?一成了美國人,曾經的同胞就都成了魯迅筆下的中國人了?如果我認為馬克·吐溫、福克納筆下的美國人是典型的美國人,那么你想聽我坦率地說出來,此刻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多么差勁嗎?”
他尷尬了。
我告訴他,我在五十幾歲時,曾寫過一篇雜文《阿Q和他的子孫們》,轉載率很高。我特享受這一過程,多一次轉載便使我多一分暗自得意,使我想象自己亦如魯迅般人間清醒,洞見通透而又所思深刻。仿佛,魯迅雖已成了歷史人物,他那不朽的光環仍可映到我身上,于是我自己也發光了似的。這是一種想象出來的優越心理——通過這種貶低同胞總體形象的方式,滿足了名利虛榮,暫時強化了自身的存在價值。
直至有一天,閑讀時讀到了一句話,如被電擊。
那句話是:“上天看人本同類,善惡區別一點心。”
講完,我對那采訪者說:“美國人,人也;中國人,亦人也。依我所了解的情況看來——美國有好人,中國也有。至于壞人、惡人、愚人,目前的世界上各國都有。《阿Q正傳》好就好在,如一面鏡子,是中國的魯迅提供的,可照出世界各國之人的人性劣根,自然包括你們許許多多美國人。至于是否包括您,您這位美國先生自己尋思。”
采訪分明無法進行下去,不歡而散。
過后,朋友主動與我手機通話,責備:“人家不遠千里回國,不過為了完成一項公干,好交差。你愿接話就接話,不愿接話可以繞過去。干嗎把局面搞得那么僵呢?有必要嗎?”
我說:“第一,‘回國’二字不適用于他,他已經完全將自己當成美國人,并將中國當成次等國,將中國人當成次等人類了。第二,他不但這樣,還打出魯迅的旗號,以阿Q為話題,企圖誘導我說出他希望錄音的話,用心不良。第三,你我可都是中國人,他的話也侮辱了咱倆。你不便反駁,我卻做不到忍辱不慍。在我家里,喝著我為他沏的茶,我為什么那樣?那就不是修養而是下賤了。第四,我沒必要浪費時間陪他這種假洋鬼子。很快就結束了,正合我意。”
在中國,很有那么一些居心叵測的面目不清的中國人,動輒祭出魯迅的旌旗,拿“國民劣根性”說三道四,弦外有音,仿佛今日之中國仍處在魯迅那個時代;仿佛今日之中國人,仍都是阿Q、華老栓、紅眼睛阿義、孔乙己;仿佛清醒著的中國人,除了死去的魯迅及他筆下的“狂人”,活著的僅有他們自己,并因喚不醒“睡在鐵屋子里”的國人而萬分痛苦。
總之,在他們眼里,中國什么都沒改變。
在我看來,他們患了“魯迅現象后遺癥”,正如西方某些人曾經患過“尼采后遺癥”。
上述人又分為兩類——一類想象自己是魯迅衣缽的傳人,于是在“精神鄙視鏈”上處于頂端,鄙視起億萬同胞來理直氣壯,以此鞏固自身的社會存在感,心態優越而自洽,活在舍我其誰的假象中。但若細看他們之人生,除了從一切方面抹黑自己的國家,貶低自己的同胞,其實從沒做過什么有利于國、有利于民、有利于社會的事。
如果說他們畢竟是病態之人,亦頗值得同情,那么,每祭出魯迅旌旗借題發揮,唯恐中國不亂的人,確實是別有用心的。
魯迅的作品,乃是中國文學的寶貴遺產。
魯迅作品所體現的文學批判精神,乃是中國文學的功能之一,理應繼承。
而以上兩類利用魯迅之名的人,每使魯迅文學遺產蒙上“負遺產”的銹色,每使文學批判精神變得稀缺而喪失應有的品質。
竊以為,有兩位歷史人物對魯迅的評價最客觀。
一是胡適。
他在魯迅死后說“魯迅是我們的人”,意謂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
毛澤東主席對魯迅的稱頌,主要是對此點的稱頌。
另一位是蔡元培。
魯迅逝世后,他在為《魯迅全集》所作的序中有言:“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
他還說,魯迅著述“蹊徑獨辟,為后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文學、文化的遺產,一再被神化,往往會走向反面。
秉持以上態度讀魯迅的書,溫情脈脈地理解他的為文為人,體諒其種種偏激和局限性,才算對得起魯迅先生。
關于文化自信
竊以為,文化自信與否,首先不取決于別國怎么評判我們,而取決于我們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當然,我們希望加速別國對我們的了解。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既然某些國家掌握文化及文學話語權的某些人對中國文化及文學采取雙重標準,已是連傻瓜都看得明白的事實(國內亦不乏居心叵測的應聲蟲),則清醒地評估我們自己的文化及文學之價值和意義,便不但必要而且必須。文化概念甚大,姑且不論。中國之數千年,文化源遠流長,絕非什么人所貶低得了的。那樣的人,自身之沒文化反倒昭然。
以下單議文學。
一
中國之現當代文學與新文化運動相伴產生,已獲文學史家們公認。
魯迅是中國“新小說”之先行者,乃不存歧見之事。
魯迅先生之“新小說”品質甚高,即使放在全世界十八世紀前后的中短篇小說中,亦屬上乘之作——我又盡量多地讀了些外國(也是指西方)中短篇小說后,說此話底氣頗足。魯迅先生的遺憾,也是我們后代作家替他感到的遺憾,乃是沒有長篇代表作。若有,中國及世界對他的文學成就的評價,當更高于現在了。
魯迅先生在世時,中國已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作家和詩人、戲劇家組成的文學方陣。除了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曹禺,還有郁達夫、葉圣陶、施蟄存及女作家丁玲、蕭紅、張愛玲、冰心、廬隱等。
廬隱的作品以短篇為多,中長篇也頗好,可惜這位有才華的作家三十六歲就因難產病逝了,令人扼腕。
最使我心疼的是幾位年輕作家的死——他們平均年齡才二十幾歲,就被國民黨殺害了。他們中的柔石,斯時已文名廣傳,他的小說《為奴隸的母親》與《二月》,真是好啊!
在詩歌方面,聞一多、戴望舒、徐志摩、艾青、田間、袁水拍也都成就斐然。
這一時期的中國作家群有一點功不可沒——使白話文寫作或曰“新文學語言”創作快速地刷新到了一種不可否定的階段。他們也有共同的一點令我尊敬,那就是總體上都追求進步。
同樣令人心疼的是——學者和詩人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而郁達夫也被日本軍方殺害于蘇門答臘。
日寇侵華戰爭之全面推進,使當時的中國作家們的創作,總體上陷入了難以為繼的中斷期,而他們又都處于創作最成熟的時期。
然而,若我們以傾聽的態度回顧歷史,排除崇洋媚外、自我矮化的卑賤,靜心而且凈心地細思忖之,則不會察覺不到——中國之近代,有著一種極為獨特的詩文遺產,構成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文學現象,那就是詩與文曾異乎尋常地與一批憂國憂民的人物發生過令后人肅然愴然的密切關系。
周恩來青年時寫的一首詩,最能證明這一種關系的內涵: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又如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葉挺的《囚歌》。還有夏明翰犧牲前的絕命詩:
砍頭不要緊,
只要主義真。
殺了夏明翰,
還有后來人!
以上詩與人的關系,何等驚天地、泣鬼神!如普羅米修斯的詩性自白,如丹柯之詩性踐行。
而毛澤東主席在長征途中口占于馬背的多首“馬背詩”,則表達了工農紅軍在經受最嚴峻之考驗、存亡每每系于一線狀況下的大無畏英雄氣概。
至抗戰時期,又有東北抗日聯軍的楊靖宇將軍為抗日聯軍所作之《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軍歌》、李兆麟將軍所作之《露營之歌》,此外還有抗聯《第三路軍成立紀念歌》《保衛白山黑水》《反侵略戰歌》《團結抗日贊歌》《兒童抗日歌》,等等。
《松花江上》一首歌,其實并非東三省向關內流亡的青年所作,而是河北定縣一名喜愛音樂的青年,在西安街頭眼見同齡人缺衣少食、無家可歸之狀,心生悲憫,噙淚創作的,算是關于歷史歌曲的一段佳話。
之后,產生了《義勇軍進行曲》(即后來的國歌),產生了《在太行山上》,產生了《黃河大合唱》《新四軍軍歌》《大刀進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抗日歌曲。已成名的詩人艾青、田間等那一時期也各自創作了在人民大眾中流傳甚廣的、激勵人民團結抗戰的“口號詩”。
古代的中國曾是詩性之國,樵夫漁父、牧童村姑、鄉賢和尚中,皆有善詩者。中國曾有過放諸世界亦敢當的文學高峰現象嗎?當然有!
唐詩宋詞便是。其驚人的數量,其多彩多姿的風格,其幾可言包羅萬象且思想境界高遠的內容,舉世無雙。
小說呢?
確乎,近代以來,我們沒有托爾斯泰,沒有雨果和巴爾扎克,甚至也沒有狄更斯。但將目光再往從前望過去,中國的“四大名著”以及《聊齋志異》《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儒林外史》所組成的小說現象,在世界上無疑處于高峰。
抗戰時期,眾多為國家命運出生入死、肝腦涂地也在所不惜的英烈,他們的日記,他們寫給父母、妻子、兒女的家書,在我這兒,也被視為文學現象之一:紀實的那種。既然《絞刑架下的報告》《死屋手記》被視為“特殊的著作”,那些在中國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由抱定戰死之決心的中華兒女寫于赴戰前夕,甚至寫于前線、寫于指揮所、寫于負傷情況下的家書,何以不能是?如此點在邏輯上是成立的,那么那些家書,即那些若編輯成書便可言之為“特殊的著作”的歷史文獻,則使抗戰時期的中國詩文更加具有中國特色。那乃是被戰火與血光重染的特色,如刑天之怒吼,如以刺刀和匕首刻寫在中國大地上的史詩。
二
新中國成立后,以上一批作家、詩人基本沉寂:有的擔任了各級文藝界的領導,有的對于反映“新現實”一時尚難適應。
然而一批從延安進入各大城市或由部隊轉業到地方的、年富力強的“紅色”作家和詩人開始成為創作主力。《紅旗譜》是我當年所喜歡的,《戰斗的青春》也喜歡。
后來,自以為有了點兒評價資格后,覺得在“十七年”小說成果中,還是反映抗戰內容的小說水平更整齊一些,如《野火春風斗古城》《苦菜花》《平原槍聲》《鐵道游擊隊》《風云初記》等。
當年,沒有哪個部門為中學生列出必讀書單,但《紅巖》確乎是多數文學青年都讀過的,出于對革命先烈的敬愛。該小說中多處情節震撼了我,至今我也不認為,震撼我的純粹是文學力量。因為我已更加明白,小說中的一些人物,并不完全是虛構的,很多是以真人真事為原型。
事實上,我對所謂文學的“純粹性”存疑久矣,大多數名著都不“純粹”,此二字騙人。
我參加兵團創作學習班時,曾與是學員的知青們討論過《創業史》,大家都認為作者寫人物寫得十分內斂,因而顯得“老道”,卻都自言那“老道”學不來,因為我們尚處在心浮氣躁的年齡。
較之于前輩柳青,當年的我們都覺得學趙樹理更容易些,他作品中的幽默元素,乃是當年中國長篇小說中少見的,這種幽默成為我們心向往之的能力。
我不知現在的評論家們如何看待《林海雪原》,但我覺得,一部長篇小說若有一個核心情節具有經典性,那么其經典性便值得后代作家刮目相看。
“舌戰小爐匠”是《林海雪原》的經典情節,正如“智斗”是樣板戲《沙家浜》的經典情節。經典即精彩。
有經典情節的小說不見得必定是好小說。
沒有經典情節的小說必定稱不上好小說。
“十七年”的長篇小說成果并不算大,平均每年兩部左右,題材不夠豐富,風格也不夠多樣。然而在詩歌和中短篇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方面都有可喜的收獲,一批特別有才華的年輕作家和中年詩人(創作小說者年齡大抵三十歲以下,詩人們的年齡卻要大十歲左右),所奉獻的作品每每令讀者耳目一新……
三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始,中國文藝界迎來了“春天”。“春江水暖鴨先知”,用這句詩形容當時的文壇極為恰當。起先是老中青三代作家和詩人即1949年以前和以后成名的,加上適時自然形成的“知青作家群”,通力營造了一種活躍又碩果累累的創作局面,時人形容為“井噴”。此現象不僅帶動了多種文學體裁的復蘇,如久違了的回憶錄、報告文學、人物傳記、散文、隨筆、雜文等大量產生,佳作多多;同時,亦促進了戲劇、電影乃至歌曲的繁榮。
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以王朔為主的“新生代”作家異軍突起,于是引燃了其他省市“新生代”作家們的創作“禮花”,為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了別樣題材別樣情,使“井噴”現象持續不斷。
對于這十年中國文學總況的評價,文學界過來人的看法較為一致——那是近代以后亦即新文化運動以后的又一次文學繁榮期,而且是高峰期。這“一致”并非由于曾經參與其中而主觀情濃、沾沾自喜。實打實地說,否認此點倒是不客觀了,因為有成果在文學史中擺著。
我個人認為,其繁榮實際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繁榮之上。今日之中國文壇主力作家,大抵本身是那一時期所“孵化”的“成果”。當年,每期發行幾十萬上百萬冊的文學刊物達十余份,亦可佐證。
那是一個泱泱大國中的文學讀者也熱忱參與其中的宏大的文學現象,亦是無須倡導甚至無須怎么宣傳更無須炒作(當年的文學界和出版界還都不懂炒作,甚至鄙視炒作),口口相傳便會使好作品廣為人知,使刊物和書洛陽紙貴的現象。
“新冠疫情”期間,我靜下心來讀了西方幾國的文學史,故敢不乏底氣地說:中國那十年的文學繁榮期,亦可用“盛況”形容。以比較之法擺在全世界來看,其時所涌現的作家之多,代際之分明,延續期之長久,作品數量之眾,佳作之頻現,對后來乃至現在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之深,都可謂世界級文學現象,非別國某一時期的文學現象所可同日而語。
俱往矣。
四
時至今日,令我記憶猶新的當代長篇小說如下:
《白鹿原》《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穆斯林的葬禮》《將軍吟》《冬天里的春天》《平凡的世界》。
《白鹿原》每使我想到《紅旗譜》,兩部小說之名相當對仗,幾近工對。《紅旗譜》是我少年時喜歡看的小說。當年我這一代人所接受的歷史教育乃是,農民和地主的關系、長工和東家的關系,是絕對對立的關系,甚或是有血仇的不共戴天的關系,簡直也可稱之為“天敵”的關系。《紅旗譜》以文學的方式加強了我的這一認知。
《白鹿原》則不同,它描寫了另一種歷史狀況:若東家是一個好人,即一個一心要做“鄉紳”的人,那么其與長工、雇農的關系,便有可能不那么對立,甚至可能是唇亡齒寒的關系。“鄉紳”之所以為“紳”,因其行事較為顧及“仁”矣。“仁”是儒家思想核心,不親儒敬儒不配做“鄉紳”。白嘉軒便是農村里一個頗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人。這樣的人在近代歷史中存在過嗎?千真萬確是存在過的。
抗戰時成立于延安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便公選了一位具有“鄉紳”風范的李鼎銘先生為副主席。李鼎銘先生不但久經儒家思想熏陶,而且與時俱進,對民主思想抱持理解和擁護的態度,故他又被尊稱為“民主人士”。
聞一多先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岳父任過縣令。地主若不大,與縣令便結不成親家。聞一多先生在他的回憶性文章中多次談到他的父親,其父分明是一位儒家思想與民主進步思想兼而有之的父親。
那等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中多嗎?
這我就不詳知了。我靠閱讀間接了解的情況是,大約每省都起碼有一位的。他們不但同情革命,往往還暗中掩護革命者,協助革命。
儒家思想果然能調和階級矛盾嗎?
我的回答是,從大歷史觀看,肯定不能。但在外部因素并不構成種種壓力的情況下,在相對封閉的局部環境中,若生存條件優上者以“仁”為行事原則,則階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一個時期內或能得以緩和。
我不會以《白鹿原》來否定《紅旗譜》的文學價值,那在大歷史觀上會陷于昏聵;也不會以《紅旗譜》來否定《白鹿原》的文學價值,那在全歷史觀上會自蹈于狹隘。
在我看來,認可這兩部小說的文學價值,有益于擴展自己歷史觀的格局。但我并不認為《白鹿原》白璧無瑕:白嘉軒似乎更是一個天性上的善人,而他理應也是一個有思想特點的人,此特點若不從思想方面有意揭示,則整部作品的思想色彩被故事性沖淡矣。即使我這樣認為,也還是欣賞其不尋常的、獨一無二的文學價值。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每使我聯想到《創業史》。《創業史》之上部出版后,柳青先生遲遲沒有寫出下部來。原因自是多方面的,但柳青先生當時肯定不只是困惑,或許也還預見到了什么。
若此推測不謬,那么周克芹先生通過《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與柳青先生的預見“接軌”了。
周克芹先生與柳青先生一樣,都是不但熟悉農村生活,而且對農村和農民深懷感情的作家。《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是感情之作,也是具有明確批判意識的小說。因有感情而批判,在當時的出版情況下,其批判不可能不是內斂的。
我還常將《平凡的世界》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聯系起來,想象孫少平和孫少安兄弟倆是許家姐妹的甥或侄,總之是比她倆小一輩的人,于是趕上了農家子弟可以進城打工的時代,于是有了不同的人生追求,演繹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農民后代的故事。
又于是,某些農村題材的小說(包括電影)在我這兒都可串聯在一起……
《紅旗譜》《白鹿原》《暴風驟雨》《創業史》《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人生》《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平凡的世界》,電影《豐收之后》,再接上《山海情》等新農村題材的電視劇——那么,從近代至現在,一幅文學與影視作品組成的、關于中國農村隨時代而演進的歷史性畫卷似乎呈現在我眼前了,也許還不全面,但基本若此。這種畫卷不同于史書的方面是,仿佛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代替了數字的、沒有生命感和人間煙火氣的行話,而且有溫度,有創作者的情懷元素。
若作者通過作品參與了這一畫卷的“集體創作”,那真是一件足夠幸運的事。
若讀者所讀較多,而不是管中窺豹、盲人摸象,只讀了一兩部小說就自以為茅塞頓開,便斷不會人云亦云,或覺得掌握了全部歷史真相,聽不進任何不同觀點。
獲此等大裨益是讀者之幸。
《芙蓉鎮》是獲茅盾文學獎的小說中廣為人知的作品之一。故事以特殊年代的小鎮為背景——中國以小鎮為背景的小說甚少。從前,《阿Q正傳》是,柔石《為奴隸的母親》和《二月》是,葉圣陶的《倪煥之》是,茅盾的《倒閉》(即《林家鋪子》)也是。但1949年后,同類長篇僅《芙蓉鎮》一例。《小鎮上的將軍》是短篇,陸文夫的《小巷深處》寫的是小城中的小巷,正如《小城春秋》寫的是發生在小城里的革命故事。
所以,《芙蓉鎮》具有拾遺補闕的特殊意義。并且,它將“十年動亂”期間南方小鎮人與人的不正常關系呈現得十分到位,對“極左人物”的諷刺性描寫惟妙惟肖,同名電影則擴大了這部好小說的影響。導演謝晉藝術功力深厚,年輕演員姜文和劉曉慶表演可圈可點。但此部電影意外的收獲是,飾演鎮“革委會”主任的女演員也由此被觀眾牢牢記住了,她將“左”演成了一種似乎與生俱來的并且非常自洽的病,但這給她帶來了“不幸”,使她體會到了演員前輩陳強演過黃世仁后幾乎成為“招人厭”的無奈。
《將軍吟》中的將軍,在“十年動亂”期間也難逃被人構陷的命運,便也尊嚴難保。構陷得了將軍的人,自然非等閑之輩,乃是他曾經的革命戰友。結合《冬天里的春天》來看這部長篇,會同時加深對兩部長篇的理解。后一部長篇中的主人公,為了替往昔的戰友洗冤,多次故地(當年出生入死干革命的地方)重游,四處走訪,進行了一次屬于個人行為的旨在替好同志收集證據的“平反”工作,其間接觸了各種各樣的群眾和干部,便也等于對各種各樣的人進行了一次人格巡視。
《人生》《老井》《黑駿馬》——此三部中篇,當年是我學習的佳作,都是獲全國中篇小說獎的作品。
《人生》中的高加林是有高中學歷的農村青年。他有機會多次進過城市(地級市),親眼見到了城市人生活的“高級”(其實,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地級市的人們,生活雖比農村人強些,但也強不到哪去)。于是高加林的人生有了方向,成為城里人遂變成他人生唯一又強烈的追求。但是,在當年,一名農村青年想要擁有城市戶口,難于上青天。高加林的優勢在于,顏值高,學習好,讀了些文學作品,較之普通的農村青年,顯得彬彬有禮,因而獲得了地委書記的女兒(他倆是高中同學)的好感。而他要實現想法的最大障礙是已經有對象了,他與同村的巧珍不但是對象還是青梅竹馬的關系。在當年,對象關系是受“道德法庭”保護的。并且,巧珍是公認的好姑娘,高加林曾經非常愛她。
在城市戶口與巧珍之間,高加林選擇了前者。他提出與巧珍分手時,“道是無情似有情”。究竟愛地委書記的女兒更多些,還是愛城市戶口更多些,估計連高加林自己也說不清。在他那兒,二者是合而為一的。
當然,他最終竹籃打水一場空,學籍也沒了,成了人人皆可鄙視的典型負心漢,連從前那個在村民眼中是“農村好后生”的高加林也做不成了,即所謂的“人設崩塌”。
此前,1949年后的中國小說、戲劇和電影中,非先進模范之人物而成為主角的情況十分罕見。連《劉巧兒》中的巧兒(女),自由戀愛的對象還是勞模吶。我所讀過的小說中,僅鄧友梅前輩的《在懸崖上》和蕭也牧前輩的《我們夫婦之間》主角不夠先進;電影也僅有兩例——《新局長到來之前》和《不拘小節的人》,皆諷刺電影。雖罕見,當時作為一種現象也還是受到了批判,被歸納為“寫灰色人物”,結論是“絕不許灰色人物污染社會主義文藝”。
毫無疑問,高加林也是典型的“灰色人物”。
同樣毫無疑問,《人生》突破了長期以來的創作禁區。并且,寫得好。
當年,有人認為高加林是中國版的于連,這說法靠譜,只不過高加林沒鬧出案件來,故不必死,命運比于連強。
當年,有評論家認為,路遙必定受了《紅與黑》的影響。我覺得,他不可能沒看過《紅與黑》,但《人生》之創作卻未必與《紅與黑》有多大關系。倘并未關注到一樁案件,司湯達斷不會寫出《紅與黑》。而即使沒讀過《紅與黑》,也會由有農村成長背景的中國作家寫出高加林的故事,區別僅僅在于,小說未見得叫《人生》,作者未必是路遙,寫得未必比路遙好。《人生》是當年現實生活的結晶,不論由誰創作,首先都是服從了現實生活的指令。
“背井離鄉”之“鄉”乃是農村人口和行政屬地,而“井”是農村人的家園地標——古老,最矮,卻又最有深度,象征義多。有學者認為,“背井”之“井”,原是“井田制”之“井”,實際指的也是“田”。這是太專業的學問,且不較真,在這里仍以汲水之井論之吧。
中國之西北缺水,這是今人大抵了解的,但在當年,由于信息傳播方式有限,飲用自來水的城市人是不太知情的。關于《紅旗渠》的新聞紀錄片使有些人了解了這一情況,但也僅限于常看電影的人而已(紀錄片加演于正片之前),當年中篇小說《老井》的發表,使關注的人變多了。
若西北某村僅有一井,而即將干涸,那么茲事體大,問題嚴峻了。《老井》風格寫實,生活氣息甚濃,字里行間充滿了作家對農民的深切體恤。吳天明將它拍成了電影,張藝謀演主角,擴大了小說的影響力。它每使我聯想到反映農村教育問題的小說《鳳凰琴》。竊以為,若一部農村題材小說之發表,引起了各級政府對關乎農民實際生活困難的重視,從而出臺解決措施,當是作家的光榮。
張承志是回族作家,曾是內蒙古知青。《黑駿馬》是他的代表作,當年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黑駿馬》是回族知青作家向內蒙古人民回獻的文學哈達,表達了作家對蒙古族人民生活態度、生命態度的禮贊。小說中的老額吉(媽媽)給人以“草原之母”的聯想,“妹妹”則代表草原的也是蒙古族的未來,寄托了作家情真意切的祝福。“黑駿馬”是蒙古族的古老傳說,在蒙古族歌曲中經久傳唱。它有不死之魂,若主人思其甚切,或遭遇了危難,它會適時出現,使主人化險為夷,給主人帶來吉祥。顯然,對于作家來說,草原母親及跨民族跨血緣的親人們,如同“黑駿馬”;反之,作家也愿做草原親人們的“黑駿馬”。此種雙向的情感、情懷、情愫、情結的表達,不難領悟且讀來令人心暖。
《桑樹坪紀事》既是知青小說,也可以歸入農村題材中去。實際上,幾乎全部知青小說都具有這一雙重性。但多數知青小說的主人公,是主要情節和矛盾沖突的引發者和卷入者。《桑樹坪紀事》擺脫了這一模式,知青退居見證者的位置——頗似《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大學生尼克——這樣,山民們就成了主要人物群像。它是當年唯一一部由知青作家創作的,并非寫自己,而旨在寫“他者”即山區農民的小說。寫到了他們的民俗,也是該小說的一大特點。
若將《人生》《老井》《桑樹坪紀事》歸入前邊所串聯的農村題材小說中,再加上賈平凹的《雞窩洼人家》《臘月·正月》,將使那一文學性的中國當代農村變化史、發展史的內容更加豐富厚實。
在當時,即從二十世紀七十年末到九十年代初,王蒙、陸文夫、高曉聲、鄧友梅、李國文、馮驥才、蔣子龍、汪曾祺、張弦、張賢亮等前輩,為短篇小說創作的多種可能性都提供了用作品說話的范例。
張賢亮是因短篇小說《靈與肉》而成名的。當年評論家閻綱評《靈與肉》的文章開篇第一句話是:“寧夏出了個張賢亮。”——當年的評論家對好作品往往“視如己出”,不太會看走眼。小說中的男主人公許靈均結束了被改造的命運后,放棄出國繼承大宗遺產的機會,甘愿留在牧場與患難之妻共同將人生繼續下去,這在今天的青年們看來肯定是不可信的,會覺人物太過理想化。無獨有偶,就在作家陸天明2023年出版的新作《沿途》中,主人公遇到了與許靈均同樣的情況,也做出了同樣的抉擇。
五
怎么看這種不約而同呢?
我想,將小說中人物擺放在當年的歷史背景下,也許便好理解一些。
須知當年之中國人,大抵沉浸于“春天來了”的喜悅和鼓舞之中:“教育的春天”“文藝的春天”“科技的春天”“法制的春天”……當“許靈均們”終于熬過了人生中苦難而漫長的“冬天”,想要享受“春天”來臨后的新生活,想要看看以后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則是較自然的事了。何況美國對他們來說是那么陌生,起初的他們害怕成為外國人,像《海上鋼琴師》中的“1900”害怕離開客輪,踏向岸邊。
我一直認為,張弦的作品當年被評論得很不夠。他的筆曾涉及獨特的創作領域,即反映某些知識女性、官員夫人之第二次婚戀的感情糾葛,如《掙不斷的紅絲線》《未亡人》等,這在后來也是中國小說較少涉及的題材。可惜他去世得早,否則會為中國文學奉獻更多的佳作。
鄧友梅的《那五》《尋訪“畫兒韓”》在當年也是別開生面的。他是“京派”小說的發揚光大者,使老舍風格不但得以延續,而且具有了當代元素,煥然一新。
陸文夫、汪曾祺、高曉聲都是出生于江蘇的作家。高曉聲的短篇像白描畫,對話極少,幾乎不進行心理呈現,全靠精準的文字線條刻畫人物,卻能使人物栩栩如生,“白描”功夫十分了得。汪曾祺的短篇則每令我聯想到豐子愷的文人畫,并且他自己也是真的興之所至時弄弄丹青的。若論文人畫,在當年,豐子愷首屈一指。他的畫主要集中于《護生畫集》,取材于民間生活,江南氣息充沛,善意恒然有溫度。汪先生的短篇也是那樣,即使寫的是悲傷的故事,亦慈悲在焉。陸文夫便又不同,他之短篇、中篇的背景一向是城市,其實便是他久居的蘇州。《小巷深處》是“理”的叩問,到了寫《井》,寫《美食家》時,“哲”的意味明顯了。而《圍墻》,不動聲色的批判鋒芒顯露,這是他與汪先生、高先生最不同處。后兩位先生的短篇有“出世”況味,或曰“入”也是“入”到大眾生活的日常中去。文夫先生的創作意圖每在“出”“入”之間徘徊,最終卻還是“干預生活”的。“井”何以為“井”,“墻”何以難拆,這是陸文夫老師總想的問題。
張弦是活躍于上海、江蘇兩地文壇的作家。他逝世得早,老天對其大不公也!
李國文老師是主張“文以載道”的,卻又一再強調文學的多功能,作家不必一味地“載道”。實際上他強調的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載道”總會有些風險的。進言之,他自己是一向“載道”的,卻希望年輕作家享受自由的創作空間。他的《月食》是有深度的“載道”之作,他自己一生都在“載道”,唯恐不及。
蔣子龍先生是中國工業題材小說的闖關人。工業題材難寫,他的《喬廠長上任記》當年是破冰之作。在我看來,其后的《鍋碗瓢盆交響曲》尤其值得點贊。他當年已是中年作家了,竟在小說中塑造出了朝氣蓬勃又個性鮮明的青年工人群像,足見他那時的創作心態仍多么年輕,也足見“工”字連著他內心里多么大的情愫!
王蒙老師的《堅硬的稀粥》智慧又堅硬。智慧性是他一向的風格,堅硬性倒是一反常態,又智慧又堅硬,便幽默,卻又寫得特嚴肅。我認為那是他最中規中矩的短篇,也是批判意識最強的短篇。
我對馮驥才老師的短篇小說的欣賞始于《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止于《俗世奇人》。前者有幾分散文的風格,后者可視作當代的《聊齋志異》,他用文字為老天津衛留下了浮世繪式、山海經式的畫卷。
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都是知青小說,也都是當年獲全國短篇小說獎的作品,我當年讀過多遍——因為欣賞。“清平灣”也罷,“茅草地”也罷,皆窮鄉僻壤,卻言之為“我的”,還一望再望,每使我聯想到“數重云外樹,不隔眼中人”兩句詩。都言“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清平灣”和“茅草地”絕無富人,人皆窮也。遙望頻頻,魂牽夢繞,個中深情,令我動容。知青是各式各樣的,知青作家對自己的知青經歷,感受不盡相同甚或十分對立。我尊重每個知青對個人感受的任何方式的表達,不論其是不是作家。但史鐵生和韓少功兩位的文學表達在我內心中是經典,是另一種心靈史。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天云山傳奇》是當年對“十年動亂”中“極左”現象之批判尤為有力的作品。
據我所知,《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是以真人真事為創作基礎的——時年天災嚴重,某地農村斷糧,數千人之命危在旦夕。李銅鐘身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找到糧站站長“借”五萬斤糧食,拯救數千人命,自己卻因過度饑餓和勞累而病亡。當年我讀此作,胸如壓磨,呼吸困難,幾番掩卷哽咽,心靈震動矣。
《天云山傳奇》雖有“傳奇”二字,然極寫實。它是當年一部反映“動亂時期”知識分子關系的中篇小說,考察隊政委因言獲罪,被開除公職。未婚妻在壓力下違心別嫁。所嫁之副書記正是一手制造她未婚夫冤案的人。但該小說有兩條情節線——雖“黑云壓城城欲摧”,卻有挺身而出正義人。一位女隊員仗義執言,力駁謬罪,卻也被開除了公職。
此作品由著名導演謝晉拍成電影,片中一段情節感人至深,男主人公不幸被瘧疾纏身,高熱以致昏迷,女主人公以人力爬犁載之,去往自己在山村的老家。時逢大雪封山,雪深及膝,寸步難行。于是,舊情已了,新愛始焉。一段患難之戀,蕩氣回腸,催人淚下。觀眾(我是其中之一)屏息斂氣,影院靜若無人。
此陳年舊事也。所以憶述,非別有用心,乃因數聞有外國漢學家、作家、文化人士之類,常言中國之文學“喪失了批判功能”云云,難核真假,且些個國人(不知真實身份的中國人),打著外國人的旗號,亦以各種方式如是說,我便覺有必要在本書中回應一下。
不知者不怪。起碼,看了此書的人,以后便知一二,大約不會再配合外國的這個家那個家隨幫唱影了。
至于那些明知而配合的人,實不知他們是怎么想的,不說他們了罷!
(梁曉聲:《不裝深刻》,中信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