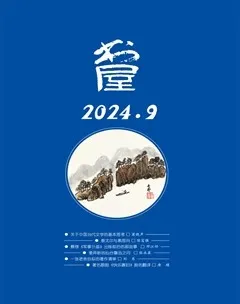我的同事梁曉聲
雖在大學時代,我便已熟悉梁曉聲的文名,但因自己一直熱衷于西方經典作家的深閱細讀,實際上并未舍得把更多時間留給他的作品,以至于連他的成名作《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也是只知其名,從沒有過了解的沖動。如今想來,令我初次對梁曉聲的小說產生印象的作品應該是他題為《冰壩》的一個中篇,記得當時是在《中篇小說選刊》上讀到的。該作敘事老道,主題新穎,營造出的緊迫氛圍如同黑夜里的海嘯悄然襲來,與我想象中的梁曉聲不大一樣。原來,他竟然有著先鋒性的一面。
原本以為,被視作“知青文學”代表的梁曉聲應該是現實主義的,而現實主義在我眼里無非是循規蹈矩的。可《冰壩》所呈現的現實主義卻有著超越傳統模式的鮮明現代意識,通過它不難發現,當梁曉聲試圖以某種強烈的危機感來體現自我的現實關切時,他便能不可抑制地爆發出超越生活的想象力。毫無疑問,作為與新中國同齡的作家,拜時代所賜,梁曉聲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這是他的優勢,然而這種優勢同時也難免不是某種限制。事實上,一個作家要是過于依賴自身的現實經驗,他的現實主義創作就必然會陷入用事實替代真實的困境。畢竟,寫作是思考,是創造,從來不是復制和轉述。《冰壩》難能可貴地規避了現實主義創作的窠臼,讓我從中見識到梁曉聲的寫作才華,盡管他關注的題材根本就不是青春時代的我所喜歡的。
有鑒于此,我沒有追蹤閱讀梁曉聲的小說,倒是他常常出現在期刊上的散文引起了我的注意。顯然,這是個有故事的人,也很會講故事。過往的風輕云淡,此刻的人情世故,他總能用最打動人心的方式向我們娓娓道來。在這些故事里,我看到了苦難,也看到了溫暖,看到了悲傷,也看到了幸福。每每聽到時下作家們在探討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問題時,我便會想起梁曉聲的散文,它們不就是最好的中國故事嗎?
已然在魯迅先生那里領教過太多負面國民性的我們,透過梁曉聲散文中這些樸素平靜的文字,則能見證國人極為高貴的一面。他們隱忍,他們良善,他們天真,他們無私。他們可以吃下全世界的苦,卻不肯輕易享受得來不易的些微之甜。若是讀過《父親》《普通人》《兄長》《王媽媽印象》等篇什,我們就能懂得,中國人不善言愛,他們不習慣說“我愛你”,他們只會說“我疼你”。從梁曉聲散文里的蕓蕓眾生中,我體會最深的即是這樣的“疼”。疼本屬身體的不適狀態,它意在借助甘愿讓個人身體承受痛苦的方式,來表達對于對方的牽掛和憐惜。
這里的“疼”是自我犧牲,所在乎的不是同甘而是共苦。向來如此,中國人不追求幸福,他們只知苦中作樂,似乎是被幸福遺忘的群體。我不清楚這樣的同胞是不是可愛的,但我十分確定的是,他們是值得被善待的。梁曉聲散文里的那些人物極易使我落淚,他們令我意識到,我的淚水正是心疼的產物。我也由此再度理解了我們的古人何以那么愛流淚,這淚水就是真誠之愛的語言啊。故此,艾青會在詩中寫道:“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基于這樣的印象,我更重視的只能是梁曉聲的散文,而非他的小說。所以,雖然時常見他有長篇新作問世,我依舊表現得漠不關心。1998年,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我的導師曹文軒教授需要我協助他編選一套共和國五十周年文學作品選,在遴選小說篇目的過程中,我特意瀏覽了梁曉聲的近期作品,仍然覺得還是他的散文最出色,因而遲遲決定不了到底該選他的哪一篇小說。在我的認知里,小說必須同現實保持一定距離,而梁曉聲的小說與現實卻是幾乎沒有距離的。
作家關心現實固然是好的,但用小說直接介入現實勢必會敗壞小說的品位。小說自成現實,甚至對抗現實,讓它俯就現實自然是不可取的。在我看來,梁曉聲與其這樣寫小說,還不如繼續寫他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吧?不過,梁曉聲終究是作家,不是社會學家,《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僅是他的文學余興產品而已,它遠遠滿足不了梁曉聲對于這個世界的思考及熱愛。文學是他的歸宿,他從那里來,也一定要回到那里去。
再次將梁曉聲和我拉近的,是首播于2000年的一部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作品始終存放在我兒時的記憶里,對我的成長產生過深遠影響。為了能重溫它,我設法從同學那里借來一個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黑白電視機,每晚待在宿舍里觀看。回憶歷歷在目,那些個心潮澎湃、思緒萬千的夜晚啊!至今,我的耳畔還時常會回蕩起那首激動人心的主題曲:
遠處的河岸點起了燈火
晚霞消失在晴朗的夜空
跨上戰馬背起長槍
年輕的布瓊尼士兵整裝出發
跨上戰馬背起長槍
年輕的布瓊尼士兵整裝出發
……
這部電視劇的編劇就是梁曉聲。他能把這部蘇聯時代的文學經典改編成電視連續劇,讓我不由得對其心存感激。特別是結尾處那濃重的懷舊感傷基調,非常契合我對這部作品的情感,甚至比原著更符合我的期待。由此我也終于認識到,在梁曉聲和我之間還是存在著某些共鳴的,即便我們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年齡上的代溝。但這并未妨礙我們都喜歡保爾,不,我們都更喜歡冬妮婭和麗達。年少時不懂愛情,只要革命意志,歷經滄桑之后,才明曉什么是生命里最珍貴的。我想,梁曉聲針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改編,不單單是為了致敬或者懷舊,他更是為了重新認識歷史,認識自己,是向青春進行的一次虔誠懺悔。一個時代賦予我們的激情和狂喜,唯有在沉寂已久的回聲里,方能讓我們真正聽清它的話語。
雖說我已有那么久不看電視,但是最近卻很想再看一遍這部電視連續劇。轉眼間,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的確有點想它。為了保爾,為了冬妮婭和麗達,也為了梁曉聲。那時我尚不知道,我正在走近梁曉聲,或者說梁曉聲正在走近我。同年7月,我獲得博士學位,入職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幾年后,梁曉聲也從北京電影制片廠調到了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我們成了一個教研室里的同事。
說實話,最初我并不希望梁曉聲成為我的同事。不知何故,那時忽然開始冒出作家進高校的苗頭,時有某著名作家調入高校任教的新聞,我以為梁曉聲也不過是為了趕這個時髦罷了。而對于作家能否勝任教授這個職位,我一向是明確持懷疑態度的。眾所周知,那個時代的中國作家極少科班出身,高學歷作家更是罕見。沒接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又怎么能給大學生,甚至是研究生上課呢?何況,對一些作家進入高校后讓人不敢恭維的狀態,我又有所耳聞。
但縱使我再怎么不歡迎,梁曉聲也還是來到了北語,因為人家壓根兒不需要我的歡迎。第一次見他,是在學院的會議室里,全體教職員工對他的加入表示了熱烈歡迎。向我們一一致意的梁曉聲顯得溫和而又謙遜,可這并不能打動我,我只想等著觀察他此后的表現。會后,在教研室里我們有了面對面的接觸。我稱呼他“梁老師”,他稱呼我“小路”,稱呼別人,他則喜歡用“親愛的同志”。
梁曉聲的衣著相當樸素,挎著一個帆布包,既不像作家,也不像教授,更像是某個工廠里的技術工人,但他說起話來卻極富親和力。幾分鐘的工夫,他便讓我們之間沒有了陌生感。得知我也從事小說創作,梁曉聲頗有些意外,并即刻將我視為他的同道,話題開始朝著當下的文學現狀深入。第一次見面結束,我已完全忘記了自己對他的不歡迎,他似乎早就已是我的同事。我轉而開始慶幸他的到來,他讓我在這個文學空氣稀薄的中文系呼吸到了久違的新鮮氧氣。
之后,梁曉聲便成了最能與我聊得來的同事。每次見面,他總喜歡問我需要他做些什么,需不需要用錢。雖然我對他的了解僅是開始,卻分明能夠感覺到他的這些話絕不是出于客套。果然,他常請學生吃飯,同事聚餐也都是由他買單。他還專門放了一筆錢在教研室,留作同事們定期聚會時使用。我要出版一本新書,請他寫序,他說“遵命”。書稿交給他沒兩天,他就遞來兩頁手寫的文章,字跡工整得令我驚訝。
在剛來北語的那段日子里,梁曉聲好像天天都在忙著為學生和同事們做事情。從他身上,我認識到了自己所缺少的慷慨品質。可以說,他是北語第一個讓我覺得有學習價值的同事,與這樣的人一起工作無疑是幸福的,我不能不珍惜。不僅限于此,作為教師,他同樣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我見過他給學生們批閱的作業,每頁都有圈點和感言,最后是長長的一段心得。很明顯,他是在和學生對話,有鼓勵,有建議,于學生而言亦師亦友。這樣的耐心,這樣的姿態,我是未能做到的。
至此,我也總算明白了,梁老師來高校任教,哪里是為了趕時髦,他明明就是為了無處安放的文學情懷啊!寫作本身并不能全然釋放他的這種情懷,他還想呼喚廣大的文學愛好者,尤其是那些青年人,一起分享文學的美妙與深刻。現實主義的梁曉聲同樣保有一顆浪漫主義的心靈。
可惜,浪漫的心靈在現實的汪洋里往往不會如魚得水。沒過多久,梁曉聲便體驗到了對于學院規制的水土不服。在參加北語首屆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一位碩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答辯時,他對那名同學關于沈從文作品中性愛意識的研究表示了強烈不滿,認為純屬無稽之談。一時間,答辯的同學和她的導師都很有些慌張,不知該如何是好。說實話,這篇學位論文完成得還算不錯,梁老師所表現出的反感不過源于他同學術界之間的隔膜。可是,這種隔膜又不可能馬上得以消除,況且他的反對又是那么的認真,也不好不尊重他的意見。于是,我給出了一個折中性的動議,就讓梁老師投他的反對票,其余評委則都一律投贊成票,這樣最終并不影響學生的論文通過,豈不兩全其美?當然,這對那位答辯同學來說,多少還是顯得有點委屈。
漸漸地,梁曉聲發現現今的中文系原來是一個沒有什么文學情懷的地方。喜愛文學的學生寥寥無幾,求知欲也是弱得可憐。他遭遇到了我初來北語時的那種尷尬和失望,流露出遺憾和悔意。一天,在辦公室里,他告訴我,他已經聯系好一家文化研究所,準備離開北語。我聽了頓時有些難過,極力勸他留下來。
我說:“梁老師,正因如此,北語才更需要您這樣的人啊。您可以走,我也可以走,那北語中文系的學生該怎么辦?其實,只要有我們這樣的人在,多多少少還是能給學生們一點影響的。要是您走了,我在這里會更感孤獨,可能也得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這番話對梁老師起到了作用,總之,此后他再也沒提調離北語的事。
這次談話后,我又一次意識到我們學校的負責人對梁老師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于是便找到他們,建議他們能給梁老師配一個獨立的辦公室,并好好安撫一下他的情緒。上課時,我也一再提醒同學們要珍惜有梁老師的時光。無論如何,梁老師是一位有影響力的作家,而且又是那樣一個真誠的人,他的存在對于學生一定是有益的。從這以后,我把梁老師留在北語當成了自己的一項責任。我讓自己的研究生撰寫研究梁曉聲作品的學位論文,提議在北語設立“梁曉聲青年文學獎”……我能為他做的也只有這些。必須承認,在我所熟悉的這些作家之中,梁曉聲身上最具有能夠打動我的品質。
基于這個原因,我雖幾度因為對校方一些管理制度的不滿,動過打算離開的念頭,但是一想到梁老師,只好又把這個念頭打消。梁老師為此也安慰我說:“不用理會這些,只管讓自己強大就是。”想想有梁老師的陪伴,北語并非一無是處,我且將那些不公正的對待都當成命運最好的安排吧。
到了退休年齡,梁老師果斷決定不再給學生上課。按理說,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是可以延遲好些年再退的。但我理解他的毫不戀棧,一是對上課他的確有些厭倦了,二是不工作卻享受著工作待遇,這太不符合他為人的秉性。好在退休后的梁老師沒有讓我感覺到有什么不同,我們的聯系依舊,有什么事情找他,他仍是一口一個“遵命”。而每次我都要提醒他保重身體,他是個忘我又勤奮的人,很容易忽視自己的健康。我不止一次目睹過他身體出現的危機。
一日,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見有人貼出梁曉聲的三卷本長篇小說《人世間》的書影,足有一百五十余萬字。驚嘆之余,是由衷的敬佩,要知道,這一百五十余萬字須是他一筆一畫寫在稿紙上的,因為他至今不使用電腦。與此同時,我也猜到了,梁老師這大概是想獲茅盾文學獎了吧?現在的中國作家但凡想摘得這一桂冠,好像都要拼命往長里去寫。按照《說文解字》的釋義,“獎”即“嗾犬厲之也”,也就是主人為了指使狗變得兇猛而運用的激勵伎倆。所以,我對各種名目的獎項都不以為意。至于梁老師,他可能并不像我這么想,茅盾文學獎在他那里也許意味著一種歷史情結吧。
那么,何不成全一下梁老師呢?我立即召集我的幾名博士生,在第一時間研讀了這部巨著,隨后分別寫出萬字評論,在一家學報上同時刊出。緊接著,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又為梁老師召開了一次作品研討會,邀請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和評論家展開熱論。《人世間》果真不負眾望,順利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然而,真正令這部作品名聲大噪的倒不是茅盾文學獎,而是它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在央視播映后引起的巨大反響。就此,梁曉聲的知名度達到了空前的巔峰。
不過,梁曉聲也為他的這一巔峰付出了代價。他失去了既往寧靜的生活,各種邀約紛至沓來。見證著他的忙碌,我有時不免心生疑惑,這是我曾經的同事梁曉聲嗎?我還是更喜歡先前那個狀態的梁曉聲,就像我早已經是“老路”了,而梁老師照舊還在稱呼我為“小路”。我也一樣繼續稱呼他“梁老師”,而不必改稱為“梁老”。我們還是有充裕的時間可以相聚,可以無話不談,可以繼續有在他那次作品研討會間隙的那種拍照:他執意要我坐在椅子上,他則站在椅背后,說讓我扮東家的少爺,他扮東家的長工……一切仍然如同開始,一切都不曾改變。
即使有所改變,我希望那也是時間不讓我們知曉的。正如有過多位讀者問我,我在長篇小說《你好,教授》中寫到的那位巴東仁先生是不是就是梁曉聲,這個問題起初讓我覺得莫名其妙。我從來就不是個寫實派,怎么會把梁老師寫進自己的小說里呢?可轉念一想,巴東仁的身上真的一點都沒有梁曉聲的影子嗎?我一時又難以給出確定的回答了。我明白,當梁曉聲開始走入我的生活時,潛移默化的改變就已注定在不知不覺間發生了。我以為他不在身邊,結果他時刻都在我的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