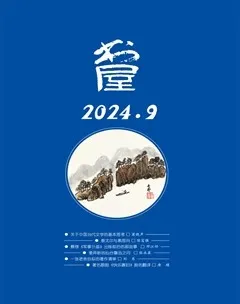傅雷《小問題》系列佚文釋讀
筆者近日翻檢民國報刊時,在《時事新報·青光》上發現了三則署名為“傅雷”的文藝短評:《小問題》《兩敗俱傷——小問題之二》《劫數——小問題之三》。根據其內容,基本可斷定這三篇短文皆出自我國著名翻譯家、文藝家傅雷之手。三文未被《傅雷著譯全書》《傅雷全集》收錄,亦不見《傅雷年譜》提及,當屬佚文。每則佚文均探討了一個文藝上的“小問題”,故可稱之為《小問題》系列。該系列文章對了解傅雷的早期文藝思想大有裨益。
一
《小問題》系列的第一篇刊載于1937年2月20日《時事新報·青光》,原標題為《小問題》。作者在文末作出了說明:所謂“小問題”,即“哀莫大于心死”的問題。全文抄錄如下:
無論何國的語言文字,外來語的引用是免不了的,有時竟是必須的;例如一切新發明的機械名稱和專門術語。但外來文法或風格的引用并非免不了的,更非必須的。Radio與Telephone是世界通用的名詞,但英文的文法與風格決非世界通用的文法與風格。
然而即是外來語的接受也是有限制的,因為語言文字有一種特殊的彈性:除了迫不得已的時候,它還是要把外來語在它的模型里重鑄一過的。就是無可改造的地名,在有些國家的文字中還要涂上一層本地風光的色彩。例如倫敦(London)在法文里變做龍特爾(Londres),巴黎(Paris)在意大利文里變做巴黎琪(Parigi)。照時行的說法,這可說是語言文字的天然防御力。
因此,中國文字雖在近六十年中容納了不少的外來語,但Radio并未照讀音稱為雷電華而稱為無線電,德律風三字在上海人口中也慢慢地變成電話。
可怪的是:現代一般青年不曾見到這些簡單的事實;他們甚至盲目地引用外來文法和外來風格。引用的時候既非因為本國文無法表白某種抽象的理論,也不是因為他所引用的外來文法或風格能夠加強他的表現力。更可怪的是:這種引用時常出現于最時髦的文字中,而這外來的文法或風格又是他們稱為“我們的敵人”的文法和風格。
這是一個“哀莫大于心死”的問題。
傅雷在文中指出當時文壇存在用詞、文法與風格“過度西化”的現象。他認為,外來詞語較外來文法、外來風格更難以被納入本國的語言文字體系。科技術語、地名、人名等外來詞語往往很難被改造,其原有形式大多得以保留。但是,傅雷也指出,本國人對外來詞語的接受是有限度的。換言之,外來詞語要經過重鑄之后,方可更好地被本國人接受,因為本國語言文字具有“特殊的彈性”和“天然防御力”。傅雷后來對某些外語人名的翻譯正是其“重鑄”觀念的體現。例如,巴爾扎克筆下的人物le père Goriot,穆木天按照通常的音譯法將其譯為“勾利尤老頭子”,但傅雷并沒有逐音全譯,而是把它放進漢語的模型里“重鑄一過”,化為地地道道的“高老頭”,絲毫不露翻譯的痕跡。
外來詞語的引用的確在所難免,但外來文法與風格的引用,在傅雷看來,則并非必須。他反對創作或翻譯中的食“西”不化的“新文藝腔”,強調使用“純粹之中文”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不過,傅雷并不一味反對外來文法與風格的引用,而是為其設置了前提條件:“本國文無法表白某種抽象的理論”,或“所引用的外來文法或風格能夠加強他的表現力”。也就是說,外來文法和風格的引用,要為提升本國語言的表現力服務。傅雷認為,在“創造中國語言”方面,翻譯家的責任要大于創作家。如何借鑒西方語言以“創造中國語言”?傅雷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致林以亮的信中對此有過具體的說明:“我并不是說原文的句法絕對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無論如何,要教人覺得盡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為中文。這一點當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譯者的taste極高,才有這種判斷力。老舍在國內是唯一采用西洋長句而仍不失為中文的唯一的作家。”由此可見,外來文法與風格要放進漢語的模型里重鑄一過,方能在保留外文長處的同時,仍不失中文的底蘊。傅雷在上文中提出后又加以闡釋的“重鑄”說是對新文學“過度西化”流弊的反思,與其后來提出的“神似”論具有一致的精神內涵。
傅雷在文末還指出了當時文壇上的一個奇特現象:意識形態上與西方敵對的“現代一般青年”,卻熱衷于引用來自西方的文法與風格。所謂“哀莫大于心死”,即指“現代一般青年”彼時的矛盾心態:他們大力批評西方社會制度的同時,卻又刻意模仿其文法與風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革命文藝的大眾化與民族化的命題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二
《小問題》系列的第二篇刊載于1937年2月27日《時事新報·青光》,原標題為《兩敗俱傷——小問題之二》。全文抄錄如下:
藝術與宣傳是截然不同的東西。藝術著重在感化,宣傳著重在辯服。前者訴之于人類的良知和本能,后者訴之于人類的利害觀念。
藝術與宣傳自有交錯的關系。成功的藝術品不求宣傳而必含有宣傳作用,成功的宣傳品必具有相當的藝術方能盡其宣傳作用。
藝術與宣傳各有其不同的運命。藝術兼重時代性與永久性,因為人類的生活形態固然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但良知和本能是不變的。宣傳只有時代性,因為利害觀念隨時、隨地、因人、因事而易。一朝環境變動,前此的宣傳會變成反宣傳。
這是說藝術并不需要宣傳,宣傳可不得不需要藝術。而兩者的領域、界限,是不容含混的。
要是只希望藝術成為宣傳,而不講求宣傳也成為藝術,那么藝術既不成其為藝術,宣傳也不成其為宣傳。
要是更進一步,認為只有宣傳才是藝術,那么藝術都會變成廣告和傳單,而且是得不到大眾信心的廣告和傳單。
這是“兩敗俱傷”的問題。
傅雷在文中著重批判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盛行于中國文壇的功利主義文藝觀。他強烈反對“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宣傳主義,指出藝術性才是藝術品的根本屬性。即使是用于宣傳目的的藝術品,也不能因其功利性的訴求而損害其藝術性。宣傳旨在以利害觀念說服他人,如果能用感人的藝術手法進行,其結果勢必會事半功倍。宣傳需要藝術,而非藝術的宣傳亦不成其為有效的宣傳,只能淪為“得不到大眾信心的廣告和傳單”。
在傅雷看來,藝術與宣傳分別屬于不同的領域,各有不同的使命,不容混淆。他甚至表示:“藝術并不需要宣傳,宣傳可不得不需要藝術。”但是,如果據此認為傅雷是反對藝術品承擔任何社會功利作用的藝術至上主義者,無疑是失之偏頗的。傅雷并不否認藝術與一時的社會環境存在緊密的聯系。這一點在他同時期的文章《我再說一遍:往何處去?……往深處去!》中也得到印證:“表現時代,是的。不獨要表現時代,而且還得預言時代。但這表現絕非是照相,這預言絕非是政綱式的口號;我們不能忘記藝術家應該表現的,是經過他心靈提煉出來的藝術品……”由此可見,傅雷既不是超然的藝術至上主義者,也不是狹隘的功利主義者。他致力于調和藝術與宣傳,強調藝術家要用藝術的手法來表現和預言時代。藝術與宣傳一旦無法調和,必定會“兩敗俱傷”。
三
《小問題》系列的第三篇刊載于1937年3月6日《時事新報·青光》,原標題為《劫數——小問題之三》。全文抄錄如下:
藝術的敵人很多,最可怕的莫過于虛偽,因為虛偽是欺詐的第一步。
一個人想滿足空洞的幻象而缺乏實在的能力時,總不免出之于下列兩種手段:一是沒有感覺而強為感覺,制造出言之無物的作品;一是以他人的感覺為感覺,一味的好新驚奇,迎合時尚。言之無物也罷,好新驚奇也罷,總之是缺乏真誠,是撒謊,是虛偽。
更糟的是:當虛榮心慫恿你作偽之后,還有利欲心唆使你欺詐。那時,不但以他人的感覺為感覺,且更以他人的作品為作品,直截了當的抄襲剽竊。而足供剽竊之古、今、中、外的作品正多得取之無盡,用之不竭。
在一個混亂的時代,大家認為這種事情是應有的現象。怕事的心理變成寬容的態度,寬容又立刻發生鼓勵的作用。
這樣,藝術才真正遭了“劫數”。
傅雷在文中批判了藝術創作中的虛偽、欺詐和剽竊行為,進而提出了“藝術需要真誠的感情”這一命題。在他看來,真誠的藝術家要做到以下兩點:一,須有感而發,不可言之無物;二,須抒發自己的感情,不可“好新驚奇”。傅雷在1956年2月29日致傅聰的信中表示:“真誠是第一把藝術的鑰匙。”他認為藝術家應具備真誠的品格,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赤子之心”的文藝批評觀。如傅聰所言,“赤子之心”是貫穿《傅雷家書》的最本質的思想。何謂“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原本指嬰兒自然淳樸、真誠無偽的本心。它亦是中國美學的核心術語,是文藝批評上“真”的價值尺度的體現。文藝上的“真”主要包括“客觀真實”與“主觀真情”兩個維度。傅雷所謂的“赤子之心”偏向于后者。他向傅聰解釋道:“所謂赤子之心,不但指純潔無邪,指清新,而且還指愛!法文里有句話叫做‘偉大的心’,意思就是‘愛’。這‘偉大的心’幾個字,真有意義。而且這個愛絕不是庸俗的、婆婆媽媽的感情,而是熱烈的、真誠的、潔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愛。”可見,真誠的感情即傅雷“赤子之心”的內核所在。藝術一旦缺乏真實的感情,便會遭受“劫數”。傅雷這篇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藝術遭受“劫數”之際撰寫的短評,可謂是其“赤子之心”文藝批評觀的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