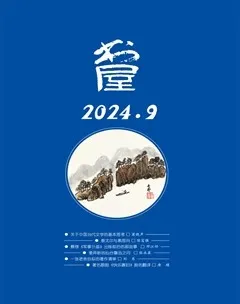不要緊題說不要緊語
姚鼐,被譽為清代“桐城派”的魁首,一生敬崇散文大家歸有光。近日讀到他寫給石士編修的私信(上海圖書館藏),信札的書法展示了姚鼐清雅雋永、雖取法晉唐卻不乏碑意的風格。內容主要談文字和文家,由對歸有光(震川)的評價引出:
久未得消息,甚念甚念,秋涼來,想佳勝耶?所寄來文字,無甚劣亦非甚妙,蓋作文亦須題好。今石士所作之題內,本無甚可說,文安得而不平也?歸震川能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深,聽其自至可也。鼐秋間因酬對應試者之勞,遂病數日,今已愈。然嘆老翁不復堪事也。今年河道艱阻,京師百物必愈貴,居者愈難。石士不至甚憊耶?若便南歸,亦未易謀一安居之策。人生如浮舟江海,聽其所至,非智力所能與矣。已涼,惟珍重,余不具。石士編修。姚鼐頓首。八月晦日。
石士,即陳用光。江西新城(今黎川)人,嘉慶六年(1801)進士及第,為散館編修二十年,官至禮部左侍郎。陳用光從小跟從舅父魯九皋學習,因魯氏與姚鼐頗有交誼,所以十分仰慕桐城古文,“及癸丑從姬傳先生游”。進京為官后,仍時常與姚鼐書信往來,請教詩文藝法,這也正是他后來成為桐城古文傳播核心人物的重要原因。
從信札可以看出,陳用光給姚鼐寄去文章,請老師指點。姚鼐對他的要求很高,并無贊賞之語,而把話題轉向震川先生歸有光,認為歸有光作文,能夠“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這是因為歸有光酷愛《史記》,閱讀時下過苦功夫,常用五色筆在上面圈點,深得太史公司馬遷的神韻。這樣的境界,石士是不能輕易抵達的。姚鼐認為,“作文亦須題好”。用今天的話說是題材一定要好,盡管這個好,卻未必像人們以為的那么要緊。寫作時在哪里著力,在哪里不可著力,全憑借文家功力。功深,聽其自然就可以了。他說得很輕松,卻令人穎悟,所謂“功”者,又何止是學識與技巧呢?
其實,陳用光的文字頗有功力。讀其散文,不難看出他對時事的關心、對民眾的同情,體現一位經世儒者“除賊如除草,撫民如撫兒”的關懷。當時,由于濉陽河決堤,致使很多地方出現饑荒,民不聊生。陳用光途經宿遷時,目睹饑民遍野的場景,揮淚寫下了詩句:“昨日見一婦,僵死委路旁,其夫不能斂,逢人訴饑腸。今日見一孩,聲嘶委路側。詎非索乳兒,不得登衽席。所見已如此,所聞更可傷。……對之不能吟,拈韻輒心惻。”悲憫之心,溢于言表。這跟歸有光從政的“惠愛”思想一脈相承。面對天災人禍,陳用光精心擬定的“救荒三策”被上司采納,產生了很大作用。后來又寫成《論令廢員修興水利折子》,議論興修水利的重要性及帶來的“三利”,也是具體可行的策略。這令人想起歸有光的《水利論》《論三區賦役水利書》。陳用光的“非徒以文章為報國之具也”,與林則徐對歸有光的評價“儒術豈虛談,水利書成,功在三江宜血食”,又何其相似!
在這封私信中,姚鼐是以歸有光為標準給文家提出要求的。
姚鼐編輯《古文辭類纂》時,從元、明兩代眾多的散文家中,僅選取歸有光一人,作為上承唐宋、下啟清代的散文大家。這也是人們把歸有光視為“明文第一”的緣由。
“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散文的精魂全在于此。震川先生的境界確非一般人能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