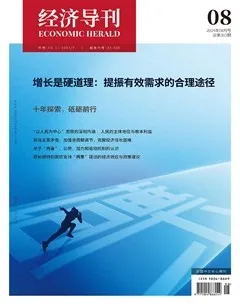關于“兩重”、公債、加力和驅動機制的認識
發行特別國債和“兩重”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現在國家推動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兩重”建設與國債資金的籌集有密切關系,超長期特別國債是在已有的國債發行機制上進一步加碼。這幾年發行量很大的地方專項債,也是中央層級特別國債的地方化,專項債還本付息最長期限是按30年進行安排。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1998年,朱镕基總理推動推出2700億元特別國債,償還期為30年。地方專項債是在地方政府沒有其他手段的情況下,幫助地方解決一些特別急迫、同時又與長期目標相結合的問題。另一個作用,就是當地方無法從別的渠道找到資金時,地方專項債可以先幫他們解決燃眉之急,也就是應急性的“以債化債”。所以地方專項債基本上是先起一個緩沖作用,此后再對接到適應長期目標的一些項目上。

總體看,目前超長期特別國債的發行情況比較順利。但在“發得出”的同時還要強調“用得上”。前些時候我曾經表達了自己的基本觀點,我認為中國現在“有效投資”項目俯拾皆是,中央和地方通過債務籌集的資金可對應的項目,可以列出幾十項。比如北京已有的軌道交通網要補充,形成密度足夠、四通八達的軌道交通網,中心區域的聯通狀態要“立體化”,而且要通盤規劃,建設全網絡狀的停車場和停車位,以及老舊小區改造等等,都是必須建設的;再加上結合鄉村建設,結合防澇抗洪的迫切需要在各地建設類似海綿城市、綜合管廊,以及必要的對接基本農田的灌溉系統等等。國土開發還有許多非做不可的事情,種種具體項目,從中央到地方都應做好中長期的資金安排。項目啟動的短期效果就是擴大內需。一般經驗,項目開工,30%-40%的資金支出是工資等人頭費,馬上就形成當期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促進消費,跟著就是優化經濟結構,增加發展后勁;這些項目主要是為了實現“正外部效應”和綜合績效,有助于積累經濟社會整體發展的后勁。從有效投資入手,帶來對全局的貢獻。當然,由政府為主體推動的項目投資機制,必須有高的規劃水平,并且需要陽光化的管理,以及項目進程中的有效管理監督(工程監理,全程監督),這就不展開說了。
現在社會上普遍對經濟增長的信心不足,增加有效投資是提振社會信心、改善預期政策組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預期往往是自我復制或強化的,如果普遍預期不好,最后就會形成不好的局面。當然提振社會預期不是簡單只靠增加投資就能夠解決全部問題,宣傳工作也要跟上。宣傳工作不能只靠宣傳部門,如果清網行動能切實打擊違反“兩個毫不動搖”和違反“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方針的錯誤言論,是可以提振信心的。
發行公債與經濟發展效應的關系:理論說明
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是從經濟學公案的“李嘉圖等價定理”(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籌款或通過收稅籌款的效果等價)切入。我認為這個“等價定理”會產生很多誤解,我們不應該再受這個所謂定理的牽制,而是應當正面肯定公債的功能及其不可缺少的作用。理論的論證,就是比照拉弗曲線:設定一個直角坐標系,橫軸表示發債規模從零點向右逐步增大(不是拉弗曲線的稅率從零向右逐步增大),縱軸表示從多角度論證的正面效應。和拉弗曲線類似,公債為零時沒有正面效應,發行公債后,正面效應開始是向上抬頭,當債務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其正面效應的曲線調頭向下——這和稅收的效應曲線類似。而政府債務規模如果發行過度就可能變成負效應——一直可以掉到負的區間,也就是產生危機。所以理論的論證可以說明,發行公債的關鍵是如何掌握合理的規模和優化相關的機制。

擴張性政策需要持續用力,更加給力
在前述理性認識的基礎上,我認為現在需要當機立斷。去年我國經過努力,爭取到了5.2%的年度增長成績,保持在合理區間的底線上。按照黨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2035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到那時中國經濟總量按人均GDP計算,要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這樣15年的年均增長速度應不少于4.7-4.9%。現階段要力爭在5%或稍高些,因為一般來說,15年的前半段速度重心應相對高,基數大了之后速度重心還要往下落。這個戰略訴求不是一廂情愿,從很多研究者所做的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研究結果可以佐證。今年開局還不錯,二季度有所回落。怎么夯牢經濟向好的基礎?不能再猶豫。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要“持續用力,更加給力”,“適時推出一批增量政策舉措”,這一精神的貫徹是非常必要的。
從“系統集成”思維把握消費驅動和投資驅動的關系
關于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的認識。我們在新供給經濟學研究中有這樣一個認識框架:整個經濟活動是需求和供給兩方互動的循環——人類生活的需求是經濟發展的原生動力,包括生存的需求、發展的需求等等,但需求這個原生動力的滿足,一定是供給側的有效供給對需求的回應。這個響應和回應機制,在近現代社會就是靠千千萬萬市場主體的創新和生產活動,所形成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有效供給,當今信息時代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出,有效供給在不斷引領和創造消費方的需求,引領和滿足用戶體驗的提高。喬布斯的蘋果手機出現之前,人們怎么也想不到能有這樣滿足用戶體驗的東西。所以要肯定薩伊的“供給可以創造和引領需求”這一定律的合理內核。“供給”對于當下現實生活的意義,也就是創新作為發展的第一動力,真正看得見摸得著的創新一定是發生在供給側。
對于投資和消費的關系的認識:要承認供需互動的循環,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基礎),但是社會消費如果能夠持續地得到滿足,它一定要具有有效投資作為源頭活水(關鍵),即供給側投資的發力。投資供給的有效性,帶出的是穩定就業的老百姓的購買力的形成。如果源頭活水源源不斷,再加上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解除了人們的后顧之憂,巨大規模的市場潛力就可以得到釋放,也就是消費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三駕馬車”,無非是把這樣的結果往前追溯為:對于一個可通約的需求方的總量作結構化的處理,分解成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這個結構性的特征一定要延伸到供給側,才能把整個循環說清楚。而供給側的結構問題就更加復雜——包括生產力布局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經濟結構以及制度結構等等。這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是真命題。

所以,經濟發展是“消費驅動型”還是“投資驅動型”,不能簡單分為兩個方面。消費作為可認同的需求側原生動力應不斷地得到供給側創新動力的回應,形成不間斷的供需循環,實際是供需兩者再加上凈出口共同驅動,在某種意義上,更多強調動員一些消費潛力,可稱之為消費驅動;而在特定階段(比如中國改革開放后國土開發進入高潮時期)會更多強調投資驅動,這些都有一定的階段性的道理,不能絕對化。改革開放初期曾經歷過投資饑渴,目前我國發展階段中則更多表現為投資不足。我們分析統計數據要分析誰更有支撐力,不能僅滿足于從統計結果看起來的貢獻比重上升(比如2023年消費貢獻率是82%,實際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
真正的發展動力是由創新驅動的,特別是供給側投資—產出的創新,這是真正可以帶動全局、能夠滿足消費作為出發點和歸宿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需要強調“系統集成”思維,把供需互動、消費和投資共同帶來的釋放活力的局面,按照改革的配套和總體的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科技創新和思想觀念創新,看成是一個必須掌握好的系統工程。
(編輯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