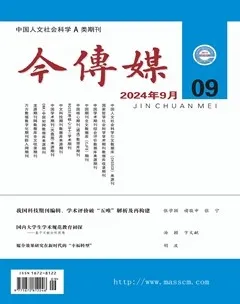改革開放以來鄉村電影鄉村形象變遷研究
摘 要: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鄉村題材影片在我國銀幕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鄉村題材電影呈現了社會變革時期人們的思想轉變,記錄了轉型期自然與社會風貌的變化,也豐富了鄉村居民的形象。本文采用敘事學中結構主義敘事學、空間敘事學理論對鄉村電影文本進行分析,旨在挖掘鄉村電影的敘事魅力,講好中國故事。
關鍵詞:鄉村電影;鄉村形象;變遷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4)09-0086-04
基金項目:2022年度山西省藝術科學規劃課題:“鄉村振興背景下山西文旅康養小鎮建設研究”(22BA145)。
一、引 言
20世紀80年代,隨著第五代導演的“登場”,我國鄉村題材電影迎來了一波創作高潮,誕生了《黃土地》《紅高梁》等一批享譽國際的影片,這些影片都傳遞出濃厚的鄉村情感,也體現了導演濃郁的個人色彩。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電影的表述對象也轉為呈現大都市的旖旎風光,鄉村電影出現了短暫的“落寞期”。直到我國開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電影界再次將目光投向鄉村,關注鄉村的變遷和鄉村居民的生活變化。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鄉村電影的發展與鄉村的變化緊密相連,鄉村電影中建構出多元化的鄉村形象。
二、鄉村電影的概念
鄉村是中國的根,是華夏文明的基石,同樣,鄉村也是中國電影創作的重要對象。鄉村電影有著廣義和狹義的分別,廣義上講,是以鄉村居民為目標受眾講述鄉村發生的故事,題材選擇更為寬泛;狹義上的鄉村電影,特指表現鄉村居民生活、鄉村生產工作,展現鄉村生活空間的“鄉村題材影片”。而以鄉村為敘述對象的影片,被認為是“鄉村題材影片”的一個類型。
三、鄉村形象變遷的動因
(一)政策的支持與引導
從鄉村題材電影的創作歷程來看,它的產生和發展與我國的時代背景、政策導向密切相關,從誕生之日起,就被賦予了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烙印,肩負著傳播黨和政府惠民政策的使命。學者韓婷婷在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鄉村題材電影的美學特征時,提出鄉村題材電影的標志性特點便是“道統特征”,并以此為依據,建立起一套獨特的敘述和角色設定模式及寫實風格[1]。
1979年,《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討論我國電影的文章,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農村影片這么少?”隨后,各大電影制片廠紛紛籌劃拍攝鄉村題材電影,其中最為成功的是1981年上映的《喜盈門》。該片關注到1978年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后鄉村的新變化,編劇從鄉村居民的點滴生活、人際交往、家庭關系之間的變化進行了細致地描繪。
近年來,電影行業的創作者也在積極探索新鄉村電影的出路,如2020年上映的《我和我的家鄉》《一點就到家》等,展現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后鄉村的新氣象。
從發展歷程來看,鄉村題材影片具有獨特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特征,所以,探討此類電影的發展歷程時要考慮到國家政策的影響。
(二)導演的代際變遷
導演是電影創作中最重要的一環。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有年輕導演投身電影事業,成為優秀的電影人。每一代導演由于時代不同和個人經歷差異,創作風格也有所不同,為大眾帶來了風格迥異的電影作品。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鄉村電影受到尋根文學影響,多關注現實問題,并且著眼于鄉村的現代化發展,試圖在鄉村中尋找一種價值和情感寄托。如陳凱歌執導的《黃土地》,就通過環境表達情感,廣袤的黃土地占據大部分鏡頭,而角色展現相對較少,體現出一種壓抑的情緒。但是,畫面展現的黃河和黃土地特別柔和,鄉村居民的腰鼓表演也充滿了力量,表達了對黃土高原的贊美,以及對黃土地承載的傳統文化的贊美。
進入21世紀,鄉村電影的創作主體以第六代導演為主,他們的作品更多表現現代文明給傳統文明帶來的沖擊。影片《暖》的編劇對原著人物暖的形象進行了改編,在視聽表達上流露出一股田園牧歌的氣息,呈現了美麗的鄉村風光,透露出濃厚的懷舊情愫。
近年來,新生代導演成為鄉村題材電影的創作主體,如黃超導演的《馬咀是個村》,致力于展現鄉村振興背景下的新農村建設。在新生代導演和第六代導演書寫鄉村的同時,一些第四代、第五代導演也依然參與鄉村題材電影的創作,如吳天明導演的《百鳥朝鳳》,就是從現代化角度展示了鄉村經濟的發展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傳承;馮小剛導演的《我不是潘金蓮》,則從現代化角度審視了鄉村的思想文化。
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之后,鄉村電影的藝術表現手法更加多元,題材也趨向多樣化,全面地反映鄉村生活,因此,電影創作中的鄉村形象變得豐富且富有魅力。
四、鄉村空間的變化研究
“空間問題是無法回避的,人們要談論敘事就不可忽視它。大部分敘事具有一個接納產生行動的空間環境。”[2]學者海闊在《電影敘事的空間轉向》一書中提出,敘事空間的研究在文化維度上存在一定的范式,需要從四個維度進行思考,分別是地理空間、歷史空間、精神空間和虛擬空間,除去虛擬空間外,其他三個空間在近十年來的鄉村電影中都有較多呈現。從地理空間而言,鄉村電影中帶有鮮明的地域屬性,如《hello!樹先生》講述山西鄉村的故事、《平原上的夏洛克》講述了發生在河北平原上的故事。從歷史空間來看,近十年來的鄉村電影并不完全是對當下生活的再現,也有對20世紀鄉村形象的記錄。從精神空間來講,電影呈現出多元化的精神世界,包括對現代化進程中倫理道德的反思與批判、個人身份的認同與回歸以及異地他鄉眷戀歸屬的思考等。
(一)“守”與“破”的對立
影片《追兇者也》《暴裂無聲》《hello!樹先生》都以企業家投資鄉村基礎建設為故事背景。其中,《追兇者也》講的是城市來的投資者要購買土地進行開發,因汽修工宋老二不同意致使開發被擱淺,由此引發一樁兇殺命案的故事;影片《暴裂無聲》也是基于類似的背景,講述了外來老板昌萬年要開采村里的煤礦資源,村民張保民因拒絕而遭受他人排擠的故事;《hello!樹先生》則講述了因開礦場導致鄉村耕地被污染的故事。在這三部影片中,主人公各自為營但命運相通,都是原始狀態的“守衛者”。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鄉村不再是農耕時期的模樣,而是吊車、挖掘機四處往來的“大型施工現場”,部分敏銳的創作者捕捉到“破”與“守”這一鮮明的對立關系,并將之融入影片創作。“廢墟影像在這些影片中如‘碎片’般嵌入,成為主人公存在和情感世界的象征,也成為傳統、歷史、地方、少數群體當前境遇的隱喻。”[3]“舊”與“新”、傳統與現代在“鄉村”這個語義場中展開較量,因此,鄉村電影中呈現出創作者既迷戀過往又期許未來的復雜情感。
(二)相對閉塞傳統的空間
自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上映以來,鄉村開始以“被看者”的形象出現,而構成這種形象的原因在于城市話語體系的“凝視”。電影誕生于城市,因此,“具備一種‘城市性’屬性,即從其城市母體因襲了城市稟賦、城市韻味、城市影響、城市文化痕跡等多樣化特征……它鮮明地展現了城市文化的現代性和公共性”[4]。在這一語境下,鄉村成為了意向化的符號。如2014年上映的影片《一個勺子》,講述了主人公拉條子在鎮上遇到一個傻子,并把他帶回家幫他尋找家人,結果遭遇到各種麻煩的故事。拉條子生活在大山里,高山隔斷了他與外界的關聯,影片由此建構了一個相對閉塞傳統的空間,并對這片“凈土”給予無窮無盡的主觀想象。有所缺憾的是,影片中呈現的鄉村形象與實際生活中的鄉村有所出入,未能刻畫真實的鄉村形象。
五、鄉村人物的建構分析
(一)鄉村人物形象的類型
近十年來,我國鄉村電影將鄉村人物形象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悲情的“苦難者”,一種是堅定的“奮斗者”。
1.悲情的“苦難者”
電影《暴裂無聲》通過展現啞巴張保民尋子而引出一系列關聯事件。張保民屬于弱勢群體,他的“苦難”體現在以下方面:(1)尋而未果的兒子。影片以張保民尋子為故事主線,但他穿梭于殺害兒子的兇手之間,卻未得到半點關于兒子的線索和結果。(2)守而不得的土地。影片前15分鐘為觀眾交代了張保民背井離鄉的原因———拒絕放棄土地而被村民群起攻之。(3)怒而無聲的話語。將張保民的人物缺陷設置為啞巴是一種失語的表達,他的妻子因病臥床休養也是一種隔絕于社會的失語狀態。
在大多鄉村電影中,“苦難”的遭遇往往與怪誕、離奇的經歷相關聯,能夠引起觀眾思考,折射出一定的社會問題。
2.追求發展的“奮斗者”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鄉村題材電影中,《咱們的牛百歲》通過講述鄉村干部帶領村民致富的故事,表達了伴隨鄉村居民思想觀念的轉變,鄉村經濟也得到了振興;《咱們的退伍兵》講述的是一個退伍兵帶領著村民發展鄉村經濟的故事。這些電影通過展現村干部、退伍軍人與村民的共同努力以及鄉村面貌發生的變化,塑造出鄉村居民謀求經濟發展的“奮斗者”形象,反映了他們努力奮斗、追求富裕的人生理想。此外,影片《人生》以青年高加林對都市的憧憬為開端,以融入都市為結尾,表達了鄉村青年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喜蓮》《媳婦你當家》等都以鄉村女性為敘事中心,歌頌了鄉村婦女為擺脫貧困、尋找致富道路的奮斗精神。
而在新世紀的鄉村題材影片中,《天狗》《十八洞村》等以鄉村建設為題材,展現了奮斗在鄉村振興一線的青年人的智慧。《一點就到家》把創業視角移到了鄉村,為新鄉村建設塑造了三位“奮斗者”形象,分別是滿腔熱血回鄉創業的彭秀兵、外來創業者魏晉北、歸鄉學子李紹群。通過三個身份、背景、學歷迥異的年輕人的振興家鄉創業之旅,讓觀眾關注到鄉村振興的路徑與方法。
鄉村題材電影常以鄉村干部帶領村民脫貧為主題,通過發展經濟這一角度來塑造謀求發展的奮斗者形象。而以個人敘事為主的電影,則多講述鄉村居民思想改變融入都市的故事。總之,鄉村居民“奮斗者”的形象是鄉村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塑造出來的,具有比較鮮明的價值導向。
(二)鄉村人物構建中性別差異的轉變
20世紀90年代之后,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績,人民的思想觀念也日益開放。這一階段的鄉村婦女思想也有所進步,如《盲山》,描繪了一個勇于和命運抗爭的新時代女性形象。與以往電影展現的女性形象不同,白雪梅具有一種積極的反抗精神。她被拐賣到山里后,雖然和其他被拐賣的婦女一樣被迫生下了孩子,但她沒有放棄出逃的希望,甚至還鼓勵村子里和她有同樣遭遇的女性出逃,在經歷了無數次失敗后最終被解救出深山。
隨著國家政策的引導、社會環境的變化,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如《香香鬧油坊》中的主人公香香,是一名有知識、膽識、魄力且富有創新精神的女性,在她的身上體現出“新時代女性嘗試樹立獨立自主的人格、獲得獨立社會地位的愿望。”[5]
六、當下鄉村電影中鄉村形象構建的不足
(一)鄉村形象不貼近現實
我國第六代導演以及新生代導演大多生活在城市中,而電影的創作需要實踐經驗的支撐,特別是鄉村題材影片,因此,缺乏生活閱歷間接導致他們展現的鄉村與實際的鄉村存在一定差異。
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我國的鄉村振興戰略已初見成效,鄉村經濟水平整體上升,居民生活也有了明顯改善。鄉村電影的呈現與表達也一改以往悲涼、壓抑、沉悶的基調,以一種輕松、愉悅的敘述方式將鄉村面貌展現給觀眾,使人們對鄉村生活充滿向往。但是,影片所選擇的是少數的鄉村,沒有普遍代表性。
(二)思考價值逐漸缺失
近年來,鄉村的現代化發展迅速,其變化之大、范圍之廣,前所未有。鄉村題材電影也慢慢偏向于“快消品”,大都是滿足即時的快感而忽略了深層意義。如《秋菊打官司》,以生動飽滿的人物形象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引起了網友的廣泛討論。影片通過秋菊展現了農民質樸的“一根筋式”的執著,缺乏法律常識的她在追求社會公正的時候陷入了法與情的困境[6]。同時,電影逐漸將創作重點放到人物塑造和故事講述,特別是一些懸疑類型影片,喜歡將敘述空間安置在鄉村,風格怪誕且都為非線性敘事,講述過程娓娓道來,由觀眾層層解密、抽絲剝繭,感受推理帶來的心理爽感與成就感。但是,這樣的敘述方式使觀眾忽略了現象背后的現實因素,難以引發他們對鄉村問題的深層思考。
七、結 語
導演在創作鄉村電影時,既要注重延續鄉村題材原有的詩情畫意,也要走進鄉村,融入到鄉村生活之中,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去創作電影。同時,對于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的新鄉村形象,要從多個角度進行書寫,展現真實的鄉村,呈現出更加深刻的內涵。此外,對于鄉村居民的刻畫與描述,要打破觀眾的既定印象,塑造出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優秀的鄉村電影不僅要具有觀賞性與傳播性,也要對不同時期的鄉村形態進行記錄。關注鄉村、呈現鄉村、表達鄉村是影視作品在創作時應有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相信我國鄉村題材電影會迎來新的發展“高峰”。
參考文獻:
[1] 韓婷婷.新中國70年鄉村題材電影的發展變化[J].藝苑,2019(4):12-16.
[2] 安德烈·戈德羅,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電影敘事學[M].劉云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04.
[3][4]楊致遠.碎片“一瞥”的現代性批判———論中國當代電影中的廢墟影像[J].中外文化與文論,2016(3):266-280.
[5][6]俞燕.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村題材電影中的女性形象[J].江蘇開放大學學報,2014(2):67-69.
[責任編輯:宋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