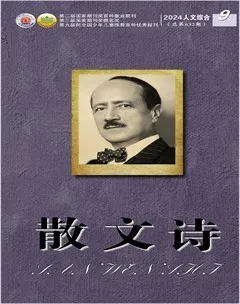休學記
那句話,我遲遲不敢說出口。我知道,一經說出,它就成了一把刀,將時間斬成兩截;或者等于打開一道閘門,我情緒的山洪便會放任奔流,過往種種亦將潰不成軍。如果繼續憋在肚子里,情形肯定會越來越糟。所以,我還是選了上午課間操的時間,一步一步,挪到了班主任的辦公室。
班主任正埋首于一堆作業中間,對于我的造訪,頗感意外。一個向來遵紀守規、成績優秀的學生是讓老師放心的,但一旦鬧出動靜,可能就不是小事了。五十上下的班主任,臉如刀砍斧削一般,他轉身面向我,將一個大大的問號擰于眉心,做好了傾聽的準備。
我說:“我不想讀書了,我要休學,并且馬上就卷起鋪蓋回家。”我的語氣既無半點水潤,也無一絲光澤,聽著仿佛來自別人之口。班主任顯然不會認為我在開玩笑,他實實在在被驚到了。他用刺痛人的眼光盯住我,長久無語。這種無語的狀態僵硬地延續著,我在這硌人的氣氛里氣急敗壞地逃離了。
那是遙遠的1988年,高二。初夏已經來臨,氣溫可感地往上竄,空氣里混雜著腐朽和生長的氣息。不明身份的雜草從校園的各個縫隙和孔洞里冒出來,瘋瘋癲癲的樣子,拔了,又長。
說這話前,我有預計它的影響。但我沒有料到,在通訊尚不發達的上個世紀80年代,這消息會像風一樣傳得那么快。我的父母不知經由什么方式也及時獲取了這個信息。我一個人的兵荒馬亂,帶出了一群人的兵荒馬亂。太陽完全落下去了,西邊飛了幾片彩霞,像淘氣孩子的胡亂涂鴉。暮色在校園里不動聲色地涌動。我來來回回走在操場四周的樹陰下,忐忑,紊亂,心里好像塌進去一大塊,一個硬生生的另一個自己已經從身體里長出來,我要如何和這個陌生的自己相處!教學樓的燈“刷”地亮開一片,人群陸陸續續朝著燈火的方向而去,只剩下最后一個我。時間似乎改變了流動的方向,我被整個世界甩在后面。頭頂的小飛蟲舞蹈得正歡,楊樹的葉片在暮光中浮起團團墨黑,它的陰影將我和周圍完全隔開。我上課時曾無數次把目光投向這片廣袤而深邃的綠,它們陪我度過了那么多苦讀的日子,它們明媚鮮妍,即之可親,望之則安,我也曾在作文里盛贊過它們的蓬勃生機、奮勇向上。現在,它的葉子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塵灰,往日的油綠鮮活不再。
操場西面緊靠學校大門,父親正是在這個日寸候裹著一身暮色進來的。他蓬亂著頭發,赤著腳,一只褲腳皺巴地垮下來,另一只褲腳卷至膝蓋上面,來不及洗凈的田泥,在腿毛上結成了泥巴疙瘩。父親右手提了一個尼龍網袋,兜著一個白瓷碗,白瓷碗上面還蓋了一個小白瓷碗。他走路時有輕微晃動,不仔細看很難察覺,他一年前替人上房揭瓦而不慎失足,落下的腿疾。
我小跑上前,沮喪地喊了他一聲。父親的臉色和天空一樣蒼灰,驚慌在臉上竄動。他滿是不解地盯住我的眼睛,急切地問:“好端端的,為什么就不讀書了?”父親平時和我鮮少親近,他話不多,不太過問我的學習,也可能是放心的原因,平日很少來學校。他是一個情緒節制的人,只有碰到大悲大喜的事情才能讓人感覺到他的在場。一個擅長沉默的人突然熱切地參與到我的生活中來,加重了整個事件的嚴重性,也加重了我對自身的愧疚感。
沒等到我回答,父親已移開眼睛,長嘆一聲:“千萬不能有那種想法啊!不讀書又能干什么呢?”
不讀書,我能做什么呢?這問題我還真沒想過。不知道是先天的原因,還是長年刻苦讀書費心費力所致,作為一個農村的孩子,父親的結實和力氣我都沒有遺傳到,我這小身板,放到田里,會被莊稼瞬間遮沒。不讀書,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把臉往一邊側了側,想借助闊大的樹陰遮擋自己的表情。我不知道要怎樣向父親解釋,這不是一句話就能解釋清楚的問題啊!我低下頭,將差點說出口的話封印在嘴里。我知道一旦開口,一定會帶出一段河流那么長的訴說,一定會迸發出如同瀑布飛濺的情緒。
晚風像任性的小孩,恣意歡快地跑過來,風里攜帶了大地上的所有秘密:將頭沉甸甸低下的油菜,綿延鋪陳的秧苗,新翻的水田,怒放的紫云英……在并不遙遠的老家,蛙鳴響徹日夜,燕子忙著銜泥搭窩,放了學的孩子們把書包往田壟上一丟,翻溝鉆渠捉泥鰍,或者在紫云英的地毯上打滾、撒野。季節送來一個又一個農忙的高潮,布谷鳥開始了它亙古不變的“阿公阿婆,割麥插禾”的啼喚。我看見老家泊在青灰的暮色里,鳥歸巢,雞人籠,炊煙起,娘剛剛從田里收工進屋,來不及攏一下被風吹亂的頭發,就又忙著做起了晚飯。灶臺前,她臉色沉重,心神恍惚。我已經狠狠掣動了這個世界的某根繩子。許多人和事在我眼前身后悄悄發生著位移。我和父親用沉默彼此對峙。兩條洶涌的暗流,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試探,沖撞。我知道父親從不懷疑我是一個學習自覺的孩子,從小就有著同齡人沒法比的堅韌刻苦。這樣一個讀書從來不必操心的孩子突然提出休學,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或擔負不起的壓力。父親的疑惑在這里,父親的哀傷也在這里。
他抖索著,揭開那只白瓷碗,連同一雙筷子,一并遞給我。我從厚厚一層鋪著的臘肉中夾起幾片勉強塞進嘴里,卻再也吞不下一口飯,我把碗筷重新推給父親,他沒有像娘那樣苦口婆心地勸我再多扒拉幾口,而是無聲地接過,蓋好,重新裝回尼龍袋。兩只碗發出生硬的碰撞聲。父親忽自言自語道:你娘聽了你的事,剛才炒菜都忘記放鹽了。面對父親半是焦慮半是疑惑的眼神,我努力放松著自己,試圖表現出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嚴重的假象。
可我實在找不到一句合適的話來安慰他,或者向他保證——我也多么希望自己能云淡風輕地對他說——自己只是一時興起,口不擇言,才會說出要“休學”的話,讓大家措手不及。其實根本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哪至于要休學呢!今天過去,明天太陽升起來時,我就會回到原來那個讓他們放一百個心的自己,成績優秀,自強不息,未來可期。我多么希望,這只是一場夢的距離,只是翻動一頁書的時間,一切很快就會過去。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此刻我給不了這個可以拯救父親情緒的承諾。我不能給父親一個謊言,謊言將帶出更多的謊言,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卷入謊言的鏈條,不可收拾的殘局將如大霧蔓延。我寧愿父親有思想準備。
學校西面圍墻外是小鎮的糧站。從早起到日落,從月升到星斜,嗡嗡機聲從未止息。機器的巨口吐出的白花花的大米,供應著這個幾萬人口的小鎮甚或更遠人群的口糧。南面圍墻靠近江堤,堤外是赤磊河,系洞庭湖的支流,一個繁盛的碼頭盤臥在此。各色人群云集于堤上堤下,生存的艱辛在此演繹出車水馬龍的喧鬧,叫賣聲一浪高過一浪。赤磊河日夜奔流,驚濤拍岸,巨大的聲響搖撼著整個小鎮。白天,我滿腦子跑火車,對圍墻外的各種喧嘩保持著高度的敏感。我已經沒法把精力集中在書本上、黑板上,那些爛熟于胸的概念、公理亂成了一鍋粥,老師的點名答問常讓我猝不及防。夜晚,在室友們交織的鼾聲里,我睜大眼睛,將視線投向窗外,與月亮遙遙相顧。糧站飄出的谷灰米灰懸浮在空中,凝結成朦朦朧朧的霧靄,籠罩在小鎮上空,將月亮也染成了橘黃色。在這張霧靄的巨網中,我疲憊,壓抑,呼吸不暢,怎么也無法入睡。在最需要擁有深海般睡眠的年紀,我卻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整晚整晚地失眠。這是一個令人多么恐懼的循環,這是一把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暗刀子。我感覺自己成了~架老舊的機器,身體的各個零件正發出潰散的聲響,我聽見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在吶喊:我要休息,我想睡覺。可我的頭腦卻始終在清醒和混沌之間來回切換,樂此不疲,睡眠始終不肯降臨。
沒有人知道我身上發生了什么,我將自己偽裝得天衣無縫。我披著上學期期末考試第一名的光環,無懈可擊地配合著學校的每一刻作息,而沒有人知道我身體正經歷的。眼見著期中考試即將來臨,我忐忑,我害怕,我擔心成績一落千丈,擔心種種不堪終將在不忍卒看的分數面前暴露無遺,無法收場。不安和忐忑像鞭子一樣每日抽打著我。我感覺自己已經走到了懸崖邊上。苦苦掙扎不得要領之后,我想到了自救。我想,唯有丟下手里的每一本書,把所有人的期待甩到一邊,方可突圍。我必須馬上尋找到一個安靜之地,用一大塊完整無缺的睡眠來修復百孔千瘡的身體。我沒有辦法再硬挺了,我必須向世界妥協。這種強烈的自救意識,讓我終于邁出了通向班主任辦公室的第一步。
多年以后,當我跌跌撞撞地遠離了這段生命暗區,卻仍落下了容易疲勞的毛病,而且特別嗜睡。我對睡眠有著強烈的依賴,每日像守衛領土般看護著自己的每一寸休息時間,不容破壞,不容侵犯,那架勢,和護食護犢的牲口毫無二致。我知道,命運要安排我用一生的時間,來彌補少年時代虧欠的那些夜晚。
晚自習鈴驟然響起。我內心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輕松,我奇怪自己身體竟然取締了對鈴聲應有的敏感。抬頭望向教學樓二樓最東邊那間燈光雪白的教室,感覺它已經離我十分遙遠。那里成了別人的戰場,我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逃兵。從向班主任宣布休學的那一刻起,我就解除了自己好學生的身份,我不再奢望別人仍然以一個好學生的標準要求我。但是,除了我自己,恐怕不會有第二個人能了解與適應這種突兀的變化。在距離高考只有一年多的關鍵時刻,一個常年考第一名、在別人看來上大學如囊中取物的尖子生,突然提出放棄,實在有點不可思議。
月亮掛上中天,父親要回去了。幾個鐘頭前,他匆匆放下農具,來不及往嘴里扒口飯,就心神不寧地踏上這條村路,顧不上煤渣、磚頭、瓦塊的硌腳。現在,夜色中,他又要踩著走過的路重新走回去。我想跟在父親身后,我們已經很久沒有一起走過夜路了,但今晚還不是時候,我還沒來得及做好正式休學的收拾整理。父親轉身的神情猶疑而沉重,臉上堆滿一萬個不放心。他孤單落寞的背影悄悄移向學校的大門,黑暗洶涌地擠向他。他僅有兩次來校,都是來參加家長會。他從這張大門進來,臉上掛著驕傲的表情。他告訴過我,有很多家長一邊恭喜他,一邊向他討教我的學習經驗。那時的父親內心是多么明亮而自豪啊。他還罕見地用玩笑的口氣嘲笑我:其實,你哪有什么好經驗啊,不就是比別人用功一些嘛。也許他這一生乏善可陳,能夠引以為驕傲的事情也實在不多。
我不知道接下來迎接我的命運是什么,但我清醒地知道,我和父親在同時走進各自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