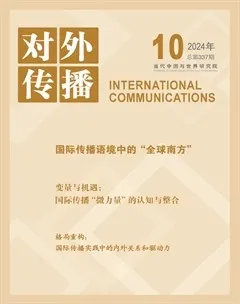“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歷史與命題:全球“知”網的想象力
【內容提要】本文嘗試論證的“全球南方傳播理論”脫胎于百年變局下國際關系具體環境的變化與國際傳播“去西方化”的歷史探索,旨在創新理論表達和話語方式,從全局性角度釋放“全球南方”之于國際傳播的潛力和價值。立足全球“知”網的知識全球史視角,梳理作為“地方知識”的全球南方傳播理論如何接續經典傳播理論的未竟事業并在學術想象力層面主動、反向設置議題。文章從主體、敘事、平臺、體系及目標五個角度歸納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核心命題,思考理論知識的解釋空間擴展與交往融匯可能。
【關鍵詞】全球南方 國際傳播 知識全球史 地方知識 平臺世界主義
從全球知識網絡(以下簡稱全球“知”網)的知識全球史視角看,“百年變局”下國際局勢與國際傳播“具體環境”(milieu)發生變化①,“全球南方”概念本身也在不斷動態調整,納入經濟、政治、社會與生態等多個維度,隨著二戰以來全球南北關系不斷演化,相繼被注入“反抗殖民侵略”“擺脫經濟落后”和“大國博弈中立”等內涵。②就信息傳播與知識生產的關系而言,建立更親密、深厚的“南南合作”,減小南北發展差異成為廣泛共識,搭建“全球南方”傳播理論(global south communication theory)的初步條件已逐漸具備。對于舊的全球知識生產系統,即西方學者占據知識生產的上游或制高點,“全球南方”的學者負責知識生產的原材料整理或初級加工,所完成的許多學術研究,往往只是西方理論的注腳,為西方理論提供一個本土化的證據或證明。③“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使命意味著發掘后發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生產潛力,書寫具有自主、復數、聯動性質的知識史。
“全球南方”的理念和實踐脫胎于冷戰時期的不結盟運動,超越了所謂“集團政治”的對抗性思維,為具有巨大地緣差異性的后發國家注入合作動力和發展信心。理解國際傳播語境中的“全球南方”,需要汲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歷史智慧,從整體性和全局性的視角釋放“全球南方”之于國際傳播的價值,創新理論表達和話語方式,在傳播路徑上謀求另一種可能性。本文的核心問題意識可概括為:如何從知識全球史的視角來理解“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知識建構及其核心命題,拓展這一理論知識的解釋空間與交往融匯?
一、行于所當行:理論籌備的歷史與契機
(一)“去西方化”的探索
部分經典傳播史論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面臨嚴重的闡釋危機:將西方社會科學及修辭學研究的代表學者奉為現代傳播學科的奠基人物、撰寫學科簡史;或借用社會學框架或突出強化媒介技術中立的色彩將傳播歷史與理論的發展嵌入資本主義線性社會發展的歷程之中,放大對傳播行為和效果的捕捉,缺乏對更廣闊世界和多線程歷史變遷的關照,陷入自說自話境地。這種闡釋的“無力感”蔓延到國際傳播研究領域,極端化約的實證主義很可能漠視跨文化差異,容易導致“以西方為全球標準”的理論生產。④
對傳播歷史與理論“去西方化”的探索在取得突破。長期以來,非西方的傳播活動被視為對美西方傳播發展的反歷史性和反常規的“模仿”。有學者采用去殖民主義視角,分析了19世紀以來土耳其傳播的商品化和軍事化議題及其影響婦女、工人階級等受壓迫群體的生產和實踐,將作為亞歐大陸橋梁的土耳其傳播網絡置于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格局和現代資本主義的演變之中,這挑戰了“昂撒中心主義”的傳播史論敘事假設。⑤此外,傳播領域內金磚國家的研究者在過去十年間的論文發表趨勢顯示出前所未有的知識生產力,有效彰顯傳播理論“去西方化”的階段性成果,但是國家之間缺乏合作,即這張“知”網不牢仍是不爭事實,“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去西方化”議程可能成為充滿“馴化”色彩的垂細化知識類別風險值得警惕。⑥
(二)“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知識醞釀
回到知識全球史的維度,全球性知識是現代世界在交流、互動中形成的一整套概念建構,對世界步入現代狀態產生深遠影響,但其中的美西方知識霸權與全球南北方之間的知識傳播不平衡關系理應受到批判。⑦以關聯、互動和比較為方法論,“全球南方”傳播理論作為全球“知”網的新興增長點,在其發酵、演繹過程中需要做到超越單一的知識考察的地方性視角,主動嵌入到從分散走向整體的人類知識交往歷程。這是對知識的地緣中心與邊緣關系、跨區域的知識流通與交換、地方性知識體系比較的一次再體認,在“多元一體”認識論下賦予“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知識產生的歷史正當性。
“行于所當行。”不論是基于國際關系的歷史性變化、傳統媒體的發展與變革歷程,還是對國際傳播基本場域平臺化變遷的把握,不少學者與國際學術期刊陣地已經圍繞“全球南方”的傳播與媒體現象,進行了前期的理論探索與知識儲備。⑧這一知識醞釀的過程為我們更好提出、勾勒“全球南方”傳播理論奠定了基礎。
二、“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地方知識”:流派與超越性
(一)“全球南方”“地方知識”的想象力
“全球南方”傳播理論是國際傳播語境內的一套基于在地化經驗與思維化提煉的“地方知識”。為了追求更廣可及性和更順暢的可溝通性,傳統的國際傳播理論與實踐力求減小不同地域和文化間的交流“熵增”(entropy production),但始終存在“去地方化”悖論,暗含對普遍主義傳播的迷思,強調跨越文化和地域界限實現更快速率交流,達成一種普遍適用的溝通方式和理解框架。⑨值得警醒的是,在實踐過程中這種迷思往往基于某些文化或地區的價值觀和實踐,將其作為普遍標準推廣卻未能充分考慮其他文化的特殊性并破壞了地方多樣性,導致對地方性知識的不公正對待或無意識的邊緣化。
如亨廷頓所言,“西方中心論”的霸權思想到20世紀末已膨脹為普遍和狹隘的“自負”,北美與歐洲的西方文明成為世界的普遍文明⑩,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全球化進程反復但世界秩序出現混亂的情況下,美西方領導者試圖按照英美自由主義模式宰制全球秩序,并將其包裝為一種“新保守主義”從而維系由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11對“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重視,原因也在于以“去西方化”的在地經驗知識生產的根本邏輯,同時連接內在異質性相當突出的“全球南方”地區,追求一種更具超現實性質的理論想象力。
對當下的“全球南方”傳播理論地方流派進行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地方知識頗具生命力。近年來在印度興盛的“瑜伽軟實力”理論綜合了地方化的瑜伽理念和源自美國的軟實力概念,不僅將瑜伽運動作為印度的民族名片和傳播符號進行宣傳,還將這一源自古印度教的精神傳統充分融入當代印度的形象建構之中,在跨文化傳播實踐中將自身的國家形象塑造成全球事務中的一股“如瑜伽般”柔軟、靈活而有益的文化力量。12印度總理莫迪多次在出訪活動中將瑜伽元素納入外交辭令13,嘗試改變瑜伽在西方過度商業化、精英化的發展趨勢,調動廣大民眾參與,將瑜伽背后的健康生活方式傳播開來。14印度還從梵文《奧義書》汲取靈感,將古印度哲學融進國際傳播,在二十國峰會上創造性提出諸如“一個地球,一個家庭,一個未來”(Vasudhaiva Kutumbakam)的文化外宣理念。
作為“全球南方”國家最為集中的大陸,不少非洲學者對“現代化”的發展傳播學傳統范式進行批判反思。例如,利用烏干達的媒體數據質疑源自西方的“社區媒體理論”無法解釋非洲地區小型媒體與社區之間的復雜關系15,在新聞領域則認為“發展新聞學”和“建設性新聞”等成為非洲國家探索發展傳播“中間道路”的重要嘗試。16拉美環境傳播學者同樣基于對“自我東方主義”的反思,批判美西方學術生產在這一領域的“特權”,將學術交往實踐和拉美發展的歷史經驗進行交叉性分析并進一步深化“生態文化認同”(ecocultural identity)的概念,旨在建立更包容、更全面、有活力的既有拉美立場又有國際視野的環境傳播學術流派。17這都可被視作特色而典型的具有地方自主性的“全球南方”傳播理論探索。
(二)超越地方性:“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議題建構力”
“全球南方”所衍生而出的各類傳播理論流派,不能僅僅作為經典傳播學“創新擴散”的驗證而存在,或是以提出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經驗總結而出現。這均沒有體現出知識全球史意義上理論的現實“型構”(figuration)價值。從地方知識的社會建構角度看,如果我們僅僅言說“全球南方”傳播理論與現行的、通用的、所謂“普世的”傳播理論有何不同或差異,追求一種理論獵奇心理,這是遠遠不夠的。同時,可能使得“全球南方”傳播理論內含的“去殖民化”理念脫離歷史唯物主義,變成諸多分散、抽象而空洞的概念。18相反,需要凸顯的恰恰是這一理論的旅行與擴展價值及其內在張力與潛在的知識革命性。地方知識應基于傳統文化實踐,通過一定手段來實現更大目標19,策略性地培養新文化,從而自下而上地改革知識秩序。
“全球南方”傳播理論在于接續此前經典傳播理論的“未竟事業”乃至反向、主動設置議題。需要在知識拼圖的意義上,拼湊描摹出一套更具新意的傳播理論,繪制編織整全性的全球“知”網,超越默頓在《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所推斷的“一般理論—中層理論—經驗描述”社會科學知識模式,調動可供使用的一切理論資源與文化經驗,不滿足于對地方化的本土經驗進行簡單總結和概括,嘗試理解、開拓所得的“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普適性,發揮出aKezuGO6ydsjlgkhIN65elhWFrCxJUtvKS7tpdfpwmA=“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議題建構能力。20
三、“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核心命題
(一)主體:國際傳播的“南方合作主義”
“全球南方”傳播理論首先需要對傳播者的主體聯合進行充分關注,落腳于搭建一個基于“合作主義”(cooperativism)的認知與行動框架。“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傳播中應建立平等互信的伙伴關系,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和共同發展的原則,確立共商、共建、共享價值觀,在“南方合作主義”框架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時,尋找共同點和合作機會。
信息占有與傳播技術等方面的獨家(exclusivity)及逐利理念下,傳播領域內的合作往往被認為是形式大于內容的展演行為。真正實現“全球南方”的傳播合作,需要超越現有排他性的認知框架。“全球南方”傳播理論及實踐不是為了消除、抹平所有傳播者之間的差異性,亦需要有引領者來推動合作和傳播實踐的發展,但這些引領者不應該成為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價值觀簡單復制到其他國家的霸權主義者。大西洋理事會2024年6日的一份智庫報告聲稱,中國引領的“全球南方”正在沖擊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塑造的全球秩序,比如在媒體合作等領域通過人才培訓等方式向世界推廣“錯誤”的中國媒體發展模式,進而呼吁西方國家在亞非拉扶持自己的力量,抵制中國擴大影響力。21顯然這延續了美西方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維,按照嚴海蓉等學者的說法,“全球南方”的傳播應是多方利益相關者的活動、互動、利益交織而成的復雜網絡,基于實際情況和需求,分享經驗、知識和技術,進而更好形成適合自身的傳播策略與發展方向。
(二)敘事:替代性與跨媒介的意義輸出
“全球南方”傳播理論要關注有別于美西方主流敘事和觀念的“替代性敘事”。究其根本,國際傳播敘事是一種意義的輸出。從批判的角度看,美國流行文化全球傳播的敘事內核包含了有意設計的服務于美國海外利益的信息,可以被接受者解碼并滲透進他們的文化中。相應地,當我們重視并鼓勵“全球南方”的“替代性敘事”時,則需要重點理清其中包含的三重邏輯。
其一,媒介技術邏輯。需要反思敘事背后媒介技術生成與運用可能存在的美西方話語霸權,理論的討論重點即“全球南方”國家與媒體能否有效地利用好新的平臺媒介乃至數智傳播方式進行自主敘事;其二是最重要的文化生態邏輯。對所屬民族與在地文化(比如鄉村與城鄉關系協調發展的故事)進行創造性轉化敘事和連通文學“原型”(archetype)及小說、動漫、游戲、影視等在內的“跨媒介敘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認識到敘事及故事世界的構筑其實是新與舊的世界觀的博弈問題,最終實現“故事世界”與“現實世界”共識性的疊印關系;22其三,政治經濟邏輯。做到媒介傳播敘事的社會轉化與引領性發展,在賦能的意義上建構敘事與社會轉型的合作與共生關系,更好契合實踐的發展。
(三)平臺:基于連接的新世界主義
“深度媒介化”的理論建構中,社會在本體意義上是“后勤”屬性的媒介所連接的,世界是一種通過交流和理解建立起來的關系構造。23無接入,不傳播。傳播在“第一性”上是一個事關“連接”(connectivity)的問題。此外,在多數發展傳播學研究的視野里,“全球南方”的數字接入程度不足也成為妨礙其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全球南方”傳播實踐與理論需要建基于當前快速變化的數智平臺與龐雜無邊的社群組織,緊密圍繞重視連接與發展議題的“平臺世界主義”(platform cosmopolitanism)來做文章。
隨著數字絲路等基礎設施化的傳播連接實踐不斷拓展,避免陷入所謂“中國威脅論”“數字冷戰”的思維定勢也是考察基于連接的平臺世界主義的重要方法論啟示。24早期有關世界主義的想象與Web2.0時期虛擬世界主義的探索實踐為當前基于“全球南方”與“新天下觀”的全球媒介文化再書寫打下了豐厚的理論與實踐基礎。作為“復數”性質的平臺化、數智化進程可能為部分北方地區和特定階層服務,加劇全球范圍內的信息鴻溝,造成“全球南方”國家的數字返貧,加之政策阻礙、資金不足、人才缺乏等難題,國際傳播語境中的“全球南方”的失語狀況需要得到研究重視與理論關照。
(四)體系:打造傳播共同體
“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另一重要命題是對傳播的“體系”和“共同體”等概念進行深刻理解。世界以非機械的系統方式而有機存在,體系則是實存事物或相關知識相互聯系而構成的整體25,傳播體系意味著將傳播主體進行有機串聯并賦予具體的信息交流活動以特殊價值和意義,進而構成廣泛存在又開放、多元的傳播共同體。對正在戰略升級的中國國際傳播而言,要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圍繞“全球南方”的國際傳播體系和“全球南方”傳播共同體建設是題中應有之義。
“全球南方”傳播體系與共同體的構建任務艱巨,需要挑戰現有并不公平的國際傳播秩序。“第三世界”作為一種方案的理念脫胎于去殖民化斗爭,當時廣大亞非拉民眾為更美好的未來而奮斗,“全球南方”的概念則出現在當下這個“新自由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霸權不受約束的貿易時期,“全球南方”之間的合作受到現有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阻礙26,要真正實現對現有國際傳播秩序的顛覆,需秉有打持久戰的心理韌性和戰略定力,兼具傳播內容、平臺、渠道與情感的體系網絡搭建,做好“傾聽”、捍衛公道與正義,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將傳播效力最大化。
(五)目標:“南方”的消弭與終結
在新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無論是里根和撒切爾為代表的美英右翼政府的領導及其聯合政策口號“TINA”(未來別無選擇),還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都遭遇了理論闡釋力的質疑,他們預言的所謂“自由—民主”制度是歷史的終極形態,然而全球化帶來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使得這一論斷受到懷疑,西方國家在部分領域的歷史“倒退”顯示出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困境,同時中國等金磚國家和“全球南方”勢力的崛起也在豐富所謂西方資本主義一元敘事的歷史走向。27但是,福山理論中關于政治秩序、國家能力及國際傳播的分析框架,為我們闡明“全球南方”傳播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可借鑒其思路來展望這一理論構想的最終目標,即“南方”的終結與消弭。
換言之,強調“全球南方”的概念不是為了默認并鞏固全球南、北方的差異性現狀,放大“全球南方”的特殊性,凸顯“全球北方”的優越性,而是為了真正打破橫亙在全球南北方之間的“物理界限”(即經濟發展的差異)與“心理距離”(即北方對南方的知識霸權)。理論本身不是目標,更好地改造社會實踐才是歸宿。在命運與共的意義上,通過“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設想,探索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全球化視角,強調全球各文化、社會與人民的平等參與和共同發展,尋求促進不同文化和社會之間的理解與合作之道,以知識為核心構建治理話語體系,鼓勵“全球南方”國家和社會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在知識轉化的層面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而貢獻更多智慧。28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相契合,各國和各民族應攜手互助,共享發展經驗,共同面對挑戰。
四、結語
阿諾特(Richard Arnott)等危機管理領域的學者指出,身處易變、不確定、復雜和模糊的“烏卡”(VUCA)時代,需有更好應對之策即“VUCA Prime”,秉持愿景(vision)、相互理解(understanding)、思路清晰(clarity)、反應機敏(agility)。任何知識的社會建構都是一個囊括辯證歷史、多層次社會與關乎未來發展的過程,對“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初步想象及其核心命題的歸納,也在于以知識全球史為理論指引,對現有的國際傳播理論進行反思、對實踐實現再引領。
編織“全球南方”傳播理論所引領構建的全球“知”網時,精準化、有針對性的區域與國別意識非常重要。29但不應該局限于宏大敘事或只鐘情于現代世界體系意義上的“國族中心主義”框架,更應融通基于網絡連接的社群團體與微觀個體。不能以西方“白左”心態陷入“全球南方”傳播現象的“犄角旮旯”處(這同樣可能是西方左翼文化研究學者常陷入的知識生產困境),停留在簡單地訴諸多元主義的“描述”之上。
總而言之,不能拋棄理論聯系實踐的斗爭性。可嘗試采用“照著講、接著講、對著講”的思想方法30,厘清一般經典傳播理論的本來面目,梳理其誕生、繁衍、拓展的歷史,在理論接續的意義上對“全球南方”傳播理論進行系統歸納,通過平等對話與交流互鑒,反思當下國際傳播領域內“全球南方”傳播理論與其他理論的互補前提、論證過程和整體結論中存在的真問題,貫通“全球南方”傳播理論的地方性與整體性。對于志在持續保有生命力的理論而言,這或是一條擺脫“空洞所指”并成為“有意義能指”的路徑。
本文系清新計算傳播學與智能媒體實驗室研究支持計劃(2023TSLCLAB001)的階段性成果。
朱泓宇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史安斌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黨委書記、教授,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注釋」
①[德]馬克斯·舍勒:《知識社會學問題》(艾彥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67頁。
②楊慧:《“全球南方”的興起、分化與中國的選擇》,《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4年第2期,第1頁。
③熊易寒:《嵌入性自主:世界知識網絡中的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9期,第22頁。
④李金銓:《在地經驗,全球視野:國際傳播研究的文化性》,《開放時代》2014年第2期,第133頁。
⑤?elik, B. Communications in Turke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A Critical History (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23, p. 2.
⑥Comel, N. et al.“ Academic Produ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BRICSBased Researchers: How Far Can the‘ De-Western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Go?”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24, vol.101, no. 1.
⑦婁煜東、王邵勵:《人類知網:知識全球史的探問與闡說》,《全球史評論》2022年第2期,第35頁。
⑧如《傳播、文化與批判》《傳播理論》《“3C”:傳播、資本主義與批判》等。
⑨Lie, R.“ Globalisation,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for localisation’,”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01, vol. 7, no. 2.
⑩[美]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41頁。
11馬德普:《普遍主義的貧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8頁。
12Gautam, A., & Droogan, J.“ Yoga soft power: how flexible is the posture?”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17, vol. 24, no. 1.
13巢巍:《文化向外交的躍變——印度瑜伽軟外交之路初探》,《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第72頁。
14Bhalla, N. et al“. Selling Yoga‘ Off the Mat’: A 10-year Analysis of Lifestyle Advertorials in Yoga Journal Magazin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022, vol. 48, no. 2.
15Semujju, B. “Theorizing Dependency Relations in Small Media,”Communication Theory, 2020, vol. 30, no. 4.
16張艷秋、陳遠:《非洲發展傳播的理論范式與實踐進路》,《西亞非洲》2024年第2期,第98頁。
17Takahashi, B.“ Towards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The role of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23, vol. 26, no. 4.
18Lechuga, M., & Aswad, N. G.“ ‘Decolonization’ As a Metaphor, Not a Movement,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 Critical Thematic Meta-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e,”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24, vol. 75, no. 4.
19Qiu, J. L.“ Three Approaches to Platform Studies: Cobweb, Billiard Balls, and Ant Societies,”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23, vol. 9, no. 3.
20謝立中:《兩種“中國社會(學)理論”及其再審視》《,學術月刊》2023年第9期,第102頁。
21Yau, N.“ A Global Sou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lantic Counci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a-globalsouth-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2024-6-13.
22呂新雨:《故事世界的背后是新舊世界觀博弈》《,社會科學報》,2024年7月11日,第6版。
23胡翼青:《論平臺世界的誕生》,《南方傳媒研究》2023年第4期,第1頁。
24Heeks, R. et al.“ China’s digital expansion in the Global South: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24, vol. 40, no.2.
25張軍:《價值哲學的存在論基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6頁。
26趙月枝等:《全球南方、社會主義探索與批判傳播學新想象——中印比較三人談》,《全球傳媒學刊》2019年第4期,第121頁。
27Aidoo, R., & Hess, S.“ Non-Interference 2.0: China’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 Changing Afric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15, vol. 44, no. 1.
28童桐:《理解全球治理中的知識傳播——基于知識類型學視角的考察》,《新聞與寫作》2024年第2期,第99頁。
29盛陽等:《走向區域:以區域國別為方法的精準化國際傳播理論與實踐》,《對外傳播》2024年第7期,第27頁。
30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185頁。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