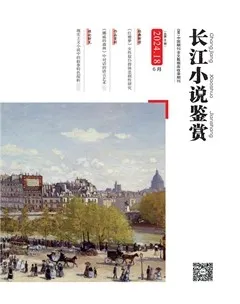斷裂與重構(gòu):論《樹民》中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
[摘 要] 《樹民》描繪了北美大陸三百余年的歷史變遷,講述了印第安人部落──米克馬克人的文化身份斷裂和重構(gòu)的艱難之旅。地理大發(fā)現(xiàn)后,隨著探險(xiǎn)者的腳步,越來(lái)越多的歐洲人來(lái)到美洲大陸,他們將與美洲土著文化截然不同的文明也帶到美洲大陸。在本民族文化與異質(zhì)文化的沖突和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碰撞中,米克馬克人的生態(tài)信仰被打破,語(yǔ)言傳承面臨危機(jī)。米克馬克人的文化身份也在沖突和碰撞中斷裂,陷入文化身份的困境當(dāng)中,而后通過(guò)主動(dòng)接納、學(xué)習(xí)歐洲文化和重新?lián)肀褡逦幕貥?gòu)自身的文化身份。
[關(guān)鍵詞] 文化身份 印第安人 《樹民》
一、引言
安妮·普魯是美國(guó)當(dāng)代重要的作家,曾獲普利策獎(jiǎng)、美國(guó)國(guó)家圖書獎(jiǎng),也是美國(guó)第一位獲得福克納小說(shuō)獎(jiǎng)的女作家。《樹民》的問(wèn)世令文壇再度掀起一股“普魯熱”。《樹民》講述兩個(gè)家族七代人在北美地區(qū)的發(fā)展歷程,跨越數(shù)百年的歷史,展現(xiàn)了歐洲人來(lái)到北美大陸后給這片土地帶來(lái)的災(zāi)難與重生,描寫了歐洲文明與印第安文明交融過(guò)程中的殘酷與疼痛,刻畫了深刻的印第安族群記憶。印第安人作為美洲的原住民,在數(shù)萬(wàn)年的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獨(dú)特的文化建構(gòu)了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然而,隨著十五世紀(jì)歐洲探險(xiǎn)者的到來(lái),西方世界的話語(yǔ)和霸權(quán)造成處于弱勢(shì)的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開始斷裂。
霍爾提出,關(guān)于文化身份,至少有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第一種立場(chǎng)是本質(zhì)主義文化身份觀,文化身份是“一種共有的文化,集體的‘一個(gè)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許多其他的、更加膚淺或人為地強(qiáng)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種歷史和祖先的人們也共享這種‘自我’。”[1]本質(zhì)主義身份觀界定下的文化身份反映著共同的歷史經(jīng)驗(yàn)和共有的文化符碼,這種歷史經(jīng)驗(yàn)和符碼為一個(gè)民族提供了一個(gè)穩(wěn)定、不變和連續(xù)的指涉和意義框架。霍爾關(guān)于文化身份的第二種觀點(diǎn)是反本質(zhì)主義身份觀,他認(rèn)為,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變化”的問(wèn)題。文化身份是有源頭、有歷史的,但是它也在經(jīng)歷著不斷的變化。霍爾主張不要將身份看作是已經(jīng)完成的事實(shí),而是將身份看作是一個(gè)處于過(guò)程之中,永不完結(jié)的“生產(chǎn)”。在歐洲人到來(lái)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由共享的祖先和共同的歷史經(jīng)驗(yàn)而建構(gòu)起來(lái)。在歐洲人到來(lái)之后,西方世界的話語(yǔ)和霸權(quán)造成處于弱勢(shì)的印第安人原本的文化身份斷裂。在此后,印第安人通過(guò)主動(dòng)學(xué)習(xí)歐洲的文化,和重新挖掘本民族文化的方式重新建構(gòu)自己的文化身份。
本文擬運(yùn)用霍爾提出的理解文化身份的兩種思路、文化身份的斷裂的觀點(diǎn),探究《樹民》中米克馬克族人文化身份的斷裂和重構(gòu)的歷程。
二、米克馬克族人文化傳統(tǒng)的斷裂
文化和身份之間存在互相限定的關(guān)系,不同的文化建構(gòu)出不同的文化身份,不同的文化身份又表現(xiàn)出不同的文化屬性。“身份的文化屬性決定了身份主體的文化實(shí)踐方式,身份主體的文化實(shí)踐方式反過(guò)來(lái)又生成了新的文化屬性。文化身份就在文化屬性、文化實(shí)踐和主體行為三者的互動(dòng)過(guò)程不斷生成,不斷重構(gòu)。”[2]在歐洲文化對(duì)印第安文化的強(qiáng)勢(shì)同化壓力下,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逐漸被瓦解,從印第安人的生活中漸漸消逝。歐洲文化對(duì)于印第安文化的同化不僅讓印第安人文化的表征從印第安人的生活中消失,更影響了印第安人的文化實(shí)踐方式,從根本上改變了印第安人新生成的文化屬性。文化之根被斬?cái)啵〉诎踩说奈幕矸蓦S之?dāng)嗔选?/p>
1.“萬(wàn)物有靈”信仰的破滅
印第安人信仰“萬(wàn)物有靈論”,他們重視與自然保持和諧的關(guān)系,將自然視為神圣的,對(duì)自然抱有尊重和崇敬之情。印第安人堅(jiān)信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不僅僅是一個(gè)生物,而是真正地有生命、有意識(shí)和感知能力,和人一樣具有智慧和靈性。在小說(shuō)中,最能體現(xiàn)印第安人的信奉“萬(wàn)物有靈論”就是印第安女人——瑪希,“對(duì)于瑪希來(lái)說(shuō),它(森林)是一個(gè)活著的實(shí)體,像河道一樣重要,充滿了藥物、衣物、庇護(hù)所、工具材料等種種恩惠,這些東西每個(gè)人都應(yīng)帶著感恩之心與它和諧地共同生活。”[3]瑪希身上的方方面面都體現(xiàn)著印第安人的生活智慧和印第安人所信仰的“萬(wàn)物有靈”理念。
阿希爾是法國(guó)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兒,在印第安族群中的生活中漸漸獲得作為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在最初面對(duì)來(lái)自歐洲文化的同化壓力時(shí),阿希爾堅(jiān)定地想按照米克馬克的方式生活,并且堅(jiān)信他的后代也將如此。然而當(dāng)阿希爾最后一次打獵歸來(lái),看到被英國(guó)士兵焚毀的棚屋以及妻子被燒焦的尸體,阿希爾最終以顫抖而不自然的聲音宣告:“我不再打獵了。我在這里的人生已經(jīng)結(jié)束了。我將離開這片屬于我們母親的土地,我會(huì)去往南方,到緬因伐木。我要去蹂躪他們的土地。”阿希爾最終離開了且終身沒(méi)有再回歸米克馬克這片屬于母親的土地,拋棄印第安人的“萬(wàn)物有靈”的信仰。阿希爾的境遇是許許多多的印第安人的命運(yùn)的縮影。處于劣勢(shì)地位的印第安的文化傳統(tǒng)受到了強(qiáng)勢(shì)的歐洲文化的侵軋,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在這一殘酷的過(guò)程中逐漸斷裂。
2.語(yǔ)言傳承的危機(jī)
美洲大陸上曾經(jīng)生活著兩千多個(gè)部落,有數(shù)千萬(wàn)的人口,擁有豐富的語(yǔ)言。語(yǔ)言本身既是文化身份的一個(gè)部分,同時(shí)也是文化身份的載體,在一個(gè)民族的內(nèi)部起著凝聚人心,形成民族認(rèn)同和文化認(rèn)同的重要作用。雖然沒(méi)有文字記錄,但是印第安人用語(yǔ)言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神話傳說(shuō)、民間故事,講述著人與大自然的親密關(guān)系,傳唱著表達(dá)印第安人喜怒哀樂(lè)的歌曲。“個(gè)人的文化身份與其過(guò)去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guān),而一個(gè)民族的文化身份也與其自身的民族傳統(tǒng)、本土文化相互聯(lián)系,因而一個(gè)民族的文化身份就是這個(gè)民族在形成和發(fā)展過(guò)程中凝練出的表現(xiàn)在民族文化特色上的一種精神凝聚力和物質(zhì)積淀。”[4]瑪希和泰歐蒂斯特、埃爾菲奇待在一起的時(shí)候總是低聲地說(shuō)說(shuō)笑笑,給兩個(gè)孩子講述古老的米克馬克故事,講述給米克馬克族人帶來(lái)無(wú)盡歡樂(lè)的復(fù)雜笑話和語(yǔ)言游戲。而隨著米克馬克人與歐洲人越來(lái)越多的接觸,其他語(yǔ)言也進(jìn)入到米克馬克的語(yǔ)言當(dāng)中,“米克馬克的語(yǔ)言中早已充斥著法語(yǔ)詞匯,還帶有葡萄牙語(yǔ)和巴斯克語(yǔ)的殘留,源于生活在他們的海岸上的那些早期歐洲漁民”,米克馬克語(yǔ)言失去了原本的純真性。語(yǔ)言的斷裂導(dǎo)致文化的斷裂,“米克馬克人遺失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傳教士們的上帝”。在小說(shuō)中,掌握米克馬克語(yǔ)言的人越來(lái)越少,他們不再講述米克馬克的傳奇故事。最后,即使是在米克馬克族群中成長(zhǎng)的最年輕的一代米克馬克人也不能流利地說(shuō)米克馬克語(yǔ)。語(yǔ)言是文化身份最重要的表征之一,也是文化身份的建構(gòu)元素之一,米克馬克語(yǔ)言嚴(yán)重?cái)嗔训木车匾舱f(shuō)明了印第安人文化身份的斷裂。
三、米克馬克族人的文化身份困境
歐洲人不斷通過(guò)種族滅絕、種族隔離和同化政策打破印第安人的文化傳承,使得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斷裂不斷加劇。印第安人既無(wú)法回歸原本純粹的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又不被歐洲文化真正接納,從而陷入了文化身份困境。
1.難以回歸的印第安文化身份
《樹民》中的米克馬克人曾非常堅(jiān)決地抵制來(lái)自歐洲的產(chǎn)物——?dú)⑺酪粋€(gè)從英國(guó)人手中拿到一個(gè)精美茶碟并用來(lái)喝水的年輕的米克馬克獵人。然而,在隱形而又無(wú)力抵抗的同化中,米克馬克人后來(lái)接受了族群當(dāng)中兩個(gè)擁有茶碟的家族。大酋長(zhǎng)梭普賽勸告族人:“如果我們米克馬克人想要存活下來(lái),我們必須一直在頭腦中保持我們米克馬克人的方式……我們必須把米克馬克人的世界清晰地保留在我們的頭腦和生活當(dāng)中”。然而,年輕的族人并不能理解梭普賽強(qiáng)調(diào)的米克馬克人的方式的重要性,反而擔(dān)心不能再使用鐵鍋,要回歸米克馬克人過(guò)去使用木盆放在熱石頭上煮東西的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器具是文化身份的一面,歐洲文明讓印第安人的生活發(fā)生了許多的改變。這些變化在無(wú)形之中蠶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我不是任何一類人,無(wú)論英國(guó)人、米克馬克人、法國(guó)人、美洲人。我無(wú)處可去。村子里的很多米克馬克人假裝一切都好,但是動(dòng)物非常少見,而且沒(méi)人知道正確的生活方式”,印第安人陷入了不知何去何從的文化身份的困境。在歐洲文化同化下,米克馬克的文化傳統(tǒng)已經(jīng)變得面目全非,處于身份困境當(dāng)中的印第安人永遠(yuǎn)無(wú)法再回歸最原始的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
2.歐洲文化的“他者”
歐洲人將印第安人視為未開化的野蠻人、原始人,印第安人的文化被動(dòng)地與落后、愚昧劃上等號(hào)。小說(shuō)中的克雷姆神父對(duì)印第安人抱有一定的同情和憐憫,但是依舊以一個(gè)高高在上的視角來(lái)審視印第安人的文化,將印第安人視為他者。“他們?nèi)紩?huì)說(shuō)法語(yǔ),而印第安人還是沒(méi)學(xué)過(guò)法語(yǔ)比較好。稍大的兩個(gè)兄弟還可以使用羅馬字母進(jìn)行讀和寫,這是一個(gè)重大錯(cuò)誤。這些人有能力造成很大危害,惹上麻煩。”雖然歐洲人有意地同化印第安人的文化,但是印第安人并不為歐洲群體所接納。印第安人一直是被排除在真正的歐洲文化之外的“他者”,歐洲人也不希望印第安人掌握可能威脅他們自身地位的知識(shí)和技能。
老昆陶將白人比喻為水,米克馬克人是油,兩者的混合是梅蒂斯人。水和油在碗中混合,油最終還是漂浮到了水面上,就像曾經(jīng)的昆陶,試著變成個(gè)白人,而最終身體中的米克馬克因子還是浮到了水面上。盡管希望有一日,水與油能夠徹底混合到一起,但是最終油還是會(huì)浮上水面。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艱難抉擇中,在本民族文化和歐洲文化的交界點(diǎn)上,印第安人既心痛現(xiàn)代文明逐漸取代部落傳統(tǒng),又無(wú)法從時(shí)代的潮流當(dāng)中抽身;既無(wú)法保留完全作為一個(gè)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又無(wú)法真正地在歐洲人主導(dǎo)的社會(huì)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重構(gòu)文化身份
霍爾主張“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變化’的問(wèn)題。”文化身份不是封閉的、已經(jīng)完成的,文化身份不固定于某一本質(zhì)化的過(guò)去。雖然文化身份有歷史和源頭,但是文化身份也在歷史、文化和權(quán)力的推動(dòng)下不斷變化。霍爾認(rèn)為“作為一種表征系統(tǒng),建構(gòu)成為獲得身份的主要途徑。而身份的建構(gòu)過(guò)程總是通過(guò)他者來(lái)確定自身,通過(guò)負(fù)面來(lái)呈現(xiàn)正面,通過(guò)否定來(lái)得出肯定的答案。”[5]歐洲人將自身建構(gòu)為文明、發(fā)達(dá)、先進(jìn)的表征,非歐洲則是與之相反的表征。在幾個(gè)世紀(jì)的時(shí)間里,歐洲文化作為美洲大陸上的強(qiáng)勢(shì)文化,占據(jù)著建構(gòu)文化身份的強(qiáng)勢(shì)地位,印第安人是被歐洲文化定義的印第安人。《樹民》中,歐洲文化逐漸同化印第安人的文化,致使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斷裂,在這一過(guò)程中,歐洲人占據(jù)了印第安人文化身份建構(gòu)的主導(dǎo)權(quán)。歷經(jīng)幾代人,米克馬克人最終覺(jué)察自身的危機(jī),認(rèn)清自身的現(xiàn)狀,重新把握了自身文化身份建構(gòu)的方向。
1.對(duì)歐洲文化的主動(dòng)接納
“對(duì)主體錯(cuò)位的辨識(shí)、對(duì)主體性危機(jī)的洞見,是從屬于社會(huì)群體和邊緣民族主體意識(shí)和主體能動(dòng)性覺(jué)醒的前提。”經(jīng)歷了驅(qū)逐、戰(zhàn)爭(zhēng)、迫害、奴役,米克馬克人深刻認(rèn)識(shí)到自身面臨著嚴(yán)重的危機(jī),也意識(shí)到“幻想他們(歐洲人)有一天會(huì)回到他們的原來(lái)的國(guó)家,不過(guò)是一場(chǎng)白日夢(mèng)。他們永遠(yuǎn)也不會(huì)從我們的家園離開的。他們會(huì)一直與我們同在。若是我們想要活下去,就得像他們一樣。”殘存的米克馬克人認(rèn)識(shí)到對(duì)于歐洲文化他們不能再保持被動(dòng)接受和被迫改變的態(tài)度和方法,于是開始了主動(dòng)接納和學(xué)習(xí)歐洲的文化,重新建構(gòu)自身的文化身份。“如果我們想要獲得任何曾經(jīng)屬于我們的土地,我們就得用白人的方式,用文件來(lái)持有它。還有錢。想要學(xué)會(huì)那些英國(guó)法律,我們就得會(huì)讀、會(huì)寫、用英語(yǔ)。孩子們必須學(xué)會(huì)那些行文方式,若是他們要在這里生活的話。否則就只能坐以待斃。”為了獲得金錢,印第安人從事著最辛苦、最危險(xiǎn)的工作,做任何他們能找到的活兒。女人們簽署了協(xié)議將孩子也送到了寄宿學(xué)校之中,接受在白人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教育。他們不再居住在舊式的工棚營(yíng)地當(dāng)中,而是居住在白人式的房子中,聽收音機(jī),在小餐館中吃飯,開車去工作。米克馬克人主動(dòng)學(xué)習(xí)歐洲文化形式的生活方式,放棄了他們?cè)镜奈幕矸葜笇?dǎo)下的生活方式。然而,與前幾代人的文化身份出于外來(lái)壓力發(fā)生斷裂不同,這幾代的人通過(guò)自發(fā)學(xué)習(xí)歐洲文化、融入白人社會(huì)主動(dòng)地進(jìn)行著自身的文化身份建構(gòu),將歐洲文化主動(dòng)地縫合到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當(dāng)中,他們不再是處于歐洲文化的同化壓力之下被迫改變的客體。
“文化身份就是認(rèn)同的時(shí)刻,是認(rèn)同或縫合的不穩(wěn)定點(diǎn),而這種認(rèn)同或縫合是在歷史和文化的話語(yǔ)之內(nèi)進(jìn)行的。”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隨著歷史的語(yǔ)境變化而變化著,新的歷史話語(yǔ)不斷縫合到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當(dāng)中。
2.對(duì)民族文化的擁抱
印第安人學(xué)習(xí)歐洲文化進(jìn)行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構(gòu)并不意味著完全拋卻作為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盡管為了生存,米克馬克人學(xué)習(xí)歐洲文化進(jìn)行自身的文化身份的建構(gòu),但許多的米克馬克人依舊珍視本民族的文化。
珍妮·塞爾和菲力克斯·米烏斯雖然在印第安族群中成長(zhǎng),但是表姐弟兩人的第一語(yǔ)言都是英語(yǔ),并不能流利地使用米克馬克的語(yǔ)言。然而,他們并沒(méi)有放棄米克馬克語(yǔ),“他們會(huì)在早上很早的時(shí)候,一起坐在電腦前學(xué)習(xí)米克馬克詞語(yǔ),跟著利斯圖古部落原住民的發(fā)音誦讀。”語(yǔ)言是文化身份最重要的載體和最直接的表征,學(xué)習(xí)民族語(yǔ)言的過(guò)程也是民族文化和歷史記憶重新參與文化身份重構(gòu)的過(guò)程。
帕薩迪西婭·塞爾是集白人、萬(wàn)帕諾亞格人和米克馬克人的基因、思想和事業(yè)于一身的混合體。帕薩迪西婭從小在白人中成長(zhǎng),接受了與其他白人無(wú)異的教育。被大學(xué)開除后,帕薩迪西婭踏上了探尋自身身份旅途,“我想要去看看塞爾家族的那些人,我想要知道我是誰(shuí)。”帕薩迪西婭獨(dú)自找到其余的米克馬克的族人,也正是帕薩迪西婭對(duì)自身的文化身份的探尋,讓一直怨恨自己米克馬克人身份的埃加與族人重新恢復(fù)了聯(lián)系。作為米克馬克后裔的帕薩迪西婭天生對(duì)地球上的植物和森林充滿強(qiáng)烈的興趣,最終投身于重新種植森林的事業(yè)當(dāng)中。珍妮·塞爾和菲力克斯·米烏斯在帕薩迪西婭的帶領(lǐng)下也參與到重新種植森林的工作中。森林曾與印第安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森林提供了印第安人賴以為生的資源,是建構(gòu)印第安人文化身份基礎(chǔ)的一環(huán)。種植樹木、恢復(fù)森林的過(guò)程也是對(duì)印第安人的文化根源進(jìn)行挖掘和重述的一環(huán),使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融入符合當(dāng)下歷史語(yǔ)境的文化身份的建構(gòu)當(dāng)中。“身份的喪失,只有這些被忘卻的聯(lián)系再次被放置于適當(dāng)?shù)奈恢脮r(shí),才開始彌合。”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的斷裂,在重新挖掘本民族的文化,重述本民族的文化中才能真正彌合。
五、結(jié)語(yǔ)
霍爾主張,文化身份不是固定不變的本質(zhì),文化身份無(wú)法毫無(wú)變化地置身于歷史和文化之外。十五世紀(jì)開始,在歐洲文化的同化之下,印第安人的原本的文化身份逐步斷裂。新的歷史和權(quán)力的話語(yǔ)逐漸縫合到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當(dāng)中,參與到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重構(gòu)當(dāng)中。《樹民》中的米克馬克人最終自發(fā)學(xué)習(xí)歐洲文化和重新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讓歐洲文化參與到他們的身份重構(gòu)當(dāng)中,同時(shí)也保留了作為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是開放的,是永不完結(jié)的生產(chǎn),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建構(gòu)也不會(huì)終結(jié),它將在具體的歷史的語(yǔ)境當(dāng)中繼續(xù)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 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A]//羅剛,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教育出版社,2016.
[2] 徐明玉.斯圖亞特·霍爾的文化身份理論研究[D].沈陽(yáng):遼寧大學(xué),2021.
[3] 安妮·普魯.樹民[M],陳恒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20.
[4] 王建平.美國(guó)印第安文學(xué)于現(xiàn)代性研究[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4.
[5] Stuart Hall.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C]//Anthony D.K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1:21.
[6] 劉英杰,田雨.從反本質(zhì)主義的“身份”到逆向文化策略——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觀探微[J].求是學(xué)刊,2021(1).
(特約編輯 范 聰)
作者簡(jiǎn)介:何燕飛,煙臺(tái)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研究方向?yàn)橛⒚牢膶W(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