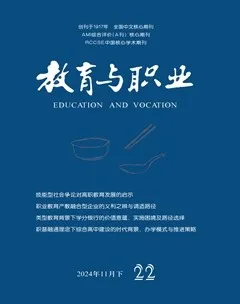技能型社會爭論對高職教育發展的啟示
[摘要]技能型社會建設與高低技能均衡、人力資本理論和技能偏向理論有密切關系。技能均衡理論對于高(低)技能均衡的概念、高(低)技能均衡的國家標簽、低技能職業發展有不同觀點;人力資本理論中關于職業教育能否增加工資收入、促進經濟發展、是否復制社會階級等方面有不同意見;技能偏向理論關于技術發展是否增加技能需求、技術是否是影響技能需求唯一因素、技能與教育是否存在競賽等方面有不同觀點。高職教育要精準把握技能社會的發展趨勢,正確對待低技能職業,改善高職教育的政策環境,建立高技能高績效的企業管理制度,培養高技能人才。
[關鍵詞]技能型社會;高(低)技能均衡;人力資本理論
[作者簡介]何楊勇(1977- ),男,浙江諸暨人,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職教所所長,教授,博士;祝巧(1989- ),女,江西上饒人,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助理研究員,碩士。(浙江" 杭州" 310018)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4年浙江省社科聯研究課題“浙江省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構建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24B088,項目主持人:祝巧)
[中圖分類號]G710"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4-3985(2024)22-0005-07
建設技能型社會成為近年來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重要理念和戰略。職業教育和培訓要加快構建面向全體人民、貫穿全生命周期、服務全產業鏈的職業教育體系,加快建設國家重視技能、社會崇尚技能、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的技能型社會。關于什么是技能型社會、怎樣建設技能型社會,不同理論間存在爭論。探討這些不同觀念,可以給當前高職教育發展提供一定的啟示。
一、高(低)技能均衡社會的爭論
關于高(低)技能均衡社會理論的提出,學界有多種觀點。較早提出低技能型社會理論的是英國的戴維·芬戈爾德(David Finegold)和戴維·索斯凱斯(David Soskice)。他們認為:“英國陷入低技能均衡,大部分企業雇傭的員工幾乎沒有經過培訓,生產和服務質量偏低。低技能均衡主要原因是社會網絡的自我強化和政府機構不斷削弱對提升技能水平的需求。促成削弱技能需求的一系列經濟制度包括:產業的組織、企業和工作的運行、與產業相關的體系、金融市場、政府和政治的結構,以及教育和培訓體系的運作。”[1]根據保羅·希松斯(Paul Sissons)的理解,英國作為低技能均衡社會有以下特點:一是英國大部分的管理者和工人從事低質量、低價值的工作。二是自我強化意味著已形成閉環的循環系統:因為需求技能水平較低,所以供給的技能水平也較低,這成為發展和拓展高價值工作的障礙。三是低技能的需求與英國特定的制度安排相關。英國低技能均衡社會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政府關注創造就業崗位的數量,勝于提升就業崗位的質量[2]。
與低技能均衡社會對應的是高技能均衡社會。根據研究者們的理解,高技能均衡社會不僅涉及技能,還應包括社會、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休·勞德(Hugh Lauder)從勞動力市場結構、教育和培訓體系、社會和文化特征、政府和市場互動四個方面,把技能社會分成高技能社會模式(德國)、制造業高技能模式(日本)、發展高技能模式(新加坡)和高低技能并存模式(英國)四種類型。德國作為理想類型的高技能社會有以下特征:有相對固定不變的勞動力市場,教育和培訓與勞動力市場比較密切,“雙元制”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很容易完成從教育向工作的過渡;社會融合程度較高,收入相對平等。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等人將高技能均衡社會的七個重要社會條件概括成為(7C):一是共識(consensus),社會凝聚力強,彼此高度信任;二是競爭力(competitive capacity),不依靠降低成本,而通過提升產品價值來進行競爭;三是能力(capability),對人力資本的持續發展和投資,特別是新技能的“情感智力”(自我約束和責任、改革與創新、適應變革、有不斷學習的能力);四是協調(coordination),相關政府政策的協作;五是傳播(circulation),高水平技能擴散到整個社會(反對技能兩極分化);六是合作(cooperation),融入社會制度之中并高度信任;七是包容(closure),在高技能社會產生利益的過程中,反對社會排斥和歧視[3]。
對于高(低)技能均衡社會的說法,學界有不同意見。其一,對高低技能的概念闡釋比較模糊。保羅·希松斯認為“對于低技均衡的闡釋還是比較模糊,對于從何種程度上加以評估,采用什么手段加以測量,都未有定論。從許多方面來看,低技能均衡更多是對結果的描述,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4]。他指出,進入21世紀,英國自主創業的勞動力出現了快速增長,但自主創業的技能屬于高技能還是低技能則難以區分。羅伯·威爾森(Rob Wilson)等人指出,芬戈爾德和索斯凱斯把低技能均衡看成一個動態的過程,個體組織有努力的必要和可能。同時,低技能與高技能之間有一個過渡銜接的范圍和空間,兩者并不是非此即彼、完全對立的概念。維吉塔·阿加瓦爾(Vijita Aggarwal)指出,如果僅僅按照學歷來判斷技能高低,那么德國算不上高技能均衡社會,因為德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并不高;英國也算不上低技能均衡社會,因為英國高等教育的回報率確實較高。如果按照技能資格證書來判斷技能的高低,則德國和英美體系對技能的理解是不同的。英美體系認為,技能是個人的才能或資本,技能更多的是指能夠完成具體的任務或工作,與行業和產業的關聯性較小。德國的技能概念是與行業相聯系的,屬于系統性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巧相結合。其二,高低技能型國家標簽的謬誤。如前文所說,對于將德國看成高技能社會、英國看成低技能社會的看法,阿加瓦爾提出了不一樣的觀點。她認為,德國屬于偏好中等技能的社會,其制造業在全球遙遙領先,然而其金融領域、軟件市場和生物科技的發展落后于英國。德國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優勢主要是產業工人比較優秀,能夠靈活、負責、多樣化地生產高質量的工業產品。德國有重視員工技能培訓的社會基礎,工人對中等技能的掌握比較普遍,適合于管理和監督崗位的技能工人數量比較充足。英國職業教育的地位則相對較低,企業主既沒有參加職業培訓的義務,也無法從技能工人培養中獲益。英國的自由勞動力市場沒有把技能作為潛在資本,企業一般不進行人力資源培訓的長期投資,但在新興產業方面有數量較多的高技能勞動力,而且高等教育畢業生的競爭力強、較少浪費。英國屬于高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兩極分化比較明顯的國家,其在“基礎科學和藝術創造”的技能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規范不多的、網絡聯系比較松散的領域如生物技術、廣告、媒體和娛樂等方面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就像德國在汽車、化工、機械和交通設備、制藥方面處于領先地位,而這些領域恰恰需要的是中等技能人才[5]。其三,關于技能社會是否需要低技能。有學者指出,在新冠肺炎感染期間,醫療和護理工作、農業、食品加工、廢品回收、環衛、超市工作、倉儲和后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成為社會和社區生活質量的重要保障。這些職業包括衣食住行等短期消費服務,對社會存續非常重要,但通常被認為不需要多少技能,工資報酬也相對低廉。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職業性質決定的。許多對社會生存發展非常重要的職業屬于勞動密集型職業,這些職業的生產力水平不高,工資水平和邊際收益都較低。二是社會偏見起作用。歷史上很多社會存續的職業通常被認為無助于社會財富的增加,受到排斥和歧視。三是技能分層不合理。老年人護理、病人護理和殘疾人護理這些職業的確需要高超而復雜的情感技能,但從資本家的立場來說,只有帶來高收益的技能才是高技能。在所謂推崇“高技能”的人看來,只有擁有大學文憑的人,才更適合這樣的工作,但恰恰很多技能的高低與學歷無關,需要從工作中學習。農業和護理人員之所以沒有高工資,主要是因為這些技能很難獲得高額利潤的生產性成果。相反,那些培訓和營銷管理人員、私人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電話營銷員和保險員的工資較高,并非因為這些職業需要高技能,而是這些工作可以使企業獲得最大的利潤。
二、人力資本理論的爭論
20世紀60年代,芝加哥經濟學派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和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等人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每一位個體都在追尋個體利益最大化,個體關于教育和培訓的投資,主要為了將來能夠獲得更多的收入。埃姆魯拉·譚(Emrullah Tan)將人力資本對個體的經濟價值概括為幾個前后邏輯相連的環節:一是個體通過教育和培訓獲得知識和技能;二是知識和技能能夠提高生產效率;三是在理想狀態的市場,個體的生產效率決定工資水平,生產效率提高,個人工資水平隨之提升。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對國家來說,通過教育投資,能提高國家整體的生產力水平,降低失業率,促進社會流動。舒爾茨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指出,“最近大量的研究證明了一個基本命題,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現代化,農業用地的重要性下降,技術和知識構成的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上升”[6]。20世紀70—80年代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新加坡經濟的崛起,都離不開人力資本的有效作用。
不可否認,人力資本理論自始至終引發了不少爭論。其一,關于教育提升生產效率的爭論。根據人力資本假設,學校教育能夠提升生產效率,但基于同樣事實,信號篩選理論提出了不一樣的解釋:一是學校教育并不是提高生產效率的原因,而是受教育者具有較高生產效率的信號。學校教育的功能在于篩選出那些符合提高生產效率的學生,過濾掉不符合提升生產效率的學生。二是由于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個人的受教育程度能夠簡單證明其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但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個人生產效率的高低之間并沒有相關性。文憑社會理論的提出者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通過他人的調查數據分析指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雇員的生產力通常不會更高;在不同級別的美國工人樣本中,有時他們比其他人的生產力還要低。”[7]其二,關于理性經濟人的爭議。有學者指出,人的計算能力和記憶力都是有限的。當面對解決問題的大量信息時,個體往往選擇滿意的解決方案。行為經濟學告訴我們,我們的決定很大程度上被我們的直覺、理解甚至錯覺所引導。一方面,人們選擇教育、接受教育并非完全出自經濟回報上的理性算計,也可能受文化、社會環境和個人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除了經濟功能,還有促進個人發展和社會融合的功能[8]。其三,關于人力資本促進個人和國家發展的爭論。人力資本的反對者認為,職業、性別、技術、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周期等因素都會影響個體經濟收益,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制度等都會影響國家經濟發展,而教育只是諸多影響因素中的一個。工資的工業和職業結構決定了國家的分配。即使技能偏向的主要支持者戈爾丁和卡茨也表示,哈佛經濟和金融專業的畢業生薪水豐厚,可能是因為華爾街的影響,而不是這些員工的非凡技能[9]。埃姆魯拉·譚通過數據分析指出,委內瑞拉在1960—2000年,隨著教育水平的逐漸提高,工資水平卻日益走低,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的盲目擴張導致教育質量下降,教育的供給和勞動力需求之間不匹配,委內瑞拉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無法讓受教育者能夠充分使用他們的技能[10]。其四,來自社會再生產的爭論。鮑爾斯、金帝斯、布迪厄等人從批判主義的視角出發,認為教育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過程。布迪厄指出,高等教育成為社會階級再生產的重要工具。他舉例說,高階層管理人員的孩子上大學的機會是工人階級的40倍、農民子弟的80倍;背景弱勢的大學生比背景優越的更有可能就讀于地位較低、未來就業前景不明確的科系[11]。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認為,當前美國的大學自主招生演變成家長經濟實力的較量,越來越多家庭收入較低的青少年無法進入名牌大學學習,教育不公平現象日益嚴重。
三、技術發展與技能偏向的爭論
新的技術發展會增加對技能工人的需求,這一假設被稱為技能偏向技術變革。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思考技術發展和創新對勞動力構成和工資的影響。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假設技術變革是一種“創造性破壞”的力量,在破壞現有就業機會和產業的同時,產生新的就業機會和產業。技能偏向的支持者主張,與信息和數字技術相關的通用技術是技能偏向而不是技能替代,新技術增加了對更高技能的需求而非用機器取代技能。他們認為,在整個20世紀,新技術的發展需要越來越多受過教育的工人,這一趨勢在知識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繼續下去。
伊萊·伯曼(Eli Berman)等人發現,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新技術工具只是取代了非技能型工作,工作崗位對于技能工人的需求有很大增加,這可以用技能偏向來解釋[12]。達倫·阿克莫格魯(Daron Acemoglu)認為,新技術的發展和對技能工人的需求之間存在內在關聯,兩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大衛·奧托爾(David Autor)等人通過數學模型,用1960—1998年人口普查和CPS文件的工人樣本進行測試,以驗證計算機在工作場所的廣泛采用可能會改變工作場所的技能需求。他們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技術的投資增長和任務的技能要求提升呈現正相關[13]。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和勞倫斯·凱茲(Lawrence Katz)指出,“新技術的確改變了對不同類型勞動力的相對需求,然而,一項新技術對工資結構的總體影響不僅反映出需求的變化,也反映出人們通過上各類學校、參加在職培訓或其他途徑所作出的供給反應。僅僅因為技術提高了對勞動力技能、教育和專業知識的需求,并不代表經濟不平等一定會上升”[14]。
對于技術偏向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有學者認為,技術的發展,會降低對技能的需求,增強對員工的監控。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指出,隨著技術的發展,工作過程的標準化,統一化程度越來越高,一些職業領域的工作出現了去技能化[15]。雷·馬歇爾(Ray Marshall)和馬克·塔克(Marc Tucker)指出,隨著技術的發展,美國鋼鐵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采用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把任務分解成流水線作業,通過廉價競爭來獲取利潤,大部分工人無須太多技能。科學技術的發展,不但沒有給一線工人帶來便利,反而監督工人生活。其二,導致了貧富分化,產生剝削。有的研究將經合組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和工資的兩極分化歸因于新技術的發展與變革。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認為,隨著技術的發展,美國經濟的生產率更高,但實際工資停滯不前,更多人失業。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指出,高新技術的發展,并不使工作越來越輕松,高端的技術產品也可能產生了大量低技能和高強度勞動。硅谷不僅僅是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生產的空間,也是基于地域和不平等的社會現實的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生產中的資本積累空間。特別是婦女和外來移民一定程度上在以計件工作為基礎的低收入的信息和通信技術(ICT)制造業里工作。由于工作場所、空氣、土壤和飲用水的污染,往往帶來各種健康威脅[16]。其三,教育與技術競賽的爭論。教育和技術競賽理論認為,隨著新技術發展,將會增加對技能工人的需求。克勞迪婭·戈爾丁和勞倫斯·凱茲對美國20世紀的教育和技能競賽進行歷史分析后發現,美國的貧富差距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是縮小的,但從20世紀末開始不斷飆升。他們通過對比得出結論:在這兩次技術變革和教育競賽中,教育在20世紀上半葉運行得更快,技術在過去30年里遠遠超過了教育。針對教育與技術競賽的觀點,也有研究指出,在現代社會,影響工資收入差異的原因不能簡單地通過教育和技能的競賽來解釋,不同性別、不同教育層次、不同職業領域,都會影響工資差異[17]。皮凱蒂指出:技術賽跑理論的最失敗之處在于無法解釋1980年來,部分超級經理人的高收入現象[18]。他認為,教育和技術競賽論的解釋主要有兩個缺陷:一是“美國工資不平等的擴大主要源自工資最頂層人群(前1%人群,甚至前0.1%人群)收入的增長”,而前1%人群“在教育水平、學校背景或職業經驗上的不連續性”,收入增長存在巨大的離散性,教育因素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19]。二是有些發達國家出現了超高薪激增的現象,有的國家并不明顯。他指出,雖然超高薪激增現象在發達國家成為趨勢,但也有差異。這一情況在美國最為顯著,英國其次,日本、德國、法國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并不明顯[20]。這表明“不同國家的制度差異,比技術進步等一般性和先驗普遍性因素起著更為核心的作用”[21]。
四、啟示與建議
(一)高低技能均衡社會爭論與高職教育發展
一是加強高技能均衡社會的建設。高技能社會不只是技能的發展,還涉及產業、制度和文化的跟進。對于高職教育來說,不僅要提高學生的專業技能,還要引導學生形成重視技能、崇尚技能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要讓學生積極參與技能型社會制度的構建。二是精準把握國家和地區技能發展優勢。技能培養是高職教育的重要依托,對于高職教育發展至關重要。德國的“雙元制”享譽世界,但這一制度與德國產業政策、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可以借鑒德國職教“雙元制”的優越之處,但也要結合我國國情。我國人口眾多,地區差異明顯,工業體系較為完整,在核電、高鐵、人工智能、5G、新能源汽車等方面有一定的產業優勢。提升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競爭力,高職教育需要加強優勢產業技能人才的培養,圍繞產業優勢,培養高技能人才,形成良性循環的高質量技能形成路徑。三是正確對待低技能職業。即使在技能型社會也會存在少許的低技能職業,這些職業可能無須太多技能,但對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極為重要。首先,要從低技能職業向高技能職業轉化。積極引導低效率、低技能的職業向高效率、高技能的職業轉化。其次,要糾正錯誤的高低技能觀。諸如護理、托管、保姆等職業,不但需要較高的專業技能,也需要高度的情感投入,需要承認這些職業的重要社會價值,為提高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和社會待遇而努力。最后,職業是個體賴以謀生的手段。即使有些職業,并不能創造多少的經濟效益,但對于處于下層的社會弱勢群體來說,關系到他們的生存,因此,保留一部分低技能的職業也是保護弱勢群體利益、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對于高職教育來說,需要積極發揮低技能職業向高技能職業轉型升級中的作用,在提升專業技能的同時,重點加強道德情感的培養,發揮高職教育的服務功能。
(二)人力資本理論爭論與高職教育
人力資本理論雖然受到諸多學者的批評,但問題在于批評者們無法提供比人力資本理論更合理、更有效的關于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邏輯假設。通過人力資本理論及其爭論,可以為技能社會建設和高職教育提供啟示。一是重視高職教育對經濟發展的價值。根據人力資本理論的假設,技能對社會和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但依賴于教育這座橋梁。無論是政府的政策愿景還是學生的專業選擇,都把高職教育的經濟價值放在重要位置。高職教育不僅僅有經濟價值,但離開了經濟價值的高職教育,也失去了其作為類型教育的本質特征。二是發揮高職教育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需要建立合理的產業發展結構,引導人力資源轉向生產領域,為社會創造財富。20世紀60—7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教育上行、工資下降的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社會制度的不合理,許多非生產性職業報酬過于豐厚,大量高素質技能人才離開生產性工作崗位,轉向雖有豐厚利潤但不創造社會財富的崗位。另一方面,高職教育要以滿足技能需求為出發點。對國家和地區來說,在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會有相應的技能需求。建立良性的高職技能需求預測機制,高職教育需要主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正當需求,通過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合理設置專業,滿足各利益主體的短時和長遠需求。三是防止文憑泛濫。英美等國已出現優質教育資源被上層階級壟斷、下層勞動人民上升無望的狀況。要打破這種局面,需要堅持高職教育以促進就業為導向、提升高職教育的質量和地位,增強高職教育的吸引力;倡導職業平等的理念,根據工作對技能的實際需要確定需要的技能和素質要求,減少學歷攀比;建立平等的薪酬體系,縮小不同學歷層次的薪酬差異。
(三)技能發展和技術偏向爭論與高職教育
從技能發展和技術偏向的爭論分析,影響技能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技術的變革和發展、微觀的企業管理制度和宏觀的政策制度導向。一是高職教育要適應技術變革和發展。隨著技術的變革和發展,職業技能需求隨之變化。有學者指出,把新技術分為兩類:一類是能使技術,“新技術增強了一些工人的技能,讓他們能完成新任務,既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率,又使他們的工資上漲了”。另一類是取代技術,“使得一些工人的技能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變得多余,給他們帶來了工資下行的壓力”。人工智能的發展,生產服務自動化對于不同職業的影響程度有所差別。諸如教育、管理、醫療技術、計算機/數學工程等領域,受自動化影響的比例相對較低,而諸如行政/辦公、銷售、餐飲/服務相關、運輸/物流、農業/漁業/林業受自動化影響的比例相對較高[22]。高職教育需要適應技術發展這些客觀上的技能需求變化,根據現實條件,選擇和確立適合的培養目標。二是建立有利于高職教育發展的企業管理組織。有學者認為,企業管理組織和高職教育之間存在相互適應、相互塑造、循環影響的關系。加強企業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改革對于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理想的工作組織方式應當是高技能和高績效的:“鼓勵雇主支付高工資、提高生產力并采用高績效工作組織形式并限制不這樣做的雇主”“鼓勵雇主為提高雇員素質而投資”“建立技術援助方案推動各種企業的管理向高績效工作組織發展”[23]。三是確立有利于高職教育發展的政策導向。皮凱蒂認為,對于資本收益大于勞動收益的社會來說,教育、知識和技術對促進社會流動價值甚微。要真正發揮高職教育的作用,需要建立一個技能致富、使知識和技能有用武之地的社會。從政府的宏觀政策而言,需要繼續保持對外開放,積極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先進技能和知識,建立良好的勞動薪酬制度;要繼續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繼續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避免超級經理人的蔓延;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使勞動收益大于資本收益。
[參考文獻]
[1]FINEDGOLD D, SOSKICE D. The failure of training in Britain: Analysis and prescription[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88 (3):21-53.
[2][4]SISSONS P. The local low skills equilibrium: Moving from concept to policy utility[J].Urban Studies,2021(58):1-18.
[3]BROWN P, GREEN A, LAUDER H.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4-52.
[5]AGGARWAL V. Skill formation systems and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 two counties:a case of Germany and United Kingdom[J].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mp; Management,2011(1):44-56.
[6]THEODORE W.SCHULTZ.Nobel Lecture: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88(4):639-951.
[7] (美)蘭德爾·柯林斯.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M].劉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26.
[8]INGRID ROBEYNS.Three models of education:rights, capabilities and human capital[J].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2006,4(1):69-84.
[9] BROWN R.The death of human capital?Its failed promise and how to renew it in an age of disrup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61.
[10]TAN E. Human Capital Theory:A Holistic Criticism[J].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14,84(3):411-445.
[11]黃庭康.批判教育社會學九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50.
[12]BERMAN.Implications of skill-b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evidenc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cs,1998,113(4):1245-1279.
[13]David Autor,Frank Levy amp; Richard J.Murnane.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an empirical explor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1279-1333.
[14](美)克勞迪婭·戈爾丁,勞倫斯·凱茲.教育和技術的競賽[M].陳竹津,徐黎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24.
[15] Harry Braverman.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8:294.
[16](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M].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04.
[17] BROWN R.The death of human capital?its failed promise and how to renew it in an age of disrup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66.
[18][19][20][21](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M].巴曙松,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21-322.
[22](瑞典)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技術陷阱[M].賀笑,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1:324.
[23](美)雷·馬歇爾,馬克·塔克.教育與國家財富:思考生存[M].顧建新,趙友華,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13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