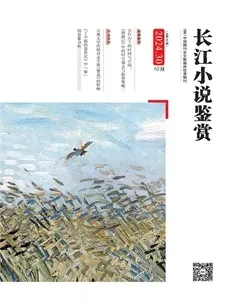沃爾夫岡·伊瑟爾文學虛構行為理論建構中的創造性接受研究
[摘" 要] 德國著名文藝理論家沃爾夫岡·伊瑟爾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了文學虛構行為理論。摒棄了在現實的視野下審視文學虛構、將其作為靜態概念界定的傳統,他將文學虛構視為一種“越界行為”。文學虛構通過選擇、融合與自我揭示行為完成對現實、語義與讀者經驗的越界,使文本世界成了漢斯·費英格所說的“仿佛世界”。文章從虛構行為理論內涵入手,分析并探討了伊瑟爾在理論建構時對費英格“仿佛”哲學的創造性接受問題,旨在為文藝理論界更為全面地了解伊瑟爾的文學理論體系提供新的啟示與參考。
[關鍵詞] 伊瑟爾" 文學虛構" 文本" 仿佛哲學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30-0090-04
文學作品一般被視為虛構之作,“虛構”這一術語便已暗示了書面語言絕非現實世界所給定的事物。傳統的理論常常將“虛構”視作現實的對立面,伊瑟爾摒棄了這一觀點,他直言文學若真的割裂了與現實之間的一切聯系,那么文學作品便是身處現實社會的人所讀不懂的天書。因此,他將虛構看作一種敘述與現實有關的某種東西的行為方式,并提出了文學虛構的越界行為理論,即文學虛構的選擇、融合與自我揭示行為。
一、文學虛構行為理論的內涵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觀,文學文本是作家對社會、歷史、文化等多重因素所作出的自由、自覺的選擇與加工。文學虛構的選擇行為意味著文本與現實之間的交叉點。“只要參照物是既定世界的組成部分,它們就可以被看作是現實本身”[1],保持其在原有體系當中的通用意義。同時,作家選擇出來的對象又脫離了原來的系統,在文本形式中獲得了新的意義與內涵,越過了原有體系的邊界。這在詩歌的表達中較為明顯,如“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在現實生活中,漁船上的燈火是我們所熟識的對象,但在張繼的詩中卻成了羈旅愁緒的象征,與我們所熟識的意義發生偏離,超越了其固有的內涵。那么,作家對多重參照系統的選擇必然會造成多重越界,被選擇的對象原本各從其類、自由自在,作家的選擇行為卻把它們組合到文本之中,使其變成了一種具體可感的事物,而未被選擇的因素則是水面之下的冰山,本文之“空白”,也將進入讀者的感知領域。如魯迅在談及典型化問題時曾提出“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魯迅創作時的多重選擇最終使許多個鮮明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他筆下的人物也常常令讀者感到熟悉,這大抵是由于被作家選擇的因素本身往往并不是虛構的產物,它來源于我們所熟識的現實世界,包含了一定的現實成分,但同時作家對參照系統進行了選擇加工,打破了參照系統的既定秩序,將它的某些成分從其原有的關聯體系中解放出來,被改造后的參照物跨過了原有系統的疆界,獲得了新的意義和內涵,使虛構與現實之間的界限變得曖昧而含糊。文學虛構的選擇行為只是作家虛構的開始,可以說作家最初從現實世界中選擇出來的是一堆雜亂無章、自相矛盾的因素,如何將這些因素組合成一個具有現實性、傾向性的整體才是作家需要把握的。伊瑟爾將這一過程稱為文學虛構的融合行為。融合的主要作用是使文本世界成為一個具有真實性的整體,這種真實性是在文本涉及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的。“融合,展開了一張無形的巨網,‘強不類為類’,使文本中的那些或造作或突兀的因素得以消弭或化解。”
文學虛構的融合也是一場跨越疆界的活動。喬納森·卡勒說:“文學作品總是在利用現存的符號,把它們組合起來,并不斷賦予它們新的意義。”[1]可見語言內部的融合現象造成詞句的多義性,如喬姆斯基創作的著名的句子“Colorless green sleep furiously”(透明的綠色思想喧鬧的沉睡著),讀者在閱讀時出于對句子穩定意義的期待,會不斷地將其置于各種假設之中,直至它獲得某種意義。意義總會受到個人傾向性與所處的社會文化的制約,而無論怎樣,最終誕生的意義早已與最初的詞語意義相去甚遠。總之,文學文本一方面通過對參照系統的選擇打破了現實的本來結構,另一方面通過對被選擇成分的重新組合,又在語義上重新界定了它們,賦予它們新的意義。
自我揭示是文學虛構的第三種行為。與說明性文本不同,文學文本中包含著大量標志其虛構特征的信號。英國語言哲學家J.L.奧斯汀稱文學文本是“表演性語詞”,它在外部世界找不到與之相對應的對象,因此它構成了一個在讀者眼中“仿佛”真實的世界。即使文本在極力宣稱它只是對現實世界的描繪而不等同于現實本身,但我們仍舊對眼前這個非真實的世界抱有無限熱情,因為我們總是渴望獲得更多的體驗,像弗蘭克·諾里斯所說:“就民眾而言,生活面極其狹窄……他們期待作家教他們超越自己的經驗范圍去理解生活。”[1]在閱讀中,接受者的現實經驗總是作為閱讀的背景而存在,而文本的意圖永遠不能與接受者的經驗相一致,因此虛構的自我揭示在讀者的經驗世界實現了越界。
伊瑟爾強調文學作品之所以把自身虛構的本相暴露在讀者面前,目的就是使讀者在閱讀活動中轉變其接受的態度,如羅蘭·巴特所說,文學中的真實注定只能是一種由文字制造的效應。讀者要了解文本揭露自身的意圖,才能在閱讀中引起恰當的反應,否則便會面臨掉入指稱幻象制造的陷阱中。閱讀時我們常常與書中人物同喜同悲,看恐怖電影時常常會恐懼尖叫,甚至劇場里會發生唾罵演員、開槍怒打“黃世仁”的情況。這在于我們的主體性自我變成了虛構故事的一部分,促使自己完全投入到了虛構的情節之中,好像那些虛構的場景完全是真實的一樣。在這一過程中,這個“虛構”也成了“真實世界”的組成部分,從而產生了不恰當的做法。因此,伊瑟爾認為讀者應該“懸置”自己的本真態度,將文本看作是“似是而非”的真實。這類似于沃爾頓將文學虛構視作一種“扮假作真的游戲”或是舍費爾所說的“共享的趣味假扮游戲”,文學文本雖有從參照系統選擇而來的現實成分,但是這些現實成分在進入文本后被虛構偽裝了起來,成了一種用假象包裝而成的真實,“以此表明它并非既有之物,而不過是被理解為一種既有之物而已。”[1]在閱讀活動中,我們需將文學世界當作仿佛的真實,這種身臨其境之感會使我們突破現實世界的桎梏,產生前所未有的審美體驗。如果在閱讀時產生的情感發自內心,那么我們就不會再固守從前持有的人生觀,這一過程中,我們將對文本世界的想象、閱讀時的情感轉化為自己經驗世界的新領域,從而達到重塑自我、完善自身的效果。
二、對漢斯·費英格“仿佛”哲學的接受
漢斯·費英格是一名德國哲學家,被譽為“虛構主義哲學理論之父”。1911年出版了虛構主義理論巨著《“仿佛”哲學——人類理論、實踐和宗教的虛構體系》,該書通過虛構理論在數學、物理學、心理學、經濟學、法理學等領域的實踐例證,說明其“仿佛”哲學的核心問題:所有關于所謂人類實現目標的說法都離不開虛構,評判虛構的唯一標準就是其效力或其實踐價值。
首先,費英格認為生活中諸如概念、理論等虛構都是人類心靈構造的事物,主要源自其實用價值。費英格從經驗主義的角度主張理解世界的愿望是荒唐的,因為所有的理解都是由對已知東西的事實上和想象的轉換構成的。因此,我們并不能絕對地了解客觀現實,而只能推斷客觀現實,在這一過程中,思維作為心靈的輔助工具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思維把現實生活所給定的感覺復合體闡述為有效的概念、一般的判斷和有力的結論,并創造出一個仿佛世界,使我們的行為可以成功地與感覺到的現象聯系起來。
其次,我們應把虛構當成一種輔助工具。虛構最為明顯的特征便是其偏離現實性,它說到底是一種主觀思維的產物,費英格認為“人類最大、最重要的錯誤都源于把思維過程當作現實本身的摹本”[1]。這種看法使得現實與虛構陷入了無止休的對比當中,因此他主張將虛構看作一種人類理解世界的手段,人們應將目光聚焦于其實踐價值。在以往的科學認識中,虛構常被人認為缺乏真實性,因此也被認為缺乏實用性,但從實踐的角度來看虛構往往會產生豐碩的成果。在數學中,推導某些公式時,需要諸如“0”、虛數、幾何形式等的虛構;在宗教中,有諸如上帝、不朽、再生等的虛構,通過這樣的虛構以便于去呈現更為復雜的現象,就像培根在談論這個問題時曾說“天體的某些運動是否僅僅是為了簡化我們的計算而被設想出來的”[1]。因此,整個思想世界的目標并不是描繪現實,而是為我們提供一種工具,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更容易地行走。因此虛構常常會在其失去效用后被忽略甚至被完全拋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虛構會被徹底否定,因為倘若沒有它們,分析與思考也就不能進行。
最后,人們在運用虛構的時候完全意識到了它的虛構性。在費英格看來,虛構是正當的,是一種“仿佛”的真實,從語法上來看,仿佛意指一個條件句,并且這個條件的陳述形式斷言了該條件是不真實和不可能的,它不與任何存在的現實相符合。“這一點保證了虛構的使用者不會錯把‘仿佛’當成‘如果’。”[1]只是將虛構當成完成自己實際目標的過程,在過程中賦予它“仿佛的真實性”。例如運用虛構的科學家們便是有意識地虛構,因此他們不會被虛構所誤導,更不會使科學變得主觀隨意。
伊瑟爾受費英格“仿佛”哲學的影響,提出了文學虛構的行為理論。他認為文學文本在歷經選擇、融合與自我揭示的越界行為后形成了一種“仿佛”結構,即費英格所說的那種“有意識的虛假性”作品。文學性虛構同費英格所說的一般性虛構一樣,都是大腦的結構,是心靈編織出的思想。無論作家編造的虛構作品多么完整精美、在外觀上多么具有真實感,說到底它并不存在于現實世界中,因為文本的參照系統歷經了多重越界才形成了最終的文學作品。“‘仿佛’這一語式的功能,正如費英格所說的,‘這一連詞連接的是一種假定的、不可能發生的情況’。虛構文本中的世界應被看作仿佛是真實的,這一句式說明,與文本相關的那些事情并不真實。”所以文本的真實是一種假象的真實,頗有一種畫餅充饑的意味,但同時這種虛構又是正當的,可以被冠以“實際的真實”,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確定的服務。那么這種“仿佛”結構何以達成呢?在這里作家的技巧便顯得尤為關鍵了,文學作品是通過虛構符號來演繹人生的悲歡離合的,一旦作家取消了這些虛構符號,那么仿佛結構也會隨之失效,文本便失去了供想象馳騁的空間,因此作家在創作活動中不必刻意去追求一種客觀的真實,文本也不可能做到涵蓋事物的所有含義。同樣,讀者應透過文本的虛構符號意識到文本的虛構性,從而將文本世界當成一個“仿佛如此”的世界,懸置起真實自我,將虛構作為一種理解世界、完善自身的工具。
三、對“仿佛”語式激活讀者想象的提出
虛構文本世界構成了一種“仿佛”語式,即文本世界并不是一個真正的世界,但是為了特別的目的又不得不被當作是一個真實世界。那么,讀者在閱讀時為了獲得精神上的平衡,便要發揮想象的作用。想象并不是一種能夠自我激活的現實力量,它必須借助外在力量才能夠得以展現,諸如柯勒律治所說的主體,薩特所說的意識,卡斯特里阿蒂斯所說的社會、歷史心理等。伊瑟爾認為在閱讀活動中,正是文本的“仿佛”語式激活了讀者的想象,他說:“如果虛構文本將其對現實的反映與那些‘不可能’的事情融合在一起,其結果必然是那些曾經看上去實實在在的東西變得捉摸不定了。這種難以捉摸的東西,就是我們所要的想象。”在這一過程中,讀者的想象力可以任意馳騁,且不受文本羈絆地進入文本世界中,這就是“仿佛”語式的重要作用。
伊瑟爾認為,讀者的想象活動賦予文本以“具體化”的空間。伊瑟爾用格式塔心理學“完形”術語來解釋這種在閱讀過程中的心理機制,阿恩海姆認為人的知覺具有構造能力,即在知覺對象的過程中將不完全變為完全的一種整合傾向。伊瑟爾受其影響,認為當文本將“空白”呈現給讀者的知覺時,讀者會不自覺地將其恢復到“完形”狀態。上文我們提到,虛構文本在歷經選擇、融合和自我揭示過程中經歷了多重越界,使文本中殘存的現實變得面目全非,文本變成了費英格所說的“仿佛”結構,這種“仿佛”結構引起讀者對其進行想象填充,使其成為讀者腦中具有穩定性的對象,在格式塔形成時,預期的想象也會在讀者的意識中生動具體地呈現。
讀者的想象活動受其經驗和實用主義態度的影響。薩特認為,作家在文本中運用語言設置了一個個路標,然而將路標連接起來向前走去的卻是讀者。“讀者的想象,通常與自己熟悉的經驗聯系在一起,不過,想象也常有與既有經驗相抵牾的時候。這時,想象就形成了一種對熟知事實越界的經驗。”既是讀者的原有經驗,也是在閱讀過程中由“仿佛”語式結構改造過經由想象賦予形式的新經驗。因此,讀者對文本對象以及意義的想象始終隨著越界行為處于一種動態的建構之中,說隨著閱讀過程中自身經驗的增加而發生改變。
四、結語
在閱讀想象過程中,讀者會不斷對現有經驗進行越界以充實自身,這也就是作品與讀者主體心理經驗的交融過程。同時,這種想象活動還受到讀者實用主義態度的影響。費英格認為,當人們將現有之物與想象相比附時,絕不只是因為對一個空洞的智力游戲感興趣,而更多是出于某種實用性目的。對于文學想象而言,探尋意義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沖動,許多強加于文本的意義,實際上是人們以實用主義態度對待想象的結果。
參考文獻
[1] 沃爾夫岡·伊瑟爾.虛構與想象——文學人類學疆界[M].陳定家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5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