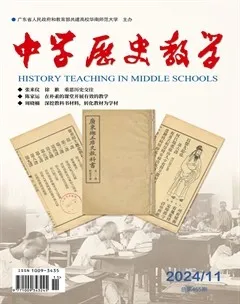用好“學思之窗”欄目的策略
摘 要:統編版高中歷史教科書所設置的“學思之窗”欄目,對提升學生的歷史學科核心素養具有重要意義。該欄目呈現多則敘事各異的史料,教師可以巧用沖突史料來創設學術情境,善用史源信息來探究歷史原因,妙用互證方法來評估史料價值等。深度研習“學思之窗”史料,能夠充分發揮教科書功能性欄目的價值。
關鍵詞:學思之窗 史料研習 啟繼位 歷史敘事
為提升學生歷史核心素養,高中歷史教科書設功能性欄目,其中“學思之窗”為關鍵欄目,一般可分兩類:一類是呈現多則敘事互相補充的史料,另一類則是呈現多則敘事各異的史料。其中后者更具挑戰性,因反映史學家對事件的不同解釋,提供了學生探究的空間。以《中外歷史綱要(上)》第一課為例,該欄目先展示《史記》與《戰國策》對啟繼位的不同敘述,提出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原因。筆者將探討此類“學思之窗”的教學策略,旨在引導學生深度研習史料,洞察不同敘事背后的原因。
一、巧用沖突史料,創設學術情境
歷史教學情境一般有學習情境、生活情境、社會情境和學術情境四種類型。該“學思之窗”呈現《史記》與《戰國策》對啟繼位方式的不同敘事,就是典型的學術情境,有助于引導學生像歷史學家一樣思考,發展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夯實歷史學科核心素養。深挖該“學思之窗”的第一個策略,就是巧用教材中有關啟繼位方式的沖突性史料敘事,然后通過問題創設學術情境,激發學術探究興趣。
材料一:益(禹晚年培養的接班人)讓帝禹之子啟。
——《史記·夏本紀》
材料二: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
——《戰國策·燕策一》
問題:材料一和材料二的內容有何不同?
通過提取和比較材料信息,學生會發現史書中對啟繼位方式的敘事是不同的。《史記》中記載啟的繼位是和平禪讓的結果,而《戰國策》中記載啟是通過暴力手段奪權繼位的,從而達到歷史解釋水平3,能夠分辨不同的歷史解釋。[1] 這類觀點沖突的史料,不僅能使學生認識到歷史記載的復雜性,而且還能激發學生的問題意識。學生會對史料產生疑問:關于啟的繼位方式,為什么會有不同的敘事說法?哪種敘事更可信?而這兩個自然生成的問題便是本次研習活動需要探究的核心問題。
二、善用史源信息,探究歷史原因
所有歷史敘事“在本質上都是對歷史的解釋,即便是對基本事實的陳述也包含了陳述者的主觀認識。”[2]除了主觀認識,作者的史料掌握情況與所處的時代背景等客觀因素也會影響歷史解釋。深挖該“學思之窗”的第二個策略,就是引導學生探究史源。史源是指史料的來源,包含作者身份、創作目的與背景等內容。通過探究史源,學生既可以了解影響歷史解釋的多方因素,又可以明辨史料的真偽。最重要的是,在探究史源過程中,學生批判質疑史料,并對史料作者的主觀意圖和所處時代進行合理想象與代入,從而提升史料實證和歷史解釋素養。
材料三: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后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
——《漢書·太史公傳》
問題一:《史記》的作者是誰?
問題二:作者在撰寫《史記》時參考了哪些史料?
問題三:司馬遷對有關啟繼位史料的掌握情況是否會影響他對該事件的記載?
問題一、二、三旨在引導學生探究作者的身份和史料掌握情況,以及作者的史料掌握情況是否會影響他對該事件的記載,從而“明了史料在歷史敘述中的基礎作用”[3],達到史料實證水平2的要求。
上一環節學生已經意識到史書作者的史料掌握情況會影響到歷史敘述,教師可以繼續補充史料,并設置問題鏈,引導學生探究史料作者的主觀立場是否也會影響他對歷史的解釋。
材料四:(鹿毛壽)或曰:“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
——《戰國策·燕策一》
材料五:(鹿毛壽)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
材料六: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史記·夏本紀》
材料七: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于民未久。
——《孟子·萬章(上)》
問題四:關于啟的繼位,司馬遷掌握了哪些史料?
問題五:司馬遷個人更傾向于哪則史料的觀點?
問題六:作者的主觀傾向是否會影響他的歷史敘事?
問題四承接上一環節,引導學生了解司馬遷對啟繼位相關史料的掌握情況。通過比對四則材料的出處和內容,學生可以發現:對啟繼位方式的敘事,《史記·燕召公世家》與《戰國策·燕策一》十分相似,《孟子·萬章》與《史記·夏本紀》十分相似,可見司馬遷掌握了《孟子》和《戰國策》等史料。問題五和六旨在引導學生深入歷史情境,體會司馬遷面臨的抉擇問題,從而理解抉擇的背后反映了他個人的主觀傾向。《史記·夏本紀》中對啟繼位方式的敘事記載是參考《孟子》中的史料,可見司馬遷傾向于《孟子》中的觀點,從而使學生認識到史料作者的主觀傾向也會影響他的歷史敘事,從而達到歷史解釋水平3的部分要求,即“嘗試從來源、性質和目的等多方面,說明導致這些不同解釋的原因并加以評析。”[4]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說明歷史不是純粹客觀的知識,人們對它的理解,往往因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階級立場和不同的歷史觀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5]時代思潮也會影響史料作者對歷史事件的敘述。為此,教師需要繼續追問,引導學生探究司馬遷最終選擇《孟子·萬章》作為史料依據的原因。
問題七:孟子是什么學派的代表人物?
問題八:在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儒家思想的發展狀況如何?
問題九:司馬遷選擇《孟子》中的史料,是否是因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問題七、八、九旨在引導學生關注司馬遷創作《史記》的時代背景,以及時代背景是否會對他的歷史敘事產生影響。學生在問題的引導下,可以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司馬遷在記載啟的繼位時,可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其歷史敘事選擇了儒家經典《孟子》作為依據。至此,學生“能夠選擇、組織和運用相關材料并使用相關歷史術語,對個別或系列史事提出自己的解釋”[6],并認識到時代背景也會影響史料作者的歷史敘事,從而達到歷史解釋水平2的要求。
三、妙用互證方法,評估史料價值
按照上述探究環節,基本上完成“關于啟的繼位,為什么會出現上述不同說法”的探究任務。根據前面的史源探究,可知:《史記》對啟繼位這一事件的歷史敘事是參考《孟子》中的史料,而《孟子》和《戰國策》都是戰國時期的文獻史料,距離啟所處的夏朝早期時間較遠,因此二者都只是二手史料。所以,還可以繼續深入挖掘該欄目,引導學術探究“關于啟的繼位方式,史書中的兩種說法誰更可信”,該問題實質是評估兩則史料的價值。
由于從史源角度已無法辨明真偽,故要運用史料互證的方法,引導學生通過閱讀先前呈現的史料,辨析史書中的兩種歷史敘事的真偽。然而,目前學術界還未發現可以確證啟繼位方式的考古資料。借此契機,可以培養學生的存疑意識,使學生意識到在人類歷史中還存在許多尚未確證的歷史問題,而對于此類尚未可證的問題,我們應該保持存疑的態度和繼續探究的動力。
史料互證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史料實證水平3明確要求學生“能夠利用不同類型史料,對所探究的問題進行互證,形成對該問題更全面、豐富的解釋。”[7]區分史料類型是史料互證的前提,并且史料的類型也會影響史料的可信度。因此在尋找其他類型史料進行互證之前,學生需要先學會區分史料類型及價值。具體的問題設計如下:
問題十: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別是什么類型的史料?
問題十一:該類型的史料有什么價值?
問題十二:對于研究啟的繼位,《史記》和《戰國策》是一手史料還是二手史料?
問題十三:如果研究戰國歷史,《戰國策》可信嗎?
為了使學生達到史料實證水平2的部分要求,即“能夠認識不同類型的史料所具有的不同價值”[8],教師依次提出問題十和十一,引導學生區分《史記》和《戰國策》的史料類型與價值并掌握區分依據。通過分析史源,學生可知:從史料載體來看,《史記》和《戰國策》都是文獻史料,文獻史料的價值在于歷史信息豐富,便于理解。問題十二、十三旨在引導學生認識到史料的真偽與價值具有相對性。從研究對象來看,如果研究啟的繼位方式,《史記》和《戰國策》都是二手史料,因為二者都不是夏朝的原始史料;如果研究戰國歷史,《戰國策》中的史料更為可信。最后學生會意識到:從史料來源來看,由于兩本史書都是二手史料,無法判斷哪本史書中的歷史敘事更可信。
承接上一環節,由于無法從史料來源的角度辨別兩本史書中歷史敘事的真偽,教師可以繼續追問,并向學生介紹史料互證的辨偽方法。
問題十四:想要辨別關于啟繼位兩種說法誰更可信,還需要什么史料來佐證?
問題十五:如果沒有夏朝的考古資料佐證,我們該如何處理這種有爭議的史料?
問題十六:教材中是如何敘述啟的繼位方式?
問題十四的提出,旨在引導學生嘗試“利用不同類型史料,對所探究的問題進行互證”[9],指向史料實證水平3。教師需要指出學生回答的史料類型的優勢和不足,并點明用來佐證的史料必須真實可信。問題十五明確告訴學生關于啟的繼位方式,學術界還未發現與之相關的夏朝考古資料。然后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處理這種既有爭議又沒可信史料支撐的說法。問題十六是給學生的提示。通過查閱教材,學生會發現:教材只提及“禹死后,其子啟繼位,世襲制代替了禪讓制”[10],對啟的繼位方式做了回避性敘事。借此契機,教師引導學生:對于有爭議的史料與敘事,沒有可信的史料佐證,我們須保持存疑的態度,不能主觀臆斷,妄下結論。
在深入推進歷史課程改革、全面提升學生核心素養的背景下,教科書中功能性欄目的價值愈發凸顯。通過深入挖掘“學思之窗”欄目,我們能夠有效地開展史料研習教學,激發學生的探究興趣,提升他們的歷史敘事能力、歷史解釋素養和存疑意識。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教師應充分重視教科書中的功能性欄目,發揮其獨特的教學價值。
【注釋】
[1][2][3][4][6][7][8][9]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71、5、71、71、71、71、71、71頁。
[5]趙家祥主編:《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第1卷歷史過程論和歷史動力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頁。
[10]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外歷史綱要》(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