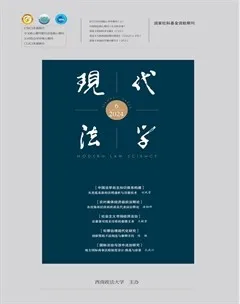民事證據收集制度之體系化
摘 要:現行書證提出命令制度與律師調查令、法官調查取證、證據保全等制度疊床架屋的局面造成了體系性混亂。混亂的根源可從外部體系和內部體系兩方面解釋。在外部體系,書證提出命令及其變種律師調查令制度采大陸法系的“當事人收集/法官指揮”模式,法官調查取證制度及證據保全制度則采“當事人收集/法官收集”模式,二者都是整體性的證據收集制度解決方案,功能相同而互相排斥。就內部體系,兩種模式背后的原則分別為“司法主導”和“司法替代”,這二者之間也很難通約。為實現證據收集制度的體系化,應采“司法主導原則”及“當事人收集/法官指揮”模式,具體路徑包括擴張文書提出命令制度、充實證據保全制度和增設法官職權命令取證制度。
關鍵詞:證據收集;書證提出命令;體系化
中圖分類號:DF72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4.06.03
在民事訴訟法的總體框架中,證據收集制度無疑占據著特別重要的地位。以它為依托,當事人方能從對方當事人或案外人處獲取對自己有利的證據,避免證據偏在的不利影響。而法院對案件真相的發現主要取決于雙方當事人的舉證,因此證據收集制度的規則配置和運轉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實體正義能否實現。而在學理上,如何配置證據收集制度中的法官權力與當事人權利,關涉到當事人主義(辯論主義)與職權主義之分野,與訴訟模式這一民事訴訟核心議題密切相關。但就這一重要議題,我國《民事訴訟法》長期以來卻處于“供給不足”的狀態,只有證據保全和法官調查取證這兩個正式的下位制度。而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對證據收集卻存在著強烈需求,由此另外兩個下位制度應運而生,其一是試點多年但尚未“轉正”的律師調查令制度①,目前已基本在全國范圍內鋪開;其二是書證提出命令制度,規定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5〕5號,法釋〔2020〕20號修訂,以下簡稱“《民訴法解釋》”)第122、123條。最高人民法院對后者寄予厚望,在2020年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19〕19號,以下簡稱“2020《證據規定》”)中對其作了大幅度擴充,書證提出命令由此從一種非常原則且幾乎不可用的狀態轉變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狀態。四種下位制度并存,共同構成了我國證據收集制度的整體框架。【本文所謂的“證據收集”,主要指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向對方當事人及案外人主動收集不屬于本方掌控的證據,在不那么嚴格的意義上等同于“取證”,因此證據交換制度不在本文的探討范圍之內。】但四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卻罕有人論及。任何法律制度的構建或完善,除了需要考慮功能上實現諸如發現真相、提升訴訟效率等目標外,更要考慮它在體系上是否能與其他制度耦合,避免出現規則間的重復、沖突或漏洞,以及規則與法律原則或法理念之間的抵牾。正如有學者所指出,如果不能從體系化的角度考慮,則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就只能是“碎片化”的,僅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張衛平:《民事訴訟法法典化的意義》,載《東方法學》2022年第5期,第94頁。】德國學者卡納里斯也指出,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所謂法的體系——法秩序的評價一致性和內在統一性——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只要將法學作為科學來從事研究就必然如此追求。【[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學中的體系思維與體系概念:以德國私法為例》(第2版),陳大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6頁。】這種體系化所帶來的體系效益主要包括:最大限度覆蓋社會生活、確保法的安定性、消除體系內部的邏輯矛盾、降低找法和法學教育成本。【參見謝鴻飛:《民法典的外部體系效益及其擴張》,載《環球法律評論》2018年第2期,第31-34頁。】有鑒于此,筆者擬以卡納里斯的體系理論為方法,從上述四種證據收集制度在體系上的漏洞入手,反思證據收集制度的內部體系和外部體系并進而思考如何推進其體系化。【鑒于學界通說認為,證據收集主要為當事人的職責和權利,因此除非特別指明,本文所論及的證據收集的主體僅限于當事人而非法官。同時,鑒于證據收集制度原則上針對的是實物類證據,若無特別指明,本文對證據收集的討論一般限于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的收集。】
一、證據收集制度的體系性難題
2020《證據規定》新增了書證提出命令的申請程序(第45條)、審查程序(第46條)、文書范圍(第47條)、制裁程序(第48條)以及擴張適用的規定(第99條)。這種變化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可以期待它不僅能部分緩解司法實務中普遍存在的“取證難”現象,而且也有助于對案件真相的發現。即便經過擴充,現行書證提出命令依然是被嚴格限制的:原則上應當以實體法上的文書提出請求權為依據,引用文書、利益文書和法律關系文書為義務文書。【參見張衛平:《當事人文書提出義務的制度建構》,載《法學家》2017年第3期,第33頁。】但悖謬的是,即便是適用范圍如此狹窄的書證提出命令,當它與律師調查令、法官調查取證、證據保全并存時,也會帶來體系上的兼容問題。
(一)現行證據收集制度之間的沖突
首先,四種功能相似的制度并存,會引發適用者的找法困難,導致“降低找法和法學教育成本”的體系效益難以實現。當事人如果想取得掌握在對方當事人手中的書證,那么書證提出命令、法院依申請取證、民事調查令和證據保全這四種制度幾乎都可利用。這對于想獲取證據的一方可謂是“幸福的煩惱”,但他需要仔細分辨這幾種制度之間的差別,才能確定自己到底有權啟動哪一種。例如調查令往往只有律師才能申請和持令調查,當事人本人并無這種權限,其他幾種制度則無此限制。而如果證據掌握在案外人手中或者證據并非書證而是物證,則書證提出命令就無法啟動,但其他幾種制度并無此限制。證據保全制度則以“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情況”為前提,其他幾種制度并無此限制。而諸如啟動方式、救濟方式、相對人的義務、程序效果等問題,四種制度盡管存在不少相似性,但也存在差別。除規范層面的差異外,四種制度在實務中的運作情況也不盡相同,由此適用者在找法時還需要考慮到實務中法院的態度。例如,四種制度中盡管法官調查取證制度在申請主體(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申請客體(包括當事人和案外人)、證據范圍(包括幾乎所有證據種類)方面最為寬泛,但其啟動卻往往是最為困難的。其原因在于,這種制度要求法官親自實地取證,這在案多人少和法官員額制的當下難以受到法官的歡迎。與之情況相似的還有證據保全制度和書證提出命令,它們在很多法院也幾乎被束之高閣,而律師調查令在實務中往往最受法官青睞。
其次,是幾種制度之間的內部矛盾,由此“消除體系內部的邏輯矛盾”的體系效益難以達成。例如,就律師調查令與法官依申請調查取證而言,兩者的前提性構成要件基本都可以概括為“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無法收集證據”,但其法律后果卻分別指向律師收集和法官收集。嚴格來說,這種看似沖突的情形不構成沖突漏洞,因為這種漏洞要求“兩個規范彼此矛盾,且無法通過解釋,尤其是借助于特別法、新法等規則確定其中何者具有優先性”。【[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律漏洞的確定:法官在法律外續造法之前提與界限的方法論研究》(第2版),楊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9頁。】而顯然這兩種法律后果在現行法上都是成立的。但借助訴訟經濟原則這一普遍的法原則考量,同時允許律師收集和法官收集的做法顯然不夠經濟。因此,這種情形依然構成了卡納里斯所謂的“原則漏洞”。【[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律漏洞的確定:法官在法律外續造法之前提與界限的方法論研究》(第2版),楊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24頁。】為填補這種漏洞,某些省份直接將律師調查令和法官依申請調查取證制度合二為一,當事人申請法官調查取證時法院直接簽發律師調查令,而后由律師持令收集證據。【2019年江蘇省16部委出臺的《關于依法保障律師調查取證權的若干規定》第9條即如此規定。】但這種規則的“縫合”卻存在嚴重的違法風險。法官依申請取證是我國《民事訴訟法》所確定的制度,當事人及律師當然依法享有申請法官取證的權利,這種法定權利不能因為地方出臺的某種地方性法規、規章或者政策就被剝奪。根據《立法法》第88條及第96條,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超越權限和違反上位法的地方性法規及規章,應當被依法予以改變或者撤銷。而地方出臺的關于律師調查令的規則本身連規章的效力都不如。【例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在執行程序中使用調查令的若干規定(試行)》(2004年)、《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調查令實施辦法(試行)》(2015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立案審查階段適用調查令的意見》(2014年)都只是由當地高院出臺的規范性文件。】
最后,是四種制度重復適用的風險,導致“確保法的安定性”的體系效益難以完成。法的安定性要求實現法的確定性和可預期性,從而增強社會的穩定性。鑒于這四種制度的適用都是“有法可依”,當事人如果啟動其中一種制度未取得期待效果時,他完全有可能再嘗試其他制度。假設某原告試圖取得在被告處留存的公司財務賬簿,原告依照《民事訴訟法》第64條申請法院調查收集但被法院拒絕,其后可根據2020《證據規定》第45條申請書證提出命令,如果被拒絕后還可向法院提出律師調查令申請或者證據保全申請。盡管在司法實務中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一般不至于基于這四種制度連續提起多個申請,但如果他試圖窮盡這四種證據收集方法,那么法官似乎也只有聽之任之。這種重復適用的可能性,實際上也構成了原則漏洞:一方面,它違反了程序的安定性原則,因為一方當事人申請適用A取證制度失敗后申請適用B取證制度,就相當于在否認A取證制度的法律效果,這會造成對方當事人和法官無法形成恰當的預期;另一方面,它也違反了訴訟經濟原則,因為針對同樣的問題進行反復解決是對司法資源的不當耗費。
(二)現行證據收集制度的缺漏
集四種制度之力,能不能恰當解決我國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證據偏在問題?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要解決證據偏在問題,就需要在制度設計上盡量減少疏漏,防止出現當事人取證困難而證據制度卻對此無能為力的情形——體系效益中的“最大限度覆蓋社會生活”。但現有的四種制度即便交織起來,所形成的“網”也是相當稀疏的,“漏網之魚”并不難找。這種區別于個別規范的不圓滿,而是“依根本的規整意向,應予規整的問題欠缺適當的規則【[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51頁。】”的現象,即所謂“規整漏洞”。基于真實發現原則,“對于當事人具有爭議的事實,應當盡量基于最大限度的證據的基礎上,作出最大限度接近真實的事實認定……如此為了發現真實的需要,對于有爭議的案件事實,賦予當事人與裁判所最大限度地發現真實的手段也是民事訴訟法的基本理念【[日]伊藤真:《民事訴訟法》(第4版補訂版),曹云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頁。】”。由此,這種證據收集領域的規整漏洞,也構成了基于真實發現原則所確定的“原則漏洞”。在證據收集領域,這種漏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是訴前階段的規整漏洞,當事人缺乏在起訴前有效收集證據的必要手段。我國民訴法上僅有訴前證據保全制度可供訴前收集證據,這與比較法上五花八門的證據開示、當事人照會、囑托調查、起訴前的證據收集處分等制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而且訴前證據保全的適用有著嚴格的前提要件(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法官也往往因為案件繁多而不愿意啟動這一程序,以至于該程序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非常罕見。【通過檢索無訟案例(https://www.itslaw.com/home)(檢索日期為2022年2月6日),以“證據保全”為關鍵詞只能得到61份裁判文書,以“訴前證據保全”為關鍵詞僅能得到3份裁判文書。在筆者的調研中,有法官表示,十年的法官生涯中僅做過一次證據保全,從未做過訴前證據保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往往只有通過公證保全證據這種方式和公證員一道偷偷摸摸地去現場取證。【這種做法被稱為“隱名公證”“匿名取證”,參見薛凡主編:《司法視野中的公證保全證據》,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頁。】其二是在訴訟階段的規整漏洞,法官缺乏發現案件真相所必須的證據收集手段。司法實踐中常常發生的情形是: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由于法律素養的缺乏或其他原因并未提出任何一種取證申請,但案件的解明度又明顯不足,且案件不屬于法官可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的類型。此時法官即便明知某方當事人或第三方掌握本案的關鍵證據,但在制度上幾乎沒有獲取該證據的恰當手段。理論上法官可以通過向當事人釋明,告知其可以向法院申請書證提出命令或律師調查令或申請法院調查取證。這種釋明可以稱之為“證據申請的釋明”,但它也存在嚴重的合法性障礙:現行法上即便是關于法律觀點的釋明都遮遮掩掩,遑論關于證據或者證明的釋明。【相關批評,參見熊躍敏:《從變更訴訟請求的釋明到法律觀點的釋明——新〈民事證據規定〉第53條的法解釋學分析》,載《現代法學》2021年第3期,第178-180頁。】而且,很多法官往往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會通過釋明去告知當事人可提出相關申請,因為這種告知可能引發另一方當事人提出“偏袒對方”的質疑或投訴。由此,在這種證據偏在情形下,法官往往只能依靠作為最后手段的證明責任進行裁判,這無疑存在嚴重的實體誤判的風險。而如果是非常有責任心的法官想去查清楚事實,他就必須冒著“非法取證”的風險,通過職權調查取證去解決證據偏在難題。
如卡納里斯所言,任何法規范都難以避免產生體系斷裂與體系漏洞,而后者更為常見。【[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學中的體系思維與體系概念:以德國私法為例》(第2版),陳大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137頁。】上述證據收集制度中的法律漏洞,均可以歸入體系漏洞,也即,通過法律原則(如訴訟經濟原則)去評價法規范而發現的與體系思維(內在統一性和一致性)無法協調的矛盾和不足。現有四種取證制度中存在的這些體系漏洞,當然可以通過對法規范的漏洞填補予以解決,例如確定四種制度不同的啟動要件從而避免制度的重復使用,并針對四種制度都無法涵蓋的情形例外地允許法院職權收集證據。但如果這樣,我們的取證制度將會變得越來越復雜,但即便如此復雜也很難保證再不會出現新的漏洞。借用現在流行的表達,我國的取證制度已經嚴重“內卷化(involution)”:制度越來越細密但其邊際效應遞減,整體制度并未躍升到更高的層級。【黃宗智首次在社科領域使用“內卷化”一詞,指土地越來越精耕細作但是邊際效應遞減,整體農業生產并沒有上升到更高的層級。參見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5頁。】
二、對證據收集制度的體系性反思
與內卷化相對立的是革新(renovation),這種革新不能基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直覺主義或經驗主義,而應當建立在對原有制度深層次的體系性反思的基礎之上。正如卡納里斯所言:“體系不外乎意味著一種嘗試,即通過運用理性的手段,把握和展現某一特定實質領域的統一性和秩序。”【[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律漏洞的確定:法官在法律外續造法之前提與界限的方法論研究》(第2版),楊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0頁。】而所謂的法律的統一性或者秩序無外乎法律的外部體系(成文法的概念、規則等法律素材所構成的秩序)和內部體系(一般法律原則的價值論或目的論秩序)。【[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學中的體系思維與體系概念:以德國私法為例》(第2版),陳大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13-45頁。】由此,這種體系性反思可以從外部體系和內部體系兩方面著手。
(一)基于外部體系的反思
外部體系的構造是由對法律素材進行盡可能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展示和排列這一追求來確定的。【[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學中的體系思維與體系概念:以德國私法為例》(第2版),陳大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13頁。】而要從總體上對我國傳統的證據收集制度的“一致性”予以描述,筆者嘗試將這種制度的規則組織形式概括為“當事人收集/法院收集”模式。有學者曾指出,我國證據制度中存在“當事人提供證據與法院調查取證相結合的方針”。【李浩:《民事訴訟法學》(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頁。】其原因在于:“民事訴訟制度的性質決定了證據的收集應當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由當事人收集和提供,其次是法院在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提出申請后進行調查收集,最后才是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李浩:《回歸民事訴訟法——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的再改革》,載《法學家》2011年第3期,第129頁。】而在規范層面,前者的體現是《民事訴訟法》第67、132、211等條文及相關司法解釋,后者的體現是《民事訴訟法》第52條、64條等條文及相關司法解釋。簡言之,在證據收集問題上,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范和學理是一致的:要么是由法院收集證據,要么是由當事人收集證據。
回顧我國40年來的證據制度,它總是在當事人收集還是法官收集之間搖擺不定。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采取的是當事人提供證據和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相結合的原則。1992年《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3條對法官可以調查取證的情形作了細化規定,似乎是有意限制。其后1998年《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也基本沿襲了前述立場。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2002《證據規定》”)則采取了較為激進的限制立場,將法官職權調查取證限制在公益性和程序性事項。但這種限制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面都遭遇不少問題,由此2015年《民訴法解釋》對法官調查取證權又采擴張立場。總體而言,無論證據制度如何變遷,它要么偏向“當事人收集”要么偏向“法官收集”,相應的規則總是無法擺脫“當事人收集/法院收集”模式。
而與中國法不同的是,大陸法系在證據收集的外部體系上基本采“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模式,即當事人負責收集證據并將這些證據提交到法庭,法院不承擔收集證據的具體工作但可以通過命令的方式要求證據源(當事人或者案外人)提出相關的實物證據,或者通過命令啟動詢問或者鑒定等方式來提出相關的“人證”【在德日證據法中,當事人本身就是一種證據方法。參見段文波:《〈民事訴訟法〉修改應當關注作為證據的當事人》,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第112頁。】,從而使得相關的證據方法能夠進入法庭。【參見[德]漢斯-約阿希姆·穆澤拉克:《德國民事訴訟法基礎教程》,周翠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頁。】這種命令一般是基于當事人的申請而作出(例如根據當事人申請而啟動鑒定),但在懷疑可能違反真實義務(Wahrheitspflicht)時法院也可依職權作出這種命令(如職權命令鑒定)。【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ZPR,16.Aufl.,2004,§10Rn.30.】
德日法上主要由當事人收集證據并向法院提出證據(也即提出證據調查申請)。當當事人并未掌握某證據時,就需要法院的公權力介入,這一點德日和我國并無區別。但與我國法官直接向證據源為證據收集活動的做法相區別,德日法官并無權力但可以作出相應的命令,這種命令一般是基于當事人的申請而作出,例外情形下也可以由法官依職權作出。由此,法官命令就成為解決當事人取證能力不足或者證據偏在問題的最關鍵手段。該命令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針對“人”這種證據方法(當事人、鑒定人、證人)的命令,如詢問當事人及啟動鑒定;一種是針對書證或者物證這類實物證據方法的文書提出命令或者勘驗物提出命令。【參見[德]漢斯-約阿希姆·穆澤拉克:《德國民事訴訟法基礎教程》,周翠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265頁。】準確地說,除證人外的其他證據方法(當事人、鑒定人、文書、勘驗物)均允許法院依職權啟動證據調查。日本法與德國法類似,差別之處在于:(1)采一般化文書提出義務,對任何文書都可啟動文書提出命令程序【參見[日]伊藤真:《民事訴訟法》(第4版補訂版),曹云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89頁。】;(2)弱化了法官職權,法官無權依職權啟動文書提出命令,除非家事非訟領域。【參見郝振江、趙秀舉譯:《德日家事事件與非訟事件程序法典》,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99頁。】通過這種法院指揮提出證據/啟動詢問或委托,德日法官可將相關的證據方法(人或者物)匯集到法庭,從而啟動證據調查來得到相應的證據資料,并以此作為裁判基礎。
通過比較不難發現,在理論上,“當事人收集/法院收集”及“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這兩種模式都可以成功地將當事人掌控之外的證據匯集到法庭從而解決證明困難問題。就取證制度而言,這兩種模式解決的是各種主體之間的基本權限劃分問題。而其他的諸如“文書提出義務”“勘驗容忍義務”“證人義務”“鑒定人義務”等,都是這個模式的下位規則。易言之,盡管手段存在差異,但兩種模式在解決證明困難的功能上幾乎等值,由此存在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同時,由于對于“什么是證據”“什么是證據調查”等外部體系中的基本概念的理解存在巨大差異【參見袁中華:《論民事訴訟中的法官調查取證權》,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5期,第188頁。】,兩種模式在某種意義上又存在“不可通約性”,選擇其一必然排斥其二。我國法上法官調查取證和證據保全制度屬“當事人收集/法院收集”模式,而書證提出命令及律師調查令則屬“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模式。由此,就不難理解法官依申請取證、證據保全制度與書證提出命令/律師調查令制度之間為什么互相排斥而難以兼容甚至是互相替代——這兩類制度的外部體系存在根本性差異。
(二)基于內部體系的反思
法律的內部體系由反映法律基礎評價(目的論或價值論)的一般法律原則所組成。【參見[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學中的體系思維與體系概念:以德國私法為例》(第2版),陳大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44-45頁。】而在證據收集領域,大陸法系和我國法分別采用了不同法律原則。在歐洲大陸法律傳統之下,司法機關在證據收集問題上的理念可稱之為“司法主導”原則,即在民事訴訟中法院壟斷證據調查的權限,并拒絕承認當事人有直接要求對方當事人或案外人提供證據的權利。傳統上,正確地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在大陸法系中被認為是司法的功能與責任的核心。由此,法院的實質意義的訴訟領導(指揮)要求對證據調查程序的緊密控制【參見[德]羅森貝克、施瓦布、戈特瓦爾德:《德國民事訴訟法》(上),李大雪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43頁;[德]羅爾夫·施蒂爾納:《當事人主導與法官權限——辯論主義與效率沖突中的訴訟指標與實質闡明》,周翠譯,載《清華法學》2011年第2期,第134頁。】,而且這種對證據調查的控制當然不能轉授予私人行使。要求持有證據的人提出該證據是一項由司法官僚所行使的國家權力,而居于私人地位的當事人則不享有該權力。由此可見,作為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之一的(法院)訴訟指揮原則構成了對司法主導原則的理論支撐。同時,修正辯論主義也賦予了法院職權提出證據方法的權限【參見[德]羅森貝克、施瓦布、戈特瓦爾德:《德國民事訴訟法》(上),李大雪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頁。】,構成了對司法主導原則的支撐。簡言之,司法主導原則與訴訟指揮原則、修正辯論主義這二者構成了下位原則和上位原則的關系,也即,前者是后者在證據收集領域的具體體現。在司法主導原則之下,德日法官可以依職權或者依申請啟動證據調查,從而命令證據源提出證據,破解證明困難問題。書證提出命令制度就是這種原則在制度層面的典型體現,而作為書證提出命令“小改款”的律師調查令無疑也體現了這種原則。
而與上述原則不同的是,中國法在證據收集問題上采取的傳統原則可以被稱為“司法替代”。法官可以直接替代當事人,并像當事人一樣到現場收集證據,這被稱為法官的調查取證權的行使。這種做法無論是與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相比都存在明顯差異。有學者將這種做法稱之為“收集調查證據法院一手包攬”,并將其視為“超職權主義”訴訟方式(模式)的體現。【王韶華:《試析民事訴訟中超職權主義現象》,載《中外法學》1991年第2期,第18頁。】超職權主義盡管被稱之為訴訟方式或訴訟模式,但究其實質就是法律原則。這種原則與司法替代原則之間,同樣構成了上位的一般法原則和具體的證據收集領域的下位原則的關系。
司法替代原則主要來源于我們自身的法律傳統。中國法律傳統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以清代民事審判為代表的帝制中國法律傳統這種舊傳統,其二是自革命根據地時期發展起來的民事審判方式這一新傳統。【參見王亞新:《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頁。】在舊傳統中,作為裁判者的州縣官的權力在司法中幾乎是不受限制的。如瞿同祖所言:“州縣官聽理其轄區內所有的案件,既有民事也有刑事。他不只是一個審判者。他不僅主持庭審和作出判決,還主持調查并且訊問和偵察罪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他的職責包括法官、檢察官、警長、驗尸官的職務。這包括了最廣義的與司法相關的一切事務,未能依法執行這些職務將引起(正如許多法律法規所規定的)懲戒和處罰。”【瞿同祖:《瞿同祖法學論著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頁。】而在新傳統中,擯棄蘇聯式的坐堂辦案作風,深入田間地頭調查取證是馬錫五審判方式的核心。【參見袁中華:《論民事訴訟中的法官調查取證權》,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5期,第193頁。】如果說舊傳統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法院和一般人的認識或意識,那么新傳統則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融入了民事訴訟的現行制度。【參見王亞新:《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頁。】歐陸法律傳統在近代以來的法律移植進程中不斷進入中國社會,但同時又不斷地遭受中國本土法律傳統的排斥和抵制。前述四種制度之間的沖突,也是歐陸的法律傳統與中國本土的法律傳統之間排斥反應的一個縮影。
三、證據收集制度的體系性變革
前述分析揭示了我國民事證據收集制度中所存在的兩種外部體系和兩種內部體系,由此可以解釋前述體系兼容性問題的生成原因。要徹底解決這種兼容性問題,必須妥善安排證據收集制度的內部體系和外部體系,通過推進體系化來實現法律的評價一致性和內在統一性。
(一)證據收集制度的體系選擇
在內部體系上,應當采司法主導原則而擯棄司法替代原則。首要原因在于司法替代原則所依賴的法律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正處于變革之中。歐陸法律傳統與中國法律傳統盡管在強調法官職權方面存在共性,但在核心問題上存在明顯差異。首先,就法官角色而言,前者法官的基本定位是中立的裁判者,依職權作出命令就是這種定位的具體體現,而后者的法官角色卻遠遠比裁判者更為豐富和多元。其次,就司法權的屬性而言,前者的司法權即裁判權,而后者中司法權和行政權的界限并不明晰。深入基層調查取證的做法其實更接近于行政權的運作方式【參見梁洪明:《馬錫五審判與中國革命》,載《政法論壇》2013年第6期,第147頁。】,它更像傳統中國的高級官員集行政司法大權為一體的包公式審判方式。【參見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頁。】但就司法權的性質而言,它本應該是對案件事實和法律的判斷權和裁決權,對此理論上幾無任何爭議。由此,我們需要摒棄司法權中不符合其本質屬性的行政權部分,使其回歸裁判權屬性。因此,要求法院替代當事人去調查取證的“替代原則”就無法維系。其次,采司法主導原則與民事訴訟法的宏觀體系更為契合。民事訴訟法的目的是公正且迅速地解決糾紛,由此有發現真實原則、訴訟經濟原則、程序安定等理念或原則以實現該目的。【參見[日]伊藤真:《民事訴訟法》(第4版補訂版),曹云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8頁。】而證據收集制度所采用的下位原則應當是上位原則的具體化【上位原則與下位原則之論述,參見[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學中的體系思維與體系概念:以德國私法為例》(第2版),陳大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46、55頁。】:司法主導原則強調法官/法院對于證據調查的主導性但并不要求法官身體力行去收集證據,較之司法替代原則具有更高的效率,由此與訴訟經濟原則相契合;司法主導原則要求法官基于真實義務而依職權調查證據,由此與真實發現原則相契合;司法主導原則下當事人僅可以依文書提出命令收集對方當事人及案外人所控制的證據,由此避免了司法替代原則下到底是當事人還是法院收集證據所引發的制度抵牾,從而可以與程序安定原則相契合;司法主導原則下原則上由當事人負責提出證據而在例外情形下由法院通過職權方式提出證據,也與修正辯論主義(提出原則)相契合。
質疑者可能會主張,解決證明困難問題是否還有其可能性。在應對證明困難問題上,比較法上除擴張法院權力外,還可反其道而行之擴張當事人權利。這種路徑在制度上的體現,就是以美國法為代表的證據開示(Discovery)程序,賦予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直接向對方當事人或者案外人收集證據的權利。鑒于這種制度充分賦能當事人而非法院,因此其內部體系可概括為“當事人主導原則”。但這種選擇對于我國而言幾乎不具有可操作性。從法律文化的角度來看,從“司法替代”直接跳到“當事人主導”明顯步子太大,改革風險過高。同時鑒于中國傳統文化中集體主義思想較為濃厚,“當事人主導”模式因其明顯的個人主義色彩也很難被我國法所接納。此外,從司法組織的角度來看,我國法院的組織形態更接近于達瑪什卡所界定的科層型而非協作型,這種組織形態下的司法程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官方程序的排外性,司法官員不在場的情形下進行的活動難以被整合到科層式程序中。【參見[美]米爾伊安·R.達瑪什卡:《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比較視野中的法律程序》(修訂版),鄭戈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頁。】由此當事人主導的證據開示也難以契合于我國司法組織形態。
而在外部體系上(也即具體規則層面),應基于司法主導原則而采“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模式。理由首先在于,基于“當事人收集/法院收集”的法官取證已經缺乏生存的司法土壤。隨著近年來法官員額制改革和立案登記制改革,法院普遍面臨案多人少的困境。由于法官取證特別耗費人力,無論是法官依申請取證還是法官依職權取證在司法實務中已經是少之又少,普通法官對此避之不及。可以說,法官取證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已幾乎名存實亡,“當事人收集/法院收集”模式已搖搖欲墜。其次,“當事人收集/法院收集”也無法滿足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要求。之前的研究早已指出,法官親自取證容易造成中立性的喪失,而且提前接觸證據也容易造成先入為主而喪失中立性。【參見李浩:《民事訴訟法學》(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頁。】再次,從司法實務的角度來看,源于“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模式的律師調查令制度的運作效果良好,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貿然改弦更張。
以司法主導原則和“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模式為基礎,我們可以重構證據收集的外部體系:以最能體現上述原則和模式的制度為中心而構建核心證據收集制度,并輔之以其他補充性制度。就前文所列的四種制度中,書證提出命令和律師調查令無疑是最能體現上述原則及模式的制度,所以理當成為證據收集制度的核心,但為避免制度的疊床架屋有必要考慮二者是否存在合并的可能。而同樣體現上述原則及模式的證據保全制度則僅在特殊情形下附帶性地實現證據收集功能,因此具有某種補充性。而法官調查取證制度則需要接受上述原則及模式改造,從而實現與書證提出命令或律師調查令的體系性協調。
(二)核心證據收集制度的完善
盡管書證提出命令更為“官方”,但律師調查令在多年的試行過程中已經被法官和律師們廣為接受,甚至在不少地方,書證提出命令因與律師調查令功能重疊而被束之高閣。【就筆者調研的情況來看,許多法院完全沒有啟動書證提出命令的相關實踐,甚至大量法官和律師對該制度幾乎一無所知。】盡管二者在制度內核上并無本質區別,但筆者傾向于選擇前者。原因首先在于,書證提出命令為司法解釋所明文規定的制度,選擇它不存在合法性疑慮。此外,書證提出命令本為德日等國的通行制度,且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已相當成熟和完善,在理論基礎和制度合理性等方面存在天然優勢,同時也便于我國法院系統處理國際司法協助等涉外問題。當然,鑒于二者的相似性,最終的解決方案應當是合二為一,通過擴張的書證提出命令來實現對律師調查令的功能替代。
現行書證提出命令明顯過“小”,無法恰當實現破解證據偏在的功能,應予以擴張。學界提出的擴張路徑包括:將申請主體擴張至反證方,被申請主體擴張至第三人;在時間要件上準用舉證期限的寬緩規定;在客體范圍上擴張至實物證據種類。【參見曹建軍:《論書證提出命令的制度擴張與要件重構》,載《當代法學》2021年第1期,第128頁。】上述觀點無疑是中允的,但不足之處在于將目光局限于純粹的制度比較而忽視了制度之間的體系問題。如果要在體系上徹底替代法官調查取證制度和律師調查令制度,那么必須在上述改進的基礎上,擯棄所謂的“超限定主義”,對書證提出命令制度作進一步擴張。這種擴張首先是書證提出義務的一般化。有學者對此持反對意見,理由在于我國尚處于從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訴訟體制的轉型過程中。【參見張衛平:《當事人文書提出義務的制度建構》,載《法學家》2017年第3期,第33頁。】這種主張的深層次考慮是避免證據制度向超職權主義復辟的風險。另有學者提出,一般化的書證提出義務可能損害書證控制人的秘密保護利益,我國法上缺乏秘密保護條款也阻礙了一般化義務的實施。【參見曹建軍:《論書證提出命令的制度擴張與要件重構》,載《當代法學》2021年第1期,第35頁。】筆者認為,從解釋學的角度考察,2020《證據規定》第47條第5款的文義已充分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對于一般化書證提出義務的認可。而從體系的視角考察,承認一般化的書證提出義務也是必然選擇。因為如采用“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模式,那么法官調查取證制度的功能就需要由書證提出命令及其他制度予以實現。只有一般化書證提出義務配合相應的書證提出命令,方可實現對于法官調查取證制度的完全替代。這種替代也不至于引發職權主義復辟,因為法官調查取證制度才是超職權主義的最為典型的體現形式,廢除法官調查取證可以大大減弱我國法上的職權主義色彩。至于秘密保護的問題,完全可以在制度修訂時予以補充。當然,這種一般化書證提出義務可能會引發濫提書證提出申請、濫用摸索證明的風險,對此可考慮通過當事人的具體化義務、真實義務及誠信原則等制度予以限制。【參見姜世明:《舉證責任與真實義務》,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232頁。】此外,這種擴張還應當體現在賦予法官職權命令提出書證的權力,從而在當事人怠于提出申請時也可依職權取得相應的書證從而發現案件真相。最后,這種擴張還需考慮增設書證的交付委托這一書證提出命令的衍生制度。這種制度主要針對法院不適合直接作出命令的案外人,例如國家公務機關等公法人。上述案外人基于公法上的協助義務而向法院交付相應的文書。【參見[日]高橋宏志:《重點講義民事訴訟法》,張衛平、許可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頁。】交付委托制度在整體上可以準用書證提出命令的程序,僅僅在相對人不遵從法院要求時的處罰問題上有所差別。【在相對人對法院的委托不予理睬時,日本民訴法也未設置處罰程序,同上注。這種情形可以考慮通過《公務員法》等公法設置相應的制裁措施。】為避免制度過于復雜化,我們無需像日本法一樣單獨設置勘驗物(物證)的交付委托程序,而可以將書證的交付委托直接擴展適用到準文書(視聽資料、電子數據)以及物證。
(三)補充性證據收集制度的革新
證據保全制度在證據收集制度中居于補充性地位。證據保全在學理上被認為是預先進行的證據調查程序(即法官通過調查證據方法來獲取證據資料的程序),通過保全程序獲得的證據資料可直接成為法官心證的來源。【參見段文波、李凌:《證據保全的性質重識與功能再造》,載《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第81頁。】而證據調查程序本身包括了證據的提出(當事人或者法官提出)、命令證據調查和實施證據調查這三個程序環節,在第一個環節中當事人對自己未掌控的證據提出申請(例如通過書證提出命令)的行為就屬于本文所謂的證據收集。盡管證據保全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于證據收集,但它在某些場景下又天然實現了證據收集功能,因此在證據收集制度的整體框架中依然需要加以考慮。即便不考慮促進審理集中化、多樣化糾紛解決等功能,我國現行證據保全制度在實現證據收集功能的層面上也存在嚴重不足,對此需要進一步完善。
這種完善首先體現在司法主導原則及“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模式的貫徹。由此,在證據保全程序中,依然是由當事人提出證據申請而法院發布相關的命令要求證據源提出證據,從而解決證據偏在問題。其次,是程序規則層面的完善。現行的證據保全缺乏必要的程序規則,導致證據收集過程中的程序保障嚴重不足,司法實務中申請人所提出的申請往往直接被法院無視(因為沒有救濟程序),而且保全過程中案外人的程序權利往往也被忽視(因為沒有法律保障的在場權)。為解決上述問題,2012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3款確立了“證據保全參照財產保全”的規則,但這種思路可謂是誤入歧途。【參見占善剛:《證據保全程序參照適用保全程序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3款檢討》,載《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對此,必須從“證據保全本屬預先進行的證據調查程序”這一基本程序原理出發,維持證據保全中兩造對立的形態,從聽審權和在場權兩方面保障當事人的程序參與。【參見段文波、李凌:《證據保全的性質重識與功能再造》,載《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第87頁。】最后,證據保全需要增設“確定事物現狀”的保全類型,從而能更好地實現證據收集功能。這種類型的保全不以證據可能滅失為前提,而且其針對的對象主要是事實問題(例如人或者事物的損害現狀),似乎與證據收集無關。但這種保全中依然會涉及到勘驗物(物證)和鑒定人等證據方法問題,在我國法的語境下則涉及到勘驗筆錄和鑒定人意見的證據收集。例如,因樓上漏水導致房屋的損害現狀需要通過勘驗來確定損害的存在,因交通事故引發的人身傷殘需要通過鑒定來確定傷殘等級。【上述問題在司法實務中往往通過公證證據保全和私鑒定來解決,但公證證據保全因為缺乏對方當事人在證據調查過程中的參與而在程序保障上存在嚴重缺陷,私鑒定則往往因為鑒定人和當事人的暗箱操作而引發公正性危機,而且在證據資格問題上也屢屢引發質疑。】
在證據保全之外,還需要對法官調查收集證據制度予以體系化改造,使其在內部體系上契合于司法主導原則,在外部體系上契合于“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模式。這種改造后的法官調查取證制度,可以作為兜底性的證據收集制度,從而彌補前述書證提出命令和證據保全制度所可能存在的漏洞。由此,首先應當取消法院職權調查取證權。【參見袁中華:《論民事訴訟中的法官調查取證權》,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5期,第199頁。】就內部體系而言,調查取證權更為契合于我國傳統的“超職權主義”原則和司法替代原則,而難以被整合到本文所倡導的司法主導原則之下。其次,在具體制度設計上,我們不僅要增設法官命令提出書證的權力,職權命令提出物證及職權啟動鑒定也應該在《民事訴訟法》修法時予以考慮。在比較法上,解決證明困難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在缺乏當事人提出證據申請的情形下賦予法官職權提出證據的權力。職權提出證據不僅包括職權命令提出書證或者勘驗物(物證),也包括職權啟動鑒定或者詢問當事人。【參見[德]漢斯-約阿希姆·穆澤拉克:《德國民事訴訟法基礎教程》,周翠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264頁。】在德國法上,法官一般會通過釋明而建議當事人提出證據申請,只有在確有必要時才選擇職權證據調查。盡管這種權力在實際運作中出現幾率不高,但作為破解證明困難和保障實體真實的重要手段,在規范的層面上卻很有必要予以保障。
由此,就證據收集制度外部體系(規則體系),我們以“當事人收集/法院指揮”模式作為規則的組織方式或內部秩序,從而統合書證提出命令、證據保全以及法官職權提出證據這三者。而就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則以證據調查階段的書證提出命令為核心的證據收集方法,同時在提前的證據調查也即證據保全階段同樣適用該方法,而作為兜底的補充方法則是法官職權提出證據。在三者的適用問題上,則應課以不同前提性要件:書證提出命令原則上以證據偏在為前提;證據保全以緊急性(證據的毀損滅失)為前提;法官職權提出證據則以可能有悖于真實義務為前提,是前二者均無法達到目標時才需要考慮的方法。由此,三種制度根據不同的構成要件確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避免了制度之間的沖突或漏洞,進而致力于實現規則整體的無矛盾性和完整性。【卡納里斯認為,無矛盾性和完整性是不可能完全達到的目標。參見[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學中的體系思維與體系概念:以德國私法為例》(第2版),陳大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22頁。但作為法律所追求目標而言,這二者是適合的。】
就證據收集制度的內部體系,我們可形成如下認識:第一個層次是正義、安定和合目的性這幾個基本的法理念;第二個層次則是貫徹法理念的民事訴訟法原則,大體包括修正辯論主義、訴訟經濟原則、訴訟安定原則等;第三個層次是證據收集領域的下位原則,主要是司法主導原則;第四個層次則是貫徹上述原則的具體法規則,具體包括書證提出命令規則以及對它形成補充的證據保全規則和法官職權提出證據規則,上述規則均以“當事人收集/法官指揮”模式構建。由此,證據收集的相關規則群可以回溯到那些少數支撐性的基本原則甚至是更上位的法理念,避免了“秩序……分裂為一堆毫無關聯的具體問題”【參見[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法學中的體系思維與體系概念:以德國私法為例》(第2版),陳大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5頁。】(也即所謂“碎片化”),從而實現了其自身的體系化。
結語
體系化是法教義學的永恒追求——盡管完全的體系化是不可能的。但正如拉倫茨所言,“一項理想不能完全實現不是反對盡可能接近此理想的努力之理由”。【[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6版),黃家鎮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569頁。】當民事訴訟法的規則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復雜,那么體系化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民事訴訟法的體系化,是指將民事訴訟法的各種概念、規則、原則等法律素材聯結為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和統一性的整體的過程。體系化的民事訴訟法學方可為法學教育、法學研究以及法學實務提供簡明而確定的知識框架,從而為法律人在找法、解釋和論證等方面的工作減負。本文所論及的民事證據收集制度的體系化,也僅是民事訴訟法體系化的一個斷面。而作為整體的民事訴訟法體系化,則需要我們對民事訴訟法的基本概念和規則予以全面的辨析與整理,對民事訴訟法的基本理念、普遍性原則及其下位原則予以更加深入的分析、提煉與總結。ML
Refbe85b5a78ed4fd29414f6dcdbf2e862f882a2ef2c117d990858ead08da872a8election on the System of Evidence Collection in Civil Procedure Law
YUAN Zhonghua
(Law School,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430073,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system for collecting evidence in civil law includes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document production orders,civil investigation orders,judicial investigations,judge evidence collection,and evidence preservation,which has led to confusion due to overlapping mechanisms.This confusion stems from two primary sources:legal technology and legal culture.The document production order and its variant,the civil investigation order,follow the“party collection/judge control”model typical of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s,while judicial investigation,judge evidence collection,and evidence preservation adopt the“party collection/judge collection”model.Both are holistic solutions to the evidence collection system,operating in afunctionally similar but mutually exclusive manner.They are also underpinned by different legal cultures—the“judicial priority”model and the“judicial substitution”model—which do not share common features.Therefore,the“judicial substitution”model should be adopted along with the“party collection/judge control”model,and areconstructed evidence collection system should include expanding document production orders,enhancing the evidence preservation system,and instituting asystem for judges to order evidence collection.
Key words:evidence collection;document production orders;systematic
本文責任編輯:段文波